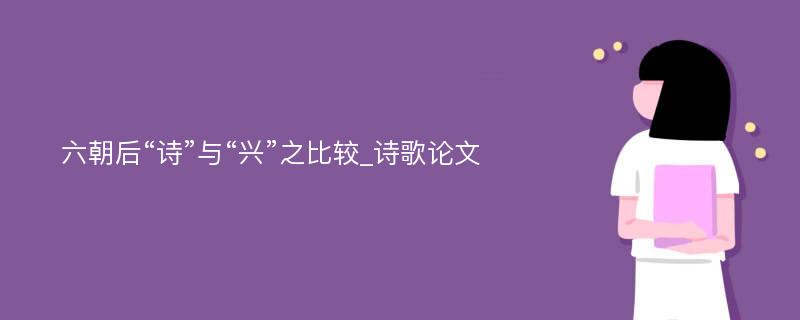
《诗》“兴”与六朝后诗歌“兴”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 (2001)02-0079-06
关于诗歌的“兴”的界说,朱自清先生早已有“你说你的,我说我的,越说越糊涂”[1](P235)的感叹。诗歌“兴”界说的缠夹, 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兴”是一个历史性的范畴。随着历史的演进,诗歌创作艺术的进展和文学思潮的变迁,人们对于每一发展阶段的诗歌“兴”的看法,自然也就难免不同。中国诗歌“兴”艺术的发展,从大处看,以六朝为界,分野显然。
一
汉字“兴”字的本义就是“起”的意思。《尔雅》、《说文》均训“兴”为“起”,例如许慎《说文解字》说舆字“从舁,从同,同力也。”刘勰《文心雕龙·比兴》则这样界定:“兴者,起也。”孔颖达《毛诗正义》也说:“兴者,起也。”当然,他们的“起”不是指会四手同力共举而起,而是指人心之感于物而引发某种思想感情的意思。后来,朱熹在《诗集传》中下的定义更为深入浅出:
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引起”云者,即指人心之感于物而引发某种思想感情。
那么,为什么“先言他物”能“引起所咏之辞”呢?从《诗经》的兴体诗来看,“先言他物”之所以能“引起所咏”,是因为“物”能引发主体的联想:联想的桥梁沟通了物与我。柏拉图、亚里斯多德曾提出联想的三定律:相似律、对比律和接近律。休谟又提出联想的三个条件:相似、时地相接、因果关系(其中“相似”还包括“对比”)。《诗经》第一首《关雎》就是通过雎鸠鸟的雌雄求偶鸣叫,以引起人类男女求爱的联想。这是相似联想。《周南·汝坟》:“遵彼汝坟,伐其条枚。未见君子,惄如调饥。”诗中的女主人公到汝水堤岸边时,不由地想起自己那远去的丈夫,内心无限痛苦。“在上古时代,开春时节,男女青年往往在水边举行盛会,选择配偶。”[2](P26)女主人公走到爱情策源地——“汝坟”而想起丈夫引发愁情,这是接近联想。《小雅·苕之华》:“苕之华,芸其黄矣。心之忧矣,维其伤矣。”诗由黄光灿灿、绿叶青青的凌霄花,联想到自己命运的悲苦。物与人形成极大的反差,这是对比联想。《邺风·绿衣》:“绿兮衣兮,绿衣黄里。心之忧兮,曷维其已!”一位丧偶的男子穿上妻子生前给他缝制的衣裳,睹物思人,哀伤不已,这是关系联想。《诗经》中的一些兴体诗,它的起兴还有的是基于习惯性联想。习惯性联想是在原始宗教产生以后,在长期的原始宗教生活中所培植起来的以一定的观念为基础的联想。在原始宗教活动中,客观物象与想象的观念内容之间,在人们的心理上由于成千上万次的不断重复而逐渐被强化和巩固,终于建立起牢固的联系,而形成了以习惯性的条件反射为特征的联想。[3](P69)例如,在鸟图腾部族那里,人们见到鸟便会联想到自己的祖先;从渔猎时代开始,人们见到鱼便会联想到繁衍,从而又联想到性爱和婚媾。荣格分析心理学认为,我们人类祖先曾有过许多不断反复的精神事件,这些精神事件所凝结的心理体验,世代相继沿传,以大脑解剖学上的结构保留在人们的头脑中。习惯性联想也可以看成是由于原型呈现而引起的联想,《召南·野有死麇》:“野有死麇,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一般解释这首诗认为吉士以白茅草包裹死鹿以赠女子来引诱她。但“野有死麇”怎么会忽然兴起“有女怀春”呢?其实“白茅是新月是女性,死麇指下山的太阳、指男性。因此这首诗翻译过来就是:野外新月,搂抱沉阳。吉士引诱,怀春女郎。”[4](P17)这样,“野有死麇,白茅包之”这一原型的呈现,由于习惯联想,自然便能由这“先言”的“他物”——“野有死麇,白茅包之”,而兴起“所咏之辞”——“有女怀春,吉士诱之”了。此外,《诗经》中以雨兴起男女欢爱,以“山”和“隰”(即“山有……隰有……”的固定格式)兴起男女爱情,以狐狸兴起两性之爱等等,都是由原型呈现而引起的习惯性联想。甚至谐音——“诗谣上与本意没有干系的趁声”[5](P702),其本质也在于联想。 例如《小雅·鹿鸣》:“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诗的开头以“呦呦鹿鸣”起兴,借“鹿”与“禄”谐音,“呦呦”与“悠悠”同声,以引起福禄长久的联想,这不妨叫它谐音联想。综上所述,可知《诗》“兴”的本质是“起”——引起联想。汉代学者早有“兴者喻”之说,《诗经》毛传、郑笺中都认为“兴者喻”;汉儒孔安国释“兴”为“引譬连类”,同样是把“兴”看作比喻。他们固然接触到了“兴”的联想这一本质,但只把“兴”囿于相似联想,仍是“瞎子摸象”。
六朝后的诗歌,其“兴”的本质在“感”。诗论家均以“感”说“兴”,如西晋执虞《文章流别论》说:
赋者,敷陈之称也。比者,喻类之言也。兴者,有感之辞也。署名唐贾岛《二南密旨》云:
感物曰兴,兴者,情也,谓外感于物,内动于情,情不可遏,故曰兴。宋儒范处义《诗补传》亦云:
铺陈其事者,赋也。取物为况者,比也。因感而兴者,兴也。清方东树《昭昧詹言》说:
诗重比兴:比但以物相比;兴则因物感触,言在于此而义寄于彼……
由以上引文可以看出,六朝以后人们心目中的“兴”,实质上是一种心物关系,即主观意识与客观物体的关系,亦即情景关系。“兴”的本质是心物交感;“外感于物,内动于情”,便是“兴”。
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的一种态度。情感总是由一定的客观事物引起的。离开了客观事物,无缘无故的情感是没有的。徐复观先生说:“兴是自己内蕴的感情,偶然与自然景物相触发,因而把内蕴的感情引发出来。”[6](P197)因此,如果只孤立地讲“兴者情也”是不对的。 “兴者情也”的“情”是“外感于物,内动于情”的“情”,它是心物交感的结果。这样,“感”成了关键。感物兴情,或者说感物起兴,“兴”,一定是感物而来。因此,从魏晋南北朝开始,人们对“兴”义做了新的理解和新的规定:“有感”才有“兴”,“有感”才是“兴”。至于钟嵘《诗品·序》所说的“文已尽而意有馀,兴也”,笔者认为这不是给“兴”下定义,而是指出“兴”因心物相融所产生的审美效果。这就是黄宗羲《汪扶晨诗序》中说的,“兴”是“景物相感,以彼言此”,亦即方东树《昭昧詹言》中说的“兴则因物感触,言在于此而义寄于彼”,因而所产生的审美效果。
徐复观先生说的,“兴”是主体“与自然景物相触发,因而把内蕴的感情引发出来”,这是否等于说“兴者起也”呢?诚然,六朝以后人们以“兴”为“感”,“感”确实也包含有“起”的含义,例如说“自然景物”“把内蕴的感情引发出来”也可以说是感物“起”情。“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这不是感物“起”情吗?那么,《诗》“兴”的“起”与六朝以后诗“兴”的“感”区别何在呢?
“感”固然也有感发而引起的“起”之含义,但“感”强调“感于物”。“物”包括自然景物与社会事物。因此,“感”是诗人处身于特定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中受到感发,滋生激情和灵感,是读者沉醉于诗歌境界而运用情感想象、联想诸多心理因素去感受和体味,产生强烈的交感和共鸣。“感”,一是自然环境的感发,二是社会环境的感发。《文心雕龙·物色》云:“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感发的关系。然而,“社会事物与自然景物虽然都可以‘摇荡性情’,但只有社会事物才是形成人的性情、心灵的根源,自然景物不过是激发和触动人的性情、心灵由潜而显、由伏而起的条件。”[7](P127)诗人身处特定的社会环境, 感时、感事、感遇,兴发种种历史感、命运感、苍茫感、流逝感……写下了许多“有感”之作,“有感”是文艺创作的动因。宋代诗人杨万里说:“我初无意于作是诗,而是物、是事适然触乎我,我之意亦适然感乎是物、是事。触先焉,感随焉,而是书出焉。”物指自然景物,“事”指社会事物。这里诗人“感于物”的“物”,是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多维整合。“感”不仅见诸创作,亦见诸鉴赏。孔子说,“兴于《诗》”,即指《诗经》中的作品能够感发读者,激起欣赏者的情感,唤起他们联想、想象、思维等心理活动。由上所述,可知“感”是指主体对处身于其中的特定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感受、体味而引发内心复杂之情意。
而《诗》“兴”的“起”,固然也有“感发”之义,但它主要是“起情”,作为眼前激发的诱因机缘。“起”,引起联想也。从前文的论述,已知《诗经》兴体诗的起兴是通过相似联想、接近联想、对比联想、关系联想、习惯性联想和“趁声”谐音联想。《诗经》兴体诗中,采取相似联想的最多。人类思想从产生时就习惯于从自然物象感发和联想某种相应的观念。先秦人仍喜欢采用这种思维方式。一般不作纯粹的抽象思辨,而往往‘立象尽意’,以具体直观的形象譬陈、暗示、论证某种理念和思想”,萧华荣先生称之为“抽象思维”。[8](P21)《周易》就充分表现了这种取象思维的特点。涂元济先生曾将《周易》中的卦爻辞与《诗经》兴体诗比较指出:“卦爻辞(其中有部分即歌谣)的结构模式与兴体诗的结构模式一致”,同象辞与告辞一样,“兴辞与中心辞之间也是以原始思维的互渗律联结起来的,其功能同样是起着象征的作用。”[9]《诗经》兴体诗也有“取象思维”的特点, 朱熹谓之“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诗》“兴”的本质是“起”,即“引起”,用于发端,是一种艺术的思维方式,一种艺术表现手段,或者说一种艺术表现方法。这种艺术思维方式、艺术表现方法的反复运用,终于凝练为“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这样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而六朝后诗歌的“兴”,其本质是“感”,主要体现为情景关系:主体内心情意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酝酿、感发而生成的。
二
作为美学范畴的“兴”,都是心物关系,亦即情景关系。《诗经》兴体诗与六朝后诗歌的“兴”,都是借“物”起兴,感物兴情,但前者“物”较单一,后者“物”较复杂。其“单一”与“复杂”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诗经》兴体诗的“物”都是自然景物,六朝后诗歌的“兴”,其“物”包括自然景物与社会景物。钟嵘《诗品·序》中就把“物”大致分为两类:“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又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娥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这里“感人”之物有两类:“春风春鸟”云云,属于自然景物;“嘉会”、“离群”以下,属于社会事物。例如王粲的《七哀诗三首》是通过“荆蛮非我乡”之自然景物描写,以引起他乡愁的抒发。傍晚,诗人乘船沿长江逆流而上,只见“山冈有馀映,岩阿增重阴。狐狸驰赴穴,飞鸟翔故林。流波激清响,猴猿临岸吟。迅风拂裳袂,白露沾衣襟。”陈祚明说:“‘山冈’数句极写非我乡。”诗人这里的自然景物描写似乎只是眼前即景,但正是这眼前的“非我乡”景色勾起了他的乡愁“羁旅无终极,忧思壮难任”。而阮籍的《咏怀八十二首》抒写他“忧思独伤心”的心境。从表面上看诗人孤独、失望、愁闷和痛苦的心情似乎是由他“夜中不能寐”看到的自然景色“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所引起,实际上阮籍的“忧思”主要感发自当时他所处的政治环境。南朝宋颜之说:“阮籍在晋,常虑祸患,故发此咏耳。”李善说:“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在那魏晋之际的黑暗时代,诗人忧谗畏祸,虽然在作品中未曾实写这种社会环境,但读者感受得到。在读者的欣赏“再创造”中,我们正是通过这首诗对自然环境的实写和社会环境的虚写,才感悟到阮籍那“忧思独伤心”的襟怀的。唐宋以后的许多诗都是通过自然景物和社会事物的描写来抒发作者的内心情感的。例如杜甫的《白帝》:“白帝城中云出门,白帝城下雨翻盆。高江急峡雷霆斗,翠木苍藤日月昏。”是自然景物描写;“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哀哀寡妇诛求尽,恸哭秋原何处村?”是社会事物描写。诗人以此感发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总之,六朝后诗歌的“兴”,其“感物兴情”的“物”,比《诗经》兴体诗“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的“物”要复杂得多。
2.《诗经》兴体诗的“物”只是单一的“物”,简单的意象,是从某一角度作“比”;而六朝后的诗歌,“感物兴情”的“物”大都是“景”,是完整的艺术形象,往往从全方位进行象征。
朱自清先生在《诗言志辨·比兴》中说:“《毛传》‘兴也’的‘兴’有两个意义,一是发端,一是比喻;这两个意义合在一块儿才是‘兴’。”这里的“发端”当指起兴,即朱熹“先言他物以引起”的“引起”之义。“先言他物”之所以能“发端”,能“引起所咏之辞”,是因为《诗经》兴体诗的“物”大都是喻体,具有比喻的意义,能引起相似联想。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篇》中说:“盖事物一而已,然非止一性一能,遂不限于一功一效,敢譬者用心或别,着眼因殊。”比喻总是单从某个角度比,从事物的某一性能、某一功效比。因此,《诗经》兴体诗的“物”只要单一的物,而不必是“景”。钱先生说:“窃谓《三百篇》有‘物色’而无景色,涉笔所及,止乎一草、一木、一水、一石,即侔色揣称,亦无以过《九章·桔颂》之‘绿叶素荣,曾枝剡棘,圆果抟兮,青黄杂糅。’《楚辞》始解以数物合布局面,类画家所谓结构、位置者,更上一关,由状物进而写景。”[10](P613)钱先生即指出《诗经》中还只是“一草、一木、一水、一石”的单一的“物”,不是“数物合布局面”的“景”。《诗经》“兴者喻”的“喻”是以单一的“物”从某一角度作“比”。例如《周南·螽斯》即是从螽蝗很会繁衍这个角度比喻,以引起人类子孙众多的联想。六朝后的诗,“物”逐渐发展为“景”。它以“数物合布局面”而讲“结构、位置”,以完整的艺术形象,全方位地进行象征。例如曹操《步出夏门行》中描写了水波、山岛、树木、百草、秋风、洪波这个完整的大海形象,象征了诗人叱咤风云的豪迈气概和吞吐宇宙的阔大胸怀,这里既是盖世英雄“气韵沉雄”的隐喻,也是大度政治家怜才爱贤的情意暗示。
综上所述,可知《诗经》兴体诗“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的“物”,只是类型化的形象,旨在引发相似联想或其他的联想效应。而六朝后的诗歌,其“感物兴情”的“物”,逐渐发展为“境”——成为诗中所抒发的思想情感借以酝酿、生发的具体环境。“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11](P103)它由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构成,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多样性统一”的“典型环境”。这个“典型环境”既能感发抒情主人公内心深处那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情感、玄思,也能唤起读者类似于抒情主人公的那种微妙超绝的精神感兴。借皎然的话,这叫做“诗情缘境发”。情感是由“物”引起还是在“境”中感发,这是《诗》“兴”与六朝后诗歌“兴”的一个明显区别。
三
《诗经》兴体诗中情与景大都只是局部交融,六朝以后诗歌的“兴”,其情与景渐趋“融彻”。
首先我们要说明的是,什么是情景交融。一般认为,情景交融是指诗文中情与景契合达到水乳交融、浑然一体的艺术境界。它要求作者主观情志和所描写的客观景物相契合:我情投射于外物,渗透外物;外物反射我情,寓示我情,从而达到情以物观、物以情存的境地。情与景怎样才是交融的呢?情景交融是心物交感的结果,“感物”是前提。《礼记·乐记》早已有言:“乐者,言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刘勰也有“睹物兴情”之说,并进而提出情景关系必须是“情以物兴”、“物以情观”。其《文心雕龙·物色》篇又具体指出诗人感物是“目既往还,心亦吐纳”,“既随物以宛转,亦与心而徘徊”。刘勰虽然还没有用后代的“情景交融”这个术语,但其意已很明显了。王夫之的情景说有集前人大成之妙。用他的话来说,所谓情景交融是指诗歌情景的这种关系:“景生情,情生景,哀乐之融,荣悴之迎,互藏其宅。”一方面,客体“景”在主体内心唤起了某种“情”,这就叫“景生情”;另一方面,主体的情感又作用于客体,“景”成了主体“情”的对象化,成为具有人的情感的东西。这也就是宗白华先生说的:“景中全是情,情具象而为景。”[12](P212)格式塔心理学理论认为,艺术作品中的景之所以能经由知觉而唤起主体的情,是因为这情与景异质同构的缘故。情与景质虽不同,但它们所形成的“力的式样”是相似吻合的,因而能交融,构成新体。简而言之,情景交融是由于心物关系的同构性。
作为美学范畴的“兴”,无论是《诗经》兴体诗的“兴”抑或六朝后诗歌的“兴”,其本质都是物对心的感发和心与物相互契合,但是两者情景交融的情况毕竟有所不同:前者,其景大都只是与诗中部分的情契合;后者情与景渐趋“融彻”。《诗经》兴体诗的“兴”,其本质是“起”,为了引起所咏,用于发端。例如《关雎》,诗中所表现的思想感情可分为三层:(1)男子春心躁动,思向窈窕淑女求爱;(2 )男子思淑女而不可得的苦闷;(3 )男子一相情愿地想象着如何吹吹打打热热闹闹地把淑女娶回家,美满幸福地过日子。诗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起兴,旨在通过自然界鸟儿和鸣求偶,联想人类社会男子向淑女的求爱。作为起兴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两句诗虽写的是自然景物,但其实并不一定是为诗中的中心部分即“所咏之辞”所抒发的思想感情构成具体环境,也不是为它作直接的气氛渲染,而主要是为了使“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引起“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联想。但“窈窕淑女”两句只是整首诗所要表现的思想感情的第一层含意。诗中的景与诗的第一层情固然具有同构性,情与景是交融的,但诗的第二层“寤寐求之”、“辗转反侧”的情意却不是由“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相似联想(相似律)引起的,而是由“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关系联想(因果律)所引起的。至于诗的第三层“琴瑟友之”、“钟鼓乐之”的情意,则是由第二层作推理联想,推想(幻想)自己与“窈窕淑女”的美满结局。也就是说,诗的第二层、第三层的情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这个景不具有同构性,可见其情景交融只是局部的。六朝后的诗,由于“感物兴情”的“物”已逐渐发展为“境”(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它的“情”是由整体“境”感发出来的,所以整首诗“情”与“境”具有同构性,达到“境”对心的自然感发和情与“境”全然契合的境界,其情景交融是整体性的,例如马致远的《天净沙》: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这首小令抒写的是一个飘泊天涯的游子思家而不得归的复杂、深厚的情感。这个情感是由同一画面中的几组景物感发出来的:第一组,“枯藤老树昏鸦”。先通过“枯”、“老”、“昏”这种意象,在情调、色彩上引起人朦胧、渺茫、暗淡的感觉。乌鸦归巢,在黄昏中飞回老树,这种景物自然会兴起天涯流浪者无家可归、不知何处是归宿的思想感情。第二组,“小桥流水人家”。这里团聚在“小桥流水”旁边的“人家”,他们平和、宁静、温暖、幸福的生活,更能反兴起天涯游子飘泊、不幸的凄凉愁绪。第三组,“古道西风瘦马”。它又通过“古”、“西”、“瘦”这种意象,给人以迟暮、凄凉、低沉的感觉。荒凉的古道上、萧瑟的西风中,骑着一匹瘦马无所归止地踽踽独行的天涯飘泊者形象,不能不令人兴发旅途疲乏辛苦和流浪生活艰难困窘的哀怨之情。整首诗所表现的思想情感,不是单独由哪一组景物所引起,而是由这三组景物所组成的整一画面——天涯游子身处于其中的环境景物而感发出来,是心感物所生的审美体验、审美感受。
从以上例证可以看出,《诗经》兴体诗的“兴”,它所体现的情景关系还只是比较单一的心物关系。它的“物”(自然景、物)主要是作为触发情感的媒介。它的以“物”起“情”,主要是通过联想(尤其是相似联想)架起的桥梁来沟通的。而六朝后的诗歌,它所体现的情景关系,是抒发主人公内心情感与他身处于其中的环境(包括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关系。所谓“感物兴情”,主要体现在整一的“境”(环境形象)激发主体联想、想象和情感体验而使人的生命本质力量获得对象化上。“境”成为审美主体特定情感和独特感受借以酝酿、感发和产生的环境渊源。
《诗经》兴体诗的“兴”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他物”与“所咏之辞”前后并列,同时出现,两者之间大都是象征、比附的关系。由于这种心物关系及其所特有的形式,所以兴体诗的情意相对较显。而六朝后的诗,其“感物兴情”的“物”逐渐发展嬗变为“境”。“感物兴情”体现为主体处身于境,身同感受,在联想、想象和情感体验中去感发某种情感而获得的一种“格式塔质”,所以六朝后的诗歌其情意相对较隐。诗人只是通过人物、景物、场面、社会背景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实写和虚写,“形成一种气氛,一种环境,一种只唤起某种感受但并不将之说明的境界”[13](P40),言在于此而意寄于彼, 因而读者往往感到蕴藉含蓄,言有尽而意无穷,有时甚至觉得它有点飘忽朦胧,仿佛镜花水月,归趣难求。
综上所述,《诗》“兴”若从“起”的特征看,它属于艺术思维方法;而从情景关系看,它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这样一种借物起情的“有意味的形式”。六朝后的诗歌的“兴”,从“感”的特征看,它是心与物适然相会而产生心理感受这样一种审美形态,而从情景关系看,它其实就是传统所谓“意境”的一种。中国古代文论中“意境”、“兴”等术语(概念、范畴)“在使用中常常互相渗透、互相消融乃至互相借代,到后来实质已成为虽各有侧重但在许多层次上大同小异的东西。”[14](P180)。
收稿日期:2000-1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