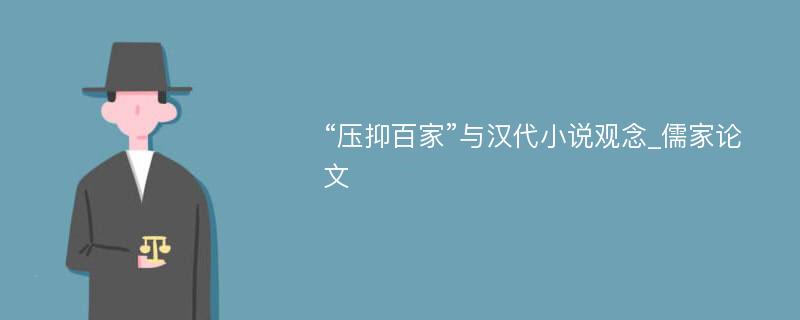
“抑黜百家”与汉代小说观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代论文,百家论文,观念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33X(2016)04-0165-05 在先秦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中,各家出于推崇自己学说的立场,往往会将其他家的思想斥为“小说”、“小家珍说”[1]。但这种小说观念随着学术思想界的发展,也在不断地变化。 随着汉帝国大一统政权的确立,思想界也迫切要求统一。早在建元元年冬十月,当时的丞相、武帝的老师卫绾就提出:“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汉书·武帝纪》)卫绾指斥法家、纵横家的思想影响了国家政权,已经暗含有尊崇儒家思想、抑制其他各家思想的倾向。而从武帝的一系列举措来看,他显然是有意于儒家的:建元元年夏四月,推行励孝政策,建元元年秋七月“议立明堂”,“遣使者安车蒲轮、束帛加璧,征鲁申公”;重用的窦婴、田蚡“俱好儒术”。尤其是建元五年置“五经博士”,使儒家所尊奉的经书变为全社会所信奉的经典,这对儒学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元光元年五月,汉武帝诏贤良对策,“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2]2523这一观点,符合当时思想界要求统一的趋势,也迎合了汉武帝对儒家思想的推崇,是从儒家学者立场上阐述的“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将“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视为全天下所要遵从的统纪与法度,而将其他诸子视作“邪僻之说”,要“皆绝其道”,使其“灭息”。这里的“邪僻之说”是和荀子、孟子的“异说”、“奸说”、“邪说”相近的表述,均是儒家学者对其他学派的指称。所以,随着思想界统一于儒学的风气之形成,儒家之外的诸子就成了特定时期内所谓的“小说”。 一、推隆儒术影响下的宗经、征圣思潮 在“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汉书·武帝纪赞》)的影响下,“宗经”和“征圣”成了主要的社会思潮,对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深远影响。“汉武帝推隆儒术,使儒学的经典教义成为判断人们言行正确与否的最高标准。汉初,大臣奏对与皇帝诏令,都很少征引儒学经典。武帝以后,几乎所有的奏书、诏令皆征引经典,以为根据。……在法律条文缺疏的情况下,经义就成为决疑断案、处理非常之事的准绳。……诚如皮锡瑞所言,汉崇经术,实能见之施行,所谓以《春秋》折狱,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诗》三百篇当谏书。这说明汉武帝独尊儒术后,许多重大活动都必须在儒学的名义下,才合理合法,才能为人们接受。”[3] 在《史记》中,如在《五帝本纪》中有:“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4]46在这段话中,司马迁阐述了当时关于黄帝传说的几个来源:儒家之外的百家所言之黄帝传说,非典雅之训。《五帝德》和《帝系姓》因为是载于《大戴礼记》和《孔子家语》,非儒家之正经,故而当时的儒家学者多不传学;在各地所收集的黄帝传说,包括《春秋》、《国语》中的相关记载,都和《大戴礼记》、《孔子家语》中所记孔子之说相近,故被认为可信。可见,儒学的独尊地位导致了对其他诸子的贬低,所以百家所言之黄帝,皆是不雅之训。因为对儒家五经的尊崇,故儒生往往不重视五经之外的著作;对孔子话语非常重视,虽不见载于五经,但因为是圣人之言,也可信赖。在《史记·伯夷列传》中,司马迁将其宗经的态度说得更为明确:“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尧将逊位,让于虞舜,舜禹之间,岳牧咸荐,乃试之于位,典职数十年,功用既兴,然后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而说者曰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耻之逃隐。及夏之时,有卞随、务光者。此何以称焉?”[4]2121这段话说出了司马迁在判断史料真实性和取舍史料的标准:“考信于《六艺》”,即便一个学者书读得再多、学识再丰厚,也只能依据《六经》来判断材料的可信性;即使《六经》如《诗经》和《尚书》是残缺不全的,仍然要信任和依靠它们。这也是宗经思想的表现。而此处的“说者曰”,讲的是尧将天下禅让给许由之事以及卞随、务光事。《索隐》云:“说者谓诸子杂记也。”[4]2122可见,司马迁从独尊儒术的立场出发,认为经书中所载才是可信的,而诸子之说则不可信用。在诸子书中,《庄子》应该是讲许由故事最多的人:在《逍遥游》、《徐无鬼》、《让王》等篇均有记“尧以天下让许由,许由不受”的故事。所以,作为诸子杂记的“说者”,肯定是包括《庄子》的。曾经将别人的学说都目为“小说”的庄子,在汉代也成了“说者”。而且庄子的这些说法,在司马迁看来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从六经的记载可以看到,古人在禅让时是非常慎重的,先是由大家推荐,然后授予官职对其进行考验,只有通过考验了,才会将王位传给他,是“传天下若斯之难也”。故在《庄子》书中记载的那个不愿接受王位、甚至以此为耻的许由,是不可能出现的,是“说者”的杜撰。这种以经书和儒家说法为标准的史学家的判断,直接导致了对诸子之说为虚构、妄诞的判断,也直接影响了后世对小说“虚构”特征的认定。 刘向在校理群书、评论作家作品时,也是以儒家经书作为评判各书价值及真伪的依据。在《晏子叙录》中评价《晏子》一书云:“其书六篇,皆忠谏其君,文章可观,义理可法,皆合《六经》之义。”[5]50刘向认为《晏子》一书之所以“文章可观,义理可法”,是因为它“合六经之义”。六经是刘向评价《晏子》价值的准绳。刘向还说:“又颇有不合经术,似非晏子之言,疑后世辩士所为言者,故亦不敢失,复以为一篇。”[5]50可见,是否合于经传,不仅是价值判断的标准,甚至成了判断真伪的标准了,不合经术的,就可能不是晏子的作品。在《列子叙录》中,刘向亦说列子“其学本于黄帝老子,号曰道家。道家者,秉要执本,清虚无为,及其治身接物,务崇不竞,合于六经”[6]。在对《列子》一书进行评价时,也以是否合于六经作为标准。视不合六经之说为“亦有可观者”,这与子夏所说的“虽小道,必有可观焉”是一脉相承的,虽然认可其价值,但还是目其为小道或小说的。另据《汉书·张欧传》颜师古注所引刘向的《别录》有:“申子学号曰刑名。刑名者,徇名以责实,其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合于《六经》。”[2]2204将刑名之学与儒家的六经联系起来,仍是以六经为宗的。 扬雄在《法言》中将这种以经书和圣人之言作为最高准则的观点阐述得更为明确,《吾子》篇:“或曰:‘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将谁使正之?’曰:‘万物纷错则悬诸天,众言淆乱则折诸圣。’或曰:‘恶睹乎圣而折诸?’曰:‘在则人,亡则书,其统一也。’”[7]14认为各种言论、思想,都要折中于夫子,孔子以后则要以儒家的经书作为判断的标准。这是对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提出的“正朝夕者视北辰,正嫌疑者视圣人”的进一步发挥。 二、抑黜百家导致的“小诸子” 与宗经、征圣相对应的,是对诸子的轻视。虽然董仲舒提出要“灭息”邪僻之说,但从史料来看,他的这一理想并没有实现,各家思想在当时还有生存空间,不仅武帝“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史记·龟策列传》),学者也多兼治诸子百家之学。只是儒学成为正统后,其他各家则被“抑黜”。故“小诸子”,是在尊崇儒学、抑黜百家的大背景下形成的。王充在《论衡·案书》中记:“董仲舒著书不称子者,意殆自谓过诸子也。”[8]439这只是王充对董仲舒的臆测。而杨雄在《法言·君子》篇中则明言自己的这一倾向:“或曰‘子小诸子,孟子非诸子乎?’曰:‘诸子者,以其知异于孔子也。孟子异乎?不异。’”[7]4扬雄认为,“诸子”指的是与孔子思想不同的其他学派,而且对于说自己“小诸子”的言论,扬雄未予反驳,可见是确有其事的。在《法言·学行》篇中,扬雄说:“视日月而知众星之蔑也,仰圣人而知众说之小也。”[7]15将儒家和圣人喻为日月,将诸子喻为众星,形象地表达了对诸子及其学说的“小”的判定。《汉书·扬雄传》记:“雄见诸子各以其知舛驰,大氐诋訾圣人,即为怪迂,析辩诡辞,以挠世事,虽小辩,终破大道而或众,使溺于所闻而不自知其非也。”[2]3580在扬雄看来,与圣人和经书不同的诸子,是怪迂之作,是“小辩”,会损害大道、迷惑众人。将诸子之说视为“小辩”,是与儒家的“大道”相对而言的,其表述方式与庄子对“小说”的论述是非常接近的。 这种以孔子和经书为基准从而导致的对其他诸子的鄙夷性表述,在《法言》中很多,如“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好说而不要诸仲尼,说铃也。”[7]8认为评判作品和学说的好坏,要以孔子为标准,即符合孔子学说的就是好书、好说,不符合的就是书肆中的繁杂作品及“说铃”一样的小说。此处提到的“书肆”,是汉代为了适应民间教育事业普及和文化学术思想发展的产物,其中的书籍因为是针对民间且是普及性质的,故其学术价值不高。在《后汉书·王充传》中记王充:“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9]1629可见当时的书肆中,多是百家语。而百家语,因为不合经典,所以被视为“说铃”。李轨注《法言》“说铃”云:“铃以谕小声,犹小说不合大雅。”[7]8汪荣宝疏云:“大者为铎,小者为铃,说铃与木铎相对也。”[7]9《论语》中有“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语,朱熹注云:“木铎,金口木舌,施政教时所振,以警众者也。言乱极当治,天必将使夫子得位设教,不久失位也。”[10]认为木铎所喻为孔子所言关于治理天下之事理。与木铎相对的说铃,则是与孔子不同的其他家学说。所以,木铎为大道,木铃为小说;圣人之说为大雅之道,诸子之学为琐屑之说。 《汉书·东平思王传》记东平思王刘宇曾上疏求诸子及太史公书,皇帝问大将军王凤,王答曰:“诸子书或反经术,非圣人,或明鬼神,信怪物,《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不可予。不许之辞宜曰:‘《五经》圣人所制,万事靡不毕载。王审乐道,傅相皆儒者,旦夕讲诵,足以正身虞意。夫小辩破义,小道不通,致远恐泥,皆不足以留意。诸益于经术者,不爱于王。’”[2]3324-3325王凤批判诸子书与经书之说相反,因其对圣人颇有非议,所以不能给刘宇。此处的“小辩”、“小道”,均为对诸子书的批判性表述,而其“致远恐泥”的评价,则与子夏的论述是相同的。 从上文的论述可知,在“小诸子”观念的影响下,儒家之外的诸子往往被视为“小道”、“小辩”。那么,可否认为在当时这些小道就是小说呢?笔者结合当时学界对小说的论述来论证这一观点。 今天的学者在研究小说观念时,一般都会论及东汉的桓谭,因为他是第一次从正面论述“小说”的。在《新论》中,他说:“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①这里对小说家及小说的界定,是含有鄙薄态度的。首先,小说,不是“作”,不是“述”,而是“合”,是收集、整理,与庄子所说的“饰”相同,都不是原创,而是抄袭或加工。其次,仍然是“小”,“小语”带有和大道相对的卑微色彩。尽管桓谭对小说的评价有鄙夷之意,但毕竟第一次从正面论述了什么是小说:它的性质是合丛残小语,它的说理和论辩方式是近取譬论,它的形式是短书,它的功能是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相对前人的论述,这算是比较明确的界定了。故此说对于小说概念的清晰化有重要意义。 《后汉书·桓谭传》记桓谭“能文章,尤好古学,数从刘歆、扬雄辨析疑异”[9]995。可见,桓谭和当时的著名学者交往非常频繁,其观点应该可以反映当时的主流看法。那么在桓谭心目中,哪些作品是具有这些特点的小说呢? 《新论》有一条佚文:“通才著书以百数,惟太史公为广大,余皆丛残小语,不能比子云《法言》、《太玄》也。”[11]桓谭对当时的著书情况作了一个分析,认为除了太史公的《史记》与扬雄的《法言》、《太玄》外,其他均为“丛残小语”,也就是小说创作的原始材料或小说的原初形态。司马迁的《史记》是史书,在传统的目录学中,属于史部,不在明理的子书范围内。而扬雄是以儒家正统自居的学者,他的《法言》等作品,正是为了维护儒家的正统思想而创作的。桓谭认为除了《法言》和《太玄》外,其他都是丛残小语,都是小说,其实就是将当时儒家之外的创作均视为小说。 在《新论·本造》篇中,亦有相近的说法:“庄周寓言,乃云‘尧问孔子’,《淮南子》云‘共工争帝地维绝’,亦皆为妄作。故世人多云短书不可用。然论天地间,莫明于圣人,庄周等虽虚诞,故当采其善,何云尽弃邪!”[12]这段话表明,《庄子》、《淮南子》等书中有很多荒诞不经的说法,故在桓谭看来是妄作。他以这两本书为例子来证明“短书不可用”,而“短书”正是前面他所说的“小说家合丛残小语”的作品,也就是小说。而且其“故当采其善”的论述,与班固的“如或一言可采”一样,体现了一种“小道可观”的兼容态度。在桓谭看来,《庄子》和《淮南子》都是小说。这也证实了他视儒家及六经之外的作品为小说的看法。 在《论衡》中,王充也多次提到了“短书”,如《谢短篇》云:“二尺四寸,圣人文语,朝夕讲习,义类所及,故可务知。汉事未载于经,名为尺籍短书,比于小道,其能知,非儒者之贵也。”[8]196-197针对王充所言的“短书”,章太炎曾云:“周代《诗》、《书》、《礼》、《乐》皆官书。《春秋》史官所掌,《易》藏太卜,亦官书。官书用二尺四寸之简书之。郑康成谓《六经》二尺四寸,《孝经》半之,《论语》又半之,是也。《汉书》称律曰‘三尺法’,又曰‘二尺四寸之律’。律亦经类,故亦用二尺四寸之简。惟六经为周之官书,‘汉律乃汉之官书耳。’寻常之书,非经又非律者,《论衡》谓之‘短书’。此所谓‘短书’,非理之短,乃策之短也。”[13]因六经为周代的官书,故得以和汉律一起被写在二尺四寸的竹简上,除此之外的其他著作,则因为是被写在短一些的竹策上,而被称作“短书”。那么,“短书”肯定是包括诸子之书的,因为它们“非儒者之贵”,不被儒家所重视,故被视为“小道”。 三、短书小传,虚不可信 除了对诸子之说“小”的定位之外,学者也经常会批判百家思想的虚妄。王充在《论衡·书解篇》中说:“或曰:‘古今作书者非一,各穿凿失经之实传,违圣人质,故谓之丛残,比之玉屑。故曰:丛残满车,不成为道;玉屑满箧,不成为宝。前人近圣,犹为丛残,况远圣从后复重为者乎?其作必为妄,其言必不明,安可采用而施行?’”[8]435此处,王充将那些“失经之实传,违圣人质”的作品,比为“丛残”、“玉屑”,认为它们不具备什么价值,而且内容必为妄作,不能采用施行。《骨相篇》记:“斯十二圣者,皆在帝王之位,或辅主忧世,世所共闻,儒所共说,在经传者较著可信。若夫短书俗记、竹帛胤文,非儒者所见,众多非一。”[8]36十二圣指古代传说中的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夏禹、皋陶、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子,关于他们的传说,在王充看来,只有在儒家的经传中才是比较可信的。至于非儒者的说法就“众多非一”了,如黄帝龙颜、颛顼戴午、帝喾骈齿、尧眉八采、舜目重瞳、禹耳三漏等,都偏离了儒家之说,不可信,故而是“短书俗记”,是小说。这里王充仍然是强调儒者所见、所说才是真实可信的。可见,王充对小说的判定,亦是站在儒家的立场上“非其所非”的结果:一方面不在儒家经传中的就是小说,另一方面则强调这些小说的不可信用。《书虚》篇云:“世信虚妄之书,以为载于竹帛上者,皆贤圣所传,无不然之事,故信而是之,讽而读之。睹真是之传与虚妄之书相违,则并谓短书,不可信用……夫世间传书诸子之语,多欲立奇造异,作惊目之论,以骇世俗之人;为谲诡之书,以著殊异之名。”“短书小传,竟虚不可信也。”[8]63王充明确提出短书多为虚妄的判定,而恰恰是那些好作怪异之论的诸子百家语多虚妄,于是就成了小说。 这种认为诸子之说虚妄的观点,影响较为深远,直至刘勰的《文心雕龙》都留有这种痕迹。在《诸子篇》中论及诸子的创作特点时,刘勰说:“然繁辞虽积,而本体易总,述道言治,枝条五经,其纯粹者入矩,踳驳者出规。《礼记·月令》,取乎吕氏之纪;三年问丧,写乎《荀子》之书:此纯粹之类也。若乃汤之问棘,云蚊睫有雷霆之声;惠施对梁王,云蜗角有伏尸之战;《列子》有移山跨海之谈,《淮南》有倾天折地之说,此踳驳之类也。是以世疾诸混同虚诞。按《归藏》之经,大明迂怪,乃称羿毙十日,嫦娥奔月。殷汤如兹,况诸子乎!”[14]认为子书是五经的支流,那些纯粹的,还中规中矩。而那些驳杂者,就出现了“混同虚诞”之辞,如《庄子》、《列子》书中的寓言,《淮南子》中的神话故事,都是因“混同虚诞”而被刘勰批判的。 关于短书、小说的产生,王充也有论及,在《龙虚篇》中说:“彼短书之家,世俗之人也。”[8]95这就提出了小说产生于民间的说法。《艺增》篇中还有“蜚流之言,百传之语,出小人之口,驰闾巷之间”[8]129,这与“刍荛狂夫之议”、“道听途说”、“街谈巷语”已经很相近了。可见,王充已经有认为小说产生于民间的倾向了。在《风俗通义》序中,应劭亦云:“至于俗间行语,众所共传,积非习贯,莫能原察。今王室大坏,九州幅裂,乱靡有定,生民无几。私惧后进,益以迷昧,聊以不才,举尔所知,方以类聚,凡一十卷,谓之《风俗通义》,言通于流俗之过谬,而事该之于义理也。”[15]这是应氏论创作《风俗通义》的目的,纠正流传于民间、为大众所接受的俗说。这些俗说就是在民间普遍流传的妄语,和王充所说的那些流传在闾巷之间的“蜚流之言,百传之语”是相同的,也是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所认定的小说。可见,当时小说观念有了下移的倾向,从先秦时可以指向各家学说,演变至此,慢慢成了指代那些荒诞的、传播于民间的流言蜚语了。 出现这种变化,与思想界对儒家思想的重新认识有关。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对儒家论述为:“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4]3289对儒家尊崇的同时,也有反思和批判。虽然汉武帝提倡儒学,使儒学在思想界的正统地位逐渐得到了确立,但在社会生活层面,人们却面临很多痛苦。比如汉武帝穷兵黩武给老百姓生活带来的苦难,社会各种矛盾的突出等等。到东汉中期,儒学就陷入了困境。各种矛盾引起了思想界的变动,许多学者由儒转道,有的重新开始对儒家思想进行反思,如王充在《论衡》中就有很多对儒家思想和六经的批判,《论衡·谢短篇》批判儒生知今不知古的情况,云:“然则儒生,所谓盲瞽者也。”[8]196将儒生批判为盲人,态度很极端。而且这种批判多集中在其“虚妄”上。如《道虚篇》云:“儒书言: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龙,群臣、后宫从上七十余人,龙乃上去。余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髯。龙髯拔,堕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与龙胡髯吁号。故后世因其处曰鼎湖,其弓曰乌号。《太史公记》诔五帝亦云:黄帝封禅已,仙去。群臣朝其衣冠,因埋葬之。曰:此虚言也。”[8]105除了此处儒者言黄帝为虚妄外,还有儒书言淮南王升天之事等,均被王充视为批判的对象。而之所以批评这些儒家著作,是因为以虚妄作为评判之标准,把儒家的很多不实之作或妄诞思想也视为不经之说。 在对儒家进行反思和批评的同时,对其他各家的学说,王充则抱着一种包容、接纳的态度,如《别通篇》云:“夫人含百家之言,犹海怀百川之流也,不谓之大者,是谓海小于百川也。”[8]206“大才怀百家之言,故能治百族之乱。”[8]208《书解篇》有:“秦虽无道,不燔诸子。诸子尺书,文篇具在,可观读以正说,可采掇以示后人。……由此言之,书亦为本,经亦为末,末失事实,本得道质。折累二者,孰为玉屑?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经误者在诸子。诸子尺书,文明实是。”[8]435都是在强调诸子之书对个人修养、治国、纠正经书谬误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至此,对于小道、小说的认识,由前期的以儒家、圣人及经书为准绳进行判断,演变为对其思想内容真实与否的衡量。于是,作为评判标准的荒诞,也就成了小说的一个重要的特征。 综上所述,汉代小说观念是在先秦小说观念基础上的重大演变:先秦时期的小说可以指任一学派之外的其他各家,而到了汉代,在“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思想的影响下,小说成了儒家之外的其他诸子。对此,清代学者已有论及。如翟灏《通俗编》卷二:“《新论》‘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喻,以作短书。’按古凡杂说短记,不本经典者,概比小道,谓之小说。乃诸子杂家之流,非若今之秽诞言也。《辍耕录》言宋有诨词小说,乃始指今小说矣。”[16]明确指出,古代是将诸子杂家之流、不本经典的作品,都视为小道、小说的,而这种小说观,与宋代以后的小说观是截然不同的。刘宝楠在《论语正义》中,考证了诸多汉人所用的“小道”一词,并指出:“据此,则小道为诸子书,本汉人旧义。”并引焦循《补疏》“圣人一贯,则其道大;异端执一,则其道小”[17],来证明汉人是将儒家之外的诸子书看作小道的。尤为重要的是,刘宝楠所引的证据,就包括有班固在《汉志》中对小说的论述。可见,在汉代的一定时期内,小说、小道、小辩等词,大多指的是儒家之外的诸子之书。这种观念影响了后世对小说为“小道”的认识。而在以儒家为本位纠绳诸子的同时,逐渐赋予了诸子书虚妄的特征。随着学术界对儒家思想的反思,妄诞又成了判定小说的一个重要标准,这对小说虚构特征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 注释: ①今本《新论》无此,佚文见《文选》卷三十一,李善注江淹《拟李都尉从军诗》所引《新论》文字。见萧统《文选》[M].李善注,中华书局,1977:444.标签:儒家论文; 国学论文; 小说论文; 庄子论文; 春秋论文; 读书论文; 淮南子论文; 孔子论文; 风俗通义论文; 黄帝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