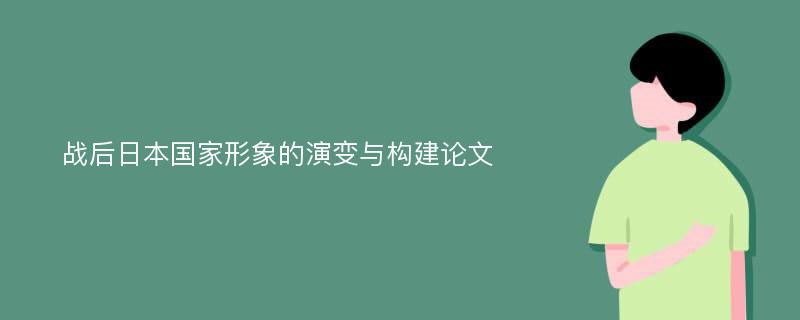
战后日本国家形象的演变与构建
毕亚娜
摘 要 :国家形象是国内公众和国外公众对该国的总体认知与评价。作为软实力的核心组成部分,国家形象对综合国力产生重要影响。国家形象的构建是战后日本国家战略的重要一环。战后日本在对国内外形势的认知与判断中,不断构建与经营其国家形象,其国家形象的范畴要素不断扩展,塑造路径愈加主动。同时,对日本国形象的评价呈现出国际社会给予积极提升和东亚邻国给予负面恶化的“两相背离”的矛盾现象。
关键词 :日本 国家形象 国家战略 构建路径
战后日本实现了从战败国到“文明国家”形象的转变,进入新世纪后其国家形象排名居于世界前列。在2005年至2014年间,英国广播公司(BBC)委托国际调查公司GlobeScan针对国家影响力进行民意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日本的正面国家形象排名长期稳居前六名,[注] GlobeSCan, “BBC World Service Poll”, June 3, 2014. https://www.globescan.com/images/images/pressreleases/bbc2014_country_ratings/2014_country_rating_poll_bbc_globescan.pdf. 日本成为国民高素质、产品高质量、发展高水平的典范。战后70余年日本国家形象的构建及经营以显而易见的方式影响着对外关系。针对战后日本国家形象的巨大转变,探究其国家形象的演进历程,剖析其国家形象构建路径是本文主要研究目的。
一 、被占领时期日本的国家形象及其构建路径
1945年至1952年,日本实际由美国单独占领,战后“民主主义”建设正式开启,日本国家形象认知与构建直面战争遗留的影响与战后国家重建的双重命题。
(一 )被占领时期日本的国家形象
1. 战争侵略者形象的遗留与战后对日恐惧
运用的教学方法主要包括:案例教学、演示教学、多媒体教学、讲练结合等。在课程的不同阶段,根据授课对象特点及课程内容灵活选择不同的教学方法。
据资料显示,化妆品零售从2014年1 158 亿元增长到2016年2 087 亿元,增长高达80.2%,预计到2020年中国化妆品线上交易规模将超4 500 亿元,中国也成为全世界化妆品消费最多的国家。到今天,美妆品牌如雨后春笋般越来越多,各种品牌琳琅夺目,层出不穷,美妆市场的竞争也愈演愈烈。
战后初期日本的国家形象被贴上了“残暴”“军国主义”[注] Sheila K. Johnson:The Japanese Through American Eye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p.18-22. 等标签。据1945年战争结束之初芝加哥大学所做的舆论调查,有6%的美国公众要求将“日本人全部消灭”,高达74%的被调查者支持对日本进行严密的监管、强制性占领与非军事化改造。[注] シカゴ大学世論調査所編:『アメリカは日本をどう見る』、佐々木文平訳、双竜社1950年版、第78頁。 对天皇战争责任的追究也成为战后处理的讨论焦点。据当年6月的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处死天皇的意见占33%,天皇应接受审判的意见占37%,保留天皇的意见仅占6%至7%”。[注] 日本史研究会、京都民科歴史部会編:『天皇制を問う――歴史的検証と現代』、人文書院1990年版、第200頁。 苏联、澳大利亚等盟国也要求将天皇作为“头号战犯”进行处置。在日本国内,与战前对天皇的敬畏相比,战后部分民众表现出了对天皇制的“漠不关心”,甚至以南原繁等为代表的思想研究领域人士公开发言支持天皇退位[注] 〔美〕 约翰·W·道尔:《拥抱战败》,胡博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99页。 。在日本正式投降之前,美国总统罗斯福设想了一种垂直的战后世界秩序,主张半永久性地削减主要敌国力量,该设想受到美国民众的广泛支持,并在1943年的“日本无条件投降”构想及《开罗宣言》中得以充分体现。因战争而引起的对于军国主义和爆发战争的恐惧,在战后初期直接反映到对日本的占领方针中来。
2. 战后日本的颓败形象与国家重建难题
2. “和平国家”与“不作为的取款机”
(二 )被占领时期日本国家形象的构建路径
1. 改变战争侵略者形象,消除战后对日恐惧
公元554年(梁元帝承圣三年),北方的西魏军队进攻江陵(梁元帝即位后,不肯回都城建康,江陵成为事实上的都城)。江陵眼看难保了,梁元帝命令舍人高善宝把自己收藏的古今图书十四万卷全部烧毁,又把宝剑折断,叹道:“文武之道,今晚全完!”有人问元帝为什么要烧毁书籍,元帝说:“我读书万卷,还落个今日亡国的下场,所以烧了它们!”(见《资治通鉴》第一百六十五卷)
第一,改变军国主义的政府形象,保留日本政府。占领初期,日本政府竭力向占领军证明其利用价值和合作意图,对内极力表现出对国民的统治能力,对盟军总司令部则做出可靠的合作者姿态。在实行象征天皇制和制定宪法等关键问题上,日本政府积极配合并适时引导,[注] 〔日〕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孔凡、张文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43页。 将日本统治集团的目标巧妙地融合在美国主导的占领政策之中。第二,改变负有战争罪行争议的天皇形象,维持天皇制。为洗脱天皇战争罪名、保留国体,东久迩内阁提出了“一亿总忏悔”和“天皇无责任论”,意在将“开战责任论”模糊为“战败原因论”。以占领军需利用天皇权威进行和平占领为契机,日本政府与麦克阿瑟多次斡旋,获得了麦克阿瑟对天皇的支持。此外,“地方巡幸”成为天皇在国民间树立战后新形象的重要手段,为其从“现人神”转化为人间的“精神”存在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麦克阿瑟的干预与日本政界的“助攻”下,天皇作为协助占领的“精神工具”得以留存。第三,改变穷兵黩武的国家形象,回归国际社会。战后日本政治家通过接纳新宪法,配合民主改革等契机,使日本的国家形象完成了从“战争恶魔”到“理想之国”[注] 〔日〕清水伸編:『逐条日本国憲法審議録 第1巻』、有斐閣2012年版、第43頁。 的转变,1946年对美舆论调查中有35%的被调查者认为日本“已真正改变”,1948年的舆论调查中有55%的被调查者认为在“之后20年间日本不会再成为世界和平的威胁”。[注] 〔日〕千葉浩美:「占領期における米国の対日世論と対日イメージ」、『国際政治』1993年2月号。 1951年片面的“对日媾和条约”的缔结宣告,长达6年的被占领时期结束,为日本构建战后国家形象奠定了基调。参与媾和的受害国在国际法层面与日本结束了战争状态,开启了赔偿谈判,正式清算与日本的战争历史。对参与媾和的国家而言,日本不再是具有侵略阴影的战败国,而成为了西方阵营的独立一员。正如杜鲁门在媾和会议的演讲中所言,“我们之间再无胜败,只有为和平而协力共进的同伴”。[注] 参见Harry S. Truman:“Address in San Francisco at the Opening of the Conference on the Japanese Peace Treaty”, September 4, 1951. Online by Gerhard Peters and John T. Woolley,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13906.
2. 改变战后日本的颓败形象,实现国家重建
众所周知,新课程改革倡导的是自主、合作、探究式的学习方式。新课程改革背景下的课堂教学首先强调的是学生的自主学习,只要是学生能够独立完成的学习任务,教师就不需要去花费更多的时间。反过来,只要是学生自主学习过程中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就是接下来课堂学习所要着力突破的。因此,无论学生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探究,都要强调他们的合作协同。因为这些疑难都是学生在自主学习过程中产生的,是个人的智慧所无法解决的,确实需要教师组织学生通过集体智慧加以突破。
老年教育属于服务型、社会性教育,对老年人的管理也是以人为本,本着关心、关爱和尊重老人的基本原则,最大限度满足老年人对兴趣爱好和教育内容的需要。老年大学和教育机构尽力为老年人提供便利舒适的教育环境,悉心、耐心、周到地为老年人提供优质和满意的服务。比如,将有共同爱好的老年人集中起来,互相交流沟通,找到精神的寄托,让老年人的子女安心工作,也填补了老年人因子女不在身边而牵挂思念的空闲时间,对于建立幸福家庭,发展社会文化事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3]。
式中:对式(3)及其中相关函数R(xi,xj,θ)选择与未知参数估计的更多介绍,可参考文献[21]。本文取Gaussian函数作为相关函数并用R软件的“DiceKriging”程序包[22]执行Kriging模型。
地方性震级ML由来已久,其测定公式(2)包含两部分:一是仪器记录的地面振幅的大小,二是与震中距相关的量规函数。新规范与旧规范的区别也主要体现在这两部分。在振幅的量取上,主要是仿真方式的区别,新规范要求仿真成DD-1型,而旧规范则要求仿真为DD-1型或W.A.型,而在实际操作中,多仿真成W.A.型。在量规函数上,新规范将之前全国统一的量规函数根据地域的不同分成了五种,而西藏所采用的量规函数与旧规范所使用的量规函数在多数情况下相同,差异处多数为±0.1,极个别情况下达到±0.2。
二 、“经济中心 ”战略时期日本国家形象及其构建路径
1952“旧金山和约”生效,日本作为独立国家重返国际社会。日本推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吉田路线”,创造了“世界第一”的经济奇迹。这个时期,日本国家形象的认知与构建是在经济困境与增长中孕育新生的。
(一 )“经济中心 ”战略时期日本的国家形象
1. 奇迹般的“经济大国”与唯利是图的“经济动物”
获得独立后的日本以“吉田路线”为国家战略,大力发展经济。1968年日本超过西德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80年代日本经济进入了令世界瞠目的“日本第一”的鼎盛时期。但因公害问题和经济至上带来的负面形象亦在加剧。60年代,日本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四大公害事件,因公害发展速度迅猛,程度恶劣,日本被冠以“公害列岛”等恶名。随着日本经济扩张的深入和影响力的增强,东南亚各国在认可其经济大国地位的同时,也出现了对日本“丧失精神的经济动物”等批判[注] 〔日〕深海博明:「東南アジアの日本観」、『アジア研究』2014年第4号。 ,70年代累积已久的对日反感集中爆发,东南亚出现了反日浪潮。1974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东南亚,在多国遭遇了反日示威。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引起了欧共体的防范与恐慌,日本首相池田勇人因在访问欧洲时大力推行“推销外交”,而被戏称为“半导体推销员”。与此同时,日美经济摩擦加剧,日本对美国的汽车出口成为日美关系的“定时炸弹”。1987年民意调查显示69%的美国人认为日本从事不公平贸易[注] 〔日〕深海博明:「東南アジアの日本観」、『アジア研究』2014年第4号。 。同年4月因东芝向苏联出口机床事件引发了美国对日本单纯追求经济利益的不满。1989年一批敲打日本的美国专著相继面世,“日本威胁论”等论调甚嚣尘上。
战争使至少270万日本军民死亡,约占1941年日本总人口的3%到4%。同盟国对日本本土的海战与空袭战毁灭了日本约1/4的财富,其中包括4/5的船只、1/3的机器设备、1/4的运输工具和机动车辆[注] 大蔵省財政史室編:『昭和財政史 終戦から講和まで 19巻 統計』、東洋経済新報社1978年版、第15—19頁。 。日本几乎所有的主要城市都因空袭而受损,东京作为日本全国最大的都市,战争造成的伤亡使其由1940年的670万人口减为1945年的280万人。1946年日本的工业生产只有1941年的1/7。[注] 〔日〕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孔凡、张文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40页。 因物资匮乏引发的通货膨胀很快造成经济混乱,国民的生命与生活受到极大威胁。在1946年5月的舆论调查中,日本民众最亟需的物资“主食”仍位列第一,[注] 「世論調査 大衆の欲しがる物資ー衣食住ー」、『朝日新聞』1946年5月27日。 甚至到1948年内阁府的舆论调查中,还有高达48.1%的民众认为自身生活状况“较去年更为恶化”[注] 内閣府官房政府広報室:『国民生活(都市住民)に関する世論調査』、1948年10月。 。从战后经济体系的整体溃败到以天皇为代表的精神支柱的崩塌,战后千疮百孔的日本面临着一系列的难题,在与占领者美国的斡旋中,日本政治精英首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即为国体的保存、经济的重振与恢复国家的独立主权。
战后和平主义思潮在日本社会成为主流。日本不仅在国内极力控制自卫队规模,同时也在发挥海外军事影响力等方面极其慎重,相当长的时期内“专守防卫”被作为其防卫政策的基本原则。在冷战两大阵营对立的国际环境下,面对美国多次加强防卫力量的要求,日本以“弱者的恐吓”加以回避,并通过提供综合安全保障经费等方式表示对西方的防卫贡献。1961年日本拒绝了联合国提出为黎巴嫩维和行动派遣人员的请求,因战后体制所限的政治矛盾初现。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专注发展“经济外交”的日本受到了巨大冲击,不介入中东战争与通商外交并没有使其成为阿拉伯国家认可的“友好国家”,日本首次强烈地感受到经济外交难以与国际政治相分离,其国家战略转换的思想开始萌芽。80年代末,美国对日本在军事上“搭便车”,经济上“大发横财”的行为批评愈重。1990年海湾战争爆发,日本尽管提供了巨额拨款却仍受到“不作为的取款机”的批评。“只要不与其他国家发生争端、不参与他国间的争端,就会被国际社会称赞为和平主义典范”[注] 〔日〕五百旗头真主编:《战后日本外交史:1945—2010》,吴万虹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版,第174页。 的理想主义被打破,纷繁复杂的世界形势使日本难以再“独善其身”。
1957年岸内阁发布了第一本外交蓝皮书《我国外交的近况》,提出“以联合国为中心”“与自由主义各国相协调”“坚持亚州一员立场”的“外交三原则”。战后日本力图以外交“三原则”为基准,构筑“三位一体”的国家形象。东南亚是日本塑造“亚洲一员”形象的重点区域,日本利用战争赔偿的契机,密切与东南亚的经济联系。但因与中韩等国关系龃龉,日本“亚洲一员”国家形象的塑造与认可变数颇多。1952年由美国主导的片面媾和将中韩等受害国排除在外,为日本与东亚邻国间的矛盾埋下了伏笔。很长时间内,中日、韩日之间因外交立场与历史问题等相互对立。相较于“亚洲一员”形象的构建,日本“西方一员”形象的塑造则颇有成效。1964年日本加入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并将此作为其自由主义国家一员的身份被欧美国家认可的标志。东京奥运会与大阪世博会成功举办,使日本国民自信心大振,“日本不再是战败国、而是发达国家的一员”[注] 〔日〕五百旗头真主编:《战后日本外交史:1945—2010》,吴万虹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版,第87页。 。1977年外务省民意调查显示日本在美信任度高达46%[注] 〔日〕白井小百合:「国家イメージ戦略の変遷とジャンパン.ブランドの今後」、『日本政治外交研究』、慶応義塾湘南藤沢学会、2013年、第108頁。 。1981年《日美联合声明》发表,首次写明日美关系是“同盟关系”,日本作为“西方阵营的一员”又向前迈出一步。但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其与西方国家之间经济摩擦加剧,“日本异质论”等批判的声音开始出现。日本陷入了“徘徊”在东西方之间的尴尬境地。
3. 尴尬的“亚洲一员”与憧憬的“西方一员”
第一,政府的有效领导与国民的共同努力。从战败至实现经济复兴的近十年时间里,日本政府发挥了积极的领导作用,在充分利用美国经济援助的同时,缓解粮食危机,抑制通货膨胀,“靠自己的脚走路”[注] 〔日〕吉田一郎:「ドッジ·ラインに対する再考」、『新潟経営大学紀要』2007年3月、第13号、第145頁。 ,实现经济自立。在政府的有效领导下,日本国民表现出了极大的克制与隐忍,他们“专心致志地进行工作”,“保持社会秩序,鲜有犯罪行为”。[注] 〔日〕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孔凡、张文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44页。 第二,朝鲜战争的爆发给日本带来了改变战后经济发展进程的契机。巨大的战争特需与商品输出使日本经济出现了空前繁荣,仅朝鲜战争期间补给军需等狭义特需就高达10亿美元,日本从国际贸易中的买方市场一举转变为卖方市场。在战争特需与商品输出的双重作用下,国内滞货一扫而空,商品生产势头高涨,矿业生产指数在朝鲜战争爆发后不到四个月即突破了战前生产水平,实际国民生产总值也在次年恢复战前水平。[注] 〔日〕内野達郎:『戦後日本経済史』、講談社1985年版、第89頁。 第三,利用战后形势变化,积极寻求美国援助,减少战争赔偿。随冷战形势的加剧,美国开始大力扶植日本经济。1945年至1949年间美国提出了一系列赔偿报告,不仅要削减日本的赔偿数额,甚至建议由美国对日本经济复兴提供资助。1949年5月,远东委员会的美国代表发表了停止拆迁赔偿的声明。事实上终止了美国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注] 郑毅:《吉田茂时代的日本政治与外交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93页。 。美国对日赔偿政策的转变对于战后初期日本经济的恢复起到了“消极的援助”作用[注] Yoshie Yonezawa: “National Economic Independence and the Rationalization of Industry”, in Juro Teranishi and Yutaka Kosai eds, The Japanese Experience of Economic Reforms, St. Martin’s Press, New York, 1993, p.261. 。日本政府深谙美国在片面媾和中的主导地位,利用美国为日本争取宽大的媾和条件,由美国代表出面游说严苛的赔偿要求。由占领初期严厉的惩罚性拆迁赔偿最终演变为“旧金山和约”中象征性的劳务赔偿。索赔国的索赔权限被极大限制,赔偿金额大幅缩水,日本以最利于其经济复兴的形式完成了战后赔偿。
5.2.3 Ecological knowledge contained in traditional costume
(二 )“经济中心 ”战略时期日本国家形象的构建路径
1. “环保大国”形象与“文化大国”形象的推进
日本严重的公害问题不仅使其国际形象受损,也引发了国内大规模的反公害市民运动。60年代后期以来,日本政府开始高度重视公害防治,推行了一系列以预防为主的环境对策。1967年日本制定了世界首部《公害对策基本法》,相关法令相继颁布,日本建立了一套完备的环保法律体系。之后,日本政府通过调整工业结构,制定全国性防治规划,加强国民环境教育等举措,使环境保护取得了良好效果。日本的防治公害对策并未止步于国内,1970年《公害白皮书》中首次提及“公害问题的国际动向”,将公害作为“世界规模”的问题加以考量[注] 『昭和47年版 環境白書』、環境省ホームページ。http://www.env.go.jp/policy/hakusyo/s47/index.html. 。日本积累的防治经验在80年代后期追求国际化意识膨胀的背景下,成为其开展环境外交、塑造国际形象的基础。日益激烈的贸易摩擦是这一时期日本经济发展带来的另一问题。为缓解贸易摩擦,日本在积极推进同他国的经济协作的同时,构建“文化大国”促进国际理解的构想也开始萌发。相较于环保领域的“对症下药”,其推进“文化大国”的前瞻性则更加意味深长。1964年外交蓝皮书开始明确肯定文化宣传活动对日本提升国家形象的重要助益,并将特色文化介绍作为其对外宣传的重点[注] 『昭和39年版 わが外交の近況』、外務省ホームページ。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1964/s39-7-1.htm. 。此后文部省文化厅、国际交流基金会等机构相继创设,日本的文化宣传活动开始有计划、成体系地推进。
2. “负责任政治大国”目标的酝酿
“搭便车”“单肺国家”等批评使日本各界深受触动。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日本民族主义思潮迅速抬头,执政党也开始宣传“国际国家”等理念,将其作为追求新的政治目标的思想工具。80年代初,中曾根内阁执政时期提出了“国际国家”构想和“战后政治总决算”口号,力图“摆脱战后体制束缚”,使日本从“经济大国”转变为“政治大国”。争任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成为日本争取发挥国际政治作用的重要手段,自1969年日本外相爱知揆一在联合国大会上表达了日本“入常”的愿望后,日本频频发起攻势,在联合国成立50周年之际日本的“入常”攻势因希望破灭而一再消极,但仍争取以非常任理事国身份扩大影响力。此外,日本通过“四次防卫预算计划”、“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等举措致力提升自卫队力量构成与装备水平。1987年中曾根内阁将当年防卫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确定为1.004%,突破了之前的“每年有关防卫费的总额应以不超过该年度国民生产总值的1%为目标”的限制,积极发挥在日美同盟中的作用,日美同盟关系开始进入实质性阶段。以中曾根等为代表的政治家提出的“政治大国”等理念的出现,以及在安保等方面的积极动作,标志着日本的“普通国家化”战略逐渐形成。
3. 搭建“亚洲与西方的桥梁”
受制于战后体制的日本难以通过政治、军事手段发挥国际作用,经济外交成为日本发挥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手段。以经济援助等为代表的东南亚外交是日本塑造“亚洲一员”国家形象的代表。为消除与东南亚国家的历史嫌隙,密切与东南亚国家间的经济合作,日本政府在50年代充分利用战争赔偿的契机,通过实物赔偿与技术援助等方式进入东南亚市场,将东南亚与日本的经济发展进程紧密相连。相较于东南亚外交的顺利推进,日本与东北亚邻国关系的推进则路途多舛。日本在东北亚地区“亚洲一员”身份的认同,不仅受历史遗留问题的阻障,更受到美国冷战政策的束缚,始终处在被动、消极的境况之中。为缓和与东北亚邻国间的关系,日本在对美协调的同时力图兼顾邻国利益,但在冷战背景下,这种中庸式的构建则尤为艰难。尽管如此,这一时期日本的东北亚外交也取得了难得的进展。在不断地斡旋中,日本相继实现了与韩国、中国关系的正常化,并通过大量提供经济发展援助与促进民间交流等形式改善与中韩关系。作为东亚唯一的发达国家,日本通过主办会议、提出地区合作构想与扩大经济援助等手段对东亚地区的发展表现出愈益积极的主导态度。
三 、“普通国家化 ”战略时期日本国家形象及其构建路径
冷战末期,日美间的矛盾因经济摩擦而激化。冷战结束后,克林顿政府将拥有强大经济实力的日本视为美国最大的威胁。然而,这一判断并未成为现实。90年代初期,日本经济泡沫崩溃,陷入长期萧条。与此相反,掌握信息技术命脉的美国,重新掌握了国际经济的主导权。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的平均增长率为1.75%,通货膨胀率为0.57%,90年代下半期日本经济陷入严重衰退,失业率在1991年初达到战后最高水平4.9%。进入21世纪后,日本经济在缓慢的复兴与危机中浮沉不定,国民生活中众多经济问题激化,加之日本对外的高调宣传,“经济失去的二十年”虽颇受争议,却成为冷战后人们对日本国家经济的普遍印象。在经济提振难以推进,国内矛盾积累日益严重的情况下,以摆脱战后体制为目标的“正常国家化”战略成为日本政府疏解压力的着力点。“普通国家”成为日本政府主动塑造并积极对外传递的国家战略。进入新世纪后,面对中国经济实力的迅速增长,“普通国家化”战略塑造的政治、军事大国形象被赋予了维持日本东亚主导者地位的新内涵。
(一 )“普通国家化 ”战略时期日本的国家形象
1. “经济失去的二十年”与“正常国家化”
酝酿自冷战末期的“普通国家化”战略,在90年代中期后日臻成熟,日本的国家战略进入“破旧求新”的新阶段,国家形象构建进入了以主动塑造为中心的时期。一方面,世界范围内日本的国家形象愈加正面、积极;另一方面,由于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逃避与反复,使其在亚洲地区的国家形象跌至低谷。
3. 挥之不去的侵略者标签
2. 名列前茅的“积极”国家排名
2014年澳大利亚经济与和平研究所公布了本年度“全球和平指数”排行榜,对162个国家与地区的国内外争端、犯罪和恐怖袭击的危险性、政治的稳定性等“和平指数”进行量化排序,日本位列第8。长期以来,排行榜的前10位国家中北欧国家占据半数,而亚洲国家则仅含日本。报告认为日本内政稳定,暴力犯罪、暴力示威及杀人率等指标均为世界较低国家;尊重人权,法律严格禁止携带枪支,战后政局一直相对稳定;军费占GDP的比例较低。2007年4月美国《时代》周刊公布的调查显示被调查的27个国家中日本形象稳居世界第一。同年,就美、英等12个国家对世界的正负面影响,BBC对27个国家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高居第二位。BBC的国家影响力调查,从2005年调查发起到2014年为止日本一直稳居前六位。[注] BBC Globescan:“Negative views of Russia on the Rise: Global Poll”, available at:http://www.globescan.com/news-and-analysis/press-releases/press-releases-2017.html. 文明、干净、安全、廉洁等正面、积极的国家形象已成为各国对日本国家形象认知的主流。
那么,这种相关关系存在吗?我们构造虚拟变量Highincome(高收入国家)、Middleincome(中等收入国家)、Lowincome(低收入国家)以区分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并在回归式中引入了kaopen和国家发展阶段dummy的交叉项。结果显示,三个交叉项中只有低收入国家和kaopen的交叉项估计系数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为负,不仅如此,在回归(7)-(9)中,引入这一项的回归(8)拥有最高的R2,说明对于低收入国家而言,金融开放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与中等收入阶段国家和高收入国家存在着明显的区别,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金融开放对一国经济增长存在负面效应。
冷战中并未凸显的历史问题,在冷战结束后却成为了日本与邻国外交的论争焦点,并在进入21世纪后转化为绑架其邻国外交的结构性束缚。早在80年代,中曾根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受到了中国的抗议,随即终止了参拜活动。进入21世纪后日本政界保守主义倾向加剧,以小泉、安倍等为代表的政治家一再参拜靖国神社,否定“慰安妇”存在的事实,发表“侵略战争未定论”等不负责任的政治言论,使日本与邻国关系,尤其是与中韩两国的关系一再陷入低谷。据2013年日本言论NPO与《中国日报》共同实施的舆论调查显示,92.8%的中国人回答对日本“印象不好”,跌至2005年调查开始以来的对日本好感度数值的最低值。[注] 「第9回日中共同世論調査」結果、言論NPOホームページ、2013年8月5日。http://www.genron-npo.net/pdf/2013forum.pdf. 在冷战后近30年的时间里,不乏村山富市、河野洋平等勇于承认侵略历史,致力于推进日本与亚洲邻国关系和解的政治家,但部分政治家一再反复的不负责任的历史态度为日本自身贴上了挥之不去的侵略者标签。
(二 )“普通国家化 ”战略时期日本国家形象的构建路径
1. 提振经济与积极追求“普通国家化”战略目标
90年代初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提振经济的政策。在社会问题愈益突出,经济提振效果乏力等难题的困扰下,经济问题成为日本难以解决的结构性困扰。为改善经济萧条的局面,1992年日本政府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从1992年8月至2000年10月期间,日本政府共实施了9次经济刺激对策,景气对策支出规模高达129.1万亿日元[注] 〔日〕篠原総一:「需要政策か供給政策か:経済政策の20世紀」、『経済セミナー』1999年12月。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着眼于完善长期经济发展结构,积极推进社会经济的结构改革,规范金融体制,扶植第三产业的发展。通过一系列改革,日本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经济产业结构,为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外,酝酿修改和平宪法,摆脱战后体制的束缚,仍是这一时期日本构建“普通国家化”战略的重要手段。90年代初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与自民党政调会长三冢博等人相继提出修改和平宪法的主张。此后,日本政界与媒体界踊跃提出各种不同的修宪方案, “宪法调查委员会”等围绕修宪问题的团体应运而生。在主张积极修宪的安倍第三次连任后,日本修改宪法的具体进程大大加快。
研究组31例中,显效15例,好转14例,无效2例,总有效率为93.55%;对照组31例中,显效9例,好转15例,无效7例,总有效率为77.42%,研究组明显优于对照组,两组效果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 正面、积极国家形象的塑造
战后日本积极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对外改变战争侵略者形象,努力塑造环保与文化大国形象,提升“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对内打造廉洁、高效的政府,在全球获得良好口碑。“普通国家化”战略阶段,日本国家形象的塑造在延续前一阶段经验的基础上,进入主动构想与建设阶段。作为国家形象塑造最重要的途径——对外经济援助,表现出了战略性倾向,日本ODA大纲作出调整,首次允许对其他国家军队提供“非军事目的”援助。此外,“酷日本”文化战略使日本的对外文化宣传开始具有了体系性。2002年文部科学省文化厅发布了《第一次文化艺术振兴基本方针》,2009年日本政府第一次在政策层面使用了“酷日本”一词,次年民主党政权公布了其经济增长纲领《新增长战略——“神采奕奕的日本”复活方案》,2011年日本知识产权战略本部发布了《知识产权推进计划 2011》,首次明确了“酷日本”战略的具体目标。2012年安倍内阁以内阁总理大臣决议的形式成立由“酷日本”战略担当大臣担任委员长的“酷日本推进会议”。在政府的推动和产业界的努力下,“酷日本”战略在传递日本魅力、构筑日本形象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3. 历史问题“流于表象”的策略性退让
进入新世纪后,日本国家形象塑造在国际社会取得了“卓有成效”的影响。但与之相对,因历史问题、领土争端问题等日本与邻国的争端却愈发加剧。21世纪初,因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与历史教科书修订等问题日本与中韩关系一度降至“冰点”,历史问题成为新时期日本塑造国家形象难以跨越的阻隔。随着日本追求“普通国家化”步伐加快,力求“摆脱战后体制束缚”的国家主义高涨,日本急于摆脱“自虐史观”的努力与东亚邻国对其正视历史问题的强烈要求,变化成结构性难题。“出于国家利益考量而维持表面友好”[注] 〔日〕朴裕河:『和解のためにーー教科書·慰安婦·靖国·独島』、佐藤久訳、平凡社2006年版、第8頁。 的策略性退让成为日本政府的应对范式。在日韩邦交正常化50周年之际,两国政府意图通过双方的策略性退让而一举解决慰安妇问题。但日本政府的“表面友好”并没有得到韩国民众的普遍认可,2016年9月盖洛普在韩国的民意调查显示认为“应该再协商”的调查者比重高达63%[注] 「日韓慰安婦合意、韓国世論が悪化『再交渉を』63%」、『朝日新聞』2016年9月3日。http://www.asahi.com/shimen/20160903/index_tokyo_list.html. ,日韩间的“慰安妇风波”并未因一纸协定而平息。
四 、结语
纵观战后日本国家形象与构建路径呈现出显明的演变趋势。一是,日本构建国家形象的范畴要素不断扩展,多层面的全方位形象构建已成为日本国家形象塑造的体系性框架。从被占领时期对经济与战争形象的聚焦,到“普通国家化”战略时期对经济、政治、文化、环境与荣誉等形象范畴的全面构建,战后日本国家形象的构建完成了从单一性向多元性,由散点化到体系化的转变,其理念建设、机构运作与对外交流愈加完善与成熟。二是,对日本国家形象的评价呈现出“两相背离”的矛盾,一方面是在国际社会综合国家形象评价的积极提升,另一方面是在东亚邻国中国家形象评价的负面恶化。前者是对战后日本国家形象成功蜕变的肯定。后者是对日本与邻国间愈演愈烈的历史问题的反映。缺乏正视历史的策略性应对,并未从根本上解决日本与东亚邻国间的历史与领土纠纷。“战争侵略者”标签的残留仍旧是横亘在日本与东亚邻国间的外交难题。三是,日本对国家形象的塑造路径由“被动应对型”向“主动塑造型”转变,其对国家形象的经营愈加具有目的性与战略性。“负责任的政治大国”“文化大国”等国家形象的塑造与其国家发展阶段战略目标的推行紧密呼应,国家形象的塑造已俨然成为日本国家战略推进的重要一环。
总体而言,战后日本国家形象的构建是比较成功的,但对历史问题反省的逃避又给这一成功塑造的正面形象蒙上了阴影。21世纪第一个10年之后,东北亚国家实力对比正发生着新一轮的变化,日本为维持地区优势地位又将其国家形象构建与国家战略的结合推向新的阶段。“价值观外交”“亚洲民主安全菱形”等战略构想的提出,使日本国家形象构建成为抑制中国崛起、争取地区领导权的政治手段,其与国家目标相结合的战略色彩也愈加浓厚。
本文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博士生
责任编辑 :乌兰图雅
DOI: 10.19498/j.cnki.dbyxk.2019.01.007
标签:日本论文; 国家形象论文; 国家战略论文; 构建路径论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