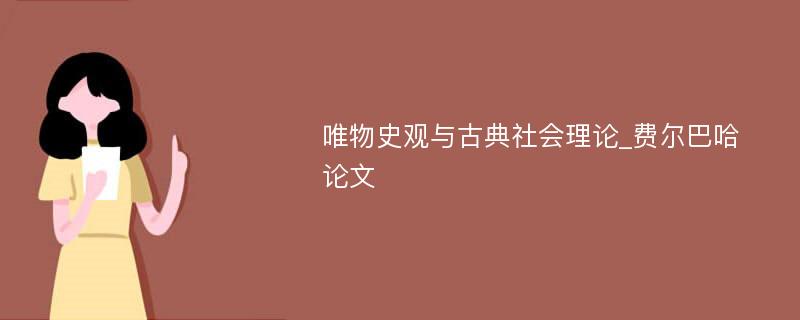
唯物史观与经典社会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唯物史观论文,理论论文,社会论文,经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0)01-0007-07
在现代西方学术视野里,马克思被看成是批判的社会理论传统的开创者,与涂尔干集大成的实证的社会理论传统、马克斯·韦伯开创的解释的社会理论传统一起,并称为经典社会理论的三大传统。经典社会理论传统,在很大程度上调整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激进形象,并把资本主义批判功能转换为服从于资本主义的渐进性改良与进化模式的分析与治疗功能。经典社会理论传统的重构,凸显了唯物史观对资本主义体系结构的认识功能,开放了其现代性问题域,也深化了唯物史观的理论复杂性,并构成当代各种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基点,值得探究。
一、唯物史观及其批判的社会理论与实证主义传统的界分
在马克思唯物史观及其批判的社会理论传统的形成过程中,一直交织着与实证主义传统的复杂关联。实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基本背景及语境。在19世纪的时代精神中,实证科学无疑是褒义的,是对统一科学(unity of science)的不同反映,而马克思无疑是肯定“实证科学”作为“一门科学”的,由唯物史观及其确立的批判的社会理论传统,同样要求具有实证科学的精确性。对马克思来说,如果没有实证科学,必定难以真正展开实践批判。在这一意义上,把唯物史观及其批判的社会理论看成是实证科学,并无不可。不过,这里的实证科学不能还原为实证主义。“马克思的统一科学的视野,并非实证主义者的视野。”“马克思的实证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后来的解释者的一个发明。”[1](P218、P217)把马克思学说判定为实证主义,正是把实证主义混同于实证科学的结果。实证主义的社会理论所延续的依然是法国唯物主义的自然主义及其环境决定论。孔德把由实证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看成是人通过启蒙环节从而自愿接受某种最优化的自然社会环境的结果,对马克思而言,从实证科学向社会主义的转变首先必定是制度改造。不触及制度变革而展开的人性改造活动,只能导致空想社会主义的出现;而通过制度改造进而带动人性的可能的新的启蒙,方使得社会主义真正进入实践环节,并使科学社会主义得以可能。
为马克思所批判的国民经济学正是当时实证主义的显学。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直接指向其抽象的理论性质、机械唯物主义以及为资产阶级辩护的政治立场。“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把这些公式当作规律。它不理解这些规律,就是说,它没有指明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2](P50)国民经济学“把工人的需要归结为维持最必需的、最悲惨的肉体生活,并把工人的活动归结为最抽象的机械运动。”[2](P122)“在国民经济学家看来,社会是市民社会。”[2](P134)
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肯定了哲学人本学,并进而向社会化的人及社会主义理念敞开。在这一方向上,费尔巴哈受到了马克思的肯定。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概括了费尔巴哈三个“伟大功绩”,其中第二个功绩即认为费尔巴哈“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实在的科学,因为费尔巴哈也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成了理论的基本原则”。[2](P96)在当时致费尔巴哈的信中,马克思明确地称费尔巴哈的《未来哲学原理》“给社会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又说“建立在人们的现实差别基础上的人与人的统一,从抽象的天上下降到现实的地上的人类概念,——如果不是社会的概念,那是什么呢!”[3](P450)这里,借费尔巴哈之口,马克思表明了自己对于社会主义不同于法国唯物主义的领会。马克思大致还是在自然唯物主义的意义上把握社会主义的。
但是,即使如此,马克思此时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还是不同于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当时已经发现了社会,但社会的实质,正如在康德与黑格尔那里一样,其本质依然是现象界或自然。[4]在费尔巴哈那里,看不到社会是“人与自然的完成了的统一”,而只是人与自然的新的抽象。费尔巴哈依然只是在自然主义与人本主义直接同一的意义上理解社会(主义),他其实是把社会当成人间神物,是其无神论思想的体现,而当他把社会当成新的偶像时,实际上又复活了神秘主义。在社会政治理想上,费尔巴哈显然没有超越法国唯物主义。不仅如此,马克思于1842年在致卢格的信中明确批判费尔巴哈,说他“过多地强调自然界,而过少地强调政治”。[3](P443)在这一意义上,费尔巴哈的自然唯物主义对于法国唯物主义甚至还是倒退的。这里也牵涉到马克思对当时诸如卡贝、德萨米、魏特林之类“实际存在的共产主义”的清算,马克思认为这些思想“只不过是人道主义原则的特殊表现”,“还没有摆脱它的对立面即私有制的存在的影响”,“只不过是社会主义原则的一种特殊的片面的实现而已”。[5](P416)因此,必须破解私有制,推进政治解放。在通过费尔巴哈的批判而阐述其新唯物主义思想时,马克思认定自己对社会形成了不同于费尔巴哈的新的认识。在马克思看来,不仅缺乏人的原则的实证主义尤其是国民经济学,而且以哲学人本学为主导的费尔巴哈的自然唯物主义,其立足点都只能是市民社会。“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①
颇有意味的是,费尔巴哈的社会观,在作为实证主义社会学学科创始人涂尔干那里再次复活。费尔巴哈把社会提升成了新宗教,涂尔干则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为社会,宗教不仅是社会的产物,而且本身就是神化了的社会,而人们对神的崇拜,本质上就是对社会的崇拜。在一定意义上,涂尔干是用社会“祛”宗教之“魅”。因而,社会是人类之父。“是社会把人提升起来,使他超越了自身;甚言之,是社会造就了人。”“如果宗教产生了社会所有最本质的方面,那是因为社会的观念正是宗教的灵魂。”[6](P552)与斯宾塞的社会不可知主义不同,涂尔干坚信社会是可以认识的。“社会绝对不是无逻辑的或反逻辑的存在,也不是混乱的和虚幻的存在。”[6](P581)
不过,与费尔巴哈异质于实证主义的哲学人类学立场不同,涂尔干对社会的理解标示着实证主义传统在改良主义方向上的延续和复兴。在涂尔干的时代,社会主义已成为欧洲主流的社会思潮,但社会主义又出现了新的分野:一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及其实践传统;二是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传统——这一传统影响了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三是向民族主义以及宗教传统的回复与结合——国家社会主义是这一路向的变异了的极端形式。涂尔干当然重视社会主义传统,而且他大体分享了第二个传统并与社会连带主义有关。涂尔干清楚地知道社会主义对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性,在其未完成的《社会主义史》中,涂尔干承认:“社会主义提供给社会科学的帮助比它从社会科学中所得到的帮助多得多”。“社会主义已经唤起了反思,激发了科学的活力,鼓起了研究的热情,提出了问题,所以,社会主义的历史不止以一种方式融入社会学的历史中。”[7](P132)但他本人看来并不认同社会主义价值观,在涂尔干看来,社会主义属于实践学说而不是思辨科学,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研究更是属于目的论,并不符合现代性与社会分工体系的要求,因此必须“降低社会主义的重要地位和意义要求”才能“承认社会主义具有真正的科学性质”。[7](P131)在涂尔干那里,社会主义的研究,与他有关分工、组织、团结、伦理、道德、失范、自杀、犯罪以及宗教等问题的研究是等同的,都属于构成性的和规范性的研究。
涂尔干有关社会主义的研究与其有关个人与社会关系研究的关联问题,有些复杂。就涂尔干创立社会学及其显示的巨大理论及实践效应看,实证的社会理论传统在马克思主义之后再度复兴,并使得自由主义在社会科学领域获得了新的话语权——涂尔干的实证的社会理论传统,在政治倾向上依然是自由主义的。与此同时,在涂尔干之后,则是马克斯·韦伯以保守主义为主导方向的解释的社会理论传统的兴起。不管是涂尔干还是韦伯,都是对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直接批判与摒弃。我们似乎也由此发现马克思之后社会主义分野的某种理据,第二国际民主社会主义的兴起,对应于涂尔干实证的社会理论传统的复兴,而社会主义向民族主义及宗教传统的回复与结合,则对应于解释的社会理论传统的兴起。作为20世纪社会理论主流的结构功能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涂尔干与韦伯两大社会理论的合流与延伸。即使西方马克思主义及法兰克福学派的兴起,其实也受到了涂尔干、韦伯以及结构功能主义的巨大影响,从而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呈现出一定的区别。
涂尔干对社会主义的处理,正是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种实证性的、而不是目的性的要素。这种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受饶勒斯等第二国际人物影响的结果。在这一意义上,恩格斯对第二国际实证主义的批判,也可以看成是对涂尔干实证的社会理论传统的批判。恩格斯在晚年致约·布洛赫的通信中,在谈到当时一些德国青年把经济因素看成是社会的唯一决定性因素时,认为马克思同他自己要承担一定责任,因为他们此前在反驳他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因”。恩格斯明确地讲:“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从思维方式上看,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与《自然辩证法》中所呈现的“自然辩证法”,与马克思在其实践批判中特别强调的主客体辩证法,其实是有差别的。在这一意义上,吉登斯肯定地说:“恩格斯把辩证法转移到了自然,忽略了马克思观念中最基本的要素,即‘历史过程中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8](P216)人的因素被抽掉,这种唯物主义便很容易退回到旧唯物主义。而这一点,同时也是第二国际在批判和排斥伯恩斯坦主观主义(修正主义)之后的思想命运,即“以强化机械唯物主义的趋势为代价”,并“回到了马克思在其早期阶段所批判和抛弃过的‘消极’唯物主义”。[6](P215)而涂尔干的社会理论,正是在社会领域里再现第二国际的思想。因此,当恩格斯把历史的决定因素看成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时,他对于唯物史观对实证主义传统的异质性,应当是有着更深入的领会与把握的。
二、经典社会理论的兴起对唯物史观的影响
马克思在激进政治思想基础上建立的唯物史观及其科学共产主义,突破了自由主义传统,也超越了空想社会主义。人们一般把1848年看成是“自由主义的分水岭”,正是在1848年兴起的由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所支撑的社会革命中,“那些盛赞1789年人权宣言的自由主义者感到了来自于大众的威胁,并由此倒向了反革命。事实上,在欧洲的大部分地方,自由主义者被革命所击败,并随后陷入覆灭。”[9](P28)这并不是说唯物史观及科学共产主义由此直接主宰了欧洲社会政治思想,毋宁说,唯物史观与科学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异质于西方既定的现代历史观念,但又具有全球现代性视野的新的酵素,激起了欧洲社会政治思想新的全面的变化,马克思之后经典社会理论的推进与变革,正是上述变化的结果。
早年马克思之所以对现实政治持激进的政治态度,为当时所处的背景所决定。对于英法“先进国家”,马克思认定将在已有的资产阶级革命基础上展开无产阶级革命,从而确定历史的主体;对于德国制度,马克思认为虽然“低于历史水平,低于任何批判,但依然是批判的对象”。[5](P455)马克思显然希望在德国推进无产阶级实践活动,但1848年之后,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一方面,马克思依然在强调其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这在他同无政府主义以及后来与第二国际改良主义等的不懈论战与批判中可以看出来,马克思依然在不遗余力地坚持其科学社会主义的政治主张。另一方面,马克思对革命形势又有了一些保留。他不再那么热衷于讨论德国无产阶级革命问题,对于法国革命,则依然视之为自由资产阶级政治的典型,对于已经置身于英国伦敦工商业革命背景中的马克思,显然也感受到了英国现实与激进社会主义的距离。实际上,到了伦敦以后,马克思的主要精力已放到了学术研究事业,放到了《资本论》的研究与撰写活动中。与此同时,马克思也受到了实证主义传统更内在的影响,正如他依然相信历史科学与实证科学。
自1851年英女王开放水晶宫从而宣布英国进入维多利亚时代以来,英国的资本主义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②马克思则把自己的工作重心转入资本论的研究与写作。1848年前后,实证主义及社会达尔文主义代表人物斯宾塞,同马克思差不多前后来到并停留于伦敦(二人并不认识),斯宾塞对当时英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判断,与马克思有很大区别。斯宾塞显然相信,当时的英国正在走向积极可行的改良主义道路,也符合以“光荣革命”为典型的英国改良主义传统。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掀起了一波激进主义浪潮,通过注入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从而强力地冲击了欧洲思想界。但是,50年代以后的维多利亚时代,却更多地需要斯宾塞的社会哲学。相比之下,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及其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影响要小得多,这一时期唯物史观的实际境况,其实是颇为艰难的。一方面,第二国际所宣讲的历史唯物主义,其实质正是恩格斯十分反感的经济唯物主义,其实证色彩十分浓厚,就连涂尔干、韦伯以及西美尔等所面对的,也是这种被改装了的历史唯物主义教条,而并非马克思、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的全面论述。③另一方面,当时的资本主义已经摆脱了早期资本主义的危机,走向了一条渐进的和相对稳定的改良主义道路,在这种情况下,真正反映马克思唯物史观及科学社会主义的革命逻辑,似乎也正在失去市场。
伴随着上述变化的,正是三大经典社会理论传统的形成。唯物史观及其科学社会主义,凭借对人的社会关系本质的洞悉以及世界历史时代的历史目的论,不仅成就了批判性的社会理论传统,而且以其特有的洞察力及原理意义,正在成为资本主义变革和发展的潜在理论。在孔德、斯宾塞之后,涂尔干则以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现代社会转型问题为实践基础,以功能主义为方法论基础,从而集实证的社会理论传统于大成。韦伯则延续了德国近代以来的保守主义精神传统,开创了解释的社会理论传统。三大经典社会理论传统其影响显然不只是在社会学一个学科,而是在于整体地推动了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形成与进展。这种状况同时也将唯物史观及其批判的社会理论传统带入现代。
经典社会理论对唯物史观的影响,大体上有如下三个方面。
1.如前所述,唯物史观不仅没有中断反而进一步强化了实证主义传统。就其本身而言,唯物史观在经济学与历史科学的意义上强化了实证科学。在这一意义上,在孔德之后,马克思成为现代社会科学的真正奠基者。就其连带效应而言,唯物史观及其批判的社会理论传统,进一步激起了实证的社会理论传统的复兴。斯宾塞之后,涂尔干在学科与理论建设领域直接推进了实证的社会理论传统,涂尔干有关社会分工、社会事实、社会现象以及社会团结等问题的研究,虽然与唯物史观有着原则区别,但在反个人主义以及肯定社会化及社会存在方面,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及批判的社会理论更有契合之处。涂尔干进一步巩固了社会理论与社会主义传统的关联。④
2.激进政治及其革命的社会主义实践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也激起了保守主义的复兴。在19世纪上半叶的德国,最主要的社会思潮是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费希特、黑格尔致力于它们的结合。但是,对马克思而言,只有突破自由主义及民族主义才能实现社会主义,马克思由此掀起了近代激进政治思潮。这一思潮的巨大反响,反过来激起了历史主义的回应,并随后带来保守的民族主义的复兴。以韦伯为代表的解释的社会理论传统,也包括部分的实证社会理论传统,都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保守主义。在这一方面,民族、国家、文化传统、宗教这一类被历史唯物主义的进步逻辑所扬弃了的因素,恰恰又在不断挑战唯物史观,并对西方当代有关唯物史观研究产生了直接影响。韦伯以及西美尔对唯物史观的批判以及对精神文化现象的重视,同时也是启发卢卡奇与布洛赫的思想资源,并对此后的法兰克福学派产生了深刻影响。正是通过卢卡奇与法兰克福学派,唯物史观之不同于经济决定论的内涵复杂性及其现代性得以全面地呈现出来。
3.重要的也许在于,无论实证的社会理论还是解释的社会理论,都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马克思唯物史观所给定的政治框架,诸如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格局及其界分。因此,对马克思批判的社会理论进行有效政治分类的基本框架,如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如果放到相关经典社会理论家那里,都不是那么适合。吉登斯的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传统的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分类法很难对涂尔干和韦伯的政治观点进行归类”。[8](P273)换句话说,韦伯与涂尔干的社会理论转变了在唯物史观及科学社会主义下的政治思想分野。为先前马克思在其唯物史观意义上所处理过的那些思想资源,如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以及实证主义,还有功利主义、历史主义、浪漫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实际上又敞开了新的视域。这些问题,与其说是思想问题,不如说是时代问题。比如,马克思、涂尔干以及韦伯对社会主义的不同把握、论证及其信奉方式,本身就值得专题探讨。马克思处理过的那些问题,主要来说是政治社会问题,且有其明显的早期资本主义特征,而涂尔干、韦伯甚至于斯宾塞,则是处理转折或上升时期资本主义的问题。在这一意义上,显然有必要结合诸种经典社会理论传统及其背景差异,以深化对经典社会理论的理解。但本文并不认同经典社会理论果然颠覆了马克思关于现代政治格局的基本判断,这涉及对经典社会理论及其与近代政治社会理论以及经典社会理论所固有的政治哲学片面性的评价,也涉及对马克思之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政治走向的历史评价,这一话题留待以后再讨论。
三、从经典社会理论传统审视唯物史观的现代性
在面对当代思想家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成果时,常常会伴随着一种困惑,即这些思想家所展开的问题视域,与通常的历史唯物主义话语并不是那么协调,有时甚至是完全迥异的。出现这种状况,与我们有关唯物史观研究中经典社会理论视野的缺失是有一定关系的。在西方学术思想史上,唯物史观的当代性研究,必定要经过经典社会理论这一重要的环节,才成为稳定的问题或课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舍弃涂尔干及韦伯的经典社会理论传统,自然容易对当代社会理论中有关唯物史观的探讨产生误解。
批判的社会理论传统本身就是从唯物史观转化的结果。唯物史观及科学社会主义,因为对实证主义的经济学、政治学以及社会学传统的批判,开启了批判的社会理论传统,而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展开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也构成了批判的社会理论的基础。但是,仅限于唯物史观及科学社会主义,还不可能全面地形成批判的社会理论传统。由唯物史观开出的批判的社会理论传统,同时也贯彻着与其他几种经典社会理论传统的对话、互动与互释,并实现了从唯物史观的基本话语到批判的社会理论话语的转换。比如,历史唯物主义所关注的生产与劳动概念,在批判的社会理论中,已拓展并转换为交往与实践概念,涂尔干的社会分工及其社会转型论,正是理解这一转换的关键环节。再如宗教社会学问题,唯物史观对宗教的批判态度是十分鲜明的,在这一意义上,任何对宗教妥协的态度,与唯物史观所坚持的彻底的无神论原则都是格格不入的。但是,在面对社会整合以及现代性社会的文化类型时,宗教传统及其社会整合意义却又显得十分重要,无论是实证的社会理论还是解释的社会理论,都重视宗教社会学。宗教的维度,同时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视角,解放神学的兴起本身就表明,马克思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已被看成是与激进的犹太—基督教传统的世俗化相同一的现代社会力量。
经典社会理论对唯物史观的现代性视域的影响当然不是全方面的,但如下几个方面特别重要。
1.经典社会理论对唯物史观提出的问题及其论域,直接拓展、延伸并影响着唯物史观的当代研究。诸如社会分工、社会分层、公民社会、社会事实、社会团结、社会整合、组织化、失范、交换、科层制、宗教、民族—国家等等问题,这些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中已被处理过并有定论的问题,因为现实实践以及理论结构的不同,成为相关经典社会理论的主要课题,而相应的研究成果也对唯物史观提出了一些实质性的反思批判,进而也激起了唯物史观的深入研究。追溯起来,人们会发现,第二国际、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晚近的激进左翼思潮对唯物史观所展开的研究与反思,在理论资源上都可以追溯到经典社会理论。
2.批判的社会理论传统的文化维度不断强化。西方马克思主义同相关现代思潮的融合也表明,历史唯物主义如何从其自足的理论体系转向了一个容纳了多重因素的开放体系,其中,文化问题的凸显至关重要,而在这方面,作为批判的社会理论在当代的代表,法兰克福学派引人注目。晚近的思想家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当代四大哲学思想之一(另外三大思想分别是现象学、分析哲学与后现代主义),主要依据就是作为批判的社会理论传统在当代的继承者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工作及其影响。不过,法兰克福学派所关注的层面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区别也是明显的,如果说唯物史观更多地关注经济与政治,所贯彻的是政治经济学批判,那么法兰克福学派更多的则是关注文化政治与社会心理,所贯彻的更多的是文化与意识形态批判。从理路上讲,法兰克福学派是在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如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等人深入挖掘早期马克思的哲学人本学思想的基础上,将这一思想进一步贯彻到社会文化领域。由此,早期马克思的哲学人本学思想与唯物史观的复杂关系,便成为唯物史观当代研究的持续不断的课题。
3.结构分析以及功能主义给批判的社会理论传统注入了新的资源。结构分析与功能主义是实证的社会理论与解释的社会理论的方法。这种方法与强调目的的马克思主义方法是不同的。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对自由主义作为当代最有效方法的结构功能主义的批判,正是这样一种区分的现代表现。但是,在某种程度上,阿尔都塞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及其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努力,正是对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的超越。在此前后,诸如吉登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以及大卫·哈维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提出,知识社会学及其谱系学方法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活动的渗透,以及态势越来越明确的宗教社会学向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渗透,等等,表明结构分析与功能主义已经深深地影响到了唯物史观的当代研究。
4.相关经典社会理论传统呈现的与马克思主义传统不同的社会政治视野,把一种政治复杂性带进了唯物史观的现代性研究。正如前面剖析的那样,马克思之后,经典社会理论家不仅退回到先前的自由主义乃至于保守主义传统,而且,通过他们的努力,使得社会政治思想呈现出不同于马克思主义视野的新的样态。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似乎被分解开来,一种看起来中立的社会政治观支撑起了一种中立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实证的社会理论引入了一种渐进式的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的自我进化机制,从而化解了唯物史观的激进政治立场;解释的社会理论,则致力于把资本主义把握为宗教文化传统之现代转换的逻辑理路,从而消解唯物史观的动力机制。这些努力,不断地强化一个观点,即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及社会批判理论,特别地属于初期或上升时期的资本主义。这样一来,不仅各种形式的晚期资本主义逻辑得以成立,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复归于马克思思想形成时期政治复杂性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潮也得以成立。
当然,经典社会理论对唯物史观的影响所做的分析,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同意这样的改造。不过,当我们在理路上对当代社会理论有关唯物史观研究的诸多新成果感到困惑时,如果能回溯到经典社会理论传统,也许对问题本身就可能清楚一些。至于从经典的社会理论向现代社会理论的转化及其对唯物史观造成的影响,同样值得深入研究。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7页。阿伦特曾认为“马克思以‘被社会化了的人’这样一个概念来预言的无阶级的未来社会的出现,实际上不仅是马克思经济学的前提,也是古典经济学的前提。”(阿伦特:《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孙传钊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01页)依据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的判断,阿伦特的上述断言其实是有问题的。
②关于这一时期,科瑟这样描述:“这是一个充满自信和自鸣得意的时代,也就是说,那个标志着工业革命的、充满着痛苦磨难的时代已经过去;宪章派的动乱已经平息;新济贫法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得到了克服;40年代大饥荒的艰难情景在人们的记忆中逐渐淡漠:流行一时的激进主义也已经不再受人们欢迎。总之,这整个时代似乎表明,英国已经稳步地走上了一条不断繁荣富裕的道路。”(刘易斯·A·科瑟:《社会学思想名家》,石人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26页)
③涂尔干受第二国际最直接的影响,他所看到唯物史观即第二国际的经济唯物主义。这样的误解也延伸到韦伯和西美尔。韦伯认为,“所谓‘唯物主义历史观’,尽管在其早期形式中,例如在《共产党宣言》中有着素朴的天才成分,但它仍然只是盛行于不求甚解的人和门外汉的意识中”,“所谓‘唯物主义历史观’,作为一种世界观或作为对历史实在性所作的一种因果解释,是应当加以断然拒斥的。”(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杨富斌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165页)Ken Morrison认为,尽管韦伯从马克思那里分享到有关“人在社会发展的经济层面所扮演的角色”的思想,并在这一意义上与唯物史观关联起来,但是,无论在“社会理论的本质与目的”还是在“对历史以及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理解”上,韦伯与马克思都截然不同(Karx,Durkheim,Weber,Ken Morrison,second edition,Sage Publication,2006,P76)。而且,在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全方位的批判中,韦伯并不把唯物史观的经济决定论化归咎于第二国际,而是归之于马克思本人。韦伯把马克思自己的唯物史观与第二国际经常使用的其实质是经济唯物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区分开来了。吉登斯则评论说:“当韦伯使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术语时,所指的往往是出版于19世纪90年代,奉马克思为鼻祖的大量学术著作。这些著作有时表述的观点被韦伯认为是对马克思思想的庸俗化,或者是对韦伯所认定的马克思思想的主要原则的显著背离。”(吉登斯:《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第219页)西美尔明确地讲:“唯物主义历史观根据经济形式来推论历史生活的整个内容,并用集体的物质生活条件的生产方式决定风俗和法律、艺术和宗教、科学冲动和社会结构,所以,整个历史过程本来应当包罗万象,它却把其中的局部现象夸大成唯一的内容。”(西美尔:《宗教社会学》,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1页)
④涂尔干的社会理论与唯物史观的区别也是原则性的。涂尔干强调,他把宗教的本质看成是社会的观点,不能看成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简单重复”。(《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第558页)因为“社会生活不仅是依赖于它的物质基础,而且还带有这种物质基础的标记,就像个精神生活依赖于他的神经系统和整个肌体一样。”(同上)涂尔干强调的是社会生活的整体性,并由此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只是单一性的,是不符合其功能分析方法的历史分析方法。在他那里,历史唯物主义本质上就是经济决定论。
标签:费尔巴哈论文; 实证主义论文; 法兰克福学派论文; 自由主义论文; 涂尔干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历史唯物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社会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第二国际论文; 韦伯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