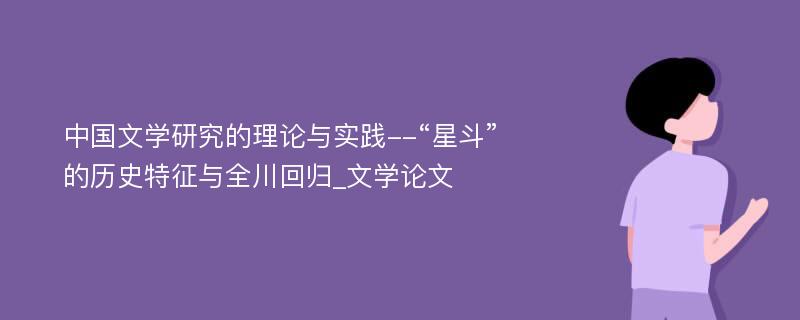
“中华文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笔谈——中华文学:满天星斗、百川归海的历史品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华论文,百川归海论文,笔谈论文,文学论文,品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多次在讲话中谈到“中华文化”“中华文学”。我认为,“此中有真意”,却绝不可以“欲辩已忘言”。这并非简单的概念,而是党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文化—文学建设发展大格局的核心理念,具有重大的历史和战略意义。践行这一理念,不仅意味着要从文艺美学思想深处,展开根本性的理论反思与创变,而且需要对学科构建、学术研究布局,进行系统、具体的再思考,做出新的定位、新的规划、新的开拓。 考古研究成果证明,中华文化具有“满天星斗,百川归海”的特点。中华文化以及作为其重要载体的中国古代文学,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多源文化—文学在交汇中交流、在交流中达成交融的产物。因此,起码应该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对“中华文学”进行悟解。 从时间上说,中华文学是一个生生不息的过程,中国古代文学是其中一个绵延久长的历史阶段,是中国近现代文学乃至当代文学的根系和前源,更是中华文学思想及理论体系建立、建设的土壤和依据。以此,今天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自然需要以大胸襟、大气魄,突破自清代以来学人们那种书斋里的“私人化”意识,摒弃“纯学术”“象牙塔”的狭隘“意趣”,从选题抉择、研究目标起,就将自己的生命汇入建设中华文化、重铸中华文学辉煌的时代洪流中。以自己的研究,再现中华文化—文学的多姿风采,寻绎其多源交汇、交流的过程,探究其共生共荣、多元交融的历史经验,在承继中华文化—文学优秀传统的同时,为铸造中华文明新的辉煌,提供借鉴,贡献思想智慧。这应该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学科价值定位。类似的话,以往也有很多,但清代人治学风习的惯性,仍使很多学者的研究理念懵懵懂懂。沧海桑田,我们同志务须打破清人“学隐”自得的精神桎梏,建立高度的理论自觉,不负学科的历史使命。 从空间讲,可以结合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理念和问题,分成几个方面: 其一,中华文化—文学本是世界文化—文学宇宙中的一个璀璨星系,不仅与其他星系相互关联,而且其内部各星体间也是相映同辉的。习近平同志提出的是“中华文化”“中华文学”。从“中华文化”上看,它取代了惯常的“华夏文化”。我个人理解,与“华夏文化”相关联的就是至今尚有人沿用的“华夷之辨”“夷夏之别”。无庸他言,“华夷”意识本身就是一种不符合史实的局限和狭隘的偏见。尽管从孙中山先生的“五族共和”,到新中国的各民族平等、团结的社会主义“大家庭”,早已在政治、法律等层面上扬弃了它,努力消除隔阂;但是,检讨我们的学科内部规划和选题,就会很容易发现,我们仍简单移植社会学、民族学的方式,将中华文学依族别区划成块,更为关键的是各自独守一隅,封闭地构建体系,“老死不相往来”。于是,对汉族与其他兄弟民族之间以及各兄弟民族之间的文化—文学的历史交汇交流,几乎无人问津。因而,既往的“文学通史”“大文学史”,都不过是汉族与兄弟民族若干孤立板块的生拼硬凑,根本没有彼此间交汇交流的历史风貌再现,更无从见出彼此的有机联系,寻不到中华民族文化—文学由丰富到丰满并走向繁荣的历史脉络。在这种现象下,显然有一种隐性观念作祟。20世纪80年代,我们曾痛批孤立的作家作品研究,把有机一统的中国文学史割成了碎片,尔后学界同仁也努力从时间维度上打通古今现当,使之贯流一脉。而目前各自孤守一隅、相互封闭的状态,不能不说是将中华文化—文学的有机整体继续从空间上碎割着。 其二,“中国古代文学”是一个时间的划分,本不应有空间、民族的局限。而我们现在的空间理念,一是出于现代民族概念,二是依于行政,并不是历史文化的。商代数千方国,周代百数诸侯,历史上都曾是部族,也是上古民族的前源。譬如现在随处可闻的“齐鲁文化”“晋唐文化”,漫言者往往不知鲁文化是周文化的沿续,齐文化乃楚文化的支系;晋为夏文化的东迁,唐为东夷文化的西徙。它们源起、演化、融合的史程如何?与之相应的文学创作特征、文学理想风神又如何?其中晋系文化美学思想既来于鲁,又有独特的文化性格,直接影响唐代古文运动的形成。对此,不要说研究,就连基础的文献搜集整理都尚付之阙如。此外,关中方言和吴侬软语的差异,梁代佛经重译造成的重大障碍所催生出的“声病说”,直接开启了格律诗的大幕,可向来无人从这个空间文化维度来考察,把原本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到唬人的程度,却依然不得要领。最典型的莫如《诗·国风》研究。吴季札观乐尚须一一辨其形神,而当下又有哪个做分别研究,探寻其怎样“满天星斗,百川归海”?不过乱炖作一锅,撒一把文学概论的“盐巴”或“新潮”西方术语的“五香粉”而已。这可以说是对中华文化—文学的一种无知浑沌,亟需大力改变。 其三,近十年来,有的同志反省我们的研究,指出不独古代文学,甚至近现代、当代文学研究都普遍存在仅有时间一维观照的“独眼龙”弊端。几乎所有文学史著述只是简单的时间序说,忘却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常识,无视文学本体的性质规定,沦为“残史”。然而,这些年大量的“空间”式选题、研究,迎合各地“文化大省”的愿望,肤浅理解,依据当下行政区划和作家籍贯设计展开,如同蜷缩在自家井底数说“我祖上阔多了”。在学理上讲,不能不说这是另一种对中华文化—文学的碎割。 文化空间不同于行政区划的截然有别,除中心区划外,两个文化空间之间有着过渡、杂糅带。这个过渡、杂糅的区域,恰是异元文化在历史上互相交汇、交流、交融之点,正可导引我们认识的切入。中华文化—文学内部如是,外部亦如是。中华文化在历史上不止向外辐射传播,为人类文化做着自己的贡献,也向内吸纳其他文化来滋养、丰富自己。这是常识,我所要说的是,这种过渡区域的文化景况与文学创作特征,这种辐射与吸收的时间、渠道和对文学的影响,及其在中华文化—文学发展中的作用,目前就是生荒地或处女地,理应成为今后很长的一个时期内中国古代文学需要大力开垦的土地。这或可以成为中华文化—文学大格局中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新的学科生长点。 其四,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作为中国文化—文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在培养理论自觉的同时,力戒“理论”浮躁。中华文化—文学的丰富性、多样性,和交汇、交流、交融关系的复杂性,决定着我们的研究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必须谨记列宁曾说过的“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可以打一个比方,中国有许多地方喜食辣,而湖南人讲究的是干辣,江西人偏尚的是鲜辣,四川人要的是麻辣,云贵人爱的是酸辣。如果只看到辣,而无视“干”“鲜”“麻”“酸”的差异,搬来某种“理论”,引申谠论,那就不唯放弃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特征和丰富性,也终归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胡扯。现在研究中一涉及宋明理学对创作的影响,不问关、蜀、洛、婺(其实还应有晋),便一体而云“雅”,全不顾“古”“淳”“典”“朴”的差异,沦为和前面说到的《国风》研究一样了。其实,于文学研究而言,包含大量历史文化信息、最具民族性的,恰恰是这些偏正词组中“偏”的部分。去年,首都师范大学左东岭教授领衔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易代之际文学思想嬗变研究”,从看似简单的历史政权更迭背后,挖掘其文化的空间交汇、交流对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发展演化的重要作用和历史影响,就非常有意义。杨义同志的“诸子还原”,则亦从文化空间探寻中华文化—文学之源,也很有价值和启迪意义。以大胸襟、大视野,扎扎实实从具体问题入手,既彻底改变陈腐观念,又一步一个脚印地推进,才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应有的科学态度。我们再不能顺着清人的轨迹,由细碎化的“雅趣”,向着粉末化的“深入”,“为学术而学术”地走下去了。 总而言之,从空间的维度上,我们确需睁开另一只眼睛,在既往研究的基础上,改变孤立个案的模式,突破封闭的疆界自守,扩大视野,转移传统研究的关注点,在中华文化—文学的历史交汇、交流、交融方面,开辟新的研究领域、方向,构成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新格局、新气象。把个人书房里的研究,投射到中华文化—文学的大视域中,汇入到时代文化—文学的发展里。 大家常说,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要“文史不分家”,假如以上所说算是“文史不分家”的第一义、一个新义的话,那么广泛吸收借鉴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文化学、民俗学等学科,关注新近研究成果,丰富研究视角,拓展研究路径,扩大研究方法,就是“文史不分家”的第二义,一个旧义新提。标签:文学论文; 中国古代文学论文; 中华文学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文化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艺术论文; 读书论文; 国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