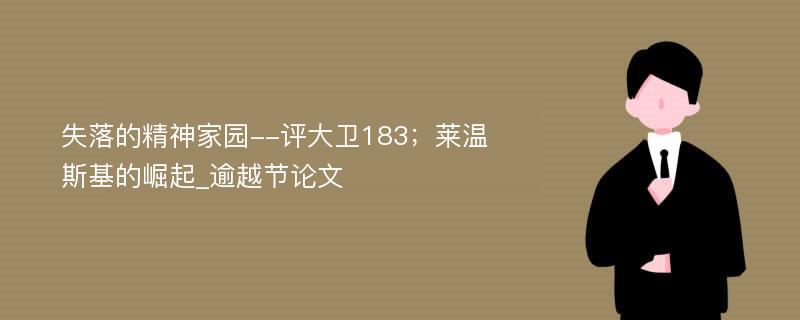
失落的精神家园——评《戴维#183;莱文斯基的发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精神家园论文,文斯论文,戴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卡恩与《发迹》
亚伯拉罕·卡恩(1860-1951)的小说《戴维·莱文斯基的发迹》(1917)被誉为美国早期犹太移民文学中最伟大的作品之一,(注:在The Jewish Writer in America:Assimilation and the Crisis of Identity,by Allen Guttmann New York: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p.13.)中,玛丽·安丁(Mary Antin)的《应许之地》(The Promised Land)(1912)与该部小说被称为“东欧新移民潮中最伟大的两部作品,形象地描述了犹太人出走沙皇俄国的经历”。)是“对一段伟大历程绝无仅有的纪录”,(注:转引自《戴维·莱文斯基的发迹》(亚伯拉罕·卡恩)中的“Introduction”,by John Nigham(New Yor:Harper & Row,Publishers,1917).)还被称作是“英语小说中对犹太性格的最佳研究之一”。(注:Sanford Pinsker Jewish-American Fiction(1917-1987)(New York:Twayne Publishers,1992),p.2.)这说明该作品不仅体现了深刻的社会意义,而且以其高超的艺术手法最终赢得了英语文学界的欣赏。据《发迹》“前言”的作者约翰·海厄姆言,这部小说1917年发行后40年内更多的只是受到人们远距离的尊敬,而没有得到人们的真正重视。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曾经生活在美国大城市贫民窟里大批东欧犹太移民的生活经历与莱文斯基的故事相似,但他们不愿意提及历史以及自己与贫民窟色彩有关的经历,并不欣赏卡恩通过莱文斯基这一人物对美国犹太移民的历史采取的那种冷漠无情的自我解剖方式,也不赞同该书对于排犹偏见进行直截了当的描述方式,因为那样容易引起新的反犹情绪从而使新一代的美国犹太人陷入困境。既然描写犹太人的书连犹太人自己都不捧场,那么在经历一战之后又面对着军人复员工作、劳工斗争、赤色恐惧等一系列问题的美国非犹太人更不会去关心一个犹太人的孤独感受了。与此同时,美国文学界更为关注的是“迷惘的一代”这一新兴的美国文学流派。因此,《发迹》这本书开始并没能跻身于美国畅销书之列,在其发行之初两年内只出版了8千册。该书直到1928年时才算受到公众的欢迎。
卡恩出生于俄国立陶宛维尔纳附近的帕布拉德,曾受过正统犹太教的熏陶,后来热衷于社会主义理论,于1882年移居美国费城。1897年,他协办《犹太前锋日报》,(注:美国犹太报业最早、影响最大的报纸,后来的贝娄、辛格等美国重要犹太作家都在该报上发表过作品。)并于1902年任该报总编辑。从1902年至1951年去世,他一直把《犹太前锋日报》作为宣传社会主义的堡垒,同时为世界犹太人的解放事业奋斗不息。
卡恩不仅用意第绪语写作,而且经过5年学习也掌握了用英语创作的技巧。早在1896年,卡恩就用英语写了小说《意克尔:一个纽约犹太人区的故事》。1898年,他发表了《进口新郎及其他故事》,1936年,他又用意第绪语撰写了5册自传《畅谈我的生活》。卡恩对美国文学的最大贡献是他的长篇小说《戴维·莱文斯基的发迹》。当然,这主要归功于他对第三代美国犹太移民生活的深刻了解以及他在《前锋报》的广泛阅历。这部小说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移民小说,而是内涵丰富,发人深思,它使卡恩成为20世纪初期最重要的美国犹太作家之一。
美国评论家莱斯利·菲德勒曾说过,“美国犹太小说家在进入美国文学的那一刻就扮演着一个多情恋人的角色。”(注:"Genesis"by Leslie fiedler,p.28.转引自The New Convenant:Jewish Writers and the American Idea,by Sam B.Girgus.(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4),p.19.)根据梭尔·利普金的观点,美国犹太文学大致存在3个明显的倾向,即,移民同化、文化适应和重新发现。(注:Sol Liptzin,The Jew in American Literature.(New York:Bloch Publishing Company,1966),p.2.)这3个倾向的划分概括了犹太文学传统在美国发生的过渡性变化。移民同化是指为美国社会所认可,文化适应意为对美国文化有选择地取舍,重新发现是指缅怀犹太传统和重新认识犹太文化的传统精神。
《戴维·莱文斯基的发迹》所着重描绘的正是移民同化这一主题。然而,作者并非单纯描写莱文斯基在经济上的发迹,而重在表现他的精神世界,虽然他在事业上获得很大的成功,但内心感受却愈来愈空虚,反而更加追念昔日的时光。从表面上看,莱文斯基出俄国似乎与圣经上犹太教创始人摩西领导犹太人出埃及的历史一样具有积极向上的意义;到达美国后,莱文斯基立即接受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很快在美国服装业独领风骚。然而,从更深的层次上看,莱文斯基的经历实际上是一个犹太人背叛犹太教传统精神的过程,背叛的种子早在莱文斯基出走俄国之前就已经处于孕育之中。
早期的磨难
1870年以后,大批波兰和俄国的犹太人移居美国,并于1880年至1920年间掀起了第三次美国犹太移民潮。当时,东欧的封建制度已经衰亡,由于地产大量集中,农民及犹太中间商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排挤。现代工厂的出现使手工业破产,农民,尤其是犹太裔农民,必须付出极其艰辛的劳动才能获得温饱。同时,犹太人还面临着集体屠杀、霍乱、饥馑、迫害、义务兵役以及居住区内的各种禁令。188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注:Alexander Ⅱ,Zar 1855-1881年在位。登基之初是自由主义者,允许犹太人移居他地,上大学,在政府机关谋职,但其末期对犹太教采取了一些不利的措施。1881年在民意党人的炸弹中殒命,使犹太人有限的解放随之埋葬。)遇刺身亡后,涉嫌被捕的人中有一位犹太妇女,这就为把罪过转嫁给犹太人提供了材料。因此,俄国政府顺水推舟,一方面为了转移当时俄国农民的不满情绪,另一方面为了对付革命者的批判和攻击,立即掀起了迫害犹太人的恶浪。沙俄政府的目标是:“三分之一的犹太人将被消灭,三分之一的犹太人将迁移国外,三分之一的犹太人将改变信仰并被完全同化。”(注:阿巴·埃班:《犹太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第296页。)1882年,沙俄政府颁布了声名狼藉的“五月法令”,明文禁止在犹太区内外建立任何新居民点,并准许农民把“有罪的犹太人”赶出去。截至1891年,在莫斯科,约有20万犹太人前后被驱逐出境。另外,俄其他各地还有50万犹太人受到同样的待遇,他们均被赶到帕累区。(注:Gerald Sorin,A Time For Building:the Third Migration(1880-1920)(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isty Press,1992),p.23.)于是,犹太人在1881年至1884年间遭到了集体屠杀及官方默许的其他暴行的摧残。俄国犹太人被迫下定决心去寻找新的家园,他们成群结队地前往西欧、英国、南美、南非、巴勒斯坦,但主要是去美国。在1891年至1892年之间,大约有107000犹太人弃俄走美。《戴维·莱文斯基的发迹》中的主人公莱文斯基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走美国的。
戴维·莱文斯基于1865年出生在俄国西北部帕累犹太区安托米尔的一个小镇,3岁丧父后,与母亲相依为命,住在一个4家合住的地下室。莱文斯基的母亲省吃俭用,把他送到塔木德(注:继希伯来《圣经》之后最重要的一部犹太典籍,其内容庞杂,卷帙浩繁,是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5世纪间犹太教关于律法、条例、传统、风俗祭典、礼仪的认知和注疏的汇编。从整体上看,它后映了7世纪前犹太教信仰、教规、礼仪、伦理等发展的历史。《塔木德》出现于公元300年左右,全书分为两部分,《密西拿》和《革马拉》。前者是由拉比犹大·哈拿西(Judah Hanassi),即犹大王子于公元3世纪汇编成书,共6卷63篇,是拉比和犹太民族的先哲们对希伯来《圣经》律法所作的讲解和阐释;后者是其后的学者们对前者进行的评述和讨论。两者共同构成了所谓的口传律法(Oral Law),以别于上帝亲授的《托拉》。)神学院接受了7年正统的犹太文化教育。莱文斯基在母亲的爱护和养育下,生活还算幸福。在他18岁那年的逾越节前夕,母亲给他买了一件新衣裳,谁知这件新衣竟给他招来了横祸。从学校回家的路上,他受到一些正在滚复活节彩蛋玩耍的异教徒的欺侮,新帽子被抢,新衣服上也糊满了鸡蛋汁。母亲看到儿子这般模样,不顾一切地冲了出去,结果不到15分钟就头破血流地被抬了回来,当晚,他的母亲就去世了。
母亲去世以后,莱文斯基不能再衣食无忧地学习塔木德了,就连吃饭都成了问题。虽然他的老师兼朋友雷伯·森德的妻子出于一时激动与同情而自愿供膳与他,但是时间稍久,便不再那么热情了,开始供膳不足,这种情况使森德尴尬惭愧。莱文斯基于是开始不断更换他的寄膳之家,直到希普拉·明斯科家接受了他和穷朋友纳夫塔利为止。现在他不再为食物而焦虑,但失去母亲后的那种孤独感却变得比以前更为真切。他每天要为母亲虔诚而热烈地祈祷3遍,希图借着对母亲的热爱来恢复过去对塔木德的感情,然而他现在所处的环境失去了以前的意义,“生活乏而无味,我渴望一种刺激。”莱文斯基对塔木德的信念产生了动摇,开始半信半疑地接受世俗的自由思想。这种自由思想最终引导他离开俄国踏上赴美国的旅程。
新出埃及记
小说起首不惜用整整80页的篇幅来刻画莱文斯基所在的这一典型的俄国犹太小镇,读者似乎可以听到其中街头嘈杂的声音,市场叫卖的声音,以及塔木德神学院学生的渎神交谈,也可以经历到安息日及其他节日的庆祝场面,体验贫穷或富裕的犹太人的生活。然而,真正弥漫于这些日常事情中的是一种恐惧和不安全的感觉。1881年和1882年反犹暴行的瘟疫在人们的脑海里还记忆犹新,镇上的沙地小区住着非犹太教徒,当一个犹太人经过时,那里的男孩就会朝他喊“犹太狗”、“杀害耶稣的凶手”,并且怂使他们的狗来吠咬。卡恩详细描述了莱文斯基母亲去世后犹太人不愿触怒异教徒的情况,送葬人数剧减,本来应该哭葬的妇女队伍极不自然地保持着沉默,仅有的几声悲泣也被一犹太老妇嘘声制止。
莱文斯基的经历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犹太史上摩西领导犹太人出埃及的历史,而莱文斯基的生活环境也使人不能不想起犹太人在法老之国埃及的情形。首先,莱文斯基早年丧父这一事实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父亲的去世使他只拥有母爱,这与摩西的童年生活相似。据《圣经》记载,摩西出生于一个利未(注:利未人系古犹太人一支。)人家,他的母亲把他放在一个蒲草箱任其漂流而下,结果法老的女儿收养了他,摩西的名字就是“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的意思,所以摩西可以说也仅拥有母爱。其次,莱文斯基在叙述他的童年时说,“在我所在种族的血液里有着一种悲伤的因素。”这句话当然是指自摩西时代起犹太人离乡背井、流离失所的命运,使主人公的故事承载了犹太历史的重荷。其三,莱文斯基所在的地区与“法老之国”埃及相似。莱文斯基谈到俄国犹太人于19世纪末移民美国的浪潮时用了两个看似乎常、实则含蓄的字眼儿,他说,“这就是已经酝酿了几十年的新出埃及的肇始,”他终于也向这股波及全国的移民浪潮屈服了,“并不是因为它是一块流奶与蜜之地,(注:指“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选人、希未人、耶布斯人的地”,见《圣经》“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八节。迦南地指现在的巴勒斯坦。)而是因为它是一块充满神秘、离奇的经历的土地。”“新出埃及”与“流奶与蜜之地”两词显见是指摩西带领犹太人脱离法老之国前赴上帝所应许的迦南之地。
莱文斯基曾是安托米尔塔木德学校的佼佼者,然而一旦离开家乡到了美国,他宗教情感即刻被美国的现代生活所化解。他一踏上美国码头,就学到了美国的实用主义,这是他的美国犹太同胞强加给他的重要一课。当他解释自己会读塔木德的时候,那个老奸巨滑的犹太工头说,“我看得出来,可那在美国没有市场。”莱文斯基第一次有了犹太书生百无一用的亲身体验。为了谋生,他理去边发,剃掉胡须,穿上西服,打上领带,任由自己的感情浪漫地流溢,并很快屈从于性要求。他逐渐开始了美国化的历程。
在卡恩的眼里,美国与欧洲之间有天壤之别。他写道,“犹太血汗工厂的生活相当艰苦,不过普通犹太移民仍然感到,与他们在旧大陆上所遭受的苦难相比,美国就是天堂。”(注:Abraham Cahan,The Education on Abraham Cahan,pp.400-1.Cited from The New Convenant,p.71.)犹太人在美国所享受的政治自由是他们弥足珍重的,“多可贵的政治自由啊!在这里,一个人享有作为人的自由。”(注:Ibid.,p.71.)而在旧大陆,一个人却不成其为人。由于这种政治上的自由,莱文斯基对美国怀有深深的忠诚。他在一场音乐会上的经历被认为是多数美国犹太人的典型写照。当时,观众表情淡漠,并不为歌剧主题或意第绪语歌曲所动,但当美国国歌响起时,所有的观众,其中多数是犹太人,都肃然起立,“他们似乎在说:‘在星条旗下我们免受迫害,在美洲大陆我们重建家园。’”随着乐队演奏,犹太人深情地齐声颂唱“我的祖国”。
美国文化继承了其移民始祖的传统思想,强调一种竞争和苦干的哲学,鼓励人们奋发图强,获致成功,视生活为弱肉强食、你死我活的竞争,认为“上帝的选民”就是竞争的胜利者。美国这种传统思想价值观充分体现在赫伯特·斯潘塞“弱肉强食,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学说中。小说中莱文斯基的故事可以说是这一理论的形象阐释。莱文斯基对世俗的文化教育有着强烈的渴望,在美国这个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泛滥的地方,莱文斯基身上逐渐产生了一种足以令本杰明·富兰克林也会感到难为情的实用主义,所以他自然而然地接受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斯潘塞的社会学理论,一旦有发财的机会,他便放弃了对知识的追求,甘受金钱及物质利益的驱遣。莱文斯基的朋友诺德尔曼把这个世界比作“一个大的养鸡场”,所有的鸡互相抓啄,为了抢得一份有限的谷粒。而这何尝不是莱文斯基的人生哲学!终于他适时地抓住机会,一蹴而起,登上了商业成功之路。他凭着自己的才干不断发展,在服装业纵横捭阖,成为一个资产高达200多万元的美国大亨。
莱文斯基的确在美国实现了自己的社会价值,在一定程度上讲,美国就是莱文斯基所寻觅的上帝的“应许之地”。
摩西逃出埃及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逾越节。(注:犹太民族的主要节日,犹太历以此节为一年的开始,约在公历三、四月间。据《圣经·出埃及记》记载,摩西领导以色列人摆脱埃及的奴役,上帝命犹太人宰羊涂血于门楣。天使击杀埃及人时见血记的人家即越门而过,故称“逾越”。逾越节时,人们腰束带子,手持棍枝,烤吃一只满周岁且无残疾的羊羔献祭,同时吃无酵饼和苦菜,重温祖先离开埃及时的仓促情景。)上帝在逾越节之夜巡行各地,击杀埃及人长子,使得法老惊惶失措,答应以色列人出埃及。以色列人为纪念他们的祖先摆脱奴役,走向自由,每年都要庆祝逾越节,感谢上帝馈赠给他们的自由。小说最后的逾越节就是莱文斯基最终得到上帝的帮助、扎根于“应许之地”之美国,是莱文斯基与美国达成新契约的象征。
莱文斯基发迹之后,虽说不大再去犹太会堂,却念念不忘逾越节,究其主要原因,是其母亲当时死于逾越节前夕。对他来说,逾越节不仅是犹太人的传统节日,而且成了他悼念母亲的日子。所以,他每年至少去会堂两次以示纪念,只是自从读了斯潘塞的书以后,便极少去犹太会堂了。莱文斯基与范妮订婚之时,正是他春风得意之际,出于对母亲的怀念和对自己事业成功的喜悦之情,他又到了一座美国犹太会堂。在这里,卡恩为说明莱文斯基与美国的新型关系,使用了较强的透视比较手法。此会堂取名为新安托米尔,使其与莱文斯基家乡的“旧”安托米尔会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新会堂里不再有正统犹太会堂的气氛,其过分艳丽的壁画和光线过强的照明设备不能给人以神圣感;会堂里仍有神职人员,但其穿戴之齐整远胜于旧会堂的同侪;“旧”会堂里的莱文斯基虔诚奉主,醉心旧约,而新会堂里的莱文斯基已成为不可知论者,更兼信奉达尔文主义与斯潘塞的社会学理论;在新会堂里,莱文斯基的心中不再有“一丝一毫的宗教情感”,倒是对作为美国公民的责任感有一种宗教式的热情。
显而易见,小说在最后安排逾越节晚宴是别有深意的,一方面使莱文斯基的精神支柱在“热热闹闹”的逾越节气氛中轰然崩塌,另一方面使莱文斯基与美国之间的新契约之戏达到高潮。
两个半个自我
摩西领导以色列人出埃及时勇往直前、义无反顾地奔向上帝的“应许之地”,而莱文斯基叙述他移民美国的经历时总是持一种矛盾的态度。在小说起首,莱文斯基宣称,自己从1885年抵达美国时兜里只有4分钱,到现在以200多万的身价在美利坚合众国车衣行叱咤风云的这种变化也不过尔尔。“当我默察内心的自我时,却发现自己骨子里与三四十年前还是一个样。我现在所拥有的地位、权力以及唾手可得的世俗欢娱等等对我来说似乎都毫无意义。”这说明,无论莱文斯基怎样努力,如何成功,他从根本上还是没能真正融入美国社会并成为其中的一员,因为莱文斯基没有忘记俄国,他梦绕魂牵的故乡安托米尔就在俄国;他也并不真正忠诚地热爱着美国,因为他个人所受到的传统教育毕竟不同于美国本土的文化底蕴。可以想见,莱文斯基的感情寄托和精神追求在美国的失落就是他在卷首喟叹的根本原因。
莱文斯基感叹自己在事业顶峰时反倒在精神上失去归宿,“我常常渴望着与来自我家乡的某些人有一次披肝沥胆的谈话。我曾尝试过与他们重修旧谊,但他们大多生活贫困,我的财富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我们交流的障碍。”追本溯源,造成戴维·莱文斯基与他人之间这种难以亲近的关系的原因在于他幼年时期的痛苦遭遇,他在商业上的成功只是加剧了这种关系的发展,财富和地位使他与他所期望之爱情和友谊的距离更加遥远。在小说《发迹》的最后,莱文斯基宣称,“我永远不会忘记过去的痛苦生活,不能逃脱过去的自我,我的过去与现在很不相称。戴维那个曾经在一个犹太会堂前仰后合地诵读塔木德的穷小子,好像在深层次上与如今路人皆知的车衣业主戴维·莱文斯基有更多的相同之处。”
莱文斯基来到美国之前,就已经分裂成两个自我了。半个自我是在母亲和老师兼朋友雷伯·森德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是那个热爱犹太传统、虔信上帝、注重家庭生活、对他人也很真诚的莱文斯基;另半个自我则是受其友纳夫塔利和初恋情人玛蒂尔达的启蒙而分裂出来的,是后来受现代思想影响、世俗而实际、对上帝的存在也抱着怀疑态度的莱文斯基。他自称自己从前半个自我“蜕变”到了后半个自我。
莱文斯基的母亲是一个传统的犹太妇女,丈夫去世后,莱文斯基成了她唯一的精神支柱和生活乐趣,是她的“小豆豆”,是她的“安慰”,是“她的皇冠”。她从不因为莱文斯基做了错事就像其他母亲一样惩罚他,但她因生活之艰辛而遭受的磨难比任何惩罚都令莱文斯基痛苦,她为生活拼命挣扎的勇气也早已潜移默化在莱文斯基的性格里。莱文斯基曾经天真地问母亲:“妈妈,别的妈妈打自己的孩子,你为什么从来不打我?”他的问题使母亲开心地笑了,“我可怜的宝贝,因为上帝已经让你吃了许多苦头。”莱文斯基的母亲是一个性格坚强的女性,她宁可自己吃点苦,也要把莱文斯基送到塔木德神学院学习,她要使莱文斯基成为一个“优秀的犹太人”。为了这一目标,她辛苦劳作,省吃俭用,不愿让莱文斯基受半点委屈。当看到莱文斯基沉迷于上帝的神性世界中时,她抑制不住心头的喜悦,“时不时地感叹一声,似乎喜悦的暖流从她的胸中自然流淌出来。”在母亲的宠爱和教导下,天资聪明的莱文斯基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在学校里脱颖而出。
雷伯·森德是莱文斯基的老师,一个正统的犹太教学者。他视莱文斯基如同己出,对其恩爱有加。当莱文斯基母亲去世时,森德和妻子首先领养莱文斯基到他们家“寄膳”;当他的妻子对莱文斯基感到厌烦而苛待莱文斯基时,他宁可自己少吃点也不愿莱文斯基受太多的委屈。不过,他对莱文斯基在犹太教精神方面的指导更为重要,使他深悟塔木德的精髓。塔木德主要是古代拉比对良知、同情及宗教职责等等的讨论,是关于“‘人与上帝’之间、‘人与人之间’的讨论”。塔木德被认为是犹太教的重要典籍,是比之世俗知识艰深奥妙得多的学问。“你能测量海的深度吗?你当然也无法测量塔木德的深度。”森德曾对莱文斯基这样说过,“乖戴维,学习上帝的神谕吧,再没有比这更幸福的了。财富算什么?痴人说梦。这个世界算什么?过眼烟云。唯有另一世界更为真切实在,唯有善行和神学才有切实的价值。”善行和仁爱正是犹太教要旨,森德孜孜不倦地对他灌输这一重要的精神,“如果一个人不善言词,不要讥笑他,而要同情他,……你要与傲慢、嫉妒及各种邪恶的心理倾向作斗争。记住,所有学问的精华可以用‘爱邻人如己’一言以蔽之。”
雷伯·森德教导莱文斯基说:“你就像我的儿子一样,戴维。要善,要全心全意敬主,如果不为别的什么,就算为我之故。总之,不要两面三刀,切勿口是心非,切忌阿谀之词。”然而,莱文斯基与上帝的亲密关系没能持续多久,因为他遇见了纳夫塔利和玛蒂尔达。
“我—它”关系
现代著名犹太教存在主义哲学家马丁·布伯的相遇哲学用“我—你”和“我—它”两种关系来说明人与他人之间的联系。“我—它”关系把他人物化,与我产生关联的他人都沦为我经验、利用的对象,是满足我之利益、需要、欲求的工具,在“我—它”关系中,我与他人之间不可能建立真诚恳切的关系。而在“我—你”关系中,我和他人双方都是主体,把自己毫无保留地交给对方,彼此之间是一种平等、互利、直接、对话的关系,是一种基于对所有人的价值尊重的关系。“我—你”关系的最高表现形式是人与上帝之间的永恒关系。戴维·莱文斯基幼年时在母亲和森德的教导下,热爱犹太传统,与他人和上帝之间曾短时期地呈现“我—你”关系,可惜好景不长,当他遇到纳夫塔利和玛蒂尔达之后,这种关系便为之消褪,代之而来的是他对他人的“我—它”态度。
纳夫塔利是一个自由思想者,对莱文斯基的成长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也读犹太典籍塔木德,但更多的时间是在读现代科学、诗歌、小说以及对犹太信仰的评论。虽然莱文斯基不敢涉及此类书籍,但对纳夫塔利就此类书内容的介绍大感兴趣。虽然他每次听到这些东西后都不免要诅咒一番,但仍然实实在在地喜欢它们。在纳夫塔利的启蒙下,莱文斯基开始接触到一些亵渎上帝的言语。他不敢对上帝进行思考,但已经对上帝的存在发生了怀疑。他再也无法全心全意地与上帝进行对话了,“我与上帝的交流现在已极为稀少。他对我的学习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感兴趣了。我现在读书时,上帝的荣耀不再。”莱文斯基企图凭藉对母亲的热爱和恢复其过去对塔木德的情感,但却毫无效果,“对塔木德的兴趣已丧失殆尽,那种魅力已无可挽回地消失了。”在失去犹太教精神支柱之后,莱文斯基发现自己陷入了孤独之渊。他与上帝的“我—你”关系戛然而止,上帝因为他的思考和怀疑以及他的疏远和异化而远离了他。莱文斯基进入了“我—它”关系的漩涡之中。
纳夫塔利是莱文斯基思想上的启蒙者,莱文斯基因他的引导对上帝的存在发生怀疑;而玛蒂尔达则是莱文斯基情感上的启蒙者,莱文斯基因她的诱惑对上帝失去了诚心,与上帝之间丧失了爱的交流。玛蒂尔达不是一个平凡的犹太女性,她已接受了俄国世俗的自由思想,并鼓励莱文斯基也走出宗教的束缚,“你为什么不试着学一学俄语、地理、历史呢?你为什么不愿意成为一个接受正规教育的人呢?”玛蒂尔达这样对莱文斯基说。她觉得像莱文斯基这样一个聪明的小伙子不应当不省世事,懵然无知,希望莱文斯基成为自己的该拉忒亚,(注:塞浦路斯王皮格马利翁雕刻的少女像。他雕好以后就爱恋上了这尊雕像。希腊爱神阿弗洛狄忒看到他感情真挚,便给她以生命,使他们结成夫妇。)不仅鼓励他接受世俗知识,而且愿意给他提供去美国的路费。
莱文斯基被移民美国的浪潮所吸引,给森德透露了也想去美国的想法,雷伯大吃一惊,“去美国?主啊!你到那时会变成异教徒的。”但他没想到,莱文斯基时已经从心理上蜕变成“异教徒”了。
莱文斯基在美国一直有一种强烈的孤独感。“你在这个世界里是孤身一人!”他在事业上升时这样对自己说。“我的商业生涯使我坚持这样一个信念,家庭之外的人类世界充满了虚伪和欺诈,犹如荒野丛林一般充满了残忍和自私。”他自称是“一个孤独者”。他的朋友梅耶·诺布尔曼对他说:“你比我所知道的任何单身汉都要孤独。你是一个孤儿,可怜的孩子。你经营着不错的生意,有很多钱和各种娱乐方式,但你仍然是个孤儿。你还是个孩子。你需要母亲的关怀。”在小说结尾,他仍旧重复着这个话题,“我很孤独,我遭受着孤独和悲伤的折磨。”
莱文斯基的这种孤独感正是他与他人之间“我—它”关系发展的结果。他初到美国时,一位好心人对他说:“犹太教在这里没有多少机会,……美国不是俄国。这里没有怜悯,没有同情。”一针见血地指出代表善良和爱心的宗教情结在美国没有市场,意即“我—你”关系在美国是不易建立起来的。就莱文斯基的情况而言,他在俄国的异化根源很快便导致了他背离犹太教,接受了达尔文主义及斯潘塞的社会学理论,把人类社会当作一个你死我活、强食弱肉的荒野丛林,自然难以进入“我—你”关系。因此,莱文斯基并未遵守他对雷伯·森德许下的“决不放弃塔木德和犹太教”的诺言,很快便远离犹太会堂,放弃了塔木德,从而确立了“我—它”关系模式。
莱文斯基在美国的发迹主要是指他自己在商界的成功。但是,他在物质上的成功背后是精神上惨痛的失败。莱文斯基与他人之间往往呈现出“我—它”关系,他在实现其自我价值时所表现出来的个人主义就是“我—它”关系的具体呈现。他到美国以后曾说过这样一番话;“我们大家或多或少都在演戏,关键在于,我们的目的何在,我们能否做出‘令人信服的表演’。”这便是“我—它”关系的最好注解,如果人们不是推心置腹,以诚相待,那便会形成互相利用的关系,从而坠入“我—它”关系的泥淖。莱文斯基的这一“表演”原则背后当然有着其深刻的社会文化涵义,它是美国社会你死我活的竞争的产物,和美国文化派生出来的心理饥荒和精神空虚有关。对物欲功利的追求极可能导致精神价值的沦丧。在弥漫着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美国,莱文斯基的自我在“我—它”关系中找到了认同,他甚至有一种“似乎达尔文和斯潘塞盗袭了我的发现”的感觉。把包括犹太教在内的精神价值和自己的感情生活统统置于这种实用主义的阴影下,结果发现,他不能融入美国文化,又不能回到犹太教中,处在一种悬置半空、进退维谷的境地。尽管他在商界取得成功,个人生活反倒不如以前充实,他与他人之间没有肝胆相照的感情交流,他与上帝之间丧失直接对话的信任基础。故此,莱文斯基的生活最终还是空虚而孤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