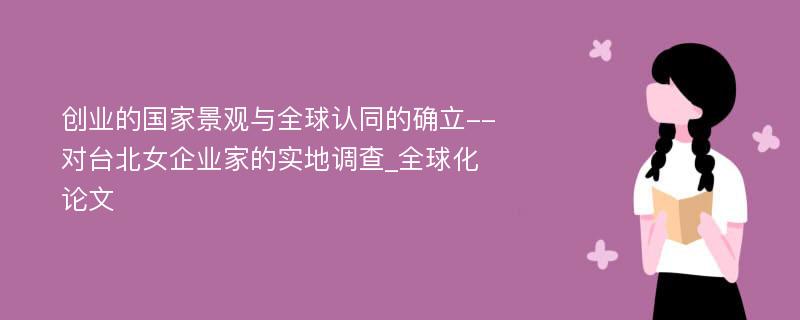
创业的民族景观与全球化身份的建立——对台北女性创业者的田野调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北论文,创业者论文,田野论文,景观论文,身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所有的社会中,个人身份(Personal Identity)都交织于权力。因为每个人所建立的身 份作为一种社会动力(Social Agent)会有力地作用于其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以及他(她)改 变这些结构的能力。因此,人类学家艾里克.沃尔夫(Eric Wolf)在他的权力理论中,把其第 一种权力模式定义为“个人所固有的潜力或者能力”,①(Wolf,1999:5)即:权力决定一个 人的自身能力和身份。据人类学家苏珊·格林海尔(Susan Greenhalgh)的研究,70年代台湾 妇女建立自己社会身份的能力非常有限,在很多情况下只好以从属的身份依附于家族企业, (Greenhalgh,1994:759)她们缺少最基本的权力。然而到了2000年,有些台北妇女却已经 做了 老板并握有实权。这些企业纯粹是她们自己的,其中没有她们丈夫的投资,她们不再依附于 婚姻和丈夫的家庭。她们在成长为女老板的过程中通常会建立新的社会身份。这些新的社会 身份通常又会成为一种新的社会资本,有时这一新的资本会使其家庭不得不按她的规矩行事 。于是女老板身份便具有了增加妇女权力的潜在力量,出现在个人身份层面上的这种情形是 非常重要的。
我自1999年8月起,一直在台北的女老板中间做田野调查,以便进一步理解创业与妇女权力 增加之间的关系。我在做全面调查的同时,对121名女老板做了简要访谈。她们是用随机抽 样的方法在台北市比邻而居的居民中选出的。此外我还对30名妇女做了深入的生活史访谈, 并花了大量时间对其中几名妇女的社会背景进行了解以充分认识她们的主观生活世界。我发 现,这些台湾妇女的身份观念出于她们的自我意识对多元文化渊源的搜寻,而这些渊源正在 从地区性转向全球性。然后,她们的身份就成为其人际关系社会资本的重要资源。
处于全球化前沿的人们,包括企业家们和商界人士,在认同自身身份时不再仅仅涵盖自己 的乡土社区和民族文化,还包括了他们对世界公民的理解。仅举其中两个例子:一位把自己 身份从全球转向台湾土著的咖啡店老板,和一位在台北和巴黎都拥有店面的时装设计师在建 立自己的个人身份时,作出了在家庭、民族、国家和被空间维系的文化意义上的另类选择。 这些妇女如何看待她们地区的和全球的身份?她们的身份建立过程在多大程度上仅仅是一种 个 人行为,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全球化结构的产物?又怎样反映了全球化过程中政治经济权力 的不平等?
全球化和身份认同的理论方法
全球化和身份认同间的关系已经成为社会学、人类学和相关社会科学的一个主流课题。(e.g.Featherstone,1995;Giddens,1991;Massey and Jess,1996;Meyer and Geschiere,1999) 这一领域内的主要理论家——印度人类学家阿加·阿帕杜拉(Arjun Appadurai,1996)指出, 在全球媒体和大众迁移时代,想象力已经变成了现代主观性(Modern Subjectivity)的基本 特征。他使用了“民族景观”(Ethnoscape)这个有地理学意义的词汇,从而超越了地域民族 的界限,并扩展至根据想象力而建立的全球身份。他是这样定义这个词的:
我们生活在其间的瞬息万变的世界是由形形色色人等构成的景观。其中的旅游者、移民、 难 民、被驱逐者、外籍工人、以及其他流动群体和个体构成了这个世界的一个基本特征,这个 特征好像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影响着各国和国际政治。这并不是说,已不存在相对稳定 的社区和亲属组织、朋友关系、职业、休闲、以及出生、居住、和其它往日形态。而是说, 对于这些稳定现象的游离无处不在地充斥在人的动机中,因为越来越多的个人和群体在应付 着被迫迁移的现实或打算迁移的梦想。进而言之,如今这些现实和梦想正在更大范围内起作 用,因为印度村庄里的男人妇女不仅打算到普那或马德拉斯去,而算计着搬迁到迪拜和休斯 顿去。而且斯里兰卡的难民发现他们到了瑞士和印度南部,正如越南的赫蒙族人被驱赶到了 费城和伦敦。(阿帕杜拉,1996:33-34)
阿帕杜拉赞美全球身份的出现,就像有些人类学家从麦当劳在东亚市场的扩张看全球化。( Watson,1997)相反,阿里夫·德里克却把全球化视为不过是新伪装下的老牌霸权主义、美帝 国主义的重生。他认为,美国多元文化主义的产生是因为跨国公司想适应全世界不同文化的 生产商和消费者,使美国向全世界输出经济、政治、文化的做法合法化。(Dirlik,1997)
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结构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有些有殖民地意识的个人要借助与殖民 政权有关的身份来为自己建立个人主观性(Personal Subjectivities)。这种过程影响了多 种民族主义的发展。(见Anderson 1983)阿尔及利亚人在法国寻求教育与现世主义,波多黎 各人认同美国都是此类例子,台湾亦不例外。在本论文中,我选择两个例子来印证在全球化 和建立个人身份上存在的限制。
加尔米咖啡馆:丝绸之路上的驿站
权力获得的最基本形式处于沃尔夫权力模式的第一级。做老板是一种自我实现的计划(A Pr oject of Self-realization)(1958)。对妇女而言,条件更加有限,其经营活动可能连生存 需求都满足不了。要想从经营活动中赚到足够的钱,通常需要雇佣工人,从他人的劳动中获 取剩余价值,然后才可以完成志向更高的自我实现计划。我访谈过的妇女们的生活计划说得 上是五花八门,诸如照顾流浪狗,赞助西藏的喇嘛寺,挣钱支持自己的离婚计划,或者开始 搞女同性恋,不一而足。我在此举例描述一个自我实现的计划,有意识把讨论引向全球化与 地区身份的问题。
梅英开了个“加尔米咖啡馆”(Gulmit Cafe),这是一个离台湾师范大学不远的一条狭窄巷 子里的咖啡店。她的咖啡店不仅向顾客提供咖啡和谈话场所,而且,正如其名称所示,是一 条丝绸之路上的驿站,一个文化交流的中心。墙上悬挂着印度和中东的充满异国情调的织品 ,她偶尔也展示些当地的手工艺品。逢周末,还举办多种多样的歌舞表演:巴厘的民间舞蹈 ,民谣吉它演奏经过改编的原住民民歌,甚至时不时还有个把台湾正当红的原住民歌星去那 儿演出。梅英明确表示自己不是老板。“我觉得我的经验跟别人不太一样,”她说,“我想 ,我只是过个人的生活,我不是大老板。”
像许多台北企业家一样,梅英讲述了一个艰苦创业的故事,出身贫寒的女孩如何最终在都 市中成长并发现乐趣。梅英起初的经历是比较黯淡的。她在学校时不能适应日常功课的压力 ,不是一个好学生。她略微夸张地谈到她最初开始走上社会时如何在一年之内更换了10多次 工作,她在贸易公司、会计事务所、大公司的办公室中尝试了五花八门的工作。她的叙述清 晰地表明,她的工作使她异化(Alienated)。她把不能适应公司环境归结于自己的个性。
然而她有许多做自己生意的朋友,开画廊、咖啡店、或者时装店什么的,她常常去帮忙。 “也许受到了她们的影响,”最后,她开了一个自己的时装店,叫做“吉普赛人”,在那里 她 卖各种各样的东西,家具、服装、布料。到这时,她已经领略到创业所带来的独立感,尤其 是与坐班的那种循规蹈距相比。她把自己的个人风格与邻居们的对照,特别强调使自己别具 一格的那种出自想象的全球特点:
很多人会问我,我是哪里的人。他们不觉得我是台湾人。我说:“不会,我是这里的人。 ”但是他们猜我是韩国人啊,日本人啊,或者是东南亚的人,或是什么什么人。因为我所有 的服饰都像……我那时候没有像现在。那时候,很多创造性的活动都是在衣服上面。我会变 来 变去,把一条布拿来做衣服然后这样,这样。然后我怕别人的眼光。所以有时候我住在东区 ,然后我坐计程车到公馆下车。然后,我从那个菜市场经过,看过很多的目光。我的邻居觉 得我在作怪。他们觉得这样子很不好,好像跟这个习俗不太一样。我没有任何的想法。我觉 得这是别人的,我只是想做我自己。喜欢我的客人,他们很赞美我,因为他们没有这个勇气 。
这个店给了她国际经验,因为她经常得去印尼和其它东南亚国家采购。她夸口她总是独自 旅行,寻找供货商,甚至不要人帮忙自己把货扛回来。到这时,她的生活发生了戏剧性的转 折 。她和她的一个男顾客恋爱了。她的健康不断恶化,这个城市的当局因为修建道路提出购买 她的店。在她情人鼓励下,她“休息了一年半。”
她和他结了婚,并生了个儿子。然而在访谈中,她略去了一部分故事,也许是因为痛苦或 窘迫;或者“婚姻”说法本身就是捏造的,为了掩饰未婚生育的难堪。她直接说到这个关系 的收场:
后来圣诞节的时候,我等了他三天三夜,然后他公司的一个女性朋友,通过我的朋友跟我 讲,说他结了婚……。我对爱情不信任。我们有很多争吵。他认为我给他人生不一样的生命 的一个空间……他好像很喜欢我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他很努力的要排除很多困难。然后, 我也通过他的老婆,还有她的哥哥,都告诉说他是想一辈子跟我走。或是他都一直跟我这样 讲。但是,很多争吵。后来,我发现我的身体慢慢好了。我觉得这样下去是没有希望的,因 为他解决不了他的问题……我就决定我要出来开店。
我就回来改开那家店,我做了很多手工。都是自己画图,自己钉钉子,自己去做。然后, 我做很多马赛克,自己在墙壁上画彩绘,那个地方的色彩,有很多神秘的东西,像印度,像 尼泊尔,像土耳其,可能说是西班牙、地中海的风格。我觉得我上辈子是个画家。
工作中,她油然生出一种对丝绸之路和巴基斯坦的精神向往,虽然她从来没有去过那个遥 远的异邦。
我刚开没多久,就来了几个朋友,外国人。他们刚好从加尔米回来。他们去过那里,在巴 基斯坦,它是一个地名。我当时取这个店名是因为我一些布料是从那里过来的。我虽然没有 去过那个地方,巴基斯坦,它是丝绸路上的一个驿站。那里有许多民族,民族性也强悍。因 为我在高中等历史课本上看过那个地名。我去查过地图,就把它翻译成中文。可是,我根本 没有去过那里,我也没有看过图片。我真的不知道那里是怎样的状况。结果,他们来了,他 们很惊讶。
刚好,那些朋友从那里过来:“好奇怪的地方,很神秘。”我刚好穿一个莎丽。他们就觉 得我就是那里人,我可能去过那里。他们很惊异我没有去过,也没有看过照片。然后,他们 找资料给我看。我说,“噢,是这样子。”我很难去解释这个东西。那,可能我自己去过, 上辈子去过。我没有办法解释这些。
她的酒吧,尤其是在她后来提供歌舞表演以后,开始在台北名声大振。《中国邮报》报道 了之后,除了当地顾客以外又开始吸引旅游者。她向我形容她的管理风格,这种风格和她现 在的店的管理方式非常相似。
我那家店,音乐方面是世界音乐。是因为我另外的一个男朋友,他一直收集这一类的东西 。我有很多音乐是世界音乐或是原住民的音乐。然后,我就打扮成这个样子,然后去跳,或 许我看录影带,belly dance(肚皮舞)。我觉得很好玩。我也会叫朋友来跳舞,来玩。
随着媒体的不断曝光,她的生意日益兴旺,而且几乎每个周末,酒店和旅游业经营人士都 带来许多希望来喝啤酒看演出的旅游团。梅英的“全球”身份,正如阿帕杜拉的全球景观中 的居民的,显而易见是出于想象力。她认同想象中的东南亚、印度、巴基斯坦。在想像中的 这些地方,她把自己从在另一种情况下使自己感到压抑的公司和社会规范中解脱。她甚至声 称 她前世曾经到过加尔米,而且在使用“全球身份”作为一种社会资本上取得了非同一般的成 功。通过对其他民族的认同,她才好穿着莎丽赤着脚在台北随心所欲四处游荡。反过来,她 的咖啡店的全球性质也吸引了一些固定的常客,一些希望从公司环境中逃脱一两个晚上的她 的同类。这给她带来源源不断的丰厚收入。
与其他许多在国民党时代受教育并认同美国的现代性的人们不同,她抵制美国化(American ization)。她为几乎没有美国人光顾她的店感到骄傲。她说:“比较有趣的是,去那边的美 国人很少,几乎没有美国人。其实美国人在台湾是很多,尤其是师大。可是美国人很少去我 的店,只有一、两个。其他的是法国人比较多,然后是英国、非洲。”
在她的独白中,提到美国人的次数不多,美国人被说成为强权人物,他们的权力使其他人 害怕。她这样描述一个人:
有一次,有一个美国妇女,很像玛丽莲·梦露,她有一个保镖。到台湾来,不知道做的怎 麽样的生意,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把她带到我店里来。我也觉得,他们就不合适。在我的店 ,我是常常不穿鞋子,赤脚走来走去,还坐地上。我还有一空间,就是我们都要把鞋子脱掉 坐在地上。我是觉得,好奇怪的人,这些人不是在我的空间出现的!可是他们不断地来。然 后,他们要我表演。要我们那个气氛。我的压力很大。我觉得,(叹气)我没有办法接受。后 来,我跟China Post讲,不要再刊登我的广告。我没有办法做下去。他们再也不登我的店名 电话号码什么的了。(叹气)
她店里的气氛变得更加具有私人性质,变成一个探索波斯和佛来芒柯(Flamenco)民间舞蹈 的场所,一群固定的顾客后来成了朋友。然而,不久这个店就被迫关张了。楼上的邻居抱怨 吵闹,经常报警要求他们停止音乐表演。最后,这些邻居告她无照经营,使她完全无法再坚 持 下去。她是如此需要这个店,以至于她觉得这是她生命中最沮丧的时刻。她的创业之梦被摧 毁了,她发誓再也不做生意。然而,因为她的强个性和难以协调的个人风格,为别人工作的 尝试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这时她遇到了另一个男人,但是并不太情愿和他在一起。她这样 说:
我那时候,就认识了我这个男朋友。他是鲁凯族,屏东的。因为他是做音乐的……我们遇 到第二次,刚好我被fire掉,那时候他在旁边帮我。那时候,我真的是……我也没有想到情 爱上面,我一直把他当作普通朋友。
他像她的许多别的朋友一样,鼓励她回到以前的生意中去。不情愿地认了命,她又开了个 小酒馆,她仍然把它叫做加尔米咖啡馆。但这次并不是以往的再现。而是脱胎换骨般从非常 全球化转向了非常本土化。她把自己新酒馆变化了的管理风格描述为回家的感觉:
我举办了那些活动之后,又回归到台湾本土的东西。因为在第一家pub,都是世界音乐。什 么印度,什么印尼,什么国际性的一些音乐。回到这个也是因为我的对象的关系。因为他是 原住民。台湾有九大族群,原住民的族群。其实以前这个店我接触过一些。我虽然没有接触 这个男朋友,但是我已经认识一些原住民的朋友。他们就是做一些艺术活动,我稍微有一点 了解,但是在这家店,透过他,我了解更多,接触的人更多。在台北的一些原住民朋友需要 做一些社运,社会活动,艺术活动,几乎都来这一家店。然后,我有一些客家族群的朋友。 所以我就收集了那些东西。我是纯粹回了头。因为以前那个是一个梦。过去都是什么土耳其 , 印度,中东的。那些都有了,我又回头,有扮原住民的演唱,扮客家音乐演唱,然后……。
与梅英三个小时的访谈所获甚丰,且令人兴趣盎然。就权力获得(Empowerment)而言,经营 企业使梅英在三个层面上获取了权力:她得到了组织权力。她控制自己的企业,就投资和分 派劳务做决定。她还获得了处理对外关系的权力,尤其是与男性关系的权力。值得一提的是 ,当她遇到她的第一个情人时,仍相信浪漫爱情及女人得依赖男人的观念。当那个关系失败 了,她立即回到生意中去。商务活动给了她得以拒绝以往关系的经济基础,使她具有了经济 自主权。她不仅养活了自己,还让她得到现在的鲁凯族情人,但是拒绝结婚。经济自主在处 理个人关系方面给了她更大的空间。
然而有意思的是,梅英自己似乎在第一种权力模式那里发现了最大的乐趣,即“一个人仿 佛与生俱来的潜能和能力层面”。(Wolf,1999:5)她对自己在没有旁人事先指点的情况下独 立 做事的能力感到骄傲,无论是在雅加达街头寻路,搬动家具,绘画,或者是学会肚皮舞。对 她来说,经营企业不仅仅是为了挣钱,而是一种完整的生活方式,一种自我实现的手段。在 她拥有的每个店,她都通过内部设计以某种方式表达了她认为有意义的东西:一个设有供人 寻求时装模特感觉的“吉普赛人”服装店,以及一个让她在其中玩文化主题的、叫做加尔米 的酒吧。在这个店的首次轮回中,她玩的是中东主题,向巴基斯坦认同,甚至唤起了前世居 住在那里的感觉。在那个店的二次轮回中,她让自己“返回台湾”,通过内部装饰、音乐和 一个原住民情人找回自己对台湾的认同。
梅英的非正统的生活态度集中地体现在她打扮自己的方式上。她对自己的异于其他台湾妇 女的装扮非常得意,表现在她叙述中提到的莎丽服,肚皮舞装,还有赤脚。这种从最基本层 面获得的权力对某些人来说可能会不屑一顾,但是却使她的生活充满了意义,成为萨特意义 上的生活计划(Life Project)。如果她被哪个公司雇佣,她在这个层面获得的权力感将大打 折扣,她对这一点心知肚明。因此,她把自己的生活方式与那些上班族划清了界限。可以说 她的生活是一种对曾把她的全部环境和她本人置于规范之中的公司资本主义的反抗。她谈话 中明确地展示了她对美国的态度,显示出她对以美国为中心的现代性和全球化的抵制。
一位服装设计师的全球身份和地区身份
洪丽芬的故事则诉说在建立全球化身份上所受的限制。
洪丽芬的工作室座落在台北清真寺后面浓荫遮蔽的小巷中,弥散着一种精心营造出的气氛 。通过大敞的窗户可以看到室外的砖墙和树丛。屋内摆放着精致的家具,上面的金属装饰雕 塑几乎是巴洛克式的。墙上悬垂着丝绸幔帐,设计风格让人联想起旗袍和中山装。墙被涂成 一种类似天鹅绒的红色,现代绘画悬挂其上。靠近门的地方摆着一摞摞卖的明信片,绘有洪 丽芬本人肖像的明信片也夹杂其中。“这里像个博物馆,”我第一次驻足这里时对她这样说 。
“这个地方,”她说,句子里混杂着中文和法文,“c’est pas seulement pour acheter les vetements.②他们都来享受这个空间。很小,可是有自己的气氛在里面。喜欢呆在里 面 这个样子……他们可以常常聚会,很多工人在一起。我一直有这样的希望,所以可能以后这 里就变成一个服装的博物馆。”
44岁的洪丽芬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她的衣着、发型、甚至脸上初现的皱纹却透出一种和 谐,她是我在台湾遇到的最美丽的女人之一。她对生活的轻松幽默方式既体现在她服饰和家 具的设计上,还流露在她个性化的外表上,以某种方式显露出她的个人特性。在台湾,大多 数人以族群分人,比如“台湾本省人”、“外省人”或“客家人”。我问她怎样从族群上把 自己归类。
“新竹人”,她说,“台湾新竹,可是父祖先大概是从福建过来。”
洪丽芬通过强调地缘出身来回避个人身份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在台湾这个话题非常政治 化并很可能引起争议。实际上,洪丽芬为自己精心建构的身份超越了台湾政治。国际化的教 育背景,精神上的四海漂泊,她为自己建立的是一个全球身份。从台湾的实践大学毕业之后 ,她先后到纽约、东京、巴黎留学。她曾在日本、法国、意大利、德国和美国举行展览。她 不仅设计服装,而且还设计家具。“洪丽芬世界网”,包括她在台北的工作室,巴黎的办公 室以及分布在三大洲的分店。无论是在艺术传媒范围上还是在民族空间意义上,她都是个巡 游于疆界之间的人物。“在服装学习之后,我没有间断过,一直往前面的目标在走,”她说 。“不只是在台湾,而且是走出去。我想这个很重要。”
多数从海外回到台湾的人强调台湾和国外的文化差异。而洪丽芬在被问及在法国学到什么 时,她又一次表现出全球化、世界主义的视角。她说:
(住在那里)让我习惯那边大家怎么生活。因为在台湾,四季如春,没有特别的冬天,没有 特别的春秋两季。大家都这么说。所以让我了解最基本上气候对服装的影响……第一个最大 的 区别,对台湾比较没有那么冷的天气、气候。我在那边可以自己体验到这个。而且真的是生 活一段时间在那里。当然,我也认识很多其他的专业上面的知识。这一段时间非常重要。
通过强调气候而不是文化的差异,洪丽芬把自己描述为一个可以在任何地方居住的全球公 民 。生活在巴黎使她得以成为世界时尚网络中的一名设计师。她说:
最重要的是让我自己更有信心,我有跟人不一样的东西。这个比什么都重要。知道我的作 品在那边是另外一个不同的东西,所以我很快出去,很勇敢去那边展览。
她强调自己已成为全球时尚舞台的一部分。她说,巴黎的设计师“都是很好的朋友”,而 且“我也是里面的一个分子。”她说:
我是国际的人,不是从台湾过去旅行的人。我常常觉得,我到哪里去,到各地去旅行,我 好像就是那里的人一样。我有这个感觉,很容易习惯那个环境。
洪丽芬具有一种淡漠国家和民族身份,适应异乡环境,获取各种人类经验的全球精神。但 是,虽然洪丽芬竭力强调自己的全球身份,而国际时尚媒体却极少这样描述她。西方的设计 师,比如Christian Dior和Donna Karan是不折不扣的全球风格设计师,在自己的作品表现 出法国农民的和美国西部风格的影响时丝毫不感到压力。而出现在《Elle》、《Marie Clai re》,甚至《花花公子》上的介绍洪丽芬的文章无一例外地强调她的国家和民族身份,称她 为台湾人或者中国人。她给我看她所收集的报刊文章,标题为“La tradition taiwanaise ” ,“Taiwanaise Sylvie Chen”,以及“二十年台湾风格的设计”等。我大声念出一个标题 :“Chic,c'est chinois.”她忧郁地叹了口气说,“没有办法。”
洪丽芬身份上的矛盾显示出全球政治经济权力的不平衡。在台湾,她的确因为自己所受的 教育和她的企业家能力获取了权力。虽然已经44岁,她依然独身,无意于陷入Susan Greenh al gh描述的那种限制妻子的婚嫁。像台北的许多人一样,她对自己的全球身份挺自豪,而这个 身份在台湾可被视为一种高水准的国际人。但是,不同于美国和法国的设计师,她的地区身 份总是被国际媒体所强调,而她的全球身份被拒绝了。她的地区身份是被西方霸权主义的后 殖民主义秩序本质化(essentialized)了。即便是在全球背景下,个人在建立自己的全球化 身份上仍然存在限制,甚至就是洪丽芬这样极具天赋的人亦不例外。她的情形与Dorinne Ko ndo所描绘的日本设计师的情形极为相似:
甚至当有些日本设计师把自己视为一个更广阔的、跨民族的叙事领域的一部分的时候,民 族-国家所积淀的历史以及各种各样的运作却一再把他们置于他们的民族、甚至常常是种族 身份之中。(Kondo,1997:56)
当洪丽芬在台北销售时装时,她被看做全球人。当洪丽芬在巴黎和纽约展销作品时,她就 被当作不折不扣的地区人。此类差异显示出霸权主义的“西方”与本质化的“东方”在与被 新帝国主义经济蒙上了面具的全球化主义(globalism)对话时,在权力上的差异。这种做法 使 得西方商品在亚洲的倾销合法化的同时,把进入西方市场的亚洲设计师边缘化。洪丽芬几乎 没有机会在纽约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就像Versace在台北所达到的那样。因此,洪丽芬已 经转向做本土的生意。她在台北设计男装和女装。她也制作非常传统的中国风格的服装,包 括为故宫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设计制服。她还为台湾的一个民众喜爱的佛教圣地佛光山设计装 置。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一个坚强和目标明确的单身妇女来说,她曾为歌剧“蝴蝶夫人 ”设计服装,而这个作品表现的是西方人讲述的关于一个非常刻板的传统亚洲妇女的故事。 (see Kondo,1997)她经营着一个有10到15个工人的工厂,此外还通过转包的卫星连锁厂家生 产更多的产品。(see Shieh,1992)
梅英和洪丽芬的生活经验显示,经营企业可以使妇女获得权力。她们俩与Susan Greenhalg h文章中“妇女的命运与她们嫁入的家庭息息相关”的描述大相径庭。(Greenhalgh,1994:7 5 9)她们俩都用企业经营的方式在人际间建立权力,而且都避免结婚。她们俩都曾通过建立个 人身份获得权力,都曾用收集到的全球的和本土的文化材料塑造自身。在这两个个案中,她 们 在建立自身身份时都带有幽默感和后现代主义意味,而且都超越了她们植根于其中的本土民 族。从更大的意义讲,她们是自己身份的建立人,而且使用这种身份去挑战她们所处的社会 结构。比如梅英曾明确地向当代在台湾处于统治地位的美国中心说(American-centered dis course)提出挑战。洪丽芬在国际压力下无法坚持自己的全球身份,表明在身份建立方面依 然存在限制。台湾仍然是全球舞台上困厄于美国领导的帝国主义霸权下的一个弱小成员。
结论
对台北女老板的研究使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阿帕杜拉(Arjun Appadurai)和德里克(Air f Dirlik)关于全球化与身份的观点是正确的。受全球化的影响,今天个人不再局限于以往 的 社会身份形式里,他们可以置身于想像的民族景观中,从而可使用完全不同来源的文化材料 建立自己的身份。德里克的正确性还在于,他认为全球化发生在一个以霸权主义的西方与其 它 各国之间不平等关系为特征的政治经济秩序中。“全球的”主要与西方公司相关,如麦当劳 和Calvin Klein等。台南的旦仔面和洪丽芬的设计依旧被看作本土“中国的”,无论是在台 北 还是在纽约,涉及其中的人都无权改变这一点。在阿帕杜拉置身于芝加哥期间,他感受到的 权力反差尤为强烈。他谈到了他的一种感受,即:每天在尝受脱离后殖民主义、移居国外、 具 有学术身份、遭遇丑陋的种族主义式的对待、成为少数民族和部落化生存之间摆动的滋味 。(Appadurai 1991:422,quoted in Kondo 1997:177)
美国霸权还明显地表现在诸如对“人权”这种全球性话题的不公平对话上。对美国来说, 对中国不充分保卫人权的批评被视为正常的,甚至是预料之中的。然而国际上对于美国人权 问题的批评声音却几乎听不到,事实上美国存在大量侵犯人权的事例。美国不停地要求中国 释放某个政治囚犯,但是中国从来就没有要求美国释放他们的政治犯。我不禁想起美国印第 安人活动家利奥纳多·皮尔特(Leonard Peltier)和非洲裔美国人毛主义者穆马尔·阿布加 莫(Mumia Abu-Jamal)。③在全球性对话中的这些不公平现象显示出美国仍然是个霸权主义 大国。许多学术论文在讨论“全球化”时忽略了全球性的权力不平等以及人们对一个国际性 反帝国主义战线的持续需要。人类学家们,尤其是发展人类学和应用人类学家们,应当对人 类学家及其研究参与者们如何陷入全球权力网络的情形加以关注。我们还必须对自己的研究 以及推动我们前进的精神进行反省。
台北女老板的故事显示了独立的妇女之解放与全球化身份的关联。梅英、洪丽芬二人凭借 创业及采用国际认同而为她们自己建立了一个新的社会空间。如梅英在她的邻居眼中看来古 怪 ,她就会宣称自己的前世是巴基斯坦人;而洪丽芬之所以选择不婚,也可从她的欧洲认同来 理解。全球化身份不只是对女人,甚至对同性恋者、原住民及其他被压迫的弱势团体而言, 都成了一种获权的来源。然而,只要这些女人走到国际舞台上,那些所谓的全球化身份就 会被拒绝。在帝国主义的霸权下,她们被媒体简称为“当地人”而非她们自己认同的“国际 人”。洪丽芬的故事只是东方与西方之权力不平等的一个小例子。真正的全球化,也就是孙 中山 的“世界大同”之理想,在所有的国家一律平等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而那需要的不只是 阿帕杜拉的“民族景观”,还需要男人与女人一起对抗帝国主义与美国霸权的斗争。
①沃尔夫认为权力有四种模式。第一种是尼采意义上的,即“个人所固有的潜力和能力” 。(Wolf,1999:5)此类权力注重个人如何进入一场权力游戏,但是不涉及游戏。第二类权力 贯穿于人们的互动与交易之中,是把自己的意志施加于对方的能力。沃尔夫把第三类权力称 之为组织权力,即对其他人展现才能并彼此互动的背景实行控制的能力。第四类权力是沃 尔夫著作的重点,即结构权力。结构权力不仅运作于自身的社会背景中,而且还指定了不同 社会背景间其能量流动的方向及其分布。(Wolf,1999:4-5)
②这句话是法文,意思是“这不仅仅是为了买服装”。
③穆马尔十几岁时曾加入黑豹党,在1982年受审判刑时曾因为这件事受到指控。在那段时 间,他曾撰文批评欧洲殖民主义者在美国作为压迫美国印第安人和黑人的历史角色。他写道 :“政治权力是从枪管里射出来的。”检查官约瑟夫·法力尔认为这一段论述明确表明穆马 尔具有暴力倾向,声称穆马尔接受了毛主义的政治哲学。后来,
Delaware最高法院在一次死 刑判决辩论时,把穆马尔案作为因政治原因量刑的一个判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