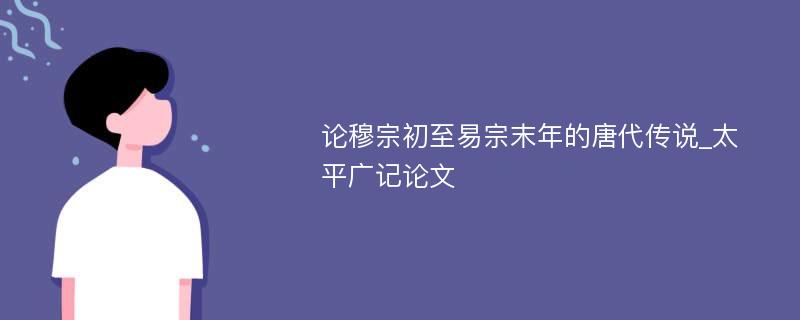
论穆宗初至懿宗末的唐人传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唐人论文,传奇论文,论穆宗初至懿宗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2X(2000)05-0008-05
从穆宗初到懿宗末(821-873)的唐人传奇成就以传奇集为主,著名的有:薛用弱《集异记》、李复言《续玄怪录》、薛渔思《河东记》、郑还古《博异志》、卢肇《逸史》、无名氏《会昌解颐录》、陆勋《集异记》、李玫《纂异记》、张读《宣室志》、裴铏《传奇》、袁郊《甘泽谣》;单篇的著名传奇有:柳珵《上清传》、房千里《杨娼传》、韦瓘《周秦行纪》、薛调《无双传》。无名氏《东阳夜怪录》也可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
一
穆宗至懿宗朝,唐王朝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危机之中。这一历史阶段的朝政大权,基本操纵在宦官手中。从唐宪宗被宦官杀害始,唐朝先后在位的穆宗、敬宗等八位皇帝,除敬宗外,全为宦官所拥立,而敬宗则为宦官所残害。宦官朝权独揽势必会削弱甚至剥夺朝臣的权力,朝臣如不甘心依附宦官,便必然发生对抗,831年、835年、854年就先后三次发生过朝臣谋诛宦官或抑制宦官的事件,而每一次都以朝臣的失败而告终。其结果是宦官权势不断加强,皇朝统治日益衰朽腐败。
除朝臣与宦官之间的斗争(也有勾结)之外,唐王朝内部还有两大矛盾:一是朝臣之间的朋党之争,主要是牛李党争;二是朝廷与藩镇的矛盾以及藩镇之间的矛盾。在上述三重矛盾的交相冲击下,唐王朝日趋没落,农民起义亦随之风起云涌:860年1月,浙东裘甫率众起义;868年,庞勋在邕州(今广西南宁一带)领导戍卒起义。矛盾更多了,原有的矛盾也进一步激化,唐王朝一天天趋向土崩瓦解。
生活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代,士大夫阶层的忧患意识较以往更为强烈。与兴盛期传奇中抒发人生感慨和关于爱情的玫瑰色的情愫不同,此期作家对政治,对重大的关乎国运的问题格外关心。伴随着咏史诗等富于批判锋芒的文学体制的兴盛,传奇亦多影射和抨击社会现实。李玫《纂异记》、郑还古《博异志》在这方面尤具特色。
末世情绪常常经由两条渠道流泻出来:一是抒发盛衰无常的感慨,名吊古而实伤今;一是着力渲染大风暴之前密云翳日令人窒息的气氛。这一时期的传奇正是如此。《太平广记》卷二九《姚泓》(出《逸史》)记某禅师于南岳遇“一物”,此物自称姚泓。禅师大惊曰:“吾览晋史,言姚泓为刘裕所执,迁姚宗于江南,而斩泓于建康市。据其所记,泓则死矣,何至今日,子复称为姚泓耶?”姚泓回答:“当尔之时,我国实为裕所灭,送我于建康市,以徇天下。奈何未及肆刑,我乃脱身逃匿。裕既求我不得,遂假一人貌类我者,斩之,以立威声,示其后耳,我则实泓之本身也。”在这种遇仙故事中,弥漫着的分明是末世的恐惧:大动乱的急风骤雨步步逼近,只要稍微敏感一些,就不免心襟摇摇。《太平广记》卷四十《陶尹二君》(出《传奇》)所流露的恐惧感更为沉重。小说写了一个“古丈夫”的奇遇。他是秦时人,为童子时,值秦始皇好神仙术,被选中,随徐福入海求仙人,他设计逃了出来,“归而易姓业儒”;不几年,又碰上秦始皇焚书坑儒,“时于危惧之中,又出奇计,乃脱斯苦”;又改姓名为“板筑夫”,偏偏秦始皇修长城,他被抓去当了役夫,“于辛勤之中,又出奇计,得脱斯难”;“又改姓氏而业工,乃属秦始皇崩”,大修陵墓,竣工后,工匠全被活埋,“念为工匠,复在其中;又出奇谋,得脱斯苦”。古丈夫从自己的经历体会到,他在世间没好日子过,“遂逃此山,食松脂木石,乃得延龄耳”。所谓“食松脂木石”而得“延龄”,仅是传奇设置情节的套式;“不遇世”以至动与祸会,这才是作品的旨意所在:时值无道之世,处处都是陷井,处处都是火坑,没有谁能安宁畅适地生活。其它如卷二八《僧契虚》(出《宣室志》)记隋宗室杨外郎“属隋未,天下分磔,兵甲大扰,因避地居山”;卷四二《李虞》(出《逸史》)记杜子华“逢乱避世”;卷四八《李绅》(出《续玄怪录》)众神谓“人世凡浊,苦海非浅”;卷四八《李元》(出《逸史》)叙秦时阉人,“避祸得道”等,无一不流露出唐代后期知识分子的“伤心”之情。
吊古伤今的唏嘘之声也不断地从这一时期的传奇中响起。《太平广记》卷三五○《颜浚》(出《传奇》)写会昌(841~846)中颜浚游广陵,与陈后主的妃嫔张贵妃、孔贵妃和隋宫人赵幼芳相遇,或“多说陈、隋间事”,或“多说陈朝故事”,而她们的诗更集中地抒写出盛衰无常的感慨,如:“宝阁排空称望仙,五云高艳拥朝天。青溪犹有当时月,应照琼花绽绮筵。”“皓魄初圆恨彩娥,繁华秾艳竟如何?两朝唯有长江水,依旧行人作逝波。”这与李商隐、杜牧的若干咏史诗的意味相近。《独孤穆》(《太平广记》卷三四二,出《异闻录》)的凄清、感伤氛围更为浓重。
人生无常,人把握不了自己的命运,李复言《续玄怪录》经常表达这一痛苦的人生经验。在这种末世的灰暗阴影里,求仙意识迅速蔓延开来,这也如同陶潜在动荡不宁、死亡相藉的乱世而憧憬温馨芳菲的桃花源一样,因此,此期传奇中的仙境也像桃花源那般诗意盎然,作者们写来总是妙笔生花(自然也不免雷同)。比如《太平广记》卷二十《阴隐客》(出《博异志》:“工人乃入穴探之。初数十步无所见,但扪壁傍行,俄转有如日月之光,遂下。其穴下连一山峰,工人乃下山。正立而视,则别有一天地日月世界。其山傍向万仞,千岩万壑,莫非灵景,石尽碧琉璃色。每岩壑中,皆有金银宫阙。有大树,身如竹有节,叶如芭蕉;又有紫花如盘,五色蛱蝶,翅大如扇,翔舞花间;五色鸟大如鹤,翱翔树杪。每岩中有清泉一眼,色如镜;白泉一眼,白如乳。工人渐下至宫阙所,欲入询问,行至阙前,见牌上署曰‘天桂山宫’,以银字书之。”卷三六《李清》(出《集异记》):“如此约行三十里,晃朗微明。俄及洞口,山川景象,云烟草树,宛非人世。”卷五三《麒麟客》(出《续玄怪录》):“下一山,物众鲜媚,松石可爱,楼台宫观,非世间所有。”“紫衣吏数百人,罗拜道侧。既入,青衣数十人,容色皆殊,衣服鲜华,不可名状,各执乐器引拜。”“其窗户阶闼,屏帏茵褥之盛,固非人世所有。歌鸾舞凤,及诸声乐,皆所未闻。”
这种种仙境,其大要有二:一是仙境的美丽自然景观实即山水诗的境界,它是对隐居生活的一个侧面的观照,所以,小说中的诸多“凡”人,在一度游历仙境后,便淡于宦情,弃家远扬了。如《太平广记》卷四六《白幽求》(出《博异志》):“幽求自是休粮,常服茯苓,好游山水,多在五岳,永绝宦情矣。”《麒麟客》:茂实“遂弃官游名山”,“后不知所在也”。二是仙境中的富贵生活则是对人世荣禄的观照,折射出部分士大夫既想躲避人间祸患,但又舍不得尘世享乐的心理。这两点是矛盾的、无法统一的:隐居则必然要忍受寂寞、清寒的人生;留恋富贵便绝不可能断绝“宦情”。患得患失,希望通过仙境来延续尘世的幸福,这种人生设计不免可笑。真正平实地表达出避难的悲剧性渴望的,是《太平广记》卷四二《李虞》(出《逸史》)。作品所展示的“逢乱避世”的隐居图景是:“川岩草树,不似人间。亦有耕者。”“有佛堂,数人仿饮茶次。”宁作“耕者”而避世,这才是绝望的“乱世民”的心理。《太平广记》卷四四五《孙恪》(出《传奇》)则着意突现上述两种追求的矛盾:第一种追求,目的在避世,《孙恪》把它具体化为恢复猿的本形,回到深山里去;第二种追求,目的在于满足人生的欲望,《孙恪》把它具体化为幻形入世,为人妻,为人母。小说记一猿精变成美妇袁氏,作了孙恪的妻子,“袁氏赡足,而恪久贫,忽车马焕若,服玩华丽”;后生二子,袁氏辛勤抚育,治家甚严。她作为人的欲望基本上满足了,却忘不了她本来的家,“每遇青松高山,凝睇久之,若有不快意”。最终还是化为老猿,跃树而去——尽管临行还“抚二子,咽泣数声,语恪曰:‘好住!好住!吾当永诀矣!’”她为什么要回山去呢?其经历告诉了读者谜底。这猿原是唐玄宗宫内的宠物,“及安、史之乱,即不知所之”。广德(763~764)间,安、史乱平,她才幻形入世。现在她回山去了,是因为天下又要大乱了。裴铏用这个故事说明:隐居生活如同袁氏的回山,非常痛苦;然而面对动乱的时世,人们却只能选择这痛苦的生活。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六十七载:
乾符五年(878),铏以御史大夫为成都节度副使,《题石室》诗曰:“文翁石室有仪形,庠序千秋播德馨。古柏尚留今日翠,高岷犹蔼旧时青。人心未肯抛膻蚁,弟子依前学聚萤。更叹沱江无限水,争流只愿到沧溟。”时高骈为使,时乱矣,故诗有“愿到沧溟”之句,有微旨也。显而易见,裴铏确实有避世的念头。只是,生活中的裴铏,不及小说中的袁氏果决:袁氏虽然舍不得丈夫和孩子亦即人间的温情,但迫于动乱的时世,还是咬牙选择了逃避现实之路。
这一历史阶段的传奇,即使是爱情故事,也常与避乱求仙有关。兴盛期传奇也写仙女与人间男子的爱情,但多是“思凡”类型,此一时期则侧重描述仙女对“凡人”的度脱。《太平广记》卷五十《裴航》(出《传奇》)叙裴航历尽艰辛,终与云英“议姻好”,于是顺理成章,进入了仙界:“别见一大第连云,珠扉晃日……及引见诸宾,多神仙中人也。”“妪遂遣航将妻入玉峰洞中,琼楼珠室而居之,饵以绛雪琼英之丹,体性清虚,毛发绀绿,神化自在,超为上仙。”卷六九《马士良》(出《逸史》)叙马士良答应娶守护上仙灵药的谷神之女为妻,不仅躲过杀身之难,且得长寿。因此,对那些不知恋爱为何物的青年男性,作品在讽刺他们如同木偶的前提下,每每更痛心地惋惜他们错过了仙缘。如卷六八《封陟》(出《传奇》),上元夫人有心度脱封陟,三番五次地向他表达倾慕之情,而他一次比一次严厉地拒绝了。上元夫人进一步明确地告诉他:“君能仔细窥朝露,须逐云车拜洞天。”意思是:你娶了我,便能成仙。但这也未能打动封陟。上元夫人不得不感叹“此子大是忍人!”夫人的侍从亦斥之为“木偶人”,“穷薄当为下鬼”。封陟错过了仙缘,果然三年后“染疾而终”,被缚往太山。适值上元夫人在太山游玩,念其朴戆,判他再活十二年。然而,十二年太短了,所以,还阳的封陟,每当想起拒绝上元夫人的“昔日之事”,便无限“追悔”,“恸哭自咎”。故事到此戛然而止,其讽喻主旨是明朗的。《太平广记》卷五三《杨真伯》(出《博异志》)与之命意相似。
侠士的形象在这一时期发展到极致。对侠的兴趣和崇拜,产生于两种心理需要:一是心理上的安全需要。时局动荡,万方多难,遭逢乱世,随时都可能遇上不测,于是,人们渴望出现那种所向无敌而又富于正义感的英雄,由他们来支撑这倾斜的世界;二是心理上的超越需要。文弱书生,碌碌百姓,太渺小了,但人们又向往那个生龙活虎、气势奔放的英雄的天地,于是便在想象中设计自己,在展望中超越自己,虽然明知是泡影,却毕竟是五光十色、富于魅力的泡影。唐代后期的社会现实,使士大夫的这两种心理需要急遽膨胀,侠士的形象也随之大放异彩。
《太平广记》卷一九四《昆仑奴》(出《传奇》)中的磨勒,仗义行侠,打抱不平,已是读者非常熟悉的形象。卷六九《张云容》(出《传奇》)中的薛昭,亦风标不凡:“薛昭者,唐元和末为平陆尉,以气义自负,常慕郭代公、李北海之为人。因夜直宿,囚有为母复仇杀人者,与金而逸之。”结果他自己锒铛入狱。
打抱不平的升华则是救万民于水火,使“义”具有更为广泛的意义。《太平广记》卷一九五《红线》(出《甘泽谣》),红线在迫使田承嗣收敛了吞并薛嵩的野心后,曾自豪地说:“今两地保其城池,万人全其性命,使乱臣知惧,烈士谋安,在某一妇人,功亦不小。”道出了其行侠的动机:她不仅仅是以此报薛嵩之恩,更主要的还是替百姓着想。卷三九四《陈鸾凤》(出《传奇》),陈鸾凤“愿杀一身,请苏百姓”的表白,亦呈露出同样高贵的人格境界。
与侠客的人格相联系,他们往往功夫非凡:昆仑奴从严密的包围圈中飞出,“瞥若翅翎,疾同鹰隼,攒矢如雨,莫能中之,顷刻之间,不知所向”。聂隐娘之师老尼,可打开隐娘脑袋,“藏匕首而无所伤,用即抽之”;隐娘本人能飞,能幻化;妙手空空儿更胜一筹。王立妾“挈囊逾垣而去,身如飞鸟”;红线来去无踪,转眼间“往返七百里”……侠而近乎仙,已非常情所能揣度。
二
这一时期唐人传奇的审美追求有不少引人注目的新因素,由此带来了传奇风格的变化。一些手法或方式,此前的传奇中已经运用过,但在这一时期又有发展和创造。
(一)一波三折的情节之“奇”
如果说兴盛期传奇偏爱“无关大体”的浪漫人生之奇,而营造情节的兴趣相对小一些,那么这一时期正好换了个方向:伴随着进士与妓女的爱情题材的急遽减少,苦心构思曲折情节的作家占据了小说界的核心位置。裴铏、李复言等是其代表。
爱伦·坡在《写作的哲学》中说:“在动笔之前,对每一个真正的情节从开始到结局要有一个清晰的轮廓,必须进行苦心经营。只有经常心怀故事的结局,使事件的发展,尤其是使一切故事的格调都指向作者意图的方向,我们才能赋予情节一种不可或缺的连贯性或因果氛围。”裴铏、李复言的传奇,其结局往往在开头部分就暗示出来了,但这并未减弱情节的戏剧性,相反还有助于增强其戏剧性。据我看,他们的成功在于抓住了下述几个关键:
1.设计了一个中心人物,他的命运成为读者关注的焦点。如《裴航》中的裴航、《崔炜》中的崔炜、《定婚店》中的韦固。
2.中心人物的目的或归宿明确。这既规定了小说的情节走向,又加强了小说的神秘感。如裴航的“蓝桥便是神仙窟”、“玄霜捣尽见云英”,崔炜的“不独愈苦,兼获美艳”,韦固的必娶“卖菜媪陈婆女”。
3.目的被阻。人物不能得到他所追求的东西,如崔炜、裴航;或人物竭尽全力逃避其归宿,如韦固,人物的命运由此出现曲折,读者的好奇心被进一步激活起来。
4.初步障碍被克服。如崔炜从任翁处脱难,裴航见到云英,韦固派人刺杀陈婆女而未遂,故事朝着既定方向推进,读者期待着预期结局的到来。
5.目的再次被阻。这次被阻较第一次更难克服。突然出现的境况使中心人物几乎像是走到了与预期结局根本不同的终点。如韦固的娶刺史王泰女、裴航的寻不到玉杵臼、崔炜的落入蛇穴。
6.突转。威廉·阿契尔在他的名著《剧作法》中指出:“如果一个剧作者在他的主题发展中,发现经过他精心设计的、异常吸引人的伟大场面没有任何不自然的紧张或过多的准备和巧合,而这个场面中的一个或者更多的人物,将要经历一种内在精神状态的或外在命运的显然转变,那这位剧作者将是非常幸运的。简而言之,对我们来说,‘突转’的理论实际上就变成了一种‘伟大场面’的理论。”现实生活中的突转是屡见不鲜的,但通常规模较小,艺术中的突转则可以将作品以惊心动魄的方式推向结尾,如崔炜被玉京子(蛇)送入南越王赵佗宫中,裴航与云英成亲而成仙,韦固娶的王泰女就是“陈婆女”。结局虽然早已预定,可结局最终到来时却令我们愕然:它既是合情合理的,又是出人意料的。
(二)意境创造的加强
所谓意境,就是情景交融的艺术形象。其美感特征是“有风韵”,有“韵外之致”。以景寓情的景物描写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一时期唐人传奇中的景物描写较之以前有所突破。《博异志》、《续玄怪录》、《传奇》里皆不乏景物描写,而《续玄怪录·柳归舜》、《博异志·许汉阳》的想象之丰富,状物之清丽,尤为可观。再看看《纂异记·嵩岳嫁女》(《太平广记》卷五十引)的一个场景:
至一车门,始入甚荒凉,又行数百步,有异香迎前而来,则豁然真境矣。泉瀑交流,松桂夹道,奇花异草,照烛如昼……其花四出而深红,圆如小瓶,径三寸余;绿叶形类杯,触之有余韵。小童折花至,于竹叶中凡飞数巡,其味甘香,不可比状……步而前,花转繁,酒味尤美。其百花皆芳香,压枝于路旁。在这样的诗情画意的描写中,我们感到了作者李玫极欲摆脱尘世污浊的渴望。
意境的形成并不完全仰赖于写景,真切的人物关系及声口毕肖的言谈,也能创造出“清淡见滋味”的意境。如《博异志·刘方玄》(《太平广记》卷三四五引)叙刘方玄自汉南抵巴陵,夜宿江岸古馆,听人(实为鬼)聊天:
至二更后,见月色满庭,江山清寂。唯闻厅西有家口语言啸咏之声,不甚辨。唯一老青衣语声稍重而带秦音者,言曰:“往年阿郎贬官时,常令老身骑偏面珵,抱阿荆郎。阿荆郎娇,不肯稳坐,或偏于左,或偏于右,坠损老身左膊。至今天欲阴,使我患酸疼焉。今又发矣,明日必大雨。如今阿荆郎官高也,不知知有老身无?”复闻相应答者。俄而有歌者,歌音清细,若曳绪之不绝。复吟诗者,吟声切切,如含酸和泪之词。幽咽良久,亦不可辨其文,而无所记录也。久而老青衣又云:“昔日阿荆郎爱念‘青青河畔草’,今日亦颇谓‘绵绵思远道’也。”仅四更,方不闻其声。老婢的絮叨以及她对小主人的感情,那种谈家常的气氛,一一活现在纸上。
这一时期唐人传奇风格的流变是由一批具有个人风格的作家的创作体现出来的,面对如此庞大而复杂的整体,想用两个侧面来加以概括,无疑是不现实的,但抓住这两个侧面,却是我们宏观地把握这一时期小说审美特征的基点。
收稿日期:2000-06-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