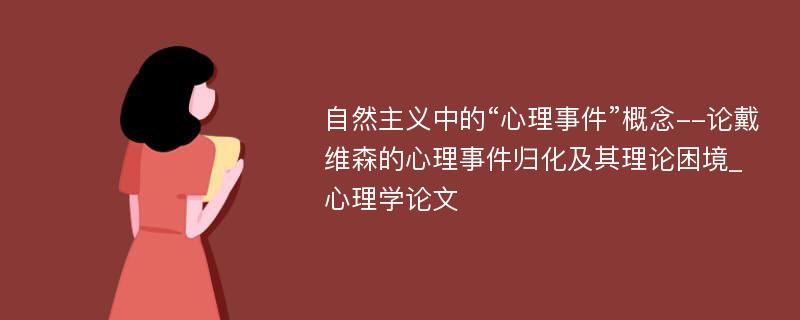
自然主义的“心理事件”概念——论戴维森对心理事件的自然化及其理论困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事件论文,心理论文,自然主义论文,困境论文,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戴维森的AM理论 戴维森在《形而上学中的真理方法》一文中曾说道:“研究形而上学的一种方式就是研究我们语言的一般结构。”(戴维森,第238页)这个原则在具体的语言分析中则表现为,“仅仅在真理理论发现量化结构的场合,才迫使本体论问题出现”。(同上,第251页)基于这个原则,戴维森得出了事件的本体论承诺。同样是基于这样的原则,戴维森在1963年发表的论文《行动、理由和原因》中认为,为了澄清语言的逻辑结构,我们要对代表事件的行为动词进行量化。而这种做法在本体论上的后果是,我们需要把特定的“行动”理解为客观的事件。因此行动被整合到了事件概念所提供的本体论图景中。 为了在这个自然主义的背景中进一步理解身心关系,戴维森在1970年发表的《心理事件》一文中认为,心灵也是物理世界中的事件。对于戴维森来说,这种本体论上的一致性,让我们能够在奎因(W.V.Quine)的物理主义框架下为身心问题给出一种自然主义的说明。这种说明可以让我们不必将行动的(心理)原因理解为某种神秘的对象。戴维森认为,我们完全可以保留一元论的这种优点,同时避免导向一种特定的还原论,即那种认为可以将心理内容完全地还原为物理学描述的自然主义理论。在语言的层面上,这种还原论会和奎因关于意义的怀疑论一起,将心灵的地位消解掉。 为了既能够保持心灵的某种“自主”地位,又能够在(事件)一元论中理解身心关系,在戴维森看来,我们就要对“一元论”这个概念做一种独特的理解。在《心理事件》一文中,戴维森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解,它被称之为“无法则一元论”(Anomalous Monism,简称AM)。在这篇文章中,AM的核心内容被表述为三条基本原则,即(1)因果交互作用原则:至少有一些“心灵事件”与物理事件之间存在因果作用;(2)因果作用的法则性原则:哪里有因果作用,哪里就必定存在一条规律(Law),它是原因事件和结果事件必须服从的,具有严格决定性的规律;(3)心灵的无法则性原则:不存在这样的一些(严格)规律,基于它们可以对心理事件进行解释和预测。(cf.Davidson,1970,pp.207-209) 戴维森认为,尽管这三条原则在表面上显得矛盾,但是,这种矛盾是可以被调和的,而起到这种调和作用的关键就是所谓的“心理事件”概念。戴维森所给出的理由是,说一个事件是心理的,这种对事件的分类是我们在理解他人的行动时不可或缺的手段。在描述他人的行动时,心理学概念为我们提供出了一套自足的分类标准,它们迥然有别于我们使用物理学概念时所运用的标准。戴维森认为,两种标准不可能被一种标准所统一:物理学概念在描述事件的时候,可以将(所有的)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纳入到严格的规律中来理解;但心理学概念却没有这样的功能,所以我们不能在两类描述所区分出的事件之间找到衔接它们的严格规律;由于心理学概念以自己的方式将某些事件描述为是“心理的”,而且这种“描述”本身作为一种认知行为并不会干预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说心理事件与物理事件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也就可以理解了。 但是,戴维森以“心理事件”概念对AM的三条原则所做的调和是失败的。在下文中,我们将指出,失败的根源在于:戴维森的行为主义意义理论无法为“心理事件”这一概念提供确切的本体论内涵。在以后的哲学讨论中,潜藏在这一概念中的模糊性让人们对AM的一致性产生了诸多怀疑。很多持还原论立场的哲学家认为,AM的三条原则根本不能互相协调。根据这类哲学家的观点,原则(2)中提到的“严格规律”是和因果作用的“机械论”机制紧密相连的。而如果按照这种机械论的因果关系来理解心灵在世界中的因果作用,那么原则(3)就会把心理事件排除在因果作用的范围之外。这就会让心灵成为一种“副现象”(epiphenomenon),所以原则(1)也就无法成立了。对于这类批评,戴维森在一些论文(如《思考原因》)中给予了回击。在下文中我们将看到,戴维森对这些哲学家的反驳是失败的。由于“心理事件”概念在涵义上的模糊性,戴维森无法解决心灵的因果性问题,而这让AM的初衷难以实现。 二、因果解释与因果关系 对于戴维森来说,所有的本体论问题都要从我们对语言的研究中得来。在戴维森的意义理论中,出于对“陷入内涵的焦虑”,他用支持外延主义的范式(T)“s是T当且仅当p”来替换内涵主义的分析范式,即“S意谓着P”。(cf.Davidson,1967,pp.22-23)戴维森赞同奎因对传统意义理论的批判以及关于意义的行为主义解释,认为表达式的意义最终要依赖于对语言共同体内部成员的行为观察。 具体而言,这就是在“彻底解释”(radical interpretation)理论的框架下研究意义的行为条件。这种理论无需提到内涵对象,从而能让我们以自然主义的方式研究语言乃至心灵的存在条件。我们因此可以避免传统(尤其是弗雷格式的)语义学所造成的种种困难,这些困难主要是由承诺涵义实体的存在而引起的。在这种外延主义的指引下,语言的发生被认为是一种经验性的事实。基于解释理论和与之联系在一起的语义整体论思想,戴维森得出结论:“意义”和“信念”之类的对象“不具有独立的重要性”。(戴维森,第168页)戴维森因此将“信念”等命题态度作为一种理论的假设物:“我们拥有的信念概念仅仅在于它在语言解释中的作用,因为它作为一种私人态度是无法理解的,除非把它看作是对由语言提供的公共规则的一种调整。”(同上,第203页) 作为一种理论的假设物,戴维森认为,所谓的“信念”和“愿望”等命题态度,是我们在对行动作一种“目的论解释”的过程中必须被假定的概念。“引入信念和愿望去解释行动,就是把行动解释为由理论所协调的行为模式的一种方式”,“我们对愿望和信念所提供的描述,必定是根据对信念内容和愿望对象的目的论的解释,展现了行动的合理性”。(同上,第192页)在戴维森看来,这个过程就是在解释理论中将行动“合理化”(rationalizing)的过程。 戴维森曾指出,合理化概念基于这样两个观念,即原因和合理性。这两者的关系是:一个行动的原因必须是“一个信念和一个欲望,鉴于它们这个行动才是合理的”。解释的作用就在于构造出某个行动的“基本理由”,从而将被解释者的行动纳入到一种更加广泛的理论中去。正是意义和信念的这些特征,以及这些特征所派生出的“意义”(在解释理论中)的不确定性,才构成了AM中原则(3)的核心涵义:以命题态度定义的心理事件与物理事件之间不存在严格的规律。 但是,既然承认了“基本理由”是一种“假设”物,就势必会产生一个疑问,即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戴维森在《行动,理由和原因》一文中提出的如下论题:“一个行动的基本理由是它的原因。”(Davidson,1963,p.12)在这篇文章中,戴维森认为特定的行动是可以被物理学描述的、具有时空属性的事件。而这就意味着,“心理事件”要想与行动具有因果作用,它就必须和行动有同样的属性,并且这些心理事件可以被AM的原则(2)中所说的严格规律所涵盖。显然,疑问源自我们在这里发现的悖谬:一方面,戴维森的意义理论要求,不能给予心理事件以机械论的说明;另一方面,这种对心理事件的理解却与他对这个概念的如下理解相悖:心理事件作为一类物理事件,具有与后者相同的各种(物理)属性。这就使得它们可以和行动具有(严格的)因果关系,而这后一种理解恰恰就是机械论的。 问题的关键在于,戴维森认为,我们可以通过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某些设想揭示出,这种悖谬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如果我们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那么AM就是一致的。他的想法是,我们可以把“心理事件”当作本体论对象,即一类事件。作为事件,它们同样具有(可以被纳入严格规律的)物理属性。(cf.Davidson,1987,p.453)心理学概念是对这些事件的“描述”,即分类。由于在这个过程中,①分类的机制并不依赖于(去观察)这些事件所具有的物理属性,所以我们也就不可能在这些事件所具有的两类属性之间找到严格的规律性;②而且,由于这种分类的机制只是对事件的“描述方式”,那么这个过程就不会干预(心理)事件与(物理)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cf.Davidson,1993,p.12)基于以上两点,戴维森认为,我们可以将看似矛盾的三条原则调和一致。 为了更加清楚地理解这一过程,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戴维森曾明确地说道:我们通常“拥有那些可以涵盖特定事件的规律的证据,这表明一些‘完全的’(full-fledged)因果规律存在着”。(Davidson,1976,p.158)这一表述的意思是,像“玻璃是脆的,通常情况下,玻璃在狠狠地敲击下容易碎”这种规律性概括,我们可以在某些具体的事件(例如,真的去打碎一块玻璃)中找出潜在的物理规律;戴维森认为,行为概括,例如“在通常的情况下,当我想喝水,并且我相信眼前的水可以喝的时候,我会把它喝掉”,也类似于这样的概括。(cf.Davidson,1963,p.16)换句话说,当我在某个时刻具有这样的信念并且付诸行动时,这个信念就描述了在我的头脑中的某些事件。正是它们,在具体的情境中与(那些属于行动的)事件发生了因果作用。 不过,在这里要注意的是,所谓的“描述”仅仅是一种形象的说法,因为对信念的描述只是在展示信念与行动在逻辑和意义上的关联。这个过程并没有告诉我们到底哪些事件是心理事件。但是,由于这些关联确实展示出了行动得以产生的必然性,又因为行动是一类物理事件,所以这种必然性的关系就必须通过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才能实现。而这就意味着,基本理由必须能够对应于某些事件。正是它们的存在,才使得基本理由与行动(在逻辑和意义上)的关联能够对应着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基于这种想法,戴维森认为,当我们将上述例子中的信念和欲望归属于他人或自己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为“喝水”这个事件提供一种因果解释。 然而,我们在上文中看到,在戴维森那里,作为一种心理学描述的“基本理由”只是出现在解释理论中的构造物。这就使得一些哲学家认为,戴维森以常识心理学所提供的行为解释不是真正的因果解释。(cf.Hornsby,p.171)他们指责戴维森:“基本理由”所解释的仅仅是行动的类型(type),即“喝水”这个类型的行动,而不是某个时刻的事件个例(token):某次喝水。(cf.Audi,p.59)这些哲学家认为,要想让心理事件真正成为某个行动的(机械论)原因,那么就必须让“基本理由”精确地对应于某个具体的物理事件,并且让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服从AM的原则(2)中的规律模式,而这就意味着,我们恰恰要找到原则(3)所否定的严格规律。如果戴维森坚持原则(3)是AM的核心原则,那么这些哲学家就据此认为,AM会导致“基本理由”只是一种“副现象”,即它和行动的机械论原因毫无干系。我们认为,尽管这些怀疑并不全然正确,但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基本理由与事件之间的对应关系在本体论上的含义。 正如上面那些哲学家所看到的,如果我们认同戴维森的物理主义一元论,那么我们就必须将那种对应关系理解为同一性关系。而要想理解这种同一性关系如何能够成立,我们就要知道心理事件如何能够具有自然因果性。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找到心理事件与物理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的机械论机制。 唯有说明了这一点,我们才能合理地说,基本理由所提供的行为解释是真正的因果解释。关键是,戴维森如何能解释清楚心理属性为什么不是一种副现象?然而,恰恰是在解释这个关键的问题上,戴维森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一种清晰、合理的证明。下面我们就来具体分析一下戴维森所给出的论证。 三、“心理事件”如何具有自然因果性? 论证1:“非还原性”不会影响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戴维森认为,上面所提到的那种企图把“基本理由”精确地对应于某个具体的物理事件的“还原论”主张是不成立的。理由如下:心理学描述产生于对行动的观察,继而构造出相应的心理学解释;这种构造的过程并没有考虑事件本身所具有的任何物理属性,因而我们也就不能说,构造出来的某个信念严格地对应着某些事件的物理属性。在戴维森看来,说一个事件是心理的,并不是因为事件本身的某些物理属性造成的,也不是因为事件本身就有心理属性。使得一些事件成为心理事件的机制是:当我们产生一个信念a:“如果我口渴,我就会去找水喝。”这一过程并不意味着某些事件瞬间具有了一种对应于a的心理属性;而只是意味着,我们的身体能够展现出一种潜在的反应倾向(disposition)。 无法则一元论使得如下的两个判断成为合理的,即态度就是以特定方式去行动的倾向。这些倾向反过来就是一些心理学状态,而最后又可被归结为物理学状态;……无法则一元论并不认为心理事件和状态仅仅是解释者投射给主体的,恰恰相反,它认为心理事件同物理事件一样是真实的,心理事件同一于物理事件,这些被归属的状态是客观的。奎因将态度的归属作为一种全然的描绘(portrayal),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可以被描绘的东西。(Davidson,1997,p.72) 按照戴维森的观点,基本“倾向”是按照行为主义的“刺激-反应”图式来理解的。与这种简单倾向形成对照,a表明了一种复杂的、潜在的反应倾向的存在。例如,当我有a时,如果我同时有b(“眼前的这杯水能喝”)和c(“我很渴”),那么我就会喝水。如果我还有d:“如果我喝了这杯水,别人就没有水喝了”,我很可能就不会喝。因此,a所表明的倾向仅仅是潜在的,它要和其他的反应倾向一起才能导出行动。 戴维森认为,反应倾向与心理学描述相对应。如果我们去研究这些对应关系,我们就可以发现事件之间的因果作用。但是,单纯的“反应倾向”并没有规定(承载它的)事件在物理学上的类型:任何能够实现它的物理事件都可以作为候选的对象。确定的是,总有那么一种类型的物理事件实际上承载了那种倾向。 因此,心理学描述并不能刻画它所针对的事件的物理类型,而实际上也不需要。现在,戴维森认为,这种对同一性的理解表明,基本理由所给出的因果解释尽管没有展示出心-物作用的具体因果机制,但是,这种解释仍然预示着心理事件作为行动的原因存在着。至于这类事件如何发挥作用,戴维森认为他能用“随附”(supervenience)概念所表明的同一性关系说明这一点。 论证2:在戴维森那里,“随附”概念主要包含两种含义:心理属性随附于物理属性之上,①如果事件e的物理属性改变了,得到e′,那么e′的心理属性将不同于e的心理属性;②如果事件e的心理属性p变为心理属性p′,那么p′所随附其上的事件e′的物理属性必然与e的物理属性有所不同。戴维森认为,在第二个含义中,心理属性表现出了某种“因果效应”(causally efficacious): 如果它们(指心理属性——译注)“影响”(make a difference to)了个体事件(指物理事件——译注)所“引起”的事物,(心理)属性就具有“因果效应”。随附性保证了心理属性能“影响”心理事件所引起的东西。(Davidson,1993,p.15) 结合我们在论证1中对“倾向”概念的说明,这段话的意思是:当我们有信念a时,我们的身体能够展现出一种反应倾向。这种倾向是随附于事件e之上的属性。当信念发生变化,如a变为a ′时,原来e所承载的反应倾向就会变为e′所承载的倾向,而这也就意味着e的物理属性发生了变化。用戴维森自己的话说:“如果随附性成立的,那么心理学属性就会‘影响’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因为它们(指心理学属性——译注)对物理属性有影响。”(ibid,p.14)在这个意义上,反应倾向的变化会“影响”物理事件的变化,而这就表明,心理属性不是被动的“副现象”。 我们认为,戴维森的以上两个论证无效:论证2的有效性依赖于论证l的前提Ⅰ:心理事件同一于某种潜在的反应倾向。笔者认为,这个前提是错误的,戴维森不可能证明它的合理性。理由如下: 在上文中我们已经看到,基本理由是按照我们对行为模式的观察而被构造出来的。这里要注意的是,所谓的“构造”并不是任意的,它要依据行为所体现的规律性:“面对诸对象和事件能够采取不同反应的倾向。”(Davidson,1987,p.450)毫无疑问,解释的过程若想顺利进行,行动就不可能毫无规律,没有规律,行动就是不可理解的。解释的过程只是在用基本理由的涵义来展现行为模式的规律性来源:行动背后的意向。唯有如此,对行动的解释才能按照如下原则进行(溯因)推理,进而展现出导致行为的特定意向,并用基本理由表达出来:“给定了恰当的条件,信念和欲望的确认部分地依赖于它们倾向于产生的行动。”(Davidson,1991,p.216) 换句话说,我们之所以能够在解释过程中“合理化”一个行动,其根源在于:行动是基于特定意向结构的调节而产生的。解释的过程并不是在赋予行动以合理性,而仅仅是揭示了这种合理性。如果接受了这一点,那么我们就不能像戴维森那样,认为“潜在的意向结构”是被“推论”出来的,而只能说,这种推论的过程将意向结构表现了出来。 我们之所以能够在心理学中“根据对信念内容和愿望对象的目的论的解释展现行动的合理性”,是因为意向结构本身就具有这种“目的性”(即意向性)。在解释过程中,我们所做的仅仅是把行动背后的意向结构用心理学概念展示出来,但这种展示并没有告诉我们心理学之外的内容,即它并没有告诉我们那种潜在的意向结构在本体论上到底意味着什么。由于心理学概念并不承诺任何本体论对象的存在,那么心理事件的本体论涵义又能从哪里来呢?换句话说,我们是如何确认Ⅰ所表达的同一性关系的呢?考察事件的物理属性吗? 戴维森的论证1已经否定了这个方案;考察事件所承载的反应倾向吗?显然也不是。因为反应倾向是潜在的,因而不可观察,可观察的东西仅仅是行为模式。由于我们在心理学描述和事件本身两个方面都没有找到心理事件的本体论含义的来源(即戴维森是根据什么确认Ⅰ的),而戴维森又没有给我们提供其他来源作为选项,那么这实际上就意味着:在戴维森那里,Ⅰ仅仅是一种(本体论)设定。 戴维森试图通过这种设定向我们表明,正是基本理由所对应的倾向结构在引起行动时实际发挥了因果作用。但问题是,仅仅通过这种设定,戴维森还不能表明,当行动出现时,是基本理由所对应的哪些事件所承载的倾向在那一刻引起了行动。如果我们无法说明这一点,那么Ⅰ所设定的同一性关系就仅仅是一种毫无根据的假设。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我们能为Ⅰ提供一套“构造性”的证明?这种证明可以为我们展示出:(1)基本理由所对应的倾向结构[a+b+c+…n]→[喝水的行动]的机械论机制①;(2)倾向结构所具有的机械论机制可以完备地“演绎”出意向结构的所有属性,从而表明Ⅰ不仅仅是一种设定,它还揭示了心理事件的本质。但我们认为,这是做不到的,因为要想建立这种构造性的证明,我们首先要分析出倾向结构中的各类基本倾向(即a、b和c所代表的倾向),并通过展示它们之间的动力学机制来表明这种演绎是如何可能的。 但问题是,这种分析的可能性要依赖一个前提条件:我们首先能够分析出意向结构的特征,然后对号入座地寻找这些特征所对应的倾向结构。换句话说,这个证明必定是循环的:证明的过程恰恰要依赖于对被证明的对象的分析。而且更糟的是,由于基本理由并没有暗示出反应倾向的自然种类和力学结构,以及它们之间的因果机制是如何最终导致行为的,所以,基本理由所提供的因果解释并没有,也不可能告诉我们它们所刻画的那些意向结构的本体论涵义。所以,对意向结构的分析不可能为我们对倾向结构的分析提供任何有效的依据。如果这种构造性证明是不可能的,那么我们就无法确定基本理由所提供的因果解释对应于哪些具体的倾向过程之间的因果作用。而这就让我们仍然无法揭示心理事件与物理事件之间因果作用的机制。 综上所述,我们的结论是:不可能为Ⅰ给出一种构造性的证明,它可以展示出基本理由与行动之间的动力学机制。这个结论意味着:Ⅰ不可能告诉我们究竟是哪些事件属于心理事件。由于基本理由所揭示的仅仅是行动得以产生的意向结构,如信念和欲望之间的意义关系,这种意向结构本身与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毫无关联,这就等于说,心理学概念并不是在描述什么本体论对象,所以,戴维森的如下说法就不能成立,即心理学概念与物理学概念的类型不同,但能够用以描述特定事件的“个例”。因为心理事件是按照心理学概念来定义的,如果将心理事件看作是一类事件,我们就会发现,定义心理事件这种本体论对象的东西与本体论无关。而如果一个定义没有说出它所定义的对象应该具有什么属性,那么这个定义就是个伪定义。 因此,戴维森是无法调和上文所提到的那种悖谬的。这种悖谬隐藏在“心理事件”这个概念的涵义中,最终让AM的三条原则不能被调和,这就使得戴维森无法反驳那些对AM的攻击。 四、对戴维森的自然化方案的总结与反思 在上一节中我们看到,戴维森对心灵何以具有自然因果性的论证要依赖这样的前提: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只能被限制在(物质)一元论框架内,从而把传统哲学中的心物关系问题转化为物质内部的因果关系问题。遵从(后期)维特根斯坦的某些观点,戴维森将语言表达式的意义标准追溯到主体之外,即将主体间可观察的行为当作构造意义理论的限制条件。基于这种理解,戴维森并不认为我们可以单独地区分出一些特殊种类的心理学机制,并在对行为进行溯因时,通过援引这些机制来解释行动——他并不认为这种因果解释与心理学解释的地位是等同的。戴维森因此不同意一些激进的还原论观点(如身心“类型同一论”)。这类观点企图通过考察生理学机制(而不是构造意义理论的恰当方式)来理解“理性”和“意向”这些在古典哲学中表达了心灵的规范性能力的概念。但是,在戴维森那里,使得心理学解释具有这种特殊地位的东西并不是这些概念在古典哲学中所表征的精神现象。在他的解释理论中,解释的可能性要依赖于某些特定的理性即“宽容”(charity)原则。在他看来,若在解释者和被解释的一方都没有理性,他们就不可能达成理解。换句话说,作为掌握语言的方法论,解释的过程必须借助于意向性的运作。 尽管戴维森承认,解释理论的这种特征使我们不可以把它看作自然语言的发生学机制,但他还是强调,语言的发生是一种缓慢且连续的发展过程,对解释理论的成功运用预示着我们进入了这个过程的成熟时期。然而,在起始阶段,原始的言语行为完全不必具有意向性。相反,这个过程只是基于有机体(在生物学机制上)的互相刺激与反应。在这一点上,人与低等动物是相似的。 戴维森认为,语言能力是智慧的必要条件,这一条件使人类有别于低等动物。继承了奎因所开启的心理主义的传统,戴维森对心灵的思索起始于这样的问题,即(1)我们如何为自然语言的表达式找出一种恰当的意义理论;(2)这种理论能够与语言的发生学机制相协调。在这两个方面,戴维森都是坚定的“行为主义者”。在他看来,语言的本质在于:它是一种(社会性的)交流媒介,正是在人与人之间能够达成一类公共标准的可能性,为语言现象的存在提供了前提条件。 按照戴维森的观点,这一前提在逻辑上先于我们(作为个体)在具体情况下对语言的使用。基于这种理解,我们就可以将传统哲学中的如下观点,即心灵驱动语言的不同用法(语言只是一种派生的现象),沿着后期维特根斯坦的思路转变成:语言的运作是“用法”在具体环境中的实现。在戴维森看来,如果我们能够以这种反向的角度来阐明语言作为一种自然现象的首要地位,即语言的特性派生出心灵的特性,我们就可以将古典哲学中的身心问题转变为语言与身体的关系问题。而这个问题又可以通过构造行为主义的意义理论来解决。 在这个过程中,古典哲学中的意向性问题将被转化为心理学概念的用法问题;心理因果性问题也可以在行为主义意义理论中转化为行为的意义结构在逻辑上的关系问题。在前文中我们看到,AM理论的一个任务就是要把具有意向性的心灵与不具有这种属性的物质之间的相互作用调和起来,从而弥合布伦塔诺(F.Brentano)在心灵与物质之间所做的区分。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戴维森的方法论的核心,即他要完成一种范式性的转换——将规范性的顺序从“心→身”转变为“身→心”。 按照自然主义的观点,这种逆向转换是可能的,这是因为奎因对先验知识的批评已经为如下观点开辟的道路:不存在先验知识,任何本体论上的对象都是物质的对象,它们独立于人的精神活动而存在,并且构成了所有规范性问题的来源。 遵从奎因对先验知识的批判,以及他所开启的心理主义传统,如下的疑问不复存在了,即如果这种本体论是不成立的,那么这里的逆向转换也不成立。在维特根斯坦那里,我们也许还有这样的疑问,即我们是否有必要将这样的认识:语言的公共属性而不是它的私人属性才构成了语言的本质,进一步拓展到有关心灵现象的发生学机制之中。现在,由于奎因的工作,这些疑问所造成的障碍消失了。 然而,在上文中我们看到,戴维森用自然主义的方法对语言以及心理因果性问题所做的分析并没有让原有的哲学问题变得更少:一方面,戴维森对理性和意向性概念所说的都只是常识性的观点,因而并不会和上述自然主义观点产生直接的关系;另一方面,他又强调,在产生原始语言的自然机制中,并不包含任何的意识和意向性的作用。然而,他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一种可以将这两个方面统一起来的有效论证,将所有的问题都推给“缓慢的发展过程”不会解决任何问题。这是因为,对于后一种自然机制,我们同样可以在低等动物那里找到。换句话说,戴维森还欠我们一种解释,即为什么动物没有语言,没有概念思维?解释语言的形成需要“意向”这一概念,而对意向性的自然化却无法解释动物为什么没有语言。如果戴维森的理论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这意味着,单凭有机体之间(由刺激反应过程所导致的)行为模式的一贯性,还不足以为语言和概念思维能力提供充分的发生学条件。这是因为,“反应倾向”这个概念在认识论上是中性的:在它的涵义中既可以包含意向性的作用,也可以单纯地发源于有机体的行为机能。 因此,如果仅仅以这类自然主义的概念来解释心灵的规范性特征,我们会发现,这种做法只能通过考察自然现象(如行为或生理结构)间的动力学关系来理解心灵何以能够对行为具有规范作用。众所周知,这种做法在康德看来显然是错误的。康德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我们之所以能够以动力学的方式构想自然现象之间的关系,这首先要依赖于感性和知性的运作,正因为心灵所具有的这些认识能力,自然界才向我们(有序地)显现出各种属性和关系。换句话说,当我们在自然现象间的动力学关系中寻找心理学概念的规范性来源的时候,这种做法就已经预设了心灵的各种机能的存在。而且更为关键的是,作为这种方法的核心,“溯因推理”是难以被自然化的。在康德看来,这个概念的可能性要以“因果关系”概念为前提,而后一个概念则是知性能力中的基本概念。 由此可见,戴维森和奎因的心理主义观点是成问题的。这一主张的核心是:不存在先验知识,一切知识都是经验知识。与这种观点针锋相对,弗里德曼(M.Friedman)曾明确指出,尽管自康德以来的数学和物理学都发生了范式性的转变,但是,这并不能抹去数学在这些转变中的独特的基础性作用:“正如康德所表明的那样,数学一直被用作构造特定的物理学理论,正是这种构造作用使得物理学(无论是牛顿的还是爱因斯坦的)成为可能。”(Friedman,p.13)因为“正是在特定的数学构造中,具体的物理学理论才会面对经验的检验,只有在这个意义上,经验才构成一个法庭。按照这种理解,说作为理论背景的数学知识也要面对这个法庭则是荒谬的”。(ibid,p.14) ①a、b、c延续上文例子中的含义,但在这个图式中代表具体的反应倾向。箭头表示因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