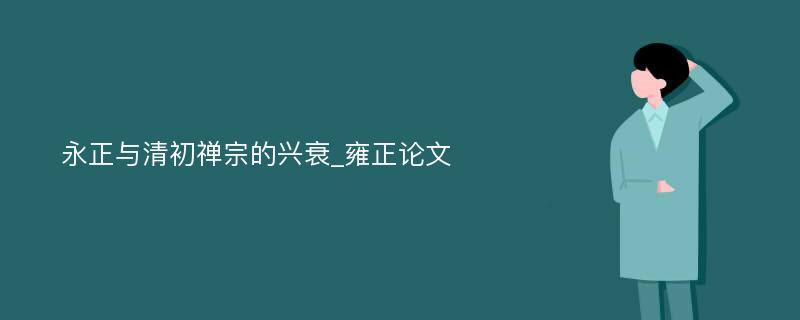
雍正与清初禅学之兴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雍正论文,清初论文,兴衰论文,禅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94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77(2007)09-0103-04
“释老之教行乎中国也千数百年,而其盛衰每系乎时君之好恶……元兴,崇尚释氏,而帝师之盛,尤不可与古昔同语。”[1]元、明两代皆因时君之垂顾,遂至喇嘛、禅僧出入宫廷,以帝师、国师参知政事,禅宗也因之盛而不衰。
清初王学衰微,士人有鉴于亡明的教训,而倡经世致用之学。朝廷虽昌明程朱理学,但因对喇嘛教的信顺,连带对禅宗思想予以推奖。顺治、康熙、雍正、乾隆清初四帝,无不与禅宗有密切关系。尤其是自号圆明居士的雍正皇帝,不仅优渥僧人,推奖禅宗,而且以人间教主、超等宗师自居,以宫廷为禅堂,以王公大臣为法友,宣讲禅法,著书立说,直接参与僧争,为禅门宗派定是非,把禅宗思想与政治完全焊接在一起。禅宗思想因雍正的推奖而耀人眼目,禅宗也因教主皇帝的推奖而每况愈下。
雍正,讳胤祯,康熙四子,幼耽书史,博极群书,既究宋学之源,也明禅家之旨。相传与十四子胤礽争皇位一事,胤祯得喇嘛僧势力的支持而登帝位,说明其与佛家有存亡绝续的政治关系。这也是佛教入世转向中的一个特点。据其自述,少年时即喜内典,从喇嘛僧章嘉呼土克图问道,并验之当时禅僧迦陵性音。他“谛信章嘉之乘示,而不然性音之妄可,仍勤提撕”,在不断地对性音以及禅门的批判中,而自证禅学。雍正以章嘉为“证明恩师”,并强调“仍勤提撕”以及对古今一些禅僧、禅风的批判,说明他以人君而兼教主,有意自创禅学的思想特点。《历代禅师后集后序》比较全面地揭示了雍正自己禅学思想形成的过程。其重点强调的是不蹈陈言,以自得为贵。这也是符合禅宗思想本旨的,尽管其具体所指不一定正确。在他谈到早年对禅宗的认识时,有一段颇富戏剧色彩的论述:“朕少年时喜内典,惟慕有为佛事,于诸公案,总以解路推求,心轻禅宗,谓如来正教,不应如是。”[2]这就是说,其喜内典,也是崇尚有为事业的,这是元、明、清乃至历代帝王利用佛教的普遍特点。不过,雍正还是富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皇帝,其对公案则强调以知解而求,故轻视“公案禅”的思维方式,这也是学者习惯于理性思维的特点在这位皇帝身上的表现。后来,与章嘉呼土克图“接茶话者十余载,得其善权方便,因知究竟此事”。[2]但其“自知未造究竟,而迦陵音乃踊跃赞叹,遂谓已彻元微,儱侗称许”,章嘉却说他“如针破纸,虽云见天”,也不过一孔之见。性音拍马屁,并未得雍正赞许(当时禅门风气,亦可知一二),章嘉之说,却“深洽朕意”,仅此可知,这位皇帝在学术上还是有“不知为不知”的自知之明。[2]
性音尝劝雍正研辨五家宗旨,雍正对其“口传”之说大不以为然,并在批判性音的同时,表述了贵在自得、五家一宗的综合思想。“口传耳受,岂是拈花别传之旨?堂堂丈夫,岂肯拾人涕唾?从兹弃置语录,不复再览者二十年……夫五家宗旨同是曹溪一味,不过权移更换面目接人,究之皆是无意味语。”[2]他反对口传耳受,鄙弃拾人涕唾,因此二十年不阅禅宗语录,实际上是对五家宗旨的否定。特别是他认为,五家宗旨不过是改头换面的不同接人方法,尤其反映了他向慧能禅学回归的思想倾向。为了说明这一点,他对一花五叶有他自己的解释。他认为五叶并非五宗,而是“由可至能”的五代传人。由于一花五叶实系传说,怎么解释都无可证实。但雍正此说显然是为了否定“五宗禅”而立论的。所以他又强调:“五宗所明,同是大圆觉性……朕既深明本旨,只图真实,以辨平生……迨即位以来,十年不见一僧,未尝涉及禅之一字。”[2]表明他所信奉的禅宗本旨,与“前后参差”,“牵合附会”,“妄定宗旨”的“五宗禅”决非一致。
为了说明他自己禅学思想的合理性,雍正也是有破有立的。他说:“今见去圣日远,宗风归地,正法眼藏垂绝如线,又不忍当朕世而听其滔滔日下也,乃选辑从上宗师吃紧为人之语,刊行天下后世”,[2]可见,雍正之所破,主要是针对禅宗末流之弊,并在此基础上振兴曹溪之真传。他痛斥当世禅僧云:“乃近代宗徒,动辄拾取他人涕唾,陈烂葛藤,串合弥缝,偷作自己法语,灾黎祸枣,诳惑人家男女。其口头实能滑利者,便鸣钟击板,竖拂惊拳……礼拜者作出身之活路,棒喝者成漂堕之黑风。如此心行,称曰度人,佛祖门庭岂不污辱?”“外托禅宗,心希荣利之辈,必有千般诳惑,百种聱讹。或曾在藩邸望见颜色,或曾于法侣传述绪言,便如骨岩、木陈之流,捏饰妄词,私相纪载,以无为有,恣意矜夸,刊刻流行,煽惑观听。此等之人,既为佛法所不容,更为国法所宜禁,发觉之日,即以诈为制书律论。”
应当说,雍正对当时禅风之抨击是激烈而中肯的,对禅门之显贵,如道态之流,狐假虎威、欺世盗名行为的批判,也是一针见血的。但他却要以王权干予僧事,用国法制裁“妄词”,则又反映了他要把佛法纳入世法轨道的思想倾向,这也同当时文字狱的思想文化专制主义相一致。对明清的一些禅宗史作,他也是一概予以否定的。他说:“朕阅《指月录》、《正法眼藏》、《禅宗正脉》、《教外别传》诸书,所选古德机语皆错杂不伦,至于迦陵音所选《宗统一丝》者尤为乖谬。古人语句专为开人迷丢,后人选集专为垂诸久远。禅宗之统,实危如一丝也。”[2]不仅如此,他还专门批判了历代狂禅呵祖骂祖之风:“如德山鉴,平生语句都无可取,一味狂见恣肆,乃性音选《宗统一丝》……专录其辱骂佛祖不堪之词,如市井无赖小人诟谇,实令人惊讶不解其是何心行……如南泉愿牧水牯牛公案,最为下品……而性音则于其它语句概置不录,所录二条,其一即是此条。具此凡眼,有何圣见可除?辄敢见人呵佛骂祖,便生欢喜采辑,鸱鼠嗜粪,斯之谓矣。”[2]呵佛骂祖,虽不一定就是超越佛祖的自在精神,但雍正诃斥禅宗末流这一流风,也不反映其对佛祖的虔诚信仰,其目的仍在于强化思想文化之专制。
客观地说,无论出于什么目的,雍正对禅宗的倾心、嗜好,以及对禅宗思想研究的贡献都远在历代皇帝之上,尽管他也难以避免“拾人涕唾”,其言行也常以禅机自诩。《御选语录》的第二部分,即《和硕雍亲王圆明居士语录》,便是他未登基时谈禅的记录。如:“一日王云:这件事,因在内所以不在外,因在外所以不在内,因不在内外所以在内外,因在内外所以不在内外……此事须实踏不二心地,非知识可解者。参!”[3](和硕雍亲王圆明居士语录)这显然是对超四句、绝百非的实践。雍正也是力图把握不落两边的超越精神。又如:“晚归寝室,呼从者点灯来。从者擎灯入室,王将灯吹灭,云:点灯来。从者重燃灯方至,王复吹灭,云:点灯来。从者云:王醉也。王喝云:速点灯来!从者急燃灯,入室擎立。王云:灯下仔细观看,余醉也,乃汝醉也?”[3](和硕雍亲王圆明居士语录)雍正酒后归寝,与侍者大显禅机,如果不是醉的话,对牛弹琴,不是更显得可笑?但雍正却煞有介事地选入其语录,则也可见其拾禅僧之涕唾,故弄玄虚而附庸风雅了。
雍正即位后,也并非如其所言,十年不谈禅之一字,而且,行政之间,常与王公大臣以禅法而谈世法,御批中时不时地显露其莫测高深之禅道。雍正二年(1724),抚远大将军年羹尧上书,这位皇帝宗师阅后禅兴大发,其批文曰:“京中有一姓刘的道人,久有名的,说他几百岁,寿不可考。前者怡王见他,此人谩言人之前生,他说怡王生前是个道士。朕大笑说:这是你们前生的缘法,应如是也。但只是为什么商量来与我和尚出力?王未能答。朕说不是这样真佛真仙真圣人,不过是大家来为利益众生,栽培福田,哪里在色相上着脚。若是力量差些的,还得去做和尚,当道土,各立门庭,方使得。大家笑一回。闲写来令你一笑。”[4]
雍正不仅以和尚自居,而且也常自称释主,他还有《自疑》诗云:“垂裳宇内一闲客,不衲人间个野僧”,也是把他自己比作不着僧服的皇帝和尚。他给年羹尧写的这一番话,表面看来与奏文无关,其实也是借题发挥,欲以禅道资助政道,即所谓真佛、真仙、真圣人,均以“利益众生、栽培福田”为鹄的,正反映了他那有为的禅学观念。他还说,那些力量差的还得去做和尚、当道士,同样也表现了当时禅宗思想入世的倾向。
皇帝谈禅说偈,以超等宗师自居,济世渡人,大臣敢不效仿,亦步亦趋?于是公庭而为道场,君臣结为法侣。据雍正介绍,在他的开悟下,一年之内,遂有王大臣八名进至觉境,其中亲王四人,郡王一人,满汉大臣三人,而得这位皇帝宗师的印可。他说:“朕自去腊,阅宗乘之书,因遇辑从上古德语录,听政余闲;尝与在内廷之王大臣等言之,自春入夏,未及半载,而王大臣之能彻底洞明者,遂得八人。夫古今禅侣……乃谈空说妙者,似粟如麻,而了悟自心者,凤毛麟角。今王大臣,于半载之间,略经朕之提示,遂得如许人一时大彻,岂非法会盛事!”[3](当今法会御制序)看起来,雍正对他自己的禅学素养是颇为自负的。他不仅能自悟、自觉,而且悟人、觉他,即教人了悟自心,而在丛林、行脚禅僧之上。禅宗思想不仅由缁衣而流入居士,而且由丛林而占据宫廷,的确可以谓之“法会盛事”。这也是清初禅宗思想发展的一大特点。
雍正的禅学观念同样也带有综合和世俗化的性质,集中表现在《御选语录》和《拣魔辨异录》之中。前者是对历代著名禅师,包括与禅有关的僧人、道士语录的选辑,并以序的形式,阐发他自己的禅见,主要是立。后者则是干预圆悟、法藏师徒争论的记录,有破也有立。它们既是雍正禅宗思想的集粹,也是清初禅学世俗化表现的一个方面。
《御选语录》编选于雍正十一年(1733),所录除历代禅师的语录外,还有如僧肇、寒山等禅门外僧人及紫阳真人张伯端的语录。每篇之后另撰序言,于评述中表述他自己的禅学思想。首先,他在总序中道出了编选语录的宗旨。他说:“念人天慧命,佛祖别传,双眉拖地,以悟众生,留无上金丹以起枯朽,岂得任彼邪魔瞎其正眼,鼓诸涂毒,灭尽妙心?朕实有不得不言,不忍不言者……是数大善知识(指序中引十二禅师及张伯端等),实皆穷微洞本,究旨通宗,深契摩诘不二之门,曹溪一味之旨,能使未见者得无见之妙见,未闻者入不闻之妙闻,未知者彻无知之正知,未解者成无解之大解。”其不得不言、不忍不言的就是其谓之“去圣遥远,魔外益繁,不达佛心,妄参祖席”的邪魔之风弥漫当时禅林。鉴于此,他欲以诸大善知识的真知灼见,即曹溪一味之旨,解禅门于倒悬。也就是说,要在禅道极度衰落之际,重新振兴六祖慧能的禅宗思想。就此而言,也可以说是切中当时禅宗思想要害的。
事实上,雍正尽管以教主自任,但他不可能、也没有对禅宗思想有任何创造性的意见。他呵斥禅宗末流,欲以“曹溪一味”的“雍正禅”取而代之。然而,行动之间,又难免拾古今禅者之涕唾,取公案之葛藤,串合弥缝而为法语,或游戏于宫廷,或卖弄于臣工,实无可取之处。然而,《御选语录》对禅宗思想的理解还是有其时代意义的。尤其是在各序中,他直以己见进退禅学,在莫测高深的禅海之中,时时流露出综合与入世的倾向。
雍正在其序中,一再强调“夫五家宗旨同是曹溪一味”,目的就是要使一花五叶的五宗禅回归于慧能的禅宗思想。他还指出:“兹集所选历代禅师,除六祖外一百五十六人语句,固皆本分极则……与前选中诸大善知识无二无别”,[2]说的也是综合五宗的意思。至于他“黜陟古今”,正是为了进一步确立其综合五宗于曹溪的思想。他指出,“如傅大士,如大珠海,如丹霞天然,如灵云勤,如德山鉴,如兴化奖,如长庆棱,如风穴沼,如汾阳昭,如端狮子,如大慧杲,如弘觉范,如高峰妙,皆宗门中历代推为提持后学之宗匠,奈其机缘示语,无一可选者”,[2]一下子否定了唐宋以下(仅高峰为元代禅僧)各宗的许多著名禅僧。比如他斥责德山“除一棒之外”,“其垂示机缘,却无一则可采”;马祖对大珠“赏叹之说,未必确实”;宗杲“数百年望重海内之人,其武库全录(指宗门武库)”“一无可取”,“而支离谬误处甚多”等等,强调他们对曹溪禅的背离。对于后世禅僧津津乐道的呵祖骂佛之举,雍正不仅视之为大逆不道的行为,而且也从理论上予以驳斥。他说:“据丹霞之见,木佛之外,别有佛耶?”而背佛坐,向佛唾,“此等见解与丹霞同,但知扫目前一像,却不觉自执千像万像矣”。[2]应当说,雍正对禅宗“于相离相”和执相的区别,还是把握得相当准确的。
雍正不仅综合五宗,而且综合禅教,综合禅净。他说:“朕于肇法师语录序,已详言宗教之合一矣。”[2]其实,他特别选录僧肇语录,目的虽然是为了说明讲经的重要性,说明经教也自有符契教外别传之旨,但客观上也证明了僧肇对禅宗思想形成所作的贡献。正如他说,如僧肇诸论,“以此讲经,正是不立文字”,[3](僧肇编序)如此,不立文字与讲经相提并论,妙悟的禅也就与解悟的教不期而合了。
于晋宋佛学,雍正特别推崇僧肇和慧远,他说:“言净土者推远公,言讲经者推僧肇”,[3](僧肇编序)“北则什公讲译经文,南则莲社诸贤精修净土”,[3](莲池编序)这些话同样表明了他禅净合一的思想倾向。《御选语录》之十三卷,专门选录袾宏之“融合贯通”禅净之言,“以表是净土一门”。[3](莲池编序)不过,在此他还特别指出,修习净土,必须以禅门宗旨为指导,如得正悟,花开见佛,也就是“直指心传”。否则,“如学人宗旨不明,即将南天阿弥陀佛一句作无意味语,一念万年,与之抵对,自然摸着鼻孔”。[3](莲池编序)他这里实际上也是把念佛当作话头进行参究的意思。可见,雍正禅净合一的净土观念,还是禅宗唯心净土的思维方式。
雍正综合的思想,还表现在对道教的综合。其将张伯端的《悟真篇》作为禅门要典选入《语录》,应当说是符合宋元道教禅化的实际情况的。他说:张伯端所作颂偈三十二篇,“一一从性地演出西来最上一乘之妙旨”,“篇中言句,直证了彻,直指妙圆,即禅门古德中,如此自利利他,不可思议者尤为希有”,比禅宗还要禅宗,连一些禅师,如薛道光等,“皆皈依为弟子”。[3](紫阳真人编序)这些话虽然有些言过其实,但其中浸透着大量的禅宗思想却是事实。因此,雍正把张伯端言论作为禅宗思想予以选录,不是没有道理的。
应当看到,雍正对禅宗思想的梳理、讲习,归根结底,还是要将其纳入治世之道,因此,也就表现了其禅学的入世精神,表现了融禅法与世法为一体的倾向。他说:“古之圣王,其于高世之士,必资其薰习身心,以为宰制万事之本”,清朝自世祖始,也是把禅门古德作为高世之士,将禅学作为“宰制万事之本”的,所以,于“万机余暇,与玉琳琇、茚溪森父子究竟心性之学,一时遇合,盖与黄帝、成汤之事无二无别,非我朝夙有崇僧之习而然也。”他告诉人们,与禅者心有灵犀,声气相求,并非由于崇僧之习,而是求助它们“宰制万事”的道理。而玉林通琇父子之书,“阐扬宗乘之妙旨,实能利人济世”,所以他才予以“采辑校刊,传示后世”。[3](玉林茚溪编序)编序中这类话虽然不多,但此言足以表现雍正以禅学翊佐王化的主体意识。特别是他反对呵祖骂佛,并非单纯由于此狂禅之风有违禅道,从根本上看,还是从“有为佛事”这个方面而发的。他说:“若此,则子孙焚烧祖先牌,臣工毁弃帝王位,可乎?”[2]他的答案当然是“不可”。于是,禅宗反对权威崇拜的超越精神,在雍正这里便成为维护传统秩序、巩固封建专制的工具,其禅学的入世倾向也就不言而喻了。
还应当指出,雍正在序中一再强调禅宗不立文字,“悟不在言”[3](永嘉编序)、“超情绝解,直指自心”,[3](圆明居士编自序)“随文生解,总无文涉”,[3](寒山拾得编序)“故无语言文字可立”[3](圆明居士编自序)等,似乎也是反对知解,因而与主张文字禅的时代风气不合。然而,他又大量地编选、自撰语录,甚至把僧肇讲经、道士悟真、寒山、拾得之诗文韵语也作为曹溪一味之旨,显然不能说他是排斥语言文字的。事实上,在他看来,无论是俗语、韵语、绮语、教语,只要有助于悟解西来最上一乘之妙旨,有助于禅学之把握,都是禅语!在其他地方,他更是明确指出:所谓教外别传的禅宗,“可以无言,可以有言”,关键在于“言言从本性中自然流出。”“世尊四十九年所说,古锥千七百则公案,总是语言文字。”[5]如此解释,与其不立文字之说,显然是自相矛盾的。其中固然与禅之不落言诠的性质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为了限制思想、言论自由,而借助禅宗的一种形式,与当时的文字狱具有类似的性质。至于他对语言文字的强调,则又是出于对法藏、弘忍批判的需要,这不仅不能自圆其说,反而暴露了他思想上的随意性以及理论上的不成熟,也可见其禅学完全是随顺其世法的。
如果说《御选语录》是为了阐扬曹溪一味之旨,重兴禅学正脉,而综合五宗,虽然终极在于用世,但仍保留了学术探讨性质的话,那么,《拣魔辨异录》则纯粹是对临济宗门内部纷争的政治干预。
如前所言,圆悟与法藏、弘忍师徒关于宗原之争,表面上看来是释迦拈花与威音圆相,直指人心与五家宗旨之争,事实上,争论的焦点却在不同的方法上。其间既有义理、方法之争,其后更有意气用事的个人冲突。无论怎么说,这也是禅宗内部的事。然而雍正皇帝却于一个世纪以后,旧话重提,以人王而兼教主的身份,著《拣魔辨异录》直接干预僧争。他痛斥法藏、弘忍之说,将其书尽行毁谤,所有徒众,“著直省督抚详细查明,尽削去支派,永不许复入祖庭”,[5]明末清初之僧争也就此结束,然而,其咄咄逼人的文化专制主义,施之于禅宗,也可以说是禅宗思想史上的不幸!
《拣魔辨异录》对法藏、弘忍的驳论,不过是重复圆悟辟妄之意,不仅没有什么创见,而且粗言恶语,连篇累牍,对墓中之枯骨发泄着刻骨的仇恨。魔藏、魔忍、魔说、魔子魔孙充溢字里行间,实在有失人君之体。他首先指出:“佛祖之道,指悟自心为本”,仅从字面上看,此乃禅门老调,但在这里,明显偏向于圆悟所谓佛祖拈花的棒喝禅。接着他又明确地说:圆悟、圆修语录,“言句机用,单提向上,直指人心,乃契西来的意,得曹溪正脉者。”法藏之言“全迷本性……肆其臆诞,诳世惑人,此真外魔知见。”于是,他便以“有德有位”的皇帝身份,起而辟此魔说。然而,他也只能循着圆悟的思路,围绕所谓威音O相和禅宗方法问题而陈述己见:“今魔藏立一O相,为千佛万佛之相,以袈裟缕缕,为宗旨所系……而魔嗣弘忍,以僧伽难提遇童子持鉴直前,为从来有相可示,证其魔师一O之象为不悖。又以多子塔前袈裟围绕一事,作袈裟为宗旨所系之明证。”“悟、修皆以一棒指人,魔藏斥曰一橛头禅……古人不得已而用棒喝,原为剿情绝见,直指人心,魔藏若以情见解会,乖谬之甚。古不云乎,一棒喝不作一棒喝用,何尝执此一棒一喝也。魔意但欲抵排棒喝,希将伊所妄章之一O相,双头四法之实法以邀奇取胜。”[5]
其实,就禅宗历史而言,无论是法藏谓之威音O相,还是圆悟乃至传统尊奉的佛祖拈花,都是想当然的附会之说,原本就没有什么是非可言。只不过法藏欲强调五家宗旨,抬出威音王佛而对抗拈花之说;圆悟为突出棒喝的方法而固守单传直指。不同的宗原之说,均表现了禅门综合的意向。方法的冲突也是积不相能,各执其说的,虽然不能说圆悟完全是错误的,但法藏以棒喝为禅之一弊,显然是符合禅宗思想发展趋势的。然而,“行修齐治平之事,身居局外,并非开堂说法之人”的雍正却认为他“洞知魔外之情,灼见现在魔业之大,予识将来魔患之深”,[5]而又不得不言,不忍不言了。
事实上,雍正也讲不出什么道理来,但他又要以人主的权威干预僧争,对于禅僧内部不同意见、不同方法乃至门户之见作出一个是非的裁判,也只有强词夺理并付诸行政手段了。比如他说:“任伊横说竖说,能出三藏十二部之外乎?”“若要诠理论文,自有秀才们在,何用宗徒?”“可知法藏父子之魔形,从数百年前,赵州早为判定,更不必到眼始知也”等等。
雍正何以对法藏、弘忍如此切齿痛恨,亲自撰文八卷,与早已死去的和尚打这场笔墨官司,并传谕直省督抚,晓示天下宗门?实在是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奇闻,也决非思想学术之争所能解释的。从表面看,它反映了清初限制思想自由的文化专制主义。然而,文中除骂詈之外,处处给人以言犹未尽的感觉。这就说明,在强词夺理的背后一定还有不可言喻的原因或者是背景。其文特别强调剪除魔见,并肆力抨击法藏一系的魔子魔孙,是很值得玩味的。他说:“今其魔子魔孙,至于不坐香,不结制,甚至于饮酒食肉,毁戒破律,唯以吟诗作文媚悦士大夫,同于娼优伎俩,岂不污浊祖庭!”“当日魔藏取悦士大夫为之保护,使缁徒竞相逐块,遂引为种类,徒至今散布人间不少,宗门衰坏,职此之由。朕今不加屏斥,魔法何时熄灭?”“如法藏、弘忍辈,唯以结交士大夫,倚托势力,为保护法席计。士大夫中,负员作家居士之名者,受其颟顸,互相标榜……况乃不结制,不坐香,惟务吟诗作文以媚悦士大夫,舍本逐末,如是居心,与在家何异。”[5]从这些话中可以透见,雍正深恶痛绝的有两个方面:一是法藏一系取悦士大夫,倚托势力;二是法藏门下散布人间,聚为种类。显而易见,其抨击死和尚也不过是项庄舞剑,意在那些活着的“魔子魔孙”们。当然,如果法藏一支取悦的是那些改事新朝的士大夫,结的是效忠于清王朝的种类,他们也就不至于遭此涂毒,甚至会受到这位教主的赏识。然而不幸的很可能是,他们取悦与所聚结的都是清王朝的异己力量。
平心而论,对于法藏、缁素,两界也都是毁誉参半、褒贬不一的。与法藏同出圆悟门下的牧云通门曾作《摄魔论》等五论,贬抑法藏、弘储师弟。他说:“夫言谤师毁师,憎师嫉师,法中大魔,乃《华严经》中普贤菩萨语耳?以是观之,汉公又非有胆气强有力者,似未可谓之魔。但挠乱正法,谓之魔亦可。”[6]通门的意思是说,法藏虽无胆气毁谤师门,但其淆乱正法,也可以说是魔,实际是想从根本上否定法藏在临济乃至禅宗中的地位。然而,清初诗坛宗匠,官至刑部尚书的渔阳山人王士禛却为法藏鸣不平,并誉之为“末法中龙象”。他说:“予尝读三峰藏禅师语录及《五宗原》,以为末法中龙象。其提《智证传》,阐发临济汾阳之旨,欲远嗣法于寂音,亦天童之诤子也。而牧翁《列朝诗》谓三峰之禅,为孽于世,诋其如此,岂别有谓耶?”[7]王氏虽是门外之言,但却不带宗派色彩,可谓之旁观者清,他怀疑诋法藏“为孽于世”别有原因,不能说全无根据。清初曹洞巨子觉浪道盛,也是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客观地评价说:“济下已仆之宗,决不可无天童,又不可无三峰,更不可无夫翁。问谁为灵岩知己,莫不是栖霞老侬。”[8]
争论归争论,是魔非魔,也是各人见仁见智之说。道盛之言,避免了不必要的争论,又肯定了双方的历史地位,争论也早该结束了。雍正却又牵出旧案,口诛笔伐魔藏、魔忍、魔子魔孙,不能不说其别有所图。丁闇公有《明事杂泳》提及汉月法藏云:“三峰汉月古禅堂,钟板飘零塔院荒,是道是魔吾不解,山门竟有蔡忠襄。”此诗隐晦曲折,但显然是歌颂法藏一系与清朝不合作态度的。蔡忠襄字懋德,是法藏的及门弟子。其于太原围城时曾慷慨陈词曰:“吾学道多年,已勘了生死,今日正致命时也。”故丁氏有“山门竟有蔡忠襄”语。黄宗羲也曾记其事曰:“潭吉忍在安隐作《五宗救》,以申三峰之屈,大概多出仁菴,三峰之道赖以不坠。”[9]他的意思是《五宗救》出自仁菴之手笔,仁菴名岐然,字秀初,也是明亡后逃禅,而全其志节者。黄氏还有诗咏其事曰:“曾入南都防乱揭,旋参安隐救宗书。”[10]可见法藏不仅有拼死抗清的弟子,而且也颇受亡明、清初士大夫的赞誉。其“魔子魔孙”也多为这一类的不合作者,即陈垣先生所说“门多忠义,亦易为不喜生嗔”,[11](p62)所以雍正对他们“吟诗作文”、与亡明士大夫沆瀣一气的不合作行为,自然是痛心疾首而又讳莫如深,非予以制裁而不可了。
统观雍正之禅语及其对僧争的直接干预,可以这样说,禅宗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全面渗透至雍正时已经达到了极致,以至于君临天下的最高统治者也不得不借谈禅来辅佐王化,并以专制主义的手段,迫使禅宗思想纳入其政治的轨道。雍正在批斥法藏时说了一句特别符合当时禅宗实际的话:“朕意禅宗莫盛于今日,亦莫衰于今日。”“开堂秉拂者不可胜计”[5]固然是盛的标志,皇帝、王公谈禅悟道尤其是盛的标志。但是他不会承认,正是因为他采取了文化专制主义的干预,久已衰颓的禅宗也就濒临绝境了,禅宗思想及其对中国文化的渗透也就真正成为强弩之末。宗门的窳败,禅宗思想的衰歇,终于唤起学者去承担对禅宗思想文化进行梳理、扬弃的使命感。禅宗思想的入世转向,应当说是自清初以后,由学者予以全面推动的,也可以说是禅宗思想近代转型之发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