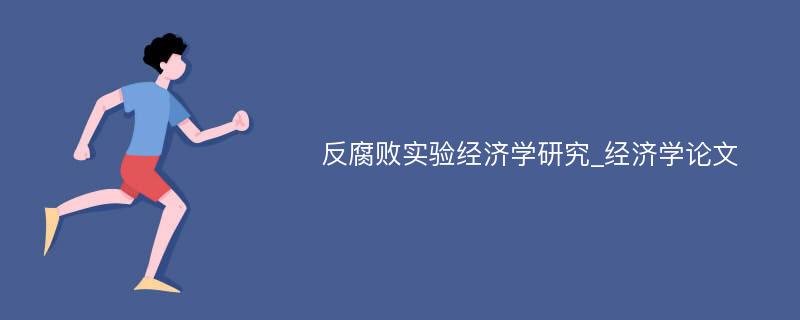
反腐的实验经济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学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感谢匿名审稿人意见,文责自负。
一、引言
腐败并不是一个新现象,在任何社会的任何历史时期都存在着腐败活动,并且腐败阻碍了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尽管早期研究认为腐败可以充当经济发展的“润滑剂”促进效率提高,可是,实证研究表明,腐败严重阻碍经济发展(陆挺,2005;Mauro,1995;Meon & Sekkat,2005),造成不公平与贫穷(Gupta et al.,1998;Olken,2006),影响教育、卫生与公共设施资金的配置(Reinnika & Svensson,2004;过勇和胡鞍钢,2003)。正因为腐败对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巨大负面影响,这促使学者们从理论与实证两个方面去研究造成腐败的原因,以及寻找反腐的政策措施。
尽管在过去的20多年中已经有许多腐败的实证研究,并且也确定了一些影响腐败的经济、社会以及制度变量,可是,这些研究主要依靠跨国数据和对腐败的主观测量。比如,在已有的跨国研究中被广泛采用的代表性指标包括:国际透明组织(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公布的腐败感知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和行贿感知指数(Bribery Perception Index),国际商务组织(Business International)公布的一组反映各国腐败程度的指数。在一项基于印度尼西亚修建公路项目的实地实验研究中,Olken(2007)为了验证腐败的主观测量的有效性,在获取村民的腐败感知数据的同时对腐败进行了直接测量。研究发现,虽然村民的腐败主观感知确实反映了道路修建中的部分腐败活动,可是,计量分析显示,在道路修建中,由直接测量所得到的费用损失(腐败)增加10%,而村民所感知到的腐败概率仅增加0.8%,这说明腐败的主观感知测量并不能够准确测量真正的腐败水平。另外,现有的实证研究还存在两个问题:(1)腐败行为的隐蔽性使得许多腐败活动难以通过实地调查来获取高质量数据,这使得计量模型的因果关系识别性差、测量的偏误以及省略变量的存在造成研究的解释性存在问题;(2)腐败行为的非法性给通过调查获取腐败数据带来了困难,这造成了适合微观层面腐败行为研究的数据库难以建立,从而难以研究个体腐败行为。为了克服这两个问题,实验研究通过模拟腐败决策环境,可以直接观察到个体层面的腐败行为,这对于现有的腐败实证研究是一个重要补充。
本文在现有反腐实验研究文献基础上,从实验研究方法、反腐政策、反腐制度以及其他影响腐败的因素等方面进行了综述性分析。希望这些来自微观层面的研究结论可以成为其他有关腐败实证与理论研究的补充,为反腐政策与制度的制定提供一定指导作用。
二、反腐研究中的实验方法与基本框架
正如科学家通过对果蝇的研究来理解人类的基因组、通过对链接着木块的滑块模型来研究地震规律一样,一个合理设计的科学实验研究是如今人们获取社会科学知识的重要途径(Falk & Heckman,2009)。在20世纪60—70年代开始发展起来的实验经济学为经济研究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实验方法为经济学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复制性和可控性,使经济学更加科学和完善。最近几年,作为一种规范化的经济研究方法,实验研究方法在腐败的特征、影响因素以及反腐政策研究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它已经成为我们获取腐败与反腐政策知识的重要途径。
(一)官员腐败的基本分析框架
在现有的反腐实验研究中,不同的学者针对不同的反腐政策或制度进行了研究,这显得比较零乱。为了对于反腐政策与制度有一个整体的认识,在这里我们尝试从官员腐败的激励视角,利用一个简单的分析框架来分析官员腐败决策(Olken & Pande,2012)。假设官员可以从政府部门获取的工资为w,若他们被政府解雇了,那么可以获取的外部收入是v。官员自己决定是否从事腐败活动,如果他从事腐败行为,那么被发现的概率是p,被发现后,政府将解雇该官员,因此,他将仅能得到外部收入v;如果官员从事腐败而没有被发现,那么他的收入将是工资w加上腐败收入b,不过,官员从事腐败将承担一个心理成本d。在均衡时,官员从事腐败活动的充要条件是w-v<1-p/p(b-d)。根据这个分析框架与腐败均衡条件,我们可以采用的反腐政策与制度有:通过提高惩罚力度来降低官员的外部收入v;提高官员的工资w水平;提高腐败被发现的概率p或者影响当事人对于该概率的主观判断,为此,我们可以通过采用多种不同形式的监督措施、举报、赦免制度,实施信息公开制度,提高官员活动信息的透明度;通过影响官员腐败收入b的取值也可以实现反腐的目的。Shleifer & Vishny(1993)认为腐败官员的行为和利润最大化的企业一样,贿赂的市场结构决定了腐败收入(腐败服务的价格)与腐败水平。比如,本文分析中的中间人与“四眼原则”等结构因素都影响着腐败收入b的值。最后,腐败的心理成本d越高,那么官员腐败的概率就越低。不过,不同官员的腐败心理成本具有异质性,这种异质性来自多个方面:官员所处的文化环境异质性影响腐败的心理成本;官员的性别也会带来心理成本的异质性;根据社会偏好理论,腐败行为对外部人所造成的负外部性会影响官员的心理成本;其他官员是否腐败也会影响官员的腐败行为决策。可见,基于这个简单的分析框架,通过比较静态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多种反腐政策与制度。
(二)反腐的实验方法
目前,有关腐败的实验研究主要采用实验室实验方法,而部分研究采用的是实地实验(Field Experiment)方法。这主要是因为相对于自然生成的数据,建立在可控制与随机性基础上的实验室数据在设别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时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具有更好的内部有效性。不过,实验室实验研究的内部有效性往往是以牺牲外部效度(External Validity)为代价的(List,2006)。因此,研究者需要获取腐败实验室实验研究结论的外部有效性,并且寻找科学的补救措施。对此,在一定程度上,在实验室实验研究的基础上,实地实验方法在腐败研究中的运用可以获取研究结论的更好外部效度。因为实地实验将经济实验从实验室中推广到了自然环境中,在真实的社会经济环境下进行受控实验,以识别因果关系与揭示潜在的作用机制,这在实验室实验和自然产生的数据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实现了单独在实验室和不受控制的数据中都不能完成的任务(List,2006)。因此,在本综述的行文中,我们会把部分实地实验研究的文献融入到实验室实验研究中。不过,综合现有的腐败实验研究文献,我们认为在腐败实验室研究方法上除了对于实验室实验研究的外部效度需要进一步澄清外,我们还需要明确如何在实验情境中刻画腐败问题。对于这两个问题的解答直接关系到实验方法在腐败问题研究中的有效性以及研究结论的价值。
经济研究者们从两个方面对腐败的实验室实验研究外部效度提出怀疑:一方面,在针对腐败的实验室实验研究中,学生被试是否具有代表性?另一方面,采用抽象语言的中性框架(neutrally framed)腐败实验是否可以得到被试的真实行为反应?
无论是经济学专业还是非经济学专业的学者,针对以学生为被试的实验研究所持的疑问或批评是: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群体与一般社会群体相差甚远,建立在学生被试基础上的研究结论无法代表一般群体的实验结果,即缺乏样本代表性。应该说这个方法论的问题和争议始终伴随着实验经济学的发展过程,早在1986年Seras就把这个问题用实验数据是一种“狭隘的数据库”(Narrow Data Base)来加以概括。在解决学生样本实验结论的外部效度问题时,实验经济学家采用的最有效途径是:获取社会职业人群的样本复制相同的实验,从而查看实验结论是否会出现偏离;结合实地实验与调查研究,比较它们所得到的结论与实验室实验研究结论的差异性。比如,德州达拉斯大学的R.Croson总结了近30篇用学生和非学生样本作为被试的同一个实验结论的差异问题,发现大多数实验结论是无差异的,即从自然市场中招募的被试(很多是社会职业人群)其行为与学生并没有典型差别。在有关腐败的实验研究中,Barr & Serra(2010)以来自40多个不同国家的牛津大学本科生为被试,研究他们在行贿博弈中的腐败行为。当他们把实验中来自不同国家的被试腐败行为数据与透明国际的感知腐败指数进行比较,发现它们之间存在高度的相关性。同时,他们的研究结论也与Fisman & Miguel(2007)有关纽约多个国家外交官违规停车与他们各自国家的腐败水平之间关系的实地实验研究结论一致。在一定程度上,这说明了腐败的实验室实验研究具有外部效度。另外,为了研究实验研究结论的外部效度,Armantier & Boly(2012)把同一个行贿博弈实验分别在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实验室进行实验,并且进行发展中国家的实地实验。他们的研究发现,三种不同环境下腐败行为很相似。他们的研究也佐证了实验室实验研究的外部有效性。
在实验室实验研究中,被试行为对于实验语言的使用或情境比较敏感,这造成了腐败实验研究的第二个方法论问题。比如,在囚徒困境博弈实验中, Ross & Ward(1996)和Liberman et al.(2004)仅仅把囚徒困境博弈称为“社区博弈”或“华尔街博弈”。可是,即使在实验指导语与博弈规则都一致的前提下,这个小小的改变却足以显著降低“华尔街博弈”中被试的合作水平。在信任博弈实验中,Burnham et al.(2000)在第一个实验设置中把受信者(trustee)称为“伙伴”,而在第二个实验设置中把受信者称为“对手”,这显著地降低了第二个实验设置中信任与可信任水平。若被试的行为对于实验语言或背景的反应如此的敏感,我们又如何能够把在采用中性实验语言基础上获得的实验结论推广到真实的社会情境中呢?也就是说,我们怎么能够相信这些实验结论的外部效度呢?尤其是在诸如犯罪以及挪用公款等腐败实验研究中得出的结论并不可靠。因为腐败总是与犯罪以及损害社会的行为联系在一起,人们对于腐败一般持否定的态度,因此,当被试处于不道德的实验情境中,我们可以预期到被试会降低腐败活动的频率,从而降低实验结论的外部有效性。采用抽象语言的中性框架(neutrally framed)腐败实验是否可以得到被试的真实行为反应呢?Abbink & Hennig-Schmidt(2006)对此进行了检验。该文所采用的博弈实验情境与AIR(Abbink,Irlenbusch & Renner,2002)一致,不过,Abbink & Hennig-Schmidt(2006)在实验指导语上做了修改。第一个实验设置中使用中性语言,而第二个实验设置中使用了可以唤起被试腐败行为的语言,比如官员、企业与行贿受贿等词语。直觉上,我们可以假设:相对于第一个实验设置,设置二中的实验情境容易激发被试负的情感,所以被试将降低腐败行为。可是,实验发现被试在两个实验设置中的腐败行为并没有显著差异。这意味着,在该腐败实验中,被试腐败行为并不受实验语言或实验背景的影响,不存在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这为腐败的实验室实验研究结论的外部有效性提供了一定的支持。尽管这样,毕竟这仅仅是一次实验所得到的结论而已,我们认为应该对该结论持谨慎态度。
(三)实验情境中的腐败问题
如何在实验情境中刻画腐败问题?腐败具有多种类型。根据不同的公权和私利,学界把腐败主要分为两大类(Tanzi,1997):第一类是政治腐败,指的是预算制定程序中的不当,如搞劳民伤财的大型形象工程,或者拨款盖过于豪华的办公大楼;第二类是经济腐败,这又可以分两种:一种是官员不需要和民间进行交易而直接损公肥私,也就是贪污;另一种是官员和民间进行权钱交易,这是腐败研究的重点。对于反腐的实验研究来说,针对不同的腐败类型应该开发出一个比较概括或通用的博弈实验情境,可是,由于现有的腐败实验研究还处于起步和快速发展阶段,目前还没有出现统一的实验研究范式。目前,在众多腐败活动中,实验研究关注最多的是贿赂腐败行为。针对贿赂腐败活动的三个典型特征(行贿者与受贿者之间的互惠性、腐败服务的负外部性、腐败活动的非法性),AIR(2002)开发出来的贿赂博弈是大量研究者采用的腐败实验情境。实质上,它是一个具有负外部性的互惠交易博弈。不过,不同的研究者在对待博弈中的外部性有不同的处理方式,比如:Abbink(2002)在信任博弈中引入被动的第三方,由他们来承受腐败行为带来的负外部性,而 Barr & Serra(2009)、Lambsdorff & Frank(2010)在互惠的腐败博弈中引入具有一定财富的慈善机构,当发生腐败行为时就从慈善机构的财富中减少一定的份额,即由慈善机构来承受腐败行为的负外部性。虽然有两种不同的处理外部性的方式,但是从腐败伤害社会的意义上是一致的。其他一些研究者针对不同的腐败问题开发出了不同的实验情境,比如,针对系统性腐败问题,Berninghaus et al.(2012)采用了协调博弈,针对贪污或挪用公款问题,Barr et al.(2009)开发了独特的赌牌博弈。
三、反腐政策的实验研究
(一)反腐与惩罚
在贿赂博弈实验中,AIR(2002)研究了外生给定惩罚概率条件下的腐败行为。由行贿者、官员以及第三方所组成的贿赂博弈具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潜在行贿者决定是否行贿,若计划行贿则行贿多少。假如行贿者向官员进行了一笔转移支付,同时会因为开展行贿活动本身而发生一笔沉没成本,比如,由于联络感情以及收集官员信息而发生的成本等等;第二阶段,官员决定是否接收这笔转移支付,若他拒绝了行贿,那么除了行贿者的沉没成本外,他们的收益没有发生变化,也不会给第三方造成负外部性。假如官员接收了行贿,那么他需要做出一个二元选择:X或者Y。如果他选择了X,那么就相当于他拿别人的钱,却没有提供腐败服务,如果他选择了互惠性的行为Y,意味着官员提供了腐败服务,这将给行贿者带来很大的好处,同时,该腐败行为给第三方带来负外部性。为了检验惩罚对于受贿与腐败行为的影响,AIR(2002)安排了一个“突然死亡”实验条件:只要官员选择接受贿赂,那么该受贿行为将以0.003的概率被发现,一旦被发现,行贿者与受贿官员都将失去所有的收益并且被开除出博弈。为了研究长期腐败关系,在实验中,根据固定分组的方式,被试将进行30期行贿博弈。实验数据显示,行贿者的行贿水平与官员提供腐败服务的频率之间具有高度的正相关关系,这意味着,行贿者与官员之间存在明显的互惠关系;在没有惩罚的实验条件下,这种互惠关系(腐败关系)并没有因为给第三方带来伤害而有所收敛,可见,依靠官员对第三方的同情而约束自己的腐败行为是不可行的。不过,在“突然死亡”实验条件中,惩罚对于贿赂行为发挥着明显的威慑作用,它使得行贿与腐败行为Y降低了三分之一。可见,即使在低发现概率的情境中,严厉的惩罚措施依然可以发挥有效的反腐作用。尽管对腐败行为的惩罚降低了腐败行为,不过,在针对官员与行贿者被抓到的概率判断问卷数据显示,他们普遍低估自己腐败行为被察觉的概率,所以惩罚的威慑作用也就大打折扣了。
给定惩罚的力度,惩罚对于反腐的作用依赖于腐败行为被察觉的概率。在现实中,发现腐败行为的概率是内生的而不是外生的。实验研究表明,监督与举报机制可以影响腐败行为被发现的概率。在这里我们设想一个腐败横行的社会,给定政府资源水平,腐败行为越普遍,审计与发现腐败的概率越低(Lui,1986),另外,由于惩罚可以通过行贿来规避,所以被发现的腐败活动受到惩罚的概率也比较低(Cadot,1987)。因此,在一个系统性腐败的社会里,不同官员的腐败活动间具有策略互补性,腐败行为被发现以及被惩罚的概率与腐败收益内生于社会上腐败的官员数量。在实验中,Berninghaus et al.(2012)采用协调博弈来研究这类腐败行为:6位被试为一组,每个组员从A与B两个选项中选其一,选择A可以得到无风险的600个实验点数,选择B,将以概率w(m)获得1000点,以1-w(m)的概率获得0点。其中,m表示小组中选择B的人数,而概率w(m)是m的单调增函数,比如:m=1,2,…,6,概率w(m)分别为0.5,0.6,…,1。可见,选择A意味着被试没有从事腐败行为,得到固定薪水,而选择B表示被试从事的是有风险的腐败行为。腐败被发现与被惩罚的概率1-w(m)随着选择腐败行为的人数增加而下降。他们的实验研究发现,被试的风险态度与他们的腐败行为之间并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而被试有关其他被试从事腐败行为的信念与自己选择腐败行为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意味着,只要被试对其他被试从事腐败行为持有高信念时,那么哪怕是一个胆小的官员也会从事腐败行为,因为他们会认为腐败被发现与惩罚的概率很低。当大家都持这种信念时,惩罚机制会成为一种摆设,该社会或小组必然会收敛到高腐败均衡的陷阱。有关协调博弈的实验研究表明,影响进入高腐败均衡陷阱的信念是人们在制度、规范以及文化约束下长期学习的结果。因此,若想真正发挥惩罚在反腐上的作用,不能仅限于惩罚机制本身,还需要政治与经济制度以及文化规范上的配合。
(二)反腐与监督
有效监督是发现与惩治腐败的前提。可是,监督对惩治腐败的有效性取决于监督本身的有效性。而监督本身的有效性与由谁来监督、监督方式的选择紧密联系在一起。两种最基本的监督方式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监督。可是,这两种监督方式都存在问题:由上级官员进行自上而下的监督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由谁来监督监督者,若该问题处理不好,监督起不了反腐的作用,而仅仅会把腐败活动由低层官员转移到更高层官员;受到官员活动或公共项目影响的民众似乎更有动力进行自下而上的监督,可是,对政府官员活动或公共项目实施的监督是一个公共产品,而对于该“公共品”的提供容易陷入“搭便车”的陷阱,从而出现监督不力。到底哪种监督方式更加有利于反腐呢?在一项基于608个要修建公路的印度尼西亚村庄的实地实验研究中,Olken(2007)检验了两种监督方式在反腐中的作用。在实验设计中,他随机抽取93个村庄作为审计实验组,这些村庄将接受中央审计机构的审计监督(自上而下的监督),并通过两种设计以实现草根(Grassroot)(自下而上)监督:一是随机抽取94个村庄,为减少在监督活动中出现“被代表”的现象,他们在每个村庄中邀请100位村民参加村庄的预算会议;二是随机抽取96个村庄,为避免村民在监督中得到报复,除了每个村庄中邀请100位村民参加村庄的预算会议外,他们还将填写匿名意见表,以此方式进行监督。为了更加准确地测量腐败,Olken(2007)采用了直接测量腐败方法。在项目完成后,在每条道路上随机选取一个地方挖开一个洞,然后取出筑路材料。由工程专家组来估计材料的质量、通过向供应商的调查来估计材料的价格、通过向村民的访谈来获取公路项目的工资成本。在这些数据的基础上,他们计算出每条道路的实际建造成本,把这个实际成本与预算成本相比较,可以得到费用损失,这就得到了事实上的腐败水平。Olken(2007)研究发现,平均费用损失(腐败水平)在24%左右。在自上而下的审计实验组中,审计显著地降低了8个百分点的腐败水平。不过,即使存在100%的审计监督概率,审计实验组中的腐败水平依然接近20%。深入研究发现,这主要是由于两方面的原因:(1)审计对于腐败活动的影响主要是针对道路修建中的一些程序性活动,它并没有触及到那些可以构成犯罪的腐败活动;(2)审计在减少费用损失的同时增加了裙带关系(比如项目负责人更多的雇用了自己的亲戚与村干部),这增加了道路修建中的劳动费用。在两个草根监督实验组中,Olken(2007)研究发现,村民参与监督在降低腐败水平方面影响更小,并且不显著;村民参与监督对于降低道路修建中劳动费用方面的腐败有较大作用,可是,对于降低建筑道路材料的费用损失方面几乎没有作用。这主要是因为劳动费用与村民修路时的工资直接相关,村民更有动力监督这方面的费用,而在建筑道路材料费用的监督方面存在明显的“搭便车”现象。这些研究结论意味着:相对于草根监督,自上而下的审计监督在反腐方面更加有效;在审计监督中,要提高针对更加隐蔽的腐败活动的监督,并且防止反腐中出现新的腐败形式;在草根监督中,必须防止“搭便车”。
不过,在一个司法制度缺乏效率且存在系统性腐败的国家,由于上级官员缺乏足够的反腐激励,这使得采用自上而下的监督与惩罚的反腐效果会受到限制。假如在自上而下的监督与惩罚机制基础上,我们再引入“公民”或企业的举报、新闻网络媒体的报道,那么是否可以改善反腐效果呢?另外,监督者的产生机制是否会影响监督对于反腐的作用呢?
在Barr & Serra(2009)行贿博弈基础上,Serra(2011)研究了“公民”或企业的举报、新闻网络媒体的报道对于发展中国家反腐的积极影响。在博弈中,“官员”与“公民”进行有关腐败服务供给的交易,他们将从腐败交易中获益,不过,社会中其他成员会因此而受损。在实验中,她安排了三个实验设置:(1)没有监督的实验设置,在该设置中被试的腐败行为不会被发现与惩罚;(2)设置二中的被试腐败行为有4%的概率被上级发现并且会被惩罚;(3)设置三中的受贿与腐败行为只有在被“公民”举报以后才会引起上级官员的关注,从而“官员”的腐败行为有4%的概率被上级发现并且会被惩罚。实验设置三所刻画的情境是,在一个处于腐败陷阱的国家,若没有人举报,上级不会主动去反腐,只有在“公民”向外报道了“官员”腐败嫌疑才会引起上级的监督与惩罚腐败。在理论上,实验设置三中的反腐效果要比实验设置二差,因为前者发现腐败的概率比后者低。不过,实验数据显示,与没有监督的实验条件相比,当把上级的监督与“公民”举报结合起来时,这显著地降低了腐败发生的概率,而仅依靠上级的监督并不能够显著改善腐败活动的频率。对此的可能解释有两个:一个解释是报道使得官员失去了社会认可,这给腐败官员带来了非经济上的成本;另外,引入报道为“公民”背叛腐败互惠合约提供了机会,而具有“背叛厌恶”心理(Bobnet,Herrmann & Zeckhauser,2008)的官员为了防止背叛而选择不腐败。
现有实验研究表明,除把自上而下的监督结合民间报道外,监督者的产生机制也影响着监督在反腐中的作用。在实验中,Barr,Lindelow & Serneels(2009)以144位纳米比亚护理本科生为被试,研究了不同的监督者产生机制对于公共服务提供者挪用公款行为的影响。他们开发了一个挪用公款的实验博弈情境。每期博弈由8位被试进行多阶段的博弈,首先,通过随机机制确定其中一位被试为公共服务提供者,然后,通过随机或选举的方式确定另外一位被试为监督者,剩下的6位被试为具有选举监督者的公共服务接收者。确定被试角色后,公共服务提供者将得到两种赌牌(tiles):一种是有价值的赌牌,另一种是无用的赌牌。首先,通过掷6面骰子的方式来确定公共服务提供者所获取的有价值的赌牌张数,它代表将要分配给公共服务接收者的资源,比如卫生健康资源、救灾款等。在这些赌牌(小于等于6张)的基础上,实验中又加入一些无用的赌牌,使得总赌牌数为10张或18张,这些赌牌与有价值的赌牌在表面上都一样,唯有公共服务提供者才能区分它们。公共服务提供者可以从10张或18张赌牌中拿出6张,把它放入袋子中,分别分配给6位公共服务接收者,余下的赌牌留给自己。由于只有公共服务提供者知道哪些赌牌是有价值的,哪些没有价值,理论上,他可以把所有无价值的赌牌分给公共服务接收者,这样公共服务接收者的收益为0,而公共服务提供者挪用了所有的公款。在公共服务提供者分配赌牌后,监督者可以通过翻看公共服务提供者留给自己的赌牌来进行监督,不过,这种监督是有成本的。若监督者从翻看的赌牌中存在有价值的赌牌,就意味着公共服务提供者挪用公款行为被发现,那么公共服务提供者的收益就为0。
实验研究发现,由公共服务接收者选举来决定监督者时,他们一般会选择在上期博弈中努力水平高的监督者为现任监督者,这使得选举产生的监督者比随机产生的监督者更加努力地监督。由于监督者越努力监督,公共服务提供者挪用公款被发现的概率就越高,因此,相对于有上级随机指派监督者的实验条件,在选举产生监督者的实验条件下,公共服务提供者显著降低了挪用公款的水平。这些研究意味着,在反腐方面,由公共服务接收者自己选举产生的监督者比由上级指派更加有效。不过,他们的研究忽视了腐败者与监督者的合谋行为,因此,对于未来有关监督与反腐关系的政策研究中,我们认为要考虑防合谋因素的影响。
(三)反腐与工资
许多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官员的腐败主要是因为收入太低,官员受到通过受贿来改善收入的激励。在实证研究中,Van Rijkeghem & Weber(2001)发现,官员的高工资带来了腐败水平的下降。不过,由于他们的研究采用的是跨国调查数据,因此,无法排除其他因素对结论的影响,比如,文化与制度。另外,他们忽视了工资对行为的影响往往取决于相对工资而不是绝对工资水平(Akerlof & Yellen,1990)。鉴于调查数据的质量与无法剥离相关影响因素,一些学者采用实验研究的方法来研究工资与腐败之间的关系。
在理论上,高工资至少可以通过两个途径来影响官员的腐败行为决策:(1)在具有监督与惩罚机制的情境中,高工资意味着官员腐败的高期望成本(Becker & Stigler,1974;Olken,2007);(2)根据礼物交换博弈中的公平“工资—努力”假设(Akerlof & Yellen,1990)、不公平厌恶理论(Fehr & Schmidt,1999),增加官员的工资意味着增加官员腐败的非经济或道德成本。鉴于这两方面的影响,我们可以预测高工资具有降低腐败行为的作用。不过,在实验研究中,高工资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与谁比较呢?Abbink(2005)在AIR(2002)标准贿赂博弈基础上,把官员的工资与“其他社会人员”的工资进行比较,在此基础上安排官员高工资与低工资两个不同实验设置。理论上,假如公平偏好决定着官员的行为选择,那么低工资的官员应该会从事更多的腐败行为。不过,实验数据显示,在腐败行为方面,官员工资的高低并没有显著差异。可是,Barr,Lindelow & Serneels(2009)在有关挪用公款的腐败实验研究中发现,提高公共服务提供者的工资可以降低挪用公款的水平。Armantier & Boly(2012)的研究也验证了高工资与官员受贿水平以及频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可见,现有有关工资在反腐作用方面的研究结论并不完全一致。Van Veldhuizen(2012)认为官员工资比较对象的选择不当是造成 Abbink(2005)研究结论与预期不一致的主要原因。在现实中,许多官员在与富有的企业家接触中感觉到不公平,从而引发腐败动机。因此,相对于其他参照对象的收入,对于官员来说,行贿者的工资更具“凸显”(salient)性。为了刻画这个腐败现实,Van Veldhuizen(2012)在AIR(2002)博弈基础上,以行贿者的工资水平为参照对象来定义官员工资的高低。为此,他安排了两个实验设置:官员工资低于行贿者的工资;官员工资高于行贿者的工资。实验研究发现,在受贿与提供腐败服务方面,相对于官员低工资的实验条件,在官员高工资实验条件下,官员接受贿赂与提供腐败服务的频率显著地下降了。在对该研究结论进行稳健性检验时,他在AIR(2002)博弈基础上分析了有无惩罚机制对官员工资与腐败行为之间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去除惩罚机制后,虽然官员的高工资对于减少腐败发生频率的作用略有降低,不过,基本结论依然成立。
四、反腐制度的实验研究
(一)反腐与举报、宽大制度
在反托拉斯与反垄断实践与理论研究中,举报与宽大制度已经得到了广泛的使用与研究,最近,在理论层面,Lambsdorff & Nell(2007)、Buccirossi & Spagnolo(2006)已经研究了这些政策对于腐败行为的影响。在理论上,作为腐败活动存在着两种负外部性:一种是腐败行为本身造成其他成员收益或效用减少的负外部性,这也就是AIR(2002)标准腐败博弈中所提到的直接负外部性;另外一种是行贿与受贿以及腐败服务的供给“挤出”了部分合法交易活动,这间接地造成了社会福利的损失,Schickora(2011b)把它称为间接负外部性。举报作为一种针对腐败关系方进行的有成本惩罚机制,它影响着腐败活动所带来的两种负外部性:一方面,相对于缺乏举报机制,举报机制的引入降低了潜在腐败官员的期望收益,提高了那些潜在守法的“公民”或企业的期望收益,从而增加了合法交易活动的比例,降低腐败行为所带来的间接负外部性;另一方面,把举报机制引入腐败交易活动中,这相当于在互惠合作关系中引入了针对背叛行为的惩罚机制。Fehr & Gachter(1998,2000)、Sutter et al.(2010)实验研究表明,在社会困境中,惩罚机制的引入会促进博弈方的互惠合作水平。在腐败交易情境中,这意味着举报机制促进了腐败互惠行为与腐败关系的稳定性,从而提高腐败交易活动的直接负外部性。可见,举报对于腐败活动存在着两个不同方向的影响,那么总的影响会是什么呢?假如对于举报方进行宽大处理,那么对于腐败活动又会有什么影响呢?在理论上,Lambsdorff & Nell(2007)研究了这些问题,Schickora(2011b)对此进行了实验研究。
在实验研究中,为了融入腐败活动的间接负外部性,Schickora(2011b)对AIR(2002)标准腐败博弈进行了两个方面的修改:(1)AIR(2002)标准腐败博弈中“公民”或企业只有两个选择(行贿或退出),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合法”策略;(2)允许“官员”主动索贿。除以修改后的腐败博弈为基准实验设置外,Schickora(2011b)安排了两个举报实验设置:对称举报与不对称举报实验设置。在对称举报中,“公民”与“官员”都具有举报的机会,他们中的任何一方实施了举报,他们都要受到相同的经济惩罚。在不对称举报中,只有“官员”具有举报的权力,并且对“官员”的举报采取宽大政策,这种不对称处罚使得“公民”与“官员”对于举报的激励强度不同。在10期重复腐败博弈实验研究中,Schickora(2011b)发现,与基准实验设置相比,举报机制的引入显著提高了“公民”或企业选择“合法”交易活动的频率,这意味着举报机制降低了腐败博弈中的间接负外部性;与基准实验设置相比,对称举报实验设置中的腐败活动水平提高了74%,而不对称举报实验设置中的腐败水平降低了15%。这说明,只有具有宽大政策的举报机制才能够真正地降低腐败活动水平,否则,反而会促进行贿者与受贿者之间的互惠合作。另外,在“公民”与“官员”以及其他社会成员的收益分布方面,实验数据显示,具有宽大政策的举报机制降低了基尼系数,促进了社会公平。
(二)反腐与“四眼原则”
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还采用“四眼原则”(简称4EP)来预防腐败,比如,对重大工程项目的招投标、与财政相关的支出、警察执行公务都必须坚持两人或两人以上把关和同行,为防止暗箱操作,不能个人单独行动。“四眼原则”作为一个重要反腐制度已经得到了很多的研究(Hussein,2005;Rieger,2005;Wiehen,2005),不过,有关它对于减少腐败行为的有效性实证研究一直比较缺乏。直觉上,两个官员相互监督可以更好地防止官员与行贿者的腐败行为,即使官员具有腐败的意图,也往往会因为行贿者腐败成本的增加以及官员需要分摊受贿而减少腐败行为动机。我们可以把4EP通过两个官员分摊贿赂而降低腐败行为的效应称为“贿赂分裂效应”。不过,4EP要求两个官员在面对企业或其他主体的行贿时需要联合做出决策,这意味4EP是通过一个群体决策过程来实现对腐败行为的影响,而群体决策与单个官员的个体决策存在很大的差异。Charness & Sutter(2012)研究发现,相对于个体决策,群体决策更加自利理性(Kocher & Sutter,2007)。这意味着在腐败博弈情境中,为了获取长期的利益,作为群体的两个官员会通过向行贿者提供腐败服务以放弃短期利益最大化,以此来换取长期利益最大化,这必然会导致行贿与腐败行为的增加。我们可以把4EP通过群体决策而提高的行贿与腐败行为效应称为“群体决策效应”。因此,在反腐的总效应方面,4EP取决于“贿赂分裂效应”与“群体决策效应”之间的相对值,而这个总效应必须通过实证来检验。
在实验研究中,Schickora(2011)对AIR(2002)贿赂博弈进行了修改,把原来由单个官员做出是否接收贿赂以及是否提供腐败服务修改为由两个官员通过沟通联合做出这些决策。为了得到4EP在反腐方面的总效应,他安排了四个实验设置以分解“贿赂分裂效应”与“群体决策效应”。为了检验“贿赂分裂效应”,在群体决策实验条件下,他安排了两个实验设置:TDT1与TDT2,两者的唯一区别在于,前者中两个官员独立获取相同的贿赂,而后者的两个官员需要平分一份贿赂。实验数据显著,TDT1实验设置中的腐败率比TDT2高了5%,这意味着,4EP在反腐方面,由于“贿赂分裂效应”的存在而降低了腐败发生的频率。为了检验“群体决策效应”,他安排个体决策实验设置(IDT1),它与TDT1的唯一区别在于,前者只有单个官员做决策。实验数据显示,TDT1实验设置中的腐败率比IDT1高了22%。这意味着,4EP的“群体决策效应”提高了腐败率。综合“贿赂分裂效应”与“群体决策效应”,4EP提高了17%的腐败率。鉴于这个实验研究结论,Schickora(2011)认为4EP对于反腐不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Schickora(2011)的研究提醒我们在使用4EP进行反腐时要注意两种不同影响效应。不过,在现实中,发生腐败的情境比较复杂,我们并不能够单靠一个实验就得出“四眼原则”对反腐方面的无效性。
(三)反腐与工作轮换
腐败交易其实也是官员与行贿者之间的谈判、签约与履约的过程。正如任何交易都受到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一样,腐败交易也不例外。假如通过工作轮换制度,官员与潜在行贿者之间缺乏长期交往的机会,那么这会造成腐败交易主体有关其他腐败主体在腐败倾向性(corruptibility)方面的信息不对称,而由此带来的不确定性会影响腐败活动的开展。最近,Ryvkin & Serra(2012)在模型中证明,当潜在行贿者与受贿者在有关对方腐败倾向性方面存在不确定时,腐败均衡水平会降低。这在理论上支持了工作轮换制度对于反腐的作用。
在实验研究中,工作轮换制度相当于基于被试随机分组的一次性博弈实验,而固定工作岗位相当于官员与潜在行贿者固定分组且进行重复博弈。因此,对于工作轮换的研究就变成了比较随机分组与固定分组在腐败行为上的差异了。在有关信任博弈的实验研究发现,即使在一次性且匿名的实验条件下,博弈方之间依然存在互惠合作行为(Berg et al.,1995;Dufwenberg & Gneezy,2000;Fehr & Irlenbusch,2000;Fershtman & Gneezy,2001)。这说明重复博弈并不是互惠合作的必要条件。不过,Gachter & Falk(2002)在重复信任博弈实验研究中发现,与一次性博弈相比,重复博弈显著地增加了合作水平。在礼物交换博弈实验中,Fehr et al.(1993)发现了重复博弈中被试间的互惠水平显著高于一次性博弈中的被试行为。在公共品博弈实验中,与随机组中被试的合作行为相比较,Andreoni(1988)发现固定组中被试显著地提高了自己的合作水平。这些有关一次性博弈与重复博弈中的实验结论在贿赂博弈实验情境中是否也可以成立呢?为了检验官员岗位轮换对于腐败行为的影响,Abbink(2004)以AIR(2002)为基础,以进行30期重复博弈的“突然死亡”实验设置为控制实验组(固定组),在岗位轮换实验设置中(随机组),他把每期“突然死亡”实验中潜在行贿者与官员进行随机组合,使得他们相互之间保持匿名性与缺乏长期关系。他们在实验中研究发现,在行贿者的转移支付方面,与固定组相比较,随机组中的被试减少了45%的行贿额;在行贿行为分布方面,随机组中接近2/3的被试没有进行行贿活动,这显著地低于固定组。在官员选择具有负外部性的Y行为方面,随机组显著地低于固定组。不过,官员对贿赂的拒绝率方面,固定组与随机组之间没有显著差异。可见,官员的岗位轮换可以有效地降低腐败行为,不过,我们认为对于该结论应该持比较谨慎的态度。首先,实验中并没有考虑岗位轮换的成本;其次,没有考虑官员或行贿者的告发行为对于腐败行为的影响,而岗位轮换与否显然影响告发腐败行为的概率;最后,假如在腐败交易活动中存在着中间人(Drugov,Hamman & Serra,2011),而中间人可以降低腐败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与不确定性,那么工作岗位轮换是否还可以有效反腐呢?因此,我们认为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应该在实验中加入这些新的因素,也只有这样才可以使有关岗位轮换与腐败行为关系的结论更加稳健。
五、腐败的其他影响因素
(一)中间人与腐败
在市场的合法活动中,中间人的经济活动贡献了28%的GDP(Spulber,1996),可是,中间人在非法市场活动也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尤其是在腐败活动中,中间人或中介机构利用其极其广泛且稳定的人际关系网络与受到行贿、受贿双方的信任,充当着“权力托儿”,增加了腐败的间接性、隐蔽性,也就无形中增加了反腐成本。由于行贿者与受贿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行贿者一般难以获取有关谁是潜在的受贿者以及如何有效行贿的信息,潜在受贿者也难以获取行贿者的相关信息,这将影响到腐败活动的风险以及腐败成功的概率。不过,中间人利用其信息优势可以降低腐败活动的风险与提高腐败活动成功的概率。另外,由于腐败活动的非法性会降低腐败合约的可实施性,而中间人的出现可以有效提高腐败合约的可实施性。最近,有关非策略性情境中分权的心理影响方面的研究为中间人与腐败关系研究提供了启发。在独裁者博弈实验中,Hamman,Loewenstin & Weber(2011)研究发现,独裁者通过分权,由代理人从事分配时显著地降低了分配给接收者的份额,并且独裁者显著偏好于选择那些进行不公平分配的代理人进行分权,因为独裁者可以通过分权而分散不公平分配的道德责任,达到通过分权而自利的目的。Bartling & Fischbacher(2012)在具有分权的一次性独裁者博弈实验情境中研究发现,独裁者利用分权的目的是:实现责任转移,达到逃避对不公平行为的惩罚。在腐败博弈中,由于出现了作为代理人的中间人,这使得行贿者与受贿者感觉到自己是间接而不是直接从事腐败行为,因此,这会在分权者与腐败活动之间形成一个心理距离,从而降低他们由腐败行为而带来的道德成本,进而提高腐败活动的频率。为了检验中间人对于腐败交易活动的影响,DHS(Drugov,Hamman & Serra,2011)在Barr & Serra(2009)实验设计的基础上,安排了三个实验设置以研究中间人是否通过消除不确定性、降低行贿者与受贿者的道德成本来提高腐败交易活动。在模拟腐败交易的实验情境中,“公民”与“官员”进行腐败交易,他们因此而得益,不过,腐败活动给“社会中的其他成员”带来了负外部性。在基准实验设置中,从事行贿活动前,“公民”并不知道“官员”类型,比如,是否属于腐败分子,需要多少贿赂才愿意提供腐败服务(简称MAB)。在中间人实验设置中,他们在“公民”与“官员”之间引入了中间人,而中间人具有官员的MAB信息。“公民”与“官员”之间的腐败交易活动可以通过中间人来实施。为了分解中间人在腐败活动中消除不确定性与降低“公民”与“官员”道德成本方面的影响,DHS(2011)安排了一个完全信息实验设置。在该实验设置中,“公民”具有“官员”的MAB信息。DHS(2011)的实验数据显示,中间人的出现显著提高了腐败比例。正如上文分析,除了消除不腐败交易中的不确定性,中间人还通过降低“公民”与“官员”的道德成本来促进腐败。鉴于DHS(2011)的研究结论,我们认为,对于活跃在中国市场上的各类中介机构、中间人活动的合法性、重大公共品供给过程中对中间人的使用确实应该引起反腐部门的关注。
(二)信息透明与腐败
在国际反腐运动中,信息公开与透明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以至于世界上从事反腐的最大非盈利性组织被称为“透明国际”。其实,有关增加政府官员活动信息的透明性以降低腐败的研究并不新颖。在非法经济模型中,Becker & Stigler(1974)认为,当潜在被害者拥有犯罪频发场景的信息时,他们可以有效地降低犯罪活动的发生。一些实证研究发现,获取政府官员活动或业绩的信息与官员的称职性以及政府的服务质量之间具有一定的联系。比如:Djankov et al.(2010)研究了揭示国会成员的相关信息与政府服务质量以及腐败之间的关系。他们的研究发现,信息越公开透明往往意味着更低的感知腐败(perceived corruption)水平,官员的财产、负债与收入来源等信息越透明,则政府的服务质量就越好。不过,他们的研究建立在截面数据基础上,这并不能够排除反向的因果关系,即高质量的政府或低腐败的官员带来信息的更加透明与公开。事实上,由于信息的透明或公开性具有内生性(比如获取有关官员活动与财产的信息往往取决于政治制度、官员间竞争与审计或司法机构获取信息的努力程度等),企图通过调查数据来识别信息透明与腐败之间的因果关系具有较大的难度(Ferraz & Finan,2008)。不过,实验研究可以为我们识别信息透明与腐败之间的因果关系提供有效的方法支持。
Banerjee et al.(2011)开展了基于2008年印度德里州议会选举的实地实验研究,研究了信息披露对于选民的选举行为以及责任感(accountability)的影响。根据印度信息披露法案,在进行州议会选举时必须在主流报纸的公布栏中披露有关在位议员的三方面信息:立法活动、参会情况、官员所管辖的资金在八类公共品中的使用情况。另外,法案还规定必须提供在位议员与两位竞选者的财产、教育背景以及犯罪记录等方面的信息。Banerjee et al.(2011)随机抽取了200个贫民作为实验组,他们免费获取主流报纸公布栏中的信息,而作为控制组的575个贫民并没有获得相关的报纸与信息。相对于控制组,实验组中的贫民选民的选举行为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首先,选民的平均出席投票率增加了3.5%;其次,实验组投票点的现金选票买卖减少了19%;最后,相对于控制组,实验组中的业绩最佳的在位者得票率提高了7%,而业绩较差的在位者得票率都显著地下降了。这三个研究结论意味着信息的披露增加了贫民选民的选举责任感,改变了选民的选举行为,进而有利于选举出高质量的议员,这为降低腐败创造了条件。在一项有关巴西当地政府腐败信息的公开披露对于在位官员选举结果负面影响的实地实验研究中,Ferraz & Finan(2008)得到了与Banerjee et al.(2011)类似的结论。自2003年4月始,巴西联邦政府启动了一项新的反腐计划。在该计划中,巴西联邦政府从所有的市政府中随机抽取部分市政府,并且对这些政府的联邦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审计,为了体现信息的透明性,他们将向市政当局、起诉人以及公共媒体公开这些审计报告。Ferraz & Finan(2008)分析比较了2004年前后那些被审计的市政府中具有资格再选市长的再选举结果;由官员违法规定的次数来刻画腐败的程度,检验了两种不同的信息透明类型(一种是仅披露审计报告,另外由当地媒体介入信息的披露)对于反腐的影响。他们的实验研究发现:当审计披露官员违法规定的次数达到两次时,这些官员在再选举中获胜的概率减少7个百分点(或17%),当披露官员违法规定的次数达到三次时,这些官员再次当选的概率甚至降低了14个百分点。可见,当选民拥有官员腐败信息时,他们会通过投票来对那些腐败官员进行惩罚。另外,他们还发现,虽然采用审计报告形式来披露腐败可以降低官员再次当选的概率,不过,采用当地媒体介入(广播与报纸)官员腐败信息披露对于降低在位官员再次当选的概率更加明显。这说明腐败信息披露方式对于反腐也具有重要的影响。
信息的透明与公开除了可以通过影响选民的选举责任感与官员再次当选的概率来影响腐败活动外,它还可以通过监督官员而降低官员的腐败活动。众所周知,印度在2005年颁发与实施了信息权利法(RTIA),该法案规定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公众可以申请获取所有以电子形式存在的政府记录。直觉上,这种信息公开赋予了公众监督官员的权力,不过,这种信息透明规则在反腐方面的作用还需要实证的检验。在一项实地实验研究中,Peisakhin & Pinto(2010,2011)检验了RTIA对于印度公共分配系统(PDS)中分配配给卡(ration card)时的反腐作用。他们从新德里贫民窟中招收了86位被试,在实验中,把他们随机地分配到三个不同的实验设置中,检验信息公开对于配给卡申请者获取食物资源所需要时间的影响。第一个是RTIA实验组,该组中的被试在提出配给卡申请后可以向公共信息官员申请获取有关自己配给卡申请的处理状态与本地配给卡处理的平均时间等方面的信息;第二个是非盈利性组织(NGO)实验组,该组中的被试在提出配给卡申请的同时附上一封当地NGO出具的推荐信。在该信中,NGO证明被试具备申请配给卡的资格,同时,督促PDS官员加快处理该申请;第三个是行贿实验组,该组中的被试并不是直接向PDS官员递交配给卡申请书,而是向中间人行贿,并且由中间人代理申请。他们的研究发现,在RTIA与行贿实验组中一年之内94%的申请者得到了配给卡,而在NGO实验组中该比例仅有21%;在获取配给卡所需要时间的均值上,行贿实验组的申请者需要82天,RTIA实验组需要120天,而NGO则需要343天。这个研究发现说明,根据信息自由法案提出信息公开申请是合理的,因为它赋予了申请者监督官员的权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发挥着向官员行贿的相同功能,因此,信息公开可以部分的替代行贿,可以减少腐败活动发生的概率。
(三)文化与腐败
文化作为一种包含各种社会规范与信念的协调机制,它使得人际间社会交往中可能存在的多重均衡收敛到某个特定的均衡(Grief,1994)。腐败博弈作为一种人际间社会交互的情境,不同的文化显然影响博弈方的信念与行为选择,从而影响腐败均衡的出现,甚至可能使一些国家陷入腐败陷阱。在实证研究中,学者已经开始关注文化对于腐败行为与绩效的关系。比如,Fisman & Miguel(2007)研究了纽约多个国家外交官违规停车与他们各自国家的腐败水平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两者之间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在实验研究中,Barr & Serra(2010)以来自具有不同腐败水平的40多个国家的牛津学生为“公民”与“官员”,在相同的腐败博弈(具有腐败外部性的最后通牒博弈)情境中检验文化与腐败之间的关系。在直觉上,给定其他条件,成长在腐败盛行社会中的人比成长在很少腐败的社会中的人更易从事腐败交易活动。在实验后的问卷中,她们发现被试对于腐败的态度以及信念与各自国家的腐败指数之间具有高度相关性,所以这些学生可以作为这些国家腐败文化的代表性样本。实验数据显示,在总体上,“公民”行贿以及“官员”的受贿与他们各自国家的腐败指数之间正相关,不过,这种文化与腐败之间的关系仅仅存在于本科生被试的行为上,研究生被试的腐败行为与他们各自国家的腐败指数关系不显著。当在计量模型中加入被试在英国生活的年数后,她们发现,在英国生活的时间越长腐败的频率就越低。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研究生与本科生被试在腐败行为上的差异。她们的结论说明,一个国家的腐败文化确实影响着人们的腐败行为选择,人的腐败行为选择随着文化观念的改变而改变。
以印度、澳大利亚、印尼与新加坡等四国学生为被试,Cameron et al.(2009)在三方(企业、官员与第三方)三阶段互惠博弈实验情境中,研究了不同文化对于腐败以及惩罚腐败行为的影响。选择这四个国家具有代表性与可比性,因为澳大利亚与新加坡是世界上腐败水平最低的国家,而印度与印尼是世界上腐败水平最高的国家。不过,他们的实验研究结论与人们的直觉并不相同。澳大利亚的被试行贿水平高于印尼,而在对于腐败行为的惩罚方面也高于印尼,新加坡的被试惩罚腐败的水平低于印度与印尼。虽然这些关系都是显著的,但是结论之间具有矛盾,在理论上很难做出合理的解释(K.Abbink,2006)。
(四)性别与腐败
在实证研究中,Dollar et al.(2001)研究发现,男性从事腐败的频率高于女性,Swamy(2001)利用世界价值调查数据检验了女性官员与腐败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女性比男性更难接受非法的腐败行为,他们利用企业调查数据发现,男性企业家或管理者更倾向于行贿活动。不过,他们的研究难以排除女性官员行为内生于自由民主的水平,因此,模型的可识别性差。为解决这个问题,实验室实验研究可以控制其他一些影响因素后得到“干净”的腐败行为性别差异性检验。在行为性别差异的实验研究综述文章中,Croson & Gneezy(2008)发现,由于男性与女性在公平偏好、风险偏好以及竞争偏好等方面存在差异,使得他们在行为决策方面存在差异,不过,这些行为差异的显著性依赖于特定的实验情境。Rivas(2008)在AIR(2002)贿赂博弈情境中检验了男女性别的腐败行为差异。实验数据显示,无论是在行贿的频率还是行贿的数额上,男性管理者都显著地高于女性管理者;在受贿方面,男性官员接收贿赂的频率显著地高于女性官员。Alatas et al.(2009)在相关的研究中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不过,现有的实验研究对于为什么男女性在腐败行为上存在差异并没有给出一个清晰的解释。我们认为未来可以对此进行研究。
六、未来研究展望
本文在现有的腐败实验室实验研究文献基础上,从实验研究方法、反腐政策、反腐制度以及其他影响因素等方面进行了综述性分析。这些来自微观层面的研究结论可以成为其他有关腐败实证与理论研究的补充,为反腐政策与制度的制定提供指导。不过,由于腐败的实验室实验研究的历史还很短,还处于研究的起步阶段。我们认为在未来的研究中,该领域的研究至少可以从六个方面进行深入研究。
(1)由于腐败类型具有多样性,而现有反腐政策的实验研究文献主要是针对特定的腐败问题进行实验研究,甚至对于相同的腐败问题,不同的学者设计不同的腐败博弈,这造成腐败实验研究的结论缺乏一致性。我们认为未来研究需要建立比较统一的腐败博弈范式,可以针对更加广泛的腐败问题进行研究。另外,现有的反腐实验研究主要针对政府官员的腐败问题,而企业管理中的腐败、医药行业以及教育领域的腐败问题亟待进行实验研究。
(2)针对反腐政策实验研究的外部有效性问题,我们认为还需要在现有研究基础上进行大量的稳健性(robust)检验与研究。在实验指导语的使用方面,到底是使用抽象中性的用语还是使用具有腐败背景语言。目前,对此具有一定的争议。因为使用抽象中性语言会失去现实腐败情境中的道德因素,而使用腐败情境语言会带来“需求效应”,所以,在实验研究中还需要进一步检验与探讨。另外,需要把自然数据、实地实验数据以及实验室实验数据结合起来,综合利用不同研究方法的优势来检验同一个反腐政策的有效性。
(3)现有大多数腐败实验研究是建立在单个腐败交易活动基础上的,然而,官员的腐败水平也受到市场结构或力量的影响(Shleifer & Vishny,1993)。比如,在一项有关印度尼西亚亚奇(Aceh)市两条长途货运路线中的军队与警察的敲诈与腐败行为研究中,Olken & Barron(2009)安排调查员陪伴货车司机记录沿线检查点与称重站的人员配备(军人还是警察以及人数)与过路费用等数据。在这个数据基础上,他们研究发现,沿线检查点与称重站的数量显著影响着沿线军人或警察的腐败水平。这意味着市场结构或力量是一个影响腐败的重要因素。虽然上文已经分析了中间人与“四眼原则”等结构因素对于反腐的实验研究,可是,从市场结构的视角进行反腐政策的实验研究很值得期待。比如,从腐败供给方来分析,官员的数量、官员决策的结构(水平结构还是垂直结构)、官员间的竞争与决策权分配等因素都影响着腐败水平;从腐败服务的需求来分析,企业或个人的数量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相互独立或合谋)、受腐败服务影响的第三方力量等也影响到腐败水平。
(4)在有关信息公开与透明对于反腐的研究中,目前,主要采用的实地实验研究方法。我们认为对于该反腐政策的实验研究可以从三个方面进一步开展:其一,在信息公开影响腐败决策的机制方面,现有研究结论建立在民主国家的基础上,认为信息公开或透明可以通过影响选民的选举责任感、监督来提高官员质量与降低腐败行为。可是,在非民主国家,信息透明影响腐败的机制是什么呢?其二,公开信息与官员隐私的界限在哪里?我们应该公开官员的哪些信息呢?哪种类型的信息公开在反腐方面影响更加有效呢?信息公开的途径是否会影响反腐效果呢?我们认为这些问题还值得进行新的实验研究。其三,现有有关信息公开对于反腐的研究主要采用实地实验方法,我们认为信息透明与反腐的实验室实验研究也值得期待。
(5)现有反腐实验研究缺乏有关官员面对反腐政策时的学习行为研究(Olken & Pande,2012)。事实上,当官员面对一种反腐政策时,他除了会降低特定腐败行为外,还会学会采用某种不受政策或制度影响的腐败行为。也就是说,官员腐败行为具有学习性、内生性与动态性。这要求我们在实验设计中安排可供腐败官员自主选择的腐败行动类型空间,检验反腐政策对于官员内生性选择腐败行为类型的影响。
(6)对于一个具有体制性、系统性腐败的国家来说,我们认为反腐政策应该具有特殊性,值得专门的实验研究。除了上文分析的Berninghaus et al.(2012)研究了系统性腐败环境中的惩罚政策对于反腐的作用外,目前,还很少有学者涉及这个研究主题。对于一个系统性腐败的国家,惩罚与发现腐败的概率都会比较小,这样就使得许多反腐政策变得形同虚设,国家陷入腐败“陷阱”。如何走出这个“腐败陷阱”呢?我们认为可以考虑把宽大或赦免政策与其他反腐制度结合起来,在一个两阶段协调博弈实验背景中研究腐败问题。这只是一个实验研究的设想。在中国的反腐现实背景中开展该主题的研究应该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