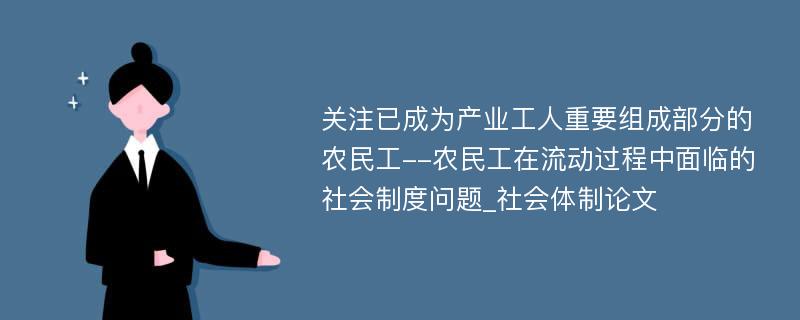
关注成为产业工人重要组成部分的农民工——农民工在流动中面临的社会体制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民工论文,产业工人论文,组成部分论文,体制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农民工”表面上看起来只是一种职业,实际上它更是一种制度性身份,也就是说,是我国现有的社会体制造就了农民工群体、农民工现象和农民工问题。所以,这里从体制层面就农民工问题,谈点看法。
一、农民工的尴尬
最近两年,国家对农民工问题很重视,特别是2003年,国务院办公厅专门颁布了有关农民工问题的一号通知(国办发[2003]1号),该通知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国家对农民工态度的明显转变,充分肯定了农民工的作用。该通知也提出了一些解决问题的办法,比如要求各地政府解决好农民工子女上学难问题,要求各地政府切实保护好农民工的权益。到了去年下半年,国家还兴起了一场清理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运动。但是,我们在调查中发现,仍有不少农民工陷入了三大尴尬境地。
第一大尴尬是农民工子女上学问题。在国务院一号通知颁布后,一些地方确实放宽了农民工子女上公办学校的限制。尽管一号通知要求公办学校不得向农民工收取赞助费,但是实际上不少公办学校还在暗中收取,并且没有明确的收费标准,完全视学校领导是否满意而定。该通知还要求放宽对农民工子弟学校的限制,但是该通知颁布后不久,北京某区还采取缔所有农民工子弟学校的突击行动。该区教育局负责人说,所有农民工子弟学校都要取缔,因为它们不符合办学条件,该区的公办学校完全可以解决农民工子女上学问题。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去请教该区教育局的一位领导,是不是彻底解决了农民工子女上公办学校的问题?他说,已经全部解决了,所有农民工子女都上了公办学校。但是,农民工们告诉我们说,自从该区取缔农民工子弟学校后,他们的孩子就没学可上了,他们或者将孩子送回老家,或者到其他区县去打工,让孩子去上那里的农民工子弟学校。这种情况不是个别现象,在不少城市都存在。
第二大尴尬是辛苦赚的那点工资,还是被拖欠了,有的好几年拿不到手。去年底国家下了很大的力气,甚至连国家总理还为重庆农妇熊德明讨工资。即使如此,也只为农民工讨回了200多亿元的工资,而实际上农民工有1000多个亿的工资被拖欠。今年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响亮的承诺,要在3年内全部清理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这个承诺给每个农民工点燃了希望之灯。但是,从这个承诺中也可以看到,清理工资拖欠问题,还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一年时间都解决不了,还得用3年。而3年时间对他们来说实在太长。
第三大尴尬是,农民工作为国家公民,与城市居民应该一样享受公民权,但是,他们就是不能获得同工同酬,也不能获得同等的就业机会,在就业上往往受到歧视性的对待,更主要的是他们无法获得迁移城市、定居城市的权利。如果将农民工与偷渡到国外的人相比较,就会觉得农民工确实受到了不公待遇。因为偷渡到西方发达国家,如果能坚持5到10年的人,基本上都能获得永久居留证,享受当地给予本国公民的除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外的所有公民待遇。
二、社会制度与利益刚性问题
在这些尴尬的背后,是我国一些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在起作用。当然,造成农民工问题的不是单项制度,而是一整套的制度设计和安排,包括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劳动就业制度、人事制度、组织制度、人口迁移制度、教育制度、财政制度、住房制度乃至政治制度等,这些具体制度从总体上将农民工与城市居民有区别地分离出来,使其成为一个社会边缘群体。
从市场制度来看,虽然农民工就业是通过市场实现的,但是这个市场是缺乏公平原则的:第一,法律上对农民工的就业权益的保障是相当缺乏的,国家对企业或单位侵犯农民工权益的监管力度相当软弱,甚至处于空白状态。第二,政府成为侵害农民工权益的一个重要主体,如拖欠民工工资最多的还是各级政府,又如不少管理部门想方设法向农民工收取各种费用。第三,我国从就业制度上将农民工排除在外,农民工不能进入国家的再就业体系,有不少城市限制农民工的就业范围,国家公务员制度也没有向农民工开放,由此可见我国尚没有形成统一的、公平的、合理的劳动力市场。
农民工更没有像城市职工那样享受国家提供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他们把青春、健康贡献给城市、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但是把年迈、伤病留给自己。这种不对等的制度在发展中国家也是少见的。
与此同时,农民工作为流入地的纳税人、国内生产总值的创造者之一,应该享受到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但是我国的财政体制和领导政绩考核体制却把他们排除在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享受之外。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按现代国家管理制度,农民工子女的教育不应该是个问题,但是,我国的教育财政制度并没有把他们列为支持对象,所以,公办学校的领导就说他们不愿意接纳农民工子女,因为政府拨给他们的教育经费并没有把农民工子女算内,除非农民工交一定的赞助费或者政府为农民工子女增拨经费;而地方政府则认为,国家实行的是分级财政制度,他们只管本辖区的居民的公共产品和服务,除非中央政府给予财政支持。而往往是中央政府只颁布政策,不掏钱,所以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虽然受到领导人的重视,解决起来就非常困难了。当然,这里还有个问题,就是各级主管教育的领导也没有外部动力去抓好农民工子女教育工作,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我国的领导政绩考核制度存在的问题:只对上负责,而作为农民工对地方政府领导前程缺乏发言权和影响力。所以,尽管中央三令五申要求流入地政府解决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但是效果并不明显。
从城市化制度上看,农民工也是被排除在外的。具体表现在这样几方面:第一,各地城市规划并没有把农村流动人口作为依据,还是以户籍人口为基数。像北京这样的超大城市,如果包括近400万外来人口,那么现在总人口当在1600万以上,但是其城市规划还是设定北京城市最大人口容量为1700万。这样的规划显然不利于农村流动人口在北京实现城市化。第二,城市商品房制度也没有考虑到为农村流动人口提供符合他们经济条件的廉价住房,城市的廉租房不是面向他们的,而只是面向有城市户口的低收入阶层。第三,更主要的还是上面提到的城市教育没有全面向农村流动人口子女开放,而教育是外来人口融入城市社会的最主要途径,对农村流动人口的子女来说更是如此,目前的教育制度只能使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社会趋向更加边缘化,造成了边缘化的代际传递,严重地损害了社会公平。
这些制度之所以难以得到有效的改革,是因为一直以来,城乡之间、地方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利益都是通过这些制度进行分配的,如果要彻底改革这些制度,势必要重新分配利益,这样,既得者的利益有可能受到损害。而现实中,利益既得者往往是社会的强势者,从某种程度上左右着改革的决定和方向。所以,尽管这几年,城市改革也在推进和深化,但是这些改革不但没有重新平衡城乡利益,缩小两者之间的差别,相反却不断扩大了城乡差距、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差距。从对有关制度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不少不利于农民工的制度是在改革开放后设置的,而不是改革前设置的,比如,收容遣送制度、城市就业划分工种制度(或叫区别就业制度)、暂住证制度、就业培训上岗证制度、就业许可证制度等等。表面上这些制度似乎是为了更好地管理城市而设置出来的,而实际上对农民工来说,更多的是限制、控制和剥夺(收费制度)。
三、全面改革和建构现行社会管理制度,促进城乡均衡、协调发展
农民工问题在制度上体现的不仅仅是农民工的权益得不到保障,更主要的是反映了我国还没有实现彻底的社会转型,还没有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制度。国家仅仅靠出台单项的政策,是难以彻底解决农民工面临的问题的,必须从整体上改革社会管理制度,大幅度调整社会利益分配机制(特别是政府转移支付机制),加快市场制度建设,建构新的社会管理制度。具体地说,当前国家要从制度层面上解决如下一些重要问题。
第一,国家应从宪法和法律层面,建立统一的国民待遇制度。这样的制度要遵循这样三大原则:一是非区别对等原则,即国家对每个公民在基本的社会政策上要一视同仁,不应区别对待;二是同酬原则,即国家保证每个公民享受同工同酬的权益;三是中央政府承担原则,即国民待遇是由中央政府提供的,也可以由中央政府委托地方政府办理,但是有关财政经费仍然由中央政府承担,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建立监督、处罚地方政府侵犯国民待遇的机制和制度。
第二,国家应将城市化确立为最基本的发展战略。仅仅提“城镇化”,已经不够了。“城镇化”的局限性忽视了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在城乡协调发展、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主导作用,同时也忽视了城乡人口的流动规律——即城市比城镇有更大的吸引力,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发展机会。只有确立城市化战略目标,才能根据城市化的要求,对农村流动人口提供技能培训、社会文明适应、教育服务等配套支持体系,让他们顺利地融入到城市社会中去,不再是长期漂浮的流动人口,他们的子女也不再被城市教育体系排斥在外。
第三,取消对农民工进入市场的制度壁垒和限制,建构公平竞争的市场体系。虽然一些城市已经取消了有关不准农民工从事某种职业的规定,但是并不意味着现实中就不存在了,实际上还有各种限制,特别是国有单位的用人、招工制度还没有全面向农民开放。开放劳动力市场,并不意味着农民工就有竞争能力,但是至少可以消除制度上使农民工边缘化的机制。与此同时,国家要建立就业公平监督管理机制,惩处不公平或歧视性用工行为。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修改《劳动法》,其次要调整政府职能,推进政府用人制度改革。
最后,国家要建立面向所有人的社会安全和保障体制。不论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都需要国家提供社会安全、保障产品和服务。特别是农民工,在外务工经商就要冒很大的风险,但是,当前我国的社会安全和保障网基本上不覆盖他们。统一的社会安全和保障体制应该包括三部分内容: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统一的社会救助和应急体系,统一的最低生存支撑体系。
从这里我们看到,没有彻底的、总体性的制度改革,不建立统一的国民待遇制度,没有把城市化作为最基本的国家发展战略,只出台单项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政策,那么,在实践过程中就不会达到预期的目的和效果,农民工就不可避免地陷入各种尴尬境地,城乡和社会经济就难以达到统筹发展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