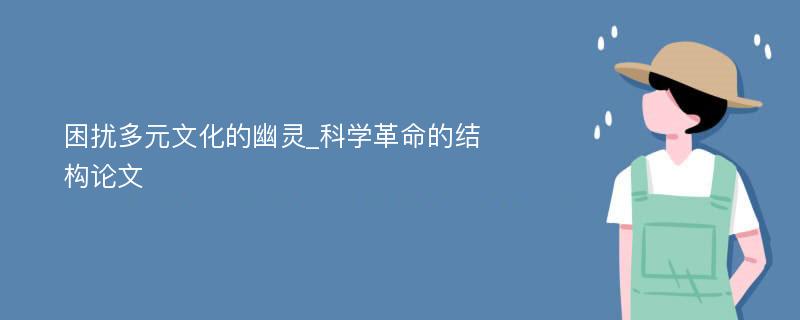
困扰多元文化主义的幽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幽灵论文,困扰论文,主义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发表于2010年3月的美国权威杂志《哲学与社会评论》(Philosophy & Social Criticism),表明了作者的文化观点。作者以哲学核心术语“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为切入点,追溯了该术语的演进过程以及多名哲学家对它的不同理解。伯恩斯坦认为,多元文化主义要求我们去寻求一些共同的立场,不同的文化应该努力通过文明对话与相互尊重来解决文化差异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消除所谓的不可通约性引发的文化冲突的困扰。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近几十年来,“多元文化主义”这个说法得到了广泛的讨论并且呈现出多种意义。但是,一个幽灵已经困扰了对于它的研讨。文化是复杂多变的,然而,当我们谈到多元文化主义时,总是难以抑制地将不同文化视为或多或少带有逻辑性的各个整体,每一种文化因其独特的完整性而区别于其他文化——我们无论是以人类学的、宗教的、政治的方式去思考这种文化间的差异,还是在种族层面上对其加以思考,都会得到同样的结果。生活在一种特定文化环境中的个体会频频感觉到作为这种文化中的成员所获得的最强烈的归属感。因此,多元文化主义问题就变成了我们将如何去思考它的问题,变成了当不同文化间存在着严重的冲突时我们如何去实际应对的问题。当不同文化语境中的成员认为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和信仰与其他文化视野下的价值观和信仰大相径庭时,由此而引发的文化上的冲突就显得尤为严重。“不可通约性”是一直困扰着这些不同文化观点的一个幽灵。我想要探究的问题是:为什么在20世纪后期有关不可通约性的研究如此流行?我相信我有理由认为这个观念的使用并没有经过辩证的思辨过程,它对于多元文化主义的研究已经造成了潜移默化的有害影响。我建议应该通过探究不可通约性在哲学发展上的渊源来做进一步的研究。
当托马斯·库恩的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在1962年出版时,知识界一片哗然。这本书造成了轰动效应,对它的研讨涉及范围很广,包括了人文主义的、文化的和社会学的领域,可以说在20世纪60年代很难再找出另外一本同样轰动的书。尽管库恩最初的兴趣是在已经确立的自然科学上,但关注这本书的自然科学家寥寥无几,这本书反而成为人文主义者和社会科学家研究问题的关键性文本,甚至已经到了将库恩理论的表述当做我们日常生活用语的程度。我们都会谈论“范式”和“范式的转变”,这些术语的使用非常频繁,以至于人们意识不到它们来自库恩的专著。有一个表述成为引发不断争议的导火索:不可通约性。突然之间,每个人似乎都在谈论不可通约性——不可通约的范式、理论、语言、词汇、文化和世界观。我不想回顾不可通约性引起的错综曲折的争辩,我认为那些内容是令人困惑的和需要进一步澄清的。我主要对另外一件事感兴趣,即不可通约性被接受的问题。为什么关于不可通约性的热烈讨论会如此广泛?这一表述是什么意思?引起众多思想家丰富联想的诸多观点究竟意味着什么?甚至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从对不可通约性的激烈争论中能够学到什么?但是,我确实想从库恩最初的文本开始研究,继而简要地探究理查德·罗蒂如何借用和转变了库恩的理论。
“不可通约性”这个表述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被使用了大约6次之多。当讨论到大多数科学学科在早期发展阶段会存在着在思想上相互对抗的流派时,库恩写道:“各种流派之间之所以存在差异,并非在于它们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方法(它们都是‘科学的’),而在于我们如何称谓它们看待世界以及进行科学实践的这些不可通约的方法。”①很久以后,当他分析科学革命的本质和必要性时,告诉我们“经历科学革命之后幸存下来的常规科学传统不仅与之前的传统相互排斥,而且往往是不可通约的”。②
但是,库恩对不可通约性的主要讨论(尽管非常简要)是在他对科学革命的解决方法进行分析的语境下进行的。库恩试图阐明为什么相互竞争的两种范式的支持者“可能[每一方]都希望让另一方转为相信自己一方的观点和方法,[然而]双方都不希望去证明自己的方法”。他剥离出三个原因来说明为什么“相互竞争的范式的支持者一定是没有将彼此的观点完完全全地联系在一起”。这些原因就解释了“常规科学传统在革命前和革命后存在着‘不可通约性’”。首先,“相互竞争的范式的支持者对于任何一种候选范式所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清单并不能达成一致意见。他们对科学评定的标准或定义是不同的”③。其次,“除了在判断标准上存在不可通约性以外,还要涉及更多方面的问题”。用以解释的概念体系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此,例如,要从牛顿的宇宙转向爱因斯坦的宇宙,“由空间、时间、物质、力等等构成的整个概念体系将不得不发生转变并对自然整体进行重新规定”。但是,第三个原因是:“相互竞争的范式之间最根本的问题是存在着不可通约性。”④我将会详尽地引用下文,因为它是关于不可通约性争议的主要资料来源。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不能作出进一步的详尽分析,因为相互竞争的范式的支持者们是在不同的世界里做着自己的事情。一个世界里满是慢慢降落的物体,另一个世界里的钟摆还在来来回回地重复着单调的运动。在一个世界里,解决方法是化合物,在另一个世界里,则是混合物。一个是嵌在平面里的世界,另一个则是在有曲度的空间世界里。由于是在不同的世界里进行实践活动,两组科学家在同一个方向上的同一点看到的却是不同的事物。我再次强调一下,这并不表明他们想看到什么就能看到什么。两者都在注视着这个世界,而他们眼睛看着的那个世界从未发生过任何改变。但是,在一些领域里,他们看到了不同的事物,他们看到事物处于不同的联系之中。这就是为什么某条规则对于一组科学家来说甚至是无法论证的,而对于另一组科学家来说也许却是本能的和显而易见的事情的原因。同样,这也道出了其中的原因,在双方希望全面沟通之前,一组或另外一组科学家必须经历这样一次转变,也就是我们一直以来所说的范式的改变。恰恰是因为这是一次不可通约的事物之间的转变,又加之逻辑因素和科学家想要保持中立的经历,因此,相互竞争的范式之间的转变不可能是一次迈一小步的渐进过程。这种转变就像格式塔,它必须立即出现或者根本不出现(尽管不一定是瞬间发生)。⑤
我已经几乎引用了库恩明确谈及不可通约性的全部内容,尽管他在其他地方说到的大部分内容和他的讨论也是相关的。但是,这些内容是具有教育意义的,不仅因为它们说出的内容,而且也包括它们尚未说出的内容——它们避而不谈的内容。请注意,库恩没有在任何文章里为他所使用的“不可通约性”这个说法下定义或作出明确说明。
但是,在评论库恩和“不可通约性”这个术语的命运之前,我想思考一下库恩的观点是怎样由罗蒂在他的著作《哲学和自然之镜》一书中被赋予新的观点和转变的——这是一部与《科学革命的结构》一样颇具挑战性与争议性的著作。我已经表明库恩试图阐明自然科学的结构和发展动态,他引入“范式”这个术语的初衷是基于这样的观点:只有诉诸范式才能使我们将自然科学与其他学科和话语加以区分。但是,在罗蒂那里却没有这样的限制。他遵循的是更大的游戏规则。他试图去做的事情简直就是解构哲学(是带有大写字母“P”的哲学),就是他一直追溯到柏拉图那里的一种传统,又被罗蒂改称为“笛卡尔—洛克—康德式的传统”。这一传统已经在专注于认识论和语义学研究的分析哲学那里焕发了新的生命。与库恩不同,罗蒂清楚地告诉我们“可通约”的意思是什么:
可通约性告诉我们如何通过一整套规则的作用在那些需要解决相互冲突的陈述的每个点位上实现理性上的一致性。这些规则告诉我们怎样去建构一个理想的情境,在这一理想的情境中,所有残留的不一致性将被视为是“非认知的”,或者仅仅是言语上的,又或者仅仅是暂时性的——是那些通过进一步的行动可以被解决掉的不一致性。⑥
由笛卡尔—洛克—康德式的传统发展而来的现代哲学,无论是以分析哲学的形式还是以欧洲大陆哲学的形式,均对可通约性情有独钟。对可通约性的探究是认识论所独有的特征。正如罗蒂所理解的那样,阐释学并不是一种新方法或者新学科的名称,而是“表达了一种想法,即由认识论的撤除所留下的文化上的空洞将是无法弥补的”⑦。通过观察罗蒂是怎样创新了库恩所理解的“常规的”和“非常规的”(革命的)科学,可以显而易见地看到罗蒂那具有挑战性的阐述的强大效应。对于库恩来说,常规的科学就是一种解决难题的学科形式,常规科学内部有一些关于通约性的广为接受的研究步骤。当异常现象不断出现,而它们似乎又不属于任何一种现行的范式时,非常规科学就产生了。但是,对于罗蒂来说,可通约性并不是常规科学的唯一特性,它应该被理解为是任何一种知识探究的特征。
这样一种探究实践(或者更概括地说,话语实践)与常规科学具有一致性——如同在注重“学术性”的人文科学中以及在“经院”哲学中或“议会”政治学中显而易见的一致性。我们可以得到这种一致性[认识论上的通约性],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在“人类知识的本质”上有新的发现,而只是因为当一种实践活动维持了足够长的时间时,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相对容易形成,这些传统观念使这一实践成为可能,并且就如何划分实践达成一致意见。⑧
总之,是根深蒂固的各种实践活动之间的“熟悉感”(familiarity)使一种话语成为常规的和可通约的。不同领域里的实践变为“常规的”实践——从物理学到神学。当熟悉的和广为接受的实践(无论它们属于哪个领域)受到挑战时,非常规的话语就产生了。“非常规的话语可以是从胡言乱语到知识革命的任何内容,没有什么规则可以描述它,只不过是有一个规则致力于对不可预测的因素或者‘创造力’进行研究。”⑨罗蒂很清楚自己的观点极具挑战性。他知道,从柏拉图时期的哲学家到当代哲学家,普遍认为通约性最不可能成为理性的一个必要条件。
常规科学如同实在一样在认识论的观念上是理性的。每个人都就如何去评价其他人说的事情持相同的意见。更加概括地说,常规话语就是在一整套约定俗成的规则下进行的相关讨论,对相关问题给出答案,提出与该答案相关的一个合理论据或者对那个答案的一个善意批评。⑩
《科学革命的结构》和《哲学和自然之镜》两部著作引发了如此激烈的讨论是毫不奇怪的。很快就出现了对这两部著作的批评,指出库恩的观点和罗蒂对非理性的赞许会直接导致一种作茧自缚的相对主义。例如,卡尔·波普尔批评库恩在支持“框架的神话”(Myth of the Framework),这种“框架的神话”的隐喻是:“我们是被困在层层框架里的囚徒,我们的理论的、期盼的、过去经验的和语言的框架在束缚着我们。我们被封闭在其中,不能同包围在截然不同的‘不可通约的’范式之内的人们进行沟通。”(11)尽管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Putnam)同意罗蒂的大部分观点,但是他还是始终如一地认为罗蒂引领我们走上了适得其反的相对主义之路。
在一片混乱的有关不可通约性的争论和评论中分清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谬误的是目前的一项任务——这些争论困扰着哲学家长达数十年之久。为什么这些争论引起了如此广泛的不同领域中众多思想家的丰富想象?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在《超越客观主义和相对主义》一书中,当我谈到“笛卡尔式的焦虑”(Cartesian Anxiety)——由伟大的“要么/要么”(Either/Or)引发的焦虑——时,对该问题已经给出了初步答案:
要么我们的存在有某种支撑物,我们的知识有牢固的基础,要么我们根本无法逃脱黑暗的力量,它用疯狂、用知识和道德的混乱来封闭我们。……认为笛卡尔式的焦虑主要是指宗教的、形而上学的、认识论的或者道德上的焦虑也许是错误的。这些也许仅仅是许多种焦虑形式中的几种罢了。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它是“本体论的”而不是“实体的”,因为它似乎就位于世界上我们存在的中心。(12)
使用罗蒂的术语,我们可能会说,如果我们放弃了可通约性,如果“词汇”之间真的是不可通约的,如果相互对立的词汇之间没有中立的和非历史的标准来进行判断和评价,就很难找到人们喜欢一个词汇或一种范式而不喜欢其他词汇或其他范式的原因。毕竟,罗蒂告诉我们,“通过重新描述可以使任何东西变好或者变坏”。
外行人可能会因哲学家们争论这些问题的狂热激情而感到困惑不已。当我们转而去考虑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道德的、政治的、文化的和宗教的因素时,类似的问题却令人感到沉痛。对可通约性的笃信是与道德的普遍性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深受这一信念的影响。他们认为,在不同的民族之间存在着普世的道德准则和人权,它们超越了不同民族之间宗教的、种族的和文化的差异性。一些评论家争辩说,这些断言“普世的道德标准”(当它们被揭掉面纱之后)投射出的却是欧洲中心论的种种偏见。这种种偏见尚未动摇一些人的信念,他们坚信一切人类都拥有不可亵渎的价值观和尊严。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要“不遗余力地”探求不可通约性的观点的话,那么我们也许会问:什么东西可以保证人们相信有普世的道德标准和人权呢?
此外,尽管在1989年共产主义阵营解体之后,人们对未来的世界有着各种各样伟大的期盼,但是我们已经目睹了各种事件的爆发,民族的仇恨、残杀,甚至是种族灭绝。波斯尼亚、卢旺达、达尔富尔以及其他许多地方发生的事件,使我们懂得了煽动凶残的仇恨并操纵普通人成为杀人犯和强奸犯是多么容易的事情。当不同的民族彼此对视时,似乎他们的全部世界观、价值观和信仰都是不可通约的——如此地不可通约和令人厌恶,以至于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进行“种族清洗”或种族灭绝。行凶者们并不认为他们违反了人权,因为他们甚至不将他们的“敌人”视为人类。罗蒂用了下述话语简明扼要地阐明了这一观点:
塞尔维亚人在90年代对波斯尼亚穆斯林犯下了持久的暴行,然而塞尔维亚的谋杀者和强奸犯们并不认为他们自己违反了人权。因为他们不对同类做这样的事情,而只针对穆斯林。他们并非冷酷无情,而不过是真正的人类对冒牌的人类存在着偏见而已。他们在做的事情就好像十字军战士在区别人类与离经叛道的狗,这与黑人穆斯林区别人类与蓝眼睛的魔鬼的情形是一样的。(13)
这也是许多纳粹分子看待犹太人的方式——犹太人根本就不是人类,他们是要被铲除的害虫。这一受到鄙视的“他者”不但同作为人类的“我们”在各个方面是不可通约的,而且还在极大地威胁着人类。
那么我们对这种不可通约性又能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呢?我的确不想假装自己能够对这些问题给出完整的答案。我有一个比较小的目标——对怎样去思考它并如何通过相关问题来开展工作提出建议。让我们回到哲学的语境当中去,在这一语境下引发了许多关于不可通约性的激烈讨论。当波普尔谈到“框架的神话”时,确实取得了一些成果,尽管我认为他对库恩的批评有些跑题了。用维特根斯坦的话来说,不可通约性所构成的某种图景束缚了我们。无论我们提及各种范式、框架、词汇、观念体系、世界观以及文化等等中的哪一个,它都是一幅图画,在这幅图画中,我们认为那些范式、结构、词汇、观念体系、世界观以及文化都是无窗的单子(windowless monads)。它们是如此地自我封闭,以至于根本没有同外界的真正交流,也没有彼此之间的真正沟通。库恩关于“不同世界”的阐释暗示的正是这样一个图景。但是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氛围中,使用可通约—不可通约的二分法是极具误导性的。库恩和罗蒂都假设,不同的范式或不同的词汇无论在某些方面多么具有不可通约性,也总会在其他一些方面是可以通约的。如果这一假设不正确的话,我们就一定连库恩和罗蒂正在一直做着的事情都无法进行了——他们一直在比较不同的范式或词汇。当我们谈论任何领域的不可通约性或可通约性时,我们应该明确说明在哪些方面(以及在何种意义上)我们正在思考着的新范式或新词汇的候选者是可通约的还是不可通约的。这一点并非微不足道,因为认识到总是存在着一些部分的重叠是进行比较和相互讨论的必要基础。但是,还有更为重要的一点,将不同文化、词汇、语言框架和范式等等之间存在的差异归结为不可通约性是非常具有误导性的,是静态的和教条的。这一图景忽视了在某种程度上任何正在使用的语言、词汇本身都是开放的。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形象地阐明了这一点,尽管我们的境况和视野总是有限的和受制约的,但是他认为所有的知识都必然是开放性的。
每一个有限的在场都有其局限性。我们对“境况”这一概念定义时会说它代表了一个立场,它局限了视野所及的可能性。因此,对于境况概念至关重要的概念是“视域”。视域是指从某个有利地点可以看到的全部事物的视野范围。将这一点应用于思维,我们会涉及视域的狭隘性、视域的延展性、新视域的开启等等。自尼采和胡塞尔起,这个字眼一直被用于哲学当中,用以描述思想总是与其有限的确定性紧密相连,以及用来表明某人的视野范围是渐渐被拓展的。(14)
伽达默尔继续批判了封闭视域的观点:
人类生活的历史性进步就在于绝对不会受到任何一种观点的束缚,因此,也就永远不会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封闭的视域。视域应该是随着我们一起移动的。一个不断移动的人,他的视域才会不断地变化。(15)
在《真理和方法》一书中,伽达默尔主要关注的是对文本、艺术作品和历史传统的理解,但是他的反思对于理解其他文化和民族起到了重要作用。他确实没有阐明一切视域、语言和世界观都是可通约的(如罗蒂所阐述的那样)。相反,恰恰是因为其他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视域同我们的是不可通约的,理解的阐释性问题便出现了。我们没有直接的可以通约的标准去理解、解释和翻译那些最初令我们感到奇怪和陌生的文化。伽达默尔并不否认不可通约性,但是他既不将其模式化也不使其教条化。无论我们是理解一个奇怪的文本、传统还是一个陌生的民族,不可通约性都为我们设置了阐释学的问题。真正的理解要求发挥想象力,学会如何倾听和作出反应。我们必须特别注意差异性,警惕肤浅的翻译形式,当我们的成见与事实不符时,要作出相应的调整。我们无法跳出自己受制约的有限视域,进入某种中立的客观视野,或者站在上帝的视角去看待问题,但是我们可以扩大和丰富我们的视域,实现伽达默尔所说的“视域融合”。从本质上说,“视域融合”就是一个对话的过程。
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在他的经典文章《从当事人的视角出发——论人类学理解的本质》中的确抓住了这一阐释学过程中的精华之所在。他指出:
使最地方性的局部细节同最全球化的整体结构之间不断缩小差距的过程是连续性的辩证过程,通常通过如下的方法使两者同时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我们在两者之间跳来跳去,部分使整体成为可能,并构成整体,整体推动着部分,也孕育了部分,我们试图通过恒久的知性运动将它们转化为对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的相互解释。(16)
格尔茨认识到他正在描述一个阐释循环圈,他认为这对于人种学的阐释极其重要,他以下面这段话作为文章的结束:
一个人所获得的关于他的信息提供者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的感觉无论是百分之百的精确还是百分之五十的精确,不取决于这个人接受——比如这种接受是这个人自身阅历的一部分,而并非信息提供者们自身阅历的一部分——的经验,而取决于这个人解释信息提供者表达方式的能力,也就是我所说的他们的符号系统。这样一种接受使得这个人不断努力去拓展接受的符号系统。理解——我这里再一次使用了这个危险的字眼——当地人内在生活的形式和困境,其实更像去理解一句谚语,捕捉一种幻象,看懂一则笑话——或者如我所说的,就像读一首诗——而不是达成共识。(17)
因为历史的视域常常是变动不居的,因此提及一个最终的或者完满的理解——从理论上讲,是一种无法进行修正或调整的理解——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即使带着这个世界上最良好的意愿,充满耐心而又细致周到地想要理解“他者的”或者同我们自己文化不可通约的那种文化,我们也许仍会失败。理解是有局限性的,我们渐渐意识到我们理解的局限性和不可靠性。伽达默尔的阐释学理论中出现的不可通约性概念完全不同于“框架的神话”。不可通约性对理解构成了挑战;它不是固定的或静态的,而是变化的、流动的,欢迎新的思考和修正。伽达默尔有关批判性地接受传统的观点可以被概括为对所有事物的理解——包括对其他文化、宗教和种族的理解。
认为强调传统中的基本因素以获得全面的理解,就意味着对传统不加批判地接受,就意味着一种社会政治学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这是一种很严重的误解。……事实上,我们的历史传统总是面临着对这种传统的批判性挑战。……每次经历都是一次对抗。(18)
我并不是说伽达默尔对于理解、视域、语言和不可通约性的反思都是无可置疑的。有时,他倾向于低估在理解时以及在不同视域进行融合时的障碍物。他并没有解释造成理解失败的所有原因或者为什么误解是如此普遍的现象。他没有谈及当今世界里的权力和媒体如何扭曲了信息的交流。他也几乎没有关注他所描述的那种对话所需的“物质条件”。正如哈贝马斯曾经指出的,伽达默尔有时在写文章时认为,似乎对话和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在任何社会或文化当中都能成为可能。然而,我确实认为从伽达默尔关于不可通约性的挑战中仍然可以吸取重要的教训。
他的阐释学的理解中存在着一个伦理—政治的视域。伽达默尔不仅仅是要描述和阐明理解的发生。他是要不断地告诉我们到达“可信的”或者“真实的”理解和对话需要做些什么。对于伽达默尔来说,对话要求学会一门很难的艺术:倾听——真正的倾听,并学会倾听不同于我们的声音。当他强调我们与不同文本、传统和艺术作品对话时,他所强调的对话是一个互惠互利的过程。但是,当我们从第二人称参与者的角度去讲话时,对方不是一个文本或一种传统,而是另外一个人,他能对我们讲话,能真实地回答是或者不是,此时伽达默尔有关对话的观点就更为重要了。这一点也是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和伦理学对话理论的核心。
真正的理解既要求发挥想象力,又要求具有谦逊的态度,想象力可以拓展我们自己的视域,谦逊的态度可以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的视域是有限的和受制约的。恰恰是有了理解,我们才能批判性地检验我们的预判和成见。只有在我们与不同于我们的他者细致入微的碰撞中或者通过这种碰撞,我们才能增进自我理解。总之,要从事伽达默尔为我们设定的任务,即进行阐释学的理解,就需要发展或培养一整套相互关联的美德。现在,我可以容易地想象一位批评家引出的下列反对之声的原因:
伽达默尔阐释学的简要描述与你们所谓的在“真实”世界里“令人恐惧的”不可通约性问题——这种不可通约性能够引发大屠杀甚至种族灭绝——有什么关系吗?难道你(包括伽达默尔在内)对在哲学家中过于普遍存在的欲望不感到内疚吗?这种欲望是指哲学家们认为政治学中的残酷世界能够或者应该被比作一个理想化的研讨会,在这样一个研讨会上,文明的对话大概是可以发生的。在“真实的”世界里,所倡导的对话往往变成一种伪装的权力游戏,其目的就是为了获得支配地位,根本不会带来双赢的思想上的交流。
作为强烈认同美国实用主义传统长达50多年的人,我不需要被提醒哲学家们由于有着这样的欲望而忽视了日常实际生活中的艰难现实。但是,让我正面回应这种反对之声。我认为人们无法诉诸哲学来解决具体的政治问题。哲学——或者更概括地说,知性的自我反思——所能做的事情就是为我们的日常生活以及面临的具体问题和任务确定方向。伽达默尔对于理解和对话的思考是与不可通约性的问题相关的,因为它们将我们引向一个实际的任务。我们所居住的世界中存在许多悖谬,其中之一是:一方面,日常的实践活动和经验具有强有力的趋同性倾向;但是,另一方面,恰恰是这些倾向使敌对的差异变得更具有不可通约性。各种各样的团体,无论是宗教的、种族的还是政治的,开始将它们自己视为自我封闭的无窗的单子,会受到“敌人”的威胁。“框架的神话”对于他们不是什么神话而是生活现实。“认同政治”的巨大危险之一是助长了一种心态,即那些具有如此心态的人坚信“他者”是无法理解的,“他者”是具有威胁性的,因为“他者”使他们(怀有如此心态的人)感到压抑和羞辱。哲学反思的首要任务在于破除“框架的神话”,进行哲学的或知性的解构,使我们逃离充斥着自我封闭的范式、世界观等不可通约的情境的束缚。不可通约性并不是阻碍理解的理论上的、认识论上的或者语义上的藩篱。相反,它向我们发起了一个实际的挑战并提出了一个实际的任务(实际上是提出了一整套任务)。“谈论”不可通约性往往是一个借口——表明从事相互理解这一困难的工作的失败。倒退到简单化的二元对立和两分法——“我们”与“他们”相对抗——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在觉察到危机存在的时候,如“9·11”事件以后的一段时间里,遍布全球的焦虑与恐惧(往往是愚弄大众的)使得简单化的二元思维方式很具有吸引力。如果我们在促进相互理解方面的态度是认真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自我愚弄地认为相互理解可以简单地通过意愿或者协商得以实现。正如我所指出的那样,相互理解要求一整套相互关联的习惯、性情、惯例。它要求努力工作。相互理解不是一蹴而就的。它要求不懈的努力和对局部的关注——相互理解通常始于带有地方色彩的背景。没有什么替代物——或者运算程序——可以取代对局部的关注而获得的实际判断。无论我们如何定义“文化”,文化都是动态的和快速变化着的。并且即使是在特定的文化情境中,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世俗的犹太人同世俗的穆斯林之间比起他们同自己族群里的正统教徒来说往往有着更多的共同之处。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具有多重身份的。
正如我所指出的那样,寻求理解不可通约的事物并不意味着完全赞同或者达成一致的意见。批判与理解之间存在着微妙的辩证关系。如果我们的批判要成为智性的批判,那么批判必须基于理解的基础之上——而不能基于不真实的描述和陈腐的思想观念之上。在真正去理解事物的时候,我们的批判性的观点也要随之调整和转变。
最近几年,哈贝马斯针对世俗主义与宗教撰写了一些颇具挑战性的文章。在此我结合了一直以来同他的一个主要观点存在某些争议的内容。通常,世俗主义者同宗教信仰者常常歪曲彼此的观点,在正视对方时,仿佛他们的“世界观”是完全不能通约的。对于哈贝马斯有关“后世俗主义”的观点,我持保留意见,但是,我很赞同他所倡导的世俗的无宗教信仰者与有宗教信仰者应该自我反思并认真努力地互相学习的观点。我同意哈贝马斯对于民主公民权的观点,他声称民主公民权对于“世俗公民心态上的要求与对有宗教信仰的公民的要求是同样的”。(19)这要求一种开放的精神,同时还要与笃信自己民族的价值观和信仰兼容并蓄。
我想通过强调三个要点来结束本文。
首先,一个告诫。我们必须警惕不现实的和多愁善感的倾向。没有任何观念可以逃脱被歪曲和误用的可能性。这一点尤其适用于对话的观念,因为对话有时被用在政治生活当中。通常,提倡对话是获取政治优势的伎俩;它是某人在权力游戏中进一步获得利益的花招。并且我们必须对这样的观念加以质疑,即冲突总是能够通过对话的方式得以解决或协商。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曾经说过,政治学的世界不是幼儿园,也不像一个理想的研讨会,在那里我们可以通过对话来化解我们不同的观点。我们可以达成一点共识,不可通约的差异性是很棘手的——我们遇到的个人或族群都没有兴趣致力于相互理解和真正的对话。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从根本上消除他们认为不同的、异己的或不可通约的东西。经历了20世纪和21世纪初期,没有人对此观点仍然天真无知。但是,一个主要的危险在于我们总是过于仓促,因而无法对棘手的不可通约的差异性作出这样的判断,而是在这样一种信念上按照被误导的方式采取行动。
其次,我一直以来都认为,这种阐释学的开放性需要实践和美德,但我们必须承认这种实践和美德具有脆弱性。对确定性的追求——追求哲学的、道德的、政治的和宗教的牢固基础——是根深蒂固的和不屈不挠的。由于哲学论辩的原因,人们很少会放弃追寻绝对真理的欲望。要容忍偶然性、模糊性、易谬性的感觉以及对于他者和与我们不同的事物采取真正开放的胸怀是很不容易的。开放性和易谬性是潜在的威胁。但我并不将这视为绝望和愤世嫉俗的理由。相反,由于面对不可通约的事物时阐释学的开放性所展现的脆弱性,因此有必要热诚地坚信我们的任务是在局部和全球的背景下真正实现阐释学的开放性。多元主义是当代生活的一个基本事实,它有善意的和恶意的多种形式。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应对多元主义。我们可以寻求去否认它或者(从字面上)去消除它——这是极权主义政体的目标。但是,我们也可以寻求去批判性地探究什么是真正不同的事物,什么让我们觉得不可通约并且真诚地努力推动这种探究,即在不否认或不歪曲不同于我们的事物的“他者性”的前提下批判性地理解它们。并且,我们必须不断地和热忱地寻求创造“物质条件”,它是我们进行坦诚的批判性探究的必要条件。
最后,我们必须诚实地对待哲学追问的重要性和局限性。正如我之前所指出的那样,我不相信仅凭哲学自身就足以解决“真实世界”里的实际问题。但是,哲学有助于解构阻碍相互理解的神话和偏见,哲学可以批判不可通约性误导的种种现象,是不可通约性造成了持续的仇恨。哲学可以澄清指导我们行为的目标和准则。当我们面对各种不同于我们的观点时,我们感觉似乎受到了威胁,因为这些异己的观点挑战了我们最根深蒂固的信仰,由此棘手的问题就会出现,哲学可以鼓励种种应对棘手问题时的文明行为和公开对话。
我引用了我最喜欢的约翰·考特尼·默里(John Courtney Murray)的一段话来结束本文,它精辟地表达了我一直以来的观点:
当人类停止按照合理的法则进行对话时,就意味着野蛮将会威胁人类。这些法则是争论的法则,如果想要使对话成为文明之举,那么奉行合理的法则将是十分重要的。当争论被激愤和偏见所支配时,争论就不再是文明的对话了;当争论的词汇变得像唯我论者的词汇时,他们(唯我论者)是基于这样的理论,即我的见解只属于我,不能与他人分享;当对话让步于各种一家之言时,当对话的各方停止彼此倾听,或者只听他们愿意听到的内容时,或者只按照他们同类的视角去看待对方的观点时……当诸如此类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人类将不能参与到争论之中。交谈变得仅仅是争吵或抱怨。文明之举也将随着对话的消亡而消亡。(20)
注释:
①②③④⑤Thomas Kuhn,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2nd edn ent.,Chicago,IL: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0,p.41,p.103,p.148,p.149,p.150.
⑥⑦⑧⑨⑩Richard Rorty,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9,p.316,p.315,p.321,p.321,p.320.
(11)Karl Popper,"Normal Science and Its Dangers",in Criticism and the Growth of Knowledge,ed.I.Lakatos and A.Musgrav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0,p.56.
(12)Richard J.Bernstein,Beyond Objectivism and Relativism:Science,Hermeneutics,and Praxis,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83,pp.18-19.
(13)Richard Rorty,"Human Rights,Rationality,and Sentimentality",in On Human Rights:The Oxford Amnesty Lectures 1993,New York:Basic Books,1993,pp.112-113.
(14)(15)Hans-Georg Gadamer,Truth and Method,London:Continuum,2004,p.301,p.303.
(16)(17)(18)Clifford Geertz,"From the Native's Point of View:On the Nature of Anthropological Understanding",reprinted in Interpretive Social Science,ed.P.Rabinow and W.Sulliva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9,p.239,p.241,p.108.
(19)Jürgen Habermas,"Religion in the Public Sphere",in Between Naturalism and Religion,Cambridge:Polity Press,2008,p.143.
(20)John Courtncy Murray,We Hold These Truths,New York:Sheed & Ward,1960,p.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