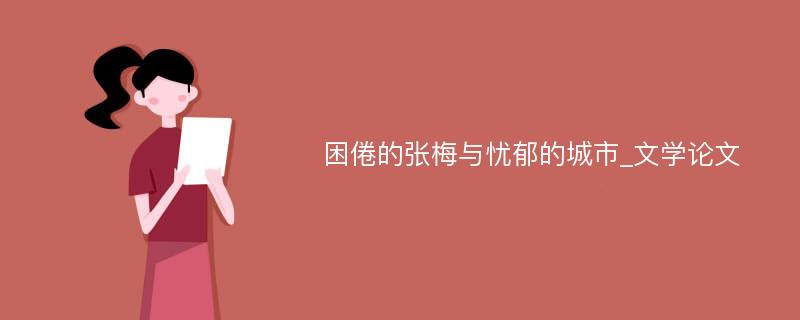
睡眼惺忪的张梅和一座忧郁的城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睡眼惺忪论文,一座论文,忧郁论文,城市论文,张梅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常常在一些文学聚会上遇到张梅。她说得不多,总是一副睡眼惺忪的样子,目光中似乎有一种十分迷离的东西。如果她对“睡眼惺忪”这个词不满意的话,我可以给她换一个——“目光炯炯有神”。我想,她更不会满意的。老实说,“炯炯有神”这个在过去的肖像描写中频繁出现的词,如今已经有滑稽色彩了。三十年前,就是那些“炯炯有神”的眼睛常常能在一点蛛丝马迹中看出“阶级斗争新动向”。今天,也是“炯炯有神”的眼睛能在哪怕是一堆垃圾中看出哗啦哗啦的钞票来。长得漂亮的小歌星大多都有一双毫无内容的、“炯炯有神”的眼睛。如果一位作家也有着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那还成什么体统。
其实,“睡眼惺忪”的状态对于张梅个人也许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它可能是一种观察都市的最好方式,我曾经被陀思妥耶夫斯基肖像上那双梦幻般的眼睛、还有波德莱尔那忧郁的眼神所打动。我似乎感悟到,陀为什么能在大都市彼得堡的小市民忧心忡忡的目光中,发现那个时代的忧郁;波为什么能在巴黎街头的拾垃圾者身上看到诗人的影子。
都市是什么?这恐怕是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的世界文学所面临的一个难题。商业化的都市是文明风暴的中心,又是罪恶的渊薮;它催生着各门类的艺术,又将它们埋葬;它培育着个人主义和自由精神,又无时不在将这些精神剥夺;在井然有序的街道背后,隐藏着无数混乱和诡秘的契机。施宾格勒甚至说:世界的历史就是市民的历史,就是城市的历史。20世纪的作家很少会像梭罗和华兹华斯那样,完全拒绝都市文明,而隐居到湖畔去对着自然吟唱。都市是可以逃避的,都市精神却无法逃避。它已经渗入到农村,乃至儿童的遗传基因中了。作家们都以各种方式介入都市文明,用各种方式去表达都市,形成了一种风格独特的“都市文学”。
在“都市文学”这一宽泛的概念中,常常混杂着军人式的和农民式的都市文学。前者的源头是古老的军事政治城堡,而不是商埠。它总想将都市里的每一个景点都当作街垒战的掩体,当作胜利的纪念碑;后者的根源在于一种土地情结,它会将博物馆前的台阶、街心花园当化田埂和放牧的草地,爱坐就坐,否则便受到伤害,便诅咒都市。所以,我们常常看到作家一方面迷恋于都市文明——文学沙龙、艺术博物馆、书市、报刊杂志、电视、作家协会等等,宁愿四处流浪最后死在人行道上,也不愿回到乡村去;另一方面又厌恶都市文明,批判它没有人情味,对人性的异化或者空气太差、太脏。所以,20世纪文学的典型风格就是“反讽”,翻译成口语就是“口是心非”。这种尴尬一直伴随着都市文学。都市文学的另一种尴尬是它时时受到新技术的冲击。印刷机和报纸断了作家用新闻体写作的后路;电视机让作家们“如实地展示生活的客观场景”的美梦破产。因此,真正的都市文学的表达方式永远是不断变化和创新,并拒绝新技术技能操作的表达方式的。
都市区别于乡村的本质在于,它有一种都市“心灵”的存在。这是靠记者所谓客观的眼睛,靠摄像机镜头无法发现的。中国的都市文学之所以不发达,就是缺少真正的都市心灵或精神,和能发现这种心灵或精神的眼。今天,都市的新的精神、新的文化语言就像巨大的磁石一样,时时在吸引着农民,同时也使广大农民受到伤害,感到狼狈,而常常诅咒或缄默无语;但当他们开始由农民变成市民时,他们便会渐渐地形成真正的都市体验,眼睛也可能会由开始的贪婪到后来的精明和豁达,许多忧伤和遗憾也会与对都市的爱交织在一起。至于能不能变得朦胧就很难说了。不过,没有一种对都市的真正的爱,就没有对都市的真正的体验和批判,更不可能有真正的都市文学。一种真正的都市经验的获得,是要付出数年乃至数十年生命代价的。当一个新的都市人回到乡村,家乡那没有污染的、纯净的空气令他咳嗽、哮喘的时候,他才可以说开始有些都市的经验了。
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曾经出现过都市文学的苗头,但都因外在原因而中断。同时,张爱玲的目光太怀旧,而刘呐鸥和穆时英的目光太贪婪,徐纡和无名氏常常见神见鬼。今天也出现了许多所谓的都市文学,但那些“炯炯有神”的目光,总是看到欲望、金钱那些摄像机也能发现的东西。他们并没有真正表达都市,无论其作品被安上什么样的与都市有关的名目。
二
在当代作家中,张梅是少数有着真正都市体验、并能用自己独特的艺术形式表达出来的作家。这得益于她有一种独特的观察视角,或者说有一双区别于“盲视”和“炯炯有神”的“睡眼惺忪”的眼情。张梅的视角是散点的而不是焦点的透视方法,它不是批判和诅咒,也不是占有之后的卑微的满足。它适合于瞬息变化、混乱无序的都市;同时它还能将都市的一切充满欲望的事物虚化,交织到市民心灵变化的过程之中。在这样一种都市文化语言的背后,一座都市的忧郁像灰色的雾一样弥漫着。
张梅生长在广州这座远离政治中心且商品气息浓郁的大城市。她无疑有着地道的都市情感方式和生活方式。我敢肯定她很爱这座留下了自己青春激情的城市。她早期曾写过一篇叫《殊途同归》的小说,可以看作是她青春激情的一座方尖碑。但是,这部小说并不是典型的现代都市小说,其中的都市带有浓郁的军事政治城堡性质。一群身份不明的人躲在烟雾缭绕的小酒馆(小铁皮屋)里密谋着、争斗着、有点像十九世纪中叶巴黎左岸区。他们喝酒、吟诗、争女人,就差没有发动街垒战。值得注意的是小说的后半部,写到了都市的文化和市民的力量、精神的颓废和欲望的膨胀如何像一场雨一样将他们的激情熄灭。小说最后的结局是,那些热情的青年无论以何种方式,都告别了“军事城堡式”的都市,而走进了真正的现代都市,也就是说由“战士”变成了市民。我可以断言,这是张梅早期生活的一个总结,也是她新的创作生涯的开始。
张梅后来的小说依然是在写都市;其小说的大多数场景也都在广州,但基调有了很大的变化。她常常以一种独特的笔调写到广州的茶楼和小点心、酒店和菜的名字、花市和花的品种、时装店和名牌服装、老城的骑楼和街道、大排档、夜总会、保龄球、桑拿浴……废话,谁不会写这些?有人在嘀咕。你当然能写这些,但你不能睡眼惺忪地写,你不能以地道的老广州市民的方式写。
你可能是一个暴发的新市民,除了你的住宅区之外,你对一眼望不到边的大都市一无所知;你不知道珠江南面的南面是什么,西关的西面怎么样。你茫然而恐惧,你觉得这座城市时时都会将你吞食,你急于想抓住什么,你离它太近、太实、太功利,你只会睁大贪婪的眼写欲望和金钱,你的写作只是为混乱的都市增添混乱、为都市的欲望加油。
你可能是一个很有学问或很有人文精神的人,你爱睁大批判的眼写乞丐写贫富差别写污染写一切都市的罪恶和痛苦。那是因为你假定了一座没有乞丐没有污染没有贫富差别没有痛苦的城市。于是,你爱写汹涌澎湃的激情,爱写小酒馆里的哭泣;你爱抒情,而不愿叙事。
正因为张梅对现代都市有着深入的体验,她才渐渐地放弃了抒情而学会了叙事,并开始沉着冷静地讲述都市的故事。因为她清楚地知道在商品化的大都市里缺少的不是“激情”,它的下水道里都流着“激情”。她甚至不惜用忧郁、虚无和厌倦来压制那盲目的激情。这种选择的无奈,或许正是她的作品中忧郁情调的根源。她在一篇叫《区别于大众情感的情感》的创作谈中提到:
我的精神状态一直是虚无的。有人说我是散淡,其实更准确地来说是虚无。我有一段时间很希望能像卡夫卡和巴赫金那样地生活,但自知没有他们的旷世才华,像他们那样生活会十分地孤独。而人生每时每刻,世俗的狂欢节夜以继日地在你身边举行,你又如何去抵制这些诱惑呢?
而且当你愈来愈无法抗拒地成熟时,你能遇到和产生的激情就愈来愈少,……你又因为激情的破灭而感到无奈。……
而一旦回归现实,我就发现写起小说来更得心应手。你在去掉幻想的激情之后,世界正以她的本来面目向你招手。形形式式的人生和欲望以各种形式表现在你面前,当你深入进去,你会感到温暖和生动。(《作品》96年第6期)
张梅以一个真正的都市人自居,并认为自己的“思想和生活习惯也是都市化的”,所以,她能在许多人厌恶的、自己也感到忧郁无奈的都市里发现“温暖和生动”的故事。张梅的确越写越好,也越来越机敏。在《老城幻事》(《钟山》96年第4期)中, 她不只是纪实性地写写广州人的饮茶,而是写出了他们的灵魂。在饮茶的态度上,我们可以看出一种古老的民俗在如何暗暗地抵御现代文明的侵蚀。崔健的摇滚、狂风暴雨也不能改变他们的饮茶时间。饮茶中隐含了这座古老城市人的全部激情。他们也因此而没有让商品交换异化成冷漠的都市动物。面对污染的灰尘时,许多市民都纷纷去寻找没有灰尘的地方。回来后他们失望地说:“那里灰尘是没有的,但其它的也没有。”他们不愿离开这被污染的城市,于是霓虹灯越来越暗,女人的脸越来越黄。“这一切都是灰尘的缘故”(尘缘?)。张梅还写了老城区的人对不断地失去的骑楼、青石铺就的街道、花市的迷恋之情;也写了防盗网、房产证等现代文明的产物,如何通过伤害的途径积淀到他们心理经验之中的。心灵的重负对都市居民的压抑,是远远超过环境污染的。在讲述都市故事的过程中,张梅总是极力地控制住自己的情感,并力求将抒情的念头控制在叙事的尺度上(《酒后的爱情观》)是很抒情的,那是因为主人公在北方出差时喝了北方的酒的缘故)。《摇摇摆摆的春天》中那一边吹彩泡一边行乞的小男孩消失之后,她写道:“那孩子是个神,他制造一个幻景催你醒悟。”这光怪陆离的都市的一切,不是神的显示是什么呢?请千万别用“宿命论”这个怪词来纠缠了!但它无论如何都是对迷途于现代生活的都市人的一种警醒。
三
在文学史上,常常推动着文学思潮、艺术观念、作品文体和语言变化的,就是都市文学。其实,都市在本质上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变化的是作家的观念。最初的都市文学迷恋于新奇的事物,并把它作为表达自由的个人主义的材料。十九世纪的都市文学把新奇事物当作震惊体验的源头来处理,震惊体验就是对人性的异化,是有人道主义情怀的作家批判的对象。十九世纪下半叶出现的自然主义思潮,则对都市的新奇事物放弃价值评判,而追求所谓科学地观察和客观地描写,包括都市里各种离奇事物和欲望。二十世纪的都市文学则把都市的新奇和震惊变成一种浓缩的心理经验来表达,并在自我意识的层面上加以夸大,形成了一种与浪漫主义有别的新的拒绝态度。作家们颠来倒去地摆弄着都市,但最终还是在城市这个“如来佛的手掌”里翻跟头。
张梅似乎对这些思潮和流派并不关注。她的写作一直是忠实于自己对都市近距离的体验和远距离的冥想。从《蝴蝶和蜜蜂的舞会》(90年)到《吃喝玩乐的日子》(《花城》97年第六期,改名为《随风飘荡的日子》),张梅的写作状态一直比较稳定,写作风格也没有大的改变。尽管这两年有人将她与一批后来者一起列入了“新状态”,但这并不一定说明张梅是一个领潮流的作家,而可能是潮流跟上了她吧。有那么一天,潮流跑得快了,远她而去,我猜想张梅还会这样写作、这样观察、这样体验。这不是我有多高的判断力,而是张梅的都市小说中有了她自己独具风格的视角、语言和观点。这一切都不是做出来的,而是她全部生命的日子和写作的岁月的果实。张梅那些独特的视角、语言风格在《老城纪事》中表现得比较明显。她写道:
老城的上空有一只眼睛。那只智慧的眼睛就常常浮现在晴天时的云朵中。当这只眼睛不满意时,晴空就会下起一场暴雨。王二小时候在自己家的平台上看见过这只眼睛。它当时隐藏在一朵马蹄状的云朵里。当王二看到了它,它也不躲避,甚至和王二对望。王二看到这只眼睛里有些忧愁,而它的忧愁也影响了王二后来的人生观。
王二有一天在茶楼见到一个长着和那只智慧的眼眼一模一样的人,特别是他眼里的忧愁。……王二定眼看他,他也不回避,甚至和王二对望。此情此景,都和他小时候在自己家里的平台上发生的情景一样。
如果张梅仅仅是个多愁善感的作家,那也不算独特。但是,她所表达的忧郁与多愁善感无关。我感到张梅的敏锐在于她凭着多年来对都市的体验、观察和写作,发现了都市的瘟疫、有传染性的瘟疫——冷漠!在《爱猫及人》、《没有鲜花的恋人》等许多篇章里,她都表达了“冷漠”这个典型的现代都市的主题。(这些小说中的人物多是些青年暴发户,而不是那些有着狂热的饮茶习惯的老市民。)
充满欲望的、混乱不堪的都市里的人,常常表现出一种充满才智的狂热、急躁和贪婪。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可能被一次通货膨胀,一桩意外的事件掩埋得无影无踪,唯有随之而来的冷漠,像瘟疫一样弥漫着,挥之不去。激情熄灭了的都市人,对一切都熟视无睹,天桥上的乞丐、夜总会的小姐、凶杀、车祸、眼泪……于是,这个一心渴望着现代化都市生活的时代,变得连一点儿“震惊”体验也没有了,剩下的只是冷漠、无聊和厌倦。都市的这种品质,成了张梅那忧郁的小说的布景。
我完全理解张梅为什么常常会突然离开熟悉的都市,去写一个西北高原的神秘故事(《红》,《作品》96年第三期),或迷恋于记录那保持着古老“女权”遗俗的顺德“自梳女”的生活;为什么常常宁愿去写“吃喝玩乐的日子”,去写狂欢的舞会(她甚至说:“许多真正优秀的人是隐藏在卑琐狂荡之下的”。);为什么面对都市常常既不愿闭眼熟视无睹又不愿睁大眼睛,而保持一种“睡眼惺忪”的姿态。
读了张梅的一本小说集《酒后的爱情观》(作家出版社,1995年12月版),还有一些最近发表在各家杂志的小说之后,我突然好像染上了忧郁症。我又想起了张梅小说《摇摇摆摆的春天》里的那段话,不禁打了一个寒颤。都市里的激情与冷漠、善良与罪恶、享乐与折磨,电网一样的立交桥、情人般地向你招手的商品,等等等等,所有这一切难道真的是神的启示不成?都市或许就是一座倾圮了的“巴别塔”,人与人之间不可能有相通的语言;也许是佛祖幻化出的种种魔障,目的是让人们能借此练习“幻眼法”而醒悟过来。否则,我们便无法解释人们为什么对它恨之入骨又不忍离去,被一种爱极恨极的两端情感折磨终生。
当然,都市是产生作家的摇篮,不要轻易地嚷嚷着要离开、要隐居到深山里或湖边上去。但面对着这无边的诡秘的都市,一位作家的职责也许不是来下判断,而是来作一个见证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