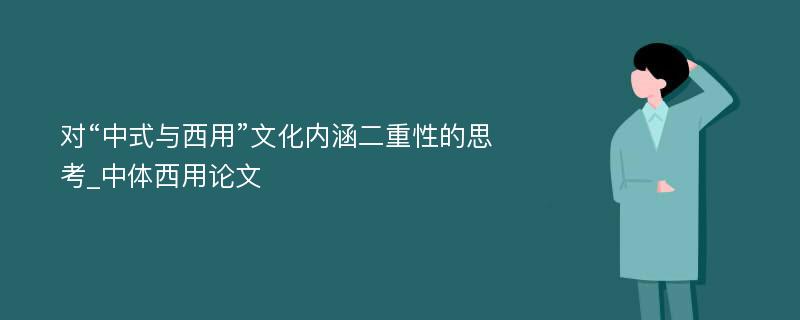
对“中体西用”文化内涵二重性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内涵论文,中体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体西用”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简称,是对“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是洋务派的理论核心和指导思想。
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摧毁了天朝帝国的陈旧壁垒,年青的西方文化以波涛汹涌之势冲击着古老的中国文化。高势能的资产阶级文化同低势能的封建文化展开了殊死搏斗。“中体西用”正是这场交锋的天然产儿。虽然先天不足的二重性使它仅仅存在了三十多年便英年早逝了,但作为在中西文化矛盾冲突中的一种重要的回应方式,这种观念却阴魂不散地流行了一百多年,至今仍影响着海峡两岸一些中国人的思想。因此,分析“中体西用”的二重性,不仅具有认清其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占地位的历史意义,更具有坚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信心的现实意义。
(一)“中体西用”命题本身的二重性
“中体西用”二重性首先就在于此命题本身就是违反逻辑的。众所周知,“体””、“用”是中国哲学特有的一对范畴。这对范畴的提出,是魏晋玄学的伟大建树。在中国哲学史上,王弼率先明确提出了这对范畴,他说:“虽贵以无为用,不能舍无以为体也。”(注:《老子注》。)自魏晋玄学起,就主张“体用一源”、“体用不二”。朱熹和王夫之是最善言体用的两位哲学大师。王夫之说:“天下无无用之体,无无体之用。”(注:《读四书大全说》。)他进一步举例论证道:“无车何乘?无器何贮?故曰体以致用。不贮非器,不乘非车,故曰用以备体。”(注:《周易外传》卷五。)朱熹也说:“如这身是体,目视、耳听、手足运动处便是用。如这手是体,指之运动提掇处便是用。”(注:《朱子语类》卷六。)可见,体、用是就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来说的,“体”指主体、本体或实体,“用”指作用、功用或用处,体、用密不可分——这就是体、用传统的最基本的内涵。
如果将中学、西学各看作一个实体,那么中学、西学各有其体、用,不存在“中体西用”或“西体中用”之说。后来有人批评“中体西用”是“体用两橛”可谓击中了要害。维新派严复对此命题的二重性作了辛辣的讽刺和批评,他说:“‘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两立,合之则两亡。”(注:《严复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58—559页。)也就是说,“中体西用”违背了体、用是一物的两个方面的中国传统的体用论的基本原则,将“中体”、“西用”毫不相干的方面生拉硬拽在一起,如同“牛体马用”一样,是一个学理不通的荒谬性的二重性命题。
(二)“中体西用”思想的二重性
“中体西用”不仅在形式上是个二重性命题,而且在内容上是一种二重性的思想。
在中国近代,“中体西用”者对待中西文化矛盾冲突持一种形而上学的折衷调和态度。它代表了在中西文化冲突中力图保持中国传统文化的本体或主导地位,并以此为基础来会通西学,以期中西合璧的一种努力。这就必然表现出其思想上的二重性:一方面要引进“西学”,一方面要固守“中体”。冯桂芬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薛福成1879年在《筹洋刍议》中阐述了“取西人器数之数,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的思想。郑观应于19世纪80年代在《盛世危言》中也主张“中学其体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1898年,“最乐道之”的张之洞撰写《劝学篇》,进一步从董仲舒的“大道源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唯心主义哲学观出发,把“中体西用”推向神秘化、神圣化、系统化。他强调“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至教”,“讲西学必先通中学,乃不忘其祖”,因此“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即是说要以孔孟之道“正人心”,以“西艺”济时需。《劝学篇》始终以“尊朝廷卫社稷”为第一义,以“保名教”、“杜危言”为己任,强调讲西学必“先以中学固其根柢”。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己完全成了镇压资产阶级政治改革的反革命思想和舆论工具。
可见,“中体西用”思想的实质是以“西学”为手段,以达固守“中体”的目的。对内用先进枪炮屠杀太平天国农民军,反对资产阶级改良和资产阶级革命;对外以对付西方列强的要挟恫吓。归根结蒂是借用西艺、西技去巩固、强化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文化。但是,由于“欧洲输入之文化,与吾华固有之文化,其根本性质极端相反”(注:《陈独秀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30页。),所以,企图要在老迈昏聩的封建纲常专制的“中体”的根基上,去发展生机勃勃的资本主义,并妄想通过资本主义——“西用”,去加固封建体制——“中体”的堡垒,这就等于在封建文化的“老牛”身上去嫁接资本主义文化“骏马”的四蹄。结果必然是非牛非马,“老牛”非但不能摇身一变为“骏马”,反而会因砍去“牛蹄”换上“马蹄”而举步维艰,气息奄奄。“中体西用”这种思想的二重性便决定了其价值的二重性。
(三)“中体西用”价值的二重性
“中体西用”作为一种政治思想和治国方针,其根本意图是重振大清王朝,捍卫封建专制体制。但事与愿违,“西用”的引进却导致了动摇“中体”的不测后果。正如列宁所说,历史总喜欢和人们开玩笑,本意想走进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
19世纪下半叶是中国被迫打破闭关锁国的局面开始走向世界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国从古代走向近代的重要历史转折时期。在古今、中西文化的激烈冲突中,“中体西用”以貌似公允、开放的心态,在适应民族文化心理的承受能力限度内,把仿效西方、变革社会的方案囿于不从根本上突破数千年封建文化本体这样一种温和的、不彻底的基本构想的模式之内,顽固地死死抱住所谓孔孟精义、封建名教不肯后退一步,企图以新卫旧,以西固中。实际上却是以消极的保守态度回应世界历史变化的潮流,阻碍了中国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束缚了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从而使西艺扭曲变形。当资产阶级维新派主张变法而触动中国封建制度这个“中体”时,当资产阶级革命派力图彻底推翻这个“中体”时,“中体西用”便完全暴露出其封建卫道者的面目,将矛头指向了资产阶级维新派和资产阶级革命派而走向反动。对于“中体西用”的这一负价值,两广总督张树声在其遗言中曾作了分析总结,他说:“夫西人立国,自有未来”,“育才于学堂,议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否恃欲?”(注:《张靖达公奏议》卷八。)
然而,“中体西用”毕竟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历史潮流,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在封建的旧文化弥漫整个中国,民族意识在愚昧落后和妄自尊大的恶性循环中自我陶醉之时,“中体西用”论以十分勉强、羞羞答答的封建文化的特有方式,表达了对近代资本主义先进生产力的爱慕之情和政治方面进行改革的朴素要求。在“中体西用”遮羞布的庇护之下,先进的西方文化才可能以“木马计”的方式神不知、鬼不觉地排除顽固的封建旧文化的重重阻挠而插足于封建旧文化这块世袭领地,给“中学”、“中体”以强烈的影响和冲击,为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争得了一定的合法地位,确实在当时起了“开风气”的进步作用。
从社会发展史看,由于西艺的引进,逐渐破坏了中国落后的自然经济,产生了近代工业的物质基础和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人们也就更认识到仅仅言艺并不能根本解决中国的命运问题,也就有了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的言政。于是,言观念、言文化、言伦理、言国民素质便应运而生,也就有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也就有了傍徨后的“救救孩子”(注:鲁迅:《狂人日记》。)以及“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觉悟”(注:《陈独秀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34页。)的摇旗呐喊,也就有了阿Q 的不朽典型和千千万万勇于冲破“铁屋子”的仁人志士的滚滚洪流,也就有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也就最终有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文化。
(四)“中体西用”根源的二重性
要深刻理解“中体西用”文化内涵的二重性,就必须提示其二重性的根源。“中体西用”二重性的秘密到底在哪里?我们不应仅从头脑观念中去寻求,而应从当时的社会历史状况中去探究。毛泽东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政治、经济的关系以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所以“我们讨论中国文化问题,不能忘记这个基本观点。”(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50页。)
考察五千年文化史可知,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其政治是封建的政治,其经济是封建的经济,反映此种政治和经济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必然是封建文化。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逐渐生长了资本主义因素。到洋务运动时期,中国已逐渐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二重性社会。这就决定了洋务派阶级属性的二重性:既有浓厚的封建性,又有一定程度的买办性;既有对外国资本主义的抵制作用,又有对民族资本主义的促进作用。“中体西用”的二重性正是社会基础二重性和洋务派阶级属性二重性在文化形态上的深刻反映:既固守封建名教,又想发展资本主义;既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又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既顺应潮流具有进步性,又逆潮流具有反动性。
这种畸形的二重性使“中体西用”发育不全,决定了其夭折的必然趋势。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经过洋务运动产生的二重性文化“中体西用”和经过明治维新产生的资产阶级文化“西体西用”,展开了一场血与火的正面交锋。甲午丧师本质上是“中体西用”二重性文化落后于“西体西用”文化的必然结局和铁的验证。
然而,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中体西用”的观念却顽强地影响着一些中国人的思想,迫使我们不得不给以深刻的思考和探究。
(五)“中体西用”二重性的启迪与思考
“甲午之役,军破国削”(注:《陈独秀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31页。),彻底宣告了“中体西用”的破产。但是,由于思想观念的历史惯性作用,“中体西用”观念并未马上销声匿迹,反而以各种变形借尸还魂,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施以阻碍作用。
“五四”以后梁漱溟的“三路向”文化观是一种新的中体西用论。1935年,陶希圣等十教授的本位文化论的理论基础也是中体西用论。抗日战争时期的新儒家理论,提出了“以儒家精神为体,以西洋文化为用”的口号。50年代后,港台现代新儒家学者主张“返本开新”,他们认为这是一种“中体西用”论。到了80年代,又有人提出了“西体中用”的理论,认为“中用”就是结合实际运用于中国,即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但笼统地主张以西方的生产方式、意识形态等为体,而不区别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意识形态。因此,“西体中用”论有若干混乱和不明晰之处。但其思维方式与“中体西用”论一样,都囿于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僵固思维模式,都不能正确解决中国的文化现代化问题。
从“中体西用”二重性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这种思想是当时社会基础二重性和洋务派阶级属性二重性在文化形态上的反映。即使在当时,其主导思想、历史作用都具有二重性,既有进步的一面,又有反动的一面。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五四”新文化运动给旧文化以毁灭性的打击。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又率领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官、封三座大山,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毛泽东提出要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就从根本上消除了“中体西用”所存在的社会基础及阶级属性。“五四”以来“中体西用”的各种变形仅仅是思想观念的历史惯性作用的一种无谓叹息而已。早已失去存在根据的“中体西用”论必定被时代潮流无情地抛弃。
有鉴于此,如何在世纪之交,在知识经济初见端倪的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进行文化建设呢?
我们主张抛弃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僵固思维模式,以开放的恢廓胸襟,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客观实际出发,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遵照江泽民的指示:“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博采各国文化之长,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建设的成就。坚决抵制各种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注: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2页。)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创造出更加绚丽多彩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文化,对人类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
标签:中体西用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