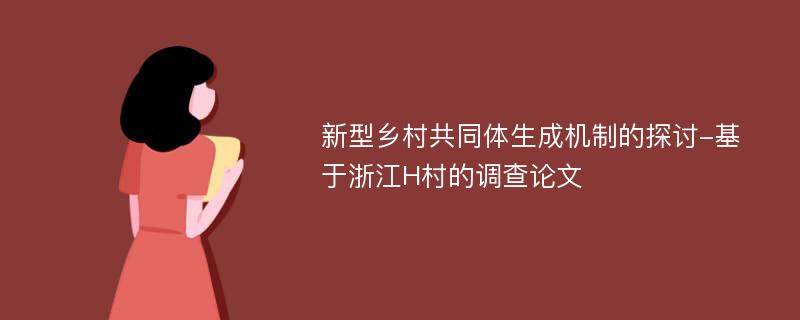
新型乡村共同体生成机制的探讨
——基于浙江H村的调查
徐建丽,朱登胜,胡晓霞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浙江金华321007)
摘要: 乡村发展,民心为本。百年变迁,乡村失魂,浙江义乌H村一群乡贤十年乡村建设,以功德银行重塑“守望相助”乡村道德教化体系;以文化礼堂为载体,重构村民“精神家园”;以新乡贤为核心力量重建乡村管理秩序;以村民经济合作组织为主体,重构乡村经济共同体。经过多年的实践探索表明,乡村集体文化的认同和激励机制的创新、村庄经济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的建立和互洽、村民乡愁情感的激发与互动,共同构成了乡村振兴与发展的内生动力。
关键词: 乡村;文化共同体;经济共同体;乡贤;乡村文化
随着现代化进程持续推进,我国乡村正经历着传统村落共同体的作用逐渐弱化,传统的伦理道德维系逐渐消失,熟人社会逐渐陌生化和疏离化,乡土价值体系和社会关系图式逐渐变更,村民的精神皈依陷入迷茫和矛盾状态。究其原因,新型乡村共同体构建的滞后,无疑是导致乡村缺乏凝聚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构建新型乡村共同体,已经成为重建乡村精神家园、增强乡村对村民的吸引力、实现乡村治理的重中之重。乡村发展,民心为本,百年变迁,乡村失魂,探索重塑新型乡村共同体,对乡村重新焕发生命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问题缘起和样本
(一)问题缘起
社会学意义上的共同体主要指自然的、地域性的、小型的,成员彼此熟悉、日常互动频繁、相互依赖、相互帮助的,以感情为纽带、具有某种共同生活方式的群体[1]。自滕尼斯提出共同体概念以来,国内外许多学者对共同体的作用、问题、境遇与趋势做了深入研究和探讨。农村的村落是真实存在的典型的共同体。村民自治、村规民约、民主协商、道德教化等只有在村落共同体的组织环境下才有实际意义。缺乏共同体的基础和道义的支撑,无论哪一类治理,都难以有效地运行,也难以有可持续性[2]。“村落共同体”对于维系村民之间的认同意识,增强村落的内聚性、向心力和凝聚力,保持村落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无法替代的作用[3-4]。乡村共同体具有传承性和阶段性的特点,其建构与发展是我国传统社会乡村稳定的重要基石。受城市化、市场化的影响,传统乡村共同体日渐式微,许多村庄出现凝聚力减弱、资源流失等系列问题。新型乡村共同体构建的滞后,是导致乡村缺乏吸引力的一个很重要因素。因此,增强村庄对村民的吸引力、重建村落精神家园、构筑村落社区共同体等已经成为构建新型乡村共同体的重中之重。如何发挥村落共同体在乡村社会和谐与发展、经济与文化建设中的作用,重塑“村落共同体”是乡村实现有效治理的重要环节。
乡村振兴的内生力量到底在哪?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如今,乡村振兴的内生力量正在悄悄地成长,它是中国乡村振兴的先导力量。作为经济相对发达的浙江,传统的乡村治理机制、治理方式将随着新经济形态的出现率先面临严峻挑战,已涌现出了如东阳花园村、桐乡新联村等具有影响力的新型乡村。
(二)样本
我们就以浙江省义乌市H村作为研究的对象和样本。
2.2临床症状以气急、呼吸困难为主,胸痛少见,这与老年人痛觉减退有关。气胸发生后,老年患者因慢性阻塞性肺气肿而产生的呼吸困难、胸闷等症状会进一步加重,在诊断过程中,会因症状与从前相同,导致自发性气胸与原发病产生混淆现象,进而导致漏诊、误诊[2]。本组1例住院5天才确诊。而中青年组均为入院当日确诊,故对老年慢性阻塞性肺病患者喘息症状加重而常规治疗无效者,应警惕可能发生气胸。
2008年,在很多人还不知薰衣草为何物时,H村就敏锐地发现了其中的商机,开始将周边13个村的荒坡地和流转农用地连成一片,大力发展以薰衣草为主的生态农业,形成一条美丽的薰衣草种植带、观光带[6]。采用专业化公司的管理模式,成立生态旅游开发中心,总投入2600万元,其中,25%的股份以村民的土地山水入股,其余75%股份由村民自愿认购。经历了从引种失败到成功的三年艰辛,薰衣草的引种成功为H村找到了“田园革命”的发展之路。每年吸引世界各地游客20余万人(依托义乌国际商贸城的特殊性),增加村集体收入470余万元,增加工资性收入500余万元,实现了以薰衣草为主线的集种植、加工、销售和旅游于一体的产业链。并在域外新疆开拓了267公顷的薰衣草种植基地,扩大了影响力,提升了美誉度和经济效益。在薰衣草乡村旅游的带动下,举办的酿曲酒节又使黄酒产业得到迅速发展,年利润可达300万元左右。
二、新型乡村共同体生成是多方资源整合互动助推的结果
(一)营造乡村文化认同铸就乡村重建启动力量
通过设立村庄共同目标途径,浙江义乌H村激发村民参与村庄建设的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强化村庄文化认同的引导,重塑村民的团队与合作理念。
3.前奏与尾声的乏味性。这是我们教师缺乏对教材、教法的深入研究。这样的准备活动与结束部分:一是内容枯燥、一般化,不能很好地体现出每个教材类型的特点;二是形式单一化,不能适应不同年段学生的身心特点。因此被视为前奏与尾声的乏味性。
1.重塑以功德银行为载体的“守望相助”乡村道德教化体系
面对当今社会传统道德逐渐淡化及消失,在以H村W主任为核心的新乡贤和村两委的模范带动和精心策划下,H村创办了“功德银行”。其目的就是通过传承积善行德的“敦风厉俗”,营造与建立起乡村互帮互助的村落共同体意识,引导村民承继淳朴、敦厚的乡风民俗,创建文明、互助、礼让、共享的新气象,重塑“守望相助”的村落共同体,建设“和美乡村”。
2008年初,在外经商十多年的村民W被推选为该村村主任,当选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领村两委与村里新乡贤、德高望重的老族长等,精心筹备创建了“功德银行”。以户为单位设立功德账号,由一名威望很高的退休教师具体负责记录村里发生的各种好人好事。例如:义务修理村里的路灯、清扫垃圾、帮助村里的残疾人、为外来人员引路、参加村里的志愿者服务活动等。
“功德银行”在村里创办以来,已设村民账号219户,积分总计已达8万多分,记录在册好事数千件。记录着H村96%以上的人做过的好事。现在村民们都能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村庄的公共事务以及各项活动之中,认为做些好事是应该的。“功德银行”运行十年逐渐形成了“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百姓亲睦”的敦风厉俗,并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新型乡村的道德体系。可喜的是,如今很多村民做好事后不愿留名,助人为乐已蔚然成风,形成了优良的民风乡风。
人情是维系乡村共同体的主要因素,生于斯长于斯的农村党员就是乡村治理的中流砥柱。以党组织为引领,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使H村破除了乡村变革中的阻力及不确定性[7]。
2.以“文化礼堂+”的形式重塑村民“精神家园”
在义乌人“无中生有”的特有思维引领下,薰衣草产业的发展让千年古村成了“东方普罗旺斯”,也注释了乡村崛起的发展公式。H村建立了薰衣草产业合作社,先用薰衣草致富再用品牌做产业,打造薰衣草和特色种植的农业产业链,实现了村里有产业、人人有事干、家家有收入,乡村发展有经济保障。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的“原子化”和“空心化”趋势不断加剧,原有的乡村公共空间不断荒废或被挤占,使得乡村公共文化组织日趋弱化,乡村文化“荒漠化”或“断根化”异常严重[5]。H村两委敏锐地抓住2013年浙江省启动的农村文化礼堂建设契机,利用闲置的何氏宗祠开展文化礼堂建设,打造村民的“精神家园”。文化礼堂既是对外宣传的窗口、村民互相交流的平台,又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更是培养村民尤其是青少年一代讲诚信、讲道德,有高尚品德和理想追求的公共空间。
何氏宗祠处于村中央位置。H村文化礼堂建在何氏宗祠内,文化礼堂正中央悬挂着一块“志成堂”牌匾,左右两侧是“簪缨从世”“理学传家”“富而安分”“贵而尚朴”四块牌匾,它们是村民传家的家族族训,教育着子孙后代要勤耕苦读,既要多为社会做贡献,又要能够保持富而不骄、贵而不奢的品格。现在的“志成堂”已经成为传承与弘扬乡村家族文化的基地,承载着国家政策法规的宣传、农村文化活动的开展、祖训家风的教化以及乡村风貌的展示等。宗祠的前厅是国家政策法规及村情的展示区。可以让村民和游客直观地了解乡村的历史以及发展概况。宗祠中厅的正中安放着供桌并悬挂了何氏始祖的画像,保留了何氏祠堂原有的尊祖崇孝等传统道德教化功能;宗祠中厅两侧墙上陈列着村民自己评选出来的道德模范的照片及其优秀事迹介绍,并在两侧的醒目位置安放了两台触摸屏一体机,用于介绍乡村的历史与发展、旅游景观、乡村文化等。宗祠后厅作为农耕文化展示区,摆放着H村村民使用的传统农具和传统生活用品。
街头的历史名人雕塑和墙体文化作为文化礼堂的载体延伸,将农耕文化、人居文化、山水文化及本村深厚特色文化等用墙体书画的形式展现出来,还在房墙上绘制了本村历史文化名人事迹,使人们在休闲观光中回味历史,体味文化。
通过“文化礼堂+”形式,H村在文化礼堂举办各种活动与仪式,如举办传统的红白喜事,过年时举办成人礼、新生儿入谱仪式,举办年轻人传统结婚仪式,重阳节举办尊老敬老仪式,新学期开学时举办新生启蒙礼等活动。重塑“精神家园”,启动了“文化礼堂+育才计划”“文化礼堂+老年大学”,以育才计划培育少年,以老年大学充实老人晚年生活。每年投资10万元,连续10年开展了“百万育才计划”,对于提高青少年道德水平、思想境界与实践能力起到了明显的社会成效。活动以主题为“孝道在我心中”“农耕生活体验”“感恩文化·大爱无疆”“和风润心田”等的“特别夏令营”来展示,让青少年认知大自然,体验农事耕作,描绘家乡美景,感受传统文化。创办于2006年的老年大学和“文化讲堂”,至今已整十三年,每逢农历初五、十五、廿五都要邀请退休干部和教师等开讲国学知识、时事政治、新农村建设、老年人养生保健等课程。
此外,通过“文化礼堂+酿曲酒节”举办何氏家酿曲酒节,既丰富了乡村文化活动,又塑造了何氏曲酒佳酿品牌,并且使何氏黄酒民俗文化得到了活态传承[5]。2018年4月的斯路晨读班是“文化礼堂+”在乡村治理方面的又一拓展。每逢农历“二、五、八”的早晨,村委会定期组织村民开展不少于一个小时的晨读学习。晨读班以“新时代,新启航”为宗旨,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递正能量,通过学“礼仪”为重点的系列教学活动,村民更诚信、友善,村庄更文明、和谐。
(二)构建以村民经济合作组织为主体的乡村经济共同体
特色农业、乡村旅游、“农家乐”等已是我国当今农村的产业新业态。H村适时成立了以村民经济合作组织为主体的乡村经济共同体,并在新农村建设中取得了显著成效,形成的乡村产业链支撑了自治组织模式的有效运转。
1.薰衣草产业链成为村庄经济支柱
(4)在建筑物加固改造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加固的顺序,一般宜先加固梁,然后再加固墙,最后加固楼板。同时施工时要采取一定的安全措施,以防在施工过程中出现安全隐患。
云小辫:鉴于该同学签名太有个性了,编编始终没弄明白姓甚名谁,但是能够掌握四门语言的意丝编编还是头一次见到。增加笑话的建议编编也会慎重考虑,毕竟编编也是很了解你们的,打开意少率先看搞笑图片和笑话的意丝应该不在少数吧,哈哈!
义乌市H村,距离义乌市区的世界小商品城15公里,常住人口1000人左右,全村总面积376.22公顷,耕地面积52.28公顷,林地273.96公顷,森林覆盖率较高。该村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的战国时期,距今已有两千多年,和千千万万中国乡村一样,这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古村曾经也十分贫穷并民风粗鄙。穷则思变,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H村大胆探索,以其独特的智慧,大胆实践乡村经济共同体与文化共同体共生互济的农村基层治理之道。2017年,H村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98万元,村集体经营性收入2240万元,集体资产上亿元;H村现已是“全国基层组织建设示范村”“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国家级生态文化村”“全国妇联基层组织建设示范村”“浙江省文化示范村”“浙江最美村庄”等。浙江义乌H村从落后山村蝶变为远近闻名的美丽乡村,其农村基层治理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
2.培育影视文化产业链
1.农村党建聚拢人心引发“蝴蝶效应”
推进乡村善治,关键在党的领导,这是乡村善治最坚实的支撑力量。在H村党员干部与村民发生纠纷时,首先处理的是查找党员干部的问题。实践证明,要夯实乡村治理的道德基础,首先是带头人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抓住了基层党员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就抓住了问题的根本。
2017以来,H村接连有多个剧组前来拍摄取景。影视剧组在H村拍摄期间,村内民宿一铺难求,餐饮店爆满,许多村民和孩子也都充当起了客串演员或进剧组帮忙,这是“文化兴村”理念的又一成功尝试。村委会还设想将H村打造成新媒体剧本原创基地,届时将举办凤凰卫视中国H村手机电影节。通过打造影视基地带动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培育影视文化产业链并形成新的经济发展增长点,达到乡村振兴的目标和任务。
H村通过打造薰衣草特色种植的农业产业链、培育影视文化产业链等,形成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新格局,以村民经济合作组织为主体的乡村经济共同体正在H村形成。
(三)乡村人才整合是乡村振兴的支撑力量
H村原本就是个土味十足的古老山村,在发展规划过程中刻意保留了部分典型的老房子,甚至连屋内的土灶台、旧家什等一并保存着,借助东阳横店影视城开创影视文化产业。
要让有德者有“得”就要建立乡风文明常态长效机制。为了激发村民常态长效参与道德信用体系的建设,构建新型的乡村信用体系,村主任以自己公司享有的信誉及无抵押贷款的政策共享给村民使用。村委会根据村民在“功德银行”的积分出具道德信用证明,村民即可到银行贷款30万元以下且无需抵押担保。只要是18至60周岁的村民并在“功德银行”积分超过50分,无任何抵押就可贷到最高60万元额度的低息贷款。如在创业之初缺乏资金的村民方庆华便是凭着“功德银行”的积分,顺利从银行贷款30万元开启创业项目。
H村在刚开始推行“功德银行”的时候,很多村民并不支持。在推行阻滞不前的关键时期,是52名党员带头做好事并“存”到“银行”,才得到村民的理解和支持,使一千多位村民成为“功德银行”的储户。村里的党员及领导干部们还在志愿服务、拆违征迁、乡风文明、治水护水环境整治等当中起带头作用。
据此我们认为“绿色2”是受西方语言的影响产生的, 由 “Green Revolution”(绿色革命)、“Greenpeace”(绿色和平组织)中的“Green”意译而来,继而它延用汉语本土的颜色词“绿色”的形式,在“绿色食品”、“绿色革命”的固定搭配中为己所用,适用范围也越为广泛。葛本仪先生在《现代汉语词汇学》(第3版)中提到现代汉语词汇演变的类型有义项的增多、义项的减少。[5]我们认为“绿色”的义项就是通过这种途径增加的。
2.发挥新乡贤力量为乡村治理“献智出力”
卓时Premier系列Precious月相功能腕表备有配以蓝色砂金石表盘的白18K金款和配以哈瓦那棕色砂金石表盘的玫瑰18K金款。海瑞温斯顿凭借精深艺术造诣,将珍贵材质与璀璨宝石浑然融合,精准描绘月球的运行轨迹。
乡贤了解乡村的历史与文化、与村民间有丰富的情感与交流,而且还存在着其自身利益与乡村利益的交融与捆绑,更因为他们是乡土社会的本地精英,在新一轮乡村振兴中应该让他们真正起到“领路者”“规划师”“带头人”的作用[8-9]。
H村就是在新乡贤的主导下逐步走上村庄复兴之路。H村主任本身就是村里的新乡贤,作为村主任的他通过村乡贤联合会、“乡贤论坛”平台,召集乡贤商议村庄发展愿景等,引导村民逐渐转变观念,积极投入到“和美乡村”的建设与实践中。利用新乡贤的家乡情怀及其广泛的人脉关系,聘请省内外专家并借助本地高等院校志愿者的力量,为H村进行规划设计、开展文化活动宣传和技能培训等,有效地激发了村落的发展活力。新乡贤力量与村两委形成的乡村治理合力,增强了治理绩效;乡贤“补位与辅治”作用促进其与其他主体间的合作共治,促进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现代乡村治理体系的形成。
三、结论与讨论
从浙江义乌H村的实践经验可以看出,培育村庄特色产业链是村庄复兴的物质基础,村庄集体文化认同是村庄重建的先导性力量,而乡村人才整合是乡村振兴的支撑力量。乡村集体文化的认同和激励机制的创新、村庄经济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的建立和互洽、村民乡愁情感的激发与互动,共同构成了乡村振兴与发展的内生动力。多年的实践探索让H村体会到,一个村庄要获得可持续发展,必须创造出持久的魅力。这个魅力就是文化,文化是魂、是核心、是真正的卖点。以文化传承为引领的旅游观光、休闲、娱乐、餐饮等产业互动才是可持续的。丰富多彩的、系列化的文化活动开展可以有效地提升村民的文化素质,实现传统农耕文化、山水文化、人居文化的有机融合。所有这些,都离不开乡村共同体,乡村共同体的重建需要从村落内外两个方面入手。
在村落外部,首先要着眼于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打破村落边界,强化村落共同体的运作效能,实现更大范围的区域联合,把村落共同体发展成为现代社会结合体的一部分[1]。H村生态旅游开发中心就是依据这一理念而成立的,是一种村落共同体与外部社会衔接的社会组织形态。其次要充分利用现代技术手段支撑村落共同体重建。利用“互联网+”为村落共同体的重塑提供服务,以村落为单位的微信群、QQ群等把相对分散的村落成员重新聚合在一个相同的网络空间内,实现村落成员的信息共享[10]。村落内各成员之间怀着共同的乡愁、讨论着共同话题,既密切了彼此关系又增进了对村落的认同感。
Three Yuan Mongolian, Chinese Manuscripts from Kharakhot
图4为3台泵运行、设双向调压塔、单向调压塔、泵出口阀两阶段关闭、尾阀两阶段关闭条件下的停泵水力过渡过程计算结果。
在村落内部,首先要强化村落经济共同体的建设,以村落为单位的经济合作社是村落经济共同体的现代组织趋势,它可以满足村民经济上互助互补与村落的可持续发展。其次要体现村民的主体作用,强化村民的主体性意识、增加农民的主人翁精神是村落共同体得以重建的重要途径。功德银行建设,既可以规范民俗行为又密切了村民间的关系,是值得推广的好经验。然后要建设好乡村新的公共空间,农村文化礼堂建设是村落共同体公共空间重塑的有益尝试。最后,利用新乡贤的乡愁情怀和人脉资源让他们参与村落共同体的建设与实践,实现乡村的经济与文化振兴。乡贤制度植根于乡土社会,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吸引有情怀、有道德、有能力,愿意为乡村振兴做出贡献的新乡贤返乡,这样有助于凝聚乡邻,整合乡村利益共同体,重塑新时代适应乡村发展的共享价值规范体系[3]。
浙江义乌H村的实践表明:中国乡村振兴必须走“文化与经济互洽互济”之道路。必须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认清中国社会大转型对乡村社会的深刻影响,顺应乡村的发展趋势,重塑新型乡村共同体,创新新时代乡村治理模式。
杆子就站在老柿树底下安排活儿。老柿树上系了两条拳头粗的绳子,拖得长长的。水真上来了,下面的人死拽着绳子冲不跑。杆子还组织人摽筏子,把附近住户的床抬出来,以备不测。有人笑干部们紧张,说他们纯粹是六个手指头挠痒,多一道子。这高岗上,啥时候上过水?汝河水几乎每年都满过,害得人每年都惶惶地跑水。跑多了,也不怕了。水稍微大一点,还能捞些从上游冲下来的生瓜梨枣。日子总像凉水一样平淡,社员们反而希望偶尔发场小水,调剂调剂生活。男女老少都带上饼子咸菜,热热闹闹地坐老柿树底下乱喷。
例 4:Kerbside materials collectionwas also attemptedin some sectors in Buenos Aires,but failed reportedly due to the high costs associated with collection and the decision not to subsidise such an effort.
参考文献:
[1]毛丹.村落共同体的当代命运:四个观察维度[J].社会学研究,2010(1):1-33.
[2]郎友兴.村落共同体、农民道义与中国乡村协商民主[J].浙江社会科学,2016(9):20-25.
[3]朱启臻.村落价值与乡村治理关系的探讨[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8(3):32-39.
[4]朱启臻,胡方萌.柔性扶贫:一个依靠乡村自身力量脱贫的案例[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5):122-125.
[5]鲁可荣,胡凤娇.“何”风润心田斯路传薪火[J].学术评论,2017(4):33-71.
[6]徐应红.生态文明背景下新农村建设的新着力点[J].理论观察,2010(5):85-86.
[7]张晓山.解决“三农问题”的行动纲领[J].中国合作经济,2017(10):14-16.
[8]傅才武,岳楠.村庄文化和经济共同体的协同共建:振兴乡村的内生动力[J].中国文化产业评论,2017(2):122-132.
[9]李军国.实施乡村战略振兴战略的意义重大[J].当代农村财经,2018(1):2-6.
[10]朱启彬.“互联网+”背景下的村落共同体重塑[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7(1):72-75.
[11]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M].史建云,徐秀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6-40.
[12]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9.
[13]莫里斯·弗里德曼.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M].刘晓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2.
Discussion on the Generation Mechanism of New Rural Community——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Zhejiang H Village
XU Jianli,ZHU Dengsheng,HU Xiaoxia
(Jinhua Polytechnic,Jinhua 321007,China )
Abstract: Rural development should be based on the will of people.On the account of centenary changes and lack of spirit of villages,a group of village elites from H Village in Yiwu,Zhejiang Province,has been working on a rural construction for ten years.They rebuild the“helping each other”moral education system based on the bank of merits and virtues;they reconstruct spiritual sanctuary for villagers taking the cultural auditorium as the carrier;with the village elites as the core,they restore the order of the rural area;they restructure the economic community with the village economic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as the main body.After years of hard work and practice,the identification of rural collective culture and the innovation of incentive mechanism,the establishment and mutual help of village economic community and cultural community,and the stimulation and interaction of villagers’homesickness constitute the endogenous impetus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Key words: rural area,cultural community,economic community,village elites,rural culture
中图分类号: C91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3699(2019)06-0018-05
DOI: 10.3969/j.issn.1671-3699.2019.06.004
收稿日期: 2019-05-30
基金项目: 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2018年课题“非物质资源整合对乡村共同体重塑的作用机理与运作机制研究”(18YJA840015)
作者简介: 徐建丽(1968-),女,浙江海盐人,金华职业技术学院教授,律师,硕士,研究方向为社会学;朱登胜(1962-),男,浙江金华人,金华职业技术学院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管理学;胡晓霞(1976-),女,浙江永康人,金华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社会学。
责任编辑:傅美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