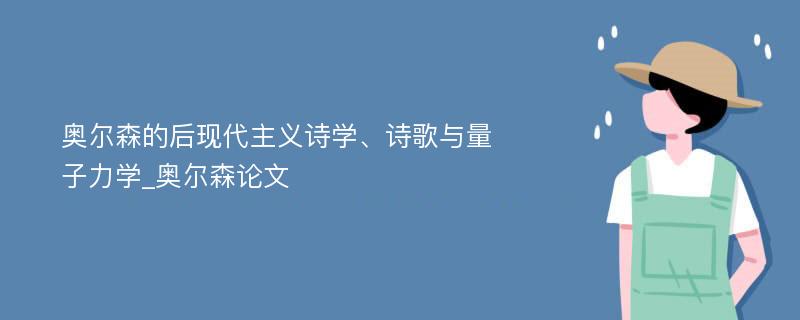
奥尔森的后现代主义诗论、诗作与量子力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量子力学论文,后现代主义论文,诗作论文,奥尔森论文,诗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02)05-0003-08
查尔斯·奥尔森(1910-1970)是著名的美国后现代主义诗人,也是西方后现代主义诗歌 中重要的“黑山诗派”的宗师。他的“放射诗”的新诗论在后现代主义诗学中具有举足 轻重的地位。他的代表作《马克西姆斯的诗》被称作“后现代主义史诗”,与惠特曼的 《草叶集》、庞德的《诗章》、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的《佩特森》并列为美国诗歌史 上里程碑式的巨著。
奥尔森成名于20世纪60年代,当时,后现代主义思潮开始在美国诞生,从理论到实践 ,整个文坛上澎湃着一股破旧立新的革命大潮。莱斯利·费德勒、苏珊·桑塔格和伊哈 布·哈桑等批评家在理论界大谈“后现代主义”观念,矛头直指包括现代主义在内的种 种流派的传统文学。小说家们也群起呼应,约翰·巴思谈论“文学的枯竭”,罗纳德· 舒金尼克和雷蒙·费德曼等人则宣称“小说已经死亡”,许多小说家进行小说革命,大 搞所谓“超小说”或“元小说”一类实验。在后现代主义小说诞生的同时,后现代主义 诗歌也应运而生。奥尔森早在50年代初就提出了“后现代人”的概念,并提出了轰动一 时的“放射诗”论,到60年代初又以令人耳目一新的诗作《马克西姆斯的诗》震动诗界 ,因而自然被目为诗界革命的先锋。
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典型特征是与现代科学层出不穷的新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当代美国著名批评家哈桑(或译哈山)在讨论后现代主义文学时,曾指出爱因斯坦的相对 论、黎曼几何、麦克斯韦等人的“场”论、海森伯的测不准原理、玻尔、薛定谔、狄喇 克、德布罗意等人的量子力学[1](P98-108)对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事实上,如果我 们检视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便不难发现,这些影响随处可见。美国作家品钦小说中的 “熵”和控制论、德国作家格拉斯和美国作家冯尼格特小说中对现代科学的奇特想象、 爱尔兰小说家乔伊斯《芬尼根守灵夜》中量子力学的痕迹、美国诗人威廉斯·卡洛斯· 威廉斯诗歌中关于“场”的观念等都是明显的例子。奥尔森的诗歌理论和诗歌创作中则 留下了量子力学的鲜明印记。
奥尔森在大学读书和执教期间除阅读大量的文学著作外,始终对科学有浓厚的兴趣。 著名数学家伯纳德·黎曼的非欧几何、诺伯特·维纳的控制论对他影响甚大;他熟悉爱 因斯坦的相对论、韦尔纳·海森伯的“测不准原理”,[2](P269、71、104)他曾在《叫 我伊斯梅尔》中说,作家或诗人需要采取一种创造性的立场,这就是物理学的立场,他 们必须要对事物做出测量,然而他们只能获得近似值,或者测知事物的速度,或者测知 事物的位置,二者不可同时兼得,这也正是海森伯的“测不准原理”所阐明了的,即要 想获得量子的准确速度,必不能获得其准确的位置,而要想获得其准确的位置,则必不 能获得其准确的速度。他在1957年发表《均等,就是,真实本身》一文,表明他十分了 解著名数学家赫尔曼·韦尔的《数学哲学与自然科学》一书的内容。他指出,非欧几何 对“真实空间”的重新界定,不仅产生了相对论、量子力学和一个连续的宇宙等新理论 ,同时也动摇了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一些传统观念。从物理学的新观点看,电磁场是 一个无限绵延的真实存在,在这个场上发生着的只能是相互关联的能量转换,因此,经 典的那个明确的宇宙已经消失,实际存在的只是一个没有方向地向四外绵延的宇宙,从 这样一个科学的观念推演开去,则传统哲学中那些形而上的分离和差异就都消失了,例 如,主客、因果、是非、彼此、心灵与肉体这些人们熟知的二元对立观念都失去了存在 的理由,剩下的只有一点:事物在事物中不确定的、变动不居的互相作用。对奥尔森来 说,真实事物的结构是曲折的、永远变化的,犹如消融在振动中的量子,它总在那儿, 但却始终处在无方向的流动状态。
奥尔森创造性地把这些来自数学和物理学的新思想运用在自己的诗歌理论和创作中。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科学对他的诗歌创作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一点与弗罗斯特不同 ,弗罗斯特是在写了许多诗之后,才意识到量子力学对自己的影响的,对弗罗斯特来说 ,科学不过是他诗作的花边和点缀,而对奥尔森来说,科学则是他诗歌创作的生命和骨 肉。毋宁说,弗罗斯特是十分被动地承认科学对其诗作的影响的,而奥尔森则积极地从 科学吸收新的理论和方法,来丰富自己的理论和实践。他认为,自然与人是一个有机的 整一体,量子力学描述的物质世界中这一“真实事物的结构”完全可以移植到人类意识 的世界中。这些科学概念为他的诗歌提供的不仅是隐喻,而且是一种理论,一种诗学。 正是从这种理论出发,他创造了所谓的“放射诗”。在这种所谓的放射诗歌中,科学与 诗已经融为一体,诗的境界就是量子力学所表述的境界,反过来,量子力学的境界也是 诗抒发的境界。
一、“放射诗”与客体主义
1950年,奥尔森在《纽约诗刊》发表《放射诗》一文,立即引起巨大反响,有人将此 文与贺拉斯的《诗艺》相提并论,在此后数十年中,它不仅引发了无数的赞美,也招来 了不少的非议,然而,不论赞成也好,反对也好,它始终不曾被人忘却。它不仅是奥尔 森创作中被各种文集选用最多的作品,也是美国许多大学文学课程必备的教科书或教学 参考书。它的问世影响了整整一代诗人的创作。它当之无愧地进入了20世纪美国后现代 诗学经典的行列。
《放射诗》开宗明义,说明自己是一种“开放诗”,从而把自己与传统的、当时盛行 的“封闭诗”区别开来。奥尔森明确指出,那种“非放射的”、“封闭诗”已经走到穷 途末路,诗歌要想继续生存和发展,必须找到自身的规律,“把诗人自己的气息和听觉 注入诗歌中”[3](P239)。奥尔森随即在技术和哲学两个层面上展开关于“放射诗”的 论述。
在技术的层面上,奥尔森提出了四个命题。第一个命题是:诗歌是一种“开放的”结 构,是一种“动能的”(kinetic)客体,一种“场上的写作”(field composition)。所 谓“开放”不仅指诗歌本身是一种开放的场,同时,指诗人必须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 诗人在构思时,要尽可能多地将其周围的种种能量和力吸收进自己的头脑中,然后在写 作中才能将这些精神的能量和力传递给读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奥尔森说:“诗歌在 一切方面都必须是一个高能结构,同时又必须是一个能量释放的结构”[3](P240)。可 见,能量的这一转换过程,就是“放射诗”的本质特征。第二个命题是:“形式只能是 内容的延伸”(Form is never more than an extension of content)。在这个命题中 ,奥尔森所指的形式是那种传统文学观念中所谓的先入为主的形式,或者说那种新批评 派所谓的经典形式。奥尔森认为,形式不能先于内容,而只能是内容的延伸,否则的话 ,形式就将扼杀诗人从自然中吸收的经验和思想。可见,这里所谓的“内容”并不完全 是传统意义上的“内容”,而是指诗人在写作过程中不断从外界吸收的思想、观念和印 象。从这个角度,我们不难看出,这个命题与英国诗人柯尔里奇的“有机形式论”有共 同之处,那就是形式应该是有生命的,应该从自然的、物质的过程中有机地生长出来, 而不应该先在地由诗人强加给诗作。按照第一个命题,既然诗歌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 、能量传递和转换的场,那么,形式就只能动态地生成,诗人作为一个行动的中介者, 其职责不是先给出形式,而是将其吸收的外在能量延伸并实现在形式中,从而再将这些 能量传递给读者。第三个命题是:诗人的感觉必须一个接一个立即地、直接地传下去。 [3](P240)这里,奥尔森强调了“放射诗”独特的写作过程。诗人从外界感知或者直觉 到的种种鲜活的力必须刻不容缓,间不容发地往下传,这样,那些充满生机的力和能力 才能毫不损失,原汁原味地传递给读者,感染读者。这也正是后现代主义诗学关于诗歌 创作过程的基本要求。第四个命题是:诗人必须把“气息”(breath)灌注到诗歌中。奥 尔森认为,“气息”是一种言说的力,是诗歌之所以能“放射”、传递能量的物质的载 体。如果说,诗歌的音节、字、词、行是蕴涵着能量的基本粒子,那么,气息就是最终 测定这些粒子的能量,并使得它们在动态中得以转换、传递的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 气息对于放射诗的品质就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了。[3](P241-246)
从哲学的层面看,奥尔森获得的新现实观为这种放射诗的诗学观念奠定了理论基础。 自从笛卡儿提出主客二分的观念,试图用主体与客体的对立解释世界以来,主客关系始 终是认识论上的一个重大课题。但无论从何种角度来认识主客关系,主客的分野和对立 却是始终存在的。即便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主体对客体的能动作用,强调主客在对立中 统一的辩证关系,主客的分野也是提出这一论断的前提。但自爱因斯坦以来的现代科学 提出的种种新论却彻底动摇了这种主客二分的基础。在这些新观念的影响下,奥尔森提 出了一种他称之为“客体主义”(objectism)的新思想,表达了认识客观现实的一种新 观念。客体主义就是要避免作为本我的个体及其灵魂的“主体”(对客体)抒情式的干扰 ,本我的灵魂的“主体”是西方人一个奇特的假设,他们把这个“主体”置于造化的创 造物,即他们自己,与造化的其他创造物,即我们并无贬义地称为客体的那些东西之间 。因为人本身也是一个客体,不论他以为自己有什么优越性,他越是能认识到自己也是 一个客体,他的优越性就越大,……[3](P247)显而易见,这里,奥尔森要削弱甚至消 灭主体的作用,他似乎宁愿使用“人”而不是“主体”的概念,所以,他才把主体置于 引号中。在他看来,人越是认识到自己也是客体,越是减少对客观现实的“干扰”,人 的作用也就越大。作为一个客体,人只是自然中的一个中介,只能参与到自然中。人必 须认识到,“人的宇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存在,他只有安居于自己的宇宙内,才有可 能作为一种中介参与到更大的外在现实中,才有可能倾听到外在世界中更大的力,也才 能通过听到的一切分享客体的秘密。奥尔森还提出,诗人要“谦卑”、“顺从”和“参 与”,诗人只有保持这样的态度来对待现实,才可以消融主客之间的界限,达到对现实 的更好的理解。按照奥尔森的说法,诗人将“气息”灌注入诗中,便可以“谦卑地”、 “顺从地”安居于自身之内,在开放的放射诗场上,居处于形形色色的能量和力之间, 自然地参与到这些能量和力的传递过程中。
二、放射诗的形式
按照放射诗自身的规定性,诗是一种“开放的”、在“场上构成的”形式,那么,这 样的诗就必然要摈弃以完整的行、节和一定的韵律为基本形式的传统结构,而模拟一种 物理学上“场”的散射的、开放的形式,在结构、排列、印刷的形式上具有多样性和不 确定性。这种诗行没有确定的数,有的只有一行,有的长达五页;诗句也长短不一,有 的只有一个词,有的多达近二十个词;诗中有时有数字、各种标点符号,有时没有标点 符号;诗行的间隔大小不一,诗行排列参差不齐,甚至往往排成各种图形,如:《马克 西姆斯的诗》第三卷中有一首两行的诗:“我的海岸、我的声音、我的土地、我的地方 /后来、在中间、那以后”排成了一个斜十字[4](P438);再如:第三卷中有一首诗的部 分排成了一个“心”形的一部分[4](P498);另一首纪念诗人故去的父亲的诗则排成了 一个人字形[4](P499);还有的诗中插着空白页[4](P288、349、350)。此外,诗中断裂 的、不完整的句子俯拾即是。
从语言的角度说,诗歌既然是一个“开放的”场,那么,组成诗歌的每一个词和符号 便是场上的基本粒子,处在永远运动的开放状态中。所以,奥尔森诗作中常出现不完整 的句子,常插入即兴的、突发奇想的辞藻和短语,诗行呈现出高度活跃和跳动的形态。 再者,后现代主义诗学认为,语言不再向浪漫主义诗歌和现代主义诗歌中那样,仅仅是 某种话语的表述,而是一种行动,或者一种偶发的事件。换句话说,这样的诗歌语言不 再指向一个确定的意义,不再具有终极的目标,而是永远处于从一个能指向另一个能指 的滑动过程之中,与内在的生命律动相应和。例如,在1957年写的一首小诗中,诗人那 些非逻辑的、跳跃的思绪清晰地体现在那些非线形的、不完全的句子中:
再见了红色的月亮
你把那样的颜色沉落在
卡特的西天我应该永远
47年后的这个月
一个星期一的早上9点
你落了我起来了我希望
一个自由的事物可能
你不是你出卖的那种悲伤的货色
播种我在升起的时候
母亲离开了我
主啊咒你主啊咒我我
对你的误解
我可以死了现在我刚刚开始生活
(月落,格罗斯特,1957年12月1日,凌晨1:58)
这诗没有标点。片断的、不连贯的、不完全的口语短语式句子在互动中向外放射着, 诗人的联想从红色的落月跳跃到对母亲的想念;从1957年的冬夜凌晨跳跃到47年后一个 冬日的早上9点;从你的悲伤跳跃到母亲的离去;从我的死跳跃到我的生。诗中充满了 不确定性和含混的多义性。诗中的“你”是指“月亮”,还是别的什么人?你为什么悲 伤或者不悲伤?你出卖的是你的悲伤,还是你的什么?我对你产生了什么“误解”?你为 什么“播种我”?又为什么“在升起”的时候?是我升起还是月亮升起?我的“死”与我 的“生”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在我“刚刚开始生活”的时候我可以死了?这些问题都不可 能有明确的答案,这种开放的结构和场上的写作无疑给读者提供了巨大的想象和联想的 空间。
放射诗是一种能量转换和传递的诗,也是一种表达关系的诗。《马克西姆斯的诗》就 是诗人以马克西姆斯的名义向“你们”、“读者”和世界传递或者说放射能量的“高能 结构”。在这种能量传递的过程中,它也同时进行能量的交流和转换,处理内在现实和 外在现实的交叉关系。《马克西姆斯的诗》以“我,格罗斯特的马克西姆斯,致你们” 为首句的“书信体”开场,围绕马萨诸塞州的格罗斯特镇展示了各种关系的转换和交叉 ,包括马克西姆斯在诗的时空中自由来去时的声音;格罗斯特的人事;当地历史上曾在 马克西姆斯的时空场上出现和消失过的人们。这和物理学家们的表述是高度一致的,物 理学家们说,亚原子粒子不过是场与场之间各种关系的焦点而已。
三、放射诗中的时间、空间和自我意识
《马克西姆斯的诗》是奥尔森实践自己“放射诗”论的典型作品,诗人试图在300多首 诗的宏篇巨制中讲述美国的历史,并以美国为缩影,折射西方数千年的文明进程。诗人 最初为这一作品设计的题目是《西方》,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诗人意欲在历史的时空中 上下求索的伟大抱负。在《马克西姆斯》的诗中,诗人从量子力学和放射诗的理论出发 ,探讨了时间、空间和自我意识在不同的“量子场”上的交汇和相互作用,在这样的“ 量子场”上,意义只有通过理解复杂、多变的种种关系才能界定。诗人把握了这一新的 力学理论,然后试图用这一理论来构筑他的诗的宇宙。在他的诗歌中,宇宙围绕着他的 故乡格罗斯特扭结成了一条没有开端和终端的带子,把诗的幻想和科学的理论结合了起 来。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诗也是一种解释的艺术。下面以其中的三首诗为例,来说明 这种体现在放射诗中的时间、空间和自我意识。
《第十五封信》[4](P71-75)从量子力学的角度来看待时间。
就传统的观点看,历史的时间是一种线形时间,这种时间表现了一种连续性和因果关 系。但从现代物理学的立场看,这种连续性就是一种支离破碎的连续性,时间绵延中的 各个部分也并没有什么“因果”关系。或者说,从总体上看,时间“过去”和时间“现 在”乃至时间“将来”只是一个无限绵延的“场”;而从部分上看,具体的时间或时段 则有如量子场上的量子般缺乏明确的边界和位置,永远处在一种相互变动的联系中。
这封“信”的副标题为:马克西姆斯致格罗斯特,暗示作为诗人代言人的马克西姆斯 要讲述的是与诗人熟悉的格罗斯特相关的历史和现在。“信”以对当地历史上一次海上 事故的回忆开场。言说者首先纠正了一些不正确的历史记录,说那次出事的不是“埃皮 ·索耶”号船,而是“普特南”号船。出事的时间也不是圣诞节的早晨,而是圣诞节的 晚上,天黑以后。诗人接着从那次航行中的“我们”、马克西姆斯本人、“儿子”、“ 水手”、“父亲”等不同角度讲述了普特南号历险的“真相”。按照“我们”的叙述, 那晚“强劲的东北飓风,夹着雪”,把这艘船吹出了海湾,“我们”大家都相信看到了 船上那位著名的航海家鲍迪奇,那飓风“直到23号才停息”。接下来是马克西姆斯的叙 述:25号那天大雾弥漫,鲍迪奇和他的普特南号必须同浓雾较量,风仍然是东北风,但 没说有雪,下午4时天放晴了一小会儿,鲍迪奇能够看到“东点”,傍晚7点他回到“萨 勒姆”抛锚。这就是说,是格罗斯特的信号灯火引导“普特南”号回到港口的,而不是 “东点”的灯火,因为当时东点并没有灯塔,直到1831年之后,东点的贝克岛上才建立 了灯塔。据“我们”说,这故事是“他(鲍迪奇)的儿子”讲述的,而那儿子好象又是在 35年后听一位曾和他父亲同船航行到苏门答腊等地的水手讲的。马克西姆斯说,显然那 水手比他父亲大20岁,他说,当船回港,船主等突然看到活着的鲍迪奇时是何等惊讶, 他们起初无论如何也难于相信,普特南号居然能在那样的风暴中安然无恙。他说这故事 时已经85岁了。这种从不同角度叙述的时间显然产生了矛盾。因为历史上的鲍迪奇生于 1773年,死于1838年,享年65岁,可按照这里的叙述,1831年之前发生这一事故时,鲍 迪奇已经是65岁了。这就和历史的记录不相吻合。马克西姆斯说,“历史是时间的记忆 ”,而记忆(从不同的角度对一次海上事故的记忆)是滑动的,不确定的,因而时间也是 滑动的,不确定的。《第十五封信》开头这一关于记忆和时间滑动性与不确定性的描述 正是《马克西姆斯的诗》的主题之一。在这首诗中,马克西姆斯所关注的不是戏剧化地 出现在一个时间场中,而是交织成一个时间的场。普特南号的历险不可能是时空中单一 的线索,也不可能缩减为一个“发生”的“事件”,这种时空交叉与多种叙述角度的手 法颇似康拉德在《黑暗的中心》和福克纳在《喧哗与骚动》中采用的手法,对于这类作 家和诗人来说,所谓“事物的核心”和确定性是不存在的。
爱因斯坦对能量的场所作的解释是:我们感觉到的物质不是别的,只是能量在一个非 常小的区域的高度集中。因此,我们可以把物质看作是由空间的若干区域构成的,在这 些区域,场极端强。在新物理学中,不可能既有场又有物质,因为只有场才是唯一的真 实。对诗人奥尔森来说,爱因斯坦的这一理论表示了超越物理学之外的更多含义。场不 仅是一个后现代诗学的隐喻,而且是一个可以广泛运用于人类社会的概念。奥尔森敏锐 地感觉到,人的意识也是一个这样的场,在这一场上,从根本上说,不存在什么确定的 事物,任何发生都处在事物之间,这就是后现代的真实。
接下来的部分突然从开篇对普特南号遇险的历史叙述转到了当代的一场对话上来。另 一位当代诗人保尔·布莱克波恩指责奥尔森总是兜圈子,语焉不详,因而“歪曲”了诗 歌:
他说,“你总是围着题材绕来绕去。”我说,“我不明白那是题材。”
他说,“你歪曲”,我说,“不错。”他说了些别的事。我再没说什么。
随后,诗歌从现在又跳回到历史:17世纪英格兰探险家约翰·史密斯曾是首先航行到 北美大陆的人,他测量了切萨皮克湾,开创了弗吉尼亚詹姆斯敦的第一个永久性英格兰 移民区。可是,北美的香客们却拒绝了他充当航海家的请求,而把这一任务委派给了16 20年乘“五月花”号来美的英格兰殖民地军事领导者斯坦迪什。诗人穿插引述了史密斯 的题为《大海的标志》的诗歌:
海浪汹涌,别靠近,
危险即将来临;
倘若我不曾遭灭顶之灾
你不曾目睹那场景:
我就躺在这岩石上
做大众的标志
被同一个大浪打落,
让人们得救唯我毁灭。
冬天寒冷,夏天炎热
交替着冲刷
我青肿的两肋,那悔恨
因它过分真实
再不会有轻松的时刻
但我何必绝望
既然有公正的承诺
总有那死亡的一日
然后,诗人从历史突然又跳回到当代,用史密斯书题中的“广告”一词把历史切换到 现在,用极为平静的语调描述了美国当代文化中信息和物质膨胀的虚假现实:
哦,共和国,哦
讲述一个幻象,最好的
是肥皂剧。真正的游吟诗人们
来自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动听的歌
是由可口可乐公司不间断地唱着的可口可乐之歌
在诗人心理的场上,历史的时间决不是线形的,时间的顺序是虚假的,历史上相隔辽 远的时代看似毫无瓜葛,但却存在着某种神秘、微妙的对应关系,于是19世纪初期格罗 斯特港湾普特南号的遇险与当代诗坛的有关论争对应起来;17世纪的探险家史密斯与当 代诗人的代表马克西姆斯发生了能量的转换,史密斯的歌也正是马克西姆斯的歌,他歌 颂的理想也成了马克西姆斯(诗人)的理想;史密斯书中的“广告”转换成了当代美国现 实的阴暗景象:广告漫天飞,肥皂剧无处不在,人欲横流,物质膨胀,精神泯灭。然而 ,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诗人应该有所作为。马克西姆斯在驳斥别人对他的指责时, 坚持说他写的是“狂想曲……”,清楚地点明了诗人对现实清醒的认识,对自己所担负 的责任的承诺。rhapsodia(狂想曲)来自古希腊语中的rhaptein和aidein,rhaptein的 意思是“用针缝”,而aidein的意思是“歌唱”。因此,奥尔森说,“诗人应该有一份 工作”,这工作便是将人生“场”上杂乱无章,如量子般变动不居的零碎事件“缝”起 来,同时,用真诚和热情在苦痛的现实中“歌唱”理想。
《透过拉科萨·胡安的眼睛初次搜寻》[4](P81-85)从量子力学的角度看待空间。
拉科萨(1460-1510)是西班牙航海家、地理学家,1492年曾随哥伦布远航,是当时哥伦 布率领的三艘船之一的“圣玛利亚”号的船长,应该说他也是北美“新大陆”的发现者 之一。他擅长于绘制航海图,是哥伦布航海事业中须臾不能分离的助手和伙伴。但更为 重要的是,他绘制了当时的“世界地图”。这一包括新老大陆的世界图今天看来当然极 不准确,但在当时却具有重大意义和影响。在诗人看来,他的这张图是无与伦比的:
……在拉科萨之前,没有人
一幅世界地图
人们今天记得他,与其说是因为他也发现了新大陆,莫如说是因为他绘制了这张世界 地图。诗人的代言人马克西姆斯正是要透过他观察世界的眼睛来观察世界。
马克西姆斯透过拉科萨的眼睛看到了什么呢?他既看到了一个完整的世界,也看到了一 个支离破碎的世界。按照爱因斯坦之后的空间观,宇宙是一个绵延的、弯曲的、开放的 整体,传统的那种扁平、均衡的宇宙已经不复存在。马克西姆斯看到:在拉科萨的世界 地图上,无论是英国的布利斯托尔、法国的圣马洛,抑或法西之间的比斯开湾、新大陆 的格罗斯特,都在拉科萨的地理空间中,它们似乎构成了一个绵延的整体,但同时又是 没有确定的相互关联的,尽管那些地方的渔民在谈论大海、潮汐,我们仍然看不到任何 确定的内在联系。随后在诗的第二和第三部分谈到的其他地方,大的如欧洲、大西洋、 新大陆,小的如安恩角、塞布尔角、安妮斯奎运河等也都既无语义上的联系,也无暗示 和潜在的瓜葛。这些不同的地域和地点仿佛量子空间中的量子本身,其位置和速度是相 对不确定的。例如:
人们,我的城市,我的两个城市
在谈论,曾经谈论加迪斯,谈论卡什的
“人们”,哪里的人们?“城市”,哪个城市?“两个城市”,哪两个城市?在“谈论卡 什的”什么呢?一切都是朦胧的,不明确的,这种不明确还表现在句子形式上的不完整 和常常没有标点上,例如这里的“谈论卡什的”(talk of Cash's)就是不完全句。再如 ,在述及1480年布利斯托尔的劳埃德横渡大西洋的航行,九周后被风暴吹了回去时,有 这样的句子:
没有蛆。风暴(No worms.Storms)
女士们和(Ladies &)
到了底部,(to the bottom of the,)
丈夫们,和妻子们,(husbands,& Wives,)
小孩子们失去了他们的(little children lost their)
这种句子像它们所代表的空间那样,是开放的,正在变化中的,永远在表示一种过程 。这也可以从诗人多次使用的“漂浮”(floating)一词看出,在诗的开头,诗人说:“ 一个漂浮的岛屿”,在诗将要结束时,诗人又说:“这些花束……随水漂走”。也许在 总体上,我们可以感到,诗人想要说的是,在发现美洲甚至建设西方文明的过程中,一 代又一代人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和生命,但就具体而言,这里所说的“损失”显然是不清 晰的。
另一方面,量子空间的量子相互间又不是毫无关系的,实质上它们始终处在某种关联 中,只不过这种关联是不确定的,不稳定的,没有清晰的逻辑线索可寻。从全诗来看, 上面引文中的“没有蛆”,把1480年劳埃德的探险,和1492年拉科萨的探险联系了起来 ,因为12年后的那次探险由于蛆蛀坏了船体而带来了灾难:
是1492:把船体钻得满身是洞
在一次航行中(“穿了洞被船蛆蛀的孔像一只蜂窝,
结果,造成了“珍珠”、“印度”、“丈夫”、“妻子”、“小孩”的丧失,造成了4 ,670名渔民的死亡。拉科萨世界图的空间是所有人(人类)共有的空间,在这一神秘的 空间中发生着无以数计的死亡,但“友爱”的纽带也许能把死者与生者联系起来,于是 ,那些年年都要抛进海中“随水漂走”的一束束“鲜花”,在死生的两个空间场上架起 了桥梁:
……每个夏季,在丰满的八月,他们把鲜花抛进激流中,顺着河道,到达港口的入海口 ……
你可以看着它们漂流入大西洋
虽然拉科萨的空间是这首诗的主旨,但空间中毕竟不能没有时间和人,于是我们看到 ,在1492年拉科萨随哥伦布发现北美,发现格罗斯特之前之后都有多次海上探险的历史 与拉科萨的空间相互交织;此外,拉科萨的空间毕竟是由马克西姆斯来观察的,马克西 姆斯曾说,“我正在制造一张世界地图,这图包含了我的存在”[4](P201)。在透过拉 科萨的空间“搜寻”时,马克西姆斯自己也变成了一个“场”,一个在拉科萨“大场” 上的“小场”,所不同的是,拉科萨的“场”是一个空间与时间或者说历史叠合的场, 而马克西姆斯的“场”却是一个心理的场。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说,再大的物理场也将 包含在人的心理场中,反过来说,每一个心理场又不能不被包括在外在的、更大的物理 场中,这样看来,不仅“小”、“大”之间的差别消失了,而空间、时间、心理等不同 场的界限也模糊了。换句话讲,在一定程度上,拉科萨的场既是空间的场,又是时间的 场,还是心理的场。
如果说,《第十五封信》是以时间的场为主旨,辅以空间的场、心理的场,而《透过 拉科萨的眼睛初次搜寻》是以空间的场为主旨,辅以时间的场、心理的场的话,那么, 《扭曲》[4](P86-90)就是以心理的场为主旨,辅以时间的场和空间的场。
《扭曲》一开始,《拉科萨》中暴风雨袭击的海岸就转换成了“我(马克西姆斯)的内 陆的河流”,马克西姆斯(诗人)要从街道尽头的“路”到派克斯顿去“寻找五月的鲜花 ”,或者“顺着去霍尔登的老路,追寻英国的胡桃”。这个“内陆的”场正是马克西姆 斯心理的场,时间和空间的场已经消融在马克西姆斯的心理场中了。读者不难发现,在 《扭曲》中处处流淌着“我”:“我回家”,“我看到了大海”,“我拾阶而上”,“ 我在港口内划船”,“我为他种花”,“整个河道/成了我姑母凡德拉给我的/纸扎的村 子,她每个圣诞/都给我/这样的玩具”,“当我醒来/在我走向的玩具房子里,那景色/ 在我的窗外/给我送来清晨/阳光里的白色”……全诗128行,仅作主格的“我”就有20 个之多,如果再加上作宾格和属格的“我”,“我”就更多了,这种情形和《拉科萨》 中没有一个“我”以及《第十五封信》中少量的“我”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在马克西姆斯的这个心理场上,许多人和事都是面目朦胧,位置不定的“粒子”,那 斜着剪裁法国式裙子的“她”是“我”的妻子吗?“和我似乎是唯一的俩人”的那个“ 他”是谁?那些要离开我父亲和我的“大人物”又是什么人?下雨的那天,我们到了,“ 我们”是谁?在“她”离开我之后,“她”留了下来,这两个“她”是哪两个人?我的妻 子?施瓦茨的岳母?我的姑母(姨母)凡德拉?……这些人事的粒子如同《第十五封信》中 那些时间的粒子和《拉科萨》中那些空间的粒子一样,既无法确定其位置,也看不清它 们的面目。但是它们之间又有着某种不确定的相互关系。
尽管为发现新大陆,建设新大陆,许多水手,许多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尽管洪水仍 旧“撕裂了第三大道的高架铁路”,但是马克西姆斯的轨道依然耸立着,那就是他心中 “希望的田野”,这田野上应该有鲜花,应该有生命。诗篇开宗明义地说,马克西姆斯 在“寻找五月的鲜花”,他的妻子给他生了“婴儿”,他要给这孩子“种花”,正是这 种对生命的渴望和对理想的追求,使他心中荡起了“春潮”,坚定了他继续在自己的轨 道上“开车”的信念。也许,正是这些“鲜花”、“春潮”和“生命”,把他心理场上 那些散乱、模糊的人事的微粒联系了起来。
在这首诗中,虽然时空的场消融在马克西姆斯的心理场上,但时空的场并没有彻底消 失,而是隐含在了其中。从爱因斯坦之后的空间观看,空间、时间、心理不过是同一秩 序的不同表达而已。按照量子力学的理论,时间、空间、心理尽管是不同的量,但它们 都是在一个绵延的宇宙中相互关联的量。在这样的宇宙中,时间场、空间场和心理场都 是弯曲的、绵延的、相互交织的、相互叠合的。显而易见,这首诗中的马克西姆斯就是 前一首诗中“拉科萨”的回声,三百年前,拉科萨曾经看到的“五月花”成了今天马克 西姆斯的追求;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成了一条蜿蜒的历史长河,这长河既存在于时间场 上,也存在于空间场上,还存在于人的心理场上:
我在单轨上
开我的车,我被吸引住了
——并非许多夜晚之前——
被那河的景象
就在桥那边
它在那里出入
尚未发现的国家,
“并非许多夜晚之前”把马克西姆斯童年的回忆和成熟之后的回忆连在了一起;而这 一历史的时间线索又突然化作了在那里“出入”的空间形象;马克西姆斯“认出了/尚 未发现的国家”,这国家自然存在于三百年前拉科萨等人发现的空间中,于是,拉科萨 的空间和马克西姆斯的空间在这里互为表里,交汇在马克西姆斯的心理场上。事实上, 按照现代物理学的观念,时、空、心理的场从来是交融在一起的,在一个可以从起点“ 扭曲”地回到起点的绵延的宇宙中,上下左右、前后内外,此刻彼时的区分是没有意义 的,也许有意义的只是对某种“真实”的追求,这样,我们对已经死去的人、对拉科萨 欠缺的“历史真实”,就化作了马克西姆斯个人回忆中的某种“真实”和对鲜花的记忆 :
这极小的顶端
在这白昼的阳光中,
在这种真实性中
那里,它们中的几条河那道路
这里,一棵黑刺莓在怒放
从《放射诗》和《马克西姆斯的诗》发表至今,近半个世纪过去了。但是,奥尔森的 诗论和诗作仍然没有失去它们在西方后现代文学中的重要地位。奥尔森的复杂性和丰富 性仍然期待着学者们进一步的开掘。这种情形在西方学界如此,在中国学界则更是如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