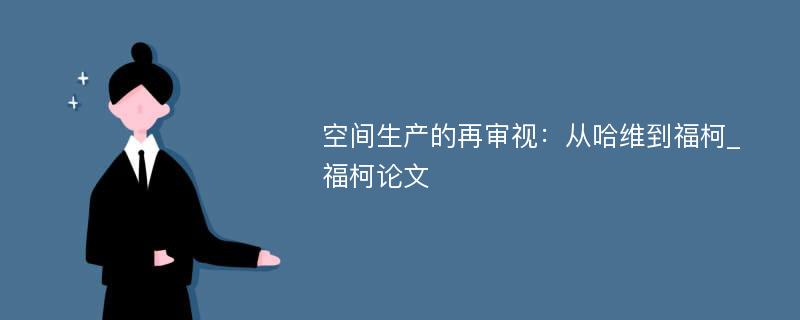
空间生产再考:从哈维到福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哈维论文,空间论文,到福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690(2013)11-1293-09
修订日期:2013-03-25
空间生产已经成为目前中西方地理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国内地理学界也已经开始对这一话题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1,2]。这其中不仅包括对空间概念的重新理解[3-7]、对相关理论的深化总结[8-12],也包括对重要著作及作者的介绍[13-17]和初步的案例研究尝试[18-27]。但是,由于这一理论源于哲学层面的思考,因而虽然经由哈维等地理学家的拓展和充实,在分析运用上仍然较难操作。同时,目前对该理论的理解和应用还存在2种疑惑或误解。一方面,对空间生产有过于简单化理解的倾向——似乎空间生产就是新的实体空间的形成和发展,如新城建设、城市美化、旧城更新,对表征的空间、空间实践和空间过程背后深刻的社会(指广义上的社会,包括政治经济)力量涉及甚少,从而失去了其理论原初的魅力所在——联系性和社会性才是其相对先前的康德主义的空间观和计量革命范式下的系统观的优越性所在。另一方面,对空间生产还有过于宽泛化理解的倾向——似乎空间生产作为一个概念的“箩筐”可以无所不包,看似新颖的“瓶子”里装的仍然是“形成模式”语境下的“老酒”,只是把原来作为背景的空间换成了作为对象的空间、将熟知的内容赋予了“玄化”的概念,从而丧失了该理论深刻的批判性反思和求实的辩证性分析。
因此,对空间生产的理论探讨仍有待进一步深入:一方面需要摒弃空间拜物教(spatial fetishism)的框架,另一方面应该去掉文字游戏(或虚构主义)的面纱。本文是校正上述2种偏差的初步尝试:一方面意在通过回归空间生产的经典文献(以Harvey的研究为主)而能够正本清源去伪存真,另一方面尝试通过整合哈维和福柯的2种不同的空间理论视角对之前的粗糙框架加以具化和修正。
文章的以下部分首先讨论上述分析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接下来通过对哈维著作的梳理探讨马克思主义关于空间生产的核心方法和视角,并简要评述其理论的局限和可供借鉴之处;继而分析福柯关于权力关系(power relations)的空间视角;最后,作者对二者的空间视角进行了总结,并基于中国的背景探讨其优缺点,从研究展望和学者责任的角度探讨在未来应用和扩展中值得注意的问题。
1 回归经典——从哈维到福柯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批判根植于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性中,无论是阶级分化、人的异化还是资本积累的断裂和可持续性的危机,都与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及其运行方式密切相关。在这一框架下,国家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superstructure)是“统治阶级”(ruling class)表达其利益并控制和剥削底层民众的媒介[28]。但是,一方面在中国“强国家,弱社会”的背景下,“看得见的手”的干预程度远远强于资本主义社会,因而有必要在自由主义视角和市场经济框架之外重新审视中国的“空间生产”过程;在此意义上,福柯关于“权力关系”的研究值得借鉴。另一方面,尽管不少海外学者将中国的体制界定为各种各样的资本主义——如“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中央控制的资本主义”(centrally managed capitalism)、“极权资本主义”(authoritarian capitalism)甚至“封建资本主义”(feudal capitalism),但是鲜有研究对“中国特色”的“资本”或是“阶级”进行了清晰界定,使得大部分研究主要在实证西方的概念而难以触及背后的深层机制。例如:资本的空间修复产生于资本主义内在的资本积累危机,那么中国有没有这种危机?中国的空间是否仍遵循创造性破坏的逻辑还是有其自身的特征(如对赶超的热情亦或“锦标赛”体制所致)?再如中国城市空间生产由资本扩张还是阶级更替所推动?若是阶级更替推动,又是哪些“阶级”?若要回答这些问题,就有必要回归到最初的经典文献——这一方面可以跳出所谓的“体制”或“特色”之争而关注其基本事实和具体过程,另一方面还可能通过理论的批判与重构完成理论“越界”(transgression)[29],为世界地理学的发展做出中国应有的贡献。
本文主要选取哈维和福柯的著作进行深入的分析,这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考量。首先,两者都是著作等身、涉足广泛的学者,且都对地理/空间有深厚的兴趣——尽管哈维在不同的阶段对空间存在不同的理解,但是空间始终是其研究的“关键词”[30];福柯同样在接受《Hérodote》杂志编辑的访谈中坦言对空间问题的关注[31],地理成为福柯隐而不宣的(implicit)兴趣[32],空间性也成为贯穿于福柯研究始终的擦不去的(indelible)主线[33]。其次,尽管两者的视角和观点有很大不同,但是二者的密切联系和哲学导向为彼此的对比和整合提供了可能。虽然福柯曾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学说[34],但正如《现代哲学》2007年第4期的3篇文章所指出,福柯在发展其学说和方法时以不带引号的形式大量借鉴了马克思的理论、视角和案例——他引用马克思的概念、句子和文章像物理学家援引牛顿或爱因斯坦的理论那样自然[35-37],因而与当代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领袖人物——哈维之间存在不少对话的空间。同时,哈维对(后)现代的反思与福柯对现代性的诊断[38]、两者对马克思主义精神的解读(如福柯提出的实际上是“令人感动的背叛”的“忠诚”与哈维对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的强调相辅相成)[36]、对理性话语霸权的批判[39]、对人群划分[40]以及国家暴力的理解(如Smith等基于哈维的垄断阶级概念所提出的revanchism及“警察化”与福柯引入的Polizeiwissenschaft①有所对应)等方面也存在很多对应。最后,两者在研究思路和方法上存在很好的互补性。总体上,如果哈维所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主要关注资本积累和国家权力的目的性(why),福柯对规训(disciplinarity)和治理术②(governmentality)的分析则试图解释经济剥削(exploitation)和政治统治(domination)的方式(how)[34,41];如果说哈维采取的是“重读经典”③的研究思路,福柯则主要采取“解剖麻雀”式的微观研究方法。因此,本文认为,构建马克思主义和福柯主义间的对话不仅必要,而且能够为中国学者的理论研究提供2个典范和重要方向。
2 哈维的空间生产理论概览
哈维通过重读马克思的经典著作并从列斐伏尔那里汲取灵感,逐渐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空间生产的理论框架。对哈维所著述的主要的书目,叶超和杨宇振等都有过概要的梳理[30,42]。纵观哈维的著作,空间生产和城市过程几乎贯穿于其分析的始终,而不平衡的发展趋势和空间景观则是其理论背后的主线。承接列斐伏尔对“空间本身的生产”和空间的三元辩证法的论述以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总体性内在的不平衡发展的剖析,哈维及其学生Smith深入剖析了不平衡发展的空间面向[43,44],将不平衡不仅看作资本主义积累过程所必然导致的地理景观、也看作资本过度积累导致的经济危机的修复途径,不仅看作资本主义的地理前提、还是历史的后果,并从自然的生产的不平衡转向(人造)空间生产的不平衡[11]。这些研究不仅细化了列斐伏尔对空间粉碎化(pulverization)和空间的爆炸(explosion of spaces)的论述[45],更将列斐伏尔对空间的三元划分进行了扩展而形成了“绝对空间-相对空间-关系空间”和“物质空间-空间表征-表征的空间”的空间性(spatialities)矩阵[43],将马克思理论系统地整合到多样化的空间生产中。而对“城市本身的理论”的关注则构成了哈维理论的另一个聚焦点[24,13]。哈维试图从资本的积累出发分析都市结构的过程及其内涵,以及城市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变迁的作用[46]。总体上,哈维尤其关注城市化与资本循环和阶级更替的互动过程,这也是目前很多对中国城市化问题研究的主要入手点;相应地,资本、阶级和上层建筑(国家和表征)则构成了哈维的空间生产理论的3个要素。
2.1 哈维对资本的解读
资本是马克思理论中的重要研究对象,也位于马克思1857年所列出的6部计划撰写的巨著(magnum opus)之首(其余的是土地所有权,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及其危机)。与马克思一脉相承,对资本的分析也处在哈维有关空间生产理论的核心。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集大成之作和哈维最得意的作品[42],《资本的限制》代表了哈维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拓展和空间生产理论的整合[47]。在该书出版后,《对极》(Antipode)杂志曾专门设立一期对其加以讨论[48-50],足见其影响之深远。哈维在该书1999年Verso版的序言中说,此书试图以一种全盘的(holistic)视角“在马克思的整体讨论框架下整合资本积累的金融(时间的)和地理(可以称之为全球的和空间的)方面”[49],催生了他后期的很多重要研究。哈维不仅在此书中对马克思的方法提供了一份绝佳概要,更进行了全面的具体化和空间化——资本循环(circuit)的模型和空间修复(fix)的概念也在这里被深化和发展④。在随后的著作中,哈维始终把“资本的逻辑”[51]及其背后的矛盾作为理论的核心,并在对城市化过程和城市管治方式转变的分析中[46,52,53]、对全球劳动分工和生产方式重构的解读中[54]以及对资本主义危机和《资本论》的解读中[55,56]不断强调和细化。可以说,对资本积累过程及其内在矛盾的关注是哈维对空间生产和城市过程研究中的一条重要主线。中国学者在对国内土地市场和城市过程的研究中也已经对哈维的资本循环模型开始进行探索性应用[57-60]。
2.2 哈维对阶级的分析
实际上,阶级与资本并非两个可以分得很清楚的概念。一方面,随着劳动力的商品化,劳动力已成为资本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资本作为抽象的“价值”也体现了一种社会阶层关系。因此,阶级分析是哈维利用马克思主义分析空间生产和城市过程的另一条主线——“财富的过度积累和赤贫阶层(rabble of paupers)的形成”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两大矛盾[51]。从哈维的著作中大体能够发现其对阶级(斗争)的持续关注。作为哈维马克思主义转向后的第一部著作和地理学“从空间科学转向历史唯物主义的标志”,《社会正义与城市》[61]开启了地理学对社会关系和阶级结构的重视和对历史地理辩证法的应用。哈维不仅在随后的著作中对此进行了扩展[62-63],还通过对垄断地租的分析[64,65]实现了对城市权利的审视[66]和新自由主义本质的探索[67-70]——前者实际上成为其学生Neil Smith后来从地租缺口(rent gap)角度研究阶层空间重构(尤其是绅士化)中的城市政治的前导[71];后者则通过将新自由主义的核心界定为“阶级回复”(class restoration)拓展延伸了阶级的解释力。因此,阶级分析是哈维对空间生产和城市过程研究中的另一重要视角。国内目前对新自由主义及绅士化的很多研究也基本沿袭了对阶层演替和空间重构的关注[72-74]。
2.3 哈维对上层建筑的分析
上层建筑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上的社会意识形态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法律制度和设施等的总和,这里主要论及国家(state)和表征(representation)两方面。正如杨宇振所总结,权力的合法性是现代社会中除资本的流动和社会结构的瓦解外的另一根本矛盾[24]。哈维早在1978年的《对极》上就对马克思的国家理论进行了系统梳理,归纳了马克思关于“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工具”的论述[75];他在2003年对“新帝国主义”的分析可以看作是他对国家理论的扩展[51](尤其是其中关于权力的“领土逻辑”的论述);他对管治与国家重组的讨论同样扩展了空间生产理论在国家分析中的应用[如46]。另一方面是对表征的分析。哈维对“想象”和“表述”同样有着浓厚的兴趣[24],因为表述不仅是权力控制的重要内容和各方的争夺领域,还不断反作用于资本、阶级和物质性。哈维在对后现代的时空体验[76]、城市体验[77]、康德及海德格尔的美学判断[78]等话题的研究中同样扩展了表征性对城市过程乃至空间生产的重要意义。
3 福柯的权力-空间视角
福柯对权力关系的分析为空间生产提供了另一重要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福柯是与列斐伏尔比翼的、前瞻性地指出20世纪人文社会科学的空间转向的法国思想家[4,79]。他对地理学影响至深的一篇文章当属“异托邦”[80],在此文中他极其雄辩地提出20世纪或许应该是“空间的纪元”。然而,他对西方地理学空间理论的影响绝不仅限于此。对西方的当代地理学(尤其是政治地理和人口地理)具有系统影响的是其有关空间权力的批判思想[80]——围绕现代空间中的权力-知识与身体和主体性的关系[4],福柯为空间研究提供了更加微观和技术性的视角以及大量鲜活丰富的案例。总体上,可以将福柯的空间视角分为以下3个部分——工具性空间生产、生产性空间的形成和空间合理性的争夺。
3.1 工具性空间生产
承接尼采的系谱学方法,福柯认为权力关系(而非权力意志)是推动历史和转化(客体化)主体的宰制性力量[81],因而权力也就安排和创造了空间[4]——空间既是权力运作所建构的工具,也是其运作得以可能的条件[4]。这种工具性空间以边沁的“全景敞视”监狱为代表,并与麻风病的大禁闭、瘟疫的隔离和监狱的规训等空间实践(practice,exercise)一起形成了一系列的统治技术(governmental technique)。总体上,福柯归纳了3种主要的权力关系形式——君权(sovereignty)、规训(discipline)和治理或安全(security)[82],每种权力关系背后都有服务于统治技术的特定工具性空间。正如福柯所说,“空间在任何公共生活形式(form of communal life)中都是基础性的;在任何权力实践(exercise)中都是基础性的”[83]。在君权中,领土同时作为权力关系的对象和媒介而发挥着核心作用[84],其主要的空间形式是封闭(如通过边界的确立)和君王特权化的空间可见性(visibility)。在规训中空间主要被用来规范身体;各种空间设计和规范手段被用来强化权力的运作——如空间分割(partition)、层级监视(surveillance)、规范化裁决以及检查/报告[85],进而形成了一种复杂的关系权力的物理学或政治解剖学;“温驯-生产-利润”原则逐渐取代了君权的“征用-暴力”原则,规范化(normalization)力量取代了暴力血腥的恐吓,可见性的不对称关系也被倒转过来——规训中权力所追求的是对个体化的监视对象(而非君王)持续的可见性和监视主体(如狱警)的不可见性。其中,福柯对于边沁的全景敞视模型的概括和推广最为清晰和经典,也开始被用于国内对摊贩的规训的研究[86]。在治理中,人口逐渐取代君权中的领土和规训中个体化的身体而成为生命政治(biopouvoir)的最终目标,效率和生产力则开始成为关注的重点;在这一背景下,普查、地监视(geosurveillance)、统计、规划和计算(calculation)[87-91]等都开始进入空间调控(regulation)和空间政策的视野。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这3种权力关系并非演替性的(successive)[82],而是构成了权力的空间技术“三角”;另一方面,福柯对于地理和空间的康德式认知框架仍然基于牛顿的绝对时空观,因而正如哈维的批判,这种分析仍然相对侧重实体的空间而显得十分呆板(stasis、rigidity)[92]。
3.2 生产性空间的形成
尽管福柯对规训的分析把权力机制及其所主导的工具性空间作为一种可以自动运作的设计,其理论探讨始终难以跳过权力的目的性问题;这集中体现在对于现代社会的宏观层面(如国家机器和社会组织)的权力分析上[36-38]。面对这一问题,福柯再次转向马克思,提出国家权力从战争—外交转化到公共管理进而到自我规训[93,94]、以及统治技术从司法到规训到生命政治(biopolitics)的发展。在这种逻辑背后,权力实践不只是压迫性的更是生产性的——国家在其中追求一种无上权力(superpower)与过剩的生产之间的一种比例关系,从而形成了一种生产性的空间视角。福柯将注意力从领土转移到人口(population)时也把微观的管治技术扩展到宏观的政治经济政策,从而与哈维的阶级和资本视角相对应,赋予权力的空间设计和机构(Apparatus/Dispositif)以生产性功能。正如波兰尼对城市形成(作为市场的衍生物和保护者)及边沁的圆形监狱功能的解读(通过大规模将失业商业化来抹平商业周期)[95],福柯同样把权力和空间不断规劝和塑造符合一定社会规范的主体的过程归结为生产性逻辑:一方面,规训不会浪费在那些不会产生回报的人身上——如国家对待麻风病人和控制瘟疫会采取不同的空间政策(对没有生产力的实行禁闭,对可能受感染的人群进行区分和隔离)、军队不会对逃兵进行规训、学校也不对智障儿童进行指导;另一方面,很多传统的暴力和强权机构(如警察等)也开始积极地创造生产性条件——正如福柯所言,“城市化与警察化(公共管理)几乎是一件事”[82]。
3.3 空间合理性的争夺
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将关注重点放在资本逻辑下积累的内在矛盾和不对称性,福柯更强调各种实践(包括所谓的新自由主义)背后“无处不在”的权力逻辑。尽管很多解读认为福柯持一种悲观主义的权力观点,本文认为福柯也同时看到了背后的解放性力量——尽管福柯在对各种形式的权力关系的分析中始终强调权力的普遍性,他同样看到了权力背后的矛盾性和变化性力量——如他在后期的一篇回顾性文章——(The Subject and Power)中就把他毕生的研究目的归结为主体性的解放[96]。福柯对空间合理性的相关论述主要集中在对“异托邦”(heterotopias)及“外边思维”⑤的分析和在治理术中对合理性(rationality)的反思中,这实际上也部分地超出了哈维关于福柯对空间持工具性理解的批判[92]。一方面,福柯在回顾西方从中世纪的层级性的神圣(emplacement)空间到伽利略时代延展性的开放空间再到当代关系性的场所(site)空间的演进历程后指出,空间可以被划分为普遍性但是虚构的乌托邦和真实而差异化的异托邦——一种同时性、并置性地呈现各种异质因素的空间场所,进而提供了一种空间“不是什么”的研究视角[97]。这种差异化视角不仅渗透在其对权力化空间的分析中,也贯穿于早期的对《词与物》中目光交织的分析和“域外”思想中关于主体消失和从外部进入内里的空间化反思[98]。因此,纵然福柯的空间观点存在一定的“呆滞性”,他所采取的尼采式视角却赋予了其空间思想的生成论内核和谱系学的流变本质,能够反对目的论及本质论而提倡“差异”、反抗整体历史而提出(非线性的)“空间化的历史观”[98]。另一方面,福柯对空间的考察始终伴随着对知识霸权和合理性的拷问。在这一视角下,空间不仅是福柯的研究对象,更是分析的概念库(conceptual armoury)的一部分——各种知识(connaissance/pouvoir-savoir)和话语(discourse)都可置于这一空间中考察,形成“文学空间”、“诊所的医学空间”和“考古学空间”等空间形式[99];分类(包括学科划分)会涉及到对话语权力的运用口[98],空间化(spatializations)同时作为分析工具和目的成为权力实践的对象和斗争的场所[99]。为此,有必要“重获迷失和隐匿的知识”[100]并确定一种“正常和正当”的社会标准[101],探求空间、权力与知识的互动和结合[102,103]。这些努力促成了与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空间正义和表征遥相对应的、对空间性背后的“真理政治”的研究,从而将空间扩展到了空间性、将治理术的空间面向从实体空间扩展到了空间的因果关系(causal logics)。这其中既包括Elden对计算与空间合理性(rationality)关系的关注——如“state与statistics”、“reason、rationality、ratio”的对应[92],也包括Huxley对空间合理性的类型总结——几何性(dispositional)、健康性(generative)和精神/指引性(vitalist)[104]。
4 对比与讨论
4.1 两个视角的对比和关联
尽管本文将哈维和福柯作为2个不同学派的代表加以介绍和分析,但是两者对于空间生产的讨论存在诸多关联。首先,尽管哈维的视角更为宏观且更强调资本的力量,而福柯则较为微观且更强调权力的实践,但是两者都将当代归结为空间的时代并将经济(或资本)、人口(或阶级)以及表征(或知识)作为其空间思想的重要核心或线索。其次,不平衡性(或不对称性)都位于两者空间生产逻辑的核心——哈维强调空间修复和利润均等化之间、阶级分化与再生产的危机之间的内在矛盾,福柯则通过对区分(differentiation)、不对称的可见性等的分析强调权力无处不在的观点,两者都将不均衡归结为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深刻批判。再次,尽管哈维在马克思的暴力革命的基础上通过增加对过程和多元性的考虑诉诸一种“辩证乌托邦”,福柯则在尼采的基础上更侧重主体性的解放(他这方面与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归宿[105]有一定的同源性),但两者都对空间正义和人的异化有深切关怀——无论是对商品化的对抗还是对权力客体化(“人已死”)的消解。最后,两者对空间生产的讨论都有尺度内涵——尽管哈维的研究更侧重于城市而福柯则关注各种微观的权力过程,但是二者都有一种试图推及到更大尺度的理论诉求。
4.2 理论的扩展与应用
目前,国内地理学界已经开始了对空间生产的研究,并以借鉴哈维等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理论方法为主,而对其他重要的研究视角关注较少。本文认为,对福柯研究的引荐不仅有助于改善和拓展当前的研究——中国历史的深厚性、国家权力的主导性和城乡社会-空间的复杂性十分有利于引入福柯的权力关系视角,还能大大拓展甚至修正福柯的研究。其中,户口制度与福柯对区分、检查(包括收容)以及警察的讨论,城市规划及政治晋升与福柯研究中对地监视、统计和计算等的分析,单位制的空间及制度设计与福柯对生产性空间的探讨,网络时代的表达及口碑与福柯对知识和话语的解读等,都是值得探索的方向。同时,对哈维和福柯研究的整合也是未来值得深入的话题,这方面国内的哲学和社会学界已做出了初步探索——如复旦大学自1990年持续至今的一些引介[106-111],但是对福柯的空间、表达、警察甚至历史/系谱学的研究还有很大空间;同时,目前英语圈地理学界逐渐兴起的“福柯热”,伴随着新近对福柯在法兰西学院十余年讲座讲稿及大量访谈资料的翻译出版,使得福柯的学说在未来一段时间里能够“常读常新”,因而值得国内地理学者的持续关注。当然,笔者之前倡导的对空间正义[112,113]、在地化-去地化辩证法[18]、历史空间(如唐晓峰的王朝地理)的形成[114]及尺度[115]等话题的研究仍值得进一步关注,这些有希望成为加强国内研究的理论化和超越“呆板”或“玄化”倾向的切入点。从尺度(或测不准原理)的角度看,越确定的认识往往越呆板(精度与运动性的取舍),而越概括的东西则越不真实(粒度与范围的取舍);因此,我们没必要把地理学限制在“空间”这一有限的领域,也没必要做一堆没人看得懂的学术,这才是空间生产理论的活力所在。
4.3 中国地理学者的责任
福柯作为一个同性恋者和积极投身社会运动的学者,保持了对弱者的关注和对主流的拷问、对真理的探索和对自身理论的不断更新(其渊博的文献材料和不断变化的概念让人眼花缭乱)、对理性的自省和对主体的关照(care),其毕生的学术追求乃至传奇的人格魅力都值得我们学习。一方面,作为知识分子,地理学者有必要保持求真的底线。从屈原的“众人皆醉我独醒”到鲁迅(甚至仍然是笔名)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从“实”事求“是”到“晋升锦标赛”,讲真话和学术独立看似极其简单的事情目前仍然是一种奢侈。但是,只有追求真理的学术体系才有持久强大的话语权,这就是为何《史记》而不是王朝的“正史”能流传千古,又为何王阳明的“心学”能取得“诸子百家”后的一个新高度。另一方面,中国地理学有必要倡导一种持续的反身性批判。福柯把对启蒙后理性的批判和主体性的回归作为其摆脱结构压迫和权力主导的重要途径,这对于增强国内人文地理学人的问题意识[116]、激活人文地理学界的理论辩论和促进主体性的回归有所启发。一个能包容批判和讨论的人文地理学才有人文的活力,一个倡导主体性解放的民族才有凝聚力——正因如此,后现代主义的散漫背后才蕴含着如此巨大的能量,法国哲学才可以撼动英美学术体系的主导权,而倡导自由主义的美国才始终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最后,由于本文旨在归纳引荐2位学者的的思想脉络,因而其框架及观点无法过于详细,部分观点也只是初步的探索,有待未来进一步完善和深入。
①该词在英文上等同于“science of police”,在17、18世纪其意义更接近公共管理(参见钱翰、陈晓径2010年翻译的《安全、领土与人口》)。但是,作为与“外交-军事”体系(diplomatic-military system)并列的治理艺术和对“规训与惩罚”机制讨论的继续,可以认为其与“警察”具有密切的联系。
②法文为gouvernementalité,没有很恰当的中文对应,也译作“规治”、“统管理性”和“治理体”等。
③哈维几乎从1971年开始每年都教授《资本论》,其课程可以参见http://davidharvey.org/reading-capital/。
④资本的空间修复在1981年《对极》中的“空间修复:黑格尔、杜能与马克思”中明确提出;而资本的循环模型在1978年的《城市和地区研究国际杂志》中即已提出。
⑤法文为“Lapensée dudehors”,中文又译作“域外”。
标签:福柯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地理学论文; 地理论文; 哲学家论文; 自然科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