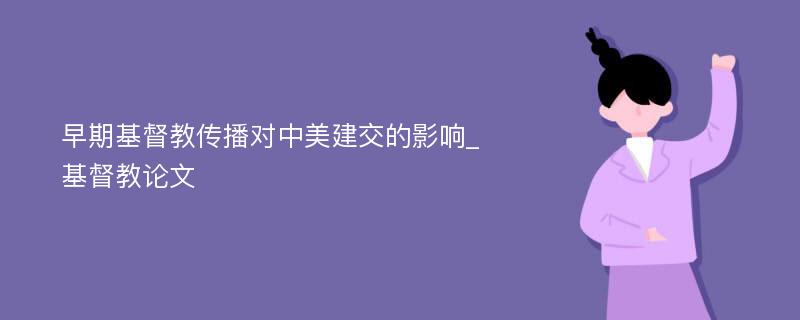
基督教传播对早期中美外交关系建立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督教论文,中美论文,外交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十九世纪初以来,基督教传播活动曾对中国社会许多方面产生过极其重要的影响。在众多的影响之中,基督教传播自身所需及其传播所引起的后果,都直接或间接影响过中美外交关系的建立。大凡两国外交关系的建立,都以双方互派外交大使为标志。中美外交关系建立伊始,曾经历过美国遣使来华修约,迫使中国打开外交门户,单方面接受美国外交使节;到中国承认中美外交现实,并遣使驻美这样两个阶段。中美互派使节在时间上前后相隔三十余年,而这一来一往,都与基督教在华传播活动关系至为密切。第一阶段中,以伯驾为代表的美国来华传教士,为打破清政府对基督教在华传播禁令,不仅积极说服美国政府开展对华外交,并亲自参与对华修约,甚至直接出任驻华外交官员,以谋取基督教在华传播之合法权利。第二阶段发展则得力于曾受教于早期教会学校的中国近代改良主义者容闳等人。他们以培养洋务运动急需的现代化人才为由,极力劝说清朝政府派教育使团赴美。又以其外交实践,最终促使清政府任命驻美外交公使,从而形成中美双边对等之外交关系。综观前后两段发展,前一阶段可谓得力于基督教传播之直接动因,后一阶段则为其传播所产生影响的间接效应。基督教在华传播对中美外交关系建立前后产生的如此影响,对于我们今天研究中美外交关系建立的起因,其意义之重要是不言而喻的。
一、美国传教士伯驾推动并参与美国对华建交的努力
最早来华传播基督教(新教)者, 为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 (Robert Morrison)。值得一提的是,马礼逊虽为英国教会所派, 但其来华传教的使命,却受到当时垄断中英海上交通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阻挠。原因是东印度公司不希望他们的对华贸易因基督教传教士来华宣教而受影响。因为当时的清政府严禁传教士来华传播基督教。为此,马礼逊只能取道美国,依靠美国国务卿麦迪逊的帮助,乘美国商船于1807年9月8日到达广州。麦迪逊还给当时在广州的美国领事卡林顿修书一封,嘱他热情接待马礼逊。马礼逊从美国官员所得帮助表明,美国政府从起初就极重视发展基督教在华传播事业。
美国政府给予马礼逊的支持,对美国教会派遣传教士来华传播基督教,产生了积极影响。为避免触犯清政府对基督教传播之禁令,美国基督教差会于1834年决定,派传教士医生伯驾(Peter Parker)前往中国行医传教。伯驾毕业于耶鲁大学,具有神学和医学学位。1834年6月1日,他在纽约布立克街一座长老会教堂,被正式宣布为来华传教士。在大会上,美国基督教差会咨询委员会代表卫斯诺(Wisner)博士告诫他,要把科学技术看作福音的婢女,医生的责任也决不能代替传教士的使命。伯驾则明确表示,他来华行医的最终目的是传扬基督教。并且宣布:“我可以用我一生之精力,来医治千百万中国人的肉体疾病,这也是我致力于解除肉体痛苦的愿望。然而,我们无法除掉这世上千年之后依然存在的病痛。我们的努力只有和拯救灵魂的事业联系起来,才能具有万世不易的重要性。我现在最大的容誉,就是我要作为耶稣基督的传教士前往中国。 ”(注:斯迪芬《彼得·伯驾的生活、 书信和日记》( George B.Stevens,"The Life,Letters and Journals of the Rev.and Hon.Peter Parker",Scholarly Resources Inc.:Wilmington,Delaware,1972),p.82)
伯驾于1834年10月来华后,在广州开办了中国第一家西式医院。利用行医之便,他广泛结识了很多中国政府官员,甚至包括钦差大臣林则徐。然而,伯驾深感开办医院终究不能改变清政府的禁教政策。于是,他转而寻求其它打开清政府对基督教传播紧闭大门的途径。当时在华的西方传教士,大多赞同用武力迫使清政府放弃闭关自守的政策。正如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在《中国丛报》上的这段言论:“他们(西方国家)不但可以,而且必须规劝她(中国);如果不能说服她,那么可能的话,就该迫使她接受一条这样的路线,这样将使他们的权利和她的义务更加一致。”(注:《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Dec.1834,Vol.Ⅲ.),p.364)但伯驾起初并不认为,西方国家的武力能征服中国这样一个庞大帝国。他倒是寄希望于,“西方国家通过与中国建立良好关系,为基督教在华传播创造有利条件。”(注:斯迪芬《彼得·伯驾》,p.127)鸦片战争爆发前,伯驾于1839年6月,曾两次会见林则徐的代表,希望通过他与中国官员的私交,来阻止中英之间的武装冲突。
鸦片战争爆发后,伯驾回美避乱。在此期间,伯驾利用各种机会向美国公众和教会介绍中国,以及基督教在华被禁的情况;并呼吁美国政府,为基督教传播事业,尽快建立与中国政府的外交关系。伯驾的报告引起了美国各大教会的兴趣,使他们考虑向中国派遣更多的传教士。为直接说服政府官员,伯驾于1841年1月18日离开家乡, 起程前往华盛顿。临行前他表示:“我把在华居住期间所了解的信息,通报给我们政府,目的是要他们此刻就采取某种行动,与中国政府建立友好关系;这种关系也许能调解中英冲突,因而拯救大批生灵。并能间接有利于福音事业在这个帝国的发展。”(注:斯迪芬《彼得·伯驾》,p.182—183。)
伯驾的华盛顿之行是他为了基督教传播事业,对美国政府发展对华外交关系一次最直接的推动。为引起政府重视,伯驾在华盛顿采取了一系列行动。 首先, 他前去面见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威伯斯特(DanielWebster),与他详细讨论建立对华外交关系的现实性和可能性; 其次,他根据威伯斯特要求,向美国政府提交了一份包含六个要点的报告,以说明美国政府建立对华外交关系的必要性;最后,他还拜会了1841年期间前后继任的三位美国总统:范·布伦(Martin Van Buren)、哈里逊(William H.Harrison)和泰勒(John Tyler),以及他们的国务卿。“他们都带着极大的兴趣关注着鸦片战争的进展,”(注:唐德刚《美国在华外交,1844—60 》(Te —Kong Tong ,"United
StatesDiplomacy in China,1844—60",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Seattle,1964),p.8.)并开始认真考虑伯驾的建议。
为说服美国政府与国会,伯驾在提交给国务院的报告中,分析了中国朝廷因宣布断绝与英国贸易而陷入的某种困境。并特别指出,这种困境将直接影响美国对华贸易。对此,他提请美国政府,“应考虑如何维持与保护每年一千二百万美元的对华贸易。”(注:斯迪芬《彼得·伯驾》,p.187。 )为打破因中英冲突而造成中国在对外关系上的僵持局面,他建议美国政府应抓住这一时机,派遣特使前往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以调解中英之间的冲突。考虑到中国道光皇帝年事已高,美国政府应选派一位熟悉公共事务的退休总统来担任特使。这样就容易取得中国皇帝的信任和尊重,也得以与中华帝国订立一项体面的条约来赢得和平。作为美国特使,伯驾推荐具有丰富外交活动经验的退休总统亚当斯(John Q.Adams)为最合适人选。
经过一年多酝酿,伯驾的建议终于被美国政府采纳。根据泰勒总统提议,出身于麻萨诸塞州的律师顾盛,1843年被美国国会任命为特使,前往中国签订一项贸易条约。在筹备出使期间,伯驾1841年提交给美国政府的报告,被使团作为最重要文件加以研究。伯驾也因此“成为美中条约外交关系的最早设计者之一。”(注:古里克《彼得·伯驾和开放中国》(Edward V.Gulick,"Peter Parker and the Opening ofChin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s,1973),p.91.)不仅如此,历史还为伯驾提供了实际参与建立美中外交关系的机会。当顾盛率领美国使团于1844年2月到达澳门后不久, 就立刻写信给仍在广州行医传教的伯驾。在得到美国基督教差会同意的情况下,邀请伯驾参加美国使团工作。
顾盛给予伯驾的任命,使伯驾可以亲自参与对华修约建交的工作,来实现其开放中国给基督教的愿望。由于顾盛不懂中文,而且对中国事务所知甚少,所以使团与中国官员联系,以及商讨条约的工作,基本上全部由伯驾负责进行。伯驾在华十年的行医和传教经历,不仅使他熟练掌握了中文,并深入了解了中国各方面情况,而且还与广州地方的中国官员建立了密切的私人关系。在和中国政府谈判签订条约时,清政府特使耆英的两名助手黄恩同和潘士诚,都是与他私交很深的朋友。因而伯驾能轻易说服他们,不但把《南京条约》的全部内容写进《望厦条约》,并且还增加了一些更有利于美国方面的条款。正如顾盛在给美国国务院报告中所说的,“《望厦条约》中有五条关于转运税和吨税的条款,是《南京条约》中所没有包含的。 ”(注:《美国众议院报告》( "House Report",Report No.596,30 Cong.,1 sess.May 4,1848),p.3—4.)对于伯驾来说,这项条约的最大意义是为基督教在华传播取得了保证。条约第十七条规定,美国公民有权在中国居住,并建造住宅、教堂、仓库和墓地。这就等于宣布,传教士在中国有建造教堂传播基督教的权利。这项规定因而“成为后来法国特使拉萼尼,要求整个帝国对基督教解禁的基础。从外交意义来说,这项条约标志着美国对华外交关系的开端。1845年, 美国参议院决定单方面设立驻华公使职务, 并任命壁耳( J.Biddle)为首任驻华公使。 而伯驾则继续担任美国驻华使团中文秘书,以后又被任命为临时代办,最后成为驻华公使。伯驾任职期间,积极利用各种外交手段为基督教在华传播创造有利条件,终于实现了他通过建立外交关系把中国开放给基督教的理想。
二、容闳为促使清政府建立对美外交关系所作的贡献
在早期接受西方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容闳是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上著名的改良主义思想家,容闳热衷于发展中美外交关系,固然符合他力图引进西方文化和现代科技来改造中国的改良主义思想。但他对西方文化的好感,根源还在于他最初受教的马礼逊学堂的教育宗旨以及他的老师布朗对他的影响。这所以马礼逊之名命名的教会学校,其教育宗旨就是通过读《圣经》和有关基督教书籍,使学生“在抛弃他们的反感、迷信和偶像后,同基督教国家大众一起,承认和崇拜真神上帝。”(注:《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Oct.1841,Vol.,p.569.)马礼逊学堂的老师布朗(Samuel Brown), 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他被美国教会选派来华,是由于他“思想中高尚的灵性和作为一个基督徒在生活上的突出表现。 ”(注:《中国丛报》 (Chinese Repository),Oct.1841,Vol.,p.568。)在马礼逊学堂任教期间,布朗除了为学生们安排中、英文和其它各门课程外,还致力于用家庭方式对学生进行基督教教育。“他们和我们一起参加早晚崇拜,我们尽力使他们感到就象在自己家一样,以此给于他们一种基督教家庭教育。”(注:《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Oct.1841,Vol.,p.569—570。)
容闳的整个教育过程都与美国教育密切相关。他1841年入马礼逊学堂,在那里接受了六年美国式的教育后,又随布朗前往美国。在布朗与美国教会帮助下,完成了中学教育。1851年,容闳进入耶鲁大学学习,四年后获学士学位,成为中国第一个留学美国高等院校的文科学生。容闳所受的教育和经历,表明他是中国第一代由基督教传教士培养的知识分子。作为西方文化的接受者和传播者,容闳为官后,自然要尽全力发展中美外交关系。这正体现了马礼逊学堂教育宗旨中“同基督教国家大众一起,承认和崇拜真神上帝”的思想。1855年,容闳完成学业回国后,投身曾国藩门下,被任命为江苏候补同知。为发展洋务运动,容闳积极参与开办工矿企业。当江南制造局开办时,他还亲自前往美国采购机器设备。
在参与洋务运动同时,容闳最关心的是通过派遣学童赴美学习,来推动清政府发展对美外交关系与培养洋务运动所需人才。早在1867年,他就提出“挑选一百二十名十到十五岁的学生到美国学习十五年,以此来改造中国社会。 ”(注:容闳《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
YungWing,"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New York,1909),p.41.)容闳这项旨在扩展中美关系的建议,在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人物的支持下,终于在1872年被清政府采纳。根据这一建议,清政府决定派遣一个教育使团,带领学童前往美国学习十五年,“课程主要集中于军事、航海、数学和机械等学科。 ”(注:容闳《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 》(Yung Wing,"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New York,1909),p.176 。)容闳作为这一计划的倡导者和清政府中唯一精通西方事务的官员,被任命为使团的留美学生监督。经容闳积极安排,中国教育使团1872年10月到达美国。使团抵美前,先行赴美的容闳已在麻萨诸塞州水泉镇(Spring Field)的私人家庭中,为学童安排了住处。并在康乃迪克州哈特福特堡(Hart Fort )为教育使团建立了总部。
教育使团驻美期间,容闳以其特殊的身分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很快与美国各界人士建立了广泛联系。他凭借留学美国的经历,以及美国外交界人士对他的好感,很快就开始与华盛顿的美国政府官员频繁往来。他经常前往华盛顿,参加各种外交活动和外国使节举办的晚会。并常常拜访美国政府外交部门官员,与他们讨论有关中国问题。他还曾经去美国参议院出席听证会,向议员们介绍中国妇女情况。并说服美国参议院设立一项基金,以发展中国妇女教育事业。为了让美国人民更多的了解中国,容闳还积极致力于介绍中国文化。他和使团成员一起,经常举办各种介绍中国文化的活动。每逢中国传统节日,更要举办中国式宴会,招待当地社会各界人士。哈特福特当地报纸对此作过这样的报道:“市长和城里的绅士淑女们都参加了中国使团的宴会,他们受到使团人员耐心而周到的接待。”(注:“恭亲王奕忻等奏请派陈兰彬、容闳出使美日秘鲁等国折,光绪元年十一月十四日”,见《外交始末记》稿本。)
此外,容闳的外交活动还涉及其它一些方面,如为清政府在美采购武器。1873年8月,他和美国格林公司达成协议, 由他们向中国出售一批武器。8月12日,格林公司代表携带武器样品, 随容闳一道起程前来中国。结果,中国政府决定从格林公司购买价值十万美元的枪支。这批武器在1876年左宗棠抗击沙俄入侵西北边疆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874年,容闳还代表清政府,前往秘鲁调查华工被贩卖以及遭受残酷迫害的情形。经广泛了解华工被害事实,并实地考察其悲惨处境,容闳很快完成了调查报告。报告中除华工提供的大量受害证词外,还有当地美国侨民出具的旁证材料,并附有华工被鞭打的照片。这些材料公布后,使秘鲁等国遭到国际舆论强烈谴责,从而使秘鲁政府在与中国达成的协议中,不仅同意中国政府向秘鲁派驻外交官,以保护当地华人的合法权益,还同意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这可以说是中国政府自鸦片战争以来,在外交上取得的最大成就。
容闳在美期间取得的外交成就,终于促使清政府决定派遣正式驻美使节。恭亲王在1875年11月14日的奏折中指出:“是美国及日国、秘国遣使一层,均难稍缓,而三国同时遣使,不易骤得多人,似以请派使臣二员,合办三国事宜为较便。”在安排公使人选时,李鸿章提出“容闳熟于洋语洋律,办事奋勉,堪被出使之选”。不过清政府后来还是任命刑部主事陈兰彬为公使,容闳为帮办。但无论如何,这一举措终于使中美外交关系,由美国单方面对华派遣使团,发展为双方互派使节的对等局面。中国对美外交关系建立后,容闳尽管名义上仅为帮办,而实际上承担着驻美公使的全部职责。因为陈兰彬虽为公使,但他任期内大部分时间,都留在国内参与总理衙门事务。故而,美国外交界始终把容闳看作中国驻美的首任公使。
纵观中美外交关系建立始末,促成这一发展的因素固然涉及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但就这一事件发展本身而言,伯驾和容闳个人所做的努力是不容忽视的。为建立中美正式外交关系,先有美国传教士伯驾奔走呼吁美国政府,陈说对华建交之利害得失;不仅如此,他还受任为美国使团中文秘书,与中国政府谈判修约,以武力威胁与私人交情等种种手段,迫使中国政府对美打开外交之门。此后,又有改良主义者容闳,以培养洋务运动的急需人才为名,鼓动清政府派遣教育使团赴美;继之又以其外交业绩,向清政府证明遣使驻美已为必需,从而使中美外交关系得以正式建立。试想,若非伯驾和容闳的极力推动,即便中美建交的各种条件均已具备,亦难于在十九世纪中期得以实施。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伯驾和容闳二人原本都不是外交官员。他们致力于建立中美外交关系的缘由都与当时的基督教传播有关。作为基督教传教士,伯驾推动中美外交关系建立的动机,是为了把中国开放给基督教;而容闳致力于建立中美外交关系的根源,还在于基督教传教士开办的西方教育对他所产生的影响。对伯驾和容闳在中美外交关系发展中所作贡献的研究,以及对他们致力于建立这个关系的思想动机的探讨,无疑将为研究中美外交关系史提供一个全新的角度。
标签:基督教论文; 外交关系论文; 马礼逊论文; 传教士论文; 美国政府论文; 中国丛报论文; 容闳论文; 容闳学校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