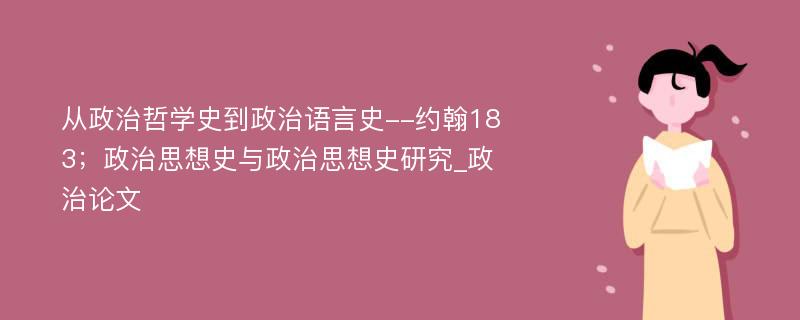
从“政治哲学史”到“政治语言史”①——约翰#183;波考克和政治思想史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约翰论文,政治论文,哲学史论文,政治思想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当前的中国学术界,约翰·波考克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说到熟悉,早在1990年,张执中就发表了《从哲学方法到历史方法》一文,使得我们得以初窥其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的堂奥,②而近年来,随着公民共和主义和剑桥学派思想史研究在中国的“热销”,波考克的名字更是屡被提及,而他的一些论文也被翻译成中文。③说到陌生,直到现在,我们仍没能译出其关于政治思想史方法论方面的几篇核心论文,④而其在该方法论指导下写就的几部经典著作的中文版也付之阙如。加之波考克古奥晦涩的学院派文风⑤(这与斯金纳轻松明快的文风形成鲜明对比),使得中国学界对波考克尤显隔膜,对其思想史研究,特别是在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中的理论和实践仍然缺乏必要的常识和准确的理解。⑥而这又反过来阻碍我们向这位学识渊深的思想大家借鉴并应用于我们自身的研究实践。
作为一种思想史研究范式,剑桥学派“情境主义”(contextualism)的研究取向是由拉斯莱特(Peter Laslett)首启肇端的,而后由斯金纳将其推至巅峰,以至于有人将这场思想史研究范式的转型称之为“斯金纳式的革命”。⑦这样,在剑桥学派的学术谱系中,波考克似乎处于一种前不立“地”、后不顶“天”的尴尬境地。但是,实际上,在剑桥学派的发展中,波考克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拓荒者。在剑桥学派的成长史上,拉斯莱特只是一个提示未来发展方向的人物,用胡适的话来讲,是一位“但开风气不为师”的人物。后来由于其兴趣旁移,转向人口和社会史研究,⑧从而未能将这一方向深入拓展下去。真正把“情境主义”的研究取向明晰化,并从方法论的高度对之进行系统思考的则是约翰·波考克。在奠定剑桥思想史学派研究范式的三篇论文中,波考克的《政治思想史:一种方法论的探讨》(1962)被誉为是“预兆未来”的经典之作,其刊发时间比邓恩的《观念史的身份》早6年,比斯金纳的《观念史中的意义和理解》早7年。⑨正是在这篇文章中,波考克首次提出政治思想的身份是历史的;在政治思想的研究中,我们所能采用的最确当的方法就是历史学的方法;我们从政治思想文本中所解读出来的“意义”必须是一种经过历史学的方法而得到确证的意义。⑩作为剑桥学派发展过程中一位不可或缺的、承上启下的枢纽人物,波科克赢得了其前辈和后辈的一致好评。(11)在《近代英国政治话语》这本向波考克“表达爱慕和诚挚敬意”的论文集中,编者写道,“从目前来看,20世纪60年代确实见证了对于政治理论史思考方式的革命性的开端,而更为确定的是:约翰·波考克本人就是最积极和最重要的革命者……他对盎格鲁—撒克逊政治的精神世界的广博学识、权威性的著说和永不满足的好奇心,继续激励大量历史著作的问世。人们仍然能够感受到从最出色的历史学家那里发出的令人心颤的历史感。”(12)
在剑桥学派内部,波考克是以独树一帜的“语言史”研究的理论和实践而声震学林。正如斯金纳所评价的那样:“约翰·波考克这位历史学家最具特色和最富成果的作为,就是将他的注意力集中在他所喜欢称谓的公开辩论的‘语言’之上。他主要的兴趣在于发掘各式各样独特的、政治论辩得以在其中展开的习语和言说模式。”(13)而波考克本人对这一说法也颇为认同,“对我而言,一种政治语言的概念意味着:先前被人们称为、作为一种习惯现在仍然被人们称为政治思想史的,现在可以被更为准确地描述为政治语言史。”(14)并且,以此为中心,波考克形成了系统的思想史研究理论和方法。下面,笔者不揣浅陋,对此做一述评。
一 从“哲学的解释”到“历史的解释”
1971年,波考克这样写道,“在过去的十年间,那些对政治思想体系研究感兴趣的学者在他们的学科内亲历了一场根本性的变革,这场变革实际上相当于一场转型。”对于这场转型,波考克自肇始阶段就参与其中,并“撰写了一系列论文,以阐明这种转型的特征”。(15)在波考克看来,这场转型的实质就在于为政治思想史研究确立“一种真正自主的方法”:既然“历史是关乎于事物的发生”,那么这种方法就“把政治思想现象严格地视为是一种历史现象,甚至视为是一种历史事件。由于事物是在一种情境中发生的,那么这种情境将决定该事件的性质”。(16)通过这种严格的界定,波考克名正言顺地对传统的政治思想史做出了这样的定性——“不合法的伪政治思想史”:它主要指洛维乔易(Lovejoy)所代表的、以“观念元”为思想史研究内容的学术研究方法。这种方法最基本的特点是纯文本性的,它既未揭示这些思想形成时所处的“情境”,也不探究隐藏在这些思想背后的言说者的“意图”,它只是把思想史建构成经典思想家关于“永恒问题”的持久对话。更为糟糕的是,这种方法常常以“影响”或“预兆”的方式来分析文本及思想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关于“影响”和“预兆”的分析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不是历史性的解证,而是一种年代倒错式的拉郎配。(17)波考克认为,传统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种种弊端以及由此引起的混乱,其根源在于“历史和哲学之间失调的关系”。鉴于此,要成功实现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转型,我们必须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重新估量哲学和历史学相遇的方式”(18):也即要正确地区分“历史的解释”与“哲学的解释”。历史的解释所关注的是“过去实际上发生了什么?”具体到思想史领域,就是关注“过去事实上发生的事情到底意味着什么?”而以哲学的解释为代表的种种非历史的解释所关注的则是“过去事实上所发生的事情对身处当下的我到底意味着什么?”(19)波考克认为,我们不应该将两者等同或混淆起来。作为思想史家,我们的首要目标就是“重建”某一特定的文本或言说的“历史意义”,也即,作为诠释者,我们所附加在文本或言说中的意义必须是该文本或言说呈现在特定历史场景(historical contexts)中的意义。当一个合格的历史学家在从事历史解释活动时,他必定会意识到,他和他的诠释对象并不是处在同一个“概念或意义世界”中,这样,为了确保解释活动的合法性,他必须追问:在多大的程度上,其解释对象(也就是作者)对其词语的使用与他(也就是现代解释者)对其词语的使用是相一致的?因为从解释者的特定立场来看,他必定观察到,解释者和作者之间的交流必定是如彼特拉克所想象的那种交流:也即其与西塞罗(或李维)之间的那种交流:“你,来自你那个时代的世界,而我,则来自我这个时代的世界”。这样,为了避免“强人以就己”式的误读,为了能与作者在同一个意义层次上使用某些特定词语,我们必须从传统中寻找概念工具,并从事一种波考克所称谓的“人文主义”的活动——也就是重建文本写作或言说行动所赖以展开的“意义世界”,也就是“用一种古人或先辈的那个时代的语言来重述古人或先辈的思想,以便理解当如此表达的时候,他所不得不说或必定要说的,以及他所关注的。”(20)但是,在波考克看来,在20世纪的政治思想史实践中,这种历史的、人文主义的原则遭到哲学的、操作主义(operationalism)(21)原则的玷污和背叛。用波考克的话来说,“20世纪的人讨厌把自己看作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矮子,他们不愿意从传统中寻找概念工具,而是宁愿构建自己的工具。”(22)其结果造成了历史解释中的“背叛行为的兴盛”。这表现在:秉持操作主义原则的解释者所关注的并不是一个作者在遥远的过去做某一表述究竟有何意指,而是其自身的当下状态可以使这一表述有何意味。他从事于解释活动并不是服务于作者的目的,而是服务于自己的目的,用中国的话说,他是“六经注我”,而不是“我注六经”。以霍布斯研究为例,在人文主义者看来,操作主义者往往只是借霍布斯之“酒杯”来浇自己之“块垒”,从而把霍布斯所不曾有的意图或不可能说的话人为地添加在霍布斯身上。所以历史学家常常向哲学家或政治理论家抱怨道,“说这些话时,霍布斯并不是这个意思,至少并不确切地是这个意思。但是很可能你是这个意思,如果你发现它对你是有用的。但是不要在你的思想前加上‘霍布斯曾说过’这样的词语,更不要加上不诚实的现在时——‘霍布斯说’。”(23)
在复原文本或言说的历史意义并重建作者的概念工具的过程中,波考克一个重要的方法论贡献就是提出了思想的“抽象层次”这个核心概念。波考克认为,对于从事历史解释的研究者来说,他必须选定一个给定作品或言说所意图(intend)在其中展开的抽象层次,也就是说,他必须判别一下作品(或言说)究竟是意图作为一种反思性的哲学行为,还是作为一种修辞性的劝诫。(24)通过采用伯克—奥克肖特式(Burkean-Oakeshottian)的定义法,波考克把政治理论定义为一种“从传统中进行抽象和精练”的行为:正是在“行为传统”中,人们展开了抽象行动,而政治思想的研究就是研究当人们展开这种抽象行动时发生了什么。在波考克看来,对于思想史研究者而言,至关重要的是:他要充分地意识到,思想家在进行思想抽象活动时,他们的目的是变动性的、多重的:“人们展开抽象活动是为了多重的目的,有时是修辞性的,有时是科学性的,其目的是经常变动的。”(25)而这种目的的多样性也决定了抽象层次的多样性:“抽象可以指向进一步的抽象,并且思想的层次经常在实践和理论的层面上游移。一个思想片段既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政治劝服行动,又可以被看成是一种追求理解过程中的一个事件。论点或概念在经过几秒的间隔之后,比之其刚才所服务的目的,既可以是更具理论性的,也可以是更具实践性的。一种哲学等其再度出现时俨然就是一种意识形态,一个党派的标语也可以转瞬变成宣扬纯正的科学性价值的一种启发教育工具。”这一点可以从对日常实践的观察中得到昭示:“经过考察,可以证明,在某一特定社会的某一历史时期中所出现的政治思想可以出现在不同的抽象层次上,而且随着它所想解决的问题的性质的变化而变化。某一特定个人的政治思想也是如此。”(26)这样,在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实践中,抽象层次的多样性就成为一个难题,它向我们发出了庄严的挑战。因为抽象层次的多样性非但没有赋予我们解释的自由,反而向我们施加了解释的限制。由于从理论上讲,政治思想可以在任何一种抽象层次上展开,因此,在实践中,摆在思想史家面前的“严格意义上的历史任务就是通过研究来确定:思想发生在什么样的一个抽象层次上”。也即,在思想史写作中,我们必须证明“我们所使用的抽象层次就是政治思想发生时所处在的抽象层次”。(27)
但是,在波考克看来,在传统的思想史研究中,“确定政治思想得以在其中展开的抽象层次”这一关键性步骤被忽略了。对于传统的思想史研究模式,波考克是这样描述的:“直到20世纪的中叶,在历史研究的所有主要门类中,政治思想史研究被处理成对传统经典的研究,而且在这种情况下,把传统经典转换为思想史是通过用哲学评论的方法——既对该传统的思想信条进行哲学的评论。”(28)这种模式实际上是一种哲学性的解释模式,其习惯于把政治思想放在一种很高的抽象层次上,并先验地把政治思想设定为具有高度融贯性(coherence)和理性化(rationality)。在这种解释模式下,对文本的解说就被等同于对文本“融贯性”的发现,于是对思想进行重建的努力就聚焦于复原文本的“融贯性”,甚至聚焦于发明一种方式,据此,文本或许可以被赋予一种作者未能也没有赋予的“融贯性”。这样,在历史中所实际存在着的抽象层次的多样性便隐匿不见了,或被人为地抹杀了,其结果,“传统被浓缩为一种发生在一种很高的抽象层次上的单一描述”。但是,波考克所要问的是:这难道是一种“有效的历史解释”吗?在他看来,那种以发现或揭示文本的“融贯性”为目标的思想史研究实际上是非历史的,甚至是反历史的:“因为从原则上讲,一个思想家既有可能成功地获得这种融贯性,也有可能在这方面失败……显而易见的是,给作者附加一种他事实上并没有获得的融贯性并不是历史学家所要从事的事”。(29)波考克认为,之所以产生这种非历史的解释,是由于人们错误地把一部政治著作作为政治理论所具有的“一致性”的特质,混同于一部政治著作作为“历史现象”的特质。当哲学家把一部政治著作先验地建构为一种政治哲学或政治理论时,他所感兴趣的思想是那些可以在严格的理性的层面上获得解释的思想。而通过把一部政治著作还原为一种历史现象或一个历史事件,历史学家所关注的是事实过程,也就是“个体思想行动者究竟居于什么样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他为什么要如他所曾做的那样来行事?”(30)在波考克看来,关于思想体系中一个观念与另一个观念是如何相联系的哲学解说就总体而言异于——只是偶然地合于——关于作者意图说什么(更不用说关于作者为什么想说它,或为什么选择以这种方式来说它)的历史解说。事实上,这两种解释之间的“耦合”只存在于以下特定情况:即只有当我们的解说对象是哲学家,而且其在著述或言说时有意在一种高度抽象的层次上层开时,我们这种以揭示或发明文本“融贯性”为目标的哲学式的解释活动才是“偶然”合法的。因为这两种解说所遵循的路径不同,其所要回答的问题也不同。在哲学家那里,他们研习文本,然后从中抽象出各种思想体系,并把它们按照历史的顺序加以排列,其中,思想体系之间的相同性被视为构成了连续性,而它们之间的不同则构成了变化的过程。但是,在历史学家看来,这种历史秩序并不是建立在历史学的方法之上的,它不是一种真实的历史过程,而只是一种超历史的、虚构的“哲学建构物”。波考克注意到,在思想史实践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种以哲学解释来取代历史解释的经典例证。以阿隆(R.I.Aaron)为例:对于洛克为什么明显对政治方面的任何历史解释均不感兴趣这一问题,阿隆试图这样来解释:在洛克所生活的这样一个理性主义时代里,人们对理性解释以外的任何解释都不感兴趣。但是,历史的探讨却表明,这种哲学式的判定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在当时,在对“历史解释”不感兴趣方面,洛克只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特例,而与洛克同时代的理论家,包括他最亲近的朋友则并非如此。(31)
对于波考克来说,像阿隆这样的诠释者之所以犯错误,一方面是由于对哲学方法的偏执,一方面是由于对历史方法的“无知”。用波考克略带调侃的话来说,“对于他们显见的义务——去研究他们所知道是历史的东西,或去写他们所知道是历史的东西,哲学家、政治理论家或批评家是心怀忿恨的(resent)。”因为当他们发现自己被卷入一种人文主义活动,并被期望去做一种历史解释时,他们并不具备这方面必要的技能或训练。其结果,“无论是他们讨厌抑或喜欢这项工作,其结果往往都是不幸的”。(32)当然,波考克以其一贯的严谨补充道,这并不是说缺乏历史训练的哲学家或政治理论家就一定写不出“优秀的政治思想著作”,只是,在这种方法论限制下写就的好作品“在某种意义上只是一种造化(chance),是由‘美德’(virtu)和‘机缘’(fortuna)凑合而成的造化”。(33)
二 从“言语(parole)”转向“语言(langue)”
虽然波考克和斯金纳都主张对言说(parole或utterance)进行“历史性”解读,虽然人们在“剑桥学派”的名目下都笼统地把他们称之为“情境主义者”。但确切地讲,斯金纳更大程度上是一位意图论者或惯例主义者,而波考克才是真正的“情境主义者”(34)。波考克曾写道,“当把政治思想写成发生在历史中的一系列的事件时,历史学家必须这样来处理:把思想看成是发生在由理论家或哲学家的思考所构成的事件的情境中,而对其的解释也只能参照该特定情境才能获得”。(35)在这里,波考克所指的解释所赖以参照的特定情境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社会情境,一种是语言情境。(36)对波考克而言,后者尤为重要:“一个言说行动在其中施行的最为首要的情境就是一种制度化的言说模式,正是这种言说模式使言说行动成为可能。对于任何要说、要写、要印刷的东西而言,必然有一种语言,以供在其中说、写或印刷”。(37)因为在波考克这样的语境主义者看来,作为言说行动的总体框架或范式,语言(langue or language)不仅决定了言说的步骤和样式,而且决定了言说的内容和意义:“社会赋予个人以语言,正是在语言中,人们才能进行他们的言说活动,正是通过语言,他们的言说活动才能获得公共的重要性。”(38)正是基于这种理论立场,波考克展开了其思想史研究中的最具颠覆性、也最具原创性的步骤,也即把政治思想史研究转换为政治语言史研究,正如波考克自己在霍普金斯大学的“告别演讲”中所总结的那样,“在我的整个一生中,政治思想史已经变得不再是一种思想的历史,而成为一种语言、话语和文献的历史”。(39)
当然,波考克的这种立场不是没有根由的。正如瑞奇(Melvin Richter)所指出的那样,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受“语言学的转向”的影响,思想史研究的基本范式也得以重塑,并由之产生了一个根本性后果:那就是,在思想史研究中,人们开始重视并致力于“研究语言的历史性角色”。(40)但是“共相”之中还存在着“殊相”。例如,斯金纳的主要理论资源来源于奥斯汀的言语行动理论,在这种理论背景下,他更多地强调“言语”或“言语行动”的层次,强调作者言语的每一次有意图的、具体的、即刻性施用,以及其中所呈现出来的“修辞性”成分。(41)与斯金纳相比,波考克的理论背景则相当驳杂。作为一个勤于且长于理论思考的思想史家,波考克的理论范式是在总结自己实践的基础上广泛采借其他学科的理论资源而形成的。所以,在其理论渊源中,我们既可以看到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language-game)、奥斯汀的“言语行动”(speech acts)的影子,也可以看到布罗代尔的“长时段和心态”(longue duree,mentalite)、福柯的“话语”(discourse)、库恩的“范式”(paradigm)的印迹。(42)但是,在这种驳杂的理论底色中,波考克最终信守的实际上是一种索绪尔式的结构主义。在这种立场中,波考克更多地是强调“语言”或“话语”的层次,强调“言语行动”在其中得以展开的结构性范式。与斯金纳等人通过“意图”来强调“作者”的“能动性”不同,结构主义者则通过“范式”或“言说结构”来凸显“作者”的“被动性”和“受约束性”。对于这种立场,伯维尔(Mark Bevir)有着准确的描述:在结构主义者那里,“一个言说行为的意义源于‘知识’、‘话语形式’或者‘范式’;他们相信,为作者所能用或可用的意义依赖于存在于社群中的思考、写作或言说的方式;作者不能摆脱一个社会所给定的结构,所以他所能说的是以一种理论性的结构为转移,而社会则赋予他们以进入这个理论性结构的通道;作者所能说的依赖于他们用之进行说的概念,而这些概念并不是不带价值取向地、客观地反映外在现实的,而是包含了经由社会而传承下来的关于世界的认定。”(43)这种观点也在福柯早期的准结构主义立场中得到鲜明的揭示。福柯认为,在诠释“意义”的过程中,“作者”的概念是多余的。因为是言说的“范式”而不是作者的“意图”“支配着作为一个独特事件的言说的风貌”。这表明:是“语言”,而不是“作者”成为“可能说什么的第一个法则”。(44)作为对这种立场的秉承,在诠释“意义”的过程中,波考克也严格限定了“作者”的作用,认为作者只是“文本写作范式(script-writing paradigms)的传声筒”:虽然作者仍然是历史的施动者,但思想史研究的单位必须是理论性的和语言性的结构,因为正是这些结构“规定了他(作者)所能说的,以及他如何去说”。通过赋予作者以其可能具有的实施其意图的方式,语言赋予作者以其所可能具有的意图。(45)这样,在思想史研究中,“语言”——作为作者在其中得以展开其言说行动的范式,就比“言说行动”具有了更大的优先性。波考克写道:“在历史的深度中,语言一旦被看成是作者据以展开其言说行动的范式,它就具有了比作者言说的‘意图’或‘语内表达行为的力量’更大的优先性,因为只有在我们已经理解作者拥有何种说任何事情的方式或手段的时候,我们才能理解他意图说什么或他想说什么,才能理解他成功地说了什么,才能理解他被认为已经说了什么,或者才能理解他的言说在修正或转变现存的范式结构方面具有什么样的效果。”(46)
需要说明的是,在其著述中,对于“作者据以展开其言说行动的范式”,波考克有时以“语汇”、“语言”、“范式”来命名,有时又以“话语”、“修辞”来命名,(47)虽然名称相异,但其界定的内容是相同的,即指拥有各自“语汇、法则、暗示、腔调和风格”的、“与众不同的语言游戏”。(48)从这种界定中我们可以看到,波考克这里所说的“语言”既不是一种自然语言,也不是作为种属意义上的民族语言(如英语或法语),而是指同一民族语言下的次语言,也即特定政治共同体中存在的各种政治语言,也即波考克所称的“政治论辩的模式”或“讨论政治的方式”。既然言说范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言说的内容,那么,为了建立一个政治文本的意义,为了发现其作者事实上都说了什么、意指了什么或传递了什么,历史学家的首要工作就是去寻找并重建这些作为政治论辩模式的“语言”,以及这些语言经由时间而产生的变动。由此,波考克彻底颠覆了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传统视角,把研究重心聚焦于“政治争辩的语言”上。如波考克所说,“我希望研究言说在其中展开的语言,而不是在语言中展开的言说。”(49)在波考克看来,每一个稳定的政治社会都会发展出形形色色的政治语言。就其内部构成而言,与自然语言相类,政治语言是由“概念”通过语法和联结性的指令系统以一种内在的秩序组合而成的。(50)那么,作为一种“有组织的概念”,政治语言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波考克认为,政治语言最初源于从特定社会和文化传统中所提炼出来的“技术性语汇”,后来,在人们建构政治思想的过程中,这种“技术性语汇”被采借和政治化,以“作为讨论政治的一种方式”。对此,波考克写道:“任何稳定而有述说能力的社会均掌握概念,并用这些概念来探讨政治事务。同时又把这些概念连接起来组成概念群或语言……这些语言在它们所由之产生的社会行为的部门上不同,在它们被使用的方法以及它们所经历的修正上也不同。有些语言是源于社会中规范公共事务的制度化模式的技术语汇,西方的政治思想主要是在法律的语汇中展开的,而儒教中国的政治思想主要是在礼的语汇中展开的。其他则源于已变得与政治相关的一些社会过程的语汇:如神权社会中的神学语汇,封建社会中的土地保有权语汇,工业社会中的技术语汇。”(51)
与技术语汇不同,政治语言具有捍卫或否定政治行为合法性的特定功能。在波考克看来,作为一种论辩范式,每种“语言”都对政治如何被概念化,以及对政治制度和政治实践如何得以合法化的方式施加了限制。(52)波考克这方面的理论视野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库恩的“范式”理论。对于库恩,波考克总是不吝溢美之词:“对于政治思想史家来说,无论怎样夸赞库恩的吸引力都不为过,因为……他提供了一种方法,从而使政治思想史具有了方法论上的自主性。”在波考克看来,通过提出“范式”概念,库恩成功地把传统意义上的“科学史”转换成一种“话语史”或“语言史”。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库恩是如下描述“范式”的:即通过预设性地界定什么才是需要解决的问题,“范式”权威性地指出了科研人员努力的方向、模式和组织形式,以及权威在那些组成“科学共同体”的个人和群体之间的归属和界定。对波考克而言,这就预示着:通过范式,库恩把“科学史”——波考克称之为“思想史的一个分支”——处理成“一个既是语言的、又是政治的过程”,把科学研究这个“高度形式化的思想行为”看成是“一种通过语言手段来进行的交流和分配权威的行为”。(53)波考克认为,对政治思想史研究者而言,这具有极大的启发和借鉴意义:作为一种范式,虽然政治语言不像科学语言那样以“解决问题”(problem-solving)为最终导向,但是却与后者一样执行着在社会体系的行动者之间分配思想和政治权威的功能:“人们通过沟通语言体系而思考,语言体系有助于构造他们的概念世界和权威结构(authority-structures),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世界;概念世界和社会世界可以被看成是互为情境的,由此我们就可以获得一幅精确而清晰的图景:个人的思想现在或许可以被看成是一种社会事件,一种范式内的交流或反馈行动,一种历史事件,一种历史时刻——也就是该语言体系转型过程中的历史时刻,以及该语言体系和语言行动与权威结构和社会世界相互建构的这样一个互动世界中的历史时刻。这样,我们就获得了我们此前所缺乏的东西:历史学家所需要的情境的复杂性。”(54)
对波考克而言,历史学家所要做的首要工作就是要学会“辨明”(identify)语言,并通过语言来阅读和理解文本,从而“把思想正确地置于它所真正属于的话语传统中”。正是从这一特定立场出发,从20世纪中叶开始,波考克就始终致力于“发掘”并“辨明”为英国近代早期的政治理论家所使用的各种“语言”,并取得巨大的成就,如评论家所指出的,“波考克的成就在于比其前辈中的任何人都更为充分地发现了多元的、相互竞争的、可为的17、18世纪英语世界作家所用的政治话语”。(55)在这一过程中,波考克总是在叩问:在政治论辩中,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批判和捍卫政治行为合法性的模式?这些模式又参照什么样的象征或原则?言说者试图在什么语言中、通过什么样的论辩形式去实现他们的目的?就此而言,波考克认为历史学家所做的工作类似于人类学家雷蒙德·佛斯(Raymond Firth)在其名著《提克皮亚人的传统和历史》(Tikopia Tradition and History,Wellington,1961)中所做的工作:也就是发掘为提克皮亚人所使用的、分属于几个不同血系的诸传统,以及这些不同的传统在维护社会团结或者在诱发社会冲突方面所扮演的角色。(56)正是依照这种途径,波考克“辨明”了17世纪后叶英国政治论辩中所存在的三种“语言”——也就是古代宪法语言、宗教启示性语言和拉丁人文主义语言。在奠定其最初学术地位的经典著作《古代宪法与封建法》中,波考克考察了其中的“古代宪法”语言(又称“先例”语言)。作为一种政治论辩的范式,古代宪法语言把英国政治,特别是与法律制度相联系的自由权归因于一种连续的、未有中断的古代习俗。波考克认为,正是这种“先例”语言为伯克提供了反对法国大革命的诸多论点。当然,在这方面,波考克影响最大、也最具典范价值的工作是由《马基雅维里式的时刻》(57)提供的。书中,波考克发掘出一种完全不同于“法学(或自然法)”语言的“公民人文主义”语言。在传统的经典著作中,无论是卡莱尔、萨拜因的著作,还是沃林的著作,政治思想史均是以“法学”语言写就的。但在波考克看来,这只是一幅由于误读而被“制造”出来的残缺不全的思想史图景。因为在现代早期的欧洲,除了“法学”语言之外,还存在着另一种与之相竞争的政治语言——也就是圭亚恰迪尼和马基雅维里等思想家在其中思考和写作的“公民人文主义”语言。尽管两者所具有的价值前提不同,其所面对的问题和所使用的论辩策略不同,但以往的思想史家却常常无视或混淆这种差别,粗暴地把“公民人文主义”语言强行纳入“法学”语言中,并由此造成误读。因为在波考克看来,以一种“法学”的语言来解读马基雅维里,实际上就等于把马基雅维里翻译成一种他根本无法认同的语言。(58)
对波考克而言,在某种意义上,与传统的“观念史”相比,这种以探寻“政治语言”为目标的思想史实践更多地是一场充满着无数惊喜和意外发现的探险之旅,一种“serendipity test”。(59)因为我们常常可以在人们未曾预想到的或被众所忽略的地方发现一种熟悉的语言,(60)并由此感受到一般思想史家无从体验的欣悦(striking)、振奋(excitement)和讶异(astonished)。(61)
三 从“一元历史”走向“多元历史”
在波考克那里,“语言”概念的提出不仅意味着政治思想史研究视角的转换,同时也意味着其解释模式“空间性”的拓展,也即由传统的一元的、平面化的解释模式转向一种多元的、立体化的解释模式。作为一种高度“制度化”的言说模式,“语言”具有与科学范式相类似的功能:也即在政治共同体内部对政治和思想权威进行界定和分配。但是,波考克同时又指出:与科学范式所不同的是,语言并不具有排他性;在同一个政治社会中,甚至是在某一特定政治话语和政治文本中,往往是数种“语言”并存。(62)既然特定的言说活动(或文本)是在特定的“范式性场景”——也即特定“语言”——中才获得明确意义的,那么,在多元共存在的“语境”(language contexts)下,一个特定言说行动(或文本)实际上可以获得多重意义。正如波考克所说的:“一个作者所居于其中的语言情境越复杂,甚至是越自相矛盾,他所能施行的语言行动就越丰富和越含混(ambivalent)”。(63)所以,在这种多元语境下,波考克一直强调“日常语言”特别是“政治言说”所具有的“含混其辞的特性”(muddle-ridden character)。在波考克看来,政治言说实际上是一种“修辞”,“它是用来调和那些追求不同价值目标和行为的人,因此一个政治言说很可能同时执行几种不同的语言功能。在有些人看来是一种事实表述,而在另外一些人的眼里,它则象征性地唤起了特定的价值。在一群听众那里唤起了一种事实主张以及与之相关的价值判断,而在另一群听者那里则唤起了另一种事实主张并举荐另一种行为决心……因而政治言说的内在含混性和隐秘性是相当高的”。(64)
在多元语境以及语言范式的历史变迁中,既然一个特定言说的意义是“开放性的”,那么,由言说所构成的“政治哲学”的历史展开模式也必定是“多元性”。故而,作为对施特劳斯、布鲁姆等人的批评(称布鲁姆的政治哲学史是“由无知和深奥创见混合而成的怪胎”),波考克认为,政治哲学并不具有“一种一元化的描述性历史”,而是多元语境下的多元历史:“政治哲学是人们反思其政治语言的产物,而政治语言则是社会行为体为了阐发和调和各种行为而聚合起来的各种原始质料。作为历史自身的基本素材,这些原始质料是极为歧异和杂乱的,因而政治哲学不可能具有一种单一的历史展开模式(single evolving pattern of history)。”(65)在波考克看来,作为一种反思性的言说活动,政治哲学可以被视为一种跨越时空的“对话”。在建构政治哲学的过程中,哲学家并不是孤立的,“他知晓其他哲学家以及其他各种政治行为主体的言说,他们的言说构成了对其意识和认知的输入。通过说其所说,哲学家对他所认定其他人所已说的做出回应(responses),而且对其他人言说行动的诠释构成了哲学家专业化活动中相当大的部分。”(66)既然政治哲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对话”,那它就逃避不了日常语言限制下“对话”的本性:即对话的参与者“往往是在不一致的目的或问答游戏(cross-purposes)中进行交谈”。(67)波考克举例说:有两个哲学家,一个叫Alter,一个叫Ego。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刻,Ego施行了一种言说活动,这种言说活动在特定的意义上是对Alter曾经施行的某个言说活动的回应。既然是回应,它必然会涉及解读问题,也就是说,Ego的回应是建立在对Alter言说行动的诠释之上的。但是,对于Ego的回应,Alter常常会说,“我并没有如此说”,“我说的并不是这个意思”。这就意味着,在谈话中,作为言说者的各方对于“正在说的”并不具有“全部的知识和绝对的控制”,也就是说他很难限定对方言说(甚至自己的言说)的“意义范围”,故而会产生意义的添附、减损或变异。(68)实际上,在历史的绵延中,Alter与Ego之间的故事会永无休止地重演下去,每个Ego都会根据自己所处的情境对Alter的言说行动进行“花样翻新”的诠释。这就预示着,在思想传承的链条中,任何一个哲学家的言说行动,都可以被其他人——无论是他的学生、门徒,还是他的对手和批评者——赋予该哲学家所不曾预想到或不曾意图的意义。
波考克认为,只要我们把政治哲学中的言说行动看成是一种“历史现象”,那么,其意义必定是“多维的”(multi-dimensional);只有在人为设定的“实验室”中,任何给定言说行动的意义才能得到“排他性”的阐发。同样以Alter和Ego为例:对于Alter“我并没有如此说”、“我说的并不是这个意思”的说法,Ego可以不无正当地回应道,“我并不关心你说了还是没说,也不关心你是这个意思还是那个意思,我想说的是,如果你所讲的是如此,那么我的评论将是这般。”波考克认为,从这一刻起,Ego就从“对话”中抽身而出,进入到一个“自我合法化”的“假想世界”:在其中,通过“自由地把他所接受的信息重塑为一种他愿意接受并对之做出反馈的信息形式”,Ego以一种专断的、“独角戏”(mono-drama)的形式判定了Alter的言说行动的意义。但是,在波考克看来,Ego的这种以“实验”代替“历史”的做法只能获得暂时的、有限的成功。在实验室之外,Alter的言说行动仍然是“日常语言世界”中的“多样性”(multi-valence)存在,仍然历史性地运转于多元情境和多元层次中。此外,Ego永远也不能排除这样的努力:即人们“以某信息在其刚开始传播时所曾是的样子来重构该信息,或者以某信息在其传承过程中任何一个居间时刻所曾是的样子来重构该信息”。在这方面,历史学家贡献甚巨,用波考克的话说,他们常常手拿“解码器”“潜入(bugging)时间之流”。
在波考克看来,思想或言说要想成为“历史”,它就必须被看成是一种“行动”(actions)(69),而其作者也必须被看成是“历史行为者”(historical actors):也就是说,我们是通过追溯某一言说在历史上“实际上都做了什么”而获得其历史的,而该言说“实际上都做了什么”则总是体现在别人对该言说的使用和反应上。但正如波考克所提示的那样:一旦思想史家以“人们对于政治言说使用的反应以及其被使用的方式追溯政治言说的历史的时候,他一定认识到这样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政治言说拥有多元历史(histories)。因为政治言说是在不同的层次上被使用、认知并激发反应。因而考虑到这些层次的语义多样性,政治言说的这些历史是彼此大不相同的”。(70)对于波考克而言,言说行动的这些“历史”(histories)都是真实存在的,每种历史都通过影响(或改变)人们的认知而影响(或改变)历史,故而都是思想史学家确当的研究对象。正是由这种立场出发,波考克开始把研究的触角延伸到“政治言说”的语言和空间形态,进而思考政治言说在“不同的交流空间或场景中(in a variety of communicative spaces and situations)的发生”:如当格劳修斯在伦敦被阅读和反应时会发生什么?霍布斯在莱顿被阅读和反应时会发生什么?洛克在那不勒斯被阅读和反应时会发生什么?孟德斯鸠在费城被阅读和反应时会发生什么?通过这些追问,波考克试图表明,在思想传承(传播)的历史过程中,既然任何人(包括作者(71))都能控制言说行动的意义,既然言说行动总是属于多元话语世界,既然言说行动总是占有多种逻辑地位和指涉背景(contexts of references),既然言说行动总是施行多种政治行动和政治功能,那么它就不可能只具有“一种”(a)历史。以《利维坦》为例:在17世纪中叶,在伦敦,人们在其中对《利维坦》进行阅读、认知并做出反应的是这样一个世界:一个乔治·托马森(George Thomason)的世界,一个纸质媒介迅速扩张和革命意识持续高涨的世界;而在尼德兰,则是另一番情形:在一个雍雍穆穆的资本主义世界,人们是在大学的讲演厅用拉丁文来阅读和讨论《利维坦》。正是这些不同的交流空间、场域和结构中,《利维坦》的多元历史(many histories)得以产生和传播。(72)在这种以“行动”为中心的对“思想”的历史主义重构中,思想史家为“哲学家”勾勒出“表述(statement)所承载的意义的丰富性(richness)”,以及由之而来的多元的历史发展模式。正如波考克所指出的,这种历史主义的批评较少是以消极作用——排除Ego所加诸在言辞(words)上的意义——为标的,而更多地是致力于发挥积极作用,也就是对像Ego这样的哲学家进行训练,让他们“在历史性中去理解另一个人的言说,也即意味着要考虑到所说、所感、所想所承载的内容的多样性(wealth and diversity),以及这些内容所能被说、被感、被想的方式的多样性”。(73)在波考克看来,对于像Ego这样的哲学家而言,这种训练无疑具有极大的价值:一方面,它极大地拓展了Ego接受和处理各种不同的信息的能力;另一方面,它又极大地扩展了Ego对于他所可玩的“语言游戏”的多样性的认知。
既然政治言说在传承中的任何时刻都不止一个意义,也不止只参与到一种历史,那么作为一个思想史家,其首要任务就是对其要解释的政治言说进行“定位”(location),并用“一种高度复杂的探测和发现技术”把它置于某一特定的意义层和历史脉络中,从而避免受“多样性”的诱惑堕入“不受规训的、随意性的解释”;其次,除了“定位”之外,历史学家还必须学会选择,选择那些他最能胜任去告诉的历史或历史的片段(piece of history)。在波考克看来,一个政治言说的“意义层”可以分为“潜在的”和“显在的”。由于政治言说的意义是以语言范式为条件的,这就意味着,随着语言范式的变迁,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刻,政治言说的某些曾经“显见的”意义层就会变成“潜在的”,而某些曾经“潜在的”意义层则会变成“显在的”。这就像一条地下河,在某些有利的地形条件下,它就会爬升至地表,并欢腾雀跃地呈现在人们的眼前,而在某些不利的地形条件下,它又会隐遁入地下,并悄无声息地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之外。而作为历史学家,他必须利用当下的历史时刻为他提供的“有利位置”(vantagepoints),把一些政治言说中“潜在的”、一直为人们所忽略的“意义层”发掘出来,从而使之成为“显在的”。(74)在这个意义上,波考克式的思想史家在很大程度上又成了一位“考古学家”,致力于发掘为历史所湮灭的“意义层”。值得一提的是,这项由“潜在”变“显在”的思想考古工作在波考克和斯金纳那里都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在《马基雅维里式的时刻》、《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和《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中,他们协同作战,成功地使曾经像地下河一样处在“潜在”状态的古典共和主义变成“显在的”。但是,我们或许可以进一步追问,在当代,是什么样的一种“有利位置”使波考克他们获得了这种使“潜在的”变成“显在的”的可用视阈?对我们而言,这或许是一个更有价值的研究论题。
作为一位思想大家,波考克最显著的特色是熔理论思考与研究实践于一炉,其著述既不乏理论上的精深奥微,又兼具实践上的细致缜密,可谓“上可腾霄云,下能入屑泥”(one foot in the clouds and the other in the mud)。但是,就其大端而言,波考克思想中最具价值和原创性的是“语言”概念的提出,以及其中所蕴含的“多元”价值观念。(75)波考克有理由认为,既然任何思想诠释都是以特定的“语言”范式为条件,那么,任何垄断思想和话语霸权的企图就显得多少有些虚妄!最后,我们可以借用一句贝尔纳·贝尔笛的话,“既然不存在幼稚的阅读,我们了解一下我们所戴的眼镜也无妨”(76)。对于思想史研究者而言,同样真实的是,既然任何思想都是以“语言”为范式的,那么在研究思想之前,我们了解一下人们用以“组织”和“建构”其思想的“语言”也无妨。或许,这正是波考克所想要传达给我们的教益!
注释:
①需要指出的是,在波考克那里,“政治思想”、“政治理论”、“政治哲学”都是不加区分地交互使用的,都是指同一个意思。在文中,特别是涉及引文的地方,为了保持原貌,作者并没有强行进行技术上的统一。
②张执中:《从哲学的方法到历史的方法——约翰·波考克谈如何研究政治思想史》,《世界历史》1990年第6期。严格地讲,这只是一篇高度浓缩的论点摘编,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研究性论文。由于波考克的理论文章本来就艰涩难读,经过这种摘编之后,就变得更加难懂。
③如《古典以降的公民理想》,载许纪霖主编:《共和、社群与自由》,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德性、权利与风俗——政治思想史家的一种模式》,载马德普等编:《中西政治文化论丛》第4辑,2004年版。
④如"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A Methodological Enquiry",in Peter Laslett and W.G.Ruciman(eds.),Politics Philosophy and Society,2[ed] series,Oxford,1962; "Verbalizing a Political Act:Towards a Politics of Speech",Political Theory 1(1973); "Language and Their Implications: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in J.G.A.Pocock,Politics,Language and Time,London and New York,1972; "Political Ideas as Historical Events:Political Philosophers as Historical Actors",in Melvin Richter(ed.),Political Theory and Political Education,Princeton,1980; "The Concept of a Language and the metier d'historien",in A.Pagden(ed.),The Language of Theory in Early Modern Europe,Cambridge,1987; "The State of the Art",in J.G.A.Pocock,Virtue Commerce and History:Essays on Political Thought and History,Cambridge,1985。
⑤对于波考克的文风,保尔(Terence Ball)评点道,“波考克文风晦涩难懂,在行文上繁复增饰,富有巴洛克风格,而有时在其声言中透露出一种难解的、神谕般的奥义”。见Dario Castiglione and Iain Hampsher-Monk(eds.),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in National Contex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128。
⑥比如,对于波考克的“Virtue,Rights and Manners:A Model for Historian of Political Thought”一文,有人把其译为“德性、权利与风俗”。这里把“Manners”翻译为“风俗”肯定是不合适的,而应当翻译为“礼俗”或“礼貌”或“礼仪”。在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特别是在以休谟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那里,存在着一种以“美德”为中心的共和主义语言和以“权利”为中心的自然法或法学的语言之间的持续的紧张和冲突,并最终发展出一种以“礼俗”(或“礼貌”或“礼仪”)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的语言。这种语言强调商业和奢侈在沟通和规范人际关系方面,在塑造人们的行为模式和建构“社交性”(sociability)、“文雅”(politeness)和“文明”(civility)方面所具有的功能和价值,从而在某些方面背离了共和主义的美德语言,而把社会行为模式的中心由强调公共领域的政治参与(公民理想)转向社会和私人层面的人际交往(绅士或君子理想)。这方面的相关论述见Nicolas Phillipson,Hume,St.Martin's Press,New York,1989,pp.17-34。
⑦凯瑞·帕罗内:《昆廷·斯金纳思想研究:历史·政治·修辞》,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⑧拉斯莱特在剑桥大学领衔成立了“人口和社会结构史研究剑桥小组”(the Cambridge Group for the History of Popul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并使之成为一个具有国际影响的人口和社会结构研究中心。见Melvin Richter,"Reconstructing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Languages:Pocock,Skinner,and the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History and Theory,Vol.29,No.1,p.3。
⑨Dario Castiglione and Iain Hampsher-Monk(eds.),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in National Context,p.159.
⑩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A Methodological Enquiry,p.188.
(11)据斯金纳讲,波考克关于“不同的政治思想家是在不同抽象思维水平中进行思考的”论点让拉斯莱特颇为称许。同时,波考克的博士论文《古代宪法和封建法》(1957)更是大学时代的斯金纳最为欣赏的著作之一。见《昆廷·斯金纳思想研究:历史·政治·修辞》,第15页。
(12)尼古拉·菲利普森、昆廷·斯金纳编:《近代英国政治话语》,前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3)Nicolas Phillipson and Quentin Skinner(eds.),Political Discourse in Early Modern Britai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p.67.
(14)The Concept of a Language and the metier d'historien,p.19.
(15)Politics,Language,and Time,p.3.
(16)Ibid.,p.11.
(17)History and Theory,Vol.29(1990),No.1,pp.54-55.
(18)Politics,Language and Time,p.3
(19)Ibid.,p.7.
(20)Politics,Language and Time,p.8.
(21)波考克区分了“人文主义者”和“操作主义者”。操作主义者的特征是:在与古人的“对话”中,他只“欲求抓住那些他注意到的一些言说行动,并用它来施行自己的语言游戏。”而人文主义者则“真正关注的是维持并肯定他与死者对话的价值”。见Political Ideas as Historical Events:Political Philosophers as Historical Actors,p.152。
(22)Ibid.,p.8.
(23)波考克区分了“人文主义者”和“操作主义者”。操作主义者的特征是:在与古人的“对话”中,他只“欲求抓住那些他注意到的一些言说行动,并用它采施行自己的语言游戏。”而人文主义者则“真正关注的是维持并肯定他与死者对话的价值”。见Political Ideas as Historical Events:Political Philosophers as Historical Actors,p.8。
(24)state of the art,pp.16-17.
(25)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A Methodological Enquiry,p.185.
(26)(27)Ibid.,p.186.
(28)Politics,Language,and Time,p.5.
(29)Ibid.,p.6.
(30)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A Methodological Enquiry,p.190.
(31)Politics,Language,and Time,p.9.
(32)Ibid.,p.8.
(33)Ibid.,p.11.
(34)在确定言说的“意义”方面,有几种不同的路径。一种是意图论和惯例主义者,认为一个给定的言说的意义源自言说者的意图,而言说者的意图则往往要依凭或受制于特定社会的一整套的社会惯例;一种是偶因论者,认为一个言说行为的场合或偶然性会影响到该言说行动的意义;一种是情境主义者,认为意义是与之相关的语言情境的产物。斯金纳是属于第一种路径,也就是企图通过复原作者的“意图”和特定社会的“惯例”来界定言说的意义。但是这种路径遭到一些学者的批评,认为第一,他们攻击意图论者没有认识到这种可能性,也就是言说的真实意义往往不同于所意图的意义,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作者没能意识到他对于言说所做的潜意识或无意识的设计而产生的影响。第二,评论者抱怨,意图作为一种难以理解的、私人的观点,是不可以被用作意义的标准。见Mark Bevir,The Logic of the History of Idea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p.32-34。
(35)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A Methodological Enquiry,pp.189-190.
(36)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in National Context,p.161.
(37)The Concept of a Language and the metier d'historien,p.20.
(38)Mark Bevir,The Logic of the History of Ideas,p.33.
(39)见波考克:《猫头鹰评论自己的羽毛:告别演讲》(The Owl Reviews His Feathers:A Valedictory Lecture)转自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in National Context,p.163.
(40)History and Theory,Vol.29,No.1,1990,p.50.
(41)T.Ball and J.Farr(eds.),Political Innovation and Conceptual Change,Cambridge,1989,p.9,n.4.
(42)The History of PoliticaI Thought in National Context,p.161.
(43)(44)The Logic of the History of Ideas,p.34.
(45)"state of the art",pp.4-5.
(46)Politics,Language,and Time,p.25.
(47)History and Theory,Vol.29,No.1,1990,p.55.
(48)(49)The Concept of a Language and the metier d'historien,p.21.
(50)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in National Context,p.161.
(51)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A Methodological Enquiry,p.195.
(52)Ibid.,p.196.
(53)Politics,Language,and Time,pp.13-14.
(54)Politics,Language,and Time,pp.14-15.
(55)History and Theory,Vol.29,No.1,1990,p.67.
(56)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A Methodological Enquiry,pp.197-198.
(57)对于这本书,国内有多种翻译法。如《马基雅维里时代》、《造就马基雅维里的历史时机》、《马基雅维里的时刻》等,但是最为准确的应该是《马基雅维里式的时刻》。这本书所考察的是自15世纪到18世纪西方世界(意大利、英国和美国)的历史进程所出现的这样一些具有“共同特征”的特定的历史时刻(specific moments),这些时刻以马基雅维里在15世纪的佛罗伦萨共和国所面临的那一特定时刻最为典型,故称之为“马基雅维里式时刻”。在“公民人文主义”这种概念性语言中,这些“时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是:在各种非理性事件中,共和国何以能保持稳定?“美德”何以不受“财富”和“腐化”的威胁?作为对这一共同问题的应对,也留下了共同的思想遗产:如“均衡政府的概念”、“动力性的美德”以及“军队和财产在塑造公民品性中的角色”等。从这个意义上,“马基雅维里的时刻”超越了历史的短暂性和当下性,从而具有了“一种真实和连续的历史”,并演变为“马基雅维里式的时刻”。见J.G.A.Pocock,The Machiavellian Moment:Florentine Political Thought and the Atlantic Republican Tradition,Princeton,1975。
(58)J.G.A.Pocock,"Virtues,Rights and Manners:A Model for Historians of Political Thought," Political Theory,Vol.9,No.3,1981,pp.353-368.
(59)The Concept of a Language and the metier d'historien,p.27.
(60)如在伯克那里发现“古代宪法”或“先例”的语言;如在霍布斯那里发现“启示性预言的语言”(language of apocalyptic prophecy)。
(61)Politics,Language,and Time,p.26.
(62)The Concept of a Language and the metier d'historien,p.22.
(63)state of the art,p.5.
(64)Politics,Language,and Time,p.17.
(65)Political Ideas as Historical Events:Political Philosophers as Historical Actors,p.140.
(66)Ibid.,p.144.
(67)Ibid.,p.146.
(68)Ibid.,pp.146-147.
(69)波考克认为,“话语史研究路径的好处是它可以使我们把思想行为史写成一种行动史(write the history of an intellectual activity as a history of actions),思想行为作为一种行动,它已经影响到其他人,并且也已经影响到人们在其中受到该思想熏陶的环境。”见History and Theory,Vol.29,1990,No.1,p.55。
(70)Politics,Language,and Time,pp.18-19.
(71)因为作者虽然不希望其“言说行动”在所有的情境中被解释,但是他却不能阻止读者在其心灵所能置身的任何一种或几种情境中去诠释作者的“言说行动”。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概念世界的变化,作者的表述肯定会被在各种他所不期想或不能预见的情境中被解释。
(72)The Concept of a Language and the metier d'historien,p.37.
(73)Political Ideas as Historical Events:Political Philosophers as Historical Actors,p.155.
(74)Politics,Language,and Time,pp.32-33.
(75)在这里,仍需指出的是:波考克的“情境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方法论与这种多元价值观是紧密相连的。从表面上看,通过主张恢复“历史的解释”,这种情境主义和历史主义的路径好像限制了概念或思想的可用意义的范围,但实际上,通过复原概念或思想的历史性解释,通过把概念和思想置于不同的、他者的,甚至相互迥异的多元话语中,波考克反而拓展了可用意义的范围,并帮助人们对他们所已接受的信念和诠释产生新的批判性洞见。
(76)引自托巴洛夫2004年在华东师范大学举办的“中法历史夏季研讨班”上的发言稿《作为社会科学建构对象的城市》。
标签:政治论文; 思想史论文; 世界语言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活动理论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读书论文; 历史学家论文; 范式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