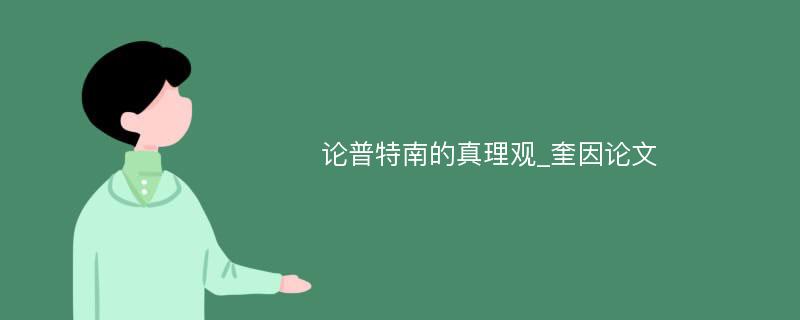
论普特南的真理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真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普特南(Hilary Putnam)是当代美国以“内在实在论”而著称的哲学家。在真理观的问题上,他批判了约定主义,认为真理中有约定的成分,但约定并不是主观任意的;他批判了实证主义,主张真理是解释和辩明,以效用为基础;他对形式主义的真理观进行了批判,反对用命题的句法结构说明命题的意义。普特南认为,真理是理想化的辩明;真理具有相对稳定性和可修正性;真理中渗透着人的价值观和实用因素。在普特南的真理观中,康德的经验论及实用主义的影响是很明显的。
一、约定与真理
在对实证主义的批判中,普特南和奎因(W.V.Quine)在怎么对待分析命题的问题上有不同的观点。
奎因指出:“现代经验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两个教条的基础上的。一是这样一种信仰,即在分析真理,或者说是意义与事实无关的真理与综合真理,或者说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真理之间有某些根本的区别。另一个教条是还原主义:每一个有意义的句子是指称直接经验的术语的某种逻辑构造。这两个教条我认为都是不对的。”[①]
奎因分析了两个基本命题:没有未婚男士是结婚的;没有单身汉是结婚的。他认为第一个命题是逻辑真理,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第二个命题涉及到对同义词的定义,就涉及到经验,因而不是分析命题。
普特南对奎因的第二个命题以及与其相类似的命题的看法是这样的:“这些命题揭示的是不同程度的某些约定和不同程度的系统含义。在‘所有的单身汉是未婚的’这一实例中,我们有最高程度的语言约定和最低程度的系统含义。”[②]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这类命题是分析命题。
为什么要讨论分析命题?普特南说:“我认为,评价不同的逻辑真理的特性,评价自然科学中物理必要真理的多种特性,和在此刻我归结在一起的构架原则——对这些不同种类的陈述的性质进行归类,是一个哲学家能做的最重要的工作。”[③]按照普特南的思想,承认分析命题,不是单纯地作语言分析,而是要用语言工具阐释科学发展中的问题。
在科学史上,动能的定义在爱因斯坦前后有不同的表达式。这是由于爱因斯坦对所有的物理规律都引进了洛伦兹不变关系式。对科学概念发生意义改变的普遍情况,而不仅仅是对动能这一特例,应该作出何种解释?
奎因深信,宣布任何免于修正的陈述无疑都会阻碍科学事业的进步;而一切陈述在原则上的可修正性说明了没有分析命题,只有综合命题。
普特南指出,事实上奎因也并不否认有些人会坚持某些免于修正的陈述,而奎因只是反对在科学中这样做。因此,实质问题是:为什么在科学中有分析/综合的区别?普特南在这个问题上做了解释效用的回答:“首先,为什么我们有分析命题(或者是严格的同义词)?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的本质在于:为什么不这样呢?它并没有什么害处。”[④]
普特南认为,承认分析命题或承认严格的同义词有以下好处:简洁性和解释。在语言的意义上,承认分析命题就是某些陈述在一种语言中免于修正,这种语言的语法免于修正,因而这种语言的用法作为一个整体在某种程度上是固定的。
普特南的分析命题的最主要特征是:(1)它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综合命题,不能被孤立的实验所推翻,也不能通过简单枚举的归纳所确证;(2)主词概念不是多义概念,因而陈述很少有系统意旨。
分析命题的本质是什么?普特南是这样说明的:“我们看来确实有这样的分析命题:它们在实践意义上不可证实,在实践意义上不能被推翻。如果一个人没有认识到这个事实的含义,即在任何理性的生活方式中必然有某些武断的因素,那么,上述说法对他说是一个谜。分析命题是‘由于语法的规律而真’;分析命题是‘由于阐释而真’;分析命题是‘由于隐含的约定而真。”[⑤]这种约定而真,在普特南看来,就是可以理性接受、理性相信的真实。
应该看到,从一切陈述都有经验因素这个意义上讲,普特南是赞同奎因对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区分的。两个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集中在对约定意义的不同看法上。普特南认为,约定程度比较高,约定意义比较稳定的命题就是分析命题;而按照奎因的分析命题标准——不可修正性来看,任何经验约定的命题都不可能是分析命题。
但是,普特南并不赞成约定主义。他明确指出:“有建立在逻辑和语言基础上的分析真理。但是分析真理并不是不可修正的。它们是不可修正的,除非我们修正逻辑或语言,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⑥]普特南认为,量子力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既有约定因素,又不能归结为约定主义。例如,波粒二象性是与概念逻辑的矛盾律相背离的;测不准原理则与命题逻辑的结合律不相吻合。
普特南对约定的态度,还表现在他对奎因正确翻译的不可能性这种观点的批判之中。
奎因的论题背景是这样的:一个语言学家想把一门外族语言翻译成自己的母语。这两种语言不是同源的,而这两个语言团体又有一个最低程度的共享文化基础。这门外族语言是一种原始语言,或被称为“森林语言”,它被这位语言学家首次翻译,这个语言学家没有这种翻译的参照标准。在此背景下,普特南指出:“一个翻译手册被奎因称为分析假说。在这样的背景下构造一个翻译手册就是从事奎因称作的极端翻译的行当。”[⑦]
奎因认为,语言学家面临着选择翻译手册的问题。如果令f[,1]和f[,2]为两个竞争的分析假说,那么,或者f[,1]被选择,或者f[,2]被选择。在奎因看来,正确翻译的概念就只能是相对于f[,1],或者相对于f[,2]而言。普特南指出,奎因的思想是“分析假说的选择是一个约定的问题”[⑧]
普特南认为:“我们不能假定术语‘距离’不变地指称一种物理量而不是另一种物理量。但是它的指称不需要由约定而固定。它能够被自洽所固定。让我们以最大限度的内部自洽与外部自洽的方式来建构整个科学。所谓内部自洽就是像简单性这一类因素,而外部自洽即与经验相一致。”[⑨]即约定并非为所欲为,科学概念、命题的约定要满足自洽性要求。
普特南运用归谬法论证了约定并不是任意的。这个论证如下:我们作出如下定义,即“火星上没有河流”等于“从地球到太阳的距离是九千三百万英里”;我们接受这个定义即分析假说;因此,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三段式:
在火星上没有河流;
光速是每秒十八万六千英里;
所以,光从太阳到地球需要八分种。显然,上述三段式是不可理解的,前提没有提供得出结论的充要条件。由此我们得知,正确的解释不完全取决于任意的约定;翻译的正确性也不完全取决于分析假说的任意选择。
从普特南对分析命题的理性接受和对约定主义的批判中可以看出他对约定在科学认识中的地位有如下的思想:约定是科学认识不可缺少的环节,它使概念、命题具有稳定性;约定的概念、命题是可以修正的;约定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它要受到理论自洽的限制。
二、理想化辩明
普特南的真理观是在批判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的实证主义和塔斯基(Alfred Tarski)——戴维森(Donold Davidson)真理形式的基础上产生的。
卡尔纳普的现象主义有两方面的:(1)本体论现象主义:事物是感觉的集合;(2)事物语句可以翻译成感觉语句而保持真值不变。
卡尔纳普关于这种“翻译”的典型例证是由感觉证明一把椅子的存在。即在正常光线条件下,一个正常人的视野和触觉中出现了椅子的形象;根据现象主义的两条原则,可以翻译成“椅子存在”这样一种事物陈述。
卡尔纳普的现象主义遭到了许多批评。牛津学派的奥斯丁(Austin)和斯特劳森(Strawson)认为,感觉语言是不可能的。即使在一个单独的感觉语句中,也包含着寄生在事物观念上的术语。
归纳实在论者威廉斯(Donald Williams)反对“翻译”的说法,主张从感觉到事物是解释,“事物理论”是比“无物理论”更好的、简单、自洽的理论,因此,事物是存在的。
普特南的基本态度是解释效用:“语言不仅是用来作解释,也用来作描述。一个比我们目前给予的更保险的描述有可能被给出而不预设事物的存在,如果我们有某些原因要避免这个预设。例如,采用感觉语言。但是事物语言的描述的效用当然是我们为接受它而辩明的一部分。”[⑩]注意归纳实在论和普特南的区别:前者是用解释说明“事物”;后者是用“事物”说明解释。
普特南并不否认卡尔纳普关于构造一套感觉语言的努力,因为这是实证主义使哲学命题更为准确的尝试之一。普特南所指出的是划分感觉语言和事物语言的不可能性。普特南认为,在科学活动中,至少某些事物观念必须在任何语言中被看作是“始原性的”,而这样的语言对于科学已足以够用。
在指称问题上,普特南批判了罗素(Bertrand Russel)的一般名词的观点,指出一般名词并不与属于某个类的必要和充分条件的集合相等。普特南指出,名词在使用过程中,其意义是变化的。例如,在两百年以前,化学家们关于酸的标准是:水溶性;在水溶液中有酸味;使石蕊试纸变红,等等。而天天的化学家谈论同一个话题酸,但是标准却是:质子授与者。现代化学中酸的范围就大大扩大了。普特南认为,术语的使用立足于“标准”之上,而“标准”不是完善的指示词。“但是这种模糊性正是我们要强调的:被接受的标准的变化反映了我们对X具有越来越多的知识这个事实。”[(11)]
在专名问题上,普特南赞成克里普克(Saul Kripke)对罗素的批判。例如,罗素以凯撤是一个罗马将军,他率兵越过卢比孔河作战,打败了庞培这样一个历史事实,说明这样一个凯撤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专名。克里普克认为,如果凯撤是这样一个专名的话,真实的凯撤如果没有击败庞培,他就不是凯撤。这显然是荒谬的。由此看来,罗素的专名理论是不对的。
普特南对罗素关于一般名词的批判和克里普克对罗素的专名的批判的实质是一样的:对象在接受名称的洗礼之初不可能有完整的定义。因而对于指称可以这样理解:指称是稳定的,但指称的含义是变化的。普特南经常论述的一个典型事例就是温度。温度是一种物理量的指称,而后来出现的理论解释:分子平均动能则是这个指称的含义的扩展。
在指称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讨论命题。如果说指称是一个确定性的问题的话,那么命题则有正确错误之分,这就是真理问题。
塔斯基的真理形式是:“P”是真的当且仅当P。例如:“存在一个真实的外部世界”当且仅当存在一个真实的外部世界。
普特南把塔斯基的真理形式叫做“去括号”的真理观;人们可以对塔斯基形式作唯物主义解释,也可以作可证实,或可证伪,或可以概率证实,或其它的各种解释。普特南进一步指出:“按这种观点。‘真实’令人惊奇地成了一个哲学中性的观念。‘真实’成了‘语意强调’的工具:把断定从‘对象语言’提升到元语言,而这个工具并未在认识论上或形而上学的含义上承认任何东西。”[(12)]普特南的批评是很中肯的。因为我们不能理解“P”和P的关系的确切含义;同时,无论塔斯基是否为自然语言构造形式化表述,塔斯基形式无助于我们对P的理解。
戴维森把塔斯基的真理形式当作是对语句意义的说明。语句的意义是由句法结构和单词意义决定的。与塔斯基不一样,戴维森是用元语言来解释或翻译对象语言;而塔斯基则以意义的对应来说明真理。
戴维森的真理形式是:S是T当且仅当P。即对象语句S只有元语句P这样一种正确解释。戴维森形式的意义有三个:它给予了保留真值的翻译的形式;从这种形式中可以产生无限新的命题;避免哲学家和逻辑学家任意选择真值条件以使命题准确,至少在形式上是如此。同时,戴维森对翻译的非确定性以及语境问题也作了适当的说明。
戴维森宣称:“一个意义的理论(在我的温和地保留的含义上)是一个经验理论,并且它的功用是解释一种自然语言的机理。像任何其它的理论一样,它也许会通过比较它的某些结果与事实而得到检验。”[(13)]而这种“对应”理论正是普特南批判塔斯基——戴维森真理形式的焦点之一。
普特南对塔斯基——戴维森真理形式的批判归结为以下两点:(1)塔斯基——戴维森形式是哲学中性的真理形式描述,没有说明真理是什么;(2)它含有对应理论,没有说明真理是什么;(2)它含有对应理论,即把符号与非概念化实在作比较,是不自洽的。
在此基础上,普特南提出了“内在实在论”的真理观:真理是理想化辩明。理想化辩明有如下特征:(1)它是一种高度近似的描述,有解释效用,如无摩擦平面;(2)一个陈述及其反面不能同时被辩明;(3)被辩明的陈述和辩明的方法都容许修正;(4)它与形而上学实在论相对立,即不承认与思想无关的客体。
三、真理的价值基础
普特南的真理观是建立在人的价值观基础上的。他在谈到科学活动中的选择性时说:“奎因指出了这样一种思想,即科学的进展就像一种正规句法构造一样。这种说法是一种神话。当理论与被认为的事实发生冲突时,我们有时放弃理论。有时放弃‘事实’;当理论之间发生冲突时,并不能总是依据已知的观测事实作出决定。”[(14)]这里就涉及到人的认知价值观问题,如我们通常所讲的简单性、自洽性、预见性以及我们对世界的总体看法等。
普特南把自洽、简单等观念称为行动引导术语,它表明人们在科学活动中的一种先验态度。普特南认为,所有的价值观都有主观色彩。如果说道德价值具有主观性,那么,认知价值也具有主观性。
认知价值在科学活动中是必要的。然而普特南指出:“辩明、自洽、简单性、指称、真理等等,从认识的观点看,都表现出了与好和善同样的问题。所有这些都不能还原成物理概念;它们都不是由准确的句法规律所决定的。”[(15)]一句话,认知概念并非一成不变。
例如,普特南认为,自洽的观念是一个非静态的认知观念,是在历史上起变化的一个观念。我们如果要求自洽的观念具有永恒的价值,则必然要求未来与过去相对于自然史、科学史是成立的,然而这是不可能的。因此,自洽是一个历史的认知价值观念。
又如,对于简单性,普特南指出:“使用‘选择与证据相容的最佳理论’的困难是它也许是不对的,或者也许将会是不对的,尽管它能够构造整个科学(在一个确定的时代)。”[(16)]也就是说,选择简单性有可能牺牲正确性。普特南进一步说明,实在论者也许会尽可能地在其知识背景中选择真实性大的最简假说,但是通常的简单性选择操作不是这样,而是以效用为原则。“当观测数据与理论的要求出现明显的矛盾时,或简单性与守恒原理正相反对时,抛弃一方是必然的,而如何抛弃一方还没有正规的规则或方法。”[(17)]
普特南对预见性持保留的批判态度:“逻辑实证主义宣称,任何陈述,如果不能间接地预见,我们(在经验哲学中)认识的最终出发点感觉刺激,就不能具有认知意义。我认为,陈述自身,甚至是间接地,也不能改善我们预见任何事情的能力。”[(18)]这就是说,我们的认知价值观预设了这种预见性。
普特南也讲客观性,但这种客观性只能是在人的价值系统中的客观性,或者叫做带人性的实在论。普特南在批判科学主义和怀疑主义时说:“第三种可能性是接受这样一种立场,即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这样一种存在,在不反映我们的兴趣和价值的情况下,我们不能有这个世界的图象;但是,我们又承认这一点,尽管某些兴趣和价值不可排除,总有一些世界的图象更好些。这也许意味着放弃一种形而上学的客观画面,但它并不意味着放弃这种观点——杜威把它称为‘问题状况的客观解决’——处于不同地点、时间的问题的客观解决,这和对‘与认识无关’的问题的‘绝对’答案不一样。然而这就是足够的客观性。”[(19)]普特南的思想有明显的康德主义特征,尤其是七十年代中期以后在批判形而上学实在论时是以康德经验论为武器的。
至此,我们可以对普特南的真理观的重要特征作一个小结:(1)真理在内容和方法上都容许随着科学认识的发展而修正;(2)认知价值观使真理具有人性的色彩;(3)解释效用始终是制约真理的重要因素。
普特南的真理观是在批判实证主义,重视语意分析的背景下诞生的。它重新恢愎了传统哲学真理观的系统研究,在现代西方哲学界有一定的影响。
注释:
[①]Willard Van Orman Quine:Fron a Logical Point of View,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0,PP20.
[②]Hilary Putnam:Mind,Language and Realit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0,PP39.
[③]同[②],PP41.
[④]同[②],PP56.
[⑤]同[②],PP68.
[⑥]Hilary Putnam:Realism and Reas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PP97.
[⑦]同[②],PP159.
[⑧]同[②],PP161.
[⑨]同[②],PP165.
[⑩]同[②],PP24.
[(11)]同[②],PP311.
[(12)]同[⑥],PP76.
[(13)]Donald Davidson: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A.P.Martinich ed.),Q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PP76.
[(14)]Hilary Putnam:Realism with a Human Fac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PP137.
[(15)]同[(14)],PP141.
[(16)]同[②],PP212.
[(17)]同[(14)],PP138.
[(18)]同[(14)],PP149.
[(19)]同[(14)],PP1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