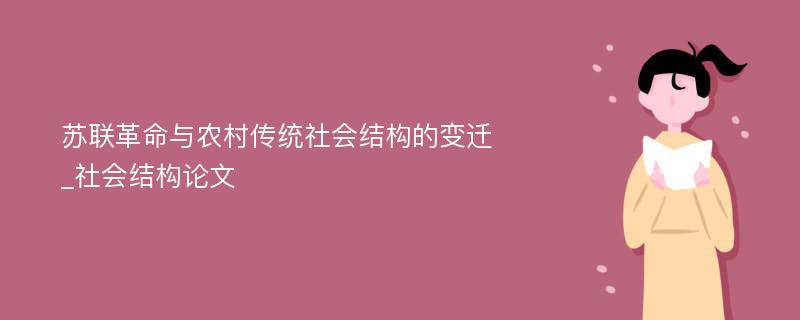
苏区革命与乡村传统社会结构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区论文,乡村论文,传统论文,结构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9.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448(2006 )03—0072—07
关于苏区革命对乡村传统社会的变迁作用,以往史学界多有涉及,尽管视角不同,但基本上都认为,苏区革命使乡村传统社会产生了结构性的变革,如汤家庆《中央苏区的社会变革与思想文化》、李小平《土地改革与闽西苏区社会结构的变化》、何友良《论苏区社会变革的特点和意义》等。研究苏区社会史的代表作,何友良研究员的《中华苏维埃区域社会变动史》一书,从政治权力结构、社会阶级结构、两性关系结构和苏区农民社会生活等方面系统地论述了革命对乡村社会变迁所产生的影响,认为革命使苏区乡村发生了“富有成效的社会变迁”和“深刻的社会变动”[1](301页)。
布罗代尔提出的“长时段”理论是社会史研究中最重要的理论之一[2]。“长时段”理论认为,革命只不过是历史长河中溅起的小浪花,社会结构则是历史长河中的潜流,它长时间不变或者变化极慢,是“十分耐久的实在”[3]。根据这一理论,笔者以为中国乡村的传统社会结构,不可能由于短短的几年土地革命而发生“富有成效的社会变迁”和“深刻的社会变动”。由于已有研究成果对中共推动苏区农村社会变迁的措施及农村社会剧变情况,有太多的论述,此处不再赘言。本文仅从乡村传统社会结构及其弹性、革命对乡村传统社会结构冲击的有限性、革命后乡村传统社会结构的反弹三个方面考察苏区革命对乡村传统社会变迁的作用,旨在说明发生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苏区革命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乡村传统的社会结构,经过苏区革命,农村社会结构依然还是传统的农村社会结构。
一 土地革命前江西乡村传统社会结构及其弹性
江西长期以来就是一个相对完整、相对闭合的地理单元。从境外看,江西的地理环境具有明显的封闭性,省境四周高,中间低,东、南、西面分布着怀玉山、武夷山、大庾岭、九连山、井冈山、幕阜山等一系列山脉,把江西与邻省分隔开来。从境内看,江西有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修水五大河,可谓水网密布,河道纵横。但江西的水系均发源于四周的群山,随地势由四周流向中间的鄱阳湖,除了在北面的湖口能与长江连接外,江西所有的河道都是在境内打圈。在近代公路、铁路交通兴起以前,江西是一个难进难出的“死盆地”。江西的地理环境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宜农性。其地形特点是周边山脉的内侧丘陵广亘,整个地势,由外及里渐次向鄱阳湖倾斜,形成了众多的丘陵与河间盆地,如吉泰盆地等。五大河中下游,分布着冲积平原,如鄱阳湖平原等。江西的丘陵、盆地和鄱阳湖平原地带,土地肥沃,气候温和,日照充足,四季分明,水源充足,非常适宜于农业耕作,无数的传统村落就分布于其间。
地理环境就像历史长河的河床,它在很大程度上规定着社会结构演变的格局和方向。由于地理环境具有封闭性和宜农性,所以,江西农村社会结构在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中相对地保持了较多的传统社会的特色并具有巨大的弹性。
近代江西农村社会结构的显著特点之一是在经济上保留了比较多的传统的自然经济和地主制经济。由于江西地理环境具有“宜农性”,历史上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江西十分发达,这种传统从古代一直延续到土地革命前夕。诸多的史料记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例如,《赣州府志》记载:清同治年间,赣南一带“一般农民以不事商贾为光荣”;《九江府志》载:赣北各乡农村“尚农业,罕事工商……无见异迁物之民”;《广信府志》载:赣东各县“粟麦耕畜之产足以自给,不仰给于外,亦不能灌输于外”;《南昌县志》载:宣统年间,即使是经济最发达的南昌县各地农民,也是“耕以足食,织以致余”;直到土地革命前夕,赣西北广大农村“经济本来是一个小农经济区域,……农民家给人足,有性颇懒。……交易还是‘日中而市’的逢圩办法,如宁冈的茅坪,遂川之黄垇、水井等是。有些地方还是杵臼时代。……人民多务农,商人及读书的占极少数,……农民在红军未来之前,颇觉安居乐业,有天下太平的气象,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老死不相往来的神气”[4](18—20页)。
近代江西农村社会结构的显著特点之二是在社会组织上保留了比较多的宗法家族制度。近代江西是宗族制度最为盛行的地区之一,清代李绂评价说:江西“聚族而居,族必有祠,宗必有谱,尊祖敬宗收族之谊,海内未可或先”[5]。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土地革命之前。如1928年毛泽东调查井冈山根据地几县的情况后说,农村“社会组织是普遍地以一姓为单位的家族组织”,“无论哪一县,封建的家族组织分布普遍,多是一姓一个村子,或一姓几个村子”[6](69页)。1929年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同样也提到赣西南广大农村地区“社会组织,大多是聚族而居”[4](14页)。对这种情况,当年参加革命的人士也多有提及,如陈奇涵回忆说,革命前江西农村“宗族社会的传统习气浓厚,规模宏大的宗祠到处林立”[7](1页)。肖华在回忆中也谈到,革命前兴国“每个姓都有一至数个祠堂,一个祠堂可以驻一个连”[7](392页)。这类记载比比皆是,说明直到土地革命前夕江西农村依然是一个典型的宗族社会。
近代江西农村社会结构的显著特点之三是在思想文化方面保留了比较多的传统的封建文化。在自然经济繁荣的基础上,江西传统文化也非常发达。江西古代书院文化之发达是学术界公认的,江西不仅是古代书院文化的发祥地之一,而且其建置数量之多亦居全国各省前列,其中白鹿洞书院、鹅湖书院、白鹭洲书院举世闻名,其办学质量之高为时人交口称赞。古代江西的科举文化也非常发达,据统计,唐至明清江西考取进士、状元的人数一直位居全国各省前列。历史上出现过一大批文化名人,诸如陶渊明、欧阳修、王安石、曾巩、朱熹等,他们提出了许多有深刻影响力的理论和学说。江西是程朱理学的发源地,封建理学的“义理之说”在江西有着较为深刻的影响,而且根深蒂固。江西发达的传统文化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演化成世代留传下来的文化传统,成为规范人们行为的依据和标准。到了近代,由于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江西人形成了明显的落后保守的人格特征。首先,江西人有浓厚的小农意识。江西土肥水美,气候适宜,在漫长的小农经济时代,江西的确安稳而又富足。这种情况,削减了江西人拼搏奋斗精神,使江西人容易满足现状,不思积极进取,缺少开拓创新精神。因此,近代以来江西人那种土里土气、安于贫穷的老俵形象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8](242—246页)。其次,江西人思想封闭保守。江西地处内陆,交通不便,信息难得,导致江西人视野比较狭窄,容易拒绝新事物。比如,近代江西并不是传教士活动最活跃的省份,却成为教案最突出的地区之一;洋务时期,其他各省洋务企业办得红红火火,江西却一个都没办;戊戌变法时期,全国各地举办新式学堂,江西经多方努力,有影响的学堂还是没办成,主办者只能发出“江省守旧人多,开化难于他省”的感慨[9](297页)。以上说明近代江西还是传统思想文化的一统天下。
综上所述,革命前的江西农村社会是一个典型的传统社会。它以家族作为社会的基本组织,这种家族组织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同农村中传统文化牢固地纠缠在一起。宗族制度是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孪生物,小农经济以单个家庭为单位组织生产,宗族制度同这种生产方式正好相适应;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宗族主义和小农意识的因素,如“尊老爱幼”、“三纲五常”、“重农抑商”等,与宗族制度和小农经济互相支持、互为表里。传统农村社会的三大结构因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环扣一环,使江西农村社会结构具有巨大的弹性,成为一个打不烂、推不跨的铸件。革命就是要改变这个社会结构,由于这个社会结构具有巨大的弹性,因而增加了革命对农村社会结构变革的难度。
二 革命对乡村传统社会结构冲击的有限性
在苏区革命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江西农村传统社会结构进行解构,力图以新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思想文化结构取而代之。但是,由于乡村传统社会结构具有巨大的弹性,革命对这个结构的冲击效果是非常有限的,并未触动农村社会深层次结构。
1.在社会组织结构方面
中共建立了农村各级苏维埃政权,取代传统的宗族权力;同时,围绕着政权这个核心,建立了工会、贫农团和妇代会等各种群众团体,几乎每个群众都加入了革命团体,宗族的社会功能被各种新型社会组织所取代;原先作为宗族活动场所的祠堂也变成了各级苏维埃政府的办公场所;族田族产被没收,断绝了宗族活动的经济来源;阶级与阶级斗争观念被导入苏区,家族文化受到严重冲击。
然而,革命对宗族势力的打击或取缔,只是摧毁了宗族活动的外在形式,并未动摇宗族组织的根基。在强大的革命势力面前,宗族势力显得孤单力薄,只能让步,但这只是宗族势力对革命的适应,不可就此认为宗族就此消亡。实际情况是,在苏区,许多农民并没有摆脱宗族的束缚,在革命中宗族势力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在乡村中还一直存在着。
第一,革命并没有消除宗族势力。据1932年江西省苏的报告,赣南苏区“农民的氏族观念特别浓厚,对于同姓豪绅地主富农表示妥协,同时过去大姓压小姓的传统到现在许多苏区中还存在”[4](445页)。在赣东北苏区,农民往往以族为单位,参加革命或者反对革命[10](296页)。在分配土地过程中农民“封建的宗族观念很严重,整村瞒田”[11](287页),即使在中共组织内部也有严重的宗族势力存在。毛泽东就发现:“党在村落中的组织,因居住关系,许多是一姓的党员为一个支部,支部会议简直就是家族会议。在这种情形下,‘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6](74页)由此看来,宗族势力在苏区各地依然存在是不争的事实。
第二,革命不仅没有消除宗族势力,反而被迫利用宗族势力。乡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在革命中,农民信任对象,并不是正式的政治组织,而是宗亲熟人。因此,革命的推动有时也不能不利用宗族势力。《铜鼓县志》载:在铜鼓县“各区党组织发展工作,初期多假作游医商贩,走亲访友进行”;《弋阳县志》载:在弋阳的中共党员“利用亲邻关系,秘密发展组织”;在东固革命者“利用家族关系,以东固附近一带山林为基础向豪绅游击”[12](167页)。事实证明,利用宗族势力有利于革命的发展。如邵式平之所以能在弋阳发动革命,就是因为他的家族有相当的势力。兴国农民运动领导人肖华也认为:“姓氏关系有效地掩护了革命势力的生长和发展,致使兴国县的党组织,一直没有遭到严重的破坏。”[7](429页)。
第三,反抗中共的宗族势力在苏区还大量存在。革命把宗族首领们作为重点打击的对象。因此,宗族首领们通常是反对革命的,这必然要影响某些宗族对革命的态度,使某些宗族与革命对抗。于都县北乡一带宗族首领敌视革命,这里的宗族势力成为苏区时期反对革命的最顽固的宗族堡垒[12](209页)。1931年冬,宁都宗族首领逃至翠微峰,“彼等与眷属同来,……与红军对抗数年”[13](35页)。宁冈县土客籍的矛盾很大,边界“八月失败”后,土籍宗族在族长的带领下大部分反水,挂起白带子带领白军烧屋搜山。东固的宗族地主,则在国民党政府名义下,组织靖卫团、挨户团与革命对抗[14](165—173页)。1930年8月,赣东北红军在鄱阳八齐乡遭到方、蔡两姓宗族族众五千余人的反抗[15]。
2.在经济结构方面
苏区通过土地革命暂时消灭了地主制经济,废除了封建租佃剥削关系,在平分土地的基础上逐步建立了农民土地所有制。
然而,尽管苏区原有的社会资源占有格局被打破,社会财富在不同阶级中进行了重新分配。但是,中国传统社会那种以家庭为单位,小农业和小手工业相结合经济结构并没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以土地分配比较彻底的寻乌为例,据毛泽东的调查,寻乌大多数地方分田后,农民的收获,除去口粮外,“不敷衣服、油盐、社会交际(婚丧年节)的日常用度”,因此,农民还必须兼做手工、挑脚、小贩,才能维持家计[16](170页)。在兴国调查中,毛泽东观察的8个农民家庭,其情形亦是如此[16](184页)。这说明革命期间农村那种小农业和家庭副业相结合的经济结构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有关调查材料提到苏区:“各县分田,多少固不一致,但平均每人约分2亩,每家若以5口计,则每家约有10亩”[17](44页),农民以家庭为单位,经营10亩土地,这是典型的小农经营。
在苏区以农业为主,以粮食生产为主的传统农业产业结构也没有改变。苏区党和政府始终强调:“农业生产是我们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6](117页)。在农业作物的种植上,则要求“发展农业生产的要项:第一是谷米,第二是杂粮(番薯、豆子、花生、麦子、高粱)”,把粮食的生产放在首要位置[4](231页)。这种生产明显的是为了满足本区域消费的需要,而不是为了市场。
苏区革命后通过打土豪、分田地,原来经济意义上的地主、富农、雇农都基本上不存在了,出现了明显的“中、贫农化”即小农化趋向。通过按人口平均分配,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农民实际上都变成了清一色的小农。小农是小商品生产者,是一个处于经常变动之中的社会阶层,由于各个小农家庭的劳动条件不同,小农不可能长期处于“平均”的状态之中,两极分化是必然的趋势。因此,“一字型”的经济结构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一俟适当环境和条件,就必然要弹回到原来的结构的状态之中,这是由经济发展规律所决定的。
经济结构是社会结构的基础,由于苏区小农经济结构没有得到根本性改造,因此建立在其之上的整个农村社会结构也不可能有大的变化。
3.在思想文化结构方面
苏区党和政府在战争环境和物质匮乏的艰难条件下,建立了极富特点的文化教育制度,同时通过强大的思想文化宣传攻势,向人们宣传革命思想,产生了一定的效果。史料记载说:“苏府范围内的农民,无论男女老幼……都痛恨地主阶级。打倒帝国主义,拥护苏维埃及共产党的主张,几乎成了每个群众的口头禅。……没有人敬神,菩萨都烧了,庙宇祠堂变成了农民工人士兵的政府办公室,或者是游戏场。许多农民家里以前供着家神‘天地君亲师位’的,现在都换成了‘马克思及革命先烈精神’,从前过年度节,写些封建对联,现在都是写革命对联……”[4](355 —356页) 这种情况说明,苏区农民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的确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但传统的思想文化在千百年的流传中,已成为中国民间百姓的基本的生活方式,已深深渗入了中国人的血液和骨髓之中。“文化传统是一个巨大而深厚的存量,它是实实在在的边际性变革,也可以说,文化传统不是剥蚀的旧墙,不会轻易地在社会变革中消失”[18](190页)。因此,革命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消灭传统文化思想。实际上,在苏区,无论是红军、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还是普通老百姓,都没有完全摆脱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毛泽东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6](85页),如“极端民主化的根苗还深种在许多同志的思想中”,“红军官兵中的绝对平均主义还很厉害”等等,毛泽东认为这些不正确思想的来源,都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6](91页)。
1932年12月5日,《红色中华》第43期第5版,有一篇题为《丰山区政府的形形色色》的文章指出,丰山区苏维埃政府大门口扎着一个纸牌楼,上面帖着八仙过海图;大厅两旁新贴全幅二十四孝图共4张;二十四孝图旁边,贴着老寿星图2张;大厅中间,从前放神位的地方,贴着马克思、列宁的像及诸位烈士之位,把革命领袖当作菩萨来供奉。文章严厉批评丰山区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具有浓厚的封建思想,严重缺乏阶级斗争的精神。
在普通农民中,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更是随处可见。比如毛泽东就提到苏区农民喜欢家长制,“封建时代独裁专断的恶习深种于群众乃至一般党员头脑中,一时扫除不净,遇事贪图便利,不喜欢麻烦的民主制度”[6](72页)。传统风俗习惯在苏区也普遍存在。1933年3月《红色中华》第59期的一篇文章说到:苏区很多乡村“都是籍着纪念乡苏的名义来维持封建的风俗,例如一月半、七月半等等……现在为了敷衍反封建、反扛菩萨的斗争,各乡苏都把这些封建的季节,改为纪念乡苏的日期,这样藉着纪念乡苏的名义,来维持封建残余,真是名正言顺,一举两得”。
可见,传统思想文化在苏区广泛存在。传统思想文化转变的迟缓性,在这里深刻地显现出来。
综上所述,苏区革命时期,具有很大的弹性的中国乡村传统社会结构,虽然在强大的革命势力的压力之下,有了浅层次的变化,但传统社会深层次结构依然在以各种方式保存了自己。
三 乡村传统社会结构的回复
国民党占领苏区后,在原苏区地区立即进行了社会秩序的恢复和重建,随之,原苏区农村的社会结构迅速向革命前的社会结构回归。
1.经济结构的恢复
1934年国民党颁发了《剿匪区内关于复兴农村之各种条规》,规定:“农村复兴委员会,处理被匪分散之田地,及其他不动产所引起之纠纷,一律以发还原主,确定其所有权为原则。”[19](1056页)这是国民党收复苏区后处理土地问题的核心政策。按照这个政策,农村复兴委员会在处理土地和业权的过程中,所有权一经认定,土地(也包括其他财产)一律立即归还原主。革命失败后,原苏区地主土地所有权的恢复进展得非常顺利。1935年3月《民国江西日报》记者钟贡勋在江西农村考察时反映“土地问题,依行营规定原则办理,尚无多大纠纷”[20]。有时尽管田契无存,“然有地方之舆论,物归原主,故土地所有权之争执,未见严重也”。也就是说,地主土地所有权的恢复,相当快捷。
随着土地、财产“归还原主”政策的实施,革命时期苏区农民分得的土地迅速丧失。国民党人汪浩在1935年对江西等省31个县进行3个月的实地调查后,不得不承认:“收复后,土地关系不仅未加改善,且有更加恶化的趋势,……大多的农民地少或无地如故也,而收复较久之区,甚至苛捐杂税之多,亦如故也。前此因土地关系之恶劣,致为赤匪所乘,而酿成空前未有之匪患,今若不加改善,其前途殊堪隐忧耳。”[17](52页)
与农村土地所有制结构回归到了革命以前的状态相适应,革命后原有的租佃关系也迅速得到恢复。据1936年闵挽澜《大动乱后的贵溪农村》一文,在赣东北地区“农民经过一个大动乱之后,……不是给人家雇佣,便只好租佃地主的田地耕种。……租佃也一样的苛刻,这里有一个普遍的特征,即都是实行对分租法。所谓对分租法,便是以该田收入总数的一半,作为佃种的租价,在这个限度以下是没有的。……地主、富农除了用雇佣和租佃方式剥削农民的血汗外,还利用高利贷来敲剥农民的骨髓。……这样重的利息,农民时常会发生信用恐慌,地主高利贷者便运用官府的法律来达到本息俱还的目的,所以农民因欠债而捉将官里去的是屡见不鲜的。”[21](70—71页) 可见革命前的租佃剥削关系和高利贷剥削关系在赣东北农村已完全恢复。
革命后的农村经济依然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从经营方式看,据1935年调查:江西农村每家农户经营的土地面积:5亩以下占20%;5—10亩占31%;10—15亩占22%;平均为11.67亩[17](20页),同革命前、革命中的经营规模相比,没有明显的变化;从农产品流向看,水稻是江西农村的主要农产品,种植面积占耕地面积的绝大部分,据1935年调查,水稻的用途是:自用占59.17%,交租占34.87%,出售占5.96%[22](107页),绝大部分是用于自己消费和交租。这说明,革命失败后的农村依然是典型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2.农村社会组织结构的回归
首先是宗族势力的恢复。国民党占领苏区后,迅速恢复了宗族原有的资产,原苏区地区各宗族祠产已查出并归还其私有权,宗族制度存在的经济基础得以重建。革命失败后农村聚族而居的情况也依然如故,如1935年国民党派往农村的特派土地督察员就发现,“安远、寻乌、信丰三县,大都聚族而居”[23]。在革命失败后的二三年内,农村那种“祠堂林立”的局面再次显现。据1938年对江西214村的典型调查,“计所调查的214村之中,共有祠堂269个,平均每村有祠堂1.3个”,各村“农民对于祠堂至为重视”,利用祠堂进行祭祀、办理婚丧等活动,以集结宗族势力。许多祠堂也重新制定了祠规,其内容主要包括“严防盗匪,禁止赌博,保护青苗,不准砍树……”等等,祠堂恢复了革命前的旧制[22](163页)。与此同时,地主豪绅又重新成为族权的主宰者,宗族的各项社会功能也逐步恢复[24](55页)。以上说明,宗族社会在革命失败后不久即得以基本恢复。
其次是保甲制度反弹。保甲制作为一种乡村制度,是中国古老的乡村制度。国民党政府在确立统治的最初几年,在农村基层推行的是乡村自治制度,仿照西方和日本实行区——乡镇——闾——邻的政权体制,这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截至1931年,江西划定“自治区者有67县402区,成立区公所者379所,编定乡、镇、闾、邻者21县”[25](297页),古老的保甲制度行将退出历史舞台。然而,国民党为了对付革命于1931年开始筹划在江西恢复保甲制度,至1935年12月江西全省83县共编练2648联保、26584保、269066甲[25](210页),保甲组织已覆盖全省城乡各个角落。此次推行的保甲制度同以前的保甲制度相比,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差不多。其编练之法也是“以户为单位,户立户长,十户为甲,甲设甲长,十甲为保,保设保长”[26](210页)。保甲制度的内容也还是实行互保连坐责任制,实行“五家连保”法,规定一家出事,五家同当;一户通匪,五户同罪,使居民互相监督,互相制约[26](7页)。通过保甲制度的推行,地主豪绅又操纵了各地乡村行政大权,“保长、联保长、以至区长,都是地方上有钱人充当的,没有一处贫民可以参杂进去,而这种保长、联保长、区长便是等级的地方官。保甲条例上明白规定了,这种职官有设法庭、办警察、审问地方讼争案件的义务。这样,地主、豪绅、高利贷者在他的剥削过程中,更得了一个指挥如意的工具,而广大农民在这个严密的组织之下也难于思乱了”[21](70—71页)。由上可见,在保甲制度之下,地主豪绅阶级重新掌握了乡村政治权力,广大农民在政治上被重新推入了受压迫的悲惨境地。
3.思想文化结构的回复
美国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在其《乡民社会与文化》一书中提出了文化结构的“大传统”和“小传统”概念。他认为,在文化结构中,存在着两个层次的文化传统。所谓大传统一般是指社会上层阶级:贵族、士绅、知识分子所代表的主流文化,而所谓的小传统是指乡民所代表的民间文化,主要以农民为载体。大传统文化反映官方的意识形态,其权威来源于国家权力的给予和支持,体现的是权力执掌者的权威与意图,它会随着政权的更替而发生显著的变化。小传统文化则由农民的传统价值、规范以及习惯构成,反映的是社会的下层、非正式的民间意识,其形成、变异、延续和发展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文化的整体结构中,大传统和小传统是互动互补的,大传统引导文化的方向,小传统提供文化的基础。只有伴随着社会的长期变迁、乡村与其外部世界紧密的关联,大传统文化才逐渐为农民所认知和接受。如若不顾小传统文化,把大传统文化强行输入农村,往往会收到事倍功半的后果。
从小传统文化来看,苏区党和政府以行政的、宣传的、教育的等等手段向农民灌输革命文化,试图以革命的意识形态替代传统文化,这样做的结果,虽然能导致农村小传统文化的某些变化,但在很大程度上,它只是对大传统文化的一种适应。据《江西农村调查》,革命失败后,江西农村小传统文化很快恢复了原状。“在所调查的214村中,有庙宇所在者115村,计有庙宇175个,皆以求财、求福、求子、求五谷丰登、求人畜安吉者居多,盖因农民向无一定之信仰,所谓‘见庙即进,见佛即拜’即其明证,然考其所以致此之由者,实因农民发财心切,以冀接济其穷,希望子孙繁殖,得继续其后,又因墨守成规,漫无组织,尤为农民牢不可破之心理”[22](158页),农村小文化传统基本上依然如故。
从大传统文化来看,在革命失败后也有一个回归的过程。革命失败后,为了消除中共在原苏区地区的影响,国民党举办了“特种教育”。其要点是:“宣扬三民主义,揭破赤匪之错误与罪恶,纠正或指导民众之思想与言行”。据教育厅长程时煃在全省义务教育行政会议上的说法:特种教育“在剿匪区内已著宏效”[27](25页)。同时,蒋介石亲自在南昌发动了新生活运动,力图恢复在我国流传了数千年的封建道德,这就是所谓的“礼义廉耻”。新生活运动的基本精神就是要重建传统的思想道德结构。
综上所述,革命失败后江西农村的经济结构、社会组织结构、思想文化结构基本上回到了革命之前的状态。
四 结论
不可否认,苏区党和政府通过建立农村各级苏维埃政权、开展土地革命、进行阶级斗争等措施,用革命的方法变革农村社会,在一段时期内的确使江西农村社会在经济结构、社会组织结构、思想文化结构等方面发生显著的变化。
但是,由于乡村传统社会结构具有巨大的弹性,因而在革命的进程中,它对革命势力的冲击进行了顽强的反冲击,尽管其浅层次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但传统社会结构的内核依然保存下来,并在苏区革命失败后,得到了全面的恢复。总之,发生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苏区革命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乡村传统的社会结构。从总体上来看,革命后的农村社会结构还是革命前的那个结构,农民依然贫穷,农村依然萧条,农业依然落后。
由此看来,乡村传统社会结构是由浅层次结构和深层次结构二部分组成的。浅层次结构反映的是当政者的意图,它随着政权的更替而发生变化。深层次结构反映的是历史长期形成的社会传统,它长期不变或变化极缓。革命引起的乡村传统社会浅层次结构的变动,对深层次结构的变迁有导向作用,但是革命能否引导深层次结构发生深刻的变革,关键要看革命对构成这个深层次结构的诸要素是否进行了长期的、连续的冲击,尤其是要看社会生产力是否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如果革命很快遭到失败,又没有使构建这种社会结构的经济基础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那么,任何建立在其基础之上的社会结构的变迁都是不稳定的,一般都是要复原的。当然,这种复原不是简单的重复,它不可避免地要留下革命的痕迹,并影响革命后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的进程。农村传统社会结构就在这种变与不变之中,辩证地向前发展着。
收稿日期:2006—03—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