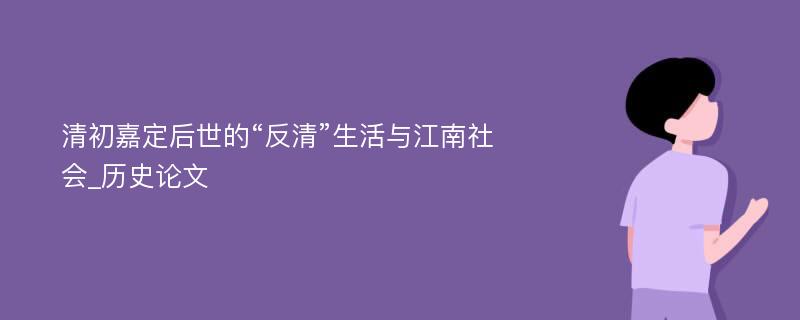
清初嘉定侯氏的“抗清”生活与江南社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嘉定论文,清初论文,江南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1)08-0123-12
一、嘉定侯氏
崇祯十七年(1644年),大明王朝在北方因李自成农民军与关外清兵先后进入北京城,而结束了其统治。江南一带继续维持的,是以南京为中心的弘光政权,由明室官僚士绅的拥戴,于当年五月建立,人们希冀这半壁江山像南宋一样可以维持长久。不料只有一年,清兵就轻易地打到了江南。这一年为农历乙酉年,从王朝更替的角度而言,已是大清顺治二年(1645年)。该年频繁出现的抵抗运动,留给后世的记忆都相当惨烈,最著名者有“扬州十日”、“江阴保卫战”、“嘉定三屠”等。
众所周知,在“嘉定三屠”的殉难士绅中,侯峒曾与黄淳耀是其中最具代表者。而侯氏是嘉定县诸翟(旧名紫隄)人,现在属于上海市闵行区诸翟镇。那里有一座关帝庙,原本是侯氏的家祠。据说侯家先世姓杨,原籍山西上谷,宋室南渡后,辗转迁居于此。从明初开始,侯家开始兴旺起来,家族子弟多数以科举入仕。侯峒曾的父亲侯震暘就在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中进士,峒曾本人则于天启五年(1625年)成了进士。在当时,峒曾与岐曾、岷曾三兄弟都较出名,人称“江南三凤”。同时,峒曾与岐曾的六个儿子,即玄演、玄洁、玄瀞与玄洵、玄汸与玄泓(后改名玄涵),被誉为“侯氏六俊”,或称“江左六龙”。① 这“六侯”为海内所习称。② 侯家在嘉定堪称望族。
顺治二年六月,侯峒曾与黄淳耀等人,一起领导了地方的抗清活动。侯自称“总督”,曾在罗店地方获得多次胜利。其实,在清兵攻打嘉定前夕,峒曾正卧病家中(紫隄村故居),在黄淳耀等人敦请下回到嘉定县城,与士绅百姓一起画地而守,即峒曾负责守东门、淳耀负责守西门。六月廿六日,峒曾还曾写信,要侄儿玄汸、玄泓多方筹款200两,以为军需。嘉定城陷落后,峒曾投水而死,他的两个儿子玄演、玄洁也一起赴难。③ 峒曾死后还被清兵枭首悬示于西城门,后被挂到城中的侯家门口。④“嘉定三屠”后,侯家多改姓杨或徐,以避劫难,采取不入仕、务农耕或设教卖画等生活方式,没入茫茫人海中了。⑤ 多年以后,侯家稍形雍容,还能于城中废宅之上建“侯氏宗祠”祭拜这些先人,以示不忘侯家的“祖功宗德”。⑥
而幸免于清兵大屠杀的人们中,峒曾的弟弟岐曾(1595-1647)早在清兵攻城时,已受峒曾之命,奉母亲龚恭人避往江村故居(因盘龙江而名,即紫隄村)。⑦ 同时峒曾的另一个儿子玄瀞与岐曾的长子玄汸,屠城时据说适在他所,因而也得以暂免诛杀之祸。⑧ 关于岐曾的生平,与峒曾相比,记载少而不详。⑨ 但因岐曾有日记存世,故其惊心动魄的最后岁月与那段悲壮的历史,还是被真实地记录了下来。⑩
侯岐曾“绝迹忍饿”,以保孤、奉母为己责,而“故国旧君之思,又时时仰天扼吭”。家人亲友间,都以“忠孝大节”为重,这是他们苟活于世的最大动力。(11) 岐曾说,他的“立孤之义”可以“与死节同炳千秋”(12)。
第二年,岐曾就开始写日记,记录了社会变化、他的日常活动及其心灵世界。日记起于丙戌年(顺治三年,1646年)正月初一,至丁亥年(顺治四年,1647年)五月初十日绝笔,次日他被清兵捕获,十四日就赴死了。(13)
这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岐曾日记所述,涉及了当时的敏感时事与地方抗清活动,因而语词之间颇多隐晦。他特别提及其姻亲夏允彝到嘉定虬江时,为避人耳目,化名“黄志华”;而他自己久称“半生主人”,与这个“黄志华”朝夕“密通往来”的,一般都是写在一小幅竹纸上的密函,抬头必称“黄老”。岐曾还说,乙酉江南之变后,仅存的那些抗清志士,都是这样改易姓名。(14) 日记曾提及陈子龙在丁亥年四月二十六日,与夏之旭避至王庵,次日子龙就改号“车公”;同时,岐曾最信任、最得力的仆人侯驯亦改称川马。(15)
日记中附有数量不少的书札,署的是岐曾的法名“广维”,或者化名“易之”。岐曾还自述了写日记的缘起:“乙酉以后,家遭覆荡,身陷□□。其间岁时阅历,都非耳目恒遘,为宜札记,以备后人稽考。”南明政权兴起后,岐曾认为应该“执笔为新天子纪年,敬竢南都克复之后”。(16) 类似的意思,岐曾后来在日记中又讲过:“予有日纪,本为身丁大乱,虽穷乡日多异闻,欲一笔之,以备它年野史采择。”(17)
在鼎革之乱后,侯家原有的优越生活与社会政治地位大都丧失,且时时需要提防清廷爪牙的缉捕,四处避难,生活之艰辛有难以用言语形容者。对这样的生活巨变,岐曾时刻萦绕于怀:“乾坤变革,家国崩离。疁邑之祸,较它邑独深;寒门之祸,较疁邑倍惨。”家国的巨变,他当然感到无奈,“事势到此,所谓天也,非人也”。(18)
清朝在江南建立统治秩序之始,首先就是要行剃发令。对剃发的程度,官府作了一定的区分。这在岐曾的日记中记载比较清楚:官府设有“清发道”,按“五等”定罪。(19) 所谓“五等”,就是“一寸免罪,二寸打罪,三寸戍罪,留鬓不留耳,留发不留头”,另外“顶大者与留发者同罪”。(20) 侯岐曾有一次听到外地还有未剃发的义士,顿时“悲慰交至”。给姻亲好友顾咸正(21) 的信中这样说道:“两年来偷生异域,无刻不经历龙潭虎窟,宛转刀山剑树之下,待死而已。然而一寸丹心,数茎白发,相依为命,死生之盟,尚不以远近隔也。”(22) 他给拒不剃发、“以气节自任”的好友杨维斗(23) 的信中,讲述了他们随时可能触及的这种危难:“吾家祸重如山,时时恐蹈危机。”(24) 岐曾的侄儿玄瀞也至死未剃发,所以日常行动,很多需要已剃发的岐曾之子玄汸代劳,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25)
留发代表忠孝,是家国大义。岐曾说:“‘忠孝’两字,吾家不敢让人。”(26) 给顾咸正的一封密信中,他又说:“死拒伪命,生入里门,不独全其眷属,且全其发,遂为千古全人矣。岂非忠义之报。”在清廷密网的控制下,要做到这样真是“步步愁亭恨水”(27)、“刻刻将死字钉在额门”(28);同样,他的生活中还事涉抗清活动,更是“将死字钉在额门”。(29) 可是,到了最后的危难之际,岐曾仍不免剃发,目的不过是为了更好地隐避乡间。(30) 岐曾虽然认为这样在龙潭虎穴中为生,是“待死而已”,被迫在乡间四处躲藏又像一个“活死人”(31),但他觉得,他有责任担起维续家庭的重任,更有义务参与光复大明江山的事业。(32)
就家庭生活而言,侯家多少还能维持下去。夏、秋两至与清明、中元、除夕等重要节期,都需要敬天地、事鬼神;其余节候,“止祭皇考及仲兄”,其他人侯家都只是权宜行事。这是1645年秋天以前侯家在嘉定城中生活的常态,但此后有一段时间祀典几废,只祭峒曾与两个侄儿了。在乡间隐居安定后,岐曾尽量恢复正常的祭祀,举行了一次较大的祭奠活动。岐曾说这是“二十余年死生大痛,攒并一时”。(33) 六月间,住在惠宁的寡嫂忽然病重,叫岐曾不知所措。(34) 六月二十七日,嫂氏绝命,当天就匆忙入棺,丧事十分简单。(35) 但丧事的经费让岐曾颇感为难,除去其他开销,这样简单的丧事两天就花费了不少。寡嫂留下的财物很快用完了。衙门中的差人又来告知官府的压力,岐曾千方百计凑了些钱,打发了他们。他十分想知道巡抚土国宝对侯家的态度是否有缓和的余地,但根据这样的情形,岐曾认为“惟有听其一籍矣”(36)。丙戌年二月廿二日,他给杨维斗的信中这样说道,这种生活艰辛的程度简直到了“皮穿骨尽”的地步。(37)
清初江南各地新建立的衙门,已开始正常地向城乡民众征收赋税。侯家虽隐居乡间,依然不能豁免。为了获得官府的同情和宽免而必须支付的赋税负担,使岐曾感到颇为艰难。加上新增派的乡间荡田税,岐曾觉得实在不堪重负,只好“仰屋一叹”。(38)
就这样,在日记中,岐曾不断提及他如何应付地方官府、处理田产等事。这些都表明,在“嘉定三屠”后,侯家应该还保留有一定的田产,有的以前就被出租他人了。
五月二十五日,岐曾给“中道人”的信中这样说:经历鼎革之乱后,“三世之业荡尽,惟存薄田。亩租籍没二令并下,支吾数月,幸得二令俱收。然从此薄田虽为二物,仅足偿子母家耳。”所剩的这些薄产,除了日常生活开销外,主要就用来应付官府的勒诈。(39) 七月初二日,岐曾写道:“取租未已,粮务又急。”正在准备叫下令杨玄、朱三将掌租诸仆召来,衙门的“逼粮差子”就到了。(40) 次日,他得知“租、粮二者,署官皆亲比严拿,万分无姑缓理”(41)。对于这样的困境,岐曾感叹道“重殃叠费,无门可诉”,不得不责成掌租诸仆,招集他们聚会,是希望能“激发其忠义”(42)。到八月初二,亡嫂过五七,城中有信来说是官府要摊派卖人参事,侯家也被派了差不多四斤,岐曾希望“领一免三”,其他还有数两杂费;管科还说,催收已刻不容迟,岐曾当即分派人手到各乡去处理。(43) 八月初六午后,派家人侯驯入嘉定城,带去应付官府的粮银20两;另交数十两给侯驯,去衙门打点。(44) 九月初二,岐曾准备派下人朱三传信各乡初六交租(44)。这些都表明,侯家确实有不少田产一直在出租。
由上述各方面情形,大概可以了解王朝更替前,江南士绅家庭所具的经济实力与比较广泛的社会关系。
二、社会关系
可以想见,与清初地方官府的周旋,是让岐曾最感烦扰与不安的事情。他的朋友中,如潘秀、得和、陆翼王等是他很重要的依赖,而与衙门中的管科、张胥、冯胥等,往来更是密切,特别是管科,在岐曾的日记中出现频率极高。这些人都是帮助岐曾与清朝地方官府周旋的得力人物,往往不可或缺,一方面需要侯家付出更多的活动经费,另一方面让那些“朋友”们承担了较多的风险。尽管当中有个别的人,如岐曾讲的那样,也不是太让他感到满意。像管科还是侯家的亲戚,也经常来索“在城粮银”,“扰扰无刻静”(46);而“身份太高”的冯胥,是所谓官府的“变产总持”(47),即使被其“老奸所卖”(48),也不得不在他身上多费银子。要对付如嘉定县令那般手段较“辣”的地方官员(49)、巡抚土国宝对侯家“无所不极”的“恐吓”(50),岐曾百般委曲与衙门中的人员往来,确是无奈之举。
岐曾在隐居乡村期间,密切关注地方的形势变化,经常派仆人或亲友入城打探官府对于侯家的态度,并联系有关人员,以期消解侯家的难局。
隐藏槎楼的时候,岐曾给朋友徐克勤的信中说:“弟寄隐于槎上,万万不能揖一客……日来老兄有何见闻,龙变虎摅,岂渐作乌头马角耶?使人养养,亦使人闷闷。”(51) 表达其对于时势的焦虑之情。
在丙戌年五月初二,岐曾托人去嘉定城中探听情况:“呼管科入城,体察变后事宜,且冀籍产一案。”(52) 五月初五日是端午节,岐曾在家陪母亲喝蒲酒,“得和见报,虏兵马步及千人入城,城中汹汹,俄尽撤回矣,总不可解”。这一天给侄儿的信中,岐曾说:“今日泛蒲佳节,朱符桃印,虽无复旧观,聊借承欢以拨闷。……有自槎来者,云槎人喧传马兵奄至,十室九逃,殊可畏也。”(53)
根据日记中的隐晦表达,地方官衙中的一些头面人物,似乎对岐曾一家多少有些“宽容”的意思。当然,衙门官吏对侯家的这种缓和态度,目的不过是希图多捞几把。
五月十九日,岐曾据管科的通报,在日记中写道:“知邑有署印者,即日至矣。令固不能久留,对张胥云:‘侯家事,乘我在此,包它申文干净,但须助我行赀。’云云。乞子面目,至此和盘托出,翻属可怜。与母相商,恐它日起炉作灶,转贻后悔,无可如何。”(54) 岐曾将嘉定知县的这种无耻贪婪行径直呼为“乞子面目”,但他仍不得不设法凑钱让管科带去。到二十一日,管科就来叩门:“道昨所囊金,大不满乞儿之意。对胥役云:‘这送你们也不够。’又亲对管科云:‘你家事大,若付掌印手,最少千金。今吾已荡尽,前日汝家送我的,俱化为乌有了。此时随分金库等器物,皆可助我用。难道我要与你家完局,你家反不理会?只索抛去便了。’予以见习惯,都无笑骂,惟谋之儿汸,各竭所有。”(55) 那一点点银两,自然难以满足知县希图千金的贪欲。
五月二十三日下午,国俊从城赶回,“道乞儿无厌已极,赂已收而复加,其声尚尔嗃嗃”。(56) 岐曾当即就给侄儿玄瀞写信,告知这几天与官府沟通的情况。又说,目前家中所集的银两,大体总是随手耗尽,他连写了两个“可恨”。另有一信是写给顾咸正的,其中就道出了侯家面临的这种困境,所谓“晨昏菽水之需,几于荡尽”。(57) 两天后,岐曾给朱茂昭去信,对朱氏为侯家奔走抚院衙门的辛劳表示感激;在岐曾看来,只要“用事之人不爽初约”,官府对侯家的籍没、征租等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岐曾随信只附上了五两银子给朱氏,说是“取酒”之用。(58) 朱茂昭与官府关系颇深,显系侯家好友。对真正的下层百姓而言,若想象侯家这样勾通官府,设法规免一些赋役负担,根本是不可能的。
到二十八日,岐曾就听说土国宝、李成栋都到了嘉定县城。他就叫金科入城,并知会管科、顾俊,想法讨取申文消息。(59) 在给侄儿的信中,岐曾对土国宝等人的到来,表示了很大的不安,说:“其中莫不有危机乎?”(60)
岐曾绞尽心力,多少争取到了与官府回旋的余地,官场中的那些朋友们还能对侯家有所帮助。六月初一的日记显示,岐曾十分忙乱,主要工作就是应付官府:“上午遣顾俊入城。下午,管科自城趋至,恶缘娆人不了。遣俊者,邀朱茂昭入郡,完抚院一局。检行缠五金,又致二十金,以防意表之费。科则持示李督飞票三纸,张胥迫我行贿于督府,莫知所以置对。”(61) 面对各种无奈,岐曾相信,“人当至穷时,仍必有一条走路”,只要能花上钱,总会找到办法的。(62) 对于地方官府的苛求,岐曾根本不能对抗。在六月十三日的日记中,充满了岐曾的愤懑与无奈:“予痛愤诛求理极,从前臣力已竭,从后将何协助?即杯铛数十器,亦为诛求之用,耗荡过半矣。”(63)
六月十九日傍晚,管科从城里回来,“说督府暂尔支吾,许宽限一月”,前提仍然是要多花钱。晚上得和从府城归来,也说:四家出重赂,已许保全,且有待侯之语。(64) 同一天,岐曾给好友陈子龙写了一信,由女婿顾天逵(大鸿)带去。信中说:“至交凋尽,弟今所属望者,惟吾兄一人……若问一年来惊涛万状,彼从而取其租,又从而没其产,又复忽放忽收,顷刻如鬼物之不可摸索,弟惟刻刻钉一死字于额门。为存孤计,孤乃幸存,此介之推所云‘天功’也。而老母以下数十口如丝之命,都幸须臾无死。”(65) 这是岐曾向好友的倾诉,支持岐曾生活下去的,就是忠、孝二字。
当然,岐曾的日记中,写下了江南许多抗清名士的活动,也揭示出了那些帮助侯家脱免官府之害所产生的社会关系网。在1646年八月初,岐曾为减轻官府摊派卖参、钱粮征比的负担,特地在惠庄邀来陆廿六宫商量。这不过是岐曾认为“有胥史[吏]径路可走”、万不得已之策。(66) 但是,不管如何弥补,官府仍计划籍没侯氏家产,准备即日具题。岐曾感到一月来奔走请托的辛劳,已付之流水,且浪掷了许多银两。夏平南就建议,可以由夏完淳写信给降清后官至弘文殿学士的李雯,李当时正好回到松江。岐曾在八月初六日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录:“入槎晤平南、存古,商所以涴李舒章者,词旨不能殚悉。”初八日还是为这事:“正促写李书……存古至,亦出所上李弘文书,情文斐蔚,或堪动听耳。”(67)
夏完淳写给李雯的这封信很长,当中有这样的话:“侯忠烈九列大臣,一门毕命,徒有申胥之志,卒被王琳之殃。而废宅芜,追呼孔迫,官征之命,络绎道途,致同气有向隅之悲,遗体有穷途之恨。”完淳还说,如果李雯援手相助,侯家将十分感激,所谓“生效执鞭,死当结草”。(68) 这样的措词,很令人动容。当时夏平南已返回松江,岐曾写了一信,托人带给平南,信中说“此举乃背城之背城。得仁人扶挽,便可邀万全之万全”。十四日,岐曾得知,李雯已有信回复,表示一定援手相助。这让他觉得有了新希望。(69) 可是,不久之后,岐曾派人打探得知,巡抚土国宝的“籍没疏”已经发出,包括侯家在内的“五家俱不免”,岐曾竟是“漠然”了。(70) 后来新任的嘉定县令居然向侯家发了优恤告示,可是岐曾从别的渠道,得到的信息却是“守城殉节者籍”,乃官府“画一之法”(71),不能改变的事。
需要说明的是,夏完淳(字存古)的父亲,是明末抗清殉节的名士夏允彝,与陈子龙是同科进士;(72) 允彝的兄长夏之旭,也是地下抗清的志士,日记中常写作“元初”;夏平南则是完淳的从兄;完淳的姐姐淑吉嫁与岐曾幼子玄洵为妻。岐曾的日记中反复出现的“端木”或“弦斋”,是明朝大学士顾鼎臣的曾孙、昆山人顾咸正。(73) 咸正是明末的举人,曾任延安府推官,逃回故里后隐居不仕,仍不忘忠于明室。他的儿子顾天逵(大鸿)又是侯岐曾的女婿。这就构成了非常紧密的姻亲关系。夏、侯、顾三家患难与共,风雨同舟,经常聚会于岐曾的侄儿侯玄瀞家内,“谈及时事,各蓄异谋”。(74) 在夏完淳避难于侯家时,写有与玄泓等人共勉的诗,其中一句“星霜握手同兄弟,风雨知心托死生”(75),就很让人感怀。
而上文中涉及的李雯,乃松江名士,与陈子龙、宋征舆曾并称“云间三子”,文名颇盛。但李雯在清兵下江南后,就与一些人北上参加了清朝举行的科考,目的当然是要博功名。(76) 这当然有违明室遗民的“忠孝”思想。1645年,李雯去北京的时候剃了发,内心是所谓“难忘故国恩,已食新君饵”,颇有悔痛之情;给好友陈子龙的小诗《东门行寄陈氏》之后的附信中曾道:“失身以来,不敢复通故人书札者,知大义之已绝于君子也。”(77) 在最后的一段时间里,据好友宋征舆的记载,李雯“深以得官为恨”,而染重病。(78) 1647年五月,子龙殉难后,当年冬天,李雯就在北京“郁郁道死”了。(79)
陈子龙差不多比岐曾小14岁,是完淳的老师,曾与完淳等人一起在松江创建过畿社(80),而与岐曾则为至交。子龙曾说:“吾生平交满天下,今日乃知侯氏父子兄弟真人杰也。”(81) 子龙最后的逃难生活,就是在岐曾的极力帮助下度过的。
三、抗清生活
弘光政权结束以后,南方各地的抗清斗争,逐渐汇聚于隆武、鲁监国、绍武、永历等南明政权的旗帜下,既是明朝的延续,又是清初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志在抗清复明的文人士大夫们,各自拥戴这些不同的政权。很多人在起事时,以明室帝王为效忠的正统,构建起他们的精神依托。陈子龙在松江地方起兵抗清,曾悬挂明太祖像,并当众宣誓;侯岐曾在丁亥年元旦,也仿设明太祖像于“甲乙轩”。由此表明,这种情况在明遗民中是相当普遍的。(82)
岐曾以颇为谨慎的态度,在日记中描画了江南地方社会各种变化的情况、全国抗清消息的听闻感受等内容。到了丁亥年的除夕这一天早上,岐曾从噩梦中惊醒,觉得“大事当不远”,家族的危难也许会随时降临,决定从丁亥年开始,日记“务略之又略”。(83) 但是,这对追索彼时抗清志士的生活史而言,仍是那样的弥足珍贵。
岐曾十分注意官府对于侯家的态度。在丙戌年四月初七给儿子玄汸的一封信中,岐曾提醒他:“伯母传语羊玄,要防拿船,似尚须一两日消停”;又说“潍[维]亭未必真抢,而居民逃窜则有之”,听说抗清的“白腰党”“布满太湖、沙湖间,潍亭一带石岸俱已抉开”,他认为这些多属“流闻”,不必太在意。至于昆山县城的戒严,他觉得是可信的。(84) 过了几天,岐曾比较概括地记下了上海等地抗清人士活动的一些情况。(85) 五月间,陆翼王来与他会面,说起新泾一带清兵“淫掠至惨”,“城中十室尚九闭”。这些都让他感到紧张。(86)
而岐曾听闻各地抗清的消息后,时常是喜忧参半,但多数归于绝望。他自己也认为,在日记中的这些记录,如所闻的“闽浙义师齐奋,隆武恩诏初颁”等,是“遥遥未可为据”的。(87)
丙戌年三月二十七日,岐曾记道:“得和从郡回,一饭而去。得大鸿札,为言龙种面授语,闽浙似合似分。隆武诏书,我今日始得见之。(自闻浙师大捷,旋闻杭州被围,大约道路流言日日有之,略记之,以需后验)。”(88) 二十九日,给女婿顾大鸿的信中说:“南州事,为母者,道基初定,一手劈开;为子者,家业世承,终身孝养:此相成不相碍之局也。……我屡欲通问南州师,而前此皆寄子侄笔端,兹正不欲为凡此情形。啍啍絮絮,烦足下夫妇即将吾此字密商之可也。”(89)
到四月初三,又给顾大鸿写信:“自相订后,即几几望足下夫妇束装东下矣。忽得尊公言旋之报,不意乱离悲痛之余有此一场狂喜。”(90) 这个“尊公”就是顾咸正。当天,岐曾就给咸正写了一封密信,其间谈及其对于当时形势与时局的看法:“兹特先驰一介叩首,百凡情话,都未暇及,惟欲一询西北情形。齐豫秦晋间,何处有反正之机?或口授大鸿,详悉见报,尤妙也。……至弟生趣已尽,止为侍母全孤,留此残生。能使残生早捐,则种种滔天之祸,不复可支矣。说到此,尚能作意表行事否乎?惟有愤闷欲绝。”(91)
岐曾与浙江地方南明抗清人士的沟通,向来十分谨慎。他也时常嘱咐相关同志,要保持高度警惕,以免引来杀身之祸。
五月二十九日,他给顾咸正的信中这样说道:“下邑变事虽繁,而初旬之约再忍不过。昨乃特奏八行,岂意复中道返也。从此音书阻达,一等之大事之不可期,庶可解烦化躁。……弟以为今日传某忠臣予恤,明日传某名士拜官,此至危至危之事,将来无数杀机尽在此中。以故陈情一疏,弟每凛凛持之。”这天,由儿子玄汸AI写作疏稿,薄暮始完。他在日记中载道:“予作三札,并前诸札未达者一一托之弦斋。侄止寄中道人一札,同疏往。城中事传说纷纷,金科至,知骈戳数人,令已下狱,尚需核实。”(92)
六月十七日,岐曾接到顾咸正的长信,大概有几千字。他觉得复明活动颇可期待:“大都策中兴之必可期,目前举动,力劝吾辈勿过于畏慎,盖谓予前札申申指点危形故也。大鸿为父陈情,即日泛海,一言告别,可云壮游。两日闻钱塘□□,大歼于萧山之伏机。昆来者言之亦凿凿,岂天人遂尔凑泊耶?”(93) 第二天早上,岐曾听说夏完淳兄弟已于昨天傍晚抵达槎楼,即派人送信问候,觉得抗清武装友人所云“□□实未渡江,胜负两皆说梦”,实在匪夷所思。(94) 当然,岐曾给夏完淳写有一信,主要是提醒完淳等人,在槎楼隐居时,行动一定要慎密。(95) 同日,岐曾给顾咸正写了一封长信道:“当此雕肝腐肠之时,忽投以益智定胆之剂,能不苏苏起立乎?……弟今日所处与兄不同,兄虽出万死一生之余,而此身既全,自当理前事以启后图。弟则覆巢遗卵,除却奉母全孤而外,誓不敢萌它妄想。而又亲见彼法之加刃于我,一步紧一步。……忠义诸家,不云暗结白腰,则云显通闽海。而忠义诸家,举事如戏,实亦有可蹑寻,则其一举手间,何异于扫尘烁冻哉!至如目前诛求家业,虽未即及性命,而身危者苦趣自知,亦安得更有闲心剩力以及其它……而今日读□新皇诏书,不觉眉掀肉舞,以为理数值其至穷,惟当以气焰相取,吾从此不敢复执所怀来矣”;又说他还需要“刻刻防擒家属,一出门即防及藐诸”,处处得谨慎行事。(96)
而给女婿顾大鸿的密信中,岐曾对抗清消息的不确,显得十分焦虑:“钱塘之事,或云渡江小败,退何杭州,或云其实未渡,或云悉众而渡”,都是“杳无回报”。他需要等待其他消息来证实。(97) 后来给顾咸正的信中,还在询问“钱塘已有确耗否?长兴白龙鱼服,不终困于豫且否?此成败大关也。雁门一网,不至株连否?”岐曾希望咸正早予确示。(98)
对于太湖地区义士们的抗清活动、浙东南明政权的北上举动以及全国其他地方的抗清消息,岐曾在日记中时加记录。但岐曾也感到,毕竟大势已去,那些频繁的抗清活动又力量有限,太湖义兵已是“势渐孤蹙”(99),浙东地方的抗清时常受挫,与传言中的抗清捷报还是有出入的。(100) 七月下旬,岐曾收到顾咸正家传来的信息,道是从江北来的人“亲见何督师(腾蛟)破泗州,瑞昌王破太平府”,而且还听说“宛陵、淮南间义兵日新月盛”,正当令人振奋不已时,岐曾从夏平南那里得知“金华已被屠,浙东不复可为”,“不觉惨沮欲绝”。(101) 至于被清兵擒获的明室旧臣的情况,也多与传闻不合,真假难辨,让岐曾“为之闷闷”(102),有人从城里来,向岐曾言及嘉定各地发生的不少变乱,说是南翔镇居民更是紧张,“终宵戒备”。岐曾在日记中说:“予飘摇转徙,蹔寄此中,万非获已,慨然识之。”(103) 到七月底,岐曾一方面希望他听到的好消息都是确实的,另一方面也希望官府的催科能够宽缓。可是南京方面并无任何异常警报,而准备参加科考的举子们正络绎前往。岐曾感到有些绝望,那些传闻浮言并无定准,而处乱之情境令人可悲。(104)
岐曾所云的处乱之情境究竟若何?在十月间给顾咸正的一封信中,岐曾有这样一段话:“当此之时,一二懿亲契友,惟以废绝往来为真往来,此乙酉七月四日以后自盟然也。比来尚有以太平物色施及寒庐者,弟几欲挥刀相向,宁可做一场人命耳。至今年六月,复遭先嫂恭人之变,弟保孤之责愈重矣,而诛求之累亦愈惨。至八月以后,弟积病乃大发,两日一疟,冰崖炎井,变换不知凡几。至此纵未能忘情往来,亦穷于时势之不可奈何矣。”(105) 这当然是侯家情境最为真实的告白。
此后岐曾不断收到的抗清消息,越来越令人不安,福建失守,隆武帝已避入江西;四川抗清的张献忠也失败了。(106) 至于北京已然“恢复”的传说,岐曾更不敢信以为真。(107) 后来他又说:“此间久闻燕京已失,今竟属荒唐。”(108) 岐曾觉得:“大事既不可期,身家水火,日甚一日。”(109) 感到危难时刻都有可能降临。
四、反清失败
在松江等地,岐曾的好友陈子龙、夏完淳等人已准备举事。他们的行动,其实是看到吴胜兆反清计划带来的新希望。岐曾给顾咸正的信中,有这样的隐晦表达:“云间既有反正之机,便能作先事之举否?”(110)
吴胜兆本是明朝军中的一名指挥,降清后南下到苏州任苏松常镇提督。后来与驻苏州的巡抚土国宝多有摩擦,被洪承畴调驻松江。在部下戴之俊等人的劝说下,准备反清。戴与陈子龙联系,子龙很兴奋,表示愿意与据守舟山的黄斌卿联系,同时派友人夏之旭去见吴胜兆。双方约定,舟山的明军于丁亥年四月中旬进抵吴淞,与吴胜兆内外配合,共襄复明大业。(111) 不过很可惜,这个反清计划因走漏了消息而未果。
顾咸正亦曾提出:“海外黄斌卿是夏允彝结拜兄弟,可结连他起兵,我等作为内应。”他与侯玄瀞、夏完淳等即各具奏本、禀揭、条陈等文书,托谢尧文交付给通海舵工孙龙,送往舟山黄斌卿处。此外,托谢尧文、孙龙带通海文书的还有“结连过苏松湖泖各处豪杰、同心内应好汉”的钦浩、吴鸿等人,他们也写就各类禀帖,推荐某人可为文官,某人可任武职(谢尧文即被荐为游击)。行前,顾咸正等郑重叮嘱谢尧文道:“你须谨慎,此事关系身家性命。”(112)
与岐曾一样,谢尧文也是嘉定人,以前因事犯狱,是岐曾救了他。(113) 他经常负有上海、松江、嘉定等地抗清义士与浙东鲁王政权之间的联络工作。(114) 很遗憾,丁亥年三月十九日,谢尧文在柘林附近的漴阙(今属奉贤),因衣冠与时不合,露出疑点,被柘林游击陈可抓获,同时搜出了一些书信表疏。据清初人的回忆说,谢在被捕前,还“口出大言”,被捕后一受刑,就全部招供了。(115)
此案恰巧由在松江的提督吴胜兆负责,所以抓到谢尧文后,只作了关押处理,没作进一步审问。不久,吴胜兆的部下发生内讧,吴的兵变失败。巡抚土国宝派人搜查吴府,发现了那些“逆反”书信与表疏,十分震惊。随后,清政府即按名搜捕,除侯玄瀞等二十二名抗清人士逃出外,其余以顾咸正、夏完淳等为代表的抗清志士计三十四人,都被捕获。(116) 侯岐曾、顾天逵等首先被杀。清刑部题本中说:顾咸正等“率皆心臆共剖,肝胆相许。文愿设谋于帏幄,武愿戮力于疆场。虽射天之弓未张,而当车之臂已怒。无将之诛,万不能为各犯贷也”(117)。不过,在刑部尚书吴达海等人审理这起大案的题本中,岐曾的情况基本上没怎么提,主要就讲顾咸正与抗清已诛侯峒曾之子侯玄瀞、夏允彝之子夏完淳“夙怀不轨之心,共造逆天之罪”,企图与舟山的黄斌卿等人联心,勾连湖泖党羽,“具应依谋叛律,不分首从皆斩”;他们的妻妾子女入官为奴,财产籍没充饷,父母祖孙兄弟不限籍之异同都“流二千里”。(118)
这样一件反清大案,当然涉及松江地方最著名的抗清人士陈子龙。(119) 陈子龙听到抓捕风声后,与夏之旭、小童子等人逃到侯岐曾家。岐曾先将他们藏在仆人侯驯的家中,后来转移到在昆山的女婿顾天逵处。其目的,就要是转道昆山进入苏州,再通过海路远走浙东。岐曾的日记于此事记载较细。他说四月二十六日,因松江风声较紧,陈子龙与夏之旭避至嘉定乡下的王庵地方,大概离侯家居地不远。(120) 可是乡间到处传言,清军大兵俱集松江,将兴大狱。(121) 他们重找避地,躲到离王庵仅三里的丰浜,应该在侯驯的家,但四邻对他们产生了怀疑。在侯驯的劝告下,他们避至槎楼。(122) 此后,想转道至苏州府常熟县再出海,不料常熟地方道路戒严,舟楫不通,就打算到唐市镇的杨彝处躲藏,却被杨氏拒绝。在顾天逵的安排下,他们仍回昆山的黄泥潭丙舍隐藏。这时,岐曾已避迹于嘉定厂头的恭寿庄。大概在五月初十日中午,侯驯回到嘉定侯家住地,汇报了这一情况。第二天,陈子龙就被捕了。(123)
在屡被后人征引的《南疆绎史》中,强调了岐曾对陈子龙这次逃难的帮助,以及他与亲友们的死难情形:“子龙亡命,同夏之旭奔嘉定,告急于侯岐曾;匿其仆刘[侯]驯家,已迁昆山顾天逵所。当事迹至嘉定,执岐曾,别遣兵围天逵家;遂获子龙,锁舟中,泊跨塘桥下。子龙乘间,跃入水死,是月二十四日也;犹戮其尸。”据说,操江都御史陈锦审问子龙时道:“何不剃发?”子龙答:“吾惟留此发,以见先帝于地下也。”再问他就“瞠目不答”了。(124)
五月十二日,岐曾被抓到了松江城。巡抚土国宝审讯之后,派人送来酒菜,要他通个家信,岐曾曰:“吾已无家,何信为?”次日再审,岐曾踞坐,大骂不止。(125) 十四日午刻,岐曾与夏完淳、顾咸正及仆人侯驯、朱山、鲍超、陆二、李爱等一起,被杀于松江城西门的跨塘桥,即“云间第一桥”。与他们一同死难的,还有顾咸正的两个儿子天达与天逵。他们皆因藏匿子龙而死,与子龙的死一样悲壮。当时有位宝山参将,还称岐曾为“好男子”(126);后来还有人说,顾咸正一家,“以藏亡通海,一门殉义,其事最烈”(127)。
通过岐曾的日记,可以看到,在最后的一段时期,岐曾的身体状况与精神状况一样,也比较糟糕,有时便秘六七日、有时又是急性腹泻(日记中常说是痁、霍乱或“河鱼暴下”)、有时是痰火病发、有时为寒热重症。(128) 五月初七,是俗传的“天生婆婆”祭拜活动日,岐曾尚未从一场严重的腹疾中恢复过来,就准备请工匠为他母亲打造一具寿材。第二天,他的心情似乎很糟,因为有人来报告“千确万确”的消息,道是官府当晚可能会来他们住的恭庄抓捕,岐曾还带着侥幸心理让家人保持镇静,晚上也确实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初九日,岐曾的母亲还在逗弄孙儿为乐,报信的人再次来传递危信,“彰彰有据”,结果晚上还是没事。(129) 岐曾还是大意了,不过在那样的时局下,侯氏一家又能躲到哪里去呢?岐曾被捕前的日记最后只写到五月初十日,十分简单:“早,汸辞入城。王内三两书来,才附一札。”(130)
日记中附的这个札,其实是封短信。原文是这样的:“唐市之行,不遇朱家,便似所问非所对。要之,行止久远,莫非天定也。元兄杳然不报,甚异!甚异!儿正驰急足伺的音,而使者亦留之,不可得其往复语尔尔,巩不宜邅迥本境矣。奈何?奈何?弟为大兵将入疁境,闻多所征捕。寒家万分极危,然不暇自计,而亟望吾翁择其所安。真切心事,不出前柬所云,但媿意有余而力不及。更无一条必稳之路,惟吾翁自审择之。”根据后来看到日记的玄汸的说法,这封短札是仆人侯驯从昆山回来,告知彼处情况后,岐曾感到情况万分危急,于当天晚上写好,准备要托人带给陈子龙的,不料第二天他们都被捕了。(131) 这封短札就成了岐曾的绝笔。
五、余论
清初帝国努力在江南推行其统治的过程中,地方精英阶层与民众的态度、依归取向,产生了很大分化。(132) 有一部分人,主要是士绅,为生活所迫,为实现个人的愿望,暂时服从了清朝的统治。(133) 而一些乡村中的强宗大族,似乎对“华夷之别”并无观念上的严格区分。如上海地区的大族曹氏,较为积极支持这个新建立的清王朝,虽然在以后的“奏销案”使他们一度衰落。(134) 但为后世多所称道的,是一些士绅与民众奋起抵抗,否认清政权已经建立的事实,以武力和文化批判等方式,进行着各种各样的反对活动。
不可否认,长期优游于江南的士绅最初对清帝国的反抗,一是出于耻为“异族”之臣民的心理,二是担忧新王朝的建立将使他们丧失原来的既得利益和社会地位。与他们一起反抗的,是以明末以来的“盗贼”、无业游民、光棍等人为主,绝大部分乡村民众并未附合(135),除了对剃发颇为敏感外,其实还是很淡漠而怯懦。而地方无赖、乱民与真正的抗清义士或义师,纠结在了一起,让后人很难区分。(136) 不过,在抗清的历史书写中,这么做似乎也无太大的意义。
在这样的历史大变局中,个人生命显得十分微渺。面对清政权摧枯拉朽式的狂飚突进,任何抵抗都有些徒劳,也时常让侯岐曾这样的抗清志士感到绝望。就像时人所论的,弘光朝结束后,江南地区的一二士子“率乡愚以抗方张之敌,是以羊投虎,螳臂当车,虽乌合百万,亦安用乎!”(137) 之所以仍在誓死抵抗,大抵是为了“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以死明义,所谓“临危一死报君恩”。(138) 明末清初松江人杜登春身历鼎革之乱,在撰写《社事始末》时就说:“乙酉、丙戌、丁亥三年之内,诸君子各以其身为故君死者,忠节凛然,皆复社、幾社之领袖也……此外之孤忠报国死而不传者,又不知凡几。”(139) 而清朝官府在城乡地区,对于反清复明分子的大规模清洗,在很大程度上又动摇了前明士绅阶层在地方上的力量。
侯岐曾等人的地下反抗活动,若非其日记的留传后世,单凭想象,人们很难能细致地感受到那种日常生活中的惊心动魄。而与岐曾暗中勾连的江南反清人士,堪称遍布太湖东南部城乡地区,有的还是一代名士。他们短暂的抵抗活动,随着清政权的全面渗透太湖地区,已趋减退。所谓“每一王兴,有附而至荣者,即有拒而死烈者”,生易死难之叹在明清交替之际更让人感怀至深。(140) 殉难时不过17岁的夏完淳,留有绝笔诗云(141):“无限河山泪,谁言天地宽!已知泉路近,欲别故乡难。毅魄归来日,灵旗空际看。”(142) 临刑前,完淳还对人说:“我辈未尽之志,慎毋相忘!”(143) 而岐曾的日记,亦如清代人讲的那样,所谓“忠孝之言,缠绵悱恻,几使人不忍卒读”。(144) 人生命运的变幻与时代的不幸遭际,时时让人体味到一种深深的悲凉。正像陈子龙遁迹江村时留下的遗诗所言:“泪尽人间世,天涯何处逢。”(145) 从这个层面而言,“嘉定三屠”后的江南社会,无疑带有浓厚的悲情色彩。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清代江南的州县行政与社会控制研究”(09YJC770005)、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衙门内外:江南的州县行政与地方社会研究(1368—1912)”(2006BLS002)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 [清]汪永安:《紫隄小志》卷2《人物》,上海博物馆藏康熙五十七年稿本,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黄友斌:《百年清白、三世英名——明代嘉定侯氏》,见上海市嘉定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编:《嘉定抗清史料集》,第22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② [清]计东:《改亭文集》卷8《嘉定侯氏宗祠记》,乾隆十三年计瑸刻本。
③ [清]查继佐:《国寿录》卷2“道臣侯峒曾传”条,第51-52页,中华书局,1959;[清]计六奇:《明季南略》卷4“嘉定侯峒曾、侯岐曾”条,第26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清]朱子素:《嘉定屠城惨史》,宣统三年嘉定旅沪同乡会刊本;[清]吴伟业:《鹿樵纪闻》卷上“嘉定之屠”条,上海,神州国光社,1947;[清]温睿临、李瑶:《南疆绎史》卷15《侯峒曾传》,清傅氏长恩阁钞本;[清]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22《纪事·记侯黄两忠节公事》,第315-318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明史》卷277《侯峒曾传》;胡山源:《嘉定义民别传》,上海,世界书局,1938;[明]侯峒曾:《与侄书》,载上海市嘉定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编:《嘉定抗清史料集》,第40页。
④ [清]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22《纪事·记侯黄两忠节公事》,第318页;光绪《嘉定县志》卷32《轶事》,光绪六年重修本。
⑤ 黄友斌:《百年清白、三世英名——明代嘉定侯氏》,第231页。
⑥ [清]计东:《改亭文集》卷8《嘉定侯氏宗祠记》。
⑦ [清]汪永安原纂、侯承庆续纂、沈葵增补:《紫隄村志》卷5《元明人物》,康熙五十七年修、咸丰六年增修,上海图书馆藏传抄本。
⑧ [清]汪琬:《钝翁续稿》卷26《墓志铭三·侯记原墓志铭》,天津图书馆清康熙刻本。1912年版的[清]孙静庵的《明遗民录》(上海:新中华图书馆出版)卷44《侯记原》(第657-658页)与1985年出版的同书卷44《侯记原》(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第328-329页)有类似记载,都将侯记原(玄汸)刊作“峒曾犹子”,当是峒曾侄子之意。
⑨ 有关侯岐曾扼要的传记,可参钱海岳:《南明史》卷32《侯岐曾传》,第1604-1605页,北京,中华书局,2006;[清]汪永安:《紫隄小志》卷2《人物》,“侯岐曾”条,第53-55页。[清]汪琬于《钝翁续稿》卷49《侯震暘传》中所附的岐曾小传,更不到百字;[清]陈鼎辑:《东林列传》卷20《侯震暘》附侯岐曾(收入周骏富辑:《明代传记汇刊》学林类三,第309-310页,台北,明文书局,1991),也十分简短,且有错讹。
⑩ 收藏在上海图书馆的这部日记名“明侯文节先生丙戌、丁亥日记”,白坚很早就作过札记,并特别勾勒了日记中有关夏完淳与陈子龙的内容,参氏著《夏完淳陈子龙研究的珍贵史料——读侯岐曾〈丙戌丁亥日记〉札记》,载《文献》,1989(4)。此后,黄慧珍则作过比较扼要的介绍,参氏著《侯岐曾与〈明侯文节先生日记〉》,载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主编:《嘉定文化研究》,第467-475页,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后来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将这个日记从上海图书馆以重金购出点校,点校者为此也写了一篇比较综合的说明,附于正文之前,参《明清上海稀见文献五种》“侯岐曾日记”前言,第478-48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本文就是利用这个版本,鉴于前述学者的相关研究工作尚未全面充分,故觉得仍有予以全面探讨的必要。
(11)(14) [清]侯岐曾:《侯岐曾日记》(以下简称《日记》),金元钰“题跋”(嘉庆十五年重阳日),第482页;《日记》,丙戌正月十三日,第486-487页。
(12) 《日记》,丙戌五月廿五日,第537-538页。
(13) 《日记》,金元钰“题跋”(嘉庆十五年重阳日),第482页。
(15) 《日记》,丁亥四月廿六、廿七日,第636-637页。
(16) 《日记》,侯岐曾“自序”,第483页。
(17) 《日记》,丙戌十二月初七日,第603页。
(18) 《日记》,丙戌二月廿二日,第499页。
(19) 《日记》,丙戌二月廿九日,第504页。
(20) 《日记》,丙戌三月初一日,第504页。
(21) 关于顾氏的传记及殉难情况,可参[清]计六奇:《明季南略》卷4“顾咸正答洪承畴”条,第259页;光绪《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27《忠节上》“顾咸正”条,光绪六年刊本。
(22) 《日记》,丙戌正月廿一日,第489页。
(23) [清]温睿临、李瑶:《南疆绎史》卷13《杨廷枢传》;[清]计六奇:《明季南略》卷4“杨廷枢血书并诗”,第256页;乾隆《吴江县志》卷36《寓贤》,乾隆十二年修、石印重印本。
(24) 《日记》,丙戌二月廿二日,第498页。
(25) 《日记》,丁亥三月初七日,第621-622页。
(26) 《日记》,丙戌二月廿二日,第499页。
(27) 《日记》,丙戌四月初三日,第515-516页。
(28) 《日记》,丙戌五月廿五日,第537-538页。
(29) 《日记》,丙戌六月十八日,第549-550页。
(30) 《日记》,丁亥三月廿四日,第625页。
(31) 《日记》,丙戌正月廿六日,第490页。
(32) 《日记》,丙戌正月廿八日,第491页。
(33) 《日记》,丙戌五月初九日,第529页。
(34) 《日记》,丙戌六月廿四日,第554页。
(35) 《日记》,丙戌六月廿七日,第555页。
(36) 《日记》,丙戌七月初一日,第556-557页。
(37) 《日记》,丙戌二月廿二日,第498页。
(38) 《日记》,丙戌二月初三日,第493日。
(39) 《日记》,丙戌五月廿五日,第536-537页。
(40) 《日记》,丙戌七月初二日,第557页。
(41) 《日记》,丙戌七月初三日,第557页。
(42) 《日记》,丙戌七月初四日,第558页。
(43) 《日记》,丙戌八月初二日,第568页。
(44) 《日记》,丙戌八月初六日,第569页。
(45) 《日记》,丙戌九月初二日,第578页。
(46) 《日记》,丙戌十一月十七日,第598页。
(47) 《日记》,丙戌七月廿五日,第566页。
(48) 《日记》,丙戌六月十一日,第545页。
(49) 《日记》,丙戌七月初六日,第601页。
(50) 《日记》,丙戌十一月廿九日,第558页。
(51) 《日记》,丙戌四月廿七日,第526页。
(52) 《日记》,丙戌五月初二日,第527页。
(53) 《日记》,丙戌五月初五日,第528页。
(54) 《日记》,丙戌五月十九日,第532-533页。
(55) 《日记》,丙戌五月廿一日,第533页。
(56) 《日记》,丙戌五月廿三日,第534页。
(57) 《日记》,丙戌五月廿四日,第536页。
(58) 《日记》,丙戌五月廿五日,第538页。
(59) 《日记》,丙戌五月廿八日,第539页。
(60) 《日记》,丙戌五月廿八日,第540页。
(61) 《日记》,丙戌六月初一日,第542页。
(62) 《日记》,丙戌六月初二日,第542页。
(63) 《日记》,丙戌六月廿三日,第554页。
(64) 《日记》,丙戌六月十八日,第550页。
(65) 《日记》,丙戌六月十八日,第551页。
(66) 《日记》,丙戌八月初二日,第568页。
(67) 《日记》,丙戌八月初五日、初六日,第569-570页。
(68) [明]夏完淳著、白坚笺校:《夏完淳集笺校》卷9《与李舒章求宽侯氏书》,第407、40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69) 《日记》,丙戌八月初八日、十四日,第570、573页。另可参白坚:《夏完淳陈子龙研究的珍贵史料——读侯岐曾〈丙戌丁亥日记〉札记》。
(70) 《日记》,丙戌八月廿九日,第577页。
(71) 《日记》,丙戌十一月十一日,第595页。
(72) [清]计六奇:《明季南略》卷4“夏允彝赴池死”条,第266页。
(73) 顾咸正的传记及殉难情况,可参[清]计六奇:《明季南略》卷4“顾咸正答洪承畴”条,第259页;光绪《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27《忠节上》“顾咸正”条,光绪六年刊本。
(74) 邓之诚:《骨董琐记》三记卷5《顾咸正一案刑部提本》,第561-570页,北京,中国书店,1991。据顾诚对照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的顺治四年八月二十二日刑部尚书吴达海等题本,邓氏记录在个别文字方面存在讹误(顾诚:《南明史》,第460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
(75) 夏完淳的这首诗《九日风雨宴侯研德宅》,很珍贵地收录于[清]汪永安:《紫隄小志》续二《诗词》,第105页。
(76) 谢国桢:《清初利用汉族地主集团所施行的统治政策》,收入氏著《明末清初的学风》,第73页。
(77) [清]李雯:《蓼斋后集》卷1《乐府·东门行寄陈氏》、卷1《五言古诗·李子自丧乱以来追往事、诉今情、道其悲苦之作、得十章》、卷5《杂文·答发责文》,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顺治十四年石维昆刻本。
(78) [清]宋征舆:《林屋文稿》卷10《云间李舒章行状》,上海图书馆藏康熙九籥楼刻本。
(79) [清]吴伟业:《吴梅村全集》卷58《诗话》,李学颖集评标校,第113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清]宋征舆:《林屋文稿》卷10《云间李舒章行状》。
(80) [清]杜春登:《社事始末》,收入[清]张潮主编:《昭代丛书》续编戊集卷16,吴江沈氏世楷堂藏板,道光年间刊、光绪二年重印本。
(81) 白坚:《夏完淳陈子龙研究的珍贵史料——读侯岐曾〈丙戌丁亥日记〉札记》,载《文献》,1989(4)。
(82) 详参黄慧珍:《侯岐曾与〈明侯文节先生日记〉》;《日记》,丁亥元旦,第608页。
(83) 《日记》,丁亥“除夕”条,第608页。
(84) 《日记》,丙戌四月初七日,第517页。
(85) 《日记》,丙戌四月十二日,第519页。
(86) 《日记》,丙戌五月初九日,第529页。
(87) 《日记》,侯岐曾“自序”,第483页。
(88) 《日记》,丙戌三月廿七日,第513页。
(89) 《日记》,丙戌三月廿九日,第514页。
(90) 《日记》,丙戌四月初三日,第516页。
(91) 《日记》,丙戌四月初三日,第515-516页。
(92) 《日记》,丙戌五月廿九日,第540页。
(93) 《日记》,丙戌六月十七日,第547页。
(94) 《日记》,丙戌六月十八习,第547页。
(95) 《日记》,丙戌六月十八日,第547-548页。
(96) 《日记》,丙戌六月十八日,第548-549页。
(97) 《日记》,丙戌六月十八日,第549-550页。
(98) 《日记》,丙戌六月廿一日,第552页。
(99) 《日记》,丙戌六月廿五日,第554页。
(100) 《日记》,丙戌七月初九日、十三日,第560、562-563页。
(101) 《日记》,丙戌七月廿五日,第566页。
(102) 《日记》,丙戌七月十七日,第563-564页。
(103) 《日记》,丙戌二月初六日,第494页。
(104) 《日记》,丙戌七月廿九日,第568页。
(105) 《日记》,丙戌十月初三日,第585页。
(106) 《日记》,丙戌十一月廿二日,第599页。
(107) 《日记》,丙戌十二月初一日,第601页。
(108) 《日记》,丁亥一月十四日,第610页。
(109) 《日记》,丁亥四月十七日,第634页。
(110) 《日记》,丙戌十二月二十日,第606页。
(111) 顾诚:《南明史》,第454-458页。
(112) 邓之诚:《骨董琐记》三记卷5《顾咸正一案刑部提本》,第561-570页。
(113) 钱海岳:《南明史》卷32《谢尧文传》,第1630页。
(114) [清]曹家驹:《说梦》,道光八年醉沤居士钞本,第1 6页。
(115) 台北中研院史语所编:《明清史料》己编第一本《刑部残题本》,第10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清]曹家驹:《说梦》,道光八年醉沤居士钞本,第16页。
(116) 柳亚子:《柳亚子文集》“南明史纲·史料”,第155-15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邓之诚指出,被捕的人数于《明季南略》及其他一些书中都作四十余人,唯乾隆《苏州府志》记为三十四人,于顺治四年九月十九日在江宁同死,这个数字与刑部尚书吴达海的题奏相吻合(《骨董琐记》三记卷5《顾咸正一案刑部提本》,第562页)。
(117) 顾诚:《南明史》,第460页。
(118) 邓之诚:《骨董琐记》三记卷5《顾咸正一案刑部提本》,第561-570页。
(119) 关于陈子龙的抗清生活史,可参朱东润的《陈子龙及其时代》,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120) 《日记》,丁亥四月廿六日,第636页。
(121) 《日记》,丁亥四月廿六日、廿九日,第636-637页。
(122) 《日记》,丁亥五月初五日,第640页。
(123) 《日记》,侯玄汸“附记”,第642页;另参[清]汪永安:《紫隄小志》卷2《人物》,第54页。
(124) [清]温睿临、李瑶:《南疆绎史》卷14《陈子龙传》。
(125) [清]汪永安原纂、侯承庆续纂、沈葵增补:《紫隄村志》卷5《元明人物》。
(126) [清]汪琬:《钝翁续稿》卷49《侯震暘传》附侯岐曾传;[清]计六奇;《明季南略》卷4“陈子龙投河”条,第268页;[清]王沄续撰:《陈子龙年谱》卷下,顺治四年丁亥五月,收入[明]陈子龙:《陈子龙诗集》附录二,施蛰存、马祖熙标校,第72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清]汪永安:《紫隄小志》卷2《人物》,第54-55页;
(127) [清]陈去病:《五石脂》,第375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128) 参《日记》,丙戌十一月廿四日、十二月初五日,丁亥元月初三日、元月十九日、元月廿一日、二月廿六日、五月初六日,第600、602、609、611、612、619、640页。
(129) 《日记》,丁亥五月初七日、五月初八日、五月初九日,第641页。
(130) 《日记》,丁亥五月初十日,第641页。
(131) 《日记》,丁亥五月初十日、侯玄汸“附记”,第642页。
(132) 参谢国桢的《南明史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与《明末清初的学风》[载《四川大学学报》,1963(2),后收入同名论文集《明末清初的学风》,第1-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魏斐德的《洪业——清朝开国史》(第451-456页:“乡绅们的矛盾心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岸本美绪的《明清交替と江南社会——十七世紀中国の秩序問題》(东京大学出版会,1999)、陈生玺的《明清易代史独见》(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何冠彪的《生与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择》(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7)、王汎森的《明末清初思想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范金民的《鼎革与变迁:明清之际江南士人行为方式的转向》[载《清华大学学报》,2010(2)]、冯贤亮的《清初江南的乡村变迁与社会结构》(载《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5辑,第82-10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等。
(133) 吴晗:《爱国的历史家谈迁》,见[清]谈迁:《北游录》,第1-7页,北京,中华书局,1960;另见该书“纪邮”上,第64页。
(134) [日]佐藤仁史:《清朝中期江南的一宗族与区域社会——以上海曹氏为例的个案研究》,载《学术月刊》,1996(4)。
(135) [清]查继佐:《国寿录》卷3“兵科郎中钱旃传”条,第100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136) [美]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第502-505、511页。
(137) [清]计六奇:《明季南略》卷4“总论起义诸人”条,第278页。
(138) 汪荣祖:《江南与明亡清兴——兼论历史地缘说》,见熊月之、熊秉真主编:《明清以来江南社会与文化论集》,第10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
(139) [清]杜登春:《社事始末》。
(140) [清]计六奇:《明季南略》卷4“总论江南诸臣”条,第277页。
(141) [明]谈迁:《枣林杂俎》仁集《逸典》“群忠备遗”条,第145页,北京,中华书局,2006。
(142) [明]夏完淳著、白坚笺校:《夏完淳集笺校》卷5《五言律诗·别云间》,第260页。
(143) [清]陈去病:《五石脂》,第290页。
(144) 《日记》,金元钰“题跋”(嘉庆十五年重阳日),第482页。
(145) [明]陈子龙:《避地》,收入[清]汪永安:《紫隄小志》续二《诗词》,第10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