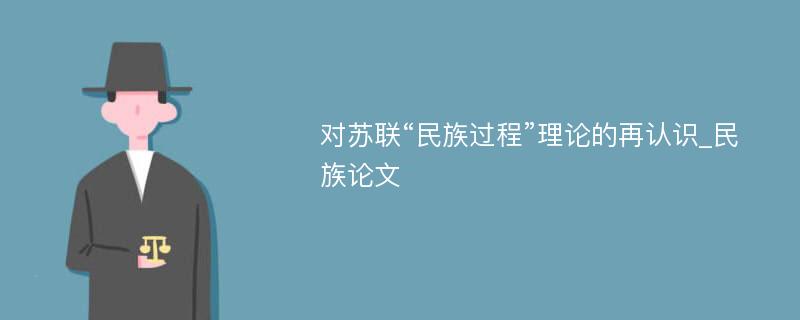
对苏联“民族过程”理论的再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再认论文,苏联论文,民族论文,过程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民族过程”是一个来自苏联的学术概念,它在俄文中有两个对应词组:этнические процессы和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процессы。两者的涵义有明显区别,前者基于этнос一词,指的是各个时代的民族;后者基于нация一词,仅指现代民族。目前,学术界一般用этнические процессы来表述“民族过程”。
20世纪80年代,苏联的“民族过程”理论逐渐进入我国研究者的视野。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我国学术界出现了一些关于“民族过程”的文章和著作。但是,学者们在注重术语引入和应用的同时,却忽视了对“民族过程”理论的理解和分析,部分研究存在宽泛化、简单化的倾向,似乎所有与民族相关的分析都可以冠以“民族过程研究”。笔者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对“民族过程”理论的误读,因为事实上,“民族过程”理论的创新之处集中体现在其对民族文化发展过程的关注,如果仅仅简单地用以概括与民族变化相关的现象,则无法体现其精髓所在。为了进一步推动对相关理论的理解和研究,本文将重新审视“民族过程”理论。
一、“民族过程”概念的由来
在人类思想史上,任何一个学术概念的形成和确立都必然受到相关学术思潮兴衰更替的影响。苏联学者提出的“民族过程”这一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前人对“历史过程”研究的启示。
“历史过程”是历史哲学研究的核心内容。最早把历史看作一种过程的是18世纪时的意大利著名学者维柯。他在其著作《新科学》中提出应把历史演变的过程当作一种自然的现象来看待,认为人类社会及其制度的发生、发展是一种“自然次序”,①从而开创了“历史过程”研究的先河。后来,维柯的这种思想被法国学者杜尔哥(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1727—1781,又译杜尔阁)和孔多塞(Marie de Caritat,de Condorcet,1743—1749)、德国学者康德和赫尔德进一步地发挥,并在黑格尔那里达到顶峰。事实上,整个18世纪的哲学和历史学研究都是围绕着“历史过程”而展开的。受其影响,马克思主义也认为:“以往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② 不同的是,历史哲学的研究者大都持一种唯心主义的世界观,例如:维柯坚信神性是“历史过程”的根源;康德和孔多塞将其归纳为理性的进步;黑格尔推崇的是人的意志。而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③ 总体来说,“民族过程”理论带有明显的“历史过程”研究的痕迹,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历史过程”的研究者将历史看作一个呈螺旋状向上发展的连续过程。正如柯林伍德所说:“这种周期性运动并不是历史通过若干固定阶段而周而复始的一种单纯的循环,它不是一个圆,而是一个陀螺,因为历史绝不重演它本身,而是以一种有别于已成为过去事情的形式出现于每个新阶段。”④ 受此启发,苏联学者也把民族的发展、变化看作一个连续过程。(2)“历史过程”的研究者大都坚持“社会实在论”,相信在历史现象的背后还存在着某种“物本身”。例如黑格尔提出:“历史上的事变各各不同,但是普遍的、内在的东西和事变的联系只有一个。”⑤ “民族过程”理论承袭了这种观点,着重研究民族本身的变化。(3)“历史过程”的研究者认为:“历史哲学的任务就是要对历史事件的详细过程写出这样一种叙述,要表示出来它那‘真正的’意义和‘本质的’合理性”。⑥ 同样,“民族过程”理论也认为民族的发展受着能够被发现的普遍规律的支配,而相关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揭示这些规律。(4)对“民族过程”理论影响最深的是马克思的“自然历史过程”理论。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序言中写道:“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⑦ 这一论述不但是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中的一个根本性的、核心的观点,而且是“民族过程”理论的思想基石。
可贵的是,“民族过程”理论不但吸收了“历史过程”研究的精华,而且还丰富和发展了相关的研究领域。由于“历史过程”的研究者大都只注意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同质性”,对其中的各个部分所包含的“异质性”缺乏足够的重视,所以,“历史过程”理论对民族问题的研究大部分都停留在宏观水平,即便是涉及到具体的民族,也都是将其置于一定的历史事件中,分析这些历史事件对民族命运的影响。这样得到的结果虽然带有很强的普适性,但不能很好地解释民族发展的主动性,即:为什么在同样的社会或历史条件下,不同的民族甚至同一民族中的不同部分会做出不同的选择?而这正是“民族过程”理论所最为关注的,它很好地弥补了“历史过程”研究的不足。
二、对“民族过程”概念的辨正
苏联民族学者提出:“各个层次的民族共同体,也象民族共同体的两种形式(民族和民族社会机体)一样,都具有相当的稳定性。一切民族共同体的特点不仅是世代相传,而且也时刻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一般称作‘民族过程’(этнический процесс)。”⑧ 所谓民族共同体的特点,即“指表现在首先是日常文化、风俗、行为准则,以及心理特点(其中包括对价值的理解)等方面的民族特有的东西”。⑨ 不仅如此,一些苏联学者还进一步将“民族过程”分为广义的和狭义的两种:“一个民族的任何一种基本要素,首先是语言和文化的显著变化都属于广义的民族过程”;“狭义的民族过程是指那些终归要导致民族属性,即民族自识性(民族自我意识)的变动的那些变态过程”。⑩ 正是以这一系列概念为基础,苏联学者演绎出了“民族过程”理论。
然而,在“民族过程”理论传入我国之后,这一概念却成为争议的焦点。我国一些学者从语言学的角度对“民族过程”的涵义及其可行性提出质疑,认为应该修改这一术语的表达方式。(11) 另外一些学者虽然勉强认同了“民族过程”这一术语,但却以苏联学者的概念过于学院化、缺乏对公众的普及和教育意义为由,对该理论的概念和应用体系重新进行了设计,提出“民族这一历史范畴,从产生、发展到消亡这一漫长的历史阶段”或“民族的形成与发展,演变与消亡,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始终处于过程之中,是谓‘民族过程’”,(12) 等等。
对此,笔者认为:一方面,语言作为人类思维的表达工具,其形式是多种多样而且日新月异的,即便是语法不通的词组,也可以通过持续地使用而逐步消除它同语言习惯的冲突。况且,目前这种“事物+过程”的组合方式已经是屡见不鲜,譬如:“政府过程就是:一个团体的活动,一种利益的表现和一种压力的行使”;(13) “组织过程就是将组织要素组合成一个整体并使其去实现组织目标的过程”,(14) 等等。既然语法上的冲突可以搁置,而且又有先例可援,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一味地对术语“正本清源”,而应该着重把握理论的内容和实质,否则就会陷入形式主义的窠臼之中。另一方面,如果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世界上没有永恒不灭的客观事物,一切客观事物都必须经历诞生、成长、成熟、衰落、消亡的过程。我国学者对“民族过程”理论概念的修改从认识的角度看无疑是合理的,也有益于“民族过程”在我国的传播和推广。但实际上,这样的修改破坏了苏联学者精心构建起来的理论概念框架,偏离了该理论创建时的初衷,其原因有三:
第一,作为对“民族过程”最为宽泛的理解,我们可以将“民族过程”看作民族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全部历程,但这只是单纯地对民族的生命历程进行描述,并不适于作为相关理论的概念,因为概念就是反映对象的特有属性的思维形式,它是人们通过实践,从对象的许多属性中抽出其特有属性概括而成的。(15) 也就是说,概念是针对人类思维有限性的抽象产物。特别是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学者们往往会根据各自的研究需要赋予某一个词或词组以不同的含义,甚至创造出一个全新的词或词组作为“理论概念”,它们在揭示研究对象本质的同时,还明确了理论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并把那些不涉及的方面“闲置”起来,从而避免了庞杂的内容对研究的干扰。具体而言,“民族过程”是由“民族”和“过程”这两个内涵丰富、涉及面很广的范畴组合而成的,为了将它和其他“社会过程”区别开来,苏联民族学者立足于自身的研究将“民族过程”抽象为某些因素的变化,并以此作为理论阐发的基础。
第二,过程研究是西方和苏联学者开辟的一个新研究领域,其目的是为了突破传统体制研究的束缚,展现不同事物各自独特的变化轨迹。所以,苏联学者在界定“民族过程”时明确指出:“民族过程”与其他“社会过程”相比,具有极强的稳定性,这既是民族变化最显著的特点,又是“民族过程”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研究范畴的关键。相比之下,我国学者提出来的定义所揭示的只是“过程”的本质,即客观事物发展所必须经过的程序,其思想内涵已从“求异”演化为“趋同”,这无疑削弱了“民族过程”理论的创新意义。
第三,一直以来,民族文化都是民族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因此,苏联民族学者在理论概念上有意凸显文化的作用。需要澄清的是,在这里,“文化”主要是指精神文化,即人们通常理解的狭义的文化,“民族过程”理论中所说的文化则主要是指宗教。然而,经我国学者修改后的定义却将一切历时的民族现象和民族运动,甚至民族产生后的一切“社会过程”,都不加区别地纳入其中,这样就使本已十分复杂的语义范围无限扩大,无助于我们很好地判断“民族过程”研究处于什么样的领域和层次。
以上这些问题的症结在于我国学者混淆了“纯粹民族过程”和“民族社会过程”。苏联民族学者注意到,民族并不像经济那样经常处于明显的变化之中,它甚至有可能超越于经济之上,所以他们将民族构成体分为两种基本形式:民族和民族社会机体。前者指的是“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的相对稳定的文化(其中包括语言)特点和心理特点并意识到自己的统一和与其他这类构成体的区别的人们的总体”,后者则是指“由于民族和社会机体的相互渗透而产生的特殊构成体”。(16) 据此,“民族过程”也可分为“纯粹民族过程”和“民族社会过程”。“纯粹民族过程只表现为民族的变化(即语言文化因素和民族意识的变化)。民族社会过程则表现为民族社会共同体的变化(首先是社会经济因素的变化)。……这种区分的依据,首先是民族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在社会活动中变化形式的不同。”虽然“在一切社会现象中,社会经济因素是最活跃的”,它“是引起民族社会机体变化的决定性因素”,但民族文化现象“具有很大的稳定性。这就决定了民族过程的变化较之社会经济过程的变化要缓慢得多。……从一种社会经济形态向另一种社会经济形态的转变,必然要引起该民族社会机体主要类型特征的变化。但是,民族(этнос)则可以连续存在于几种(两种、三种甚至四种)社会经济形态之中。”(17) 结合上文提到的“民族过程”理论概念,我们可以发现,苏联的“民族过程”理论偏重于“纯粹民族过程”的研究,其着眼点是民族的文化。虽然我国有个别学者注意到了这一点,将“纯粹的民族”译为“族体”,(18) 但大多数人都将“纯粹的民族”等同于“民族社会机体”,进而在介绍相关理论时将“纯粹民族过程”和“民族社会过程”通译为我们在一般意义上所说的“民族过程”。这样一来,“民族过程”这一术语的价值以及相关理论的特点便无法得以充分体现,人们很容易将其误认为是一个宏大的无所不包的社会理论体系。
总之,概念作为一种精练的语言形式,对于理论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苏联的“民族过程”理论中,“民族过程”是一个限定严格、实践性和应用性很强的民族学专业术语,而我国学者却往往将其视为一个简单而时髦的复合词。这种对概念认识的语境差异很容易造成许多认识上的误区,导致理论与具体的研究实践之间出现裂痕。
三、对“民族过程”理论内容的分析
我国学者之所以没能厘清“民族过程”理论的概念框架,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忽略了对理论内容的分析。实际上,理论的内容是理论概念的延伸,概念中很多语义模糊的地方都能在相关的内容中得到补充说明。因此,分析理论的内容有利于加深我们对理论的认识。
首先,“民族过程”理论对影响和制约民族变化的体制性因素包括语言、宗教、心理、地域、人口、地理环境、物质生产、经济联系、阶级和国家等,进行了多方面的分析。
其次,“民族过程”理论将“民族过程”分为两种基本形式:民族分化过程和民族联合过程。
民族分化过程,“即原来是一个统一民族的人们逐渐分化为几个单独的民族,或者由某个民族分化出几部分,各自成为独立的民族”。(19) 造成民族分化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一个民族的一部分人的迁徙,以及一个民族共同体被国界分割为几个部分。民族联合过程,“即把原属不同民族的人们联合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民族发展的辩证法在这里表现为:几乎每一个联合的过程,都必然要在新的基础上导致这些参与联合的民族同其他民族的分离。”(20)
“民族过程”理论对民族联合过程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将其细分为三种类型:民族聚合过程、民族同化过程和民族一体化过程。学者们对此的提法大同小异。
民族聚合过程:“几个在起源上、语言上和文化上相近的民族共同体(或它们的各个部分)汇聚为一个民族,此即属于民族聚合”;(21) “民族的聚合是一些有血缘关系的民族(部落、部族)溶合为较大的民族,或者是已经形成的民族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而进一步团结”;(22) “几个在语言和文化上有亲属关系的民族单位融合为一个民族共同体的过程,此即属于民族聚合”。(23)
民族同化过程:“处在另一个民族的环境中间的某个民族的某些集团(或其成员)的溶合过程称作民族同化”;(24) “所谓同化是指居于某个(通常比较大、比较发达或数量上在当地占优势的)民族共同体环境中的个别民族集团汇入这个民族共同体之内,这种过程往往在民族毗邻地带得到发展”。(25)
民族一体化过程:“民族间的一体化意味着在几个民族中产生了文化和自我意识的共同特征。但有别于同化的是,这不会发生一些民族性集团吞没另一些民族性集团。”(26)
此外,“民族过程”理论还特别关注民族属性的变化,它将导致民族成员的民族意识的改变,使人们从一种民族状态转变为另一种民族状态的过程称为“民族变异过程”;将那些表现为一个民族某种基本因素的显著变化,但并不直接引起该民族民族意识改变的过程称为“民族进化过程”。
可见,面对错综复杂的研究内容,苏联民族学者以民族文化发展轨迹为核心,制定了一系列考察标准,对“民族过程”进行划类分型。这样,人们不仅能够对民族发展的总体进程展开宏观描述,而且可以对具体民族的变化进行微观分析,有条有理地勾勒出民族的建构过程,进而探讨民族变化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复杂关系。
四、对“民族过程”理论的再认识
如果仅仅按照常规从群体和时间层面进行思考,“民族”和“过程”是两个互不相干的概念。可是苏联的“民族过程”理论却将二者结合在一起。这不是一种牵强的结合,也不是人为造出的一个时髦的复合词,而是出于研究的需要而自然产生的一个新概念,它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民族”有其独立运行的规律和特征,所以我们研究“民族”,就不能不研究民族变化的规律及特征。但遗憾的是,学者们长期囿于各自学科的传统视角,把大部分的注意力都放在外部环境对民族的影响之上,从而造成了各个研究领域各自为战、条块分割的局面。“民族过程”理论则有助于改变这种状况。
从本质上说,“民族”是一个动态的整体,它按照一定的结构方式在一定的外部条件下存在和发展,所以,只有按照一定的秩序对与民族相关的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寻找主要因素,才能看清民族变化的全过程。基于这种认识,苏联民族学者把民族变化归纳为一个由多个子过程集合而成的母系统过程,提出了“民族过程”的概念。通过分析各个子过程所处的层次和所起的作用,他们发现,尽管民族的走向无时无刻不受到复杂的外部环境的影响——关于这一点学者们已经做了充分的研究,但“民族”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被动承受者,它具有改造和创新环境的能力,而这种能力主要是源于民族的文化。因此,他们在设定“民族过程”理论概念时,并没有强调经济或政治,而是将文化置于显要的位置,并在对民族文化体系的直接“关照”下,发掘民族实践的具体形式和规律。“民族过程”理论这种赋予民族变化以一定的结构和层次,并将民族结构作为一个构造因素融入民族变化框架之中的研究范式,应当说既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又着眼于面向实际;既追求历史探索的深度,又追求现实眼界的广度,为我们对民族变化的现象和规律进行系统、综合的分析提供了一整套比较具体、实用的操作方法。
不仅如此,“民族过程”理论把民族的变化还原到文化层面的研究理念,也非常值得我们借鉴。一直以来,由于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苏联和我国的民族研究都是以少数民族的社会形态为中心,其内容主要是强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等,民族文化研究长期处于从属地位。可是,苏联民族学者在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理论进行实际研究时,逐渐感到马克思过于注重经济研究,忽视了文化在“民族过程”中的重大作用。诚如马克思所言,经济的发展决定民族的变化,但这种决定作用是“归根到底”意义上的,而绝非直接意义上的,文化也是左右“民族过程”的有力杠杆。所以,我们在关注政治和经济的同时,应该更多地从文化的视角对民族变化进行研究。在这方面,“民族过程”理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范例。
此外,民族发展是我国民族学研究的主题。由于民族的发展是发生在“民族过程”之中,民族发展的规律也是通过“民族过程”表现出来的,所以通过研究“民族过程”,我们能够认识和掌握民族发展的规律,从而及时、正确地处理社会中的各种民族矛盾和民族关系,维护社会的稳定,促进民族的有序发展。
然而,“民族过程”理论作为一种“人造”的工具,无论它被设计得多么精细,都无法摆脱抽象的局限性。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苏联学者将“民族过程”抽象为“民族意识”或“民族属性”的变化,提出了“狭义的民族过程”概念,甚至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有意割断“广义的民族过程”与“狭义的民族过程”之间的联系。笔者认为,这是对“民族过程”极度狭隘的理解,它对于深化“民族过程”研究来说是不适当的。诚然,抽象能够增强理论的实用性,但我们无需过高层次的抽象思维和范畴,因为民族是个复杂的体系,各要素之间相互渗透,若只是从牵一发而动全身中去探寻民族属性的变化,对贯穿“民族过程”始终的历史时代、自然条件、经济生活等毫无涉及,必然造成研究过程的简单化和研究成果的“千篇一律”,从而限制了对“民族过程”多样性和丰富性的发现。尤其令人费解的是,“狭义的民族过程”概念假设“民族过程”取决于“民族属性”的变化,它既没有明确说明什么是“民族属性”,也没有对其作用进行合理的和令人信服的解释,其论证明显不够严谨。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民族过程”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所有客观的、变化的“民族集合体”;一是苏联民族学者针对这个“民族集合体”所提出的专业理论概念,其目的是在学科积淀的基础上,启发人们对民族变化进行深层次的、全方位的理论思考。鉴于“民族过程”理论的价值和不足,我们在使用该理论的时候应该尽量避免两种倾向:一是过分笼统地泛泛而论,企图用一个概念概括所有的情况;一是完全锁定研究范畴,过分简单、机械地把“民族过程”视为“民族属性”或“民族意识”的变化。我们在运用苏联的“民族过程”理论分析一些实质性的问题时,应该调动与“民族过程”理论相关的一些概念。
注释:
① 参见〔英〕利昂·庞帕编、陆晓禾译:《维柯著作选》,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52—15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7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2页。
④ [英]柯林伍德著,何兆武、张文杰译:《历史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77页。
⑤ [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5页。
⑥ [英]沃尔什著,何兆武、张文杰译:《历史学导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9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08页。
⑧ [苏]Ю·В·勃罗姆列伊、г·Е·马尔科夫主编,赵俊智译:《民族学基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7页。
⑨ [苏]Ю·В·勃罗姆列伊著、赵龙庚译:《苏联的民族过程》,载《民族译丛》,1984年第4期。
⑩ [苏]В·и·科兹罗夫著、林柏春译:《世界民族过程的某些问题》,载《民族译丛》,1982年第5期。
(11) 参见修世华:《“民族过程”一词在汉语中行得通吗?》,载《民族译丛》,1988年第2期;贺萍:《对术语译名“民族过程”的再思考》,载《世界民族》,2005年第3期。
(12) 周光大:《民族学概论》,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156页。
(13) 朱光磊:《政府过程的学说与方法及其在中国的适用问题》,载《南开学报》,1994年第4期。
(14) 王思斌:《社会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24页。
(15) 参见《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第3564页。
(16) [苏]Ю·В·勃罗姆列伊著,李振锡、刘宇端译:《民族与民族学》,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9、42页。
(17) [苏]Ю·В·勃罗姆列伊、г·Е·马尔科夫主编,赵俊智译:《民族学基础》,第8页。
(18) 参见[苏]Ю·В·勃罗姆列伊著、贺国安译:《论民族学研究现实的迫切任务》,载《民族学译文集》(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年,第304—326页。
(19) [苏]Ю·В勃罗姆列伊、г·Е·马尔科夫著,赵俊智译:《民族学基础》,第78页。
(20) 同上。
(21) [苏]В·и·科兹罗夫著、林柏春译:《世界民族过程的某些问题》,载《民族译丛》,1982年第5期。
(22) [苏]с·и·布鲁克著、周启元译:《民族与民族过程》,载《民族译丛》,1984年第5期。
(23) 参见易明:《苏联民族过程理论述评》,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2期。
(24) [苏]Ю·В·勃罗姆列伊著、赵龙庚译:《苏联的民族过程》,载《民族译丛》,1984年第4期。
(25) [苏]В·и·科兹罗夫著、林柏春译:《世界民族过程的某些问题》,载《民族译丛》,1982年第5期。
(26) [苏]Ю·В·勃罗姆列伊著、赵龙庚译:《苏联的民族过程》,载《民族译丛》,1984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