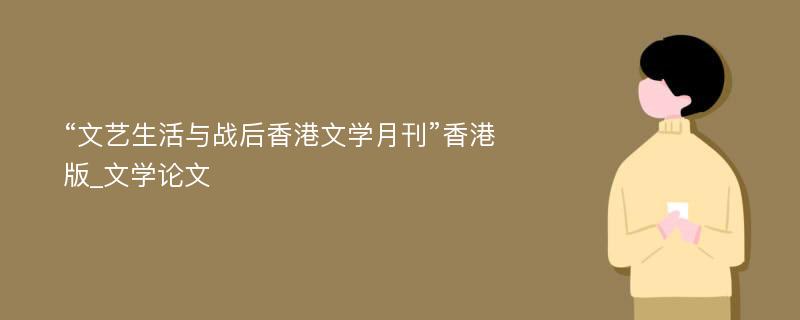
港版《文艺生活》月刊与战后香港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香港论文,战后论文,月刊论文,文艺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4)09-0153-05 一、港版《文艺生活》月刊与战后香港文学的基本属性 关于现代文学期刊和现代文学及现代文学史的关系,刘增人认为:“期刊是现代文学最初的原生态,文学史写作应从原报原刊入手,并倡导对现代文学编辑的研究。”[1]此观点强调了现代文学期刊研究的三重意义,即期刊对于现代文学的原生态意义、期刊对于现代文学史写作的资料库意义以及期刊和期刊出版本身所具有的文化研究意义。目前的期刊研究无出此三者,成果亦斐然。但是,现代文学期刊不仅仅是现代文学的原生态,固然我们需要从期刊文本的阅读中可以体会作家即时的精神状态、感受时代的文化氛围;现代文学期刊也不仅仅是文学史写作的资料库,固然我们需要从文学期刊中获得第一手材料;现代文学期刊也不仅仅是构建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阵地,固然我们需要研究其作为传播媒体对现代文学的传播方式、生成机制等方面的影响作用。现代文学期刊和现代文学本质上是一种共生的关系,是一种互文的关系。二者共生于现代中国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是现代文学期刊的出现使得中国文学从古典文学步入现代文学时期。二者同时具有互文性,相互参照,彼此牵连,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互文本。港版《文艺生活》月刊①与新文学史视野观照下的战后香港文学之间便是这样的一种关系。 从整个中国新文学史的发展脉络来看,战后香港由于恢复了港英政府的管理,在言论上相对自由,因此成为各派文化力量竞相施展才能的舞台,香港文坛也由此成为内地文坛在海外的延伸。在左、中、右三派文化力量中,中共领导并影响的左翼文化活动是香港文坛活动的主流。在文化、宣传阵地上,南来的左翼文人通过创办有影响的报纸、文学期刊、书店、出版社以及学校等方式,②“从作者、编者、读者及其共享空间上构筑成了一个左翼文化影响、传播机制”,“这一机制在全国反独裁、争民主的背景下运行得异常顺畅,几乎主导了本时期的香港文坛。”[2]香港学者郑树森、黄继持、卢玮銮在编选《国共内战时期香港文学资料选》(1945—1949)时也坦承“左翼的活动几乎占绝大部分”,“当时左翼活动俨然是香港文坛活动的主流”。[3]而此时“左翼的文艺工作是全国配合的,华南不过是其中一个环节”,这就使得“内地多项文学论争及政策趋向往往在香港出现”。虽然此阶段的香港文学“不一定与香港本土的文学发展有密切关系”,却可以被看作“整体中国文学其中一个特殊而带地方色彩的部分”。[4] 香港学者基于史料、在整个中国新文学史的视野下对战后香港文学的概括十分到位。首先,无论从战后香港文学的实际创作情况还是从其对于中国大陆文学传统的归属来看,战后香港文学都是“整体中国文学其中”的一个有效组成部分。其次,战后香港文学在中国新文学史中处于一个特殊位置,有自己的特殊性。战后香港文学无论从创作主体(南来左翼文人)、创作内容(左翼文学)还是面向对象(华南及全国的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上,都显示出浓厚的政治性。甚至可以说,战后香港文学完全是50年代新中国文学的一种前奏或预演。最后,战后香港文学虽然作为当代文学的肇始而显示出特殊性,但其仍表现出自身的地方色彩。值得注意的是,战后香港文学的地方色彩不在于香港本土市民文学特色的展示,而是显现为香港的传统文化地域归属——华南的风俗民情和方言土语的独有魅力。华南色彩成为战后香港文学的地方色彩和前述战后香港文学的特殊性密切相连。 战后香港文学所具有的浓厚政治性和鲜明华南色彩这两个特质,在同时期出版的港版《文艺生活》月刊上得到了印证。作为战后香港文学的互文本,港版《文艺生活》月刊中的诗歌、小说和剧本的创作主题和地域色彩也分别表现出政治性和华南性。 二、港版《文艺生活》所刊作品的政治倾向 1948年5月15日《文艺生活》海外版第3、4期合刊中有这样一首《送别诗》:“有我所爱的,是你现在要去的地方。/有我所憎的,也是你现在要去的地方;/我爱它,我的家乡在那儿,/我憎它,独夫武士在那儿”。[5]这首诗典型地展现了南来左翼文人在北望故园时具有的复杂情绪:心向家国的柔情和欲归不得的愤恨。这种具有明确指向的愤恨必然化作某种行动,左翼文人必须利用香港这个没有硝烟的“前沿阵地”来和中国内地进行对话。其行动的结果即文学文本,必然显示出浓厚的政治性。 以体裁来看,诗歌由于自身的特点首当其冲成为左翼文人传递诉求的工具,港版《文艺生活》上相关诗歌的数量亦十分可观。③这些诗歌主要有三个指向。一是同情民众,描画国民党治下各层民众的苦难生活。其中,既有被“沉重的军粮公粮”、“内战的担子”压死的农民尹大嫂,[6]又有“长工帮了一辈子/临死一身空大空”的帮工汉;[7]既有“样样东西涨价,/只有薪水跌价,/为此呈请照加,/折扣不可再打”的公教人员,[8]又有在四大家族挤压下破产、“背负着羞耻/从饥饿里逃生”至美洲成为流浪汉的民族资产阶级;[9]既有“人人怕上小菜场”,“青菜豆腐买弗起,/鸡蛋荤腥依弗要想”的上海市民,[10]又有因为按日征收水费而“唔使讲到喫饭,今日就算係饮水都够艰难”的广州百姓。[11]二是愤恨讽刺独裁、内战,鼓舞民众起而反之。“这是神话里的国度/仓内有粮食生霉/仓外有无数饿殍//这是神话里的国度/空气要抽税/阳光要专卖”;[12]“三民煮,煮三民,三民煮得烂如泥;/三民肥的瘦,三民瘦像柴;/三民填炮眼,三民为狼豺,三民煮家硬说‘前世该’!/宋一碗,孔一碗,总裁肚里盛个满。”[13]“中国大火了!/……/放火的倒是四万万的人民//烧死你呀!暴君/连你的遗嘱也要同时火葬,埋在坟墓里的人民/也要爬出来咒骂你呵!”[14]三是表达对中共执政的憧憬和寄望。“勿说伲穷人一世穷,/共产党一到伲挺起胸,/砖头瓦片亦有翻身日,/共产党一到伲运道通!”[15]“时间开始了——//毛泽东,他站到了主席台底正中间/他站在飘着四面红旗的地球面底/中国地形正前面/他屹立着像一尊塑像……”。[16] 就小说和剧本而言,港版《文艺生活》上相关文本的文学题旨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表现国民党政府、官员、军人对百姓的欺压以及相应的群众的反抗,一是表现共产党政府、官员、军队对百姓的爱护以及群众的拥护。前者如沙汀《催粮》(光复版第7期)、海兵《借粮》(海外版第14期)、陈残云《兵源》(海外版第13期)都揭露了国民党为了内战粗暴地进行征粮、征兵而逼得百姓无法存活的社会现实;陈残云《救济品下乡》(光复版第9期)、楼栖《枫林坝》(海外版第16期)、于逢《一个军人》(光复版第8期)以及瞿白音的剧本《南下列车》(海外版第14期)则描写了内战发生时国民党的乡长、军人对百姓的欺压,以及大溃败时国民党上至立法委员、部长、集团军副总司令,下至伤兵各色人等成为丧家之犬的心态和行为。而蒋牧良《余外婆》(光复版第16期)则讲述了一个被称为“余外婆”的老好先生——一个镇上的国民学校的校长觉醒的故事。孟超《鼻子》(光复版第17期)写的是一个热情、有正义感的青年新闻记者阮放冲破各种阻力终于将重庆学生为反内战、反饥饿而举行罢课的消息报道出来的故事。后者如林柳杞《自从死了黑煞神》(光复版第10期)、伯子《十五只杯子》(活报剧,海外版第10、11期合刊)、岳野《人人说好》(独幕剧,海外版第16期)、楼栖《新破镜重圆记》(南方采茶戏,海外版第17期)以及丁波、林韵《姊妹献粮》(秧歌剧,海外版第20期)都表现了共产党军队对百姓的爱护以及百姓对其的拥护和爱戴。林柳杞《自从死了黑煞神》写的是一个八路军和老百姓围绕一头黑猪发生的喜剧故事。小说笔调轻松幽默,尤其表现在描写炊事员李叫好抓猪以及“黑煞神”死后油醋店老板杨寿康的心理活动上。小说令人啼笑皆非的结尾也让人们对国民党与老百姓的关系有了深入的认识。而直接将国民党和共产党对百姓的不同态度进行对比、构思成章的是岳野《人人说好》。剧本处处使用对比手法,使得国共军队对百姓截然不同的态度清晰呈现。 左翼文人创作的文学主题还包括表现农民和地主的矛盾冲突。这些文本除了周而复《春》(光复版第10—13期)成稿于抗战胜利前夕,描写解放区的农民(阎争先、陈五儿等)如何在政府帮助下和地主徐绍堂(绰号坏莞豆)在减租减息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其余文本都是在国共内战期间写成,以国统区农村和农民为描写对象,并以表现农民和地主的残酷斗争为主旨。如《卢大爷回来了》(碧野,光复版第6期)、《田家乐》(沙汀,光复版第14期)、《逼上梁山》(温涛,独幕剧,光复版第15期)、《老坑松和先生秉》(华嘉,海外版第5期)、《一个最后的男子》(岑砧,海外版第10、11期合刊)等等。 以新文学史的视野来观照港版《文艺生活》中的上述文本,我们发现,左翼文学力量所主导下的战后香港文学——无论是用诗歌来向内地的隔空“喊话”,还是用小说和剧本去表现国共斗争(占多数)和地主农民斗争,其实都指向表现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即无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以及与封建地主阶级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资产阶级的矛盾。战后香港文学所呈现出来的这种浓厚的政治性特点正是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新中国文学所具有的特质。在洪子诚根据“权威文学评论”和“各次文代会对创作的总结性评述”所列举的50—60年代的21篇代表小说中,[17]以表现国共阶级战争和建国后农村阶级斗争为题材或背景的有16篇,占了76%。④50—60年代小说对阶级矛盾的重视正是代表左翼文学在战后香港的延续和拓展。战后香港文学是左翼作家在理论和创作上为推行延安文艺整风所确立的“文艺新方向”——为工农兵服务的无产阶级文学之后所取得的成果,而50—60年代的文学则是进一步巩固延安“文艺新方向”、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一个起始时期和重要阶段。二者所带有的浓厚政治性是一以贯之的。 三、港版《文艺生活》所刊作品的华南地域倾向 通过对1945—1949年这一时期的香港文学资料进行整理,香港学者发现,当时居留香港的众多左翼文人在思考问题的时候都有一种“要把香港归入华南或更大的中国状况去处理”的潜在思路,因此“南来文人虽然是谈香港,但目的并非为香港”。[18]而司马文森在香港写的《谈加强时间性、战斗性和地方性》里重点强调的地方性也不是香港,而是整个华南。[19]在这种思路下,在战后香港进行的一些文学运动其实和香港本身关系并不是很大。如声势很大的方言文学运动便是如此。 当然,“在香港”的文学必然要与香港发生某种关联。港版《文艺生活》也有一些以香港为描写对象的文学作品。如海外版第6期上就有一组名为《香港风情画》的6首短诗和海兵的一篇报告文学《风灾》。《风灾》写的是香港占四大渔区第二的长洲在1948年7月遭受大风灾后渔民所遭遇的惨剧。这篇报告文学和稍后海外版第7期上发表的小海燕《种子》、戈云《周求落魄记》,由于在取材上关注了香港受灾的渔民、摸索活路的流浪少年和走私冒险的鳄鱼头而得到了司马文森的肯定。小说和剧本中亦有以香港为背景表现内地人到香港讨生活的种种情形的,但香港作为叙述背景往往比较模糊,内地却清晰得多。如陈残云的小说《受难牛》(海外版第3、4期合刊)讲的是内地农民受难牛到香港“避风势”,由于他“胆正、命平、力大”而在油麻地苦力堆里站住了脚的故事。秦牧《情书》(海外版第13期)则通过描写荣嫂请写字先生给出走香港三月有余的丈夫亚荣写信的方式,侧面表现了当时内地乡村的生存环境。《受难牛》和《情书》虽说和香港有关,但它们其实更多地具备“岭南乡土小说”的特点:即“在明晰的政治背景上”,“展开主人公离乡漂泊的命运;在关注乡村小人物命运中弥漫开浓郁的南国风味,在对南中国乡俗风情清婉细切的描写中不时渗透出某种政论倾向;着力开掘方言土语的生活蕴量,人物对话甚至全部用方言,以增强小说对华南读者的阅读冲击力。”[20]在《情书》中,荣嫂絮絮叨叨的话里透出很多华南独有的乡俗风情:隔壁二叔刚死,孩子吃人家给的糕不吉利;孩子拉肚子是“湿热”,写张红纸贴到榕树上,“契给榕树爷”;等“天变地变”亚荣平安回家便“烧猪还神”;荣嫂被人非礼,她婆婆到乡公所交涉要求“烧爆仗”、“赔金花红绸”;“一个月喝几次凉茶”……荣嫂的半方言叙述和写字先生的文言总结相互映照,使得这些风俗民情更显生动鲜活。但比较而言,秦牧的文字只能说是带有方言性。真正运用方言来增显作品华南色彩的要数陈残云、华嘉和易巩等人。陈残云《受难牛》和《救济品下乡》(光复版第9期)、华嘉《老坑松和先生秉》(海外版第5期)、易巩《珠江河上》(光复版第7期)中的叙述语言都是普通话,人物对话却用了很多方言。如《珠江河上》,小说开头便是一个在珠江河上撑艇妇人的咒骂:“衰瘟鸡呀!十世不修德呀!这样冤气的埗头,在这里撑过艇的都没利市呀!……丢那妈,你撑吧!你撑吧!一早撑到黑,撑得多少渡?又要埗头钱,又要艇租,又要牌照费,人心没餍足的契弟,坐地分肥的灾瘟呀!又不见水鬼拉他们下水呀!又不见他们吃了肠穿肚烂呀!”这样一个满嘴粗话、对盘剥她的埗头、警察不吝最恶毒咒骂的妇人却爱憎极为分明,面对发生在河上的抢米事件,她一直在为抢米者加油、指引,而大骂为警察撑艇的两个蛋家妹。整个抢米过程在妇人纯粹方言的咒骂和指引下显得十分惊险。通过方言土语的运用,易巩成功地塑造了一个饱受苦难、愤怒喷张又爱憎分明的个性人物。应该说,《珠江河上》是一部既反映华南底层人民生活现实、又颇具华南色彩的出色作品。 由港版《文艺生活》的上述作品看来,战后香港文学的地方色彩不在香港而在华南。华南独有的风俗民情和富有魅力的方言土语使得战后香港文学染上鲜明的华南色彩。 在一些香港学者看来,战后香港文学处于尴尬的境地。一方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战后香港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中间站”角色,为新中国的文艺理论与实践提供了彩排的舞台和空间。而另一方面,由于左翼文学主导文坛,香港本地文学的发展无形中受到了压抑,貌似繁荣的战后香港文学却只是“在香港”的文学,而不是香港文学本身主体性的建设。且不说主导战后香港文坛的左翼文学明确显现出的政治性特点和香港社会的市民趣味大相径庭,即使那些南来作家创作的和香港相关的小说也并不具备香港本地的特点。这些小说仍然大多以内地华南农村为题材背景,得以让广州人和香港人增加切近之感,战后香港文学的地方色彩也由此被渲染为华南色彩而非市民香港的本土特色。事实上,真正以香港小市民趣味为主、体现香港本土文学特色的还是香港本地的作家如侣伦、经纪拉(三苏)等人。但由于当时左翼文人、左翼作品主导香港文坛,香港本土作家的作品虽有受众,但在数量上还是稍为逊色。因此,战后香港文学必然作为“整体中国文学其中一个特殊而带地方色彩的部分”而存在。 对于战后香港文学这一特定时空域的文学进行研究,取广泛的文学文本、历史文本来讨论固然是一种方法,取一个动态开放又相对凝固的文学期刊作为载体,探究期刊文本和文学历史之间的互文共生性,从而给特定时期的文学、文学史做侧面画像,也不失为期刊研究和文学研究方法的新尝试。 注释: ①《文艺生活》月刊由司马文森主编,1941年创刊于桂林,1950年停刊于广州,共出了58期。其中,光复版第7至18期和海外版第1至20期,即1946年8月至1949年12月25日期间的这28期(中间有四个合刊)《文艺生活》月刊都是在香港出版的。这28期《文艺生活》即本文题中所指的港版《文艺生活》。 ②报纸如《正报》(1945年11月13日创刊),《新生日报》(1945年12月15日创刊),《华商报》(1946年1月3日复刊),《人民报》(1946年3月1日创刊)以及香港版《文汇报》(1948年9月9日创刊)等等;文学期刊如《中国诗坛》(1946)、《野草》(1946,后改为《野草丛刊》)、《文艺生活》(1946)、《大众文艺丛刊》(1948)、《新青年文学丛刊》(1948)等等;书店如生活书店、南国书店、民主书店、新知书店等等;出版社如新民主出版社、人间书屋、大千出版社、有利印务公司等等;学校如达德学院、建中工商专科学校、香岛中学、培侨中学等等。 ③《文艺生活》光复版(1946.1.1—1948.1)共17期,共发表诗歌97篇,反映上述种种诉求的就有88篇,占了91%,平均每期5篇。《文艺生活》海外版(1948.2—1949.12.25)也是17期,共有诗歌48篇,相关诗歌31篇。相关诗歌数量的减少缘于国共战局的变化。随着1948年以后共产党开始转入反攻,1948年到1949年间反国民党的诗歌便消弭了不少。但从1946年到1949年,《文艺生活》上刊发的相关诗歌达到了119篇,数量还是十分庞大的。 ④前者如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吴强的《红日》、曲波的《林海雪原》、罗广斌和杨益言的《红岩》等;后者如柳青的《创业史》、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冯德英的《苦菜花》、浩然的《艳阳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