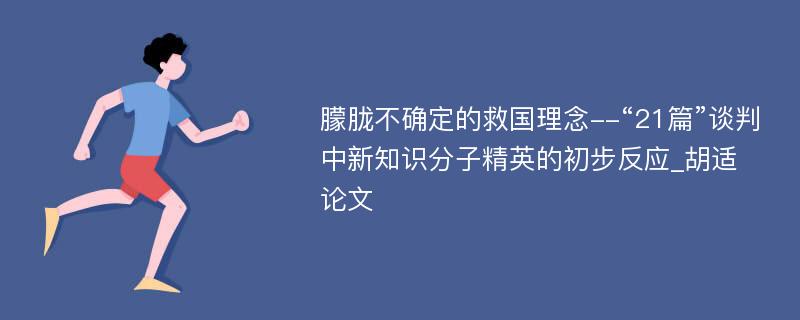
朦胧的、不确定的救国理念——“二十一条”交涉期间新式知识精英的初步反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不确定论文,二十一条论文,朦胧论文,理念论文,精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15年1月,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后,中国各界都感到极严重的威胁,感到日本欲独霸中国的咄咄逼人的野心。但人们的反应是各不相同的,以袁世凯为代表的统治阶级最终选择了屈辱求和(陆军总长段祺瑞等军人虽提过不惜以一战拒绝日本,但并未真正付诸行动);① 国内知识界、商界等一度掀起排日和抵制日货的运动,进行了自发的抗争;② 孙中山革命党人内部此时分裂为不同派别,黄兴、陈炯明、柏文蔚、钮永建、李烈钧等一派表示将抵御外侮置于优先地位,“谨守绳墨,使不危及邦家而已”,但中华革命党孙中山、居正、陈其美等却“对于此事,默不一言”,认为根本问题不解决,以在野之身表示抗议于事无补,号召党人应先“急速去袁”。③ 而堪称中国新式知识界的精英、将在其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崭露头角的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胡适等人,此时的表现和反应又是如何呢?这是本文探讨的问题。④
一、李大钊:“策政府之后,以为之盾”
辛亥革命失败到五四运动之前的几年,即使不是20世纪中国最黑暗的一个时期,也是中国最茫然不知所措的一个时期,孙中山民主共和革命的理想昙花一现之后,即屡遭挫败,中国人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之路,似乎已走到尽头,新的救国之路在何方?还没有人能够作出回答。恰在此时,日本向中国提出了空前苛刻的“二十一条”,中国人感到了新的灭顶之灾来临前的恐惧,但这残败贫弱的国家,该如何应对?这时还属于分散的、立志救国却无从救起的新式知识精英作出了不尽一致的反应,提出了自己朦胧而初步的救国主张,但这些答案相对于万分艰巨的救国重任而言,还是显得太肤浅幼稚了。
这一年,蔡元培47岁,在法国;陈独秀36岁,在日本;李大钊26岁,在日本;胡适24岁,在美国。
在这些人当中,对“二十一条”事件作出最直接、最激烈反应的是李大钊。与蔡元培、陈独秀等参加过反清、反袁的革命家不同,此时的李大钊还只能算是一个刚露头角的青年志士,虽有充沛的爱国激情与献身民族解放事业的崇高志向,但其政治见解和政治觉悟都还处于尚不成熟、更不稳定的状态,1907—1913年,也即他18—24岁的一段,他在袁世凯创办的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了6年,交游的圈子主要是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及北洋法政学会,并且常常站在拥护袁世凯的立场批评革命党人。1914年初,他到日本留学,9月进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本科,在日本因投书章士钊主编的《甲寅》杂志,结识章士钊,从而接触到大批革命党人,他的社会关系、政治见解才开始发生至关重要的变化,开始对袁世凯的专制独裁表示不满(但彻底转向反袁是在1915年下半年之后)。因此,1915年1月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时候,他对于事件的反应,就与许多留日学生一样,带有明显的对袁世凯政权还抱有幻想的青年爱国知识分子的痕迹。同时,也受到了站在黄兴派立场的章士钊的影响(即“停止内争,一致对外”)。⑤
1915年2月11日下午,在日本东京神田区基督教青年会所在地,3000余名中国留学生召开大会,反对“二十一条”,李大钊积极参与,并以留日学生总会李大钊的名义撰写了《警告全国父老书》。6月又发表《国民之薪胆》一文,8月在《甲寅》杂志发表《厌世心与自觉心》,他以沉痛的笔调,揭露日本在1894年甲午战争、1904年日俄战争和1915年“二十一条”对中国日益猖獗的侵略,意在唤起国人挽救国家民族的觉悟,不要忘了救国的责任,但国人应如何救国呢?李大钊开出的是这样的药方:“吾国民今日救国之责维何?曰:首须认定中国者为吾四万万国民之中国,苟吾四万万国民不甘于亡者,任何强敌,亦不能亡吾中国于吾四万万国民未死以前。必欲亡之,惟有与国同尽耳。……吾国民应以锐敏之眼光,沉毅之实力,策政府之后,以为之盾。决勿许外敌以虚喝之声,愚弄之策,诱迫我政府,以徇其请。盖政府于兹国家存亡之大计,实无权以命我国民屈顺于敌。此事既已认定,则当更进而督励我政府,俾秉国民之公意,为最后之决行,纵有若何之牺牲,皆我国民承担之。……虽亡国杀身,亦可告无罪于我黄帝以降列祖列宗之灵也。”[1]119
李大钊提出国民要“策政府之后,以为之盾”,要“智者竭其智,勇者奋其勇,富者输其财,举国一致,众志成城”,说明他对袁世凯北京政府还抱有某些幻想,以为人民还可以在这样的政府之下,一致奋起,各尽天职,挽狂澜于既倒。但“最后之决行”何指?国民究竟如何奋起,如何尽其天职,是武力抵抗,还是经济绝交,民众是否应该组织起来,抵抗强敌,拯救国家,究竟应从何处着手?李大钊并未提出具体可行的主张,实际上,李大钊这时还未找到救国的答案。
中日“二十一条”交涉签字之后,李大钊在6月发表的《国民之薪胆》一文,对于政府仍是相当体谅和宽容的,他说:“弱国外交,断无不失败之理,吾人今欲论政府办理此次交涉之失败与否,惟问其失败之程度如何。然国家根本之实力,既脆弱不足以自支,吾人亦何敢侥幸于外交当局一时比较之胜利,……故对于政府,诚不愿加以厚责,但望政府之对于国民,亦勿庸其欺饰。盖时至今日,国亡家破,已迫眉睫,相谋救死之不遑,更何忍互为诿过,互相归咎,后此救亡之至计,端视政府与国民之协力。”他写此文的目的,“亦欲促政府之反省,奋国民之努力而已。”[2]131 所谓政府之反省,李大钊指的是:“政府果不愿为亡国之政府,则宜及早觉悟其复古之非,弃民之失,速与天下更始,定根本大计,回复真正民意机关,普及国民教育,实行征兵制度,生聚训练,以图复此深仇奇辱。”[2]134 此处李大钊对袁世凯政府有所批评,包括“复古”、“弃民”、操纵“民意机关”等等,但李大钊是在认同现政权合法性的前提下提出这些批评的,希望这个政府能痛定思痛,从此改弦更张,担负起政府所应尽的责任。
所谓国民之奋发,李大钊指的是:“国民而不愿为亡国之国民,亦宜痛自奋发,各于其本分之内,竭力振作其精神,发挥其本能,锻炼其体魄,平时贡其知能才艺于社会,以充足社会之实力,隐与吾仇竞争于和平之中;战时则各携其平时才智聪明素积之绩效,贡其精忠碧血于国家。”[2]134 这种对于民众的希望还是很泛泛的、缺乏具体指导和真知灼见的一般性期待。
但此时的李大钊表现出来的最可贵的品质,就是这种在极其黑暗、极其险恶的环境下决不放弃、决不气馁的乐观主义奋斗精神,尽管还看不到什么希望,还没有具体的、切实可行的办法,但他始终鼓励人们要向前奋斗,要有不顾千难万险去拯救国家的勇气。他也深知,此时的中国正遭逢“晦盲否塞之运”,“一切颓丧枯亡之象”呈现无遗,“政治之罪恶既极,厌世之思潮,隐伏于社会”,“伤时之士,默怀隐痛”,“哀哀斯民”,了无“生趣”,国家很不“可爱”。[3]136—137 但不能因此就放弃对国家的责任,就不为这个国家的未来而奋斗。而应当有“自觉心”,“自觉之义,即在改进立国之精神,求一可爱之国家而爱之,不宜因其国家之不足爱,遂自断念于国家而不爱。更不宜以吾民从未享有可爱之国家,遂乃自暴自弃,以侪于无国之民,自居为无建可爱之国之能力者也。”[3]137 表现了他坚决的爱国反帝立场。
李大钊对袁政府被迫签字后,一些人对国事绝望而愤然自杀的行为,不表赞同,他说,“近者中、日交涉,丧权甚巨,国人愤激,骇汗奔呼。湘中少年,至有相率自裁者。”这种“爱国之诚”,固然可嘉,但决不可提倡,因为国民中还处于“昏梦罔觉者”已“去其泰半”,“其余丧心溃气者又泰半”,“聪颖优秀”之人本来就甚“寥寥”,如果这批人再“或以精神,或以躯干,纷纷以向自杀之途”,则国家就真是“万万无救矣”。李大钊此处提出了一种“精神自杀”的概念,这应是当时国中多少志士救国无望、意气消沉的写照。他勉励国人也是以此自勉:“中国至于今日,诚已濒于绝境,但一息尚存,断不许吾人以绝望自灰。”“即怀必死之志,亦当忍死须臾,以待横刀跃马,效命疆场,则男儿之死,为不虚死。”[3]139—140 李大钊在此万马齐喑的时期还能有此顽强的意志和毅力,诚不愧为后来一个新时代开启者的风范!
二、蔡元培:提倡“御侮会”与“专在社会间效力”
蔡元培是国民党的元老,但在党内多是从事革命的宣传鼓动工作,辛亥之后,出任教育总长,办过“进德会”,组织过“留法俭学会”,与李石曾、吴稚晖等过从甚密,对发展近代教育学术文化兴趣浓厚,是学者型的革命家,又是有革命精神的学术大师,这时因反袁在国内无法立足,与李石曾等流亡法国,致力于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与学术文化活动。⑥ 在得知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消息后,与在法国的汪精卫、陈璧君、李石曾、谭熙鸿及在伦敦的吴稚晖等有过会商和讨论,提出过一些或激进或平缓的方案与设想,意见未能统一,实际上也还处在探讨之中,稍后蔡元培且流露出不愿再直接参与政争的打算。
事起之初,蔡元培还是想有所动作的,他说:“日本竟下辣手,虽以我等之奄奄如陈死人者,亦大为之刺激,以为不可不采一种急进之方法,以为防御。”[4]230 蔡起草了“御侮会”会章若干条,是一种唤起民众自发御侮的设想,所拟条文倒是简明扼要,其主要内容为:
(一)本会以凭藉己力(不倚赖政府,不倚赖军队)、济度同胞、排除外侮为宗旨。
(二)本会会员应尽之普通责任:1.锻炼体魄;2.了解并自备适当之武器,如匕首、炸弹、手枪、毒物等;3.养成抑强扶弱之习惯;4.力持可杀不可辱之气节;5.见敌人侮我同胞者击之,事变如有株连,则挺身任之;6.不购敌人货物(书报及武器例外);7.不乘敌人船舶;8.不与敌人之银行交易,亦不用其钞票;9.不租屋给敌人;10.不售地产给敌人;11.不服役于敌人;12.华人有犯6—11条者,竭力劝止之;13.有华人助敌而侮我同胞者,诛之。
(三)本会会员得量力以尽之特别责任:1.入敌境而侦探之;2.入敌境而以相当之手段破坏敌侮我之阴谋及武器。
(四)本会劝导同胞之种种设备:1.印刷品;2.公开或秘密的演讲会。
(五)本会为会员尽责提供各种便利条件,如采运廉价货物,增设交通机关;收购地产,介绍职业;制备各种武器等。
此外还有与各国革命党联络之类。[5]351—352
在民族主义进一步觉醒的时代,一方面,这些办法反映了蔡元培等中华民族先进分子较为清醒的、自主的爱国意识,一种在现政权不可恃的情况之下,自觉、自动起来承担国民责任的可贵精神,是近代中华民族在捍卫民族生存、唤醒民族意识的长期奋斗过程中一个不能忽视的环节。但另一方面,在政府和军队对其应尽的职责缺位之时,仅靠上述这些办法,能否真正有效地实现御侮救亡的目标?如何使民众都来参加并齐心协力照此实行?蔡元培等流亡者能否深入到民间去做危险艰苦的宣传发动工作?这些在当时恐怕都还是一种过于奢侈的要求。
在章程提出讨论时,汪精卫提出,此会本属秘密性质,不必用会名,也无须会章,“但言抵抗强权之办法亦可”,得到大家的同意。
对于是否应立即付诸行动,李石曾“仍持先筹万国革命之说,又颇谓日本之事,似尚有从容对付之余地,不可过于张皇云云”。汪精卫则认为,“万国革命,缓不济急,目前只能持抵抗日本之惟一主义”,并打算先到南洋后根据局势发展再定或急或缓的应对办法。所谓“急”法,就是“归国效死”。所谓“缓”法,则是“筹款以设机关”。谭熙鸿提出,如果是设机关,最好是设立学校,“行精神教育”。[4]231—233
待北京政府基本接受“二十一条”、不会以“开战”抵拒日本之后,下一步如何进行,蔡元培设想了自称是“老生常谈”的三种方案,即“(一)从根本上解决,即前在杜城所商之扩充教育事业;(二)提倡抵制外侮之精神,即从前汪先生在时所拟之御侮会之类;(三)先革政府而借政府之力以修战备,及振兴教育实业。”第一种办法,即以教育宣传唤起国民觉悟的办法,蔡主张“仍当积极进行”;第二种办法,即振奋国民精神、共同抵制外侮,蔡说,此法汪精卫、陈璧君诸人“必尽力鼓吹”,且抵制日货也已取得相当成效,“或不至呈虎头蛇尾之旧观”;第三种办法,则是要先推翻现政权,在新政府主导下充实国力、捍卫国权,蔡认为,在袁世凯接受了“二十一条”的“今日或亦一机会”,但这件事“非相当之人不能当其冲,而相当如汪先生者,且逊谢未遑,似只能听李(烈钧)、钮(永建)、章(士钊)、彭(允彝)诸人集合而为之”。但究竟应取何种方案,蔡元培也无明确的倾向性意见,他问吴稚晖,“对于现在之时局尚有别种急救之方法否?”[4]245 在另一封信中,他提到“精卫先生曾来一函,对于中日交涉结束后之情形,仍抱悲观”。[4]247 他自己则表示,“将来如弟果归,则必不投身政治之旋涡,而专在社会间效力”。[6]256反映了此时蔡元培等人虽仍怀忧时救国之抱负,却一时拿不定一种切实可行的具体方案而踌躇徘徊之境况。
三、胡适:“以镇静处之”与“执笔报国”
此时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的胡适倒是有他自己的一套见解,这时胡适到美已近5年,在留美学生社团中相当活跃,且经常投身于美国的现实社会政治生活中,加以体验和观察,对于一些重大社会政治问题,已形成一些较为系统的看法。当大多数留美学生提出激进的反日爱国主张之后,他公开站出来表示反对。在他看来,中国现时还无力与日本抗衡,激烈的抵抗也无济于事,只能是长期积蓄力量,恢复国力,以待将来。他提出个人须采取负责任的行动,不作一时无谓的牺牲,应冷静地培植救国的能力,使每个人的作用得到最有效的发挥。应当承认,胡适的主张也有其可取的一面,1915年的中国,确实还无可能战胜日本。主张立即以举国之力作最激烈、最彻底之抵抗,宁抵抗而牺牲(如他的一些留美同学所倡言的“对日作战,必要的话,就战至亡国灭种”,“纵使对日作战不幸战败而至于亡国,我们也只有对日作战”),精神固可嘉,但确实还不是一种“清醒”、“理智”的应对。要爱国,但也必须考虑爱国的策略与实效,有策略、有方法,不一味鲁莽冲撞的爱国,与不爱国是完全不同的。
在得知日本逼签“二十一条”的消息之前,胡适已认识到日本是将来中国最大的威胁,他说:“中国之大患在于日本。日本数胜而骄,又贪中国之土地利权。日本知我内情最熟,知我无力与抗。日本欲乘此欧洲大战之时收渔人之利。”“总之,日本志在中国,中国存亡系于其手。”但胡适这时的一个想法是,要将日本作为宣传其所信奉的人道主义的首选对象,对这个“信强权主义甚笃”的“霸者”加以沟通感化。鉴此,就要认真研究日本的语言文化,提高沟通两种文明的能力,并一时产生了自己亦到日本留学数年的念头。他说:“吾之所谓人道主义之说,进行之次宜以日本为起点,所谓擒贼先擒王者也。且吾以舆论家自任者也,在今日为记者,不可不深知日本之文明风俗国力人心。……不可不知日本之文字语言,不可不至彼居留二三年,以能以日本文著书演说为期。吾国学子往往藐视日本,不屑深求其国之文明,尤不屑讲求沟通两国诚意之道,皆大误也。”[7]26—27
论到个人的责任,胡适说:“今日祖国百事待举,须人人尽力始克有济。位不在卑,禄不在薄,须对得住良心,对得住祖国而已矣。幼时在里,观族人祭祀,习闻赞礼者唱曰:‘执事者各司其事’,此七字救国金丹也。”[7]58
胡适是一个爱国者,但也是一个较为典型的渐进的、文化教育救国论者,他认为:“国无海军,不足耻也;国无陆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无公共藏书楼,无博物院,无美术馆,乃可耻耳。我国人其洗此耻哉!”[7]57
“二十一条”事起,留美学子“开特别会”、“议进行方法”,但胡适却发表《致留学界公函》,主张“以镇静处之”。他说:“以余观之,吾辈学子,远去祖国,当务之急,当以镇静处之。……不可让报章上所传之纠纷,耽误吾辈之学业。”要严肃、冷静、不惊、不慌,安于学业,力争上流,“为将来振兴祖国作好一番准备,只要她能幸免于难——余深信如此——若是不能,吾辈将为在废墟上重建家园而努力!”[7]89—90
一直到后来的抗战初期,胡适都是一个唯实力、唯武器论者,这时也已露出端倪,他声称,“此刻言及对日作战,简直是发疯。我何以作战?主笔先生说,我有一百万敢决一死战之雄狮。且让大家来看一下事实:我仅有十二万士兵谈得上是‘训练有素’的,然其装备甚为简陋。而且,我海军毫无战斗力:军中最大之战舰乃一三等巡洋舰,其排水吨位仅为四千三百吨。另外,军火又如何呢?我何以作战?”对主张抵抗者,胡适简直就是痛斥:“余赤诚以报祖国,此时言及作战,纯系一派胡言,愚不可及。其后果,不仅于国无所改观,而且所得只是任人蹂躏!任人蹂躏!再任人蹂躏!”[7]90
但胡适自己也承认,事情究竟如何演变和发展,中国的出路究竟何在,他也还没有找到答案:“远东问题最终解决之症结,不系于对日作战,不系于某些列强施加之外来干涉;不系于任何治标之方法,也不是由列强在华势力均衡或门户开放政策所造成的;更不系于采用日本之门罗主义;凡此种种皆不是最终解决之方法。真正、最终解决之道一定是另有法门——它较吾人今日所想象者当更为深奥。余也不知其在何处,只知他不在哪些地方罢了。还是让吾辈作些冷静、客观之研究吧!从长计议罢!”实际上,这同样流露了一种还不能找到出路的、困惑而迷茫的心态。⑦
胡适不赞同以武力抵抗,但正面评价了国内抵制日货的运动,说这是目前适宜的抗拒行动,并认为“上策”还是要从长远着手:“东京及祖国书来,皆言抵制日货颇见实行,此亦可喜。抵制日货,乃最适宜之抗拒,吾所谓道义的抗拒之一种也。”是不得已而求其次的办法。“上策为积极的进行,人人努力为将来计,为百世计,……必不得已而求目前抗拒之策,则抵制日货是已。若并此而不能行,犹侈言战日,可谓狂吠也已!”[7]114
胡适此时因其反战而受到一些留学生的痛斥,⑧ 但他在这前后几次撰文驳斥美国一些报纸上贬低中国或主张中国应由日本管制的论调,以他的方式为国效力,即他所谓的“余无能逐诸少年之后,作骇人之壮语,但能斥驳一二不堪入耳之舆论,为‘执笔报国’之计”。[7]61 如2月份的《致“新共和周报”书》、《致“外观报”书》,3月4日《致“标准邮报”书》,[7]73 5月4日的《致绮色佳“每日新闻”书》。对于有人在报上声称共和制不适于中国、远东问题之解决视乎“日本对中国事务之管理是否负责”的论调,胡适指出:“余作为一名中国人,深知同胞之志气与抱负,因此余敢断言:任何想要在中国搞日本统治或‘管理’之企图,无异于在未来之中国播下骚乱和流血的种子”,“他定将看到年青而英勇的热血流遍我华夏之共和国!”尽管现在中国还无力抵抗,但“君不见反日之仇恨已燃遍了神州大地么?”⑨ 胡适在另一篇公开信中指出:“纵然日本对中国之统治,在短时间内会取得像模像样之成功,中国人难道就会长期容忍日本来掌握它们自己之命运乎?”“不论过去还是现在,日本在中国之所作所为无异于是在中国人心中播下仇恨之种子,也是在持人道主义之各国的眼中自降身价。”[7]116—117
在胡适看来,由于中国完全无力抵抗,即使暂时全部接受日本的条件,也是无可奈何之事。因此,当交涉结束在别人视为“国耻”的不平等条款签字之后,他反而还有几分庆幸,对袁世凯政府和日本都存了一点幻想:“此次交涉,余未尝不痛心切齿,然余之乐观主义终未尽消。盖有二故焉:(一)吾国此次对日交涉,可谓知己知彼,既知持重,有能有所不挠,能柔亦能刚,此则历来外交史所未见。吾国外交,其将有开明之望乎?(二)此次日人以青岛归我,又收回第五项之要求,吾虽不知其骤变初心之原因果何在,然日人果欲以兵力得志于中国,中国今日必不能抵抗。日之不出于此也,岂亦有所悔悟乎?吾则以为此日人稍悟日暮途远倒行逆施之非远谋之征也。”[7]129
胡适学究式的、偏于冷静的实用主义,使他在国家民族灾难深重的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少了一点必要的激情和牺牲的勇气,而总是在承认现实的前提下来谋求对现状的改变。较为理性、客观、冷静是他的长处和优点,他一生孜孜于追求中国社会的合理与公正,有其旁人不及之处。但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对于革命的洪流和热血,实在是太饥渴了!中国的复兴无疑需要具备各种条件,需要聚合各种力量,需要踏实的耕耘和渐渐的积累,但在那个特定的时段,无数呼啸着、呐喊着的战士和青年的血,恐怕同样是迫切需要的吧。
四、陈独秀:“国家主义,实为吾人目前自救之良方”
笔者暂未找到陈独秀对“二十一条”问题直接反应的资料,但事件前后,他对国事发表过十分激烈的言论,这当然是以这期间包括“二十一条”交涉在内的若干重大事件的刺激为背景的。
1914年11月lO日,陈独秀在《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中指出,国事如此不堪,政府固难辞其咎,国民之程度不够,也是重要的因素:“今吾国之患,非独在政府。国民之智力,由面面观之,能否建设国家于二十世纪,……诚不能无所怀疑。”惟现在的国家,不仅不能尽其御侮保民之职责,却以残民为能事,人民有理由不爱这样的国家,有恶国家还不如无国家,这样的国家就算是亡了也不足惜:“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务,其国也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眼下的中国,就正是这样的国家:“若中国之为国,外无以御侮,内无以保民,不独无以保民,且适以残民,……如此国家,一日不亡,外债一日不止;……杀人敛钱,亦未能一日获已。”现在的中国,甚至连殖民地、租界都不如,“贪吏展牙于都邑,盗贼接踵于国中,法令从心,冤狱山积,交通梗塞,水旱仍天,此皆吾人切身之痛,而为印度、朝鲜人之所无。……以吾土地之广,惟租界居民得以安宁自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即亡国瓜分,亦以为非可恐可悲之事”。这样的国家,根本不值得去爱,自然也没有必要去保卫。“盖保民之国家,爱之宜也;残民之国家,爱之也何居!”[8]118—119
陈此处所说的“国家”,与李大钊说的“国家”、胡适说的“祖国”,意思颇有不同,他说的“国家”,本意指的应是政府,即他稍后所说的“伪国家”。他以这样决绝激进的方式谈论这个问题,目的就是要针对这时还“代表”着中国的袁世凯政府。是对袁世凯专制独裁统治最彻底、最悲愤绝望的否定。虽然以现在的眼光看,用语稍稍有些偏激,但陈独秀以安徽都督府秘书长的身份在二次革命失败后被抓被绑、险被袁氏爪牙杀害、亡命海外的经历,国事日非、长长的黑夜看不到尽头的无从排解的压抑,苦苦求索、又一时找不到正确答案的难言的苦闷,这恐怕是我辈没有身临其境的今人很难体味到的处境,他何尝不知道要提倡爱国,何尝不知道“亡国为奴,岂国人之所愿”,[8]118 但他说出来的,却偏偏是这样一些看似有些偏激的、绝非四平八稳的肺腑之言,这毋宁是我们民族的思想巨人陈独秀在重新崛起前的一个短暂的阵痛,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拯救者为震醒无数还处于浑噩中的同胞所发出的最愤激的吼声!
以这种对袁政府深恶痛绝的态度,在“二十一条”事起之后,自然不能想象陈独秀还会有什么“策政府之后”的想法,对于像甲午之后那种奋起救亡的激情,也已感到无益和厌倦,陈独秀甚至对政治革命,都已失去信心(这一点,与蔡元培倒有共通之处,这恐怕也是其后新文化运动中二人相与携手的思想基础之一),而开始意识到:应当从事思想的革命!
关于这一点,据刘仁静回忆,陈独秀曾对他讲:“袁世凯承认二十一条的时候,对他刺激很大,他认为中国还是军阀当权,革不成什么命,在中国进行政治革命没有意义,要从思想革命开始,要革中国人思想的命,因此他就写文章批判孔子,批判旧礼教。”[9]214 这样,他就与孙中山革命党,与此前辛亥时期的同志柏文蔚等区别开来。
1915年6月,陈独秀回到上海的法租界办杂志。9月,《青年》杂志创刊,他又以一个战士的身姿披挂上阵了,在创刊号开篇《敬告青年》中,明确举起了“科学与民主”的大旗,一场对于封建专制主义的更为坚决彻底的进攻开始了。陈独秀旗帜鲜明地发出了向“恶社会”挑战的誓言:“人之生也,应战胜恶社会,而不可为恶社会所征服;应超出恶社会,进冒险苦斗之兵,而不可逃避恶社会,作退避安闲之想”,要“排万难而前行”![10]132,135 这是“二十一条”事件后中国新式知识精英作出的一个最有远见的反应。
在10月间的另一篇文章中,陈独秀则肯定中国还处于需要“国家主义”的时代,对此前的应否爱国问题,在说法上有了明显调整。他说:“衡之吾国国情,国民犹在散沙时代,因时制宜,国家主义,实为吾人目前自救之良方。”但这个国家,是人民为主人的“真国家”,而不是以人民为奴隶的“伪国家”:近世的国家主义,“乃民主的国家,非民奴的国家。民主国家,真国家也,国民之公产也,以人民为主人,以执政为公仆者也。民奴国家,伪国家也,……以国民为奴隶者也。……若惟民主义之国家,固吾人财产身家之所托。人民应有自觉自重之精神,毋徒事责难于政府。”[11]144 将反封建与爱国(反帝)初步地结合了起来。开始触摸到这个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迈出了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逐步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过渡的重要的第一步。
以上就李、蔡、胡、陈四人对“二十一条”交涉的反应及应对之道作了大致的梳理,笔者由此得到的初步结论是:
其一,1915年是1910年代最低谷的一段时间,是从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失败后步步沉沦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渐渐开启新时代曙光的转折时期。这是一段令人窒息、令人绝望的日子,一些人投靠了袁世凯,许多人逃到了国外,不少人意气消沉(这时的鲁迅也是百无聊赖,以抄写古碑打发时光,他这一段的日记,多是一些沉闷乏味的书帐)。这一年,起首即是日本的蛮横敲诈,袁政府被迫接受之后,不思发愤雪耻,反而野心益炽,疯狂复辟,是实实在在的“外患侵逼、内政紊乱之秋”。[12]323 但这黑暗之中,因《青年》杂志的横空出世,也微露出一线光明。
其二,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此时的中国确实还无力抵御。在统治阶级方面,实力、勇气既不足,⑩ 其所谋也不在此。孙、黄的态度已如前述,人民自发的反日运动也还无力阻挡日本的侵略步伐。一时还没有什么人、什么力量有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和方案,能够解决当前的危机。中国的复兴和崛起,只能是一个长期的、痛苦的过程,要以无数先驱者的生命和苦难为代价,李大钊、陈独秀及其两个儿子,都是为此而献身的人物。
其三,与此相应的,先进的中国人对救国救民道路的探索,也必然会是一个漫长的、曲折的过程,要找到一条真正适合中国国情的,能在险恶的现实危难、沉重的历史包袱及变幻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将中国引向光明的道路,绝非易事!确实是“知难,行亦不易”!从李、蔡、胡、陈上述的反应,不难看出,他们这些开启后来中国思想革命新时代的核心人物,这时的救国主张还是较为含糊、朦胧的,甚至是苍白贫乏的。
在具体主张上,他们有差别,如在当前是要抵抗、还是抵抗也无济于事(李要,陈、胡不要,蔡不确定);还应不应当支持和信任现政府(李、胡信任,蔡、陈不信任);中日矛盾还有无调和的可能(胡有幻想)等等。但他们又有许多共通之处,其中最大的共同点,就是都在努力寻找救国的方案,寻找国家、民族摆脱困境与屈辱的途径,甚至开始感觉到要从根本上、从教育上、从办大学入手,要对人民进行启蒙,提高国民的觉悟,使国民都能尽自己的责任。
但以什么内容来对人民进行教育?以什么学说来启发青年的觉悟呢?这时他们所崇尚和提出的,仍然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民权学说,这是当时中国最进步的思想,他们希望以此取代国人头脑中的旧思想、旧观念,唤醒他们的觉悟,从而缩小与西方先进国家的距离。这是他们在其后的新文化运动中成为同路人的重要政治基础和思想基础。虽然此时他们对于这一点还不是非常清晰,但已开始指向此一方向。1916年10月,陈独秀发表《我之爱国主义》一文,将爱国主义与改造国民性、提高国民道德相联系,认为“为国捐躯之烈士”,还只是一时的、治标的爱国主义,国民能养成“勤、俭、廉、洁、诚、信”的品质,才是持续的、治本的爱国主义。他说:“今日之中国,外迫于强敌,内逼于独夫,……而所以迫于独夫强敌者,乃民族之公德私德之堕落有以招之耳。”是亡于“国民之行为与性质”。“欲图根本之救亡,所需乎国民性质行为之改善,视所需乎为国献身之烈士,其量尤广,其势尤迫。”[13]206—213 从而开始了他们改造国民性的伟大工程。
其四,他们四人都是开风气之先的人物,不是善于具体操作、具体实行的革命家、政治家,是新旧相搏的时代引领时代进步的人物。应对1915年的具体问题,非他们所长,但这一次的刺激,对于他们进一步思考国家的前途命运、拯救国家的方案,都有着很大的推动,对目前是“苦无良策”,但必促使他们作长远的思考。中国革命是一场伟大的革命,这个革命必然要有不同的阶段,必然要分为当前目标和长远目标,有当前的、应对目前局势的方案与长远的根本解决的方案,对此问题,他们都有所考虑,但确实都还在反复的探索之中。他们这时的救国主张之所以是朦胧的、不清晰的,也与当时的国际背景有关,因为此时整个世界也正陷于空前的焦虑不安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人们切实地感觉到了西方先进的物质文明并非尽善的一面,而在西方早已诞生的马克思主义这时还无成功的先例,亦未引起中国人的真正注意,而且,从理论上讲,中国面临的问题,也还不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担忧的在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之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问题。世界究竟向何处去?中国究竟向何处去?在在都是疑问,他们这些对旧文明刚刚有所挣脱的人,要一下子就目标明确,头脑清醒,还真是不容易啊。
他们怀抱着救国的理想,从不尽相同的地方出发,两三年之后,以北大为基地,相交、融会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洪流之中,随后,又随着客观环境与主观认识的变化,由于其个人的性格与特质,而渐渐发生分流,奔涌在不同的河道上。
注释:
① 参见曹汝霖:《二十一条与巴黎和会》,杜春和等编:《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81页;另见黄纪莲译:《沙俄与日本对华“二十一条”——俄国外交文件选译》,《近代史资料》总第54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页。
② 罗志田《救国抑救民?——“二十一条”时期的反日运动与辛亥五四期间的社会思潮》一文对此及相关问题有很深入的论述。(见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③ 参见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编辑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15年卷),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81年版,第201、237页。
④ 在此期间,梁启超发表了《中日最近交涉评议》、《外交轨道外之外交》、《中国地位之摇动与外交当局之责任》、《示威耶挑战耶》、《痛定罪言》等一系列见解深刻、说理透彻的时评(均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二、三十三,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版第4卷),既有对日本朝野死马当作活马医般的“效忠告”,告诫其恶化两国人民感情,攫得眼前之利益,甚至就算是一时征服中国,也绝非日本人民之福,而终将是自掘坟墓;也有对袁世凯政府善意的批评与痛切的警示,认为中国将来之一线希望,即维系于“至劬瘁至质直”的善良的下层人民身上,而不是那些地位优越、但十中有九皆不善良的官僚士大夫,这是“二十一条”事件中颇值得关注的言论。因本文拟主要考察稍后参与发起新文化运动的数人,故不将其并入此文讨论。
⑤ 关于李大钊对袁世凯存在幻想及对袁本质认识的过程、李大钊在“二十一条”问题上的态度受章士钊影响的问题,朱成甲先生在《李大钊早期思想和近代中国》(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一书中有较好的论述,见该书283—286页。
⑥ 罗志田先生在《地方意识与全国统一:南北新旧与北伐成功的再诠释》一文中曾说,北伐时,由于大量新文化运动青年的注入,“使早已不怎么在党内活动的新文化运动文人如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等影响大增”(《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第189页)。从史实看,在二次革命失败后的一段时期,蔡元培的交游与志趣,似与孙中山主流派有别,与黄兴一派也联系不多。在另一处,罗志田先生称蔡元培“一身兼国民党元老和新文化运动的监护人”(《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第196页)。如果我的理解不错的话,是视蔡元培为五四新文化阵营内的人物。1940年,陈独秀在《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中曾说:“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蔡建国编:《蔡元培先生纪念集》,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71页)故本文将这期间的他与陈、李、胡等并在一处加以考察,或许还不致太谬。
⑦ 参见胡适日记(1915年3月19日),《胡适全集》第28卷,第91页。在此稍前的《致“外观报”书》中,胡适曾说“远东问题之最终解决乃在于中日双方之相互理解、相互合作。然此种理解与合作决不是由一次次之武装征服所带来的”(《胡适全集》第28卷,第67页)。一二十天后,胡适又说不知最终解决之道何在,或许这也反映出他此时的一些看法和意见还处在探索、思考和不断的修正之中。
⑧ 参见胡适日记(1915年5月25日,此处可能应为4月25日——引者),《胡适全集》第28卷,第106页。
⑨ 参见胡适日记“为祖国辩护之两封信”(1915年3月),《胡适全集》第28卷,第64—68页。
⑩ 日军出兵山东时,袁世凯问陆军总长段祺瑞军方的意见,段答:“如总统下令,部队可以抵抗,……不过由于武器、弹药不足,作战将十分困难。”袁问:“到底能够支撑多久?”段答:“四十八小时。”袁再问:“四十八小时以后怎么办?”段望了望总统说:“听候总统指示。”袁政府遂决定走外交妥协途径。(见《顾维钧回忆录》一,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20页)
标签:胡适论文; 陈独秀论文; 李大钊论文; 知识精英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精英主义论文; 历史论文; 袁世凯论文; 蔡元培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五四运动论文; 北洋军阀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辛亥革命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