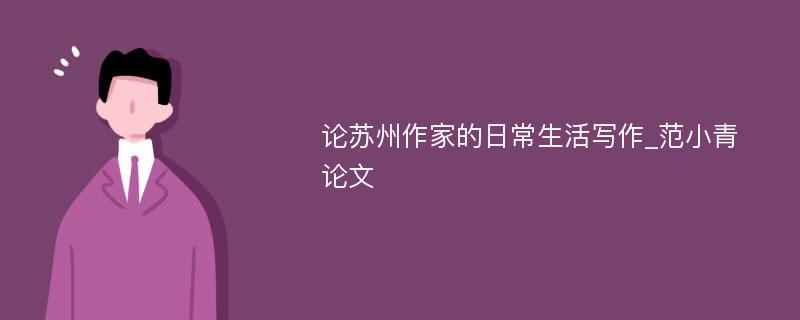
论苏州作家的日常生活书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州论文,日常生活论文,作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苏州地处长江三角洲中心,东邻上海,西枕太湖,北依长江,南接浙江,自然条件优越,历史悠久。1990年代以来,苏州抓住上海浦东开发开放的机遇,抢先一步,加大对外开放力度,依托新区、开发区建设,外向型经济迅速崛起,使苏州再次进入高速增长阶段,形成一城两翼(老城、开发区和新区)的城市空间格局。老城苏州风景秀美如画、传统文化发达、历史底蕴深厚,拥有大量的自然景观和历史古迹,基本保持着古代“河街相邻、水陆并行”的双棋盘格局、“三纵三横一环”的河道水系以及“小桥流水、粉墙黛瓦、古迹名园”的独特风貌。王尧老师很早就指出:“‘一城两翼’的新空间,其实并不只是城市的格局变化,并不只是产业的调整,并不只是财富的聚集,并不只是跨国资本的介入,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文化的整合”,而“吴文化仍然是这两翼的幽灵,但是在这个新的空间组合中,苏州文化已经处于一种混杂的状态。不同文化的扩张和缩小,在碰撞中对接和共生”①。 在这种大背景下,一些敏锐而敏感的苏州作家嗅到了传统文化或异变或消亡的气息,开始在自己的文学园地里,构建精致古雅、闲逸诗情的老苏州旧式文人的生活天堂。美食、昆曲、苏州园林、太湖风物民俗、老苏州消逝的风景等等表征着散文作家“行走”苏州日常生活空间所在②,其中的风土人情、言谈举止、场景氛围流淌着浓郁的“苏州味”,总能使人很自然地联想到作家本人生活的苏州古城——市民安居乐业的温柔之乡和诗意栖居的精神家园。不仅散文,苏州小说创作也逐步走出1980年代形成的“小巷文学”的政治格局,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但是对以书写苏州文学空间为主的苏州作家来说,日常生活空间生产仍旧是他们参与苏州城市空间生产的一种渠道,也是作家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甚至就是他们的一种“行走”方式。 一、范小青的规避、转移和找寻 在苏州土生土长的作家范小青,自1985年开始由青春主题写作转向苏州市民原生态日常空间的打造。日常生活的耳濡目染、精神世界的无形塑造和熏陶都使得“苏州”成为范小青创作选材的一个重要基点,并且成为一种强烈的内在冲动和创作动因。“从来就没有、也不可能有脱离了日常生活的宏大,如果硬说有,那就是硬说出来的,其实是没有的。”③范小青的苏州空间仍然继承陆文夫先生的“行走”传统,从日常生活的小巷起步,但是不限制于此,苏州的小巷、苏州的园林、苏州的美食、苏州的评弹昆曲、苏州的民俗风物、逝去的老苏州风景等等,这些日常生活空间的现实景观以及记忆中陈旧的风景都作为范小青个人独特的,又具有一定共性的空间体验,有意无意地被作家纳入作品,如《瑞云》、《顾氏传人》、《单线联系》、《文火煨肥羊》、《天砚》等,苏州古城的文化风貌与日常人情共同构建成不可或缺的苏州日常生活的表征空间,而且营造出“佛文化”的淡远意境,折射出了哲理的韵味。在《昨夜遭遇》、《城市陷阱》、《病历》、《失踪》、《谎言》、《错误路线》中作家撷取了一个个日常生活空间片段,人与空间的矛盾,人与人之间的、人与自我之间的隔膜在这一系列空间转移、并置中得以巧妙地展示,直指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危机。 小说《短信话吧》的副处长在官场不停的空间转移,从多人监视下的大办公室努力升迁到两个人的副处办公室,从误会重重的此单位调到彼单位,但是具体单位的调动仍然无法摆脱短信、手机等虚拟空间对人的制约和操纵,于是在《我们都在服务区》中的桂平决定一天不拿手机,得到短暂的轻松自由之后就是无尽的莫名惶恐,别人找不到自己的同时,感觉自己也被社会遗弃了,于是采取各种拔卡、换号等小手段,经过几番折腾表面看来桂平似乎回到原点,但是桂平内心对日常生活的韧性增强了,一边抱怨一边去适应这样的生活。虽然在官场权力、器物与人对空间的争夺和彼此规训中,政治空间和虚拟空间无孔不入奴役着人的日常生活观念,即吉登斯所言的“时空分延”,实质是“现代人身处文明与野蛮的双重合谋和屠杀中”④。但是在被分离和压缩的时空中,人没有一味沉沦或顺从,也没有完全迷失自我,而是采取各种小伎俩、小手段来改造日常生活,丰富个体的精神空间、增强自我的心理韧性,这些仍然是范小青小说背后透露出来的信息,否则就不会出现主人公一次次的空间转移和坚守了。《人间信息》的建一在讨债为主的日常生活空间中疲于奔命,险些命丧车祸,要到债务后,周围的亲戚和朋友都逐渐淡忘他的生死之旅,包括建一自己也麻木遗忘,并且获得自我解脱。建一的遗忘是主动地选择,是相对消费社会金钱至上、人情冷漠的主动逃避,不是向外扩张反抗而是向内的自我挣扎,建一用改变自我的非对抗性策略来平衡日常生活空间的冷淡平庸,虽然悲凉但也是无奈的选择,“一种孤独而凄厉的尖叫声正从来自日常生活的腹地深处和洞穴中升起……川流不息的沟通以及穿梭往来地信息传递相反却导致了难以忍受的孤独”⑤。此外,反映城乡差距的《城乡简史》,作者有意摒弃对历史的进化论线性时间讲述,而是通过两个普通底层小人物王才和自清分别在城市乡村两个日常空间的“双向寻找”来展开城/乡结构和城/乡关系的探寻,“乡下人进城”寻找“香薰精油”的背后憧憬着现代消费生活的神话;“城市人下乡”则找寻“账本/书”被遗弃后的精神寄托。沉闷贫乏的城/乡日常生活空间因为外来者的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寻找”而重新被激活,“戏剧性中散发的那股倔强的延异性力量”直抵俗世的灵魂。范小青“依靠小说的智慧来刺激沉闷、庸常的生活。因为,日常生活的平庸性,是消费社会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心理基础,冲决、解构这种平庸性,切实而机智地表达对这个时代人性的理解和深刻洞察,穿越表象、直抵事物背后的荒诞和遮蔽,发现惟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事物的原生态样貌。”⑥ 二、苏童的游荡和逃亡 从苏州走出去的作家苏童,他的童年和少年时光是在苏州城北的一条百年老街上度过,创作中三分之一部分都和苏州的“香椿树街”有关,可见香椿树街承载着作家童年的成长记忆,也是苏童“行走”日常生活横切文革历史的重要空间。居住在弯曲、闭塞、阴暗的香椿树街的人们虽然远离政治中心,但是“文革”的紧张和不祥还是降临于此,于是香椿树街的心境和生存境遇逐渐发生改变,甚至弥散着突然降临的死亡气息。日常空间对于政治权力的实施并不是完全被动地顺从地格式化,香椿树街的各色人对于“文革”出现不同的经验和心思,普通生活的空间逻辑在面对革命政治的侵入时自发地启动了运作机制,某种程度上是对革命权力的抵制和消解。这是一代人对于“文革”的另一种记忆空间,少年视野里的“文革”岁月充满了日常的灰暗无聊和青春的绝望躁动。苏童对暴力的迷恋和激情流淌出与陆文夫、范小青等平和冲淡、柔糯文雅的苏州日常记忆的一种变奏。 如果说范小青善于用规避、转移、遗忘、找寻等策略来抵抗日常生活的平庸,那么苏童则善用游荡、逃亡来完成日常生活中精神的还乡。“游荡”是本雅明在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中读出的对资本主义城市生活寓言式观察、体验和表达的方式,“游荡者”(flaneur)虽然隐身于人群之中,却不同流合污。在苏童的狭小、杂乱和破败的“香椿树街”这个日常生活空间中也存在一个少年游荡者,香椿树街是游荡者的背景,它没有早期工业技术的勃勃生机,更多是一个自然景观——白铁铺、药铺、裁缝铺,耍蛇的、卖西瓜的、拣破烂的——加剧了它的沉闷、单调和乏味。“一条狭窄的南方老街,一群处于青春发育期的南方少年,不安定的情感因素,突然降临于黑暗街头的血腥气味,一些在潮湿的空气中发芽溃烂的年轻生命,一些徘徊在青石板路上的扭曲的灵魂。”⑦香椿树街如此狭小有限,淹没吞噬着孑然一身的少年游荡者,于是“游荡”或者与回眸对视,游荡者最终留下一个孤独忧伤的身影,例如喜欢观望那些悲惨的死亡现场、喜欢收集死人遗物的剑听着那些人对死因的推测感到可笑而荒唐,他始终鄙视旁观者们自以为是或者悲天悯人的谈论,每逢那种特殊的时刻,人群中的剑总是显得孤独而不合时宜。但剑依然执着于他在铁路上漫游和寻找(《沿着铁路行走一公里》);“游荡”或者和挑衅结盟,游荡者最终演变为一个滋事者,如“东风中学”的少年们日常生活乐趣就是打沙袋和拜师学武,达生最终用生命完成一场暴力恶斗的祭奠(《城北地带》),小拐目睹触目惊心的帮派血战后反而激起更狂暴的梦想,刺青暴力的代价就是把他渐渐地变成孤僻而古怪的幽居者(《刺青时代》);“游荡”或者与情欲互动,游荡者成长为一个躁动的个体,如毛头和丹玉在竹林带有诡谲唯美的以身殉情(《桑园留念》),为了报复母亲的堕落,少女舒丽与舒工上演的荒诞情欲(《舒家兄弟》),红旗对香椿树街上最美丽的女孩美琪的青春躁动(《城北地带》)。总之不管是忧伤美丽的身影、还是滋事者、躁动者都颠覆着传统小城镇的温情、纯朴的诗意想象,也解构着都市市民日常生活空间的琐碎、无聊,这里上演着被遮蔽的、原生态的、粗糙的、苦难的、但不是“一潭死水”的民间市井生活:一个贫乏的“恶之花”时代里阴暗的人性和压抑的激情渐次登场,而毁灭性的后果必然成为游荡者出逃的理由和动力,正如《南方的堕落》中金文恺那苍白的脸和枯瘦的手指与“小孩,快跑”的箴言,也正如《沿着铁路行走一公里》的剑对那列上海至哈尔滨列车的向往和猜想,里面蠢蠢欲动着对铁路、生命、世界的好奇和渴求。 苏童曾说:“逃亡好像确是我所迷恋的一个动作”,“这样一种与社会不合作的姿态”,“是一个非常能包罗万象的一种主题,人在逃亡的过程中完成了好多所谓他的人生的价值和悲剧性的一面”⑧。在作家的主体审美结构中,都需要历史和现实的存在时空的支撑。苏童选择了由崩溃人性和堕落欲望聚合在一起的时间碎片和空间缩影,无疑这是非常现代感的时空观念。于是在“香椿树街”和“枫杨树乡”空间游弋中,在城市和乡村地理边界中,“逃亡”成为缝合碎片时空的一条主流,金桥要设法逃离污浊、腥臭的肉联厂(《肉联厂的春天》)、孔令丰要沉醉于戏剧演出躲避父母阴暗人性的角逐(《园艺》)、牛车队要逃避战争的惨烈,实现镇静优雅地行走(《三盏灯》)、139个新老竹匠疯狂执拗地逃离故乡涌入城市(《1934年的逃亡》)……诸如此类摆脱固有生活空间的逃亡行动,虽然被动无奈、虽然难逃宿命的失败,但是对他们来说,只有逃亡才有生存的可能和希望,而生存的希望空间就在不断逃遁中,这个逃亡实质是对既定生活和命运的拒绝、反抗和反征服。如《逃》中的陈三麦无法忍受单一的日常生活空间,他逃离家乡、逃离妻子、逃离朝鲜战场,一生都在用疯狂的逃亡为生命寻找新的空间,直到临终仍是逃亡的姿势“竭力挣脱婶子的怀抱,把头侧向窗外”;《米》中的五龙逃离了故乡的水灾旱灾,千辛万苦在颠簸的夜色中逃亡,光怪陆离的城市收留他却又设下重重罪恶的陷阱,于是五龙成为霸主之后在垂死之际执拗地带着一车白花花的大米逃离城市、奔向故乡,荒诞的是即便回乡的火车向北开,五龙的心仍然在向南堕落。“不断逃亡”就是陈三麦、五龙们的日常生活空间的支柱,也是他们寻找精神家园的动力,现代人失落漂泊的灵魂只有在逃亡和还乡的悖论中寻找皈依,或者说逃亡、漂泊、还乡的三位一体的日常生活空间本身就构成对精神家园皈依,从中我们可以触摸到苏童对现代生存的彻骨痛感,也体现出人类在超越和救赎日常生活空间时亘古不变追寻彼岸世界的韧性和执拗。近年来,苏童的现实行走依然离不开香椿树街,但是已日渐从晦暗走向澄明,并不断提供进入世界新的通道,苏童依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下去。 三、朱文颖的隐忍和超越 上世纪七十年代生于上海、现居苏州的作家朱文颖,对故乡苏州的文化场域和日常空间构建方式有其独特的认知视角,认为苏州是一个有“风,雨,雾,雷,电”,有“土壤,湿气,河水,巷道”,有“谷物,黄梅雨季,以及清晰可辨周而复始的四季轮换”的自然空间,型塑着苏州“极具炫惑力的外表:阴柔、湿润;华丽,灵秀——既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又繁花似锦,歌舞升平”⑨的人文品质,苏州是寓言的城市,是一个边界模糊、底子暧昧的寓言。所以“由真实的生活中”建立起来的“一个虚构的、寓言性质的存在世界”是朱文颖独特的行走方式。《浮生》在作者虚拟的历史空间和情绪空间中,沧浪亭爱莲居的沈三白与芸娘的日常生活完美再现,苏州小巷、寺庙、人物都漂浮在古典与现代的空间交错中,人性和生活的某种普遍永久的奥秘得以揭示。心理病态的日常空间,则是近几年来朱文颖小说的鲜明的特点,现代社会中医院与社会具有同构性:“现时社会是封闭社会或凝视社会。可以说,医院作为关闭——凝视空间,正是整个关闭——凝视社会的缩影。”⑩《病人》中,知识分子、文化人、都市白领等人群的神经质正是在医院一样的权力空间中被规训被生成;《猫眼》中李春慧医生窥探欲望在“猫眼”的看与被看的审视空间中不能自已,《宝贝儿》中,则把主人公贝先生的压抑病态生活放置在“一种很不真实的发疯的气味”空间中,气味所到之处一一解构着一个个看起来如此“理智而幸福”的家庭。 如果说范小青和苏童对日常生活空间的处理策略——不管是转移还是逃亡,都可以称为一种动态的非对抗性抵抗的话,那么古典气质的朱文颖则以静制动、以柔克刚,用隐忍克制的柔弱气息慢慢地、丝丝缕缕地侵入瞬息万变的嘈杂空间,虽然有时让人感到绝望的痛苦和无奈,但毕竟不是苟且,更不是妥协,而是一种隐忍柔弱的坚守和拒绝,升腾出作者对超越日常生活空间、构建细腻唯美的精神空间的无尽迷离。 小说《水姻缘》中的女主人公沈小红是一个小跑堂的女儿,没有显赫的背景,也没有出众的容貌,但是也憧憬着电视广告的消费神话,于是作者构架出沈小红与康远明在“婚姻保卫战”的日常化生活空间:诸如富有情调的沧浪亭、古香古色的玄妙观、怀旧的老字号饭店、讲究奢侈的米园花宴等,这些物理空间不是诗意化背景,而是男女二人对婚姻的算计而有意设定的,它们也成为这场姻缘胜败与否的重要砝码和手段。此外,沈小红从日常衣着、饮食、行为举止都刻意透露出男人欣赏的苏州式古典淑女气质,可谓用尽精明心思、使出浑身解数、甚至显得卑微迎合,但依然被康远明玩弄、背叛,“克己的现实、知人识务的现实”的生存哲学支撑沈小红隐忍到最后付出失去孩子的代价,得到一个不牢固的婚姻。近作《莉莉姨妈的细小南方》中的“细小”“南方”更是在与“宏大”“北方”的空间并置、错位中凸显出日常生活空间的柔软外表与坚韧内核——这是朱文颖个人化的南方想象,也因此型塑出王宝琴、童莉莉、“我”这样一个个精致细腻而又粗鲁野蛮的空间主体。王宝琴一辈子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爱她的丈夫童有缘和恨她的丈夫童有缘;童莉莉因为恋人潘菊民的迟滞不归而长达几个月的追踪成为一生最辉煌的经历,日常生活的无法把握致使莉莉姨妈少女和老年时代没有真正界限,直到老年仍有少女般柔软腰肢,“她内心有一种奇怪的东西,谈不上好坏,难以论雅俗。正是它们,最终打败了她的年龄以及她脸上垂褶累累的皱纹”一如“她那细高跟的鞋子发出的声音,清脆的,激越的,仿佛仍然在和什么东西赌着气”。叙述者“我”则“和亲爱的莉莉姨妈一样,和这个虚荣、做作的女人一样,我的深情和暴烈像毒一样埋在心里。”这样一群“细小”南方主体的日常生活成为“坚硬的、枯燥的历史/时代一道异样的风景,使历史/时代变得饱满、丰富而有趣,使历史/时代具有了非同寻常的文学性和精神意味”(11)。 总之当代市场经济下,面对消费社会异化、扭曲的生存空间,沈小红、“我”和王小蕊、安第都在用一种东方式的节制力、隐忍力来承受生存的艰辛和无奈,“伤痛是存在的,有许多本质的东西,有许多隐藏在生活潜流下面的痛感。这是每一代人、每一种社会进步时都会面临的困境。”(12)对此,朱文颖喜欢用一种蕴藏着力量的、隐忍的表达方式来处理困境,用一种东方式的、个人化的激情表达方式来叙说自己的感悟,于是即使血淋淋的现实,主人公也始终沉浸在一种含蓄、平静、无大起大伏、无紧张感的情绪中,在回忆中整理着杂乱、零碎、非理性的日常生活空间。这和朱文颖对日本的歌舞的理解是一脉相通的,“日本的歌舞伎与演歌,我特别喜欢。他们是怎样来处理悲哀的,那种痛彻心扉的悲哀?……在日本美的世界里,特别是在歌舞伎的表演中,不论表现如何痛苦的场面,都不至于大放悲声。观众从那沉静的强忍悲痛的舞蹈中,可以理解人物内心的忧伤……我喜欢这样的表达方式。我认为它是一种东方的表达方式,也是一种激情表达。它不以释放为渠道,而是更深的隐忍。忍到了极至。这种忍其实是非常可怕的,非常蕴藏着力量的。”(13)这种对日常生活空间的隐忍策略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坚守和执拗,也是一种绝望中的超越,所以,作者笔下的人物还有梦想和幻想:阿三在丢失小猫迷失回家的路的漂泊中依然渴望理解和温情(《阿三与猫》);《水姻缘》中婚姻是沈小红的空气,康远明因为这个女人也有了点刘邦的感觉;《病人》和《一个沙漠中的意大利人》中的“我”在对现实男性的失望后,将幻想寄予一个偶然碰见的陌生男人;《高跟鞋》中两个女孩幻想着美人鱼的童话;《老饭店》中的舒先生,更像一个过去的理想,照亮了女主人公苏也青惨淡的现实生活;《莉莉姨妈的细小南方》中童莉莉和王宝琴依然相信运河里浸淫着梦想,认为那个荒唐毫无道理的吹箫人是对的,箫声里面的他显得华丽而准确。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三位作家对“行走”的写作姿态以及行走在世俗日常空间的偏爱,从表面上看来,他们笔下的人物都生活在寻常巷陌之中,但这些小人物的生存命运却与历史的走向、社会的大气候、文化的承传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日常生活空间正是与之关联的重要通道,也是苏州文化和城市文明表征的主要场所,可以说,日常空间的生产和实践本质上现代社会文化、文明的过程和目标。试析之,众所周知文化是文明的精神灵魂与精神内核,文明是文化的对象化和外显载体。追求社会文明的进步,是任何一个社会不变的价值向度,也是一个城市、一个民族与国家走向未来的路标。而保持自己文化的先进性,并使自己文化的先进性始终保持有竞争力的状态则是文明进步的前提与基础。从历史发生论上看,文化和文明都生长在人类社会生活的土壤中,离开人类社会生活,文化和文明都不能生成也无以存活。同时人的“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14),因而推动人类社会文化与文明发展归根结底是人类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即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它是社会文化和文明发展的杠杆和永不衰竭的动力。列斐伏尔认为:“日常生活是一切活动的汇聚处、纽带和共同的根基。也只有在日常生活中,造成人类和每一个人存在的社会关系的综合,才能以完整的形态与方式体现出来。在现实中发挥出整体作用的这些联系,也只有在日常生活中才能实现与体现出来。”(15)日常生活空间成为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起点和终点,人的解放只有在日常生活空间中才能真正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讲,苏州作家的日常生活空间的书写意味着人文知识分子参与苏州城市文明建构的主体意识和强烈责任感,小说文本也成为苏州城市文化的文明载体和文化景观。循着“行走”在粉墙黛瓦、茶肆小巷的足迹,面对日益同质化、平庸化、世俗化的小桥流水人家,苏州作家没有单纯沉浸在历史怀旧的感伤或消遣中,触摸到社会空间的粗粝和日常生活的痛感,不约而同地采取了“柔韧抵抗”策略——“以柔克刚”、“以慢制动”看起来是无限柔软、缓慢,却也坚硬无比、韧性十足,文本空间呈现出一种奇异的审美格调。当然这和苏州城市的水巷、园林、评弹、美食、茶园等地景空间对作家的情感结构的型塑息息相关,更是柔糯、飘逸、风雅、冲淡、精致的吴越历史文化长期浸润的结果,最主要的还是知识化、文明化了的苏州新市民群体和文人群体对现代性的一种不失机警的抵抗策略,为生存空间、文化空间的多元化建构提供了一种可能。“苏州人没有梁山好汉的气魄,可苏州人有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的精神,苏州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他们的追求,他们的奋斗。”(16)于是在苏州人对传统文化的固守和城市现代文明的追求中,历史和传统得以复活,苏州文脉得以承传,并且鲜活地保存在园林、水巷、评弹、茶坊以及苏州人的日常生活中:范小青、苏童和朱文颖三位作家和苏州日常文化空间互相型塑的关系和价值得以凸显——重要的是“他们”就在苏州之中,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占用了苏州日常文化空间,并把它转化为挥之不散的“苏州情结”诉诸于属于自己的异质的、多元的诗性空间,而这种对日常生活空间的占用恰恰改写了特定空间之上的消费权力符号。正如德塞图所分析,日常生活具有一种创造力(inventiveness),一种重新使用与重新结合异质性材料的作为的能力。于是苏州是典雅的现代,苏州是高贵的低调,苏州是永恒的包容。 注释: ①王尧:《空间》,《双城散记》[M],苏州:古昊轩出版社,2009年5月版,第170页。 ②代表作家作品有陈益《天吃相》、《收拾起》,车前子《品园》、陶文瑜《纸上的园林》,陶文瑜《太湖记》,车前子《鱼米书》、金曾豪《蓝调江南》等等 ③范小青,汪政:《灯火阑珊处——与〈赤脚医生万泉和〉有关和无关的对话》[J],《西部华语文学》,2007年第5期,第93—111页。 ④晓华:《论范小青短篇小说的转型》,“苏州作家与中国当代文学”研讨会,2012年11月17日。 ⑤Lefebvre,H。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M]。New York:The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2000:125 ⑥张学昕:《人间信息的生命解码——范小青短篇小说论》[J],《当代作家评论》2012年第3期,37—48页。 ⑦苏童:《自叙》,《苏童文集·少年血》[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⑧苏童:《苏童文集:世界两侧》[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⑨朱文颖:《何谓享乐生活——以苏州为例》[J],《东方杂志》,2003年3月2日。 ⑩于奇智:《凝视之爱——福柯医学历史哲学论稿》[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66页。 (11)吴义勤:《大时代的“小生活”——评朱文颖长篇新作〈莉莉姨妈的细小南方〉》[J],《当代作家评论》2011年第3期,第118—122页。 (12)朱文颖:《一个年代的迷惘与信念》[J],《作家》2000年第8期,第73页。 (13)吴俊,朱文颖:《古典的叛逆》[J],《作家杂志》,2001年第6期,第51—57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6页。 (15)Lefebvre,H。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M]。London:verso,1991(I):97。 (16)范小青:《裤裆巷风流记》[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6年4月版,第3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