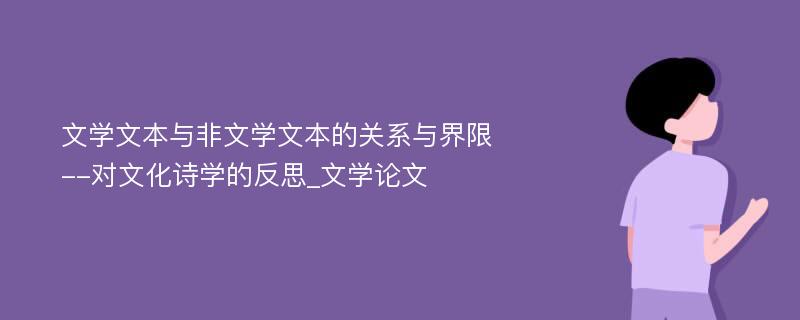
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的关联与界限——重识文化诗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本论文,诗学论文,文学论文,界限论文,与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4)06-0040-05
在我几年前写的一篇讨论美国的文化诗学对中国现代诗学可能的影响的论文中,我多少是有些先人之见地肯定了文化诗学作为文学研究的“系统哲学”性质,认为它具备巴赫金所说的“在人类文化的整体中通过系统哲学来论证艺术事实及艺术的特殊性”这一特点。[1]通过对文化诗学与可以将之囊括其中的文化研究更多的了解,我认识到,文化诗学与文化研究就其总体而言,更多地是想恢复人类文化的整体性,即恢复各种文化文本之间的关联,而对区分、确立各种文化文本之间的界限似乎没有太大的兴趣,换言之,“论证艺术事实及艺术的特殊性”并不是它的关注点,恰恰相反,它的关注点是要模糊这种特殊性。这正是我想在本文中重识文化诗学的缘由。我的关注点是:在恢复了文本的关联之后,是否仍然存在区分文本界限的必要?
文本的关联与膨胀的文本概念
文化诗学(Cultural Poetics)又称新历史主义(New Historicism),在美国兴起于20世纪70到80年代,是对此前占主导地位的文学分析方法——新批评的反拨。如果说,新批评的文学分析方法关注文学文本本身甚于关注文化、历史、作者与读者,那么,新兴起的新历史主义文学分析方法则强调:是文化、历史和其他相关的因素决定了文学文本的意义。文化诗学关注历史,并关注形成历史的各种文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在文化诗学的批评家看来,文学文本是历史和文化的产物,是存在于作者、社会、习俗、制度和社会实践的文化网络中的社会性文本。美国学者伊丽莎白·福克斯-杰诺韦塞在谈到新历史主义的这一文本观时,说:“本文不是存在于真空中,而是存在于给定的语言、给定的实践、给定的想象中。语言、实践和想象又都产生于被视为一种结构和一种主从关系体系的历史中。所有以集体名义写作——虽然可能十分狭隘并以自我为中心——的本文制作者们,都是带着这样一种意识写作的,即他们是那些组成社会和文化的大众的特权代言人。对不同文本之间联系的关注把他们引向历史。……作为社会和性别关系的表现形式的本文本身就构成了种种关系体系:不是与历史无干的关系,而是由时间、地点和统治所构成的历史联系。如果对这些关系的结构缺乏清醒的意识,那么对本文的阅读就会沦为私下的琐事。”[2]确实,在文化诗学研究者看来,文学文本是各种社会力量交汇的场所,一方面,它是在社会文化的语境中形成的,另一方面,它自身也对这种社会文化的形成起到重要的作用。
而关键一点还在于,在文化诗学的批评家确立了文学文本作为社会性文本的这一特性之后,原来似乎更多地只是文学领域的专有概念的“文本”概念经历了几乎是无限地膨胀过程。文化诗学的一种基本假设是语言形成了文化,文化同时也以之形成。而在文化诗学看来,语言的涵义很广,包括各类话语、文字作品、文学、艺术、社会活动和任何个人或集体依赖把观念和行动施加于他人而形成的社会关系。这样,把文本视为处于活动中的文化,文化诗学批评家跨越了艺术性产品和其他别的种类的社会产品或社会事件的界线,这些批评家要求我们把艺术家的作品当作社会性的文本来阅读,同时要求我们把美国总统的就职典礼当作像任何诗歌一样充满着符号和结构的修辞的审美事件来阅读和阐释。就这样,文化诗学在文本、语言和话语的旗帜下跨越了学科间的樊篱,在文学、历史、文学批评人类学、艺术、科学和别的学科之间没有了明确的界限。一个艺术品,就是一个文本,和别的所有的社会话语一样,是靠和它产生于其中的文化的互动关系而产生意义的。没有一种话语要优于另外一种话语,所有话语都是被社会所形成同时也形成社会的必要参预者。[3]这样,文本就无限的膨胀了,也唯其如此,文化诗学在80年代后期很快地被更具有兼容性的“文化研究”所包括,它在新批评与文化研究之间似乎是担任了某种架桥铺路的中介角色。在文化研究中,那被文化诗学所奠定了基础的“文本”概念进一步无限度的扩张了,正如一切无往而不是文化一样,现在一切无往而不是“文本”了。很快地,文学文本似乎边缘化了,文化研究以大众的名义很快地扩张了文本范畴,影视、广告、摇滚乐、MTV、体育、玩具娃娃、购物中心、城市等和文学一样成了文化研究的范围。
对文本的“文化解读”
概括地讲,新历史主义的操作方法可以用代表人物葛林伯雷的一种努力来说明,即试图探讨“文学本文周围的社会存在和文学本文中的社会存在。”[4]如果将社会存在理解为社会、历史或者说是更大范围的文化,那么,我们几乎就可以明白为什么葛林伯雷本人认为“文化诗学”比“新历史主义”一词更贴切地描述了文本分析的方法。也就是,新历史主义在文本分析上的倾向是“文化诗学”的,其内涵即是面对文本时,并不相信从孤立的文本内部能够阐释文本的意义,而是相信,要阐释一个文本的意义,我们必须做到这样两个工作:(1)探讨“文学本文周围的社会存在”,即探讨文学本文产生时的社会、历史与文化语境;(2)探讨“文学本文中的社会存在”,即探讨存在于文学本文中、通过特定的文学语言表现出来的社会、历史与文化语境。鉴于此,学者布莱斯勒在谈到文化诗学的方法论时说:“为了理解文本的意义,文化诗学的批评家考察三个相关的领域:作者的生活,能在文本内发现的社会法则与规定,和被证明存在于文本中的作品的历史语境的反映。”[5]这里的后两个领域可以说即是上文葛林伯雷说的两个因素,而第一个领域所说的“作者的生活”,其实也可以纳入到“文学本文周围的社会存在”这一点中去,因为作者是作为社会存在中的人生活的,正是这样的人创造了作品,即使是他的个人关怀,也可视为作为个体的人的社会存在在作品中的反映。
新历史主义的这种批评方式被美国学者伊丽莎白·福克斯-杰诺韦塞称为“文化解读”(cultural reading,也可译为文化阅读)。[6]这可以视为是一个与新批评的“细读”(close reading)相对应的词,代表了新历史主义批评的一种文化分析倾向:分析文本赖以产生的文化和体现在文本中的文化。伊丽莎白·福克斯-杰诺韦塞在谈到“文化解读”时,也谈到了“厚描”(thick description),并将这两者同时称为以《表述》杂志为“机关刊物”的新历史主义批评家“有声有色的欢宴”。[7]他在谈到新历史主义时,甚至直接将之定义为“是一种采用人类学的‘厚描’方法的历史学和一种旨在探寻自身的可能意义的文学理论的混合产物。”[8]因此,“厚描”可以被视为新历史主义学者在描述文化现象时采用的一种描述方法。这种方法来自于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兹,他是在六七十年代一系列的文化人类学论文中提出自己的文化概念与“厚描”(又译深描)的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他认为人必须被视作是“文化的造物”。而文化这一概念在他看来“实质上是一个符号学(semiotic)的概念”,他说,“马克斯·韦伯提出,人是悬在由他自己所纺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我本人也持相同的观点。于是,我以为所谓文化就是这样一些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因此,对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我所追求的是析解(explication),即分析解释表面上神秘莫测的社会表达。”[9]正是为了使“对文化的分析”成为“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克利福德·格尔兹提出了“厚描”这一概念,尽管这一概念借自于另一人类学家,但是他本人丰富了它,并使它成为自己文化人类学研究的一种基本方法,这个概念意为详细深刻地描述文化系统中的各种因素,可以是一首诗、一部历史、一项仪式、一种制度、一个社会,而且这种描述是一种解释,这种解释“能够把我们带入它所解释的事物的本质深处”。[10]应该说,在文化概念的理解、文化分析的观念与文化分析的方法上,新历史主义批评家都深受克利福德·格尔兹的影响。
文化诗学关于文学文本作为社会性文本与文本概念的膨胀的观念体现在具体的文本研究当中。文化诗学的批评实践主要集中于两个领域:英国文艺复兴研究和当代文化研究。在英国的文艺复兴研究中,他们更关注描述历史的新的方法与文学文本究竟是如何与历史构成同谋的关系的;而在当代文化研究中,他们更关注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是如何在资本主义经济条件相互流通,并构成同谋关系的。文化诗学的批评家是用自己的批评方法将这两个看似不相关的领域共同纳入到自己的批评视野之中的,即:考察作品与社会的相互形成的过程。换言之,共同的出发点都是恢复各种文化文本之间的关联。
葛林伯雷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造型》一书中提出了“自我造型”这一既关系到作者和文本,又关系到社会文化的概念,其方法即是“文化诗学”,其重点在于:“观察作家于表达观念、感情,呈现本身的欲求时,所牵涉到的社会约束、文化成规、自我的形成及表达方式。”在分析莎士比亚时,他以《奥塞罗》为例,说明莎士比亚本人与其中的角色伊阿古的关联:“剧作家也能把未被见到的(政治、性行为、宗教、意识问题),加以铺写,将现成的资料转化为舞台的脚本,一方面将他人、社会的‘真理’视作意识形态的产物、构成,一方面则能加以盗用、推翻。”也就是说,“文学的戏剧排场是以‘含纳’、‘转化’、‘不苟同’的方式,去演出错综的意识形成与拒抗过程,在作品里一直是以‘我’与‘他’、‘权威’与‘外在’的冲突来达成自我塑造”。与葛林伯雷的研究方法相类似,孟酬士在谈到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诗人锡德尼时,提出了“劝说”与“操纵”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蕴含了作者与读者、诗与宫廷(女王)、写作与政治、臣服与支配的关系”。孟酬士认为,锡德尼“将宫庭的游说修辞加以运用、操纵、经营,不仅以寓喻的方式向女王争宠,而且教谕她统治国家的道理。诗人反成了主宰,不纯只是臣民。”[11]新历史主义批评家的这种文艺复兴研究表明,文学文本并不像新批评说的那样是一个封闭的客体,而是一种社会性存在的产品,作者是促成这种产品的论述主体,正像社会是由各种不同的主体与权力相互斗争形成的,文学文本也如是。这些文学文本确实是在社会的文化网络中形成的,同时也对这种文化网络的形成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们今天所称为文化的东西,正是所有这些文本相互交织形成的结果。
关于当代文化分析的例子,我们可以举葛林伯雷的一个例子来说明。对葛林伯雷来说,这是一个“将娱乐或消遣、美学、公共领域、私人财产结合在一起的实例。”
1976年,一个名叫盖瑞·吉尔摩的罪犯从联邦监狱获释,迁到犹他州的普罗沃。数月后,他因拦路抢劫、连杀二人被捕,被认定犯杀人罪收监。此案轰动一时,因为吉尔摩自己要求处以死刑。由于法律保护,这一刑罚在美国已多年没有执行。结果,尽管遭到美国民权自由联盟和全国有色人种进步促进会的强烈反对,还是照吉尔摩的意思去做了。此案的法律诉讼过程和最后的枪决于是成为全国新闻媒介注意的事件。早在判决宣布之前,诉讼过程就引起诺曼·梅勒和他的出版公司沃纳书社的注意,按照所印书籍书名页上的说法,这是“一家通讯公司”。梅勒的调查助手杰尔·赫森伯格和一名雇佣撰稿人兼调查员劳伦斯·席勒进行了广泛的访问调查,弄到了法庭审判的文件、记录,以及吉尔摩与他的女友之间的情书之类的个人文件。这些材料当中,有些是公开的,但许多是不公开的,只好花钱买来,这些细节本身也成为上述材料的一部分,所有这一切经过梅勒的再加工,都写进了他的《行刑者之歌》这部小说中。这部小说被称作是“真实生活小说”,是真实文献记录与梅勒独具特色的传奇主题的绝妙结合。小说在批评界和市场上都大受欢迎。紧接着,它就上了全国广播公司的电视微型系列节目,一连许多晚上被用来帮助推销汽车、洗衣粉和除臭剂。
梅勒的小说又进一步生出一些未曾预料到的枝节。在《行刑者之歌》撰写过程中,《民众》杂志曾刊载一篇评论梅勒的文章。一名叫杰克·爱波特的罪犯读后便写信向梅勒提供有关监狱生活的第一手资料。于是他们开始了通信交往,信中所提供的详细的信息以及梅勒所谓的“文学的分量”给梅勒留下了越来越深刻的印象。这些信件经兰登书屋编辑厄罗尔·麦克唐纳的剪裁加工成书出版,书名为《野兽的肺腑之言》。这本书也受到广泛的好评,在梅勒的帮助下,作者获假释出狱。
梅勒在爱波特一书的前言中写道:“当我写下这些话的时候,爱波特今年夏天看来会获得假释出狱。他的确该出狱了。”爱波特则在书中写道,“在过去近二十年中,除了格杀、争斗和暴力行为,我从来没有同任何一个人有过身体接触。”爱波特成了名人,他在获释后不久的一天来到一家通宵餐厅,他问一名侍者能否用一个男厕所。这位名叫理查德·艾登的侍者——他的愿望是当演员或剧作家——告诉爱波特餐厅内没有男厕所,请他上外面去。艾登陪他走到人行道上,而爱波特显然以为受到了挑衅,便操起一把厨刀刺进了艾登的心脏。爱波特被逮捕,又一次以杀人罪下狱。这些事件本身被写成一个剧本,也题名为《野兽的肺腑之言》,最近又受到好评。
通过对这个例子的详细列举,葛林伯雷意在说明:“社会话语”和“审美话语”之间存在着非常复杂的关系。他说:“文学批评论及艺术作品与所反映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有一套熟悉的术语:我们称之为隐喻、象征、寓言、再现,而最常用的是摹仿。这些术语各有其丰富的历史,是绝对必要的,可是,不知怎么的,如果用它们来说明梅勒的书、爱波特的书、电视系列报道、剧本等等构成的那种文化现象,它们总让人觉得又不那么合适。不仅对于当代文化现象不合适,对于过去的文化也是一样。这样,我们就需要有一些新的术语,用以描述诸如官方文件、私人文件、报章剪辑之类的材料如何由一种话语领域转移到另一种话语领域而成为审美财产。我认为,若把这一过程视为单向的——从社会话语转为审美话语是一个错误,这不仅因为这里的审美话语已经完全和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捆绑在一起,而且因为这里的社会话语已经荷载着审美的能量。吉尔摩不仅明确表示,《飞越疯人院》的电影使他深受感动,而且,他的整个行为规范似乎都是由美国通俗小说、包括梅勒本人的小说所再现的种种特点铸造的。”这样,葛林伯雷就认为,在资本主义的社会话语和审美话语中间存在着“流通”,而正是这种流通构成了现代审美实践的核心。本着这种观念,他进一步审查艺术作品的形成,并且认为“艺术作品本身并不是位于我们所猜想的源头的纯清火焰。相反,艺术作品本身是一系列人为操纵的产物,其中有一些是我们自己的操纵(最突出的就是有些本来根本不被看作是‘艺术’的作品,只是别的什么东西——作为谢恩的赠答文字,宣传,祈祷文等等),许多则是原作形成过程中受到的操纵。这就是说,艺术作品是一番谈判(negotiation)以后的产物,谈判的一方是一个或一群创作者,他们掌握了一套复杂的、人所公认的创作成规,另一方则是社会机制和实践。为使谈判达成协议,艺术家需要创造出一种在有意义的、互利的交易中得到承认的通货。有必要强调,这里不仅包含了占为己有的过程,也包含着交易的过程。艺术的存在总是隐含着一种回报,通常这种回报以快感和兴趣来衡量。我应该补充说,这里总要涉及到社会的主宰通货——金钱和声誉。我这里用的‘通货’是一个比喻,意指使一种交易成为可能的系统调节、象征过程和信贷网络。‘通货’和‘谈判’这两个术语就是我们的操纵和对相关系统所作调节的代码。”在这里,葛林伯雷用一种隐喻性的商业语言说明了艺术作品文本形成的文化机制:作为“通货”,它是创作者与“社会机制和实践”“谈判”所形成的“协议”性产物。而这正是葛林伯雷通过在社会话语与审美话语进行跨学科文化分析得出的结论。
重新确证文本的界限?
美学者阿兰姆·维塞在编辑《新历史主义读本》时,在细读了新历史主义批评家的批评文本之后,认为新历史主义的一个理论假设是“文学和非文学的‘文本’不可分离地流通”。[12]上述文化诗学的批评家对文艺复兴与当代文化的“文化解读”实践,确实已经给我们以这种印象。在这里,文本概念确实被无限地扩张了。正如斯图亚特·霍尔所说的,文化概念被“大众化和社会化”,甚至连艺术也不再具有早期理论框架中的“优越地位”,被作为“文明最高价值的试金石”,现在重新被限定为“一般社会过程中的一种特殊方式:意义的给予和获取”。[13]这样,这种文化概念所导致的文本的扩张就带来了两个极为明显的后果。一方面,大众化和社会化的文化文本进入了学院和社会的文化研究的范围,带来了民主的平民意识形态,知识分子以其文化批判者的形象通过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同性恋研究、传媒研究等极富有文化参与精神的文化研究形式介入到当代民众的生活及其精神世界中去。另一方面,文学失去了独特性,文艺似乎又回到了传统的“摹仿”论中去了,它只是对社会生活的某种真实反映,艺术更多的只是在“意义”上被使用,而其本身更为复杂的结构和审美形式又缺席了,文学降低为例证,其本身的艺术性被搁置不论了。这样,我就仍然抱有这样的疑问:是否有重新确证文本的界限的必要?就像上述葛林伯雷的研究中,小说似乎只是文化网络中混同于各种社会事件的一个事件,它本身的艺术性似乎并不重要?我注意到葛林伯雷花大量的篇幅在描述审美话语和社会话语的流通,在提到小说时只是浮光掠影地说到“小说在批评界和市场上都大受欢迎”,“这本书也受到广泛的好评”,我无法对这一文化事件,特别是这两本书作深入的研究,但我关心的是,评论家的兴趣似乎转移了,由对审美话语内在的审美研究转向了审美话语与社会话语的“关系”的研究。或许,这种对文化文本之间的“关系”的注重导向了文本界限的消失?例如,在上述葛林伯雷所描述的文化现象中,小说作为审美话语真的与其他社会话语是毫无界限的?或许,就其生产的来源说,我们可以得出这一结论。但是,读者阅读的往往不是文化现象的全部,而只是作为这种文化现象的产物的小说自身,就像我们在地铁上、在公园中、在居室里,看到读者手捧一部小说阅读时所表现的那样。这种阅读又在更为具体的公众实践中重新区分了审美话语与社会话语某种有形无形的界限。
诚然,新的文化诗学与稍后兴起的文化研究对阐释当代文化现象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可以说,不借助于这种文化现象,我们根本无法认清当代文化现象,即使是稍有了解。在这种文化现象里,娱乐、消遣、美学、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很好地合在了一起。比如最近围绕着《手机》的一系列文化现象。据说崔永元参与了该部电影的早期制作,而这部影片后来被指责为影射“实话实说”这一广受中国大众喜爱的集娱乐、思想这些很难调和在一起的节目与崔永元本人。于是崔永元本发表了对电影长达万言的“批判书”,而这种批判又被部分的媒体记者指责为“过火”,是一种炒作,据说本身又成为崔永元本人正在制作的另一电视节目“电影传奇”的推销。确实,这里的“通货”如葛林伯雷所言,是“金钱与荣誉”,也正像维塞评论新历史主义时说的,“新的经济学需要新的诗学”。[14]我们很难从单一的一个文本出发认识这种文化现象。在这种现象里,一切都成了消费。这样,就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可以认为文化诗学与当代的文化研究所研究的文化现象确实是具备着充分的消费文化的特点的,而且,这种消费文化更多的是将自己的基础建立在“经济”上而不是审美上的,或者说,审美也是为某种经济的目的服务的。文化研究热衷于揭示美丽的语言与丑陋的政治、经济、或者说是权力的共谋。我们也不难发现,文化研究最初的活力很大一部分要依赖于此,就像女权主义批判传统文学文本的男权倾向,后殖民主义批判传统文学作品的欧洲中心论倾向。但是,这是否真的能证明文学与政治、经济、权力一样丑陋呢?正像在白居易的《长恨歌》里,我们不难发现美丽的文学语言与政治的共谋,但“君王的爱情”是否一定是对现实政治的反讽?文本可能依然固我,它的魅力依然会是一种“艺术”的魅力。建立起白居易的《长恨歌》与社会历史的关联是相当容易的事,但要区分《长恨歌》作为一首诗的存在与别的社会存在确有不同却相当困难。或许,这才是真正的“文化的诗学”要解决的任务,即:在建立起文本的关联之后,仍然区分文本之间可能的界限。
标签:文学论文; 艺术论文; 新历史主义论文; 文化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艺术批评论文; 长恨歌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