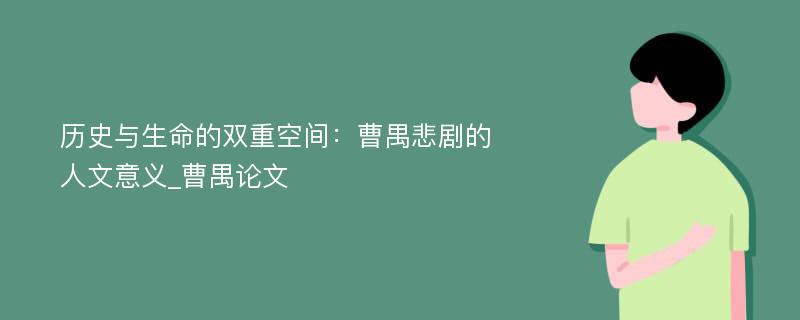
历史与生命的双重空间:曹禺悲剧的人文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悲剧论文,人文论文,意义论文,生命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悲剧,作为一个美学范畴,它最强烈地体现了创作主体对人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价值的关注。曹禺作为一位人类苦难的歌人,在他《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四大杰作中,他那注入全部情感的特殊的生命体验,他所经历的人世的不公、冷漠、庸俗、卑劣,难以言述的愤懑情绪,对“家”的解构渴望,对畸形都市人际关系的厌恶,以及他对人生、生命的形而上的痛苦思索,则无处不在地浮现出曹禺那深沉的历史感悟和广厚的人文关怀。
一
在《雷雨·序》中,曹禺说,起初有了《雷雨》模糊影象时,逗起他兴趣的只是一两段情节几个人物,和一种复杂而原始的情绪,但“写到末了,隐隐仿佛有一种情感的汹涌的流推动我,我在发泄着被压抑的愤懑,毁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注:《雷雨·序》,《曹禺文集》第1卷,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版,第211页。)。曹禺前期创作对人的生命、对人类命运进行着紧张而痛苦的思考,甚至乐于使用乌托邦式的宗教情绪去审阅人的生活,但并没有割断人与其生活着的世界的联系,通过对人生存的这个世界的打量和审视,去发现阻滞人的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的痼疾存在。可以说,曹禺的整个艺术世界,是建构在以人为中心的历史与生命的双重空间之中的,他把悲剧的根系深深地扎进了中国历史和社会的土壤中,对传统的道德文明给予了决绝的批判。
家族文化是整个中国文化体系的缩影。“中国的大家族制度,就是中国的农业经济组织,就是中国二千年来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政治、法度、道德、学术、思想、风俗、习惯,都建筑在大家族制度,作他的表层构造”(注: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96页。)。家族制度最大弊害是家长专制,对尊卑有序男女有别的家庭角色的心理认同,对“人”这个社会主体的个体价值的理性忽视,以及因之而扩张的外力压制。
周朴园是父权、夫权的象征。“他的脸带着多年的世故和劳碌,一种冷峭的目光和偶然在嘴角逼出的冷笑,看出他平日的专横、自私和倔强。”(注:《曹禺文集》第1卷,第58页。)为了将家庭成员纳入“最圆满、最有秩序”的轨道,他说一不二,苛酷地要求每一个人,从精神上、心灵上折磨着妻子和儿女,扼制他们的人性,窒息他们跳动的心灵。周冲善良、天真而充满幻想,然而在严厉的父亲面前却很懦弱。繁漪是周朴园的妻子,年轻、聪敏,不甘于沦为丈夫的附庸、玩偶,即引起周朴园的不满,对她冷落之外,用种种可以利用的伦理标准来钳制她,直至给她扣上“神经病”的帽子,把她“磨成了石头一样的死人”。曾皓家道趋于衰落,已失去周朴园那样的绝对权威,但他仍坚持“以诗礼为不可更改的信条”。“他非常注意浮面上的繁文缛礼,以为这是士大夫门第必不可少的家教,往往故意夸张他在家里当家长的威严”(注:《曹禺文集》第2卷,第502页。),动辄教训儿孙。儿媳曾思懿是曾家伦理纲常的执行者,当瑞贞不肯听她的话喝下安胎药时,她勃然变色,声色俱厉地斥责道:“叫她喝,要她喝!她要不听话,你告诉我,看我怎么灌她喝!”曾思懿尽管是女性,但在文化内涵上却是一种男权符号,一种父权符号。
家族制度表面上重视人伦亲情,然而温情脉脉的背后制造的是虚伪、荒谬和淋漓的鲜血。如傅立叶所说:“再没有比家庭小组(指家族制度——引者)占支配地位的文明社会和宗法社会更虚伪的了。野蛮社会比我们所处的社会更具有血腥味,更富于压迫性,但虚伪毕竟要少一些”(注:《傅立叶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1页。)。曹禺笔下周朴园们的作恶,并非那样直捷痛快,他们要冠冕堂皇得多,也阴损得多。周朴园“真心”地“关心”繁漪“药喝了没有”,“请大夫来看看”;曾皓死死拉住愫方,却还言不由衷地表白“不肯嫁的女儿,我不是一样养么”。周、曾作为男权代表,对女性而言,带来的是无穷尽的压逼和眼泪。繁漪在这枯井一样的周公馆,闷得透不过气来;愫方在精致而死寂的曾家旧宅磨去青春和朝气,一点点地把世界缩成一颗寂寞的心。在周家、曾家还有焦家(焦阎王固然死了,但那张诡秘的相片却无时无刻笼罩着剧中每一个人,仇虎对他的相片连开三枪,或许也是一种象征,对其阴魂笼罩的反叛),他们是种种罪恶的制造者、支撑者,尽管他们最终去处是隐入历史的黑暗,但他们的力量依然那么强大,以至使所有人特别是女性,陷入孤立无告的悲惨境地。
生命活力的获得是以人对自己生命主体性的拥有为前提的,家族制度对人的主体性肆意践踏、玷污,生命活力于是被窒息和扭曲。在曹禺剧中,封建家族子辈形象都有着萎缩、怯弱、无聊、空虚的精神特征。周萍本来并不缺乏年轻人的激情,也不满父亲的专横,正是这一点使他赢得了繁漪的爱情,周冲的敬重。然而他“性格上那些粗涩的渣渣经过了教育、提炼,成为精细而优美了”,因此,“在他灰暗的眼神里,你看见了不定、犹疑、怯弱同矛盾”(注:《雷雨·序》,《曹禺文集》第1卷,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版,第53页。)。对繁漪的疏离是他“蛮力”销蚀的表现。半是慑于父亲的威严和所谓道德谴责,半是为着厌倦,他转向单纯善良的四凤;而对一心一意指望他的四凤,他也怯于门第观念不敢负起责任。在无法解决的重重矛盾中,最终只能发出“我够了,我是活厌了的人”的哀叹,饮弹而亡。如果说周萍因精神委靡而异化为“情感和矛盾的奴隶”,焦大星则有着相似的精神历程。他本来体貌不凡,“身体魁伟,亮晶的眼有的是渲泄不出的热情”(注:《曹禺文集》第1卷,第490页。),但母亲与妻子为他的争斗使他由苦恼而趋于怯弱。焦母在剧中代表着父权,她以挑拨儿子与儿媳的情感来维系自己的威势,焦大星怕极了疼他又控制他的母亲,他想躲开母亲与媳妇的争夺,终究只是白费了半天力气。像这样的男子,对女人来说是“恶”的意义上的好人,他的怯弱恰是最不能原谅的品格。无怪金子轻蔑地称他是一辈子没有长大,总是在娘怀里吮渣儿的“孩子”。与周萍、焦大星相比,曾文清身上更具有传统士大夫家庭的烙印,他外表清俊飘逸,谈吐不俗,琴棋书画,茶道养鸽,无一不精,然而他生活在“仿佛生来就该长满髭须,迈着四方步”的曾家,养成沉滞、懒散的个性。面对真诚爱他的表妹愫方,他不敢表达内心情感,只会躲到一边去吟诵陆游《钗头凤》。他从不敢涉足社会,即使下决心走出家门,外面的风雨一下就把他吓了回来。在安逸、寄生的生活中他已经泡酥了骨头,麻木了神经,就像是养惯了的鸽子,再也飞不动了。在宗法社会里,父(母)辈为了家族的延续,总是按照家族制度规定的行为准则为子辈们确定人生道路,铸造他们的灵魂。特别是家族中的长子,是家族文化的继承者,被赋予了极大的期望,也承受了更大的压力。周萍、曾文清们除了心甘情愿地放弃独立的意志和人格,满足家族的要求,别无选择。
家族文化不仅肆意扼杀家族内人的主体生命,而且在更大范围内限制了人的心灵空间和精神视野,使社会各阶层的人性发生着畸形的异化现象。与世家子弟不同,仇虎不属于封建家庭,他是黑暗制度下的受害者和叛逆者,复仇是他向恶势力挑战的特定方式,然而他的复仇是典型的家族复仇,是以血亲利害为尺度的。按封建伦理,“父之仇,弗与共戴天”(《礼记·曲礼上》),按孔颖达疏:“父是子之天,彼杀之父,是杀之天,故必报杀之,不可与共处于天下也。天在上,故曰戴。”父仇子报以行孝道,成了仇虎唯一的生存价值;而仅从家族立场出发的报复行为具有极大盲目性,很容易违背普通世道人情,表现为非人性的残忍。当仇虎发现焦阎王已死,复仇对象不复存在,便在家族情绪催动下,以“父债子还”为由,残酷地杀害了焦大星和小黑子,以使焦阎王“断子绝孙”。然而这又使他陷进与人类道德本性的冲突之中,导致他的精神分裂,以至最后的毁灭。仇虎激烈的复仇行动最终演变为家族宗法观念的外化,他的反抗愈激烈,愈彻底,表明他受传统的束缚愈深,从而形成了一种文化的悖论,文化的悲剧,作品由此达到了令人震惊的历史深度。
家族文化在“五四”以后新文学作品中受到了解构和颠覆,然而在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遏制人的个体生命、造成人的异化,除古老的宗法家族制度外,还应包括现代都市文明。资本主义突破封建桎梏得到一定程度发展,是一种时代的进步,然而无限制获利的欲望,对物质、金钱的狂热追求,同样会束缚人性的健康伸展,使人在高度物质文明中间迷失了自我。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货币乃是对个性的普遍颠倒,它把个性变成它们的对立物,赋予个性以与它的(现实)特性相矛盾的特性”(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8页。)。
曹禺作为一位天才的现实主义作家,他不只抨击了传统家族文明,而且对现代都市文明的非人道性进行了深刻的揭示。与家族文明一样,畸形繁荣的都市文明同样是人性异化的渊薮。《雷雨》中的周朴园在家庭是暴君,在社会则是贪婪凶狠的资本家,他为积攒资本而不择手段,昧着良心故意让承包的江堤出险,淹死二百多名小工,为的是从每个小工性命扣下三百元钱。这同英国的圈地运动一样充满了灭绝人性的血腥。为了煤矿公司的利益他叫警察开枪打死三十名工人;而当周冲指责他不给受伤工人抚恤金,他不屑一顾地训斥道:“现在一般青年人,跟工人谈谈说两三句不关痛痒同情的话,像是一种很时髦的事情!”这些场景和对话充分显示了人性在金融社会的极端异化。在《日出》中《雷雨》的血缘纠葛已不复存在,代之以人与人残酷的拼斗。从大都市的高级宾馆到宝和下处这人间地狱,到处是颠狂、混乱、挣扎和呼号,一片郁热、紧张和焦虑的气氛。金钱像一个紧箍咒,套在每个人心头上,摄去了他们的灵魂。人们在金钱的驱策下,疯狂着、格斗着、奔跑着、撕杀着,人人想尽办法抓钱。潘月亭耍尽伎俩,笼络异己又剪除心患,裁员减薪又虚张声势地加入公债投机,企图逃避破产结局;李石清为了钱,压抑着人的自尊,对有钱人阿谀逢迎,以无聊的凑趣去逗人家高兴。当金钱诱惑和肉体欲望结合到一块时,就会产生光怪陆离的交易:粗俗臃肿的顾八奶奶因为有钱,惹得油头粉面的胡四当她的面首;张乔治因为有钱,就可随心所欲地抛弃妻儿,朝三暮四地向一个又一个女人求婚。金钱在制造种种风流与荣耀故事的同时,也在制造着更多的欺凌和压迫的惨剧,小录事黄省三病入膏肓,还是一天到晚抄写,以图十块二毛五去养活三个孩子,然而这微薄的希望也不能满足,最后竟落入求生不得求死无门的惨境。
叔本华说:“欲望按其实质来说是痛苦”;“如果我们对人生作整体地考察,那么我们只强调它的基本的方面,那它实际上总是一场悲剧,只有在细节上才有喜剧的意味”(注:转引自全增嘏主编:《西方哲学史(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12-413页。)。人们对金钱、物质的欲望越是强烈;她也就将承担更大的痛苦。陈白露曾经是一个追求精神自由的新女性,她有过对爱情的憧憬,然而平淡的婚姻生活击碎了她的爱情梦;她走进城市一心追求自由的理想,想扮演强者的角色,但受不住奢华生活的诱惑,他从婚姻的笼中飞出来,却投入更封闭的金丝笼。她讨厌自己的生活,厌恶把自己的青春买走的客人们,但腐朽的生活方式,使她丧失了挣脱牢笼的勇气和能力,在对世界彻底绝望后同自己的青春诀别。
弗莱德·R·多尔斯说:“我们把现代性主体性的兴起和以人为中心的个体主义看作是一种可以避免的错误,然而却是人的解放和成熟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尽管这一个阶段的内在缺陷现在已变得非常明显了”(注:(美)弗莱德·R·多尔斯:《主体性的黄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对家族文化的解构只是意味着中国文化从根本上走向现代化的开始,如果对现代文明造成人性异化的一面缺乏清醒的批判态度,那么人们从封建主义精神束缚下挣脱出来,还会陷入新的精神危机之中,而无望真正获得救赎。尽管曹禺当时的认识还有不少困惑,然而他所创造的艺术形象已经提出了现代人难以回避的这个重大的课题。
二
曹禺前期剧作不仅是对旧的文化制度的批判,它更为夺目之处是对人类命运的关怀,对人类意识深处的关注。在他笔下,宇宙像一张大网,人在其中挣扎,永远处在压抑与抗争之中,有无可消除的无望和恐惧,人类的软弱性制造着他们永恒的悲剧人生,“他们怎样盲目地争执着,泥鳅似地在情感的火炕里打着昏迷的滚,用尽心力来拯救自己,而不知千万仞的深渊在眼前张着巨大的口。他们正如一匹跌在沼泽里的羸马,愈挣扎,愈深沉地陷落在死亡的泥沼里”(注:《雷雨·序》,《曹禺文集》第1卷,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版,第213页。)。曹禺不仅仅停留在历史的表层,而且还穿透了社会历史的外壳,剖析人类生命本体,寻找人类社会深层的破坏力和创造力,因而他的剧作不仅具有广泛社会批判意义,而且具有深刻的现代文化意蕴,让人从最根本的生命价值层面上启迪人生感悟人生,可谓生命的启示录。
朱光潜在《悲剧心理学》中分析易卜生作品时写道:“悲剧之产生主要正在于个人与社会力量抗争中的无能为力。这些社会、自然力量虽然可以用因果关系去加以解释,但却像昔日盲目的命运一样沉重地压在人的头上”(注:朱光潜:《悲剧心理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08页。)。把这句话用来形容曹禺的命运也是观念十分恰当的。《雷雨》中的八个人物都像笼里的困兽,无法逃脱。侍萍承受不了被遗弃的痛苦而投河自尽,却被救了起来;三十年风风雨雨使她明白了“人性太弱,太容易变”,对生活中可能引起的纷争与不幸,她采取处处回避的态度,但命运偏偏选中她与她周旋,在她稍有疏忽时悄悄找上门来,在她身上发生过的悲剧在她女儿身上继续下去了。周萍不止一次地要离开恐怖而又郁闷的周公馆,他痛苦着、行动着,也躲避着,可是繁漪的一再阻拦,双重乱伦的打击,使他终于无法离开,并以死亡为终结;繁漪向专制、无情的家庭、丈夫挑战,近于枯竭的生命开始复苏,然而她很快便发现周萍并非是她所能依靠的男人,却又不甘心就此罢手,她开始行动,作出周密安排,万般无奈下甚至表示愿意周萍带她和四凤一起离开,但得到的却是周萍轻蔑的一笑,这迫使她不顾一切地作最后一搏,与周家一起毁灭。至于剧中那个冷酷而又矛盾的周朴园,难道他不也在苦苦地挣扎么?他要挣脱的是三十年前薄情寡义留下的阴影和苦果,他也无法逃脱——苦果和惩罚最终还是降临了。
在《雷雨·序》中剧作家有一番关于人与命运的叙写——“我念起人类是怎样可怜的动物,带着踌躇满志的心情,仿佛是自己来主宰自己的命运,而时常不是自己来主宰着。受着自己——情感的或理解的——的捉弄,一种不可知的力量的——机遇的,或者环境的——捉弄;生活在狭的笼里而洋洋地骄傲着,以为是徜佯在自由的天地里,称为万物之灵的人物不是做着最愚蠢的事么?”(注:《雷雨·序》,《曹禺文集》第1卷,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版,第212页。)这段话是对人生悲剧的高度概括,这种不可知又不可免的命运使曹禺悲剧带上了宗教的色彩。有的论者甚至认为“基督教的‘原罪’与‘报应’思想对《雷雨》具有整体构思的影响。”(注:宋剑华:《试论〈雷雨〉的基督教色彩》,《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8年第1期。)但我以为与其说曹禺有意识地用宗教来诠释世界,不如说宗教作为一种解释宇宙神秘因素的方式暗合了曹禺对命运之谜的执着探索和对生命意义的渴求。
曹禺出身于家境优裕的官僚家庭,但沉闷得坟墓似的家庭气氛使他从小心情苦闷,性格忧郁。在耳闻目睹了许多人世的苦难后,他从中外先哲著述中深切体验到旷野里凄厉地为人类悲惨处境呼唤的悲剧情感,引发了对人类生存处境和终极目的的思考。“我当时有一种感觉,好像是东撞东撞,在寻找着生活的道路。人究竟应该怎么活着?总不应该白白活着吧,应该活出一点道理来吧?”(注:曹禺:《我的生活和创作道路》,见田本相《曹禺剧作论》,中国戏剧出版社1981年版,第370页。)他在创作中对人物命运的关注和对人物心灵的体验,即包含着他对生命意义的追问,对生命的困惑和求索。《雷雨》中周冲即是作家的一个视角,“是全剧最具有人文精神的人物”(注:王蒙:《永远的雷雨》,《读书》1993年第4期。)。他那样纯真,完全生活在自己的理想之中。那段“明亮的天空”、“无边的海上”、“一条轻得像海燕似的小帆船”梦幻般的独白中特别说到:“现在的世界是不该存在的……我们可以飞,飞到一个真真干净、快乐的地方,那里没有争执,没有虚伪,没有不平等……”这段话看上去空洞无力,曹禺理智上也许并不赞同,但从感情上来看,正如钱谷融先生所言,作者对这种思想还不能完全抛弃,甚至还十分的依恋(注:钱谷融:《〈雷雨〉人物谈》,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59页。)。它透露出作者道德理想国中,人应该是平等、自由的,没有争斗,只有和谐,是一个充满乌托邦人文意味的彼岸世界。事实上,剧作家的道德理想与社会感性存在极不平衡,他借《日出》中方达生之口表达出这样的困惑:“人与人之间为什么要这么残忍呢?为什么允许金八这么一群禽兽活着?”他甚至痛下“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的决心。由此可见,曹禺将对宇宙间许多神秘的事物的憧憬注入悲剧创作之中,尽管带着宿命的色彩,但这是一个探索的灵魂对现实观照时产生的迷惘与愤慨,更表达了他抑制不住的道德焦虑。对于曹禺而言,他对命运无常的思考,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作品的历史容量和审美空间,赋予了作品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
“观赏一部伟大悲剧就好像观赏一场大风暴。我们先是感到某种压倒一切的力量那种恐惧,然后那令人畏惧的力量却又将我们带到一个新的高度,在那里我们体会到平时在现实生活中很少能体会到的活力。简言之,悲剧在征服我们和使我们生畏之后,又会使我们振奋鼓舞。在悲剧观赏之中,随着感到人之渺小之后,会突然有一种自我扩张感,在一阵恐惧之后,会有惊奇和赞叹的感情”(注:朱光潜:《悲剧心理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84页。)。《俄狄浦斯王》中神谕作为命运代名词,扮演着一位令人畏惧的角色。俄狄浦斯王在命运播弄下的无可奈何,在上天命运安排下一步步走向罪恶和最后的惩罚,具有着永恒的艺术魅力。在曹禺笔下,“雷雨”式的“郁热”,不只是戏剧的氛围,同是暗示着一种生命的存在方式:不可遏制的情热,超常态的欲望和对欲望超常态的压抑,二者互相撞击激起生命白热化的爆发,又迅速跌入黑暗的深渊。曹禺痛苦地审视他的人物,发现了生命的无奈和挣扎:每个人都渴望把自己从不堪忍受的生存方式中解放出来,却没有自我拯救的力量,只能心造一个幻影(周冲、周萍兄弟之于四凤,繁漪之于周萍),死死揪住不放,却不自知地犯了更可怕的罪恶,导致最后的死亡——这才是剧作家真正的恐惧和愤激。陈白露想摆脱平庸,渴求自由,但生活的艰辛和享乐的欲望又使她甘于堕落,在人生歧路上越走越远。当方达生叩响她对生活的希望时,尽管她看穿了世界的荒谬,寄生的生活却使她丧失了飞翔的能力。仇虎怀着刻骨仇恨前来复仇时,直接的仇人却不复存在,他按封建观念复了仇,自身却在报仇之后陷入灵魂的分裂与挣扎。陈白露、仇虎,还有曾文清等,他们都是现实意义上的人,他们都有自己的情感追求,这感情是他们精神空间的内在支撑,但在多重压力下被失落生活理想后的绝望所淹没。
“宇宙正像一口残酷的井,落在里面怎样呼号也难逃这黑暗的坑”,这种看似消极的宿命观与叔本华的悲观哲学有联系,但在曹禺这里,笔者以为有着特殊的意义。一方面,他并没有把人的命运抽象化、理念化,而是把对社会人生的思考和切实展示融合起来,这只要看周萍与繁漪的乱伦关系就是双方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这种有意识的乱伦极为深刻、极为强烈地折射出封建家庭对人性尤其女性的束缚,到了怎样忍无可忍的地步,这就使《雷雨》的现实主义锋芒,穿透命运主宰的迷雾,显出逼人的寒光;另一方面,曹禺对命运的思考立足于人类生存的悲剧性体验,表现人在恶劣、荒谬的生存环境下的无助和无奈,让人看着美好的东西眼睁睁地被无情地摧残,撕裂,不能不感到无比的愤慨和恐惧,同时让观众一点一点地感受到人性的力量,并与自我内心渴望冲破樊篱的冲动相结合,激发出对生命的憧憬和激情。
阿伦·布洛克在《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中说过这样一番发人深思的话:“一方面是人类经验的令人丧气的普遍情况,另一方面又是人类在自信心、承受力、高尚、爱情、智慧、同情、勇气方面能达到非凡的程度,这两者的对比一直是人文主义传统的核心。如果仅仅强调一般男女能够达到尊严、善良和伟大的潜在能力,而忽视我们大多数人是有分裂人格的,很少人能够达到本来能够达到的程度,那么这样一种人文主义就是浅薄的,说不通的”(注:(英)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65页。)。曹禺的人物不是拯救或者美好世界的力量和代表,他们的确有着精神分裂的共同特征,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认,其中许多人并不愿屈服于命运的主宰,而是作了困兽犹斗式的奋争。
曹禺曾经将《雷雨》的人物按照生命力的强弱分为两类,他们“流着血,不是恨便是爱,不是爱便是恨;一切都走向极端,要如电如雷地轰轰地烧一场,中间不容易有一条折衷的路。代表这种性格的是周繁漪,是鲁大海,甚至于是周萍,而流于相反的性格,遇事希望着妥协、缓冲、敷衍便是周朴园,以至于鲁贵”(注:《雷雨·序》,《曹禺文集》第1卷,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版,第214页。)。繁漪被三十年幽闭生活消融了她的青春,却没能俘掠她的热情和意志。她从不后悔和周萍一起在屋子里“闹鬼”,对这种乱伦关系,她充满奇异的道德自信。当事情再无挽回余地,她索性豁出一切,如雷雨般爆发,对周萍万般柔情瞬间转化为极度的憎恨。繁漪形象的力量不在她的“善”,而在她的“恶”。她撼动人心的地方不在她外表,而是她生命底层掩藏着的活力,在温良文弱背后时刻郁结着的“更原始的一点野性”。爱情是人类精神中最深沉的冲动,性爱意识作为社会意识一部分更接近于人的自然属性和深层意识。“也许繁漪吸住人的地方是她的尖锐。她是一柄犀利的刀,她愈爱的,她愈要划着深深的创痕。她满蓄着受着抑压的力”(注:《雷雨·序》,《曹禺文集》第1卷,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版,第216页。)。这“力”,便是她的热情,她的欲望,也就是一个顽强的生命之赖以存在的内在力量。刘西渭在看《雷雨》后写道:“就社会不健全的组织来看她无疑是个被牺牲者;然而谁敢同情她,我们这些接受现实传统的可怜者”?(注:刘西渭:《〈雷雨〉》,见《李健吾戏剧评论选》,1982年版,第5页。)周萍是怯弱的,但作者却把他的性格与繁漪、鲁大海相提并论,这表明他身上亦潜在着生命冲动的精神因素。当他听命于内心情感而将道德观念约束抛诸脑后,“一种可以炼钢熔铁,火炽的,不成形的原始人生活中所有的那种蛮力”(注:《雷雨·序》,《曹禺文集》第1卷,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版,第53页。),在他身上便奇迹般地复活了。他没有按早已安排的他们这一类人的命运,娶一位有钱有势门当户对的小姐,他争取爱的自由,这表现在他对繁漪的爱,这爱使他不顾一切地投入到激情中去,干灭伦的事也不怕。陈白露陷身于都市靡烂生活,但她精神世界里保留的却是另外一种生活。在看到玻璃窗霜花一刹那间,从她“孩子似的”一番惊喜,我们发现在她所厌恶的环境里生活多年,她对精神生命的渴求并未全部耗损,在她心灵深处尚保存着一方纯净天地,保有一个真的生命追求。当她暂时保护了小东西的时候,她欢呼太阳,读《日出》时,“我喜欢太阳,我喜欢春天,我喜欢年轻,我喜欢我自己。”可见在她这颗女性的柔弱心里奔流着怎样汹涌的向往光明自由的人性波涛。可周围的环境不适宜生长这样的生命热情,她对环境依赖的惯性愈见强大;但她性格的复杂在于她心灵中仅有的一点抗争的力量,虽不足以让她随方达生离开自己厌恶的生活,可这力量却能够让她决定不愿为这腐朽的生活殉葬。陈白露最后的自杀,不是因为物质生活没有退路和保障,就她自身生命的自主性而言,应该说她的自杀不是毁灭,而是保全。仇虎在复仇过程中纠缠于剧烈的内心争斗,无法摆脱精神重压;但我们不能据此就否定他在整个行动中表现出的烈火燃烧的仇恨,不可阻遏的反抗意志,炽烈的性爱,扭曲的生命激情,咄咄逼人的威势。这是与传统精神重压下的腐朽空虚精神状态相对立的。他以复仇这一非常态的行为来表现自我尊重,确证自我,固然表现为盲目性一面,而从价值观来看,我们不能不肯定他是一位与旧世界势不两立的硬汉子,在他身上突显了封建时代所缺乏的人的胆识和阳刚之气。金子是一个意志力极为强悍的女性,不加掩饰的爱与恨,完整地集于她一身。比起繁漪、白露来,金子是幸运的,她指望的男人是有着浓烈生命力的仇虎,他们的结合纯粹是性格上心灵上的契合。她对命运的反抗不是绝望的挣扎,而是主动的攻击。她敢于反抗凶狠的焦母,敢于支使丈夫,甚至公开宣布“我偷汉子”,表现了对封建束缚的蔑视。在她与仇虎火辣的爱情上,金子的生命本性得到了舒张。为了天边外的“黄金城”,她舍弃了安定富足的焦家,跟着仇虎颠沛流离,历尽恐慌惊吓,却终不后悔。
在《北京人》中曹禺让人类学家说出了“北京人”的气质:“那时候的人要爱就爱,要哭就哭,要喊就喊,不怕死,也不怕生。他们整年尽着自己的性情,自由地活着,没有礼教来拘束,没有文明来捆绑,没有虚伪,没有欺诈,没有阴险,没有陷害,没有矛盾,也没有苦恼;吃生肉,喝鲜血,太阳晒着,风吹着,雨淋着,没有现在这么多人吃人的文明,而他们是非常快活的!”(注:《曹禺文集》第2卷,第535页。)在对原始人类的憧憬中,正寄托着剧作家对人类未来的希望。从生命力的角度思考人类的历史走向,是曹禺臧否人物的重要标准。他不喜欢没有生命热情的人,即使他们对社会敷衍得很好。有着善良、温顺性格的愫方,像是一个例外,其实不然。她的容让并非毫无主见的任人摆布,在她柔弱的身躯里有一个希望支持着她——她爱文清,愿意分担他的痛苦,并企冀他能走出旧家过上真正人的生活。这是她唯一的精神支柱和安慰;而一当曾文清回来,她的“天”也就塌了下来。“人总该有忍不下去的时候”,于是她不再将自己的幸福寄托在别人身上,而要去寻觅一片自己的天空。像如此软弱柔顺的女性,终于“忍不下去”,那不是昭示人的本性、人的生命活力在任何严重摧折下仍然不会泯灭么?
加缪在《西西弗的神话》中说:“失去了希望,并不意味着失望。大地的火焰完全可以与天堂的芬芳相媲美。”(注:加缪:《西西弗的神话:论荒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08页。)如果没有对生命的张扬,曹禺悲剧世界会变得流于凡俗,而缺乏那种夺人心魄的热力和魅力。在那个郁闷得像一口古井似的人间,曹禺的悲剧是一种抗争,也是一种寻找,一种对生命的呼喊。曹禺以他精湛的形象塑造和命运安排形成了自己的悲剧美学,具有深邃、长远的人文价值。我以为光是凭这一点,曹禺悲剧便可以屹立于世界戏剧文化之林,永远得到人们的珍爱和崇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