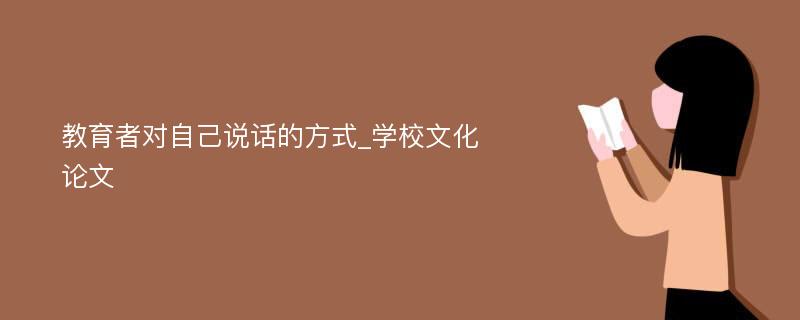
教育家的话语方式:自说自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说自话论文,教育家论文,话语论文,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5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808(2010)08-0007-07
教育家的成长是由一个合格的教师和校长成长为名师、名校长,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独特的教育思想,引领地区与时代的教育发展,成为众望所归的教育家。形成自己独特的教育思想是成为教育家的关键所在,而独特思想的标志就是有自己独特的话语方式。语言是思想的直接外化,一个人的话语方式直接反映出他的思维方式,独特的教育思想一定具有独特的话语方式,那就是自己说自己的话,即“自说自话”。
一、当下“万人同语”话语方式的表现
当下,学校教师、校长在话语方式上出了问题,他们的话语内容、话语方式表现出明显的趋同性,出现“贴标签、换概念”的现象。校长、教师在追风逐浪,流行什么追什么,时髦什么赶什么。研究性学习、体验式学习、小组合作学习,校本课程,校本培训,学习型组织,现代学校制度,多元智能,我们不停地更换概念,基础教育界几乎是万人同语话教育,流行什么概念,就群起而说之。更有甚者不读原著,不问含义,不加区分,张冠李戴,偷换概念,为时髦而时髦,错误地运用别人的理论。例如,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声音——“我的课堂我作主”,不加区分地让所有孩子对所有内容都“自主学习”,这背后是“建构主义”理论在支撑,但建构主义理论是指整个人类建构知识,而不是指单个儿童在建构知识,这种现象是值得我们反思的。我们当然知道国外有许多思想理论是先进的,但我们不能简单地拿来就用,更不能盲目夸大其作用,不能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我们对教育应该作一些形而上的思考和追问。
这几年,基础教育界一波又一波的概念潮流不断涌现,面对时尚我们应该作出正确的选择;面对时髦,我们首先应该问一问:它的含义是什么?它是正确的吗?它适合我们吗?我们必须保持足够清醒的头脑,对其进行理性的判断。著名学者王元化说,潮流不都是趋向光明和进步的。[1]我们应该慎对潮流,读懂潮流,追问潮流,反问潮流。时尚教育口号不等于教育真理,现在有不少教育专家所倡导的教育时尚潮流,有一些是正确的,且符合我国教育的国情;有一些虽然正确,但未必适合我国国情;有一些还只是处于实验阶段,并未取得实质性的成果;有一些连基本的科学性都尚未得到证实,匆匆忙忙拿来效仿,这显然是不对的。对于时尚潮流,我们应该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应该认识到潮流性的东西未必全是正确的,未必全是科学的,而且我们完全还可以追问一下:所谓潮流真的是世界潮流吗?还是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的理论主张、行为实践?教育不应该封闭,不应该排外,但教育同样不是一种时尚,做教育的不能赶时髦,教育改革和发展应该适应本国国情。“中国式文化创新”不仅需要我们对西方各种人文观念进行“中国改造”,同时也需要对中国传统人文观念进行“原创性改造”。
二、“万人同语”背后的深层原因及带来的问题
深究我们的灵魂深处,可以看出有一种自卑感。
我们对自身的教育缺乏足够的信心,我们的教育不够现代化,于是我们有了一个教育现代化的诉求,我们希望与世界发达国家的教育接轨,希望尽快赶上世界发达国家,实现教育的现代化。在这样一种失去从容的心态下,我们往往不能正确认识世界各国教育的真实情况,而是把几个经济发达国家的教育做法看作教育现代化的象征,将之树为追赶的标杆,称作“世界潮流”。我们不停地喊出与国际接轨的口号,但很少有人追问有轨可接吗?接谁的轨?接得上吗?欧洲的学校不想与美国的学校接轨,美国的学校也不想与欧洲的学校接轨。许多人经常谈论一个观点,学校发展要建立一个国际参照系,把学校发展纳入到国际教育发展的主流轨道。这种观点无疑是居高临下的,但是如果真的这样想,这样做,那么是不切实际的。中国的教育发展有着它自己的主流轨道,它与所谓的国际主流轨道,是两条轨道。任何一条轨道后面都有很深厚的民族特性在支撑着,要脱离正在跑着的轨道,跳到另一个轨道上去,在行驶过程中是办不到的,也是有危险的。我们不断地期盼与国际接轨,进而使自己尽快“普世化”,并没有把中国特色、把我们的话语权认真当一回事,如此下去,我们究竟还要不要中国教育发展的自主性和独立性?
学者冯增俊认为:“教育现代化不是西方化。这是一个最重要的认识:其一,任何国家的教育现代化都不是单纯照搬西方模式的结果,也不是单纯受某一先进国家作用而发生;其三,教育现代化往往引用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作为推进指标,制定相应的标准,但并非是对这些西方教育指标的简单满足和机械套用,因而不可具有统一的标准;其二,后发外生型国家教育现代化需要外力,但却决非为简单的外力推进的产物;其四,后发外生型教育现代化要重视借鉴作用,但并非为国外教育模式的直接移植。一句话,后进国家教育现代化不是直接外生的,不是西方化。亚太许多国家的教育现代化,往往都是在西方作用下启动的,并且借鉴了西方的许多经验和改革成果,但是从没有一次是靠照搬西方模式改革教育而取得成功的。”[2]教育领域里所讲的“普世化”进程,很大程度上是从以美国、日本、英国为代表的地方经验中总结提炼出来的,而那个经验过程不只是高度的组织化和远离自然的过程,同时也包括地方的文化特性。但是在一系列进程中,西方的经验被社会科学概念化、“普世化”了,它们因此竟变得如此顺畅,如此平和,如此理性,如此正确,以至于多少年来,几乎每一次,当遇到这种“普世化”理论与经验相矛盾的时候,我们都没有想到理论可能也会有错;几乎每一次都是认定我们这儿的经验出了问题,都是要不断改变我们的现实来适应“普世化”的理论;几乎每一次我们都没有想起“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这样的老话来。更何况,对于中国具有悠久文化历史长廊和博大人文地理空间的多元社会来说,自己几千年的教育经验就一定是狭隘的,而别人的局部教育经验就必定是“普世化”?这在情理上、法理上说得过去吗?
其实任何一所学校都是具体的、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它所具有的复杂性是其他学校的经验所不能完全涵盖的,也是理论所不能充分验证、诠释的。追风逐浪、大浪淘沙的过程淘尽了校长的思想,淘尽了教师的原创能力,使我们的教育界患了可怕的“失语症”,我们的校长、教师不会说话了,不会说自己的话了,用他人的思考来代替我们自己的思考,用他人的理论来作为我们自己的理论,用他人的实践来代替我们自己的实践,甚或用他人的实践来规定我们的实践,以至于在自己的领域里失去了话语能力,进而失去了话语权。
办学的雷同、话语的雷同,从根本上反映了校长、教师思想力的弱化,思想力的弱化是思想深度缺席的表征。教育家办学无论如何不能缺席思想,这当成为我们的共识。
三、教育家“自说自话”话语方式的实现
现在是学校教育发展模式多样化,教育界的有识之士都在倡导学校要走自主发展的道路,这取决于校长、教师有没有个性化的教育思想,有没有自己的话语方式,教育的现代化应该体现为我们自身主体的个性化。爱默生提醒美国学子,希望他们今后不要成为美国的“德国学者” “英国学者”或“法国学者”,而是要成为立足于美国生活的“美国学者”,他认为“美国人倾听欧洲的时间太长了,以至于美国人往往被看成是缺乏自信的、只会模仿的、俯首帖耳的人”。当前中国教育界也需要有人提醒我们的教师、校长不要成为中国的“美国教师” “英国校长” “德国教师”“法国校长”,不要把自己变成复印机、扫描机,不要让自己的思维只留下一个复印扫描的功能。言必称希腊,而不知中国,不懂中国学校当下的情况,不能用自己的话语阐述自己的教育思想,那是不可能真正成为教育家的。
早在20世纪早期,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十分反对“洋八股”思想,反对以西方的教育传统为根基来分析和解决中国的教育问题。因为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往往是在学习和研究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时,先产生一些问题,形成理论预设,然后再到经验中寻找相关材料来验证这些问题”。[3]这种情况下,本土经验不可能充分而真切地展现出来,中国教育实践的价值仅仅局限于支持西方的教育理论前设,连证伪西方理论的可能性都没有,更不可能反思自身以获得发展,说严重了就是将中国教育经验出卖给西方理论传统。所以,我们只有按照中国自身的教育发展逻辑并运用本土的话语来表达中国的教育,才能使中国的本土经验彰显出来,从而显现出本土教育传统的问题和需要,体现中国教育家的价值。否则,我们所看到的永远只是西方话语下的问题和需要,而不是我们自身的真实需要。
从历史发展进程的角度看,我国校长、教师要成为教育家,在西方的教育理论、课程理论面前应该有三种选择:第一是照着说,第二是接着说,第三是自己说。这里是借用哲学家冯友兰的提法,冯先生认为哲学史家是“照着讲”,比如柏拉图怎么讲,孔子怎么讲,哲学史家把他们介绍给大家。而哲学家就不能满足“照着讲”,他要“接着讲”,即根据时代的需要,有所发展和创新。比如柏拉图讲到哪里,孔子讲到哪里,哲学家要接下去讲。我们这里所谓“照着说”,就是照着西方的课程理论、教育理论说,别人怎么说,我们怎么说,在引进西方教育理论、课程理论的初始阶段当然应该这样,可以称之为搬用阶段。所谓“接着说”,就是按照西方的理论接着往下说,可以说是西方理论的延伸阶段,这是第二步。所谓“自己说”,当然就是第三阶段,总结自己的实践,提炼自己的思想,形成自己的理论。既然校长、教师已经意识到了,那么我们当然要行使自己表达的权力,自说自话,应该按我们的方式表达我们自己的教育传统和需要,表达我们的理解和思想。这种权力如果被抹杀了,那么也就不存在自己说了。因为话语的表达和被倾听是对话和交流的前提,而只有对话和交流才是教育者“自己说”的正常状态。教育者“自己说”应当是一种平等的交流关系,而这种平等就是话语权的平等。郭华认为:对话需要资本,需要自信、自尊,需要相互间的尊重。如果我们的研究只是在用他们的理论解释我们的实践,用他们的话语(而非中国话语、中国气派)重复他们的研究,即使有所谓的对话,也类似于课堂上教师提问而学生复述一般,这样的对话只能是单向的传播,只能是不对等、不对称的交往,而非平等互惠的对话。[4]而没有平等的对话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家。
我们的校长、教师应该深思:怎样由“跟风说话”逐步走向说自己的话;怎样由西语霸权逐步走向建立自己的话语系统、民族的话语系统。任何一个教育家都是在一定的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同时中国教育家的教育探索就应该充分地体现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情怀。因此,笔者认为应该从寻根开始。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根基,真正好的教育是扎根在自己的文化根基上的。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是中华民族的巨大财富和资源。在中国走向现代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我们不能一味地关注西方、崇尚西方,而忽略本国文化优良传统的发掘与弘扬。我们应当在深入研究中华文化中,增强民族的自信心、自尊心。
假如把一所学校比作一株小草的话,我们应该寻找草根,寻找学校文化之根。每一所学校都有自己的历史,但很多学校不珍惜自己的历史,却去搬别人的文化。有的学校有悠久的历史和优秀的文化沉淀,但疏于总结、提炼和升华,去聘请从事企业形象识别的文化公司帮助本校设计文化形象识别系统,或者生搬其他学校的文化建设成果,导致了“文化移植”现象的产生。
在寻根的基础上,还必须觅泉,觅现实生活之泉,觅教育、教学实践之泉——因为这是师生生命之泉。教师、校长不仅处于极为有利的研究位置,而且还拥有最佳的研究机会。教师、校长有能力对自己的教育行动加以反思、研究与改进,由教师、校长来研究改进自己的专业工作乃是最直接最适宜的方式。外来的研究者对实际情境的了解往往不那么深入,因此提出来的研究建议往往无法切入。教师、校长最主要的活动场所是学校、是课堂,从实验研究的角度看,学校、课堂是最佳的教育研究的实验室,教师、校长可以通过一个科学研究过程来系统地解决学校、课堂中遇到的问题。从自然观察的角度看,任何外来研究者都会改变学校、课堂的自然状态,如要想既达到目的,又不改变原有的气氛与状态,就只有依靠教师、校长。教师、校长是最理想的观察者,因为教师、校长本来就置身于学校教学中,他们是掌握观察方法、了解观察意图而又不改变原来学校情境的最佳人选。所以,我们要使自己站在教学研究的最前沿,努力去研究探索,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研究者、教育家。
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自己的教育教学实践和课改实践,从实践中去分析、去提炼、去概括、去抽象。我们常常津津乐道:人是思想的苇草,人是思想的冒险家,我思故我在,以我的思考、我的思想来证明我的存在。我们常常说,校长是思想的播火者,是播撒阳光的人。思想从何而来呢?思想从思考中来。思想的主要来源之一就是自身的不懈思考。校长、教师要学会思考,既要居高临下,又要脚踏实地。我们脚下的土地,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教学,这是工作、创造的根本所在,别忘了我们的初衷。
这次国家课程改革是自上而下的课程改革模式,由理论家们主导一切,使得校长、教师没有多少机会说话。自上而下的改革模式往往要求实践者能够按照决策者、设计者所制定的纲领、计划不折不扣地实施。教师仅仅是受专家们培训的对象,是课程改革的执行者,因而在课程改革决策者和设计者面前必然处于弱势,难以发出自己的声音,理论和实践严重失衡,导致课程改革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教师也应该具有批判精神,敢于否定自己,敢于否定过去已经习惯了的东西,敢于否定权威的理论,这样才可能有所发展,才能形成自己的话语方式。两院院士王选曾经很有感慨地说道:世上有些事情非常可悲和可笑,当他26岁处在研究的最前沿、处于第一个创造高峰时没有人承认,真正是权威的时候不被承认,反而说他在玩弄骗人的数学游戏;当他已经脱离第一线,55岁创造高峰已经过去了,不干什么事情了,已经堕落到了靠卖狗皮膏药为生的时候却说他是权威,1992年开始连续三年每年增加一个院士头衔。他一再告诫青年:千万别把院士看成当前的学术权威。教育家不应再迷信权威和书本,应该坚信,一切现存的文明都是对人类过去经验的总结,他要做的是如何站在前人的肩上向新的高度攀登。教育家不应再迷信自己,不应再把自己的职业角色神化,要敢于批判自己,甚至敢于否定自己。事物在发展,时代在前进,教师、校长不可能穷尽过去和未来,他要做的就是在不断的批判自己中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