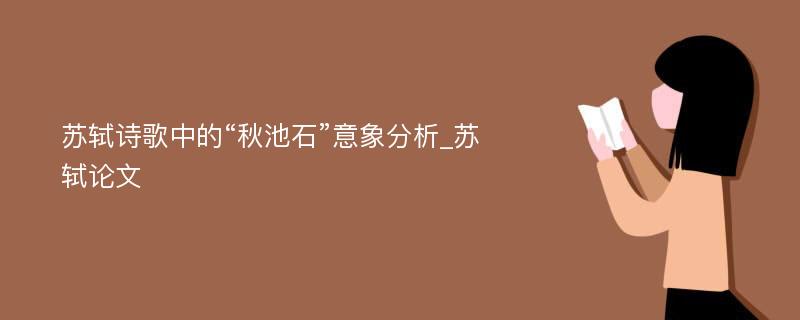
苏轼诗歌的“仇池石”意象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意象论文,苏轼论文,诗歌论文,仇池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①。宋代文化之发达,体现为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两个领域的高度繁荣与和谐相依。徐飚《两宋物质文化引论》,扬之水、孟晖“名物寻微”式系列考证文章,通过对宋代器物艺术的剖析寻微,为我们再现了一个细致精美的物的世界②。以之为基础,古物收藏、文房清玩、名物鉴赏等围绕物所展开的艺术活动亦广泛流行于宋人之间。在这些活动中,物超越原初的实用功能,成为宋人审美活动的对象。 “物的审美”是宋代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关系到如何理解士大夫物质生活与精神层面的互相影响与塑造。诚如艾朗诺在《美的焦虑:北宋士大夫的审美思想与追求》一书中所指出的,宋代士大夫对物的态度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他们既为物的感性之美所动,又需在伦理价值层面上自我辩解,为与儒家传统观念相龃龉的“美的诱惑”作出辩护③。因此,如何理解宋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展现宋人对物的审美方式,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而在以物为对象的诸种审美活动中,诗歌写作是极为重要的一种形式。正是通过文学性的想象与书写,特定物品得以从“物质的艺术品”(Material Artifact)转化为“美学的对象”(Aesthetic Object)——这两个概念指称对象看似相同、内涵却迥异:“前者是物质性的书籍、绘画或者雕塑本身,后者则仅仅存在于人对于这一物理事实的解释之中。”④而诗这一文体所具有的抒情性与想象性特质,又使呈现于这一艺术形式中的“美学的对象”,拥有了异于谱录、笔记、散文等其他文体之记载的独特形态。 与前代之诗相比,宋诗对物的审美赋予又尤具其特殊性。唐诗中常见的抒情意象往往是自然物象等具有普遍象征意义之物,而宋人却较前代远更频繁地将日常生活中真实存在、具有唯一性与特殊性、尚未在诗歌写作传统中形成固定审美联想的物象纳入诗中,这类物象因此而具有“实指性”与“特喻性”⑤的特点。诗人书写的是生活中真实存在的特定之物,并以自我的人生感悟,而非历史传统或文化记忆为其赋予象征意义与情感内涵——这既体现出宋人对物之审美的个性化色彩,也带来诗歌抒情形态在宋代的转变。正是基于“物的审美”问题在宋诗中的特殊形态,对诗歌物象内涵与情感意义的解读,就需结合诗人的具体写作语境与人生经历展开,在文本细读的过程中进行逐层剖析与细致呈现。 本文选择以苏轼诗中的“仇池石”意象为对象,作精细化文本释读。事实上,与“仇池石”相关的诗歌书写已获得不少研究者的关注。杨晓山在《私人领域的变形:唐宋诗歌中的园林与玩好》一书中,通过解读苏轼以仇池石的归属为主题赠予王诜等人的诗作,论述北宋诗人间物的交换关系⑥。艾朗诺《美的焦虑:北宋士大夫的审美思想与追求》在分析苏轼围绕“占有物”的命题展开的哲学之思时,同样给予了这组诗不小的解读篇幅⑦。周裕锴《苏轼的嗜石兴味与宋代文人的审美观念》一文,则从整体上论述苏轼及其所代表的宋人对石的审美观念,其中也涉及仇池石的例子⑧。这些研究皆具见地,论述苏轼思想尤为深刻,从不同角度给人以启示。不过,上述研究又都以探究苏轼思想为旨归,多将诗歌文本用作反映诗人思想的直接材料,不太关注“诗”的文体特性与诗人的写作语境对物之意义的塑造作用。这便为本文的解读留有空间。本文将以苏轼与仇池石相关的三次写作及黄庭坚对苏轼的追忆之诗为考察对象,在对诗的文体特点、游戏性写作语境及诗人经历的具体还原中,细致描述苏轼为仇池石赋予意义的过程,呈现仇池石在苏轼生命中的独特位置。 一 从“双石”到“仇池”:归隐之梦的物质寄托 苏轼对仇池石的最早记录,见于元祐七年所作《双石》一诗。此诗诗序称:“至扬州,获二石。其一,绿色,冈峦迤逦,有穴达于背。其一,正白可鉴。渍以盆水,置几案间。”⑨由“双石”这一诗题可知,此时,这两块石头尚未获得“仇池石”的命名。对苏轼而言,它们并无特殊的意义。“冈峦迤逦”“正白可鉴”是描述外形之美;汲水置盆、将石置于模拟自然山水的人工环境之中,也是苏轼所惯用的一种赏石方式。忽一日,苏轼发现了一个新的角度观看此双石——他记起了元祐六年颍州任上所做的一个奇怪的梦。这一角度的得来非常偶然,甚至有些不合常理,苏轼于诗序中称:“忽忆在颍州日,梦人请住一官府,榜曰仇池。觉而诵杜子美诗曰:万古仇池穴,潜通小有天。乃戏作小诗,为僚友一笑。”⑩“仇池”是山名,在甘肃省成县西。山方百顷,四面斗绝,有东西两门,盘道可登,上有水池,故称“仇池”。梦中苏轼来到一个题写着“仇池”二字的官府,醒后则借杜甫的诗句理解其意义。“万古仇池穴,潜通小有天”两句出自杜甫《秦州杂诗》。“潜通”是暗暗通往的意思;“小有天”在河南省王屋山,为道教三十六洞府之一。杜甫将仇池山上的池穴设想为暗通仙境的秘途,一个能够使人得道成仙、躲避世俗之乱的福地。 换言之,“仇池”二字具有浓厚的象征意味。苏轼之梦因此而值得玩味:本为福地圣山的仇池,为何会以官府的形象出现?这似乎是此梦最为明显的矛盾。不妨做一个简单的“梦的解析”:做此梦时,苏轼为颍州知州。官府是白日生活中的现实场景,意味着苏轼当时的政治身份。仇池则是一处理想之境,可以借此获得心灵的安宁。世俗之所与出世之境不合常理地结合在一个画面中——这是梦境显示内心冲突的特有方式。可以这样理解:避世归隐是苏轼的梦想,仕途责任则是他的现实,这一人生状态的矛盾,亦即出处进退的问题,对传统士大夫而言并不特殊。对此进行调和有多种方式:梦以“超现实”的场景对此进行调和,无如哲学高度上的价值安顿更为长久。然而苏轼“戏作小诗”,以梦为背景观看双石,将“仇池”的名称与象征意义赋予偶然得来的石头,则是一种属于诗人的方式。 《双石》一诗如下: 梦时良是觉时非,汲水埋盆故自痴。但见玉峰横太白,便从乌道绝峨眉。秋风与作烟云意,晓日令涵草木姿。一点空明是何处,老人真欲住仇池。(11) 梦中真切的场景在醒后淡去,苏轼又回到了汲水埋盆、赏玩二石的日常痴举中。然而这一次,“一白”“一绿”两块石头向苏轼呈现了不一样的景象:仿佛梦一般,连绵的群山在他眼前生动地展开。苏轼说自己才见到太白山为积雪所覆盖的巍峨高峰,便借由飞鸟之径来到了峨眉山顶。这是化用李白《蜀道难》“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的句意。苏轼大约是先观白石,再赏绿石,诗句却将这一简单的过程描述为群山间的飞跃穿行,意气超绝又兴致勃勃。接下来的描写则更为细致。苏轼已不再由外观看山的全貌,而是置身山林间的草木云烟之中,甚至借由具体的景物感受到了时间的存在:秋意弥漫山间,秋风时而聚拢云烟,时而吹散它们,增加了风云变幻中的起伏意态。初升的朝阳穿透云层,在林间投下一缕光线,沐浴着阳光的植物显得精神蓬勃,姿态万千。如果说前面的描写还是基于双石的自然形态,颈联两句对“秋风”“晓日”等具体时间的感受则纯然基于想象,诗句中没有了石头的影子,苏轼已经完全“入境”。在此铺垫之下,诗末无端地发问也显得自然。在一片若幻若真的山林之景中,苏轼发现自己找到了一个神秘的洞穴,这让他想到了可以通往神仙居所的仇池穴。于是苏轼自问:这是什么地方?难道是仇池山?我是否真如梦中所见般,已然身处仇池? 留意诗序的读者自然明白,现实中的绿石“有穴达于背”,“一点空明”所指正在于此。双石,尤其是那块身负一洞的绿石,借着与“仇池穴”在形态上的对应,被苏轼想象为仇池山,并由此诗获得了“仇池石”的名字(12)。这一点空灵的想象,是苏轼自称为博“僚友一笑”的游戏之思,却也是诗歌写作超越生活、为物赋予意义的方式。从“双石”玲珑精巧的形色出发,苏轼由之展开联想,在诗中造境。当梦境已逝,欲往仇池而重寻无处时,借由石所展开的游戏性想象,提供了一条现实中的替代之路,让苏轼以诗的方式实现他的仇池之梦。而在一个更大的语境中,“仇池之梦”并不仅指颍州时的具体梦境,这一真实存在的地名已在苏轼诗中带上了个人化的情感色彩,从公共意象转化为个人意象,是象征意义上的“梦”:它不再指代具体的仇池山,而是苏轼心中的告老归隐之地,并在很多时候等同于同样地处西南、青山连绵的蜀地,他的故乡四川。杜甫咏仇池山是即目即景的实写,对这一地方并无特殊的感情。苏轼则不然。他并未去过真正的仇池山,仇池因而是“梦想”。颍州任上的苏轼,人生之路走过大半,经历过乌台诗案后的黄州贬谪、元祐更化时重招回京任翰林学士的荣耀,此时又外任地方官、继续江山间的漂泊,不免易生沧桑感怀,归隐还乡的渴望也愈加强烈。诗中出现了诸如“此生终安归,还轸天下半”(13)的感喟。此时出现的仇池之梦像是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仇池”因而成为苏轼表达归隐之思、还家之梦的象征性词汇:“梦中仇池千仞岩,便欲揽我青霞蟾。且须还家与妇计,我本归路连西南”(14)、“万古仇池穴,归心负雪堂。殷勤竹里梦,犹自数山王”(15)、“东坡信畸人,涉世真散材。仇池有归路,罗浮岂徒来”(16)。在空间和时间的双重意义上,“仇池”都是一个理想化的“他处”(17)。 也正因此,“仇池石”内涵独特,绝非“产自仇池的石头”之意。而其所寓含的象征意义由具体的诗歌文本所塑造,离开了这一文学语境,物之上的寓意便极易流失。南宋杜绾所作《云林石谱》释“仇池石”称:“韶州之东南七八十里,地名仇池,土中产小石,峰峦岩窦甚奇巧,石色清润,扣之有声,颇与清溪品目相类。”(18)苏轼之仇池石确实是由程德孺携自广东(19),然而此处将仇池理解为韶州附近的地名,却完全有违地理实情。后世记载将石的命名纪实化时所产生的误解,显露出一种将诗的虚构性想象合理化的倾向。“仇池”内涵的“特喻性”却也随之流失。有趣的是,苏轼自觉到诗中的想象是假想的“虚辞”,在诗序中称“戏作小诗”,“为僚友一笑”。“仇池”寓意与石的结合,到底是偶然和虚拟的,诗句在“老人真欲住仇池”这一假设性的表述中戛然而止。假若以清醒的现实为观照,“汲水埋盆”的举动是“痴”,“真欲住仇池”的可能性也值得怀疑。然而,假若众位“僚友”代表了外在眼光清醒的审视,在苏轼自称为“戏作”的诗歌空间中,虚构却是合法而自足的。正是在此间,诗人能借微物而咏神奇,在一块石头上实现山水、四季、故乡和梦境之寄寓。 二 “仇池石之争”与“诗战”:以物为媒介的精神交游 《双石》一诗使两块形色优美的石头超越了单纯的“娱目”功能,具有了“娱心”的意义。而在不久之后的一场事件中,“仇池石”则跃然成为苏轼及其诗友唱酬的焦点,甚至引发了一场所谓的“仇池石之争”。 元祐七年九月,苏轼被召还朝,进官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通过此时其与汴京僚友的唱酬之作可知,一次,苏轼的旧友驸马王诜(字晋卿)欲借仇池石为观,苏轼认为这一行为“意在于夺”,便写诗与之周旋(《仆所藏仇池石,希代之宝也,王晋卿以小诗借观,意在于夺,仆不敢不借,然以此诗先之》)。这组唱和引发了钱勰(字穆父)、王钦臣(字仲至)、蒋之奇(字颖叔)的关注,他们纷纷次韵为诗(已佚),表达对是否应借石于王诜的不同意见。苏轼再次前韵,一并回应了他们,认为若欲借石,王诜需以两幅韩幹马相交换(《王晋卿示诗,欲夺海石,钱穆父、王仲至、蒋颖叔皆次韵。穆、至二公以为不可许,独颖叔不然。今日颖叔见访,亲睹此石之妙,遂悔前语。仆以为晋卿岂可终闭不予者,若能以韩幹二散马易之者,盖可许也。复次前韵》)。王诜没有同意这一提议,为了解决这一矛盾,苏轼和朋友们另有主意,有的欲画、石兼得,有的建议二者并弃,苏轼再次作诗,认为石与画皆是身外之物,对此都不可执着(《轼欲以石易画,晋卿难之,穆父欲兼取二物,颖叔欲焚画碎石,乃复次前韵,并解二诗之意》),最终化解了这场“争执”(20)。 围绕此事件留下的三首诗因其中所体现的物的交换关系、苏轼对占有“外物”的矛盾态度而为杨晓山、艾朗诺等研究者所关注。曾声称“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21)的苏轼,在这场事件中却表现出了对石的留恋与不舍,实际行为与其思想观念似乎有所矛盾。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组诗完成于与友人交游、唱酬的语境之中。若将苏轼好玩笑、“多雅谑”的性格特点及其酬人之诗中常见的“戏赠”态度考量在内(22),我们对“仇池石之争”或许会有不一样的认识。从第一首诗的诗题“仆所藏仇池石,希代之宝也,王晋卿以小诗借观,意在于夺,仆不敢不借,然以此诗先之”的表述开始,苏轼没有明言,但叙述中的戏剧化口吻却非常明显。比对《双石》一诗可知,以“希代之宝”形容仇池石显然是夸张之语。王诜之诗如今已佚,未知内容为何。苏轼对其进行“意在于夺”的推测,或许确实有现实的根据(23),只不过,以“夺”释“借”,仍带有对朋友用意的戏谑性揣度,是故作严肃之词。可与之参照的是,苏轼题跋中有《记夺鲁直墨》一则小文,亦以“夺”形容自己的取墨行径。有趣的是,这则题跋本身便是用所取之墨写就,苏轼文中称“遂夺之,此墨是也”(24)——语气洋洋自得而颇见其乐。这里的“夺”绝非指真正的抢取,而是对友人间日常交往行为的戏谑化描述,亦是苏、黄二人亲密友谊的体现。此处,苏轼再次使用“夺”字描述王诜的行为,也带有同样的戏谑意味。而从第二首诗开始,钱勰等人参与了唱和,各持己见,众声喧哗。苏轼欲“以画易石”、钱勰欲“兼取二物”、蒋之奇建议“焚画碎石”,这些提议并不能轻易付诸现实行为,更似于观点的争锋和对话——几位诗人欲从观念上穷尽解决这一问题的不同可能。而在诗中表达“异见”、故意形成争端,这同样也是常见于宋诗中的诗人戏谑方式(25)。并不总是正襟危坐的严肃思辨,体现在“诗”这一文体中的说理方式具有很强的灵活性。戏剧性、想象性、游戏性的说辞,皆能为诗人用作理直气壮的辩护逻辑。 在第一首诗中,苏轼试图这样说服王诜:“老人生如寄,茅舍久未卜。一夫幸可致,千里常相逐。风流贵公子,窜谪武当谷。见山应已厌,何事夺所欲。”苏轼提及自己漂泊的一生,年岁已老却仍无处可归依。而王诜曾因在乌台诗案中受牵连而贬谪于湖北均州,在那里饱览了武当的山川秀景。苏轼劝说已有过如此经历的王诜不必再抢夺这块石头,因为他曾历览过真实的山川,已经感受过那种精神的满足。而在第二首诗中,笔下变化多端的苏轼又换了一个论说的角度,他称: 相如有家山,缥缈在眉绿。谁云千里远,寄此一颦足。平生锦绣肠,早岁藜苋腹。从教四壁空,未遣两峰蹙。吾今况衰病,义不忘樵牧。逝将仇池石,归溯岷山渎。守子不贪宝,完我无瑕玉。 苏轼以“相如”喻王诜,又借用《西京杂记》中“卓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之典,称其家中已有一山,就在所爱女子姣好的眉目间(26)。诗称这一女子随着王诜经历过富贵生涯与贬谪时期的贫困岁月,但即使家徒四壁,也从未“蹙眉”、流露过忧伤不满之意。又说自己已然年老,想着归隐之事,欲将仇池石带回四川边境泯山边的小溪中。“守子不贪宝,完我无暇玉”一句,是对上述对比关系的总结,化用了“子罕辞玉”的典故(27),苏轼劝说王诜不妨以“不贪”的品德、而非具体的石头为宝贝。然而这句诗也可从字面意思上理解为:请王诜守护好家中不需贪图别人便已获得的宝贝,也就是他所爱的女子;而使苏轼能拥有他所珍贵的石头,即仇池石。在《双石》一诗里,苏轼在普通的石头中看到了他的家乡之山。此处,借着诗意化的想象,苏轼不断提醒王诜他生命中所拥有过的山。除了武当真实的山峰之外,苏轼甚至还为王诜找到了更为美丽、持久、值得守护的山色。 在第三首诗中,苏轼援引了大量佛经典故,称“明镜既无台,净瓶何用蹙”“焚宝真爱宝,碎玉未忘玉”,意图从根本上解消众人对物的执念,跳出“拥有”与“放弃拥有”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诗中有“欲观转物妙”之句,正可用以描述上述几首诗中的论辩逻辑。与受物所役、迷己于物、为物所转的被动状态不同,苏轼不断转化观物的角度,为王诜寻找“仇池石”的替代品。至于具体的物是武当还是“家山”并不要紧,关键在于观赏者能够自足于其中、获得精神满足的观照方式,以及将外物化为己用的态度。在这首诗中,苏轼称“盆山不可隐,画马无由牧”,道明就其物质形态的本质而言,仇池石不过是“盆山”,并无玄妙之处,正如韩幹的马也只是画家的创作而已。这一次,苏轼开解王诜的方式是在现实世界中寻找“真实”的解脱:“三峨吾乡里,万马君部曲。卧云行归休,破贼见神速。”然而苏轼是真的要告老回乡,并劝王诜领兵沙场么?并不一定。这仍是一种说辞,一种可能性的假设,一种用语言和思维“转物”的方式。 苏轼三首诗中包含的对话性如今已无法还原,而随时间一道散落的还有真正的历史。值得追问的是:在现实世界里,是否真的存在一场关于仇池石的“争夺”之战?王诜对“借石”之意的表达、苏轼对王诜之意的理解和回应、旁观之人对此进行的开解与议论,皆由苏轼之诗知晓于后人。然而苏轼借物而为的凿凿之语,并非对现实生活的严肃记录,更像是变化百端的精神游戏。其中既包含精妙的智慧,也不乏艺术性的想象与游戏性的说辞。 如果考虑到“仇池石之争”中的游戏成分,那么仅以这三首诗为依据,解读苏轼对仇池石的态度或苏轼和王诜之间的关系,这一方法便值得推敲。如此解诗的前提是将这三首诗视作苏轼严肃的言志之作,将句意直接等同于诗人的思想和心理。然而若以此逐句探求,便可能引起解释上的困境,带来对苏轼心理的猜测性描述,或使诗中反映的诗人形象显得很不统一(28)。考虑到诗人写作语气的游戏性色彩,句意与诗人形象间便不能过于简单地画上等号。然而,对诗人写作态度中游戏性成分的强调,并非为了消解,而是为了补充对苏轼思想的完整认识。观物角度的多变、虚构性想象的丰富、戏谑姿态与严肃说理的并存,这些特点正是苏轼独特智慧的体现。在这三首诗中,仇池石时而被称为“希代之宝”,时而是“海石”(29),时而仅仅是“盆山”,苏轼不断玩味意义与现实之物的不同结合的可能性。真正让诗人乐在其中的并非对物的实质性占有,而是写作过程中与不同人的思维、才智的碰撞和对话。 在这场事件中,表面上看是众人争夺中心的“仇池石”,其实始终“无动于衷”,并未真正离开苏轼的居所。它是引发写作的开始,却绝非最终的落点。这场以互赠诗歌、借诗说理的方式进行的“争夺”更近似于一场“诗战”(30),是智慧的交锋与情感的对话。作为物的仇池石并非众人现实欲望的对象,而是引发诗歌议论的话题与承载精神交游的物质媒介。 三 变化命运中的情感落点:作为抒情意象的仇池石 “仇池”意象再次见于诗中已近苏轼晚年,与其因政治之难南迁、继而北归的人生经历相关,并伴随着苏轼对另一块石头“壶中九华”的题咏。对命运的感受与对石的描写相交织,“仇池”意象的抒情意义在命运的动荡中得到了凸显与深化。 绍圣元年,哲宗起用章悖为相,开始“绍述”之政。苏轼再遭弹劾,落两职、追一官,责知英州。贬窜途中,三改谪命,最终以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的身份远赴广东。在通往岭外的路上,苏轼路经湖口(今江西九江),看中了李正臣所藏一座形似九峰的异石:“湖口人李正臣蓄异石九峰,玲珑宛转,若窗棂然。予欲以百金买之,与仇池石为偶,方南迁未暇也。名之曰壶中九华,且以诗纪之。”(31)九华山实有其所,在安徽青阳。苏轼以石形近似,便以“壶中九华”名之,心有所好却未及购买。绍圣四年,苏轼再遭追贬,责授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赴海南贬所。而在苏轼已准备终老海南之际,元符三年,哲宗去世,徽宗继位,重用元祐旧党,苏轼由海外招归。建中靖国元年,历经世事之变、已近人生之暮的苏轼重过湖口,发现壶中九华石已被他人取去,便又作诗一首,“和前韵以自解”(32),此时据上一首诗的写作已过八年,两首同韵之诗互为对话,记录了苏轼发现壶中九华石的惊喜与失去此石的遗憾。而在与“消失”的壶中九华石的对比中,八年来陪伴苏轼几番渡海、经历命运之变的仇池石显得温暖而恒久,如同情味深长的朋友。 “壶中九华石”是两首诗正面书写的对象。与《双石》一诗类似,苏轼借石展开了对山的联想。所不同的是,这一次的联想与现实尤为切近——不再是遥远的梦境与故乡,而是南迁途中的真实所历:“清溪电转失云峰,梦里犹惊翠扫空。五岭莫愁千嶂外,九华今在一壶中。”此行一路山高水急,群翠过眼,连绵山峦让人目不暇接,亦让人感到行旅奔途不由人控。千山五岭之外的南方是行途的终点,遥远而陌生;九华之峰作为中原秀丽之景的象征与此行的追忆,或可于石中获得,作为迁谪之人的慰藉。对苏轼而言,秀美的壶中九华石犹如贬谪途中“此生归路愈茫然,无数青山水拍天”(33)之景象的缩影,羁旅漂泊、行程不定之“惊”,远途迷茫、难以把握之“愁”,皆化解于壶中九华石所带来的惊喜之中。 大约正是因为与“壶中九华石”的相遇发生于特殊的人生状态之中,此石所激起的情感意义有异于常;八年后,得知此石已被“好事者取去”的苏轼,在诗中用了一个精彩的多层比喻,将失去此石的遗憾描绘得荡气回肠:“江边阵马走千峰,问询方知冀北空。尤物已随清梦断,真形犹在画图中。”苏轼以千峰之失形容壶中九华石的被取,山的消失,又在同一个句子中被形容为有如群马过江,不仅形象丰足,而且呈现为一个持续的、阵阵相继的过程,仿佛能见到众马之群像,亦可听闻喧嚣不止的马蹄声。正如宇文所安所指出的:“在从前的一首诗里,苏轼曾经有效地运用过这一奇异的比喻:‘船上看山如走马,倏忽过去数百群’。”(34)以奔马比喻山势是苏轼诗中的常见修辞(35)。此处,苏轼以“江边阵马”之意象所形容者却非真实的山峰,而是“石被人取走”这一过程,尤以本体与喻体间的巨大差异而显出诗人的情感强度。在第二句中,苏轼继续发挥了这一联想,用了伯乐过冀北而马空的典故,以“冀北空”描述群马过江后的景象。在伯乐相马的故事中,良马是贤士的隐喻。此处,巧妙嵌套了这一典故的苏轼,将其对壶中九华石的相知、欣赏与尊重放置于隐晦的修辞中,慨叹与此“士”失之交臂的遗憾。而无论“阵马”“千峰”还是“冀北空”,苏轼将情感上的失落具象化为饱满的形象与辽阔的空间景象来呈现,仿佛失去的并非一块石头,而是人生版图中的半壁经历。 方勺曾在《泊宅编》中质疑苏轼对壶中九华的审美:“(壶中九华)予不及见之,但尝询正臣所刻碑本,虽九峰排列如鹰齿,不甚崷崪,而石腰有白脉,若束以丝带,此石之病。不知坡何酷爱之如此,欲买之百金?岂好事之过乎?”(36)然而,石的外在形态未必是苏轼对之留恋不绝的真正原因。方勺又称:“予恐词人笔力有余,多借假物象以发文思”,或许更近实情。壶中九华石是触动诗人文情的引子,而“仇池石”便在这样的语境中再次出现。苏轼在诗题中提到,以“百金”购买“壶中九华石”的目的是欲“与仇池石为偶”,“百金”之数与诗人对仇池石的感情构成了平衡,或为虚指,却显出仇池石的分量。诗中虽以“天池水落层层见,玉女窗虚处处通”的玲珑形制形容壶中九华形态之美,但“念我仇池太孤绝,百金归买碧玲珑”才是诗人留恋此石更为深刻的情感之因:欲买壶中九华石是因为念及仇池石太过孤独,需要陪伴——在这推己及物的一“念”中,仇池石被人性化了。这一“念”,也是苏轼自我情感的流露。“一白”“一绿”两块石头,本可互相为伴,未必真正孤独。某种意义上,此处的“仇池”意象指代的是苏轼自己——那将要在未来的人生中太过孤绝之人。借仇池石而为的感发,是对自我命运的抒怀。 八年后,得知壶中九华已失,苏轼的感怀再次落到了自我身上,在诗中说:“归来晚岁同元亮,却扫何人伴敬通。赖有铜盆修石供,仇池玉色自琮珑。”暮年的苏轼回视自我,以隐居避世的陶潜、冯衍自比。在闭门谢客、隐居辞世的生涯中,将有谁来作伴呢?苏轼再次将目光落在了仇池石上。失去了陪伴的仇池石与没有客人作访的老人无言相伴着彼此。诗中的仇池石与初次出现时一样,被“汲水埋盆”以安置,“玉色”依然“琮珑”。苏轼在仇池石的恒定之态中找到了情感的依慰。这一长久而真实的情意,铺成了这两首诗温暖的底色。与此同时,这一意象与“归来晚岁”的诗人苏轼之间构成了一种微妙的象征关系。“玉色自琮珑”的仇池石,其玉洁冰清的本性并未随时间与经历而改变,也并不依赖于它物的认可。晚年由海南召回的苏轼,曾以类似比喻描述由政治之辱中平反的自己:“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37)在身不由己的政治处境中,不曾改变的是诗人高洁的本性与自守的精神坚持。同时出现在这两首诗中的“仇池”意象,与两首诗的主题——“变化”构成了角力,以其稳定之态成为诗人情感的落点,象征着那在动荡人生中支撑生命的恒久不变的精神之力。 在许多文章中,苏轼屡次强调对物的超然姿态,批评对物的“占有”之欲;然而在诗歌写作中,抒情的诗句替代了抽象的哲理,苏轼可以非常自然地流露对物的依恋和感情。“仇池”意象的抒情性,与其作为苏轼生活中的“现实物象”、和诗人相伴多年的特殊性质密不可分。历经光阴镀染的“仇池石”久而有情,正是这层私人的情感联系,使之成为苏轼动荡人生中真实的慰藉。 四 回声:黄庭坚追忆苏轼之作中的物、诗、人 在苏轼饱含情感的观照下,仇池石不再是普通的石头,也不仅是外形优美的艺术品,甚至也不完全是抽象的象征,苏轼赋予了它人性化的情感和生命。 真实的生命却总有消逝的时候。建中靖国元年,苏轼离世。之后一年,黄庭坚路过湖口,在壶中九华石曾经的主人李正臣处看到了苏轼旧作。重遇旧时情、事,“感叹不足”的黄庭坚次韵一首,既是对苏轼原作的回应,也是对师友的深情怀念。在某种意义上,这首诗也可看做为苏轼和仇池石的故事所写下的句号: 有人夜半持山去,顿觉浮岚暖翠空。试问安排华屋处,何如零落乱云中。能回赵璧人安在?已入南柯梦不通。赖有霜钟难席卷,袖椎来听响玲珑。(38) 这是一首精心巧构的诗。诗句表面的意义和深层的抒情之间相互交织,构成了多层次的回声。就其最浅显的意义而言,此诗是在回应壶中九华石被人取去之事:沿用了苏轼惯用的想象,石在此处依旧被比喻为山。黄庭坚称这座山在静夜里被偷偷取走,让人觉得眼前空空若失。三四句借反问而议论:对石的命运而言,被安置在华丽的堂屋里,哪里比得上“零落”于自然的状态中有幸。五六句感慨那个能“完璧归赵”的诗人苏轼已经不见了,石头因而再也没有机会被取回。尾联是对全诗所问的回答:好在还有湖口附近的石钟山是无法被带走的,无妨以衣袖携铁椎来敲击,听它发出如石钟般清脆的响声。在这里,黄庭坚欲用石钟山长久的存在,告慰苏轼壶中九华石被取走的遗憾。 无法忽视的是,被取走的石头,同时也是生命消逝的隐喻。石头的命运与苏轼的命运互相言说,黄庭坚巧妙地使纪实成为象征。而这一隐喻能够实现,与典故的作用密不可分。诗歌首句是对《庄子·大宗师》之名句的化用:“藏舟于壑,藏山于泽,谓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负之而走,昧者不知也。”在《庄子》的文本中,能够负山而去的夜半有力者是运运不息、创造生与带来死的大化,正是这同一种力量带走了苏轼的生命。值得注意的是此句的修辞。苏轼形容壶中九华石被取走,用了“江边阵马走千峰”这一极具画面感的比喻。黄诗中的戏剧感则体现在对动词的精心安排上,细微却令人深味。与《庄子》中有力者“负”之而走的表述不同,黄诗用了“持”山的表述方式。轻巧的“持”与沉重的“山”之间并不协调的搭配,显出所谓的“山”只是一个虚假的修辞。或者不如说,对一个更强大的力量而言,世间所有看似坚固、恒定的存在,都只是虚假的修辞。死亡的无奈与必然便皆由这一个字而出。颔联则是对曹植“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之句的化用,同样是在比喻死亡。颈联“能回赵璧人安在?已入南柯梦不通”两句,则在工整的流水对形式下,以自问自答的语气道出无限的追怀和感伤。黄庭坚将苏轼的死亡比喻为一场他人无法进入的梦。“梦”是介于生与死、现实与虚幻之间的一种状态,以此形容苏轼的离世,恍如留有一丝生存的气息。然而“南柯一梦”是可醒的,在此比照之下,死亡却显得难以挽回,无从追步,令人慨叹不已。末句的石钟山之响,不仅是对壶中九华石的回应,也是黄庭坚对苏轼的致敬和追念——以一种看似轻巧的,与死亡之沉重并不相称的方式。 以石钟山的永恒回应壶中九华石的消失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袖椎敲击,倾听石钟山的回响,却是一个看似无意义的行为。这个贸然出现的结尾,似乎消解了此诗前半部分对死亡的深沉追问。然而这一“玲珑”之响,是曾经的“生”的回声,它本身便构成了与死亡的对话。作为一首追忆亡者之诗,此诗抒情表现上的丰富,不仅体现在“壶中九华石”与苏轼命运的对照书写上;更为令人动容的,恰是诗中一些看似无意义的“回声”式存在。例如,“能回赵璧”一句,并非对“完璧归赵”之典的简单运用。苏轼为“保护”仇池石而写给王诜的诗中便已用过类似比喻:“欲留嗟赵弱,宁许负秦曲。”苏轼以赵国自喻,用秦、赵争夺和氏璧的故事隐喻仇池石的归属。故而此句不仅是用典,也是苏轼往日诗句的“回声”,借此唤醒有关“仇池石”故事的整体记忆:包括苏轼和朋友间日常相交的友情、流露于其中的机智和幽默以及所有那些精心而为的诗作。与之类似地,黄诗在末句提及石钟山,并不仅仅因为它坐落于湖口附近,是切合时、境的实写,其同时也是对苏轼《石钟山记》一文的回应。在那一篇著名的文章中,苏轼好奇于石钟山之得名,嘲笑唐人李渤验证“石钟”之名的笨拙方式:“得双石于潭上,扣而聆之”“陋者乃以斧斤考击而求之,自以为得其实”(39)。在诗中欲“袖锥”以敲击、听石钟山之鸣响的黄庭坚,正是将自己化作了苏轼文中的人物、化作苏轼以其智慧所嘲笑的对象。在此“回声”之中,《石钟山记》这一文本重又鲜活,苏轼的嘲笑之声宛然如新。 黄诗的写法并非长歌当哭的抒情,而是通过对过往生命片段的激活,而使死亡如同虚设。过往的生命片段以文本为形式保存,对它们的征引与呼应取代了直诉式的情感表现,非常有效地传递着黄庭坚式的深情:在对情感的刻意节制中营造出深邃的追思。然而对生命之消逝举重若轻的表达,丝毫没有削弱其中蕴含的情感力量,因为这一略显轻巧、隐含幽默的写作语气是对苏轼的致敬:面对那个以机智的诗思保护仇池石、用勇敢的冒险探求石钟山的命名、为壶中九华石被取走而喟叹不已的苏轼,面对这样一个活泼、生动、丰富的人格,不该以悲伤的方式哀悼他的逝去。然而幽默所反映的生的活泼,却最为有力地映衬出死亡的漫长。在死亡的背景下,一切当时不知其意义的片段,都因代表着生之生动而熠熠生辉。黄庭坚的这首诗如同万花筒的透视镜般,将彩色的碎片幻化为美丽的图像,却又时时提醒我们它们碎片的本质。苏轼与“仇池石”相关的故事便是这些碎片中的一块,组成了回忆之诗令人动容的抒情图景。 “梦时觉是醒时非”的苏轼,最终进入一个更为长久的梦境之中。在“梦不通”的时候,与曾试图重往仇池之梦的苏轼一样,黄庭坚选择以作诗为方式,将物与人的生命象征化、抒情化、诗意化,使它们成为梦的某种见证。写诗是现实中做梦的方式。 在《双石》一诗里,苏轼赋予石头以“仇池”的象征意义;而在后人的追忆中,物的象征意义即是苏轼曲折而斑斓的一生。故人的情貌与哀思,戏笑及智慧,他的整个生命世界的鲜活与丰富,以物的故事为方式诉说。凡物易朽而文字长存。作为实物的“双石”早已不知所踪,而苏轼与仇池石相关的诗作却留了下来,成为后人“潜通”古人心中“小有天”的“一点空灵”(40)。 凭借对“仇池石”相关诗作的细致阅读,我们得以探知苏轼如何通过想象性、游戏性及抒情性的诗歌书写,使物与归隐之思、交游故事以及变化命运中的情感相联系,将仇池石从“物质的艺术品”转化为“美学的对象”。这些寄托了个人之“梦”、融会了艺术想象与哲学思考的诗歌书写,体现了诗人对物的个人化观照方式,是一种“寓意于物”的审美实践。与此同时,现实中的独一性特质又使物具有了特殊的抒情性。可以说,诗人用自己的人生经历为物赋予了诗意。 此外,交际语境也是考察宋人与物关系时一个值得重视的因素。这意味着,宋人对物的审美活动并非仅为一种单纯的个人行为,而是内嵌于一个广泛的文化网络之中。具体之物所具有的故事性、诗人借物所展开的智慧交锋与情感交流,亦汇成物之意义的一部分。而交际之诗所特有的游戏色彩及其为诗歌句意带来的虚拟因素,亦值得正视。虽具游戏性,然而以相互理解的智慧为基础分享语言与思维的密码,宋人间这一交往方式背后的意义是严肃的。 这类围绕物的审美而展开的诗人故事远非仇池石一例。欧阳修文人集团对“澄心堂纸”“月石砚屏”等物的集体吟咏,苏门文人间以“猩猩毛笔”“高丽松扇”为主题的唱酬等皆是宋代诗歌史上为人津津乐道的佳话。正是伴随着士大夫集体走向政治、文学、艺术等各领域的前台,这些紧密体现了士人生活方式与审美趣味的物品也获得了自己的身份和意义。而物与人之间通过诗歌写作建立的深层关联,使对物的审美及书写成为一种延续文化记忆的方式。因此,对这类意象的发掘,对凝聚其上的艺术、情感与记忆的重现,将对深化认识古典诗歌的“抒情传统”有所助益。 注释: ①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45页。 ②参见徐飚《两宋物质文化引论》(江苏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扬之水《宋代花瓶》(《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年第1期)、《两宋香炉源流》(《中国典籍与文化》2004年第1期)、《奢华之色——宋元明金银器研究》(中华书局2011年版)等文章或著作,以及孟晖《花间十六声》(三联书店2006年版)书中收录的《床上屏风》《枕前的山水》《帐中香》等文。 ③[美]艾朗诺著,杜斐然、刘鹏、潘玉涛译《美的焦虑:北宋士大夫的审美思想与追求》,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 ④[捷]穆卡洛夫斯基《作为种种社会事实的美学功能、标准和价值》,转引自[英]特雷·伊格尔顿著,伍晓明译《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7页。 ⑤侯体健在《刘克庄的文学世界——晚宋文学生态的一种考察》一书中提到,刘克庄诗中的“荔枝”意象具有“实指性”与“特喻性”的特点。“实指性”意谓这是指向当下生活世界中的具体物象,是“现实意象”而非“历史意象”;“特喻性”意指这一意象对诗人而言有着特别的意蕴,与其传统意义不同。如“荔枝”在刘克庄诗中便“多隐逸之趣而少放逐之悲”,对应于诗人“心灵深处的、具有象征意义的莆田”。参见侯体健《刘克庄的文学世界——晚宋文学生态的一种考察》,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4-57页。 ⑥参见[美]杨晓山著,文韬译《私人领域的变形:唐宋诗歌中的园林与玩好》第四章“言辞与实物:诗歌的交换和描写交换的诗歌”第四节“三首诗、两块石头、一幅画”,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⑦参见《美的焦虑:北宋士大夫的审美思想与追求》第四章“苏轼、王诜、米芾的艺术品收藏及其困扰”。 ⑧参见周裕锴《苏轼的嗜石兴味与宋代文人的审美观念》,《社会科学研究》2005年第1期。 ⑨《双石》(并序),苏轼著,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卷三五,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6册,第1880页。 ⑩见《双石》诗序,《苏轼诗集》,第1880页。除这一记录外,苏轼对其“仇池”之梦还有一个更为详细的描述版本,如下:“予在颍州,梦至一官府,人物与俗间无异,而山川清远,有足乐者。顾视堂上,榜日仇池。觉而念之,仇池武都氐故地,杨难当所保,余何为居之。明日,以问客。客有赵令畴德麟者,曰:‘公何问此,此乃福地,小有洞天之附庸也。杜子美盖云:‘万古仇池穴,潜通小有天。’他日工部侍郎王钦臣仲至谓余曰:‘吾尝奉使过仇池,有九十九泉,万山环之,可以避世,如桃源也。’”参见《和陶桃花源》(并引),《苏轼诗集》卷四〇,第7册,第2197页。 (11)《双石》,《苏轼诗集》卷三五,第6册,第1880-1881页。 (12)在之后的诗作中,苏轼便自称“予有仇池石,希代之宝也”,坐实了“仇池石”的名字,而在晚年的诗作中更是直接以“仇池”称呼此石。详见后文。 (13)《上巳日,与二子迨、过游涂山、荆山,记所见》,《苏轼诗集》卷三五,第6册,第1865页。 (14)《次韵晁无咎学士相迎》,《苏轼诗集》卷三五,第6册,第1870页。 (15)《过杷赠马梦得》,《苏轼诗集》卷三七,第6册,第2028页。 (16)《和陶〈读山海经〉》(其十三),《苏轼诗集》卷三九,第7册,第2136页。 (17)后人将苏轼的笔记命名为“仇池笔记”,亦可见出“仇池”意义对苏轼而言的特殊性。 (18)杜绾《云林石谱》,《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页。 (19)参见苏轼《仆所藏仇池石,希代之宝也,王晋卿以小诗借观,意在于夺,仆不敢不借,然以此诗先之》一诗自注,《苏轼诗集》卷三六,第6册,第1941页。 (20)《苏轼诗集》卷三六,第6册,第1940-1948页。 (21)《宝绘堂记》,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一一,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册,第356页。 (22)苏诗中极多戏谑之作,且多发生于交游背景之下。旧题南宋王十朋编《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一书即列有专门的“戏赠”一目,录诗32首。参见《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卷一五,中华再造善本据国家图书馆藏宋建安黄善夫家塾刻本影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 (23)艾朗诺指出,米芾的《画史》提到过王诜借人之画而不还之事。参见《美的焦虑:北宋士大夫的审美思想与追求》,第224页。 (24)《苏轼文集》卷七〇,第5册,第2226页。 (25)例如欧阳修《戏答圣俞持烛之句》一诗,开篇即称“辱君赠我言虽厚,听我酬君意不同”。参见欧阳修著,洪本健校笺《欧阳修诗文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上册,第383页。 (26)杨晓山书中认为“相如”是苏轼的自指,“文君”则指仇池石,认为“仇池石之于苏轼,如同卓文君之于司马相如”,这一理解似可商榷。使人疑惑的地方在于:将石比喻为自己的妻子,进行女性化的想象,既不符合苏轼对“仇池石”的态度,在苏轼诗中也找不到类似例子。且苏轼与仇池石相伴只一年,“平生锦绣肠,早岁藜苋腹。从教四壁空,未遣两峰蹙”的追忆亦无从谈起。杨晓山自己也提到了这一理解的不圆满处:“然而,苏轼把自己与仇池石的关系说成夫妻关系,这个暗喻马上就显得不那么恰如其分了。因为,苏轼的仇池石在被女性化以后,其化身更像是一名姬妾,而非妻子。”(《私人领域的变形:唐宋诗歌中的园林与玩好》,第160页)。鉴于此,本文倾向于将“相如”理解为对王诜的代指。诗人起首先述王诜经历,“吾今况衰病”后再述自己与仇池石的关系,这样较为符合苏轼以诗辩争的对话语境及写作目的。 (27)出自《左传·襄公十五年》所记:“宋人或得玉,献诸子罕。子罕弗受。献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为宝也,故敢献之。’子罕曰:‘我以不贪为宝,尔以玉为宝。若以与我,皆丧宝也。不若人有其宝。’”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册,第1024页。 (28)杨晓山书中留下了一些未解的疑问。除了上面提及的将仇池石比作卓文君的不恰当之外,还有如:“苏轼和王诜的争论却是双方欲望的直接冲突。有些令人不解的是,苏轼的欲望之所以合情合理,是因为他只拥有两座盆景小山。曾几何时,王诜却可以把武当群山一览无遗,拥为己有。……难道苏轼是在调侃王诜,警告他说,二人之间再进行礼物交换可能会有风险?”(《私人领域的变形:唐宋诗歌中的园林与玩好》,第158页)此外,杨书中还有一些对苏轼心理的推测性描述如:“我们不禁要猜测,苏轼在提出以石换画的时候,是不是对自己十几年前遭受的政治迫害仍然耿耿于怀?”(第161页)又如:“在三首诗中的第一首里,苏轼把石头描绘成他极度喜爱的东西。那时,他表现出一个收藏家的典型心态。……在第二首诗里,苏轼这个占有欲很强的收藏家变得通情达理。……在第三首诗里,苏轼这个精明强干的艺术品商戴上了诗人哲学家的面具,俨然一副超然洒脱的模样。”(第164页)据笔者看来,杨书似乎太过严肃地理解了苏轼的写作态度,将诗句与诗人心理直接对应,忽略了诗人写作语气的游戏性成分与诗歌艺术的虚构性特征,其结论之有效性颇堪质疑。 (29)“海石”之称见这组诗中第二首诗的诗题。王文诰释此曰:“此不云仇池石,而云海石者,又以盆水为海也”,并指出“石无定名”的特点。参见《苏轼诗集》卷三六,第6册,第1945页。 (30)对宋人“诗战”的论述,参见周裕锴《以战喻诗:略论宋诗中的“诗战”之喻及其创作心理》,《文学遗产》2012年第3期。 (31)《壶中九华诗》(并引),《苏轼诗集》卷三八,第6册,第2047-2048页。 (32)《予昔作〈壶中九华〉诗,其后八年,复过湖口,则石已为好事者取去,乃和前韵以自解云》,《苏轼诗集》卷四五,第7册,第2454页。 (33)《慈湖夹阻风五首》,《苏轼诗集》卷三七,第6册,第2034页。 (34)《只是一首诗》,[美]宇文所安著,田晓菲译《他山的石头记:字文所安自选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0页。 (35)诸如《游径山》诗中“众峰来自天目山,势若骏马奔平川。中途勒破千里足,金鞭玉镫相回旋”(《苏轼诗集》卷七,第2册,第347页)等句。 (36)方勺《泊宅编》卷中,《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87页。 (37)《六月二十日夜渡海》,《苏轼诗集》卷四三,第7册,第2366页。 (38)《湖口人李正臣蓄异石九峰东坡先生名日壶中九华并为作诗后八年自海外归过湖口石已为好事者所取乃和前篇以为笑实建中靖国元年四月十六日明年当崇宁之元五月二十日庭坚系舟湖口李正臣持此诗来石既不可复见东坡亦下世矣感叹不足因次前韵》,黄庭坚著,任渊、史容、史季温注《山谷诗集注》卷一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上册,第411页。对这首诗,宇文所安《只是一首诗》一文有专门的讨论,田晓菲《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版)书中“得失之间”一章亦有所涉及,皆可参看。 (39)《石钟山记》,《苏轼文集》卷一一,第2册,第370-371页。 (40)南宋人曾协作有《赋赵有异仇池石次沈正卿翰林韵》一诗,诗中有句称:“长公仙去后,兵马遂南牧。尤物落何许,心知委沟渎。何期超世贤,爱石不爱玉。夜半负之走,包裹随窜伏。一朝返窗几,时清端可卜。”(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卷二○四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7册,第23003-23004页)杨晓山与艾朗诺皆据此论及仇池石在现实中的命运:北宋灭亡之后,仇池石曾被弃置沟壑,复又为赵师严发现并收藏。由于缺乏其他材料作为佐证,我们很难确认曾协提及的“仇池石”就是苏轼旧物,这一解释仅可聊备一说。在历史的变迁中,仇池石难脱遗失、消亡的命运,无如见诸文字记载的“仇池”意象经久恒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