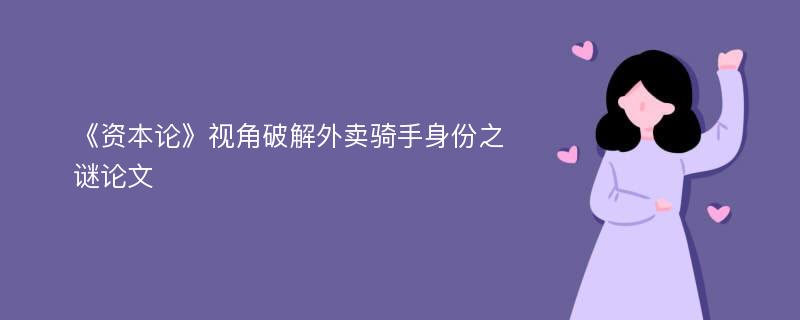
《资本论》视角破解外卖骑手①身份之谜*
周子凡
(武汉工程大学 法商学院,湖北 武汉 430205)
[摘 要] 商品在空间上的流通,使得骑手运输成为追加的生产过程。平台垄断配送业务,骑手的活劳动为其创造新的价值,但骑手雇佣却存在乱象。除与专送骑手建立劳动关系外,平台对外包、众包骑手采用隔离手段,只用工不用人。《资本论》揭示,劳动关系的客体是服从性劳动。因此,人格从属性应为劳动关系认定的核心标准,骑手身份定位应抛开表象看本质。政府应加快平台立法与互联网劳动立法,对弱势骑手施以特殊保护。
[关键词] 骑手;劳动价值;身份定位;规制路径
快捷的移动支付,四通八达的配送网络,精准的定位系统以及快速配对的搜索引擎,迅速催生了一批以美团、饿了么、滴滴外卖等为代表的网络餐饮服务平台。与此同时,与平台相伴而生的一类新型职业——骑手也异军突起。新业态带来新就业,“平台+骑手”新型用工日渐盛行,给现行劳动法律带来颠覆性冲击。骑手游走在法律边缘,无劳动合同,无社会保险,无劳动保障,变成互联网时代的“三无人员”,在权益保护方面成了“隐形人”。
而他采取以学术期刊搭建社会体育指导员交流平台的举措,堪称为走在时代前列;其创办的《体育研究与通讯》期刊中“通讯”栏目,每期都会刊登各县公共体育场工作人员对于社会体育指导等问题的回复,在指导提问者进行社会体育工作的同时,也为其他体育场的社会体育指导员提供了工作问题解决范式。期刊还刊登了大量的体育基本知识、教学教法等文章,无疑也为一线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提供了范式。
“从来治国者,宁不忘渔樵”,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作为底层劳动者,骑手理应受到关注和保护。其身份定位是劳动关系的核心,是劳动权益保障的前提。劳动关系是否和谐事关经济发展与社会安稳,党和国家对其历来高度重视,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进一步强调完善“劳企两利”的劳动关系制度。《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不仅要扶持“新就业形态”,还要“保障非正规就业劳动者权益”。《关于做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则针对当前“痛点”,提出要抓紧完善“用工和社保等制度”。厘定骑手身份,需要剖析错综复杂的劳动问题,就有必要回到劳动价值理论的源头,即《资本论》中去寻找答案。恩格斯指出:“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1]当前,劳资关系仍是我国最基本的社会经济关系,《资本论》所揭示“经济运动规律”同样适用于我国。剔除特殊的资本主义成分,《资本论》有关劳动关系的一般理论仍然能为当下分析骑手用工关系提供有益的理论指导。
研究表明,流域内城镇建设占用了大量耕地,同时存在一定程度的高生态型土地利用类型向低生态型土地利用类型转换的现象,主要表现在林地退化明显,围湖造田、植被破坏等补给耕地。这种显著的土地利用类型转换特征也表明该阶段巢湖流域的土地利用主要服务于城镇化建设。
一、 骑手的劳动价值
骑手是指依托互联网平台提供配送服务的劳动者。其配送服务,从本质上讲,是发生在流通领域的运输劳动,而运输劳动对商品价值的实现极为必要。马克思说:“非占有者”需要“商品使用价值”,[2]餐厅想要获取利润,必然要让渡外卖商品的使用价值,最后才能实现其价值。然而,“物品的使用价值只是在物品的消费中实现”,“凝结”在商品中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必须通过售卖,使商品转化为货币”后,才能得以实现。[3]因此,外卖商品必须要全面转手。但是,外卖商品不会自己挪动位置,自动跳到消费者即需要使用价值的人手中,并且每个消费者也不可能都“恰好生活在他所消费的所有商品的产出地”,“商品在空间上的流通即实际的移动”,需要骑手的劳动介入,因此,“运输成为一种追加的生产过程”。[4]
骑手的配送服务是一种生产性劳动。马克思最初从人与自然关系层面,提出一般生产劳动概念,他说:“实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为生产劳动。”但他同时又指出该定义“对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绝对不够”。随后,他又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层面,提出了特殊生产劳动概念,他指出“工人和劳动产品之间的关系是……社会的、历史的生产关系”,且工人是“生产剩余价值的直接手段”,他认为“只有直接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5]那么,骑手的配送劳动是否生产剩余价值呢?在谈及运输劳动时,马克思“把运输业归类为连接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的桥梁,并把投入运输业的资本叫做生产资本”,[6]他认为,流通领域的运输劳动,与生产领域中发生的运输劳动一样,“它的生产性质只是被流通的形式掩盖起来了”。马克思解释道:“这里所以产生迷误,是因为社会关系表现为物的形式。”[7]因为,从物化劳动的角度来看,骑手配送即流通领域的运输,只是改变了外卖商品的地点,没有改变其形态,其在外卖商品形成过程中没有留下丝毫具体劳动的痕迹。因而,从表面上看,骑手配送仿佛不创造价值。但实际上,“运输业上的生产资本”,会随着“运输工具的价值转移”,以及“运输劳动的价值追加”,部分地“把价值追加到所运输的产品中去。而后一种价值追加……分为工资补偿和剩余价值”。[8]不支付骑手的运输费用,外卖商品的使用价值就不能最终实现。因此,其配送应是生产性劳动,配送所消耗的活劳动即他们的劳动力能创造出新的价值和剩余价值。而骑手配送费用则需通过外卖商品的销售,进而得到补偿。
二、骑手的雇佣现状
骑手是“信息生产力”下的产物。随着“互联网+”的出现,人们的“生产方式”发生改变,“一切社会关系”也随之改变。[9]首先,网络改变了骑手劳动方式。随着信息技术的出现,人类已进入数字时代。在外卖领域,网络和数据日渐成为重要的生产资料。餐厅通过签约,接入外卖平台,进而搭上互联网便车。平台拥有完备的信息系统,包括:餐厅展示、网上下单、会员中心、订单管理、订单自动通知、地图搜索、物流配送、用户评价等。消费者通过搜索引擎快速找到餐厅、下达订单并选择物流配送,最后通过在线支付划转货币,整个交易均在网络上完成,网络信息联接着外卖商品的生产、流通、消费环节,成为不可或缺的生产资料。餐厅按订单生产,骑手按订单配送,生产、劳动方式均发生了相应的转变。其次,网络改变着骑手劳动关系。目前,外卖配送有餐厅自配送和平台配送模式,餐厅自配送需雇佣并管理骑手,为节省用人成本,集中发展主业,餐厅往往把非核心业务即配送剥离,外包给平台(如饿了么)。平台独揽配送业务后,改变了原来的中间渠道(用人单位),将传统的“用人单位+员工”模式替换为“平台+骑手”模式,通过一定的法律手段,直接或间接地使用骑手,“即需即用,用完即散”。当前,骑手与平台间的用工关系主要有三种类型:
第一种为专送模式。在众多骑手中,“专送才是平台的亲儿子”,是平台自营骑手,是正规军、全职骑手,与平台形成劳动关系。专送骑手是平台内部员工,有“五险一金”。专送骑手由系统派单,派送范围一般在3公里以内,取餐及配送时间在35分钟左右。专送每单提成基本固定,不受距离影响。专送骑手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有固定底薪,薪资月结。专送更注重服务质量,如“饿了么”专送有“准时达”服务,此外,专送还有距离补贴和重量补贴等。
第二种为外包模式。为补充平台直营(专送)骑手的运力不足,平台还会采用第三方团队模式即外包模式,平台将业务外包给外包公司,如“饿了么”平台将配送外包给“蜂鸟配送”,骑手由外包公司自行招募,与外包公司建立劳动关系,骑手以劳务派遣等形式输送入平台,骑手与平台间只存在用工关系,无直接劳动关系即用人关系。
1.用工多样始料未及
三、骑手身份定位的困境
(一)理论准备不充分
《资本论》对非典型劳动关系鲜有涉及,其所述资本雇佣关系是典型的劳动关系。而限于时代特点,马克思也不可能预见到网络的加入,进而对“平台+骑手”模式下的用工进行论述。因此,非典型的“互联网+”劳动关系理论研究出现空白。面对新型用工,传统的雇佣理论显得捉襟见肘。
食管癌放疗患者普遍发生白细胞下降、放射性皮肤反应、放射性食管炎及放射性肺炎等毒性反应,经护理有效缓解。见表1。
第三种为众包模式。社会化众包即平台“向大众外包任务”,把过去由其组织内部员工执行的配送任务,外包给非特定的骑手,美团、蜂鸟等都有自己的众包配送系统,众包骑手无需受雇于固定的用人单位,只需登陆APP、注册帐号,即可抢单配送。众包骑手多为社会闲散劳动者,是杂牌军,是兼职骑手。众包实行抢单制,由餐厅派单,骑手竞争抢单,手快,则单多,送单多则挣钱多,不抢单则零收入。众包配送范围一般比较大(如5公里),配送按距离收费。众包骑手上班时间自由,无固定工作地点,薪资随时提现。
骑手的活劳动,如前所述,的确能创造剩余价值。“活劳动是在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力消耗”,劳动力是劳动者“体力和智力的总和”。但是,骑手的劳动力并不天然就是劳动。在“互联网+”运营模式下,“信息的生产、处理与传递成为生产力与权力的主要来源”。[10]对骑手而言,“有订单才能生产”,然而,餐厅的商品流通运输业务早已外包给平台,“平台实际上控制了市场和接触市场的渠道”,未经授权,骑手无权从事运输活动。当骑手“不拥有使自身劳动力得以实现所必需的生产资料时……劳动力买卖还会存在”,[11]然而,骑手“劳动力的使用权”最终又卖给了谁呢?现实中,骑手可以有多种选择:或卖给平台,与之形成劳动关系(专送);或卖给外包公司,再以派遣工形式为平台所用(外包);或自行注册APP众包软件,自备工具,自行组织劳动(众包)。对于平台运输业务层层转包现象,《资本论》的解释较为透彻,即计件制提供了“一个十分确定的计算劳动强度的尺度”,餐厅先将业务外包给平台,平台再与外包公司“签订按件计酬合同”,外包公司再“自己负责招募帮手和支付给他们的工资”。[12]然而,对于众包模式,《资本论》却难以解释。马克思认为劳动力买卖双方明确之后,才形成资本雇佣劳动关系,但是如果众包骑手的劳动力没有买方,骑手是否还是劳动雇佣关系中的劳动者不得而知,众包这种特殊用工已超出传统劳动用工范畴。
对众包类用工的司法认定已然成了世界难题。在餐饮外卖领域,众包骑手多为非雇员。法国定为“个体企业主”(Auto-entrepreneur,相当于我国个体工商户),澳洲被归类为独立合 同 人(Independent Contractor), 德 国、英国的被称为自由职业者,美国为独立承包商(Independent Contractor)(Uber司机在2016和解中仍被认定为独立承包商)。虽然各国众包骑手称谓不同,但其境遇均出奇相似,均不享受雇员待遇,如美国独立承包商没有“在职责任险和工伤补偿险”,[21]没有资格申请失业补偿金,在年底报税时使用的是1099表格,而不是W2表格。平台将骑手定性为独立承包商,可以不支付雇员福利,而被砍掉的费用通常占雇主给雇员“工资成本的32-37%”。[22]
2.众包骑手身份难以解释
外包、众包骑手与平台都是“使用而非拥有”的关系,外包骑手尚有外包公司作为其雇主,但众包骑手却成了“孤儿”。从表面上看,众包骑手貌似没有签约雇主,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所有者和使用者,类似于个体户或自雇劳动者。在众包模式中,平台貌似中介机构,对外宣称自己是“网络服务提供者”,不与众包骑手存在劳动关系,它“独立于任务发包方与接包方,是‘神经中枢’,发挥着集聚信息、匹配供需、促进对接等功能”,[13]根据交易额收取信息服务费。众包骑手与众包平台间关系好似“我搭台,你唱戏,吃瓜观众去买单”。
平台“凭借信息技术高效地捕获市场信号并组织生产活动攫取利润”,[14]因此,汤姆·斯利(Tom Slee)认为,平台实际上就是“向劳动者收租的新地主”,[15]众包平台所收信息使用费仿佛与租金相似,但平台与众包骑手间关系绝不等同于简单的租赁关系。从经济学角度,众包骑手按每单报酬一定比例向平台上缴信息费,其劳动是平台创收的唯一财富来源。众包骑手服务价廉、快捷、品质优,增进消费者剩余,形成消费粘性,使平台得以持续生存与盈利。社群好评是平台的“连接红利”,在马太效应下聚焦更多消费群体,占领结构洞,使平台在竞争中形成垄断优势,生产者剩余增加。众包骑手从事的是生产性劳动,骑手劳动力的使用价值(配送劳动)能创造出新的价值,这个新价值比骑手劳动力自身的价值更大,能给众包平台带来利润。然而,遗憾的是,众包骑手却不一定存在于雇佣关系之中,平台将众包骑手“拒之门外”,宣称双方为信息服务的居间关系,而非劳动雇佣关系。那么,从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理论来看,众包骑手没有雇主,其创造的剩余价值又被谁占有了呢?平台还是社会,抑或消费者、餐厅?“利之所生,损之所归。”众包平台显然是受益人,受益人应对骑手承担相应的责任,否则,其所受利益若无正当权利来源,是否应定性为不当得利呢?对于这些问题,《资本论》难以充分解释。
(二)判定标准不明晰
20世纪末,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计算机新技术(Web技术、Java技术、数据库技术等)的出现,图书馆集成管理系统的架构发生了变化,开始使用客户端/服务器计算模型[7],并模块化地集成各类图书馆业务功能,允许用户通过OPAC、基于Web的在线门户网站等使用图书馆的服务[8]。 Aleph 500、Horizon、Voyager、Millennium、U-nicorn等知名图书馆集成管理系统的雏形在这一时期形成,并于随后的十年间逐渐成熟。
1.组织从属性弱化,“为谁提供劳动”认定困难
(1)主体虚拟趋势明显,实体企业日渐遁形。劳动关系主体只提及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主体资格”要求符合法律、法规。平台经济下,利益相关者众多,“更多的社会力量卷入到劳动关系的格局中来,成为了新的主体”,[16]多方主体相互关系如何定性,成为谜题。此外,用人单位趋向虚拟化,平台的加入使得企业的边界变得更加模糊,平台角色难以定位。形式上,平台不具备物质外形;管理上,消费者主导评价,对骑手进行激励和约束,似乎没有管理者。根据科斯企业边界和规模理论,企业的确可能存在缩小乃至虚拟化趋势。但是,平台是“液态化的公司”、虚拟的用人单位、生产工具抑或信息管理者?“平台+骑手”用工复杂多变,这些问题尚难定夺。
离女人的座位不远处,已经有个颏下打领结的小男孩在弹门德尔松的钢琴曲,指法稳健而灵活,俨然一副投入的样子,十分的忘我。
(3)业务类型复杂多样,是否从属难以界定。“网络平台由广告信息平台,进而网上销售平台,发展到生产要素组织平台(即利用网络平台组织生产要素以产出产品和服务),而步入平台经济阶段”,[17]平台业务分配更趋多样,有“指派业务型”(如专送骑手)、“竞争业务型”(如众包骑手)、“混合业务型”。骑手从事的运输劳动是否为平台业务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实难判断。平台宣称其业务为信息收集发布,不直接经营实体业务,似乎骑手所从事的配送与平台主业相去甚远,但配送等可否界定为与平台有关联的业务活动?能否对其业务进行扩大化解释?
2.“人格从属若即若离”,[18]“接受谁的管理”难以界定
然而,承认这一时期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上的局限,并不意味着否认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意义。虽然,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手稿中,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阐发在直接的意义上服务于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清算,但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也已经充分意识到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非历史特征,并且强调从生产的社会关系出发,批判政治经济学范畴的抽象(形而上学)本质以及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特征。
(2)劳动报酬给付更加多元化。劳动报酬的属性已难以判断。当前,骑手劳动报酬支付更加复杂,骑手报酬或由平台支付,或由消费者给付,是否为工资模棱两可。此外,劳动报酬的支付很难有书面证据。工资支付凭证一般记录在职工名册中,书面工资支付记录证明包括工资卡、工资存折、工资条等。但在平台经济下,诸如支付宝、微信等已改变了传统的支付方式。并且,与传统劳动关系工资稳定性与周期性发放不同,外包、众包骑手一般不存在固定薪酬,有的甚至没有底薪,劳动报酬按件计费,多劳多得,不劳不得。工资金额由业务量决定,工资不再按月定期支付,这和传统意义上的工资区别很大。
2018年11月21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推进物流枢纽布局建设,促进提高国民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率。会议强调,要加快物流领域“放管服”改革,打破阻碍货畅其流的制度藩篱,坚决消除乱收费、乱设卡等推高物流费用的“痼疾”。此中既有崭新举措,亦有陈年手段。坎坎坷坷二十余载,相关部委、各级各地,此番不应再负业界期待。历史经验证明,体制成本上升,整个国家民族就会为其所累。而唯有不断提升政府效能和行政效率,转变政府职能,才能建设国人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才能体现主政者之魄力和担当,才能不断优化办事创业和营商环境,才能持续引领中国经济与中国物流破厄前行。
3.经济依赖减弱,“由谁支付报酬”不易判断
史尚宽先生认为,“劳动关系谓以劳动给付为目的之受雇人与雇佣人间之关系”。传统理论认为劳动者须依赖用人单位提供的生产资料,才能进行劳动,并从而获取工资以养家糊口。平台经济下“劳动者接受用人单位指示给付劳动并换取报酬这一劳动关系的核心并没有发生动摇”,但有些细节发生了改变:
(1)生产资料的提供发生重大转变。王全兴认为平台经济“未改变劳动力与生产资料(劳动条件)相结合的本质”,[20]只是结合方式发生了改变。平台提供的生产资料和劳动条件的确发生了改变,骑手自带劳动工具的情况普遍存在,平台提供的信息服务及订单生成、控制系统等日渐成为虚拟的并且极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劳动条件)。但是,能否因此而认定,但凡运用平台生产资料(劳动条件)的骑手,如外包、众包骑手均与平台建立劳动用工关系?
平台与骑手间是否为劳动关系,是当前“互联网+”用工绕不开的棘手问题。目前,劳动关系尚无明确的法律定义,且劳动关系与诸如劳务、合作、雇佣关系等其他民事法律关系边界、区分规定不详。大多数平台不与骑手签订劳动合同,我国劳动法律对事实用工关系的判定严重滞后,司法实践仍适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中的“劳动三属性”标准。该《通知》于2005年颁布,如今已难以应对平台经济下的劳动关系。“平台+骑手”用工关系更趋个体化,用工关系的主体、客体、内容均发生诸多变化,变量增多,表现弹性,判定事实用工关系更是难上加难。总体而言,除专送外,其他骑手身份定位面临以下困境:
(4)两序槽间接头施工。双轮铣槽机施工的防渗墙槽段间接头一般采用切削法进行槽段连接连接。施工过程中,通过切削掉部分Ⅰ序槽墙体与Ⅱ序槽结合处的混凝土,使Ⅰ序槽墙体露出粗糙的新鲜混凝土面,混凝土浇筑前用钢丝刷将接头处泥皮刷洗干净。其平面示意图如图1所示。
劳动关系的客体是服从性劳动,服从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接受间接与抽象管理,即“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二是直接与具体的管理,即“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传统劳动关系建立在集体化劳动基础之上,而互联网技术的出现,瓦解了这一模式,尤其是众包骑手不坐班,无固定工作场所,工作时间碎片化,“而碎片化与《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规定中的劳动关系持续性有所矛盾”,[19]合同期限、劳动时间等问题将难以判定。在管理界定方面,有两个突出问题亟待解答:一是规章制度难以判定。用户评价、积分制度等是否为规章制度?员工参加培训的记录、员工的签收记录等是否为制度“适用”不得而知。二是管理手段难以认定。平台管理以用户需求为导向,以用户评价体系来管理骑手。平台利用管理软件,在网页公告消息,或通过QQ、微信,视频会议等,不需与骑手面对面接触,即可安排工作并控制工作进度,在“监督”和“力度”上都不再强势。此外,平台的一些类似管理措施很难判定,如骑手统一服装,按预设统一流程提供服务,按统一收费标准收费、服务接受平台调配以及平台对准入条件的限制、培训等是否等同于管理?派单,签到、定位,适时跟踪、考勤表、出勤卡等是否为劳动管理?一些行业惯例与劳动管理又该如何区分?这些问题如若无法解答,将给骑手身份认定带来不小的阻力。
(3)对单一用工主体经济依赖减弱。平台经济下,“斜杠青年”逐渐增多,众包骑手为兼职骑手,可以下载多个平台APP,同时兼任厨师、美甲、配送等职位,其兼职就业对其中一个平台很难造成实质影响,骑手的“忠实义务”已打折扣,骑手是否可以同时与数个平台建立劳动关系,答案不详。
(2)员工身份难以认定,组织联系日趋淡化。骑手很难证明其是平台或外包公司组织成员。由于管理网络化,电子合同、网上“用工通知”等难以认定为劳动合同。用工管理采用网上签到方式,很少点名考勤,骑手难以证明其是组织成员。虽然骑手身着印有平台标志的工作服、驾驶印有平台标识的车辆,持有平台登记的编号或注册号,但在司法判例中,这些表象均没有作为劳动关系判定的实质标准。从组织性来看,骑手之间联系松散,集中参与活动很少,骑手间互相协作很少,甚至有些互不认识,因此,组织凝聚力趋弱。
(三)司法审判不统一
1979年,中国科学院在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建立草原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对典型草原进行草原生态系统研究,标志着我国开始对草原进行综合、深入、广泛和定量化研究。经过20多年的系统研究,我国在草原现代生态特征、生态系统生产力、退化草地生态系统的恢复和改良、人工草地的建立和利用和草地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取得很多科研成果[19-24]。其中,关于草地生态系统的恢复和改良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植被以及土壤环境退化特征、退化等级评价指标、退化草地恢复演替规律、改良措施对比试验和改良机具的研制与开发几个方面。
反观我国,众包类骑手身份认定同样棘手,近几年的司法审判显得极为纠结。确认“网约工”(骑手是其中一种)与平台建立劳动关系的判例很少,如“好厨师”、“滴滴打车”、“神州专车”案、“闪送员与闪送平台案”;确认未建立劳动关系的,如“美美哒”、“五八到家”、“e代驾”、“网红”主播、游戏主播案;确认雇佣关系的,如“外卖小哥撞伤路人案”、“代驾司机撞倒骑车老伯案”;确认居间关系的,如 “女子网约美容灼伤双眼诉河狸家案”;确认建立劳务派遣关系,如“AA租车”、“一号专车”案。
“同事不同判”,司法判例不仅难以定止纷争,反而会诱使平台打法律擦边球,规避劳动法律责任。除专送骑手外,其他骑手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被遗弃”现象。获利者,只用工而不用人,不仅不为骑手承担法律责任,甚至还反将竞争压力、交通伤残风险等转嫁给骑手,“羊毛出在猪身上、让狗埋单”的闹剧屡屡上演。为规范平台用工,政府应与时俱进,进行制度创新,为保护骑手劳动权益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
四、骑手用工的规制路径
“经济发展不应以牺牲劳动者权益为代价”,骑手无论以什么方式进行劳动,都是劳动者,理应受到法律的尊重和保护。作为生产关系的重要组成,劳动关系的选择、取舍关乎民生。外卖平台劳动用工关系如何定位,“劳企两利”怎样平衡,考量着政府的执政能力。当前,骑手用工的法律规制可从以下方面着手:
(一)完善平台用工立法
当法律对“新生的社会关系”难以规制时,平台便“肆无忌惮地将法律漏洞利用到最大化”,[23]它们刻意模糊劳动关系和其他关系边界,炮制“四不像”用工混淆是非。为遏制这种趋势,保护“身份不明”的骑手,政府绝不能再“养虎为患”,应正视现实,及时填补法律漏洞,杜绝不法行为再次滋生。
首先,加快平台责任立法。当前,平台早已不再是简单的媒介,它已“枝繁叶茂”,甚至已长成“参天大树”,当平台“由信息中介转而呈现越来越强的管理性”,[24]或其实力壮大到可以垄断资源时,平台应负的社会责任应逐渐加大。纵使当前立法无法将骑手用工定性为劳动关系,也理应对平台“加以功能性的规制”,[25]以彰显社会公平与正义。为规范平台运营,政府应加速制定《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责任法》,明确平台经营者的法律性质,认定平台在骑手用工中的主体资格,明确平台与第三方外包公司、专送、外包、众包骑手间的权利义务,制定平台行为规范,明确平台责任范围。在劳动立法尚未完善之前,应有条件地让平台承担部分责任。按照“谁用工、谁负责”原则,若骑手为派遣工,平台则为实际用工单位。根据《劳动合同法》第92条第2款规定,骑手因配送业务自身遭受事故伤害的,平台和外包公司应承担连带保险责任。而依《侵权责任法》第34条第2款,当骑手造成他人伤害的,平台应承担侵权责任,待平台先行垫付之后,再向有问题的骑手追偿,外包公司有过错的,则“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为防止平台滥用劳务派遣、假外包,监管部门应严格按照《劳务派遣暂行规定》,限定平台使用的被派遣骑手数量不得超过其用工总量的10%。此外,为防止第三方外包公司(劳务派遣公司)“用工不用人”,不与骑手签订劳动关系,我国立法应借鉴建筑外包做法,依据“谁发包,谁管理,谁主管,谁负责”原则,规定平台承担用工主体责任,即当平台将配送业务转包、分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第三方(如自然人),或第三方未与骑手签订劳动合同时,若骑手从事承包的配送业务因工伤亡,平台应对外包公司招聘的骑手承担用工主体责任即工伤保险责任。
在时间为150 s及γ=30噪声水平下,对机器人传感器网络节点位置信息进行了测量,如图2所示.通过显示与原始节点之间的实际位置、估计位置,对MDS结合KL定位方法进行了定性评价.由于噪声的影响,估计的位置与节点的实际坐标间存在较大的距离误差.采用MDS和KL联合定位方法,误差的波动远小于传统的MDS定位方法.
其次,完善互联网劳动立法。《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颁布至2018年已有13年,当时的立法背景以及经济形势如今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以落后的立法来规范全新的用工关系,无异于“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在“互联网+”时代,平台用工已司空见惯,我国立法不能坐视不管,为规范此类新型用工,亟需出台《共享经济劳动关系管理适用办法》、《共享经济劳动关系基准法》等法律,明确界定互联网劳动关系的定义,将平台用工下的各种灵活用工纳入劳动法的保护范畴,规定各种用工的构成要件、劳动主体资格以及相关主体的权利义务。进一步廓清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合作关系、雇佣关系、承揽关系等边界,对法律关系的竞合尤其是“四不像”问题做出明确规定,即当用工模式兼具两种以上的法律关系特征时,立法应明确规定鉴别方法。在劳动用工管理方面,立法可持开放姿态,考虑到骑手人数众多,平台管理可以创建“劳资共决制”,无论何种用工模式,一旦平台旗下各类骑手人数超过200人时,平台拟定规章制度的表决应有骑手代表参与。唯有骑手共决、共治,才能扭转平台一手遮天、骑手无力发声的被动局面。
(二)明确劳动关系判定标准
在判定劳动关系时,我国立法规定,劳动关系双方应自用工之日起签订劳动合同,当劳动合同缺位时,应从人格从属性、经济从属性、组织从属性三方面,来认定是否存在事实劳动用工关系。但当前平台用工,劳动“三属性”发生了或强或弱的变化,甚至有些雇主故意弱化其中某个特征,让“三属性”变得残缺不全,使得劳动关系的认定变得扑朔迷离。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应有一双“慧眼”,通过抽丝剥茧,来认清平台用工关系的实质。
回归到《资本论》,其所述劳动关系的客体应是服从性劳动,劳动关系的实质应是人格从属性。马克思曾说:“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内进行的”,在流通中,劳动力的卖者和买者,双方貌似自由平等,而一旦离开这个领域,“假象就暴露无遗”。[26]在劳动过程中,一个“雄心勃勃”,而另一个却“战战兢兢”。平台与骑手的劳动雇佣关系也是如此,平台是骑手劳动力的使用者,行使“劳动力的指挥权”,监督其“有规则地并以应有的强度工作。”[27]平台设定严苛的管理制度,如延时罚款、消费者差评罚款、跑单量不够罚款等,引导、管控、甚至迫使骑手付出劳动力。人格从属性是劳动关系判定核心,这是我国学者通识,同时也被德国、英国、美国等多国认可,如美国认为雇员没有“足够的议价能力”,只得将“工作的控制权拱手让与雇主(以此换取未来经济状况的改善) ”,相应地,“法律则要求雇主提供最低水平的经济和人身安全保障”。[28]
相比而言,经济从属性可居于次要位置,尽管骑手劳动所需的生产资料并不完全依赖于平台,但若其收益主要来源于平台,平台甚至可以卡中其“咽喉”,这种弱势骑手,社会显然应出手相救。而组织从属性可予以适当忽略。因为“企业的组织化只是将雇主对劳动者的直接指挥转变为组织化的指令”,属于“人格从属性”的一部分,“并且劳动者相互之间的协作关系与判断劳动关系之间并无直接关系”,[29]“组织从属性”可被人格及经济从属性所吸收。
本工程粗集料采用怀集县东八里碎石,其各项技术指标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均满足规范要求Ⅱ级,部分指标已满足Ⅰ级要求。
实践中,各国均重点考核人格从属性。英国早于20世纪60年代起就一直采用多因素认定方法,美国也用类似方法进行了多年测试。如美国国税局用“20点清单”审查“控制程度来判定雇佣状况”,[30]清单分成三类:即“行为约束、财务约束以及相关方关系”。但清单却没能“指出哪些指标可以分别来判定雇员或承包人”。[31]美国许多州还采用ABC测试非雇员,即“无论是在履行名义合同还是实际合同”,不受“雇佣者的控制和指示”; 其“工作超出招聘实体正常工作范围”;通常从事独立业务,且其业务与雇主有“相同的性质”。[32]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则扩展为“经济现实”测试,即“控制、投资、获利或受损的机会、持续性、技能、营业的整体性”。[33]
结合我国用工实际,当前判断平台与骑手间的人格从属性,首先,应考虑控制的紧密度及关联性,即平台的监管、考评与骑手所提供的服务相关联。至于平台管控的主要手段---用户评价是否为劳动管理,要看“劳动关系中评分管控是对过去工作报酬的控制和对未来劳动关系存在与否的双重控制”。[34]其次,判断人格从属性要看用工实质,而非合同表面。从民法角度来看,骑手与平台签订用工合同,应遵循意思自治原则,双方只要不存在意思表示不真实、不自由的证据,所签合同当属有效。但从劳动法角度考虑,劳动关系是否成立应属法定范畴,不应由双方自由决定。如若劳动领域允许意志绝对自由,那么平台就可以利用外包、众包掩盖雇主身份,通过“隐蔽性雇佣”,达到“追求轻资产、不养人、逃避社会责任”的目的。为矫正劳资实力不均衡,达到实质上的公平,判断平台与骑手间的用工关系,不仅要看协议名称,最关键的还要审查合同中双方权利义务以及实际履行情况。如果平台“以一种与骑手的独立身份不相符的方式指挥并监督其工作”,制定各种规则,通过培训、派单、定位、签到等对骑手进行管理,通过用户评价、限时送达、催单、罚款等方式要求骑手保证服务质量,并且骑手实质上并不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没有平等协商的权利,那么平台与骑手间关系就应定性为劳动关系。
(三)加强众包骑手的特殊保护
众包模式一直为世人所诟病,在欧洲被称为“平台资本主义”。刘皓琰认为,“没有物质形态的工厂并不意味着没有工厂”,众包实际上是一种隐蔽雇佣,即“以一种表面关系掩盖真实的雇佣关系”,是“合法外衣下的隐性剥削”。[35]
批评归批评,但批评无法消弭问题,众包骑手的身份定性还需政府及时拿出应对之策。从当前判例来看,众包多被判不存在劳动关系,但也有少量例外。2018年6月6日,北京海淀法院判定闪送员与“闪送”平台成立劳动关系。平台被认定为从事货物运输业务经营的公司,而不是信息服务中介。因平台限定闪送员用工条件,且报酬是闪送员主要劳动收入,法院认定两者间具有从属性。法院还在判决中指出,平台不能因“采用新技术手段与新经营方式”,利用“相关配套制度尚不完善而拒绝向劳动者提供基本权利的救济”。该判例将对今后的同类案例起到积极的指引作用。但要彻底解决众包之痛,还须进一步突破瓶颈,对不具备劳动关系特征的众包予以规制。这些骑手自行抢单,对平台任务不是必须服从;以兼职形式劳动,但经济来源又大多依赖平台;不与任何用工主体签约,不属组织成员。这类骑手,若认定为劳务关系,又不具备平等性,若定性为劳动关系,又缺乏组织性,这类用工夹杂在两者中间的“灰色地带”,让法院对骑手身份进行认定,无异于法官“手握一个方形钉子,被要求在两个圆孔间做出选择”。
对这类用工,我国学者多建议定性为全新用工关系:如服务共享关系,独立自由职业者,自雇型劳动者,基于工作交易关系的劳动关系等。国外众包骑手多被认定为自雇劳动者或自由职业者(类似个体工商户),他们被假定有“足够的议价能力”,但事实上,根据2018年5月美团点评研究院发布的《2018年外卖骑手群体研究报告》,我国众包骑手恐难定性为自雇劳动者。骑手中75%的来自农村,84%的没有上过大学,31%的属于“去产能产业的工人”,超6成骑手已婚,且已婚者中,又有87%的已生育,且二胎比例达到32%,众包骑手收入多在4千元以内。[36]经济基础薄弱、文化层次不高、家庭负担过重,这些骑手若认定为创业者,显然有悖现实。实际上,这类骑手类似德国的“类雇员”(即“类似雇员”),即“那些具有经济从属性而且像雇员一样需要倾斜保护的人”。[37]我国可借鉴德国做法,将众包用工定为类劳动关系,并将劳动用工分出“多个层次的梯级缓冲带”,如劳动关系、劳务关系、雇佣关系、承揽关系、类劳动关系等,并“实现灵活用工的标准化”,[38]让不法平台不再对灵活雇佣抱有“幻想”。
在身份认证方面,可采用个人申报登记办法或借鉴MBO Partners的认证制度,由劳动主管部门认证为“类雇员”,一期认证三年,期满可续期。在社保方面,建立匹配的保险制度。在无法全方面保护之时,至少可以优先考虑众包骑手人身权利保护问题。鉴于当前骑手在配送过程中,交通事故频发,伤残死亡无人埋单,政府可创建可转移福利保障体系,建立“分享社保账户”,要求每一雇主(平台)按比例支付到众包骑手账户,骑手更换工作可随意提取。在维权方面,创建众包骑手协会。众包骑手虽然人数众多,但实则一盘散沙,没有组织归属感,当骑手与平台产生冲突,如众包系统将骑手拉黑,封停账号,导致骑手在众包APP账户中收入无法提现,或平台扣、罚款产生纠纷时,众包骑手限于所受教育以及维权渠道的缺乏,往往无处申诉。为切实解决众包骑手劳动用工纠纷,政府可督促平台在较大的社区配置众包骑手维权点,以便就近、集中处理骑手申诉,及时化解纠纷。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3][4][5][12][26][27]卡尔·马克思.资本论[M].何小禾,编译.重庆出版社,2018:17; 299;180;96;112; 32;56.
[6]刘伟.一本书读懂资本论[M].哈尔滨: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128.
[7][8]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M]//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54;168.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42.
[10]姚建华,刘畅.新媒体语境下众包新闻生产中的弹性雇佣关系研究[J].新闻爱好者, 2017(11):24-28.
[11]荣兆梓,等.通往和谐之路:当代中国劳资关系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2.
[13]余琨岳,顾新,王涛.第三方众包平台的价值实现机理和路径研究[J].中国科技论坛,2017(4):22.
[14]刘皓琰,李明.网络生产力下经济模式的劳动关系变化探析[J].经济学家,2017(12): 37.
[15]汤姆·斯利 .共享经济没有告诉你的事[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7.
[16]孟泉,刘明月.什么是社会劳动关系?——概念辨析、调整对象与分析框架[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7(06):143.
[17][20]王全兴.“互联网+”背景下劳动用工形式和劳动关系问题的初步思考[J].中国劳动,2017(8): 7;8.
[18]全军,吴克孟.“互联网+”经营模式下劳动关系认定的把握尺度[J].北京市工会干部学院学报,2017,32(3):45.
[19]朱海龙,唐辰明.互联网环境下的劳动关系法律问题研究[J].社会科学,2017(8):89.
[20][21][29] 玛丽昂·麦戈文. 零工经济:在新工作时代学会积累财富和参与竞争[M].邱墨楠,译.中信出版社,2017:223;21; 156 .
[23][38]袁文全,徐新鹏.共享经济视阈下隐蔽雇佣关系的法律规制[J].政法论坛,2018,36(1):120; 128.
[24][33][37]于莹.共享经济用工关系的认定及其法律规制——以认识当前“共享经济”的语域为起点[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8,21(3): 59; 55; 57.
[25]丁晓东.平台革命、零工经济与劳动法的新思维[J].环球法律评论,2018,40(4): 96.
[28][32]赛思·D·哈瑞斯,汪雨蕙.美国“零工经济”中的从业者、保障和福利[J].环球法律评论,2018,40(4): 9;24.
[29]王天玉.基于互联网平台提供劳务的劳动关系认定——以“e代驾”在京、沪、穗三地法院的判决为切入点[J].法学,2016(6):56.
[30]奥利·洛贝尔,汪雨蕙.分享经济监管:自治、效率和价值[J].环球法律评论,2018,40(4):45-54.
[34]彭倩文,曹大友.是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以滴滴出行为例解析中国情境下互联网约租车平台的雇佣关系[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6(2):95.
[35]刘皓琰,李明.网络生产力下经济模式的劳动关系变化探析[J].经济学家,2017(12):35.
[36]美团点评研究院.新时代 新青年:2018年外卖骑手群体研究报告[EB/OL].(2018-06-08)[2018-05-06].http://www.looec.cn/detail/6448092.html.
A Study on Takeaway Riders' Identifi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apital
ZHOU Zifan
( School of Law and Business, Wuh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Wuhan 430205 )
Abstract: The circulation of goods in space makes the additional production process of riders transportation necessary. The living labor of riders creates new value for the platform, which monopolizes the distribution business. However, their labor employment is in chaos. In addition to establishing labor relations with the riders, the platform isolates outsourcing and crowdsourcing rid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apital, the subject of labor relations is the subordinate labor, and the personality subordinate attribute should be the core standard of labor relations. The riders'identification, accordingly, should look beyond their appearances. Therefore,the government should speed up platform legislation and Internet labor legislation, giving special protection to the disadvantaged riders.
Key words: Takeout riders; labor value; identification; regulation path
[中图分类号] D41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2375(2019)01-0056-09
*[收稿日期] 2018-08-23
[基金项目] 本研究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互联网+’劳动关系的认定及规制路径研究”(项目编号:17YJAZH134)部分成果。
[作者简介] 周子凡(1974-),女,湖北钟祥人,武汉工程大学法商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经济法、劳动法。
① 为节省篇幅,本文中将“外卖骑手”简称为“骑手”。
[责任编辑:苏 清]
标签:骑手论文; 劳动价值论文; 身份定位论文; 规制路径论文; 武汉工程大学法商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