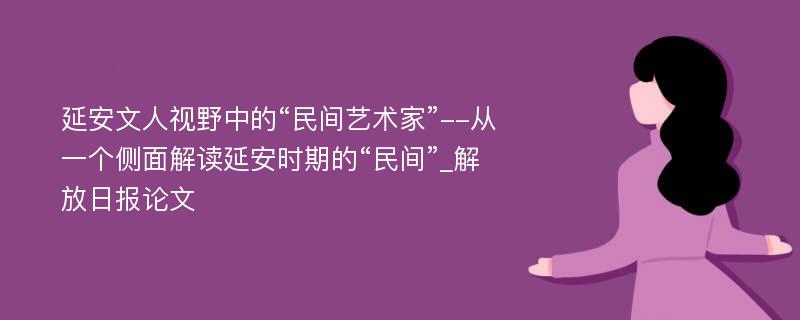
延安文人视域中的“民间艺人”——从一个侧面理解延安时期的“民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延安论文,民间论文,视域论文,文人论文,侧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意识形态本性上,延安文学随着延安时期政治文化境遇的历史性转换,以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为标志,发生了一种毋庸置疑的深刻变化。我认为,在抗战时期“民族形式”论争中,尽管延安文人在民族主义话语架构内从民族文学发展的角度对于“民间”的意义作了充分肯定,但当时以周扬、何其芳为主的主流观念坚守的却是一种二元论的艺术形态观念,而且站在启蒙主义的立场上,对于那种意欲以民间艺术形式为本来构建新的民族文学的说法进行了不留情面的批评。①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之后,情势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以往的二元论文艺观遭到清算,“党的文学”观凭借政治权力得到完整确立,并且在文学创制中日渐定型为新的意识形态权威话语。根据“党的文学”观的内在限定,农民不仅成了延安文学必将予以表现的重要对象,而且也成了延安文学赖以存在的重要依据所在。于是,以农民为主体所固有的民间文化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民间文化不仅成了抗衡“五四”新文化的重要一脉,而且在一定意义上成了延安文人进行文化创制的源泉之一,这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正积极回应了向林冰此前所谓民间形式是民族形式中心源泉的论点,而从近处说,亦即正面应和了萧三、光未然等人在延安“民族形式”论争期间所持的类似观点。自此之后,延安文人积极响应毛泽东向他们发出的“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②的号召,掀起了一场全面走向民间的文艺运动。“民间”也因之在更高意义上改写了现代中国文学的地形图。
民间之所以在整风前后才得以更为全面地进入延安文人的视野,其原因除了抗日战争所带来的中国文化结构和知识分子生存空间的深刻变动之外,更重要之点在于,它因应了正在中共内部完整崛起的新的意识形态权威的需要,因为按照毛泽东的看法,农民不仅成了抗战的主体,而且是未来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主体,因此,农民及其精神构成在新的意识形态理论构建中自然具有某种先在的优越性。在此种情形下,知识分子与民间的关系必然发生根本性变化,即必然由原先的人文主义启蒙立场向民间转化。既然新的意识形态理论不仅对民间表现了密切关注,而且民间本身已经作为一种“民族形式”的构成要素成了新的意识形态理论构成的有机部分之一,因此,知识分子原有精神立场的变化其实正表征着知识分子与新的意识形态富有亲和力的关系的形成。对于整风后的延安文人来说,由于他们基本上已经成了为新的意识形态所改造了的“有机化”知识分子,因此在逻辑上其实跟新的政治意识形态再也不会构成一种冲突关系,而只会形成一种认同关系。所以在我看来,延安文人、权力意志与民间三者的关系其实可以简化为权力意志与民间的关系。众所周知,民间既具有自由自在我行我素的泼辣风格,也是一种独特的藏污纳垢的文化形态,用毛泽东的话来说,乃是民主性的精华与封建性的糟粕交杂在一起。③于是,新的意识形态必将对民间进行符合其话语需求的转换和改造,民间也因之必将成为一个意识形态化了的民间,一个政治符号化了的民间。所以,毛泽东要求延安文人走向民间其实并非要使自在的“民间”得以全面复活,而是希望延安文人在倚重民间文化对农民大众进行有效的意识形态教育或阶级启蒙时,也对“民间”予以意识形态化的改写和重塑,并在此之上创制出新的文化形态。正因为如此,在延安文人、权力意志和民间三者之间,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只能是权力意志或新的意识形态,而延安文人和民间所起的都仅仅是一种工具性作用。权力意志或政治意识形态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对于延安文人和民间来说,也都会起到同样的规约作用。我想追问的是: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延安文人是怎样听凭政治权力的指引并与之结合而对“民间”进行深刻的改造和利用的?
我认为,在延安文艺运动的广泛开展中,“民间”其实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概念。它既包括民间伦理、民间文化、民间艺术形式,也包括熟知并在民间传播这些民间文化的民间艺人,既是指一种底层民众尤其是农民的生存空间,也是指这些底层民众的存在样态。延安时期对“民间”的意识形态化改造和利用,正是以这个总体性的民间作为对象的,因为毛泽东本就希望党的宣教部门能用新的意识形态去把一切民众组织、发动起来,能让新的意识形态占领民间的每一个角落。本来,知识分子和新的意识形态在延安时期对于民间意义的发现是从发现农民不可忽视的精神力量开始的,因此,在探讨“民间”的生成及其意义构造时,应该始终把“人”当作它的传承主体来考察。正因为如此,我想在此主要对民间艺人所经历的改造情况做一番叙述,希冀有助于人们从一个侧面理解延安时期尤其是文艺整风后“民间”的意识形态化改造及其被利用的情形。
应该说,当我们在探究延安时期尤其是文艺整风后“民间”的意识形态化历程时,首先对民间艺人在新的历史场域中所经历的心态与角色变迁做一番较为细致的考察,这是非常富有价值的,也是非常符合当时延安文人在“民间”改造过程中的经验体会和认识实际的。在一定意义上,民间艺人在延安文人的观照下呈现出一种新的状态,并且把这种新的状态所体现出来的历史意蕴直接带入了后期延安文学的创制中。我认为,延安文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延安文人不断被予以意识形态化形塑的历史,进言之,后期延安文学中某些审美形态的形成其实包括了一部延安文人的心态变迁史,其间也自然包含了一部分民间艺人的心态变迁史。而延安文学尤其是后期延安文学赖以形成的隐秘机制之一正在这里,它构成了延安文学中晦暗不明的历史之一部分。在这方面,现代文学研究界的探讨显然是严重滞后了。人们在考察延安文学中的“民间”要素时,往往忽略了新的意识形态话语和政权机构对于民间艺人的收编和改造,而在我看来,1942年后延安文艺中的意识形态化“民间”在逻辑起点上正是从收编和改造民间艺人开始的。任桂林在当时谈到平剧的改造时就曾指出,人之改造是改造平剧的基础和前提。他说,改造平剧自“五四”算起,“时间不算短,人才不算少,技术不算差”,但为何收效甚微呢?他认为,最主要原因乃在于“没有改造平剧工作者”:“在旧时代与旧环境下,平剧工作者不会得到改造,也不可能改造,因此,平剧也就很难改造。在延安,有了人民的政权,有了马列主义的思想,有了改造平剧工作者的条件,因此,平剧才开始起了变化。”这说明,在平剧改造中,思想改造较技术掌握远为重要,因为“一个平剧工作者,即使是掌握了技术,如果思想上有病毛(应为“毛病”——引者),还是不能真正改造平剧的。”④这里谈的虽是戏改工作者的思想改造问题,但对民间艺人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所以当有人谈到要改造陕北的说书时,才会认为首先要“改造说书匠”,原因在于“这是改造说书的中心环节”。⑤其实,就延安时期党的文化政策来说,这也是为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方针所决定了的。毛泽东对此作过明确指示。他说,“在艺术工作方面,不但要有话剧,而且要有秦腔和秧歌。不但要有新秦腔、新秧歌,而且要利用旧戏班,利用在秧歌队总数中占百分之九十的旧秧歌队,逐步地加以改造。”在人员方面,“我们的任务是联合一切可用的旧知识分子、旧艺人、旧医生,而帮助、感化和改造他们。”⑥其中所谓旧艺人就是指民间艺人。毛泽东在此说得非常明确具体,他希望文化工作者不仅要改造和利用民间艺术,而且要改造和利用旧戏班和民间艺人。按照丁玲的理解,之所以要“改造旧艺人”,乃是因为“这些人对旧社会生活相当熟悉,对民间形式掌握得很好,有技术,有创作才能。他们缺乏的是新的观点,对新生活新人物不熟悉,他们却拥有听众、读者。时代变了,人民虽然不需要那旧内容,但他们却喜欢这种形式,习惯这种形式,所以我们要从积极方面,从思想上改造这些人,帮助他们创作,使他们能很好地为人民服务。”⑦
问题是,民间艺人作为栖息在民间社会的特定人群,长期以来形成了他们特有的生存方式、价值观念、审美趣味乃至特有的意识形态,且在文化属性上承袭了较多的游民文化意识,而这些虽然与官方的意识形态自古以来有其相通的一面,但也有其独异的一面,这就在文化习俗和存在样态上形成了他们自身的小传统。那么,新的政治权力意欲对他们进行新的意识形态化改造和利用,这是可能的吗?对此,延安文化界不是没有争议,而是展开了较为激烈的争论。有人认为,民间艺人由于长期生活在底层社会,因此“他们大都染上了烟、酒、嫖、赌的恶习”,而且具有陈陈相因的保守观念和迷信思想,你要改造他们,可他们会抱持“老瘾难戒,老戏难改”的民间观念,依然我行我素,而在艺术表演上也“总是坚持着他们师傅的老一套办法”。⑧因此,民间艺人在本质上是不可改造的,或者说难于改造的。这个看法甚至在1944年10月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召开期间的小组讨论会上仍然得到了部分与会者的坚持。⑨但是,对于这种消极看法,延安文化界在总体上持反对态度,因为它既不符合民间艺人愿意接受改造并且可以改造的事实,也不符合毛泽东在边区文教会上所确定的文化工作上的统一战线方针,按照毛的规定,“统一战线的原则有两个:第一个是团结,第二个是批评、教育和改造。”⑩这个原则在成为延安文化界必须执行的方针政策时,也就必然要求延安文人把对民间艺人的改造和利用纳入到对民间文化的整体改造和利用的轨道上来。早在1941年,有人在总结如何改造和利用“旧剧人”(民间戏子)的经验时就明确指出:“他们并不是绝对不变的。他们是可以改造的,他们的演剧技术是可以利用的。”他们是可以从“旧剧人被改造成新剧人的”。(11)末一句话在整风后的文艺话语中乃是指民间戏子或民间艺人可以被改造为党的文艺工作者。或许是为了对上述主流看法进行更进一步的事实性支持,也为了表达民间艺人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所呈现出来的新的精神面貌,以及延安文人对民间艺人应该采取一种怎样的正确态度,丁玲在1944年边区文教会召开期间颇有感触地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民间艺人李卜》。李卜是一位精于演唱郿鄂戏的民间艺人。他很偶然地被一位演员介绍给了民众剧团负责人柯仲平,然后在后者的邀请下参加了民众剧团举行的一系列演出活动。在柯仲平等人的开导下,本来就爱好和平的李卜“从此明白了共产党与抗日的关系,抗日与人民的关系”。从此,他毫无保留地向剧团成员传授了自己深有体会的演唱技巧:“他从不保留他的技术,而且教人都是从窍诀(诀窍——引者)上使人易于掌握。”在此种情形下,“他觉得大家都是好人,只有自己不争气”,还有一种吸食鸦片的坏习惯,于是“一狠心,难受了几天,也就熬过去了。几十年的老烟瘾,想不到在他五十一岁的开始,在腰腿不好、牙齿也脱落了的情况下,竟一下子就戒绝了。”慢慢地,他开始感受到了集体生活的温暖和意义,他觉得民众剧团就是“他的家”了:“他舍不得向他学戏的那样纯洁的娃娃们,舍不得热情的团长老柯,舍不得这个团体的有秩序有情感有互助的生活。虽然他的家现在也是边区了,在家里也可以生活得平安,可是这里教育更好,这种集体的生活更使他留恋,并且他认识他现在所做的工作,是为了大家,为了所有受苦人的幸福。这种工作使他年青,使他真正的觉得是在做人。他决定要参加这个剧团了,当然很受欢迎。从此他找到了他永久的家了。”于是,他觉得走上了新的人生旅途,“自觉到公家的东西就是自己的东西,公家的事就是自己的事”。所以当有人在边区文教会上慨叹民间艺人难于改造的时候,他立即站起来“以他自己简短的历史,做了说明”。他承认旧戏子的确有不少坏毛病,但并非不能改。由于他们“在旧社会里是受压迫的,只要一解开革命道理,头脑弄通了,改起来也很容易。譬如他自己,几十年的烟瘾,还不是因为参加了新的生活,一下子就戒绝了吗?”因此,他请求大家改变“旧戏子难于改造”的观念,而要想法把更多的旧戏子纳入到新的文艺运动中来。至此,李卜的社会角色发生了重要变化,他以前不过是一个“抽大烟的穷戏子”,一个“民间的艺人”,而现在却成了一个“革命的群众艺术家”。(12)显然,李卜由民间艺人逐渐转化为文艺工作者(“革命的群众艺术家”)的过程,其实正是一个不断遭遇新的意识形态化改造的过程,而在这民间艺人得以改造的途中,延安文艺也就不断拓展了它自身的艺术表现领域和生存空间,因为它体现了新的意识形态话语通过融会民间艺人而包孕“民间”的意图,体现了在此之上意欲造就新的文艺样式的真正开端。
延安宣教部门和延安文人对于民间艺人的改造和利用在说书艺人韩起祥身上得到了又一次成功体现。说书在陕北农村非常流行,倘说信天游是流行于陕北黄土高坡上的民间抒情诗,那么说书就是流行于陕北农村的民间叙事诗了。据当时有人估计,陕甘宁边区大约“平均每县有十来个书匠”,(13)这些说书人大都常年在乡间来回走动,不断开展说书活动。因此,说书在农村具有较为广泛的影响,在新的历史情境下对其进行意识形态化改造和利用也就必然会引起大家的注意。1945年4月,陕甘宁边区文协成立了说书组,由安波、陈明、林山等具体负责。说书组确立了联系、团结、教育和改造说书艺人的基本方针,并在日后对说书艺人的意识形态化改造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在边区政府对说书艺人的改造中,韩起祥的成功转变是当时为延安文化界所乐于称道的。1944年,早在说书组成立之前,延安县政府就对“说书和书匠采取了正确的态度——不是硬禁止,也不听其自流,而是积极地进行改造”。其中尤其把说书艺人韩起祥列为争取和教育的重要对象,主要是尽力去“改变他的思想,具体地帮助,奖励他编新书,发挥他的创作才能”。韩起祥当时三十来岁,双目失明,是延安有名的说书艺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帮助和教育,他在思想上取得了积极进步,并且很快按照政府有关部门的引导创作和说唱了不少新书,根据他在自编“说书宣传歌”中的交代,他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共编了《红鞋女妖精》、《反巫神》、《阎锡山要款》等十二本(篇)说唱新书,其中还对编唱新书的缘起、目的等做了简要说明:“文协、鲁艺、县政府,/奖励我来说新书,/新书说的是什么?/一段一段宣传人。”末了还对同行表明了他的意愿:“希望一般说书人,/学习新书要实行!”(14)上述所言“一段一段宣传人”,他在另外一个说书场合是这样表达的:“过去说旧书,去年自编新书到乡间,为的是帮助革命作宣传……”(15)可见,他的思想已经接受了意识形态化的改造,说书在他那里也就随之成为一种可以用来进行政治意识形态宣传的民间艺术样式了。据说,延安县这样来改造说书人,“不光在群众中起了作用,收到宣传教育的效果,还影响、推动别县也来提倡新书,改造书匠了。”林山作为边区文协说书组的负责人之一,因而对此大发感慨地说:“想想看,改造一个像韩起祥这样的书匠,可以起多么大的作用!有多么大的意义!而所费的力量却很小。费力小收效大,真是‘事半功倍’。”(16)
韩起祥作为一个被改造成功的民间艺人典型,无疑更进一步坚定了新的政权在日后改造和利用民间艺人的决心。只是延安时期对于民间艺人的改造还处在尝试性的探索阶段,其改造手段和方式较后来五、六十年代在全国性的戏改运动中所使用的相比,毕竟要温和得多。当时采用的改造方式主要是以利益诱导和教育为主,在实践中不断对之进行说服工作,教育者特别注意肯定其改造途中的点滴进步,当然,边区政府也采用过集中受训的教育方式。(17)此种改造方式给民间艺人带来的伤害也因之比后来全国性的体制化改造时期要小得多,(18)因为它毕竟具有较大的可接受性,也毕竟没有完全剥夺民间艺人较为自在的生存方式,换言之,延安时期的民间艺人尽管被权力机构和延安文人联手给予了意识形态化改造,但毕竟还有一定的自主权,不像后来完全被改造得失去了生机与活力。
综上所述,我认为延安时期对于民间艺人的意识形态化改造不仅成了当时“民间”意识形态化的有机部分之一,成了后期延安文学赖以成形的一部分奥秘所在,而且也为后来民间艺人改造的国家体制化积累了一部分可资利用的宝贵经验,因此,我们在探究延安文学的形成与延安文学的本质时仍然应当引起高度关注。
注释:
①参阅拙作:《民族—现代性:“民族形式”论争中延安文学观念的现代性呈现》,《文艺理论研究》2005年第4期、《新华文摘》2005年第22期。
②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61页。
③参阅陈思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第122-123页。
④任桂林:《从〈三打祝家庄〉的创作谈到平剧改造问题》,《解放日报》1945年9月8日第4版。
⑤林山:《改造说书》,《解放日报》1945年8月5日第4版。
⑥毛泽东:《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12页。
⑦丁玲:《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张炯主编:《丁玲全集》第7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第115页。
⑧石毅:《旧剧人的改造》,《解放日报》1941年10月4日第4版。
⑨参阅丁玲:《民间艺人李卜》,《解放日报》1944年10月30日第4版。
⑩毛泽东:《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12页。
(11)石毅:《旧剧人的改造》,《解放日报》1941年10月4日第4版。
(12)丁玲:《民间艺人李卜》,《解放日报》1944年10月30日第4版。
(13)林山:《改造说书》,《解放日报》1945年8月5日第4版。
(14)林山:《改造说书》,《解放日报》1945年8月5日第4版。
(15)付克:《记说书人韩起祥》,《解放日报》1945年8月5日第4版。
(16)林山:《改造说书》,《解放日报》1945年8月5日第4版。
(17)参阅石毅《旧剧人的改造》(《解放日报》1941年10月4日第4版)、林山《改造说书》(《解放日报》1945年8月5日第4版)诸文。
(18)关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艺人改造的国家体制化论述,请参阅张炼红:《从“戏子”到“文艺工作者”——艺人改造的国家体制化》,载刘东主编《中国学术》第12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