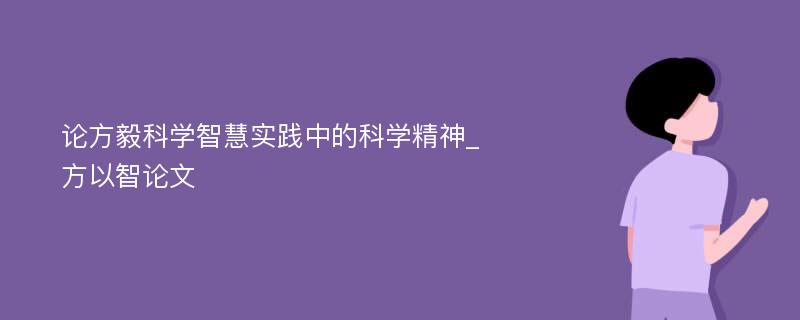
论方以智科学实践中的科学精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论文,精神论文,实践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46.5
文献标识码:A
科学精神是科学活动之灵魂和动力,科学精神决非西方文化的特产[1],不同类型的科学文化都有着与之相应的科学精神,它们既各具特性,亦存在着共性,而且还可以相互补充、融会。在方以智这位明清之际杰出科学家的科学活动中,就较好地实现了中国传统科学精神与西方近代科学精神的共存和融会。他努力学习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力图融会中西,在哲学、数学、医学、物理学、天文、地理等诸多领域都卓有建树。在伟大的科学探索活动背后,必然蕴含着指导支撑这些活动的精神动力,发掘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有助于我们进行科学探索,弘扬科学精神。
1 “天地一物”、“物共一理”的理性观念
明清时期,西学是以西方传教士作为中介而传入的,故伴随着近代科学知识而来的是西方的宗教神学。对此,方以智持有一种正确的文化选择立场:吸收西学中的自然科学知识和实证实验方法,而摒弃了上帝创世等宗教神学的内容。他坚持了中国传统的唯物主义观点,提出“天地一物”、“盈天地间皆物”等命题,并继承了中国气一元论的哲学路线。他说:“一切物,皆气所为也。空,皆气所实也”,“虚,固是气;实形,亦气所凝成者,直是一气而两行交济耳”[2]。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火”这一特殊的哲学范畴,以之作为更为根本的物质元素,火蕴藏于气中,是“所以为气而宰其中”的物质内在运动的动力,“凡运动皆火之为也”,从而建立了“火—气”一元论的唯物主义自然哲学[3]。这一关于世界本质的理性认识,赋予物质和运动统一的原理以一定的科学基础,从哲学上否定了上帝、鬼神等传统人格神的主宰地位,是方氏科学精神中的主要内涵,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在“火—气”一元论的基础上,方以智进一步揭示客观世界的统一性和简化性,他在《此藏轩会宜编·性故》中说:“千之万之,无非阴阳”,“物各一理,而共一理也,谓之天理……人物灵蠢各殊,而公性则一也。公性在独性中”。世界是统一的,又是多样的,事物的个性和共性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故他又在《一贯问答》中指出:“一是多中之一,多是一中之多。一外无多,多外无一”。他力图寻求一种能够融会各门学科并高于各门学科的“通知”之学,追求对各门学问的会通。他说:“圣人通神明,类万物,藏之于《易》,呼吸图策,端几至精,历、律、医、占皆可引触。”[4]他所崇尚的圣人不仅有广博的知识,而且善于融会贯通各门学问;不仅能从万物中抽象出一般规律,寓于《易》理之中,而且研究《易经》的卦策和河图洛书的精微道理,进而触类旁通,将其与历法、乐律、医学、占卜等结合起来研究。
我们知道,《周易》的卦象是一种高度抽象的符号,它概括了事物的普遍规律,借助于这一抽象的符号系统,人们可以大致推演出具体事物的发展变化规律。因此,以孟喜、京房、邵雍为代表的周易象数学派将一些自然科学知识引入到易学中,试图从中悟出事物的某些内在规律。不过,由于当时科学发展水平和人们认识的局限性,上述学派中掺杂了不少神秘主义糟粕,而且,将具体的、变化多端的自然现象纳入卦象的固定模式,也不免有牵强之处。方以智的易学属于河洛象数学派,他将天地万物皆纳入河洛象数学的框架,他在《周易时论·序》中说:“一切征诸《河》、《洛》”,认为“自天地以至人物,有一不范围于《易》中者乎”?这种看法虽然不无牵强附会,但亦体现出方以智对客观世界的统一性的认识,并试图以简化方式统御、表现世界图像,这显然蕴含着重要的合理因素,映射出科学理性精神。
爱因斯坦曾说:“相信有一个离开知觉主体而独立的外在世界,是一切自然科学的基础”,“人们总想以最适当的方式来画出一幅简化的和易领悟的世界图像;于是他就试图用他的这种世界体系来代替经验的世界,并来征服它。”[5]他还认为,对于世界的统一性、简化性的坚信和追求,是科学家们进行科学探索活动的“积极的动机”[6]。这就是说,对于世界规律存在和可理解性的坚信,世界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和一致性、统一性,并试图以简化方式统御、表现世界图像,这些思想是科学理性精神的基石,方以智以上认识与此是相一致的。
2 “有穷理极物之僻”的求索热情
强调经世致用,是中国学术的重要特点,而经世致用的主旨往往又在于为现实政治服务,故讲求修齐治平之学始终是中国学术的主流。这一传统有助于扫除空谈心性的流弊,固然有其社会历史意义。但如果站在科学发展的角度来看,就可以发现,科学的深度进展往往不是来自经世致用的功利目的,而是来自于那些热爱真理,乐于求索,为科学而科学的人们。故爱因斯坦十分欣赏莱辛的名言:“对真理的追求要比对真理的占有更为可贵”。法国作家法朗士认为,好奇心造就科学家。可见,对于万物之理的探究热情是科学精神的主要内容之一。
在方以智身上勃发出这种强烈的探究热情。他曾充满豪情地吟诗以抒发求索和著述的乐趣:“著书因宿好,手自不停披。欲辟羲农秘,才消天地疑。户庭皆纸笔,笥簏伴流离。”[8]他自诩说:“不肖以智,有穷理极物之僻”[9],“自小而好此”,“且以自娱”[10]。这种穷理极物僻好,完全超越了世俗的功利目的,对于科学的探索只是出于自身的喜好和兴趣,对科学真理的追求胜于对科学真理的占有,探索之外别无他求,这种追求真理、献身学术的高度兴趣和热情,是推动科技进步、特别是蕴育有深远理论意义及潜在应用价值的基础科学成果的精神力量。这种不同凡俗的对真理之爱,支撑着他在屡遭世变、文网森严,搬迁流离,付梓困难的情况下仍然孜孜不倦地著书立说,吸引他进入到极为宽阔的科学探索空间。
当时不少士人由于受到传统治学模式的制约,故他们的研究主要局限于社会政治、伦理道德等方面,而方以智在这方面显出过人之识。他意识到儒学囿于社会政治领域的局限性,将学术区分为“质测”、“宰理”、“通几”三大类。“质测”以具体事物为研究对象,他在《物理小识自序》和《通雅·文章薪火》中表达了这种看法,他说:“物有其故,实考究之,大而元会,小而草木螽蠕,类其性情,征其好恶,是曰质测”,这是研究各种实际事物的性质和规律的自然科学;“宰理”是研究“治教”,即社会政治理论的学问;“通几”则研究“所以为物之至理”,“深究其所自来”,探究事物根本之理,相当于哲学。这种分类方法突破了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分类法,很可能是受到西学学科分类影响所致。在学科分类的基础上,他进而认识到哲学与具体的自然科学学科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一方面,“通几护质测之穷”[11],哲学理论能够指导具体自然科学的研究;另一方面,“质测即藏通几”[12],具体的自然科学知识中涵蕴着一般的哲学原理。因此,这三类学问各有其特性和研究价值,故方以智力图超越“儒家唯守宰理”的藩篱,将探索的视野投向天地自然。他曾概括自己的治学范围说:“吾所读者,玄黄五彩之编,万物短长之籍,因龙马之章句,纪奇偶之号数,仰观俯察,近取远取……”[13]这说明,他的探索活动广泛地延伸到诸多领域,不仅涉及到儒佛道诸家,亦研究“奇偶之号数”等自然科学,特别是注重从大自然中学习,读大自然这本“天地短长之籍”。正是这种“有穷理极物之僻”的求索热情,造就了方以智广博精深的学术造诣,使他成为堪与西方“百科全书派”学者相媲美的启蒙思想家。
3 “坐集千古之智”的宽阔胸怀
科学精神的另一重要内容是兼收并畜,博采众长,这也是方以智治学的一大特点。这种宽容精神可以从多个方面体现出来。
首先,他没有那种自居正统,排斥异端的偏见,而是平等地看待各家学派:“《易》一艺也,禅一艺也,七曜、四时,天之艺也”[14]。他将被儒家奉为群经之首的《易经》与目之为异端的佛禅和被官方严禁私习的天文方技皆视为某种“艺”,全无重此轻彼之心。对于儒释道三家,他也不是毫无选择地全盘接受,而是明确表示:“而今后,儒之,释之,老之,皆不任受也,皆不阂受也”,“横竖包罗,逼激机用以补理学之拘胶”[15],既不排斥某家,也非毫无鉴别选择,而是取各家之长以补理学之不足,充分体现出他兼收并蓄的胸怀。
第二,方以智主张不同学派“相胜”、“相救”,既可以互相驳难,亦应当相互吸收。他作了一个十分生动的比喻,说明各家相互补充的必要性:“石火不击,终古石也……然无灰斗以扩充之,石虽百击,能举火耶?是糟粕而神奇寓焉”[16]。火石必须经过打击才能产生火星,但无引火物助燃,则仍然不能使火星燃烧为烈火。可见,单纯的一家一派是十分有限的,而糟粕之中亦藏有精华。因此,无论是一技一能或是至玄之道皆不可固守:“凡自一技一能以至至玄之道,皆不可执”[17],“学有专门,未可执此以废彼也”[18],故他立志“坐集千古之智,折中其间”,提出了“集儒释道教之成”的三教合一主张[19]。这一思想在当时是十分可贵的。入清以后,随着政局的巨变和王学的衰落,学术界一反明中叶以来三教合一的倾向,兴起了一股维护儒学正统、排除异端的思潮,极力摒弃渗入儒学内部的佛道思想,以维护儒学的纯洁性。尽管它的产生有其复杂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但从宏观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文化上的倒退现象,清代学术的保守和沉闷,与这种力排异端的倾向是有一定联系的。相反,学派间的互相融合和驳难才是学术繁荣的必要条件,三教合一对于促进学术发展和完善是有积极意义的。
在这种学术日趋单一化的潮流中,方以智却继续坚持三教合一的主张,对于已经渗入儒学内部的异端因素,他也不站在正统儒家的立场上予以排斥,而是进行积极的改造和吸收,创造出自己的学派。如,当时不少著名学者包括黄宗羲、王船山等人皆曾极力辨明《易经》中的河图洛书非儒家原始《易经》的内容,而是来自宋代道士陈抟。探明河图洛书的来龙去脉固然有其学术意义,但当时诸儒的目的乃是排除异端、维护儒学的所谓纯洁性和文周孔子的独尊地位,因此,这是一种儒学独尊的文化排它主义。在这种文化倒退倾向中,方以智却公开宣称:“智每因邵、蔡力嚆矢,征河洛之通符”[20]。即以邵雍等人的象数之学为治学之基础,精研河洛象数之学,他61岁时,还寄书梅文鼎,与之讨论象数之学。这种兼收并蓄的态度,使方以智得以集各家之精华,构筑自己独特而精深的学术体系。
第三,主张“以远西为郯子”[21],以明智的态度努力学习西方科学文化。郯子是春秋时期东夷郯国的君长,据《左传》所载,他于昭公十七年朝鲁,讲论自然知识,孔子前往就学,并说:“天子失官,学在四夷”。方以智借用这一典故来表达学习西方科技知识的意向。他在少年时代即开始接触西学,成年之后又向意大利传教士毕方济和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学习天文历算、物理化学等方面的知识。他对西学采取了择善而从之的态度,不断地将西方先进科技知识纳入自己的知识体系中。他从西方的天文学理论中看到了中国自“开辟所未有”的知识,以之补充中国的天文学体系,“是天象至今日始全”[22]。据冒怀辛等先生所引资料,在《物理小识》中就有五十四处来自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的《职方外纪》,书中所记载的人体骨骼、肌肉种类等知识,全引自汤若望的《主制群征》一书。他还吸收西方的解剖学知识,认识到思维和记忆须依靠大脑;又接受了西方的地圆说,并以数据加以证实。更为难得的是,方以智既广泛地吸取西方科技知识,又能摒弃其中的宗教神学糟粕,并能洞察到西学的缺陷:“详于质测而掘于通几……彼之质测,犹未备也”[23]。这种兼收并蓄而又不盲目崇拜、全盘照搬的文化选择观对于当今学习西方,推进科技文化的发展更新依然是富于启示意义的。
4 “善疑”、“以实事证实理”的怀疑实证精神
批判与怀疑精神是科学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是科学精神的精髓之所在。在方以智的治学生涯中,始终贯穿着批判、怀疑精神。“是当吾前之必有者,皆可疑也”,“天地间一疑海也”[24],主张勇于思考,敢于怀疑:“物理无可疑者,吾疑之,而必欲深求其故也。”[25]在《物理小识》《东西均》等书中,他常就一些人们习以为常的问题发问说:“星辰何以明?雷风何以作?动何以飞走?植何以荣枯?噫!怪极矣。”“天何不可下?地何不可上?”“目何以视?耳何以听?手何以持?足何以行?”[26]
方以智不仅倡导敢于怀疑,更告诫人们“善疑”。何谓善疑呢?他回答说:“不疑人之所疑,而疑人之所不疑。善疑天下者,其所疑,决之以不疑;疑疑之语,无不足以生其至疑。新可疑,旧亦可疑,险可疑,平更可疑……旧而新者,新遂至于无可新;平而险者,险遂至于无可险,此最上善疑者。入此,谓之正疑。”[27]以自己的头脑去思考,以自己的眼睛去观察,将一切放在理性面前进行审视,方能不断地从“疑”到“不疑”,解决疑难,发展和深入自己的认识。
方以智的“疑”,并非是毫无根据地怀疑一切,而是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实证精神基础之上的。他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学术中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他强调,只有脚踏实地、求真务实才能真正有所收获。他在《墨历崖叨问》和《墨历崖警示》强调:“一见知归,此是平素脚踏实地,倘构不上。一心不退,脚踏实地,终保必得。”“发真实心,行真实行,方肯真实;参真实参,方有真实;疑真实疑,方有真实;悟真实悟,始信悟同未悟,始知真实践履。”故他在科学探索中注重实证方法,力纠好空谈、轻实证的弊病:“吾以实事证实理,以后理证前理,有不爽然信者乎?”[28]他强调“核物穷理,毫不可凿空者也”。[29]对于以往的传说,他从不盲目信从,而是力图通过实验、实证的方法来加以验证,例如,他通过实证方法了解到:“日射地上之水,或置镜及放光石,使火照之则光入屋梁”,以此揭穿某些方士的骗术:“今术家使人见光之法,亦暗悬一镜于衣襟或袖口,列灯烛香烟于地……烛照镜光,摇镜则光于壁,或悬猫精与大金刚石,则能见五色光”[30]。在当时科技知识尚未普及的情况下,他以自己的实验结果点破装神弄鬼、故弄玄虚的勾当,这是有积极意义的。确如他在《物理小识·编录缘起》所说:“每有所闻,分条别记,如《山海经》、《白泽图》、张华、李石《博物志》、葛洪《抱朴子》、《本草》,采摭众言,或无征,或试之不验。此贵质测,征其确然者耳”,而这些努力的目的则在于“更精求其故,积变以考之”。他的《通雅》、《物理小识》等著作,正是运用这种实验、实证的典范,书中记录和考证了古今中外关于天文、地理、历数、气象、物理、生理、药理、矿物、植物、动物等自然科学现象和知识,充分反映出他对西方知识和实证精神的吸收和融合。
在这种理性怀疑和实证精神指导下,方以智在学习西方文化时,能够采取一种去粗取精的明智立场。例如,他吸收了传教士宣传的九重天之说中的科学内容,介绍其中关于诸天体运行周期所需时间,同时又驳斥了“宗动天”的神学理论,并列举多种西学著作关于“宗动天”运行周期的不同说法,来证实此说的自相矛盾之谬。这些看法,体现出方以智卓越的批判、怀疑精神。
当然,由于时代和传统的局限,方以智在科学探索活动中,仍然未能脱离笼统、直观的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在对待西学时,他还有着“西学中源说”的陈旧观念。尽管如此,方以智身上所充溢的“穷理极物”、实事求是、兼收并蓄、怀疑实证等科学精神,依然映射出中西科学精神共存并融会的理性之光,弥足珍贵。
收稿日期:2000-12-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