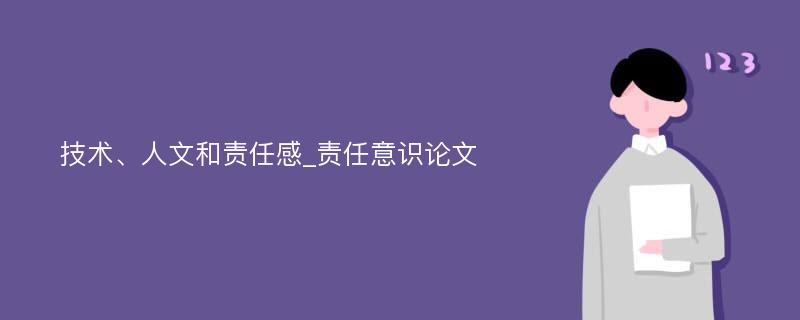
技术、人文与责任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责任感论文,人文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3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80(2008)06-0048-06
责任伦理学家尤纳斯认为,人是唯一能为其行为承担责任的生物,也正因为如此,唯有人才具有责任的理念——责任感或责任意识,这也是人之为人并值得人为自己骄傲的地方。也可以说,责任感是人被规定为人的特性(人性)之一,它和所谓的道德、人格、觉悟等等人文品质联系在一起,通常是人文论域的一个重要话题。
然而,当技术全面影响尤其是现代技术日益深刻影响人的日常生活时,人的责任意识无疑也可以纳入到技术的视域中来考察,甚至可以发现和探索“治疗”一部分人的责任感匮乏或“增强”人的责任意识的“技术途径”。当然,由此也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探讨这些问题,可以开启对技术人文之间关系的新认识,同时也可以以更开阔的视野来看技术与责任问题。
一 责任感:从人文视域到技术视域
责任感是一种优良的人格品质。我们希望多与有责任感的人打交道,也希望自己在别人眼中是有责任感的人。是否有责任感,成为选举领袖、选拔管理者、招聘雇员乃至择偶的标准。从文明发展的角度看,责任感是人的道德素养、社会的民主建设和政治文明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社会发展的一种精神推动。一个民族,如果有许多仁人志士怀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这个民族就更富于进取精神,就更可能走向兴盛和强大;反之则不堪设想:如果人人都缺乏责任感,处处逃避责任,世界将会怎样?
责任感如此重要,也从未被人类自己轻视过。但长期以来,责任感问题只被定性和定位为一个人文问题,责任感被认为只是人文教化的结果。如果公众的责任意识不理想(即责任感匮乏),就会被一些人文学者从“国民性”的高度加以分析。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中就列举了这样的一些特征,如死不认错、喜欢讲大话、空话、假话、谎话,一个民族如果都是这样,会使我们的错误永远不能改正。往往用十个错误来掩饰一个错误,再用一百个错误来掩饰十个错误。甚至一些习惯性表述也体现了这样的不负责任:他说记得小时候,老师向对学生说:“国家的希望在你们身上。”但是现在轮到我们向青年一代说:“你们是国家未来的希望。”这样一代一代把责任推下去,推到什么时候?今天的社会中推诿和不愿意承担责任的现象也比比皆是,如见死不救、见难不助所反映出来的冷漠、麻木,又如经济活动与学术领域中的“假冒伪劣”所反映出来的无自信、无诚信以及无社会责任的担当,此外,更有许多事故和人为的灾难都是由于责任心不强造成的,或最后都能在责任意识上找到根源。总之,社会责任意识淡化,道德责任意识薄弱,即所谓“责任意识危机”,是“道德滑坡”或社会道德危机的直接原因。
责任意识问题的严重性或许使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责任意识假定”:逃避责任有可能是人的天性,或者说是为数不少的人在特定场合下的自我保护性的旨在利己的“本能反应”,因为承担责任就意味着更多的付出(如承担事故的责任,就意味着要受处罚和惩罚),而人通常是更愿意获取而不愿意付出的,尤其是没有获取的付出。这也正是承担责任需要有“勇气”的原因所在。
因此从哲学的意义上人是唯一具有责任感的动物,但从法律和经济的操作层面上,人又是唯一能够千方百计逃避责任的动物,人性中的这种结构性矛盾,使得如何实际地提高人的责任意识成为一个亘古的课题,成为人文教育和道德教化的一项恒久任务。
但是千百年来的人文教化是否使人的责任意识状况有所改善呢?或者说现代人比古代人是否更愿意承担责任了呢?其实我们看到,更善于“算计”的现代人并不一定比过去的人更有责任感。这也表明了人文教化的有限性或并非万能性。
在责任感上要有所进展,就要对传统的观念有所突破,使责任意识从单一的人文视域扩展至技术视域,认识到责任感除了通过人文的途径生成之外,还可以技术性地生成这样来思考责任感现象,可以为改善公众的责任感状况开辟新的通道和路径,也是为技术发挥其积极的社会功能和人文效应扩展空间,同时还是人与社会的发展对技术提出的更高要求,是技术人性化提升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一语境下,技术不仅是人用来改造客观世界的手段,而且也可以充当改造人自己的主观世界的手段,成为人格提升的手段。
技术视域的展现,使技术哲学回应了这样的问题:责任意识如此重要,技术能为其做些什么?而且,也使得技术的责任问题获得了新的含义,甚至意味着一种技术责任观的转型,也是技术伦理的转型。技术与责任问题,是技术伦理的一个重要问题。通常意义上的“技术与责任”论题只谈论科学家与工程师的社会责任和伦理担当。由于责任感问题的普遍性,其视野也应具有开阔性,不仅存在着主体指向技术的责任,而且也有技术反身指向主体的责任,即技术对技术主体的责任感的造就和影响。而且,这种技术主体不仅是发明技术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而且更有使用技术的一般意义上的人。这样才能构成技术与责任之间的双向互动的整体性关系。因此,这样的视域扩展,使得技术与责任可以不只以一种方式来谈论:从人要对技术负责再过渡到人要使技术对改善人的责任感状况负责,人由此而使技术承担一种新的责任:技术性地建构人的责任感。
从“技术责任”到责任感的技术性生成,这一视域中的技术伦理,也是从一种被动性地防御一些伦理问题到主动地寻找和解决一些伦理问题,从被动地限制技术的负面效应和风险到主动性地建构公众的积极的人文品质;从只利用技术解决物质性问题到也利用技术解决精神性问题,这无疑是对技术的更高的人性化要求,是技术走向人文的一种实际操作,也是为走向民主社会所进行的一种“技术性准备”,从而是一种在含义、价值甚至本体论基础等方面都有所突破的“新技术伦理”。
二 本体论基础:技术的责任感之双重效应
人一开始使用技术,技术就对人产生各种影响,其中就包括增强和消解人的责任感的双重影响,这也是技术的所谓“双刃剑”功能的一个方面,正是这个方面构成了技术具有责任意识效应的本体论基础。
历史上的人文思想家们主要看到的是技术消解人的责任感的负面效应,无论是庄子感叹技术使人萌生“机心机事”从而“纯白不备”,还是卢梭声讨技术使人奢靡并削弱勇气从而失去英武,或是马尔库塞批判技术把人变成“单向度”的人,都直接或间接地把技术定性为损害人的责任意识的“祸源”。
其实,更客观地看,和技术的人性效应从总体上具有双重性一样,在责任感效应上也同样如此。
人是在实践中形成的,意味着也是在使用技术的过程中形成的,亦即技术是塑造人的。因此,选择一种技术,不仅是选择一种生活方式,而且是选择一种塑造我们人格的“座架”,也就是在决定我们成其为什么样的人。使用一种技术会形成相应的行为方式和思维习惯,也是拉普所说的技术影响人的心理的过程:对人来说,“技术不仅会产生物理上的作用,同样还会产生感情和精神上的影响。”[1]他认为人既是技术的创造者,同时也是技术的创造物,主体成为客体,目的变成手段,技术的发展已经内在地规定了主体必须依附于客体的倾向,因为技术在设计开始的同时也就把人作为一个考虑的因素。卡莱尔也表达过类似的思想:人“如今不仅外在与物质方面由机器所操纵,内在与精神方面也是如此……这种习惯不但规定了我们的行动模式,也规定了我们的思想与感觉模式。”[2]总之,使用技术的过程,就是人的行为特性形成的过程,也是品格特征乃至人性的形成过程,当然也包括责任意识的形成过程。使用不同的技术或对同一技术的不同使用,可能会产生增强责任感或削弱责任感的不同效应,进一步还可能造就出不同的人:勇于负责、有责任感的人或是逃避责任、缺少责任感的人。
无论从技术的价值负载论还是技术中性论出发,都可以分析出这种双重性。例如,从技术价值负载论出发,可以将技术区分为责任型技术和非责任型技术;从技术中性论出发,则可将技术的应用区分为责任式应用和非责任式应用。
由于技术的价值负载论将技术的“善恶”视为一种内在的属性,认为技术一开始就被制造者设计为有意地造福于人或加害于人,因此也必定会将某一技术是否有责任感效应视为其前置的固有的特性,抑或说一项技术先在地就是用来增强或削弱人的责任意识的。当然,即使我们不同意这种将技术进行这种“先在”的归类的方法,也可以发现现实生活中的技术,在客观上有的主要起到了强化人的责任感的作用,包括一些技术装置强制性地使人被动性地遵守一些规则和纪律,如一些公共场所的排队装置和监控设备,它们可以通过“外在”的束缚和制约来使人避免不负责任的行为,并“习惯成自然”,内化为人的一种“遵纪守法”的观念——一种维护社会正常秩序的底线状态的责任意识。
而有的技术则相反。例如高度自动化的技术就常常造成人的责任感的丧失,像公共场所中电灯的声控开关,久而久之会使人不再有“离开公共场所时随手关灯”的节约能源的习惯,从而也就没有相应的责任意识。可以说,技术的自动化智能化程度越高,能够替代人做的事情越多,就可能越多地使人从需要自己负责的领域中撤离出来,越来越少地需要使用自己的责任感,久而久之,造成人在责任感上的“用进废退”,会逐渐使人失去负责任的欲望和负责任的能力,把一切自己能做的事都交予机器,成为只会享受的受体。或许这也是人文退化的一个方面。由此,高度自动化的技术,更倾向于削弱乃至“剥夺”人的责任感。
技术中性论会认为技术本身并没有什么先在的增强或削弱责任感的本性与意图,之所以会有不同的情况,是因为使用技术的方式不同所导致的不同效果,从总体上这种功能应该是双重性的,或者说需要对具体技术的具体使用进行具体分析。
这方面的事例也比比皆是。例如,人在网络空间中以匿名的方式登陆,也就是使用网络技术时,是更倾向于有责任感还是无责任感,就是依据不同使用方式而产生不同的效果。网络可以使一些人参与到在现实中无法参与的领域,如参政议政,发表对国家大事和社会热点问题的看法,从而成为有责任担当的公民;但网络也可以为有的人不负责任地制造虚假信息提供方便,尤其是利用匿名的方式造谣中伤、发泄私愤等等。同样,对于计算机,如果作为游戏机去使用,会导致网络和虚拟世界沉溺,最后会使人逃避现实、丧失对真实社会的责任感;但作为学习和研究的工具,其对人的信息能力的扩展,则通常会带来促进人去更多地认识世界的责任。这就是同一种技术手段的不同使用产生了不同的责任感效应。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过度依赖性地使用某种技术,有可能造成责任感的流失。例如现在的许多计时计价计数的自动系统,已全面取代人在相应领域中的功能和责任,一旦出错或被质疑有错,通常很难追究到人的责任,一切过错都被推给机器,如银行账目的错误,程控电话计费的差错所引起的客户与相关机构的冲突都常常很难追究到“真正的责任主体”,这类情形或许也可称为“技术使用中的制度设计缺陷”。久而久之,这种有缺陷的技术使用方式,会造成人的相应责任感的流失。
只要使用不当,不仅复杂的技术会剥夺人的责任,甚至简单的技术也会剥夺人的责任,即使是手工工具也会剥夺人使用赤手空拳的责任,从而使这方面的能力退化,这一点早就为卢梭所分析。这也可视为技术异化的表象之一,当技术异化使得人的主体地位丧失时,其附随现象就是责任感的丧失。
技术价值的负载论和中性论的上述看法可以形成互补。正是这两种视界的合成,使我们可以更全面地看待技术的责任意识效应,从而更充分地看到其“双刃剑”的特点。于是,有选择有意识地让技术发挥积极效能,让技术参与人的责任意识的提升,这也是技术走向人文的一种实际操作。具体说就是:使那些可能削弱公众的参与性和责任心的技术受到限制,使那些可以增强公众的参与性和责任心的技术得到更多的应用;对于同一种技术,尽可能责任式地加以使用,避免非责任式地加以使用。通过抑制非责任技术和技术的非责任应用,让技术成为培育优良品性和人格的土壤。
这也是技术伦理学家伦克所倡议的:明智地对待科学技术力量,理性地调节技术的进步,承担扩展的责任,或者说,要仔细谋划发明和使用什么样的技术以及如何去使用技术,尤其要小心使用那些替代人做决定、负责任的技术,那些躲进虚拟世界与逃避现实责任的技术。从扩展的意义上,技术的使用还多方面多层次地间接影响着人的责任感,例如技术对人的情绪和心理状态的影响,就可以延伸到影响人的责任感;甚至对技术负作用的关注扩展到对人类前途和命运的担忧,也会通过“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拯救”的方式来唤醒人的责任感,使用技术过程中的“先污染、后治理”,“先制造、后销毁”也蕴含了一种“由结果反馈的强制性的责任意识”,如此等等。
三 构建责任意识:从传统技术路径到高技术路径
可以说,人使用一种技术的过程中被技术所潜移默化,这是技术影响人的责任感的“传统路径”。随着高新技术的出现,可以期望还将会有新的技术路径参与到这一过程之中,如芯片植入和基因修饰等方式。这种高技术路径使得技术更深刻地介入到人的责任意识的生成和改善过程,这也是技术从改造物质世界到改造人的精神世界的更富价值的延伸。
拿基因修饰来说,一个人的思想或行为模式中如果总有逃避责任的趋向,不排除可能有基因方面的原因。也就是说,喜欢负责与不喜欢负责的人之间,可能有基因差别。这就为从基因层次上改善人的责任意识状况提供了可能性。
阿根廷《民族报》2008年3月30日发表一篇题为“基因可能影响我们的政治态度”的文章,其中所援引的研究和看法可以为上面的“高技术路径”提供某种启发:
美国得克萨斯赖斯大学的政治学家约翰·奥尔福德说:一种最新的观点认为,政治立场主要是由生物学决定的,不受任何劝说的影响。这些思维方式深刻地根植于我们的头脑之中。尝试劝说某人不要成为右派或左派就相当于说服此人相信自己眼睛的颜色不是先天的颜色。对于劝说,我们应当三思而后行。神经学家也认为,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大脑活动模式不同。
奥尔福德2005年发表一篇文章,在文中分析了20年来对行为基因的研究,其中包括大量的关于弗吉尼亚3万对异卵双胞胎的政治观点的数据。此项发表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季刊上的研究表明,同卵双胞胎比异卵双胞胎更有可能对政治问题作出相同的回答,例如,关于是否应征收个人所得税,4/5的同卵双胞胎作出了相同的回答,而异卵双胞胎的比例为2/3。说明回答的内容受基因的影响。
加州大学的政治学专家詹姆斯·富勒认为,如果某人决定在大选当天参加投票,而不留在家中,那么这个决定可能来源于基因。
显而易见,投票的行为具有感情因素。例如,投票人对自己支持的候选人有一定程度的信任。这说明5HTT(5-羟色胺转运体)和MAOA(A型血清素转运体)这两种常被研究的基因可能参与其中。这两种基因参与对血清素的控制,而血清素是一种与信任和社会互动有关的大脑区域中产生影响的神经递质。
这两种基因效能越强的人越善于交际。根据富勒分析,这些人应当更倾向于投票。富勒在《政治学杂志》季刊上发表的研究结果证实了这一点。2 500个美国人的资料显示,那些拥有能够更好地控制神经递质的MAOA基因的人与基因效能较弱的人相比较,前者参加投票的可能性比后者高1.3倍。[3]
政治态度可视为责任感的一种表现,如果基因可能影响我们的政治态度,也就完全影响着我们的责任意识,或者说明责任感来源于基因。如果说“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大脑活动模式不同”,则爱负责任的人与不爱负责任者的神经结构也会不同,而这种不同也可以归咎于基因。于是,提高人的责任感在未来也许可以通过基因修饰的途径。
基因技术手段对于改善责任意识的有效性,只能建立在责任意识具有生物学基础这一事实之上。一定意义上承认责任感的有无强弱具有先天性遗传性,即把责任意识视为不仅是一个远离生物性的“觉悟”问题,而且也是一个与生理条件纠缠在一起的心理问题,生理和心理的纠缠使得心理的改造就可能牵涉到生理的改造,而生理的改造就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是技术性的,甚至心理的改造也可以直接是技术性的。正因为如此,责任感问题的解决才可以诉诸于基因技术手段。
有的人身上责任感的匮乏可能源自身体上的不适感或缺少幸福感,例如,“疾病不仅影响到主体的健康,而且还妨碍他自主能力的完全发挥”[4],当然也可能影响到人的责任感的发挥,因此,通过消除疾病等不适感(及其所导致的消极、颓废、退缩)或增加幸福感(及其相应的积极、乐观、进取心态),无疑也可以提高其责任意识。由于增加幸福感也是可以通过技术手段特别是基因技术手段来达到的[5],因此高技术也可以在这里以间接的方式来提升人的责任意识。
当然也要注意,如果将一切归咎于基因,有可能反而是在推卸责任;人文的视域无疑会极力反对极端的技术视域,反对将责任感全部还原为一种脑内物质或一段基因,否认基因可以完全编码人的责任感。在这里,基因决定论是与技术决定论联系在一起的,将责任意识完全归结为基因问题,也就是将责任意识完全纳入到技术的视域中,从而将责任意识完全归结为一个技术问题,进而,不仅责任意识问题,而且人性问题最终都可能被归结为一个技术问题。于是从完全依赖于基因技术改变人的责任感,到完全依赖于基因技术改变人性,便走向所谓的“生物政治”的立场上,这无疑是用还原论的方法完全消解了责任意识以及人性问题的复杂性。
在这个问题上,显然也需要两种视域的互补:既不能搞极端的基因决定论,也不能认为责任感与基因等生理因素毫无关系,因为至少可以说,一种没有物质载体和生理承托的精神现象(责任意识也是精神现象之一)也是不可能存在的。如果从身心统一观上来看,责任感既是一种主观努力,也是一种生理状态。可以通过改变人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来改变人的责任感,也可以通过改变心境、情绪、性格等来改变责任感。由于责任感具有生理和心理的双重根源,由此可以由技术的和人文的双重方式来加以改变。
通过改变责任感的生理基础来改变责任感,是技术途径之一,此外还有改变人的生活、行为方式来改变责任意识的技术途径,即传统的技术路径。因此在这里还需要处理好这两种路径的关系。两种技术路径通常有外在与内在的关系,传统的技术路径如前面提到的监控技术通常是外在性地影响人的责任感,而高技术路径如基因修饰或芯片植入则是内在地改变人的责任感状况。当然外在可能转化为内在,这就是技术性外在规定的行为成为人的习惯后就转化为一种内在的自觉意识。
四 审慎处理两种责任感的关系
通过传统的人文路径产生的责任感和通过技术路径尤其是高技术路径产生的责任感,成为来源不同的两种责任感,可称之为“人文性责任感”与“技术性责任感”,一种是自然形成的,是社会性教育和影响的结果;一种是人工合成的,是技术性操作的结果。如果两种责任意识可以并存,那么它们会造成人的什么样的不同感受?不同来源的责任感是否会导致不同的责任行为?当责任感可以成为技术性操作与改造的对象后,责任感的本质是否发生了变化?哪一种路径更能从根本上解决责任感的匮乏问题?如此等等,都可能是我们提出两种责任感后可能面临的新问题。
在实施技术手段时,无疑要对其负作用和风险性有充分的估计。所以技术不成熟不完善时决不能推广使用。但一旦技术变得成熟和完善后,如果只需一个小小的技术操作就能彻底解决人的责任意识匮乏的问题,那么通常需要漫长的时日和艰难的教化才能取效的人文手段还有用武之地吗?思想政治教育之类的培养责任意识的传统方式比起简洁快速的(高)技术方式来是不是就显得事倍功半了?历史上的“科学与人生观”的争论此时极可能衍生为“技术能否解决人生观问题”的对峙。从技术与人文相互制约的内在关联上看,责任感问题解决路径上的技术主义和人文主义尤其需要寻求一种平衡与和谐。从原则上,医治人的生理疾病时,通常是(医疗)技术手段失效时我们才主要诉诸人文手段;相反,在解决人的“心理疾病”或精神问题时,通常是人文手段失灵时我们才会诉诸技术手段。因此,对责任感匮乏的“治疗”也是如此。可以认为,即使在将来,高技术路径的这种使用应该遵循的是“优后原则”而不是“优先原则”,而且也需要像生命伦理学为基因治疗提供的要求那样,即使这种高技术的路径可行,也只能限定于“治疗”而非“增强”。
我们还可以认为,无论技术将来如何发达,技术手段也不可能完全取代人文手段。对于责任感匮乏问题的解决,不仅要看到人文手段的有限性,而且也要看到技术手段的有限性。例如,责任感的“内容”问题(如对“谁”负责、不同的场合下以及充当不同的社会角色时负什么样的责任以及负多大的责任等等)就不可能靠基因技术来解决。不仅如此,技术手段还必须受到人文精神的制约,其中之一就是要充分认识技术活动的伦理限制问题。就像对克隆人的争议一样,技术性地治疗责任感的匮乏或增强人的责任意识,其中必须要认真探讨其中是否存在着“不可逾越的伦理障碍”?例如,这样做是否会消解了人的本质、不再把人的人文特质视为一种神圣的存在、而变成可以随意地技术性操作的对象,从而有损人的尊严?还有这样去做必定有一个技术完善即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是否能接受不成熟的技术施加作用的后果?
与此相关联的还有对缺乏责任感的认可与认定问题。增强责任意识的技术手段、尤其是高技术手段无疑是不能滥用的,只能是针对“适用对象”即缺乏责任感的人才能应用。然而,“缺乏责任感”是由自己承认还是社会认定?如果由自己承认,通常情况下谁会自己承认自己没有责任感?如果由社会或专门机构来认定,一是如何保证这种认定的客观性和公正性以及不会用来作为一部分人加害另一部分人的手段?二是如果要进行这种检测是否也需要遵循自愿原则?一旦需要自愿才能被检测,则又回到前面的问题:谁会承认自己的责任感有问题从而去接受这种检测呢?可见,一定意义上“认可”比“施治”更难,而“认可”问题就是个社会问题,更为根本则是个“自我认识”的人文问题。这种“自我认识”的人文障碍是否也会成为实施该项技术的“难以逾越”的鸿沟呢?
还需要“超前”思考的问题,就是通过技术性治疗和增强后,是否有可能导致总量上的“责任感过剩”?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负责任”也有一个适度发挥的问题,不分与境地时时处处去“体现”强烈的责任感,有可能干涉别人的责任,还可能妨碍他人的自由,如家长对孩子的过强的“责任感”从而无时不在的“管教”就常常导致孩子的正常成长受到不良影响。强国也经常是以“对国际事务负责”的名义去干涉弱国的内政。所以不能一概而论地说责任感越强越好,否则也会因“我要负责”而爆发额外的冲突。从社会分工的角度,也需要承担不同社会角色的人在责任感的类型和强弱上有所不同,如果都是“强责任感”类型的人,反而形不成和谐的群体。而技术性解决方案是否会考虑到这些个性化的要求,是否会因为对责任感的基因修饰而“正常化”后也“齐一化”?由于人人都有“充沛的”的责任感而变得“责任感过剩”,从而处处都是“好事者”,使社会反而不得安宁?因此,无论是一个群体,还是整个社会,还需要有一种合理的“责任生态”,其中有的是强责任,有的是弱责任,甚至有的在某些场合下是无责任;同时还要避免责任意识上的“两级分化”,尤其是改变社会弱势群体即使有责任感也无责可负的状况,才能使责任的社会价值得到正常的体现。而所有这些,都呼唤着责任感问题的“综合治理”,那就是人文手段和技术手段的“互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