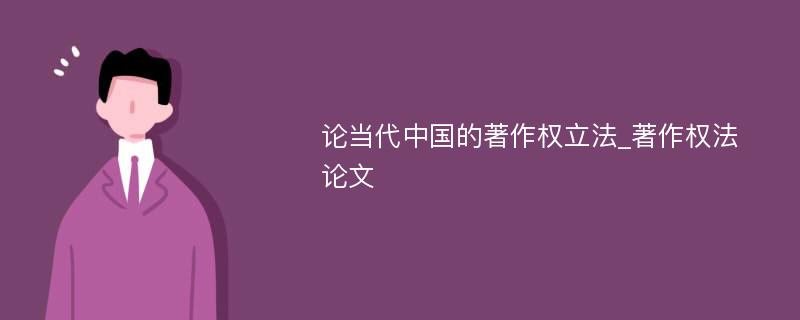
近代中国著作权立法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著作权论文,近代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现有史料来看,我国著作权保护观念在宋代就已经产生。但由于统治者长期奉行“重农抑商”的传统政策,严重摧残和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以致著作权保护长期停留在原始、简陋的保护水平上,最终未能孕育出近代无形产权的观念,也无法转化为近代著作权保护制度。直至1910年《大清著作权律》的颁布,我国才开始了近代著作权保护的历史,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才逐渐建立起较完备的近代著作权法律制度。
一
(一)1910年《大清著作权律》
鸦片战争后,随着现代印刷术的流传,国内新式出版业获得了极大发展,也推动了科技、文化事业的发展和繁荣,大量西方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著作被译介到中国,既产生了众多的出版商、著作者、译者,为清末著作权立法提供了必要的社会空间,同时也使西方版权等法律观念、法律思想传入中国,国人的版权保护意识逐渐增强,版权纠纷也日益增多,如文明书局与北洋官报局版权纠纷案。但因无相关版权法规可依,版权纠纷往往难以诉讼,因而一批有识之士不断呼吁,要求实行版权立法,保护“著、述、译、纂”者的权利[1]。在这种情形下,清政府也逐步认识到“往往有殚毕生心力著成品物发行未久,翻制已多,是著作者尚未偿劳,而剽窃者反获利,殊非所以奖励学术之道”[2]。与此同时,清政府也面临着日、美等列强提出的版权要求压力。内外交困中,清政府终以“文明进步惟恃智识之交通,学术昌明端赖法律之保护”[2]为由,于1910年颁布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著作权法——《大清著作权律》。
《大清著作权律》共5章55条。从其编纂体例和内容来看,该律是中西合璧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历史局限性。这主要表现在:
一方面,《大清著作权律》吸收了大量欧美法律观念,律条杂抄众国。该律移植了日本的“著作权”法律用语,名称使用“著作权”。但受英美法的影响,仍将著作权界定为“专有重制之利益者”,强调的是出版权和发行权,仅授予著作者防止他人翻印或仿制其作品的权利(见该律第1条)。而对表演权、翻译权等邻接权利未作规定;对作者的署名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等人身权利仅以“禁例”形式间接规定;对著作权的取得则参照英国《安娜法》实行注册制度(见该律第4及第11条)。但注册机构则参照日本法,不归司法官厅,而属行政官厅民政部(注:笔者认为,注册制度除为参照英国法的结果外,与晚清当局通过注册对著作物审查,从而达到禁锢人民言论的意图有关。这一立法制度对后世著作权立法产生了重要影响,如1928年国民政府颁布的著作权法就明文规定,对“显违党义者”、“其他经法律规定禁止发行者”不予注册。)。对著作权的保护期限又参照了德国、奥地利、日本的著作权法,规定作者终身及死后30年。对著作权争讼时效虽规定了2年,但却未规定起算方法,等等。
另一方面,由于封建官僚体制没有改变,因而在著作权注册呈式、继续呈式,以及著作权立案、侵权处罚中保留了不少封建习俗的痕迹。如著作权的呈请注册呈式、继续呈式和立案呈式,使用的用语是“窃某人”、“伏乞”;当事人除签名外,还需画押等。
总之,《大清著作权律》是杂抄众国,驳杂不精,没有真正形成著作权体系。其颁布后未及实施,便随着清政府的灭亡而成为废纸。但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著作权法,它吸收了先进的西方文化,顺应了世界著作权立法潮流,开启了我国著作权立法的先河,对后世著作权立法和观念的确立产生了重大影响,也为民国时期的著作权立法积累了一定经验。
(二)1915年《北洋政府著作权法》
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中华民国成立。但新的社会秩序结构并没有随着新政权的诞生而瞬时建立。因此,民国初年,凡涉及版权的争议仍是依照《大清著作权律》处理。但这毕竟是权宜之计。随着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传播,人们版权保护意识日渐提高,国内版权纠纷以及中外版权纠纷迭起。如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的初等小学新国文、新算术各书在全国范围内被盗印、美国经恩公司控商务印书馆翻印出版《欧洲通史》案、英商伊文思书馆控上海商务印书馆案等[3](P178-192)。而《大清著作权律》对侵犯版权行为的处置以及对外国人著作权的保护并不十分得力。在这一情形下,1913年6月,美国要求与中国建立中美双边版权同盟,以超越原有的商约版权保护条款。这引起了国内一些出版商的反对,也引发了一场关于是否应加入版权同盟的论争。
在纠纷和论争的压力下,北洋政府于1915年颁布了一部《北洋政府著作权法》。该法共5章45条。从其编纂体例和内容来看,该法是在《大清著作权律》基础上增删修改而成,但与《大清著作权律》相比有所发展变化:
第一,在编纂体例和结构上,《北洋政府著作权法》首先将《大清著作权律》的“章、节、条”结构删减为“章、条”结构,条文由原来的55条减为45条,比《大清著作权律》更为简洁。其次,在体例上对《大清著作权律》作了一些删改,如将《大清著作权律》“通则”改为“总纲”;“权利期间”改为“著作人之权利”;“禁例”改为“著作权之侵害”、“罚例”改为“罚则”等。因此,在体例结构上,笔者认为《北洋政府著作权法》比《大清著作权律》更为合理。
第二,在内容上,《北洋政府著作权法》首先将《大清著作权律》中有关注册程序的规定以“教令”形式另行规定。其次,扩大了著作物的保护范围,将文书讲义演述、乐谱戏曲均列入条文之中,并明确了著作权人有转让著作权的权利。再次,虽与《大清著作权律》一样实行注册取得著作权制度。但《北洋政府著作权法》不是直接确认这一制度,而是以侵犯著作权行为发生时著作权人能否提起诉讼或能否对抗第三人的间接形式加以规定(见该法第25、26条)。此外,《北洋政府著作权法》以“著作权之侵害”的形式确认了著作权人的署名权、作品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等人身权利,不同于《大清著作权律》的“禁例”的形式(注:笔者认为“禁例”形式反映了封建王朝的强权心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国资产阶级主张的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之自由以及有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等民权思想。
由上可见,产生于民国初年的《北洋政府著作权法》无论是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或多或少体现了资产阶级民权精神,进一步清除了封建法律的痕迹,顺应了当时世界著作权立法的趋势,为1928年《国民政府著作权法》的制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中国近代著作权立法史上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历史作用。
当然,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其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如依然没有给予外国人作品著作权保护;虽将乐谱戏曲列入著作权保护范围,但依然没有规定表演权等相关邻接权利;虽明确了诉讼时效的起算,但是以“注册之日起,二年为限”。将注册与诉讼时效扯在一起,“诚难索解”[4](P418)等等。
(三)1928年《国民政府著作权法》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民国初年军阀混战和地方割据的局面结束了。国民政府为规范内部事务,稳定长期处于混乱状态的社会秩序,巩固其统治基础,也为应付西方列强在议决撤消在华领事裁判权之前对我国司法状况进行的调查,迅速开始了新的法律体系的建立过程。1928年5月14日国民政府颁布了《中华民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1928年著作权法”)及其施行细则,并于同日实施。
该法共40条,尽管与《北洋政府著作权法》一脉相承,但内容上还是呈现出不同特点:
第一,首次给予外国人作品著作权保护。开埠以来,中外版权纠纷一直困扰着近代中国政府,从晚清到北洋政府,基于保守意识,在著作权法中均未确认外国人作品著作权。至国民政府时期,在西方列强的压力和国内进步人士的呼吁下,国民政府首次给予外国人作品著作权保护。尽管这种保护不是在著作权法中而是在实施细则中界定,内容上也不充分(注:1928年《著作权法》没有明确规定外国作品著作权,但同日颁布实施的实施细则却予以规范。不过有前提条件:一是仅对与中国实行了对等原则的国家的国民的作品予以保护;其二是外国人作品必须是“专供中国人应用”的作品,并且只享有重制权,无翻译权(见该细则第14条)。)。但它毕竟迈出了历史性第一步,具有继往开来的历史意义。
第二,在著作权权利内容上,1928年《著作权法》首次在“重制”内容之外,就乐谱、戏剧作品增设了公开演奏或排演之权,使自《大清著作权律》确立的“著作权”体系名副其实(见该法第2条)。
第三,与《北洋著作权法》一样,实行注册取得著作权制度。但不同的是,《北洋著作权法》是以注册之日起算著作权之年限,其“注册之请求与否可听人民之自由”[3](P142)。而1928年《著作权法》是以最初发行之日起算著作权年限。将发行与著作权起算联结起来,使得尚“可听人民之自由”的注册变成强制注册。因为依据出版法的规定,著作物出版发行必须呈报获得发行许可,否则不仅不能发行,还要受违反之处罚。而著作物不能发行也就无从计算著作权年限。与此同时,1928年《著作权法》也明文规定:显违党义者或其他经法律规定禁止发行者不得注册;大学之教科图书未经大学院审查前不予注册。显而易见,这是国民政府强化其一党专政的结果。
总的来说,1928年《著作权法》及其实施细则吸取了《大清著作权律》和《北洋著作权法》的立法经验,并趋附世界著作权立法潮流,它的颁布和实施标志着我国近代著作权法律制度正式形成。
之后,随着《中华民国民法》的颁布实施,民法债编中也纳入了有关出版与著作权的内容,涉及的条文有13条之多。同时为解决法律适用的疑难,司法院自1928~1937年间也发布了至少17条适用著作权法及其实施细则的疑义令[3](P238-251)。一套以《著作权法》为主体,辅之以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比较系统、完备的著作权法律体系由此成型。此后,该《著作权法》几经修正,一直被台湾地区适用到1985年。1985年,台湾地区在美国普惠制贸易待遇压力下对著作权法进行了一次规模比较大的修订,将强制注册改为任意注册,采用著作权自动取得原则,登记注册仅为著作权转移时对抗第三人的条件(见该法第16条)。作品范围扩大到计算机程序、建筑及工程设计图形著作等,逐步摆脱了1928年《著作权法》的模式,日渐与国际接轨。
二
综上可见,我国近代著作权立法历经了一个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从其风雨飘摇的20多年的立法过程中,可窥见近代著作权立法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在立法动因上,近代著作权立法一直是在外力的催化下发生的,是一种“被动式”立法,并且贯穿始终。众所周知,晚清修律是在内外交困下进行的。与宪政、民律、刑律等法律的修订相比,《大清著作权律》的仓促出台,除时局危压下社会各界人士的吁请和稳定自身统治所需外,最主要的原因是外力逼迫所致。自《大清著作权律》始,我国近代发生的每一次著作权法的修订几乎都与外力有关,是清政府为了履行20世纪初期与西方列强签订的若干不平等条约的规定而起草制定的,其被动修订的色彩更浓一些。
第二,在著作权取得制度上,近代著作权立法一直实行注册原则,直至1985年台湾对著作权法的大规模修正,注册原则才被废弃。诚如前文中所述,近代著作权立法实行注册取得著作权制度,既有参照英美法的因素,但更多的是因为通过对著作物的注册审查,可以限制著作权人的正当权益,为政府控制人民的思想、言论打开缺口。这从清政府修订报律、印刷专律和著作权律时一部分大臣的上书中可以看出。1903年《苏报》案后,清政府中的许多人意识到控制舆论与稳固统治的关系,他们希望政府“不可不亟为防范之计”[5](P1677-1678)。而“查东西洋各国所出各报,每经政府核明,始行刊布,其于谚议泄漏,亦皆悬为禁律,中国未有报律,各国传闻之词,既多失实,甚至邪说肆行,大为风俗人心之害”[5](P276)。因此纷纷上书或发表言论,建议政府取寓保护于取缔政策。不言而喻,注册取得著作权制度正是这一政策的体现。此后,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著作权立法一直沿袭这一立法制度。1928年国民政府在著作权立法中更是赤裸裸地宣示:显违党义和其他法律禁止发行的著作物不得注册。
第三,近代著作权立法历经了兼采二系到融入大陆法系的发展过程。清末在移植西方国家著作权法律制度时,虽与移植其他民商法律一样,主要是以日、德两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的著作权法为主要移植对象,但由于版权概念最早源于英国,并且英国诞生了世界历史上第一部著作权法《安娜法》。因此,清末著作权立法不同程度上还是受到了英美法系的影响。如前文中所述的只授予著作人重制权、注册取得著作权制度等,都能找到《安娜法》的痕迹。至1928年《中华民国著作权法》才开始增设表演权,真正形成大陆法系的著作权法律体系。
第四,近代著作权立法对侵犯著作权行为的惩罚力度经历了由弱渐强的发展过程。民国初期,一方面受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影响,著作权属个人私权;另一方面,也出于急需发展新文化的国情考虑,近代著作权立法对翻印、仿制以及其他侵害他人著作权行为,都只处以罚金。二战以后,凯恩斯主义盛行,个人权利受到限制,法律的发展出现了社会化的倾向。受此影响,1944年国民政府修正《著作权法》时首次对侵害他人著作权的行为严重者处以监禁,并处罚金,加强了对侵害著作权行为的惩罚力度(见该法第30条)。
总之,中国近代著作权立法的过程向人们表明:法律近代化不仅仅是内部土壤的培植,也需要外部力量的不断催化,才能得以顺利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