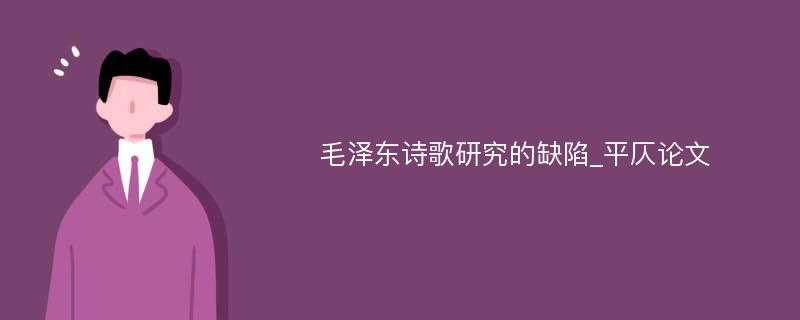
毛泽东诗词研究领域的缺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研究领域论文,诗词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从毛泽东诗词于1957年《诗刊》创刊号集中发表以来,近半个世纪中,各种注释、评论(包括文学史著作)多不胜数,全是褒词。唯一加以贬抑的毛泽东本人,但他的自贬从未引起评家注意;即使注意到了,也必定视之为“伟大的谦虚”而忽略过去。这在“左”风肆虐、个人迷信盛行的年代不足为奇。奇怪的是,当两个“凡是”早经纠正,唯实的学风重获提倡后,尽管毛泽东诗词又多了几种版本,新的注释、评论也不断出现,却仍然无人重视毛泽东的自我评价(也含有他对别人如陈毅的诗的评价)。究其原因,不外二端;一是缺乏诗词修养,根本不懂毛泽东说的一些内行话;二是虽有修养,但有余悸,于是惯性使然地继续“为尊者讳”,而不管“尊者”自身是否讳言。
这实在是毛泽东诗词研究领域的一大缺损,因为毛泽东是懂诗的;他的自评真诚直率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语气的谦抑并没有掩盖一些重要的见解。从某种角度说,正是毛泽东本人对他的诗词作出了最朴素最贴切的评价。
毛泽东的自评大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总体性的评价;二是对具体作品的说明。前者以致陈毅的信为代表,在致臧克家、致胡乔木的信中也略有涉及。后者则见于他对诗词所作的批语、解释以及致李淑一、致周世钊的信。他的自贬主要体现在总体性评价中;特别是在1965年7月21日致陈毅的信中说了这样一段话——
你叫我改诗,我不能改。因我对五言律,从来没有学习过,也没有发表过一首五言律。你的大作,大气磅礴。只是在字面上(形式上)感觉于律诗稍有未合。因律诗要讲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我看你于此道,同我一样,还未入门。我偶尔写过几首七律,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如同你会写自由诗一样,我则对于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剑英喜七律,董老善五律,你要学律诗,可向他们请教。
1978年1月此信首次于《诗刊》刊出,跟着就出现一批谈体会的文章,但对上引这段话都好像视而不见,避而不谈。那时周扬刚刚复出,在海运仓总参招待所的礼堂作报告。我恰好在京,便去旁听。记得他也曾谈这封信,从《诗经》的比兴手法一直谈到别林斯基有关形象思维的论述,然而对上述引文也是只字不提。迄今为止,我没有看到一篇文章对这段话加以分析。难道它真的没有研究价值么?我看不然。事实上它从文体、格律的角度明确地表述了作者的一些基本见解;他的自评、自贬正是由此生发出来。或者也可以说,在他的自评、自贬中包含了对于文体、格律的基本见解。
首先,毛泽东将诗的内容与形式作了区分,认为内容再好,再有气势,如果不讲平仄,就不能算是律诗。这是一句常识性的话,也可以说是对陈毅诗作的实事求是的评价。陈毅很有才华,且富于诗人的激情,但不精通格律。只须翻开他的诗词选,就会发现多数诗词都是不讲平仄的。甚至著名的《梅岭三章》,其手稿的平仄也不符合诗律。这在毛泽东看来,就是“还未入门”。有趣的是,多年来论及陈毅诗词的文章不少,却从未有人引用毛泽东的这句评语。我想多半是评论者本身也不知平仄为何物,当然难以发表意见了。
现在的疑问是,毛泽东是讲究平仄的,他替陈毅修改《西行》,主要是推敲平仄,使之符合五言律的格律要求,那么,他又为什么要自贬,说“我看你于此道,同我一样,还未入门”呢?这里可能有两方面的因由。一方面是为了使语气显得轻松、和缓,因为“还未入门”是一句很重的话,等于从诗律的角度对陈诗作了否定,而有了这句“同我一样”,顿时化重为轻。另一方面则含有对自己的诗作尤其是五律的不满。毛泽东写过五律,但生前从未发表过。在身后出版的诗集中,收有五律四首,其中格律较严整的是《挽戴安澜将军》和《看山》,虽然前者第七句出现三仄声,后者第三句失粘,但这类微疵在前人诗中多有,不足为病。至于《张冠道中》、《喜闻捷报》则错得较多,可以说是“不讲平仄”的了。应当指出的是,毛泽东自己对这些平仄上的毛病是一清二楚的。《张冠道中》、《喜闻捷报》均作于1947年戎马倥偬之际,诗兴突来,遂无暇在格律上细予斟酌。如果有充裕的时间和兴趣,他大概也能像替陈毅改诗那样,把这几首五律改得珠圆玉润,毫无瑕疵。只是他后来似乎已失去反复推敲这些诗的兴趣,也无意公开发表了。
写到这里,一个新的问题便自然出现:毛泽东的不少词也作于戎马倥偬之际,如他自己所说,是“在马背上哼成的”,可是都很符合词律,没有平仄上的毛病,这又如何解释呢?
其实,毛泽东在上引那段话中已经作出回答,即他认为诗(狭义的)与词、五律与七律具有不同的文体特征;词人不一定是诗人,诗人也不一定是词人;诗人对各种诗体往往有所偏爱,不一定都擅长。我认为这一见解完全符合文学史的实际。譬如宋朝的二晏、柳永、周邦彦、李清照、辛弃疾、姜夔等等都只是词人,而非诗人;明朝则276年间一个有影响的词人都未出现。古代也有些人是兼擅诗词的,但像苏轼那样成功者不多。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便两次提到“欧(阳修)秦(观)之诗远不如词”,并指出原因在于“其写之于诗者,不若写之于词者之真也”。
从这样的见解出发,毛泽东把自己定位为词人,只是语气谦逊,说“我则对于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事实上他的词除了像许多评论文章指出的那样,在思想艺术上有新的开拓,某些作品如《沁园春·雪》可谓震古铄今外,就是在形式(格律)的把握方面,也进入了自由的境地。因为他喜爱长短句,许多词牌都烂熟于心,所以即使在马上吟咏,也自然合律,不会出错。这也不是毛泽东独具的才能,但凡在词的格律上下过功夫、有较多创作实践的人,都不难达到这种境界。从目前发表的毛泽东的词作来看,没有一首是“不讲平仄”的。有时在用韵、平仄(包括将拗句改为律句)方面与词谱的规定略有出入,那往往别具匠心,并非无知所致。懂格律者的变通与不懂格律者的乱写不可相提并论。譬如韵脚方面,《蝶恋花·答李淑一》一词二韵,有违常规,而毛泽东对此很清楚,其所以不改,是不想损害原有的诗意,如他自己所说:“上下两韵不可改,只得任之。”又按词律规定,入声不能与上去声通押,而《如梦令·元旦》中,“路隘林深苔滑”一句偏偏以入声字“滑”与“化”、“下”、“画”等去声字相押,读来并不难听,这是一个创造。平仄方面,《沁园春·雪》起首三句都按词谱采用平收;而《沁园春·长沙》第二句“湘江北去”却抛开词谱,采用仄收,这同样是个创造,不仅考虑到诗意的连贯,而且声调上形成仄仄平平(“独立寒秋”)与平平仄仄的对比,十分悦耳。此外,前人填“贺新郎”,喜作一二句七言拗句,而毛泽东不论早年还是晚年所作《贺新郎》,均改拗句为律句,这就更是声律上的着意追求了。
相形之下,毛泽东对自己所作诗的评价要低得多,不但对五律予以否定,而且对七律也表示一首都不满意。我们当然不能据此认为他的七律都作得不好。事实上在谈到具体作品时,他于谦词中还是流露了对一些诗句的自得之情。譬如对《七律二首·送瘟神》,他一方面在该诗《后记》中谦虚地称之为“宣传诗”、“招贴画”,另一方面又在致周世钊的信中对“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详加解释,显然对这一以地球的自转和公转为依据、堪称前无古人的用典是满意和得意的。又如他创作《到韶山》和《登庐山》后,在致胡乔木的信中写道:“主题虽好,诗意无多,只有几句稍好一些的,例如‘云横九派浮黄鹤’之类。”可谓于自贬中略含自褒。更值得注意的是他接下来说的一句话——
诗难,不易写,经历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
从该信的上下文可以看出,这里所说的“诗”,也是狭义的,不包括词在内。只说“诗难”而不说“词难”,说明他写诗写得比较艰辛。而两次请胡乔木把诗稿送交郭沫若“审改”,则表现出他的认真。最有意思的是“冷暖自知”一句。只须将汗牛充栋的评介文章与毛泽东三言两语的自评放在一起,立刻就能体会到这句话的份量。毛泽东的自评都说得很实在,擅长或不擅长,好或不好,了了分明。而评介文章却总是一派恭维:词好,诗也好;讲平仄的好,不讲平仄的也好;首首都好,句句都好。这种态度,不但使评论失去标准,变得庸俗,而且难免对某些诗句作出似是而非的诠释。行文至此,我想起了治学严谨、受人尊敬的老编辑周振甫。他的《毛泽东诗词欣赏》,着眼于典故的溯源和修辞的分析,有一定的特色和价值;然而在只褒不贬方面他也未能免俗,有时为了“为尊者讳”,甚至不惜作出十分荒谬的解释。
譬如《七律·有所思》作于1966年6月,通篇表现的是毛泽东在“文革”初期的所思所想。经历过十年浩劫的人一读就能感受到当年那种紧张的政治斗争气氛。以首句“正是神都有事时”为例,显然指的是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后,在北京许多学校出现的揪斗校长、教师的浪潮,以及刘少奇等决定派工作组到校协助领导运动,中央文革乘机进行挑拨、捣乱等事态。而毛泽东对当时形势的看法则是完全错误的。就在写完这首诗后不久,他就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把矛头直接指向了刘少奇。以周振甫的阅历,对诗的背景和含义不可能看不出来,但他却故作糊涂地这样写道:“在首都有什么事呢?作者要把首都建设成社会主义的首都,当然有事做。”对全首诗的解释也都是这种口气。看得出老先生笔下仍有余悸,但他忘了,对“文革”和毛泽东晚年错误的结论早已写进《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他装糊涂,能将学问做明白吗?
平实地说,毛泽东的诗不如词。他的诗也有相当的才气和功底,这从他青年时期写的《五古·挽易昌陶》、《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以及“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等诗句已可看出。他晚年随口替乔冠华续打油诗:“莫道敝人功业小,北京卖报赚钱多。”虽是玩笑,但平仄丝毫不错,显示出扎实的基本功。尽管如此,他的诗在总体水平上仍然不如词。平仄只是近体诗的一个起码要求,除此之外,诗还有各种讲究。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洗炼,即用最经济的手段来表达最丰富的内涵;故而名家作诗,从用字、用典到句式、对仗总是尽量避免“合掌”。杜甫的七律,甚至连出句末尾的那个仄声字都要求上、去、入三声俱全,目的就是为了避免单调、重复。毛泽东当然明白这个道理,但知易行难,实际做得不够好,——可能这也是他对所作律诗不满意的原因之下。下面聊举二例:
《七律·长征》是影响很大的一首诗。其颈联出句原为“金沙浪拍悬崖暖”,后改为“金沙水拍云崖暖”。“云”和“铁”都是名词,“悬”却是动词,用“云崖暖”对“铁索寒”较初稿要工稳得多,所以这个字改得好。至于易“浪”为“水”,则是不想重字,如他自己所说:“改浪拍为水拍,这是一位不相识的朋友建议改的,他说不要一篇内有两个浪字,是可以的。”我不知道提建议的那位朋友是谁,但他似乎思虑欠周。他只想到“五岭逶迤腾细浪”而忘了“万水千山只等闲”,当他为避免“两个浪字”而把“浪拍”改掉时,诗中却出现了两个“水”字,真是顾此失彼。
律诗的中间两联除要求词性、平仄形成对仗外,在表达的意思上也是忌讳重复的。在毛泽东的七律中,凡属较好的对仗,其对句都能在出句的基础上另翻一层新意。然而也有不尽如人意处,如“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七律·冬云》),据说上句是反帝,下句是反修;但就字面而论,两句的意思是全然重复的:“英雄”与“豪杰”雷同,“虎豹”与“熊罴”合掌。无论如何,这不能算是很成功的句子。
毛泽东对所作诗词的不同评价,还表现在愿否公开发表上。现在出版的诗词集,将他的作品分为正编和副编。副编所收25首,大都是他不愿发表的作品。其中词只有5首,另外20首均为诗。不愿发表,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这个比例还是足以说明他对长短句的满意程度远远超过了诗。
最后还想说的是,对副编中某些根据抄件复印的作品是否有错讹,我是颇感怀疑的,因为有几首诗在用词、平仄方面错得莫名其妙,简直不像是毛泽东的水平了。当然我并不清楚实情,但是不久前读报发现的另一件事使我深感由不懂格律的人来抄录诗词是多么容易出错。那是在1月30日的《光明日报》上,刊出了钟敬文口述的遗稿《百岁寄语》,记录者穆立立系诗人穆木天的女儿(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应该说,散文部分整理得不错。遗憾的是,她显然不懂格律,在记录两首七绝时,均有失误。第一首错得很可笑:竟将第二句移为末句,不但平仄不谐,连意思也欠通了。其正确的排列应为:“勇以捐躯六十春,灵山今日吊忠魂。抚碑心事如泉涌,无计从君一叙论。”(“论”读平声)第二首第二句“此事旁人笑如痴”的“如”字也有误,盖“仄仄平平仄仄平”,这里需要一个仄声字。至于该版的那位责任编辑,平日文笔倒也不错,可惜同样不具备判别平仄的能力,所以她对这类错误也根本看不出来。
既然如此,由毛泽东身边一些并不懂诗的工作人员抄录的诗词,难道就不会出错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