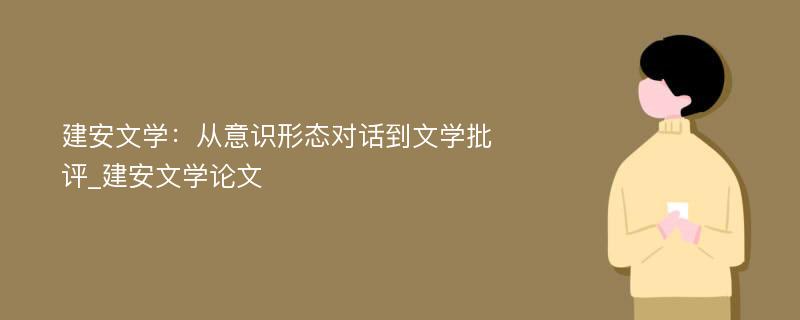
建安文学:从思想对话到文学批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建安论文,文学批评论文,思想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建安文学批评是建安文学中的亮点。人们常说建安年代是文学的自觉年代,主要是指这一时代不仅产生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而且形成了自觉地对于这些作品进行反思与批评的理论作品与书信品评。中国文学批评重视思想对话的传统在这一时期的文学批评实践中获得彰显,并衣被后世,影响至大。
从历史纪年来说,建安本是东汉末年献帝刘协的年号,从公元196至220年,共计25年,但是这一时期却是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年代,以曹氏集团为代表的文学集团开一代风气。当时,帝王与文士的关系,由秦汉大一统封建王朝的专制君臣关系,变为相对随和的上下关系和友伦关系,先秦百家争鸣的局面得以在一定程度上复现,各类人物之间的各种思想对话能够不拘一格,建安年代重要的文艺批评典籍与论述,许多是在思想对话的语境下产生的,比如曹丕、曹植与建安文士讨论文学问题的重要书信,都是在平等对话的情形下形成的,曹丕《典论·论文》也是在整个对话氛围中酿成的。从文学批评的文体角度来说,曹氏父子与建安文士的书信体首开风气。在此之前,西汉司马迁的《报任安书》采用书信方式吐露心曲,提出了自己发愤著书的写作观念,但是集中而大规模地用书信来对话,共同探讨文学问题,却是在汉末建安年代。
建安时代文士与帝王的思想对话,实际上是东汉末年士大夫清流与帝王、宦官进行思想抗衡传统的延续,是所谓“党锢之祸”中士人独立人格与精神的复兴。这种对话彰显了和而不同的中国思想文化与文学批评互动机制,颇令人关注。因此,从对话的角度去探讨当时的文艺批评,是把握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特点的重要门径。
汉末建安年代是一个天崩地坼的年代,长期积累的各种矛盾开始总爆发。
建安文学的慷慨多气,就是指曹氏父子和建安文人出于人文情怀,渴望建功立业的精神气概。当时,曹操所代表的曹魏在三国中最有实力,延揽的文士最多。东汉专制帝王的统治与威权已不复存在,汉献帝只是曹操的傀儡,没有实权,到了曹丕继位后,自然而然地在时机成熟时将其废除。在中国历史上,建安文学时代是帝王与文士关系较为融洽的时代。建安文学一般可以分成前后期,前期是指建安十三年至二十四年(208~219),后期指曹丕称帝后的黄初元年至太和六年(220~232)。前期为曹操集团壮大过程中文士们聚集于邺下的阶段;后期则是由曹植独树一帜,开创建安文学向正始文学转变的时期。前期是建安文学鼎盛的时期,钟嵘《诗品序》称道当时的文士之盛曰:“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尔后陵迟衰微,迄于有晋。”钟嵘指出建安时期的文士聚集有百人之众,彬彬之盛,为史所无。
造成这种氛围与环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曹氏父子的首开风气。他们打破了两汉专制政权帝王与文士之间森严的壁垒,冲决礼教的网罗。曹操本人就是一位敢于打破传统礼教,崇尚通脱的人物。《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书》曰:“是以创造大业,文武并施,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这里记载曹操是一位文武兼备的英雄人物,文学创作是他当时政治与军事生活中的有机构成部分。同时,雅性节俭,不好华丽,对待部下也比较通脱,他爱好文学,深知文学创作之契机,由此对于文士的心机与短长很是了解。这也影响到他对于文士的恩威并重。
曹操的两个儿子曹丕与曹植也如乃父作风。特别是曹植不拘小节,结交文士,颇有战国时的养士之风,为此而受到曹操、曹丕的怀疑和猜忌,丢掉了太子的位置。《三国志·魏书·王粲传》中注引《魏略》,记载了曹植与著名文士邯郸淳的交往趣闻:
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与谈。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遂科头拍袒,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讫,谓淳曰:“邯郸生何如邪?”于是乃更著衣帻,整仪容,与淳评说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区别之意,然后论羲皇以来贤圣名臣烈士优劣之差,次颂古今文章赋诔及当官政事宜所先后,又论用武行兵倚伏之势。乃命厨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无与伉者。及暮,淳归,对其所知叹植之材,谓之“天人”。
可见曹植对于看重的文士是很欣赏的,也不摆什么架子。在交往中可以坦诚地进行对话与讨论,从而心心相印,视为知己。在对话中,上天入地,旁及文章写作,这与两汉时期高高在上的帝王与匍匐在下的文士关系是大不相同的。汉代帝王与文士论文,往往采用的是诏答体,臣下则诚惶诚恐,除了附和帝王外不敢置一词,比如汉明帝与班固的诏答论司马迁就是一例。
这种宽松气氛的一个重要表现,便是曹氏父子与文士的书信往来成为思想对话与文艺批评的一种绝好方式。其中曹植与杨修的书信往来,以及曹丕与吴质的书信交往便是典型。在建安之前,帝王与文士只有章奏往来,绝无书信来往。通过书信交流文艺与人生问题,是建安时期帝王与文士关系改善的重要标志,在中国古代文艺批评史上起着开风气之先的作用,同时拓展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文体样式,书札与尺牍体成为人们进行批评的常见文体,它轻松自如,平等交谈,令人解颐会心。关于这一点,《三国志·魏书·陈思王传》注引《典略》曾加以记载:
杨修字德祖,太尉彪子也。谦恭才博。建安中,举孝廉,除郎中,丞相请署仓曹属主簿。是时,军国多事,修总知外内,事皆称意。自魏太子已下,并争与交好。又是时临菑侯植以才捷爱幸,来意投修,数与修书,书曰:“数日不见,思子为劳;想同之也。仆少好词赋,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幹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大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也。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今尽集兹国矣。然此数子,犹不能飞翰绝迹,一举千里也。”
从曹植写给杨修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出,汉末以来,一些原来栖居高位的贵胄散到各个统治集团之中,后来大多汇集到曹氏集团。曹植看重杨修的文才,与杨修深相交纳。曹植在这封给杨修的信中,回顾了建安文士为曹氏所笼络的情况。那些名士在动乱中虽然失却了东汉大一统帝国的庇护,但是却也因此而振作一时,各擅其长,“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也”,这几句写出了他们意气奋发之情状,也可见当时文士与帝王人物相处的情形。刘勰《文心雕龙》对此种情形加以评价:
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仲宣委质于汉南,孔璋归命于河北,伟长从宦于青土,公幹徇质于海隅,德琏综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乐。文蔚、休伯之俦,于叔、德祖之侣,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时序》)
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辞少瑕累,摘其诗赋,则七子之冠冕乎!琳、瑀以符檄擅声,徐幹以赋论标美,刘桢情高以会采,应场学优以得文,路粹、杨修颇怀笔记之工,丁仪、邯郸亦含论述之美,有足算焉。(《才略》)
这两篇文章概述了建安文士与文学昌盛的状况。其中提到的王粲,是建安文士的领袖人物。从王粲在汉末的命运遭遇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汉末世家大族文士与曹氏的关系。王粲原为东汉末年的世族出身,文才盖世,当时遭乱流寓,投奔刘表,不为所重,自伤不遇,后来转投曹操,自谓找到知音。他的经历,颇似战国时代的士人命运。两汉文士在解嘲自伤类的赋作中经常感叹的战国士人的自我选择,倒是在此时又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实现。曹丕在著名的与吴质的两封信中,也曾谈到他与建安七子的亲密关系:
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既妙思六经,逍遥百氏,弹棋闲设,终以六博,高谈娱心,哀筝顺耳。驰骋北场,旅食南馆,浮甘瓜于清泉,沈朱李于寒水。白日既匿,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舆轮徐动,参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乐往哀来,怆然伤怀。余顾而言,斯乐难常,足下之徒,咸以为然。今果分别,各在一方。元瑜长逝,化为异物,每一念至,何时可言!①
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谓百年己分,可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观其姓名,已为鬼录,追思昔游,犹在心目,而此诸子,化为粪壤,可复道哉!②
曹丕在这里满怀深情地回忆了当初与建安文士诗酒相会、极宴娱人的情景,哀叹他们的逝去。《三国志·魏书·王粲传》中记载:“始文帝为五官将,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学。粲与北海徐幹字伟长、广陵陈琳字孔璋、陈留阮瑀字元瑜、汝南应玚字德琏、东平刘桢字公幹并见友善。”从这段记录看来,当时曹氏父子与文人确实是较为友善的,在他们去世后加以痛悼,其中最有戏剧性的是《世说新语·伤逝》中记载的一则小品故事:“王仲宣好驴鸣,既葬,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这则故事说明了曹丕与建安文士之间的随和与亲密。
值得注意的是,曹氏父子与建安文坛共命运,同悲欢,他们与文士结成了患难之交,由于当时战乱与疾病死亡的困扰,他们的命运在不经意间已经结成一体了,因而彼此之间往往打破君臣界限,无话不谈,对话的穿透力与交融性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的。当时的诗酒相聚更是促成与加浓这种对话与交流的添加剂。建安文士的许多诗作,正是在这种酒宴上写成的,也因此促成了建安文学题材与风格的特点,即前期好慷慨悲歌,中期叹人生苦短,后期哀壮志难酬。曹氏集团中,在与文士进行思想与文学交流过程中,最有成就的人物当推曹丕。《文选》所收的谢灵运《拟邺中》杂体诗小序中,曾以拟代的形式,叙述了曹丕与建安文士相处的情形:
建安末,余时在邺宫,朝游夕宴,究欢愉之极。天下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难并。今昆弟友朋,二三诸彦,共尽之矣。古来此娱,书籍未见,何者?楚襄王时有宋玉、唐景,梁孝王时有邹、枚、严、马。游者美矣,而其主不文。汉武帝徐乐诸才,备应对之能,而雄猜多忌,岂获晤言之适?不诬方将,庶必贤于今日尔。岁月如流,零落将尽,撰文怀人,感往增怆。③
谢灵运在这篇拟代体的小序中,通过后人对于曹丕的理解,写出了曹丕与建安文士的相处,不同于以前君王与文士关系的独特之处,在于“晤言之适”,即能够作为知音进行真诚地对话与交流。其代魏太子拟诗中也描写了当时与建安文士诗酒流连,极宴相娱,无所隔碍的情形:
百川赴巨海,众星环北辰。照灼烂霄汉,遥裔起长津。天地中横溃,家王拯生民。区宇既涤荡,群英必来臻。……罗缕岂阙辞,窈窕究天人。澄觞满金罍,连榻设华茵。急弦动飞听,清歌拂梁尘。何言相遇易,此欢信可珍。
诗中最后两句写出了曹丕与建安文士欢娱一时的种种情形。文中还代徐幹自拟当时曹丕与文士的相交友谊:“清论事究万,美话信非一。行觞奏悲歌,永夜系白日。”值得关注的是,其中描述到曹丕与建安文士以清言相交,畅谈与对话的情景,而这种对话与交流是当时文学创作与批评赖以繁荣的基础,曹丕《典论·论文》显然是建构在这种人文氛围中的。谢灵运的这组代拟体诗中还有一首代刘桢所拟的诗,其中有这样的诗句:“既览古今事,颇识治乱情。欢友相解达,敷奏究平生。”《文选》六臣注曰:“解达,言相谈说而进达也。《方言》曰:‘解,说也。’”尽管这些诗是谢灵运所拟,并非当时的曹丕与文士所写,但是这种后人代拟的诗歌与序文,我们不妨将其看作建安文学时期帝王与文士至诚相待、互相对话的写照。透过后人的阐读与回顾,我们也可以看出,曹丕与建安文士的创作与文学观念肯定受到此种情形的影响。
由于处在一个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年代,建安文学的慷慨风骨与文体样式也就自然而然地与此有关。比如乐府诗的流行,即与曹氏父子与建安文士的这种酒会风习互相联系。刘勰在《文心雕龙·乐府》中指出:“至于魏之三祖,气爽才丽,宰割辞调,音靡节平。观其北上众引,《秋风》列篇,或述酣宴,或伤羁戍,志不出于杂荡,辞不离于哀思。虽三调之正声,实《韶》、《夏》之郑曲也。”也是看到了曹氏好用乐府与题材“或述酣宴,或伤羁戍”有关,而这一切都是在与文士交游中写成的,这一点也算是印证了孔子“诗可以兴”,“诗可以群”的观点。我们通过曹丕与吴质的信可以看得很清楚。另一方面,这种诗酒流连的生活确实也给建安文士的诗作带来一些局限,特别是在建安文学的当中阶段,即建安十三年至建安末(208~220)邺下文士集团形成后,建安文学早期的风骨有所失落,而描写个人功名与诗酒饮宴的应酬之作多了起来,文学中的人文精神有所淡化。④
不过,这种相对宽松和谐的关系,对于文学对话的开展却是有益无害的。在这种气氛下,曹氏父子与当附文士的对话纵论古今,无所避讳。其中最有价值的便是关于文士才性的议论。建安文学批评的中心可以说是作家论而不是创作论,这是有着独特原因的。汉末建安年代是皇权相对衰落而士人地位有所上升的年代,由于士人地位的上扬,客观上也冲击了传统的才性观,士人特别是文士的道德品性与创作才华的关系,便自然而然成为人们议论的中心,曹丕《典论·论文》一开头便谈到“文人相轻,自古而然”的问题,并进而涉及当时的建安文人,这并非偶然,曹丕的文论是从作家论推演到文体论与风格论,彰显出当时是一个从人的自觉到文的自觉的年代,尽管这几年有的学者企图否认这一观点,但是参照当时整个时代的方方面面,特别是人文思潮的兴起,与两汉经学一尊的情况迥然不同,曹丕文学批评的人本光彩是无法遮蔽的。建安文学批评在如何看待作家才性这一问题上,本着对话的精神与方式,进行坦诚的讨论,而不是用儒学的标准式来定夺,这是它的特点。
有关文士个性才华与道德短长关系是自古以来的一个老话题,牵涉到对于文士与文学价值的评价。传统的儒学观念是文人无行与辞赋雕虫小技,不足以道。魏晋时代,此种观念得到改变,一方面统治者自己嗜好文学写作,另一方面则是儒学的价值观受到冲击与改变,以刘劭《人物志》为代表的才性论广为流布。曹丕的《典论·论文》便提出“文以气为主”的观念,将当时的才性论引入文艺评论中去。才性论主张对于人的才性之短长加以全面分析,既不讳言具体的偏至之才的所长与所短,也倡导要加以全面地分析与任用:“王粲长于辞赋,徐幹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曹丕在这里具体分析了这些文士在文学写作上的个性特点及其才华表现,对于其中的缺点也毫不隐讳。曹丕这里用的理论方法与刘劭用的名理学的方法一样,立足于鲜活的人物个性,从个性出发来谈论人的才能,包括文学才能,而不是如两汉儒学的文学批评方式那样,偏执于僵化的道德标准,强求一律,导致批评与评论的偏颇。个性论的批评方式与对话精神正是互为一体的。
在曹氏兄弟与文士的书札对话中,这种讨论更是广泛展开。由于采用的是书信对话,所以许多在冠冕堂皇的文章中不宜多谈的话题私下里倒能展开,甚至一些攻讦也可以从中道出。比如曹植在写给好友杨修的书信中,谈到对于当时一些文士的不满与批评:
以孔璋之才,不闲辞赋,而多自谓与司马长卿同风,譬画虎不成还为狗者也。前为书啁之,反作论盛道仆赞其文。夫锺期不失听,于今称之。吾亦不敢妄叹者,畏后之嗤余也。世人著述,不能无病。仆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昔丁敬礼尝作小文,使仆润饰之,仆自以才不能过若人,辞不为也。敬礼云:“卿何所疑难乎!文之佳丽,吾自得之。后世谁相知定吾文者邪?”常叹此达言,以为美谈。昔尼父之文辞,与人通流;至于制《春秋》,游、夏之徒不能错一字。过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见也。⑤
曹植在与杨修的信中,批评陈琳不擅长辞赋却偏要自拟司马相如。陈琳与曹丕关系较好,而与曹植的关系一般,因此,曹植对于这位擅长文章而不娴辞赋的建安文士的不自量力,缺乏自知之明,颇有几分不屑,讽刺他画虎不成反类犬。可笑的是,陈琳竟然对于他的皮里阳秋听不出来,反而认为是在称赞其文,令曹植哭笑不得。曹植进而慨叹知音难寻,同时坦诚地提出,世人著述,不能无病,自己的诗文也常请人加以批评,乐于加以修改。这些知心之谈,非通过书信的对话方式不能托出。此亦可见对话之于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重要性。
曹植与其父兄曹操、曹丕是当时文坛的领军人物。在居高临下的俯瞰之下,文士的个性与短长是可以互置的,横看为长,侧看则为短,有些文士的文体与个性在这个领域是长处,在另一个领域则成了短处。陈琳长于书檄,但是辞赋不擅。另一位汉末名士孔融的影响与资历比陈琳要大得多,但同样存在着这样的毛病,孔融长于诗赋却不娴于书论,乃至于杂以嘲谑,充分暴露出汉魏文士的个性与文章特点,影响到魏晋风度。曹丕《典论·论文》为此批评他:“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应当说,曹丕对于孔融的批评还算是客气的,北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六二对孔融则毫不客气地加以批评:“北海太守孔融,负其高气,志在靖难,而才疏意广,讫无成功。高谈清教,盈溢官曹,辞气温雅,可玩而诵,论事考实,难可悉行。但能张磔网罗,而目理甚疏。造次能得人心,久久亦不愿附也。其所任用,好奇取异,多剽轻小才。”在卷六五中又记载:“融恃其才望,数戏侮曹操,发辞偏宕,多致乖忤。操以融名重天下,外相容忍而内甚嫌之。”后终被曹操罗织罪名所杀。现在看来,司马光的批评所持标准是儒家的道德标准,对于文士的个性比较苟求,曹丕则要宽容得多,所持的主要是文学批评的尺度,曹丕对于孔融的人格有所非议,但对于他的诗文作品还是很喜欢的,在孔融死后,还以重金募集孔融的文章。
应当说,即使是在《典论·论文》中,曹丕也是明显地受到当时书札体中对话氛围的影响的。他在写作与思考中往往情理交融,方方面面都尽量加以考虑,推心置腹地进行交流。⑥读过《典论·论文》的人都能够强烈感受到其中的许多论断都是在对于当时的文士创作才性与现状的具体分析中引申出来的,是所谓自然流出,与两汉许多文学评论从经学中导出大为不同。尤其是在曹丕私人书信中,谈出了这位表面威严的储君的内心忧惧与悲观,以及对于著述立说的真实想法,这些想法与看法显得弥足珍贵。比如《三国志·魏书·文帝纪》注引《魏书》曰:
帝初在东宫,疫疠大起,时人凋伤,帝深感叹,与素所敬者大理王朗书曰:“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疠数起,士人凋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故论撰所著《典论》、诗赋,盖百余篇,集诸儒于肃城门内,讲论大义,侃侃无倦。
这段记载令人深思。参照这段记录,我们可知《典论·论文》中提出的“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与曹丕感于生命无常,年寿不永的心态是相关的,他在与好友大理王朗的信中,最为坦诚地说出了当时作为王侯的他忧惧死亡而写出了《典论》等篇章,是为了实现人死而不朽的目的,他撰著《典论》与诗赋百余篇,与诸儒共同讨论大义,侃侃无倦。在对话中,我们更能看到他内心深处的坦荡与实情。另外,从这段记载中我们还可以得知,曹丕典论中的许多观点,就是在与诸儒士人的对话与讨论中建立的。比如关于汉文帝与管子、晏仲的优劣比较,就可以看出其中的观点是在对话中有感而发的,今天《典论》中的此类论文大都是在这种情形下形成的。
在当时,展现士人与帝王关系的另一典型例子,便是曹氏兄弟与吴质的关系。从两封信中可以见到曹丕、曹植与文士相处的微妙关系。曹丕对于当时文士才性关系的看法,在与吴质书中说得最坦率,这大约与曹丕与吴质的亲密关系有关。曹丕与吴质的关系非同一般。《三国志·魏书·王粲传附吴质传》中记载:“吴质,济阴人,以文才为文帝所善,官至振威将军,假节都督河北诸军事,封列侯。《魏略》曰:质字季重,以才学通博,为五宦将及诸侯所礼爱;质亦善处其兄弟之间,若前世楼君卿之游五侯矣。”这段记载表明吴质是一位善于在曹丕与曹植之间周旋的人物。他以文才受到曹丕与曹植的器重,同时在政治上也颇有手段,是一位嗜好权势的士人,受到后人的诟病。曹丕与他的关系很密切,裴注引《魏略》曰:“帝初亲万机,质以辅弼大臣,安危之本”,“质先以怙威肆行,谥曰丑侯”。从这些记载来看,他为曹丕的心腹,曹丕有些知己的话与他谈得最多,在《与吴质书》,曹丕谈出他对于当时文士的评价,可以与《典论·论文》的看法互相印证:
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而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矣。著《中论》二十余篇,成一家之业,辞义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矣。德琏常斐然有述作意,才学足以著书,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间历观诸子之文,对之抆泪,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为繁富。公幹有逸气,但未遒耳,至其五言诗,妙绝当时。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也。仲宣独自善于辞赋,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至于所善,古人无以远过也。昔伯牙绝弦于锺期,仲尼覆醢于子路,愍知音之难遇,伤门人之莫逮也。诸子但为未及古人,自一时之俊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
曹丕在与吴质的这封信中充满着伤感之情,他对于建安文士的看法虽然受到传统的影响,比如他仍然强调“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也就是说,古今文人很少能以名节自立,而徐幹所以称道,就是他能在文士中注重名节,是最能传之不朽,可见曹丕即使在当时的年代之中,也没有完全摆脱传统文学观念的影响;但是他另一方面也认为对于文人不能求全责备,故从才性论出发,具体剖析了文士的创作特点与短长,结论是“诸子但为未及古人,自一时之俊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可见曹丕在与吴质对话中彰显出来的文学观念既传承了古人,又融入了当今。值得关注的是其中与文士深挚的感情,引为知音,坦诚对话与讨论的精神与方式。卞兰在《赞述太子赋》中称道曹丕曰:“讽六经以崇儒,嘉通人之达节。笑俗士之守株,匿天威之严厉。”⑦颇为传神地写出了曹丕的为人与教化方式是兼融古今,从而开一代文学批评新风气,是当时文学自觉的重要表现。
有意思的是,曹丕虽然身为王侯重视文学,宽容文士,但吴质由于心存政治野心,故而对于文学与文士有所不屑。吴质在答曹丕的信中,与曹丕怀着深厚的情谊追悼建安文士、高度评价其人的观点不同,坦言自己对于他们的评价,并没有超出关于汉代那些“言语侍从之臣”的看法,语调中颇多不屑:
陈、徐、刘、应,才学所著,诚如来命。惜其不遂,可为痛切。凡此数子,于雍容侍从,实其人也。若乃边境有虞,群下鼎沸,军书辐至,羽檄交驰,于彼诸贤,非其任也。往者孝武之世,文章为盛,若东方、枚皋之徒,不能持论,即阮陈之俦也。其唯严助寿王与闻政事,然皆不慎其身,善谋于国,卒以败亡,臣窃耻之。至于司马长卿,称疾避事,以著书为务,则徐生庶几焉。而今各逝,已为异物矣。后来君子,实可畏也。⑧
吴质一方面也承认陈琳等人的才学,但是他仅仅承认他们“于雍容侍从,实其人也”,而在建功立业方面,则无所成就。他认为这些人顶多就是汉武帝时代的东方朔、枚皋之徒。至于司马相如,称疾避事,著书为务,苟全性命而已。吴质由于贪恋权势,注重事功,对于文士的看法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也是不足为奇的。
吴质在答曹丕的信中,坦言自己的志向在于从政,建功立业,不屑以文才自居。一方面他也说过“伏惟所天,优游典籍之场,休息篇章之圃,发言抗论,穷理尽微,摛藻下笔,鸾龙之言语奋矣”,好像要在以文自娱中终其天年。他在《答东阿王书》中,对曹植也说过类似的话:“若质之志,实在所天,思投印释黻,朝夕侍坐。钻仲父之遗训,览老氏之言。对清酤而不酌,抑嘉肴而不享。使西施出帷,嫫母侍侧,斯盛德之所蹈,明哲之所保。”⑨好像已经超脱世事,一副逍遥游放,以文自娱的姿态,另一方面,他内心是充满不平的。在《答东阿王书》中,他先是赞美曹植的文采:“质白信到,奉所惠贶,发函伸纸,是何文采之巨丽,而慰喻之绸缪乎!夫登东岳者,然后知众山之逦迤也;奉至尊者,然后知百里之卑微也。”慨叹自己无法企及。然而话锋一转,又发起了牢骚:“质小人也。无以承命,又所答贶,辞丑义陋,申之再三,赧然汗下。此邦之人,闲习辞赋,三事大夫,莫不讽诵,何但小吏之有乎?重惠苦言,训以政事,恻隐之恩,形乎文墨。墨子回车,而质四年,虽无德与民,式歌且舞,儒、墨不同,固以久矣,然一旅之众,不足以扬名步武之间,不足以骋迹。若不改辙易御,将何以效其力哉?今处此而求大功,犹绊良骥之足,而责以千里之任;槛猿猴之执,面望其巧捷之能者也。”这封书信中确实表现出吴质复杂的心态。吴质在建安文士中,富有文采,不然也不会得到曹丕与曹植的赏识,《文选》中收了他多封书笺,因此,他对于文学很喜好,但是在这里他也委婉地表示出自己不愿意以文士终其一生,而是要在建功立业上实现人生价值。当时,这也是建安文士的共同心态。吴质由于和曹丕关系甚密,曹丕秉政后,吴质任权当势,行为有亏,死后被贬为“丑候”也是情理中事。他与曹丕的书信不管怎样,是说了真心话,而坦率地对话,总是可以将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摘发出来,从而引起批评的深入。比如后来关于文士作用与地位的讨论,在建安文学之后,重叠了更深入的讨论,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经常论及的一个话题。
在曹氏兄弟与吴质的书信中,关于文士的地位与个性风采论述由于所处境遇不同,视角不同,差异甚大,并非偶然。曹氏父子,任权当势,对于文士自可以居高临下地说一些尊重的话,对于文学与文士的价值大加褒扬,而对于处在弱势地位的文士来说,他们的价值最终还得通过地位的上升来获得,而没有地位的保障,身家且不保,何况文学的价值实现,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当时文士与文学价值上升了,但是文士与帝王的关系从根本上来说,仍然还是君臣上下关系,只要这种地位不改变,文士与帝王的关系不可能真正的平等。而与此相适应的文学的独立价值也就不可能实现。通过这些出于不同身份与地位的帝王与文士的对话,我们更可以感受与了解到建安年代文学观念与文士价值观念中复杂与隐蔽着的奥秘,它是比一般的文学史专论更清楚彰显出来的事实。
在曹氏父子的论述与对话中,这种复杂的文学价值观是随处可见的。在曹植与杨修的书信往来中便表现得很明显。曹植虽然钟爱文学,辞藻灿烂,文华盖世,为一代文宗。但是由于他在政治上雄心勃勃,意欲建功立业,因此,不甘心做一名文人,在《与杨德祖书》中便继而说起文章不中用的话:
夫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也。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昔扬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犹称壮夫不为也;吾虽薄德,位为藩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颂为君子哉?若吾志不果,吾道不行,亦将采史官之实录,辨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虽未能藏之名山,将以传之同好,此要之白首,岂可以今日论乎!其言之不怍,恃惠子之知我也。明早相迎,书不尽怀。⑩
这封信真实地展示了曹植矛盾的心态,一方面酷爱文学,性行也以文学相缘,但是身为王侯,自然不能不萌生建功立业,参与政治的念头,尽管他并不具备政治家的才干与能力。他引用扬雄的话来说明文学乃雕虫小技,壮夫不为,自己的心志乃是经国立业,流惠下民;其次采史家之言,定是非辨曲直,效法孔子修《春秋》,而不愿以辞赋小道显名后世。可见传统的文学观念仍然在左右着曹植这样的文坛大人物。深知他心曲的杨修则在对话中不同意他的观念,坦诚地与曹植交换看法,既有劝导,也有安慰:
伏想执事,不知其然,猥受顾锡,教使刊定。《春秋》之成,莫能损益。《吕氏》、《淮南》,字直千金;然而弟子钳口,市人拱手者,圣贤卓荦,固所以殊绝凡庸也。今之赋颂,古诗之流,不更孔公,《风》《雅》无别耳。修家子云,老不晓事,强著一书,悔其少作。若此,仲山、周旦之徒,则皆有愆邪!君侯忘圣贤之显迹,述鄙宗之过言,窃以为未之思也。若乃不忘经国之大美,流千载之英声,铭功景锺,书名竹帛,斯自雅量,素所蓄也,岂与文章相妨害哉?(11)
杨修在信中赞扬曹植的诗赋作品文采灿烂,超绝众人,非凡庸可比。这些话不光是阿谀,而是真诚地赞美曹植的文华盖世。但杨修在这里重点指出,文章之美与经国之大美,流千载英声并不相妨。为此他甚至批评祖先扬雄老不晓事,硬说文章为雕虫小技,悔其少作,语句可谓激烈。他的观点与曹丕《典论·论文》中的文章观倒是很接近。其实,曹植也是佯作姿态,他的内心并不认同传统的辞赋小道、不足以道的观点。他在《前录序》中曾提出:“故君子之作也,俨乎若高山,勃乎若浮云,质素也如秋蓬,摛藻也如春葩,汜乎洋洋,光乎皜皜,与雅颂争流可也,余少而好赋,其所尚也,雅好慷慨,所著繁多,虽触类而作,然芜秽者众,故删定别撰,为前录七十八篇。”(12)从这些地方来看,他似乎又是很看重文章作用的。曹植在文学的价值观念方面确实表现出深深的矛盾与复杂的心态。但不管怎样,曹植通过与杨修的对话,发摘隐曲,吐露心志,从正反两面彰显了文章的价值。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汉末建安文学中的思想对话与文学批评,是秦汉以来士人精神人格的复兴,先秦时代的士与帝王关系,是相对独立与自由的,在此基础之上才有可能产生百家争鸣与灿烂的诸子学说,两汉建立的专制王朝则扼杀了这种自主性,思想对话的缺失,导致两汉文学批评的经学化与沉滞,而东汉末年的各种因素,促成了建安文学的兴盛,在此过程中,汉末的清流文化与士人精神开始复活。建安文学领导人物曹操所代表的曹魏统治集团,与当时文士的关系颇为微妙,建安文士中的孔融、杨修等人显然是与汉末清流人物有关,甚至直接受到党锢之祸的冲击。他们在当时与曹操的相处中,显然保持着汉末党锢人物遗风与清流文化的特点,譬如孔融对于曹操的态度便是如此,而曹操与这些人物的关系也很复杂,一方面他要团结与利用这些士大夫,在曹操后来的事业中,党锢集团中的汝颍人物始终是他倚重的力量。如荀彧、荀攸、钟繇、陈群、荀悦、杜袭、戏志才、郭嘉等,大多为汝颍地区的士族文人。曹操在建安十二年颁布的《封功臣令》中提出:“吾起义兵,诛暴乱,于今十九年。所征必克。岂吾功哉?乃贤士大夫之力也。”(13)从历史渊源来看,这些人基本属于党锢人物的后代。另一方面,曹操的用人观念与这些清流人物有着深刻的矛盾,正如陈寅恪在《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一文中,认为曹操是汉末宦官集团代表,“其在汉末,欲取刘氏之皇位而代之,则必先摧破其劲敌士大夫阶级精神上之堡垒,即汉代传统之儒家思想,然后可以成功”(14)。曹操在后来的政治斗争中提出过不拘德行、唯才是举的用人思想,也吸取了刑名之学,破除了汉末浮华交游的恶习。曹操杀孔融与杨修也是如此,因此,汉末士人与曹氏统治集团的矛盾是中国传统士人与帝王矛盾的必然反映,建安时代的思想对话与文学批评是士人与帝王既融合又抗衡的心态与行为的显现,整个魏晋六朝这种对话与批评中隐藏着的士人精神与统治者的博弈都是存在着,构成了丰富的人文内涵,也是六朝文学士人风操与精神在文学事业中的照耀。通过思想对话去促进文学批评,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积极态势,是其成功的一面,也是今人研究文学批评中的亮点之一。
注释:
①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文选》卷四二,中华书局影印胡克家刻本。
②曹丕:《与吴质书》,《文选》卷四二。
③谢灵运:《拟邺中》,《文选》卷三○。
④参见徐公持《魏晋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
⑤曹植:《与杨德祖书》,《三国志·魏书》卷一九《陈思王传》裴注引,中华书局标点本。
⑥余冠英《三曹诗选》“前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5页)中指出曹丕在邺下文人集团中,地位尊隆而措辞谦逊,高屋建瓴不失一个领袖的风度。
⑦卞兰:《赞述太子赋》,《艺文类聚》卷一六,中华书局本。
⑧吴质:《答魏太子笺》,《文选》卷四○。
⑨吴质:《答东阿王书》,《文选》卷四二。
⑩曹植:《与杨德祖书》,《三国志·魏书》卷一九《陈思王传》裴注引,中华书局标点本。
(11)杨修:《答临淄侯笺》,《文选》卷四○。
(12)曹植:《前录序》,《艺文类聚》卷五五。
(13)《三国志·魏书》卷一《武帝纪》,中华书局本。
(14)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43页。
标签:建安文学论文; 曹植论文; 曹操后人论文; 三国人物论文; 三国论文; 汉朝论文; 文学批评论文; 典论论文; 曹丕论文; 曹操论文; 文选论文; 魏略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