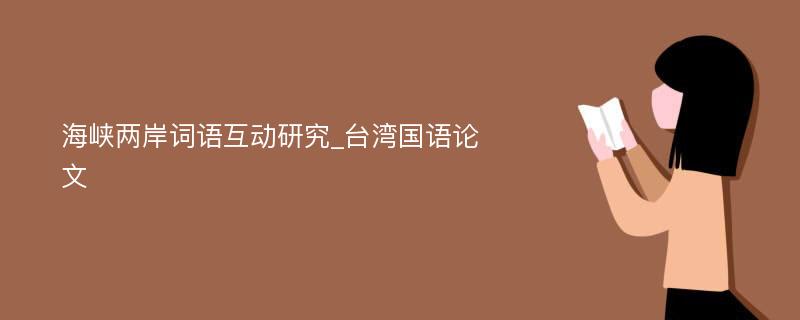
海峡两岸词语互动关系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互动关系论文,海峡两岸论文,词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语言作为社会现象的一面镜子,社会的发展和社会关系的调整必然会带来语言关系的调整,不同社会交际群体的语言交际因而得以相互影响。就海峡两岸的语言交际关系而言,既有大陆语言交际对台湾的影响,同样台湾语言交际也必然会影响大陆。也就是说,海峡两岸的语言交际正处于一种互动关系之中。随着两岸交往的进一步发展,这种互动关系的深度和广度都在进一步深入发展。本文以词汇系统的变化为视角,来探讨海峡两岸语言交际的互动关系。
本文的主题“互动”(interaction)一词,据学界分析,最初是在台湾语言交际中使用的。北京语言大学和中华语文研习所(台湾)合编的《两岸现代汉语常用词典》(2003)是这样释义的:①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互相交往的过程,②互相影响,③交替;更迭。这个词后来被大陆词汇系统所吸收。①本文的“互动”采用的就是第二个义项。根据这种理解,海峡两岸词语互动既包括台湾词语对大陆交际的影响(如上例),也包括大陆词语对台湾交际的影响,还包括来回传递的过程。目前学界对于海峡两岸词汇系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词语的对比和差异的分析上,偶有研究涉及两岸的词语融合,但仍没有基于互动观念对相互交往过程的研究。本文尝试提出“词语互动”这一概念,借此来系统研究两个词汇系统之间互相影响的方式及其语言后果和语言学意义。
本文所依据的语料主要有两个来源:大陆的语料主要来自北京大学CCL语料库,台湾的语料则来自“中央研究院”现代汉语平衡语料库。同时还参照了一些报纸、网络上的语料(如《人民日报》《国语日报》等媒体资源)及相关工具书。
本文首先详细描写海峡两岸词语互动的基本模式,接着具体刻画海峡两岸词语互动的层级,然后分析互动过程中出现的同步现象及相关的合力作用问题,最后指出这种基于互动观念的研究对动态地研究词汇系统乃至语言系统所体现出的理论意义。
二、海峡两岸词语互动的基本模式
根据海峡两岸词语互动的过程和方式,我们将两者之间的互动模式概括为替换式互动、单边增量式互动、双边增量式互动、返还式互动、他源式互动、新生式互动、激活式互动这样一些类型。这里互动模式的各个名称是笔者为了说明问题的方便而拟定的。
1.替换式互动
替换式互动是指同样一个概念,在大陆和台湾分别用词语A和B来指称,经过互动以后,A替换了B或者B替换了A。在这种模式下,发生互动的一方是词,另一方是短语或短语式多音节词②。具体说来有两种情况:
1)词—短语替换,即复合词或缩略词取代了被影响一方原先用来表达相应概念的短语或短语式多音节词,使后者逐渐淡出交际系统或其使用领域有所限制。例如台湾“国语”中的“房车”,指一种配备了家具、厨房、浴室等设施的旅行用豪华汽车,因其具备了住房的功能而被称为“房车”。这一概念过去在普通话中只有“野营旅游车”的形式,后来受了台湾“国语”的影响,现在“野营旅游车”已经几乎完全退出日常交际,而为“房车”所取代。普通话的“面包车”被引入台湾后逐步影响台湾“国语”中“厢型小客车”的使用空间,而使其使用频率很快降低,逐渐缩小交际范围,也是这种情况。这些由复合词或缩略词取代短语和短语式多音节词的情况,既有经济性原则的影响,还跟词语的色彩有关,相对而言,“房车、面包车”较好地体现了指称对象的形象色彩和功能色彩。
2)词—词替换,新词的引入往往伴随着与其同义的既有词语的淡出或两者交际功能发生调整。一般而言,两个语义、语法、色彩、语用完全相同的词在同一词汇系统中往往不会长期共存,在语言交际的选择过程中,或者一方被替换,或者两者发生功能分化。这里要讨论的是一方被另一方替换的情况。例如,普通话的“电工”、“博士后”进入台湾“国语”后替代了原来的“电匠”、“超博士”,台湾“国语”中的“单亲家庭”进入普通话后替代了原有的“半边家庭”。
2.单边增量式互动
单边增量式互动是指,系统A向系统B单向提供一个词语的情况。同时,引入方原有的词语、义项并不会消失,但是在语义、语法功能和语用上一般会发生调整。
例如台湾有一系列跟政治经济有关的复合词已进入了大陆词汇系统,如“脱困(摆脱困境)、请辞(申请辞职、请求辞职)、操控(操纵控制)、缺失(缺点和失误)、掌控(掌握和控制)、体认(体会和认识)、共识(共同的认识)、造势(制造声势)”等等。这些词都是普通话和台湾“国语”共有短语的缩略形式,但是由于某一时期在政治经济方面台湾比大陆更活跃,因此随着使用频率的增长,这些短语在台湾率先实现了缩略;在大陆政治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势必要使用此类词语,加上与台湾地区的密切交往,因此会受到台湾已完成缩略词语的影响。③与此同时,大陆也有一部分词进入了台湾“国语”,例如,“动漫”表示“动画和漫画”或“动漫画”,“魔方”表示“魔术方块”。
但是在这种互动模式下,复合词又不完全取代其缩略前的短语形式,而是两者各自占据着一定的交际空间,它们语义上的差别非常小,主要差异体现在语用功能上。例如普通话从台湾“国语”中引入的“请辞”一词既可以用在口语语体中,也能用于书面语体,而一些解释说明性的语体中则仍然常使用短语形式“申请辞职”或“请求辞职”。
单边增量式互动也包括词语义项的增加或调整。最典型的就是比喻义的互动。有不少台湾“国语”中的单义词通过隐喻方式引申出的新义项被大陆吸收。例如,“出炉”在两岸的基本义都是“从烤炉中取出烘烤或冶炼好的东西”,但是在台湾它还有比喻义“方案出台”;“来电”的基本义在两岸都指“打来电报或电话”,但是台湾还引申出了“对异性产生强烈感情”。这些源出于台湾的比喻义现在都进入了大陆的词义系统当中。又如“渠道”在海峡两岸的共有义项是“人工挖凿出的水道”,现在产生于大陆的比喻义“途径、门路”也逐渐现于台湾“国语”中④。
单边增量式互动也可表现为词性的增加或调整。如“决议”在大陆是一个名词,在台湾除名词外却还有动词用法,意思是“通过讨论决定”用法,现在大陆有时也将“决议”作为动词来使用。我们不排除词性的转化可能是一个语言系统自发的演变,但是由语言社团的接触而引发的词语互动无疑会使这种变化更有可能发生,产生以后也更容易扩散使用。
3.双边增量式互动
双边增量式互动就是指互动双方各自从对方引入一个概念相关的词语的情况。这种互动带来的后果是双方的同义词场和词义系统的调整。
这类互动最常发生在两个同义词之间。其中有的是由于深度交往带来的,其互动词语往往出现于两岸社会交往最密切的领域,因此互动词语较容易在对方词汇系统中扎根,稳定地在交际中扩展,但是语义和语用必然会发生一些分化。
以“课业—功课”为例(前者的源出地为台湾,后者为大陆),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的释义,“课业”的范围大于“功课”,泛指学业,而“功课”则表学习的知识、技能,或老师布置的作业,二词的词义已经分化。而根据《新编“国语”日报辞典》,“课业”在台湾指学生每天必须温习预习和练习的功课,“功课”则指学生所学的课业。可见,这两个词词义的引申路径是一致的,在引入了一新词形之后,新的形式恰好承担了最新的引申义,于是造成互动之后的两个词在表义上发生了分化,其词义在两岸呈现互补分布状态。
有的互动极不稳定,例如很多两岸科技术语的互动都有这个特点,如“网路—网络、软体—软件、飞弹—导弹、太空梭—太空飞船”等等,对两岸交际者来说在理解上可能没有问题,但不太会主动使用对方的词语。.
词语义项之间异步引申后的交融式互动也属于双边增量式互动。这是指在引入对方一个义项的同时,又给对方提供一个义项。例如“小儿科”最初在两岸都是医疗术语,后来两岸分别发生了引申。台湾引申义为“小气、吝啬”,大陆引申为“价值小、水平低,不值得重视的事物”,现在两岸的词典都收录了对方的义项。
4.返还式互动
返还式互动即指系统A向系统B提供一个词语或义项,该词语或义项通过语言调节产生了新的用法,而后又回传给系统A并被系统A所接纳。
例如台湾“国语”中的“名嘴”指“因言谈机智而出名的人”,被大陆引进后转指为“知名主持人”,这是由于大陆一般被大众所熟知的“言谈机智的人”往往都是电视节目主持人,这一过程就是词义在大陆语境下的重新调整,是系统中新引入的成分发挥了其调节功能,使语言能够适应和满足交际的需求。在影响大陆的同时,“名嘴”在台湾并没有“知名主持人”这一义项,但是后来发生了回传,现在台湾“国语”中“名嘴”也能用来指称某些节目的知名主持人了。发生返还式互动时,词语或义项在输出与回传之间往往会经历一段时间差,互动词语或义项在期间可调整自己来适应引入方的词汇系统和交际需求,因此往往会引发语义的调整,而语义调整所带来的新义和新颖色彩又为该词语或义项重新被源出方吸纳提供了可能。这是互动双方不断循环交替互相推动的结果,有助于保持词语的新颖度和活跃度。⑤
5.他源式互动
他源式互动不同于其他互动模式,发生互动的词语是一个外来词或方言词,普通话和台湾“国语”只是作为词语借入的中介而存在。
台湾“国语”里日语借词对普通话的影响最为显著。台湾“国语”借用的一大批跟日常生活有关的日语词,如“欧巴桑、欧吉桑、玄关、料理、宠物、恶搞”等等,都影响了普通话的表达。有些外来词在被台湾“国语”吸收的时候就发生了语义调整。例如“欧巴桑、欧吉桑”引入后与系统中已有的同义词产生分化,“欧巴桑、欧吉桑”被赋予戏谑色彩,从而在语用功能上区别于同义的本土词“大婶、大叔”。此类色彩在随后的语言接触中也随着词形本身被引入普通话词汇系统。也有不少日语词是1949年以前就由大陆直接从日语借入的,1949年以后大陆借入日语词主要以台湾“国语”为中介,当然,我们也不排除日语对普通话的直接影响。尤其是近些年随着日本技术产品、文化产品的输入,为普通话交际系统提供了很多新的表达。
台湾“国语”中源于闽南方言的一些词语因为具有特殊表义功能或者新颖色彩也往往也具备一定的互动能力,先进入台湾“国语”中,然后再为普通话词汇系统所吸收。例如闽南话中表示“差错”的方言词“乌龙”,现在已经进入了普通话,有“乌龙球”和“乌龙事件”的说法。在闽南方言对普通话的影响过程中,台湾“国语”可以作为中介,闽南方言词经由台湾“国语”进入普通话,也可以直接从方言直接进入普通话词汇,这两股力量往往汇成一股合力,共同影响着普通话词汇系统。
6.新生式互动
有一些新事物或者新概念,在大陆或者台湾出现后,随着社会交往的深入,才由一方传播到另一方,这些概念对于互动双方来说,都在不同时间层面上实现为新词语。例如台湾把部分青少年疯狂骑机车的玩命游戏称为“飙车”,近年该词已进入了普通话。这一互动带来的副产品是:“飙”的派生能力由此被激活了,成为普通话中一个十分能产的构词语素,派生出了“飙速、飙戏、飙骂、飙脏话、飙泪、飙高音、飙歌、飙舞”等词。这个构词语素是在海峡两岸互动的过程中随着新概念被引入大陆的。于根元(2005)指出,这些新词在新引入的时候是其最活跃的阶段,使用多了其新颖色彩就会逐渐潜藏。“飙”之所以有如此强大的派生能力,与其本身的新颖色彩密切相关,同时,要使词语继续保持其新颖色彩,利用构词语素派生新词不失为一种途径。而新词带来的全新表达也会反作用于构词语素,使其新颖度得以保持,从而继续派生新词。
还有一些概念反映的是大陆或者台湾特有的事物和社会制度,表现为两个社区特有的词,即社区词⑥的一种。于根元等(2003)把“社区词”的定义扩展为“形式上是普通话词而在某个社区流通”的词,施春宏(2010)则进一步将社区词看作方言词和通用语词之间的一个环节,但是比方言词更具互动能力。虽然社区词一般只能在本社区内部流通,但是随着特定时期两岸互动的加速,在一定条件下,有一些社区词也能够在不同社区内产生互动。例如大陆的“下岗”有两个义项,一是“在岗位上执勤的人结束工作离去”,二是“企业中多余的职工失去工作岗位”。其中第二个义项是内地特有义项,随着国企改革的开展而在使用频率上迅速上升。后来这个词形被台湾“国语”所吸收,但由于经济体制的差异,没有义项二的所指,而是自动调整第二个义项,具有了“下台”义。现在,“下台”义又回传给了大陆,表示“失去职位”。
社区词语义的调整是社区词互动的一大特点。语言是一个动态的系统,语言要素和要素之间的关系会通过语言调节来适应交际功能的需求;而交际功能的变动又会带来要素及其关系的变化,即语言变异。(施春宏,1999)在借入社区词时,词语的形义关系为了适应不同社区的交际功能,往往会发生适应性调整。“下岗”一词进入台湾“国语”后的语义调整便反映了语言调节的作用。
7.激活式互动
在一个词汇系统中,一些词语本来就存在,但由于某种历史原因暂时淡出了交际系统,而后在特定的交际场景中,这些词语又被激活了,实现了新的交际价值。大陆有很多古语词,如“福祉、昭示、秉持、厘定、漏夜”在1949年以后曾逐步退出了交际系统,然而这些词语在台湾“国语”中仍有相当大的使用面。现在,这些一度在大陆已经隐退了的古语词又被广泛使用开来,我们推测可能是受到台湾“国语”的影响。
语言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系统,语言成分及其关系处于潜→显→隐(→再显)的变化中。处于特定交际时空中的某些语言成分后来不怎么用了,转而潜藏下去;到后来某个交际时空中,它又显示了出来,实现了新的交际功能。由显而隐,不一定就消失了,而是在“轮休”、“充电”(于根元,2005)。由隐再显,便是受到新的交际场景的激活。这种激活既可以由系统内部的要素带来,也可以由两个系统的互动所导致。如果单纯是后者造成的词语复现,那么就可以归入激活式互动。然而词语复现的原因非常复杂,常常包含了词汇系统内部和外部要素的共同激活。
在1949年以后,大陆出现了一批富有时代特色的新词,与此对应,汉语词汇系统中的另一批词则进入了“轮休”状态,潜了下去,特别是上面指出的一些古语词;然而到了今天,这些古语词又显现出一种新颖色彩,于是它们在大陆复活了。与之相反,台湾“国语”中却一直保留着这些古语词。这批古语词在大陆的复现,一方面是因为这些词经历了“充电”后又能够实现新的交际功能,这属于普通话词汇系统的自我调节;另一方面,也可能受到方言、社区词,甚至外来语的影响。由于两岸交往的加深,台湾“国语”中的古语词便很有可能在一些特定交际场景中激活普通话中处于相应潜藏状态的古语词。
这些词被激活后,会与已处于“显状态”的同义词发生竞争,竞争的结果往往是两者分割语义或语用空间。例如“福祉”在被激活前普通话已有“幸福”这个词语,两者唯一的差别在于语体色彩不同。依据冯胜利(2010)对语体的切分,[正式性]和[典雅度]是切分语体的两个维度。对于“福祉”这类古语词来说,它们有浓重的典雅色彩,而“幸福”这类词由于经常使用,典雅色彩已经被磨损了,几近通俗色彩,因此它们由于色彩的不同而得以在不同的语用空间和语体中共存。“福祉”通常用于典雅、正式的语体中,而“幸福”可以用在正式性和典雅度都较低的语体中。可见,激活式互动也会造成同义词在功能上的分化。
8.关于不同互动模式的相互关系
以上我们对于互动模式的归纳,都是基于各个侧面的分析,因此,各个互动模式之间不免会产生交叉,而且常常出现交叉的情况。也就是说,互动过程的发生虽有可能是单个因素作用的结果,但常常是几股力量共同发挥作用的产物,有的是共时层面上的合力作用激活式互动、他源式互动和单边增量式互动就能够产生合力,例如“福祉”在大陆的复活可能是由激活式互动和他源式互动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是单边增量式互动。有的则是历时层面上的合力作用,即不同的互动模式在不同时期分别起作用。有的词语在发生新生式互动、单/双边增量式互动后又继而引发返还式互动,例如台湾在引入“下岗”以后又发生了词义回传大陆的现象。他源式互动也可能随后引发替换式互动,很多外语借词都是与已有词语共存了一段时间以后才实现替换的。因此,互动现象也并非一蹴而就,也往往不是单一模式,而都要经历一个复杂的过程,不同的互动模式可以通过共时和历时两方面的合力作用于一个词语。所以互动并不是扁平的、单一的,而是一个立体的、多层次的过程。
三、海峡两岸词语互动的层级
互动不仅在模式上有差异,在影响上也有区别,有时是双向的,有时则以单向影响为主。也就是说,互动的程度和方式是有所不同的。因此,需要进一步考察互动的过程和方式及其表现出来的层级关系。
海峡两岸词汇系统的互动过程存在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我们把这个过程理解为互动的层级(interactional hierarchy)。关于互动层级的研究,前人已从多个角度给了我们很多启示。如汤志祥(2001)把台湾“国语”在普通话中的使用情况分为群众广泛使用、报刊书籍使用、权威辞书选用三个阶段,词语的使用逐渐由不稳定到稳定;Haugen(1956)从语言接触的角度提出了两种语言融合的三个阶段:切换、干扰、整合,其中,“切换”即所谓的语码转换,是语言接触的最初表现,指同样的说话人在同样的会话里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成分。我们认为,互动层级是一个前后相继的连续体,而各个层级又有其相对独立性。其连续性表现在有的词语在一个词汇系统中可以经历从切换到整合的发展过程,例如“电工”逐渐替换“电匠”;其独立性表现在发生了接触的词语不一定都要经历切换到整合的过程。有的词语互动能力强,或者词汇系统中存在空位,因此可以直接与系统整合,如“玄关”在大陆本来就存在概念空位,因此在普通话系统中很快就稳固下来。但是有的词语互动能力弱,只能一直处在切换的阶段,例如“网络”之于台湾“国语”。不同的词语,接触的历史也有长短。有的词语虽然互动能力强,但是由于接触的时间不长,因此仍然处于一个较“浅”的阶段。因此,我们初步将两岸的词汇互动状况划分为三个层级:深互动、浅互动、潜互动。
1.深互动
进入深互动阶段的词语,一般词语的互动能力比较强,互动历时长,使用范围广,频率高,很多都已经被收入词典中,且无论在书面还是口语中,交际人群都能够主动输出这些词语。处于深互动层级的词语,有些已经与其同义表达在交际空间上完成了分化,有些则会调整自身的语义结构和语法功能,有些构词语素甚至会发展出派生能力(如“飙”),这反映了互动语素已经具备了能产性,其互动效果最为深入。深度互动除了词语本身的原因之外,两岸的深度交往也是深互动的必要条件。一般替换式互动、新生式互动、返还式互动、他源式互动和激活式互动都能到达深互动这一层级。处于深互动阶段的词语一般已经与引入方的词汇系统融合,成为词汇系统中相对稳定的部分。
2.浅互动
处于浅互动阶段的词语,一般互动时间还不太长,使用范围比较局限,受到语义、语用等方面的制约,且大多处于口语中的自由切换阶段,还没有与引入方的词汇系统发生整合,可以理解而很少主动使用。
处于浅互动阶段的词语有两种发展趋势:一是随着接触的进一步延续进入深互动阶段,二是停留在新词与原词的临时切换这一阶段。第一种情况如有些发生单边增量式互动的词语,互动后会给系统带来两个甚至多个同义词,此时,系统会自动调节同义词之间的关系,分化语义和语用空间,为其进一步互动创造条件。第二种情况是虽然接触的时间很长但是也没有进入更深的层级,许多双边增量式互动就属于这一层级。这种现象往往是由互动条件不充分所造成的,例如“网络”对“网路”的影响便是如此。虽然“网络”偶现于台湾口语,也被词典收录,但是由于“网路”在台湾历史更悠久、使用更广泛,因此其等义词“网络”在竞争中失势,它们的互动属于浅互动。
3.潜互动
有一些词语,本身具有较强的互动能力,却并没有在现实中实现互动,这种情况我们可以称之为“潜互动”,即应该发生互动而还未发生互动。
那些在一个词汇系统中存在表达缺位的词语便可视为处在潜互动的阶段。以部分社区词为例,它们当前只在一个区域流通,但是具备较强的互动能力。例如台湾“国语”中用来表示学生对女老师丈夫的称谓“师丈”,这个概念在大陆目前还没有相应的表达,但是随着大学中女教师的增多,“师丈”的叫法应该会在大陆逐渐蔓延开来。这些年“宜居城市”在大陆是一个出现频率很高的新词,台湾并无相应的词语。因此“宜居城市”也应存在于潜互动层面,随着大陆媒体的广泛报导,这个词应该很快能实现互动。
处于潜互动层级中的词语之所以没有发生互动,主要是互动时机还没有到来,或者由于词汇的接触还没有发生,或者由于这些词在引入方的词汇系统中都有对应的同义词,并且这些词的新颖色彩还没有被磨损,因此仍然处在比较活跃的“显”语言状态。但是由于表达缺位的存在,因此互动趋势是显著的。
四、互动中的同步现象和合力作用
我们在描述词语互动现象时,都涉及到了两个词汇系统间的接触,事实上,词汇系统的变化除了系统间的直接影响,还必须考虑系统自身的调节能力。在对上述互动模式的分析中我们也发现,词汇系统的演变都是逐步调节的。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促动了这一过程的发生。一是系统内部的因素,即词汇系统自身的调节机制,包括词义的引申机制、词语的借入机制和缩略机制等等;一是系统外部的因素,即由接触所带来的结果,即一方的词汇系统直接从另一方系统引入相关成分,而新引入的成分又会对既有系统产生调节作用。由于海峡两岸词语在构词材料和规则上的一致性,有些现象可以不依赖接触而在一个词汇系统中自发地显现。这就是同步现象的根源。
许嘉璐(1987)提出了“同步引申”的概念,指一个词意义的延伸过程常常扩散到与之相关的词身上,带动后者也沿着类似的线路引申。许文所指的同步现象是一种聚合类推现象。事实上,同步引申不仅出现在相关的一系列词之间,也出现在存在于不同社区的相同词语之间,相同的词在不同社区之间的缩略过程,以及同一个外来词或方言词被不同社区借入的过程也常常体现出“同步效应”。因此,我们尝试将“同步现象”进一步理解为:如果同一个词语在不同的社区里不依赖于系统外部因素的影响而有相同或相似的引入和演变轨迹,那么我们也可以看作这个词在不同系统中发生了同步现象。
同一个词在大陆和台湾的词义引申过程就能说明这类现象。例如台湾“国语”中的“清纯”有两个义项:秀丽纯洁,一般用来形容少女;清新洁净。普通话“清纯”原来只有第二个义项,但是现在大陆的“清纯”也常常用来形容少女,并且第一个义项也被收入了词典。“清纯”的词义发生引申除了可以解释为由互动造成之外,也能用同步引申来解释。因为义项一和义项二之间具有明显的引申关系,台湾“清纯”的引申轨迹可以扩散到大陆,使大陆的“清纯”也按照相同的线路引申出义项二。也就是说,同步引申不仅发生在同一个词汇系统中意义相关联的词之间,也可以发生在具有同源关系的不同词汇系统之间。
同样,大陆和台湾对外来词或方言词的借入也可能是在各自词汇系统内完成的“同步借入”。以闽南方言中的“乌龙”为例,该方言词进入普通话词汇系统有两种可能途径:一是经由台湾“国语”或其他方言的中介进入,二是普通话直接从闽南话中借入。如果是第二种途径,那么就可以说普通话和台湾“国语”在没有互相接触的情况下“同步借入”了一个方言词。
此外,两岸词汇还存在“同步缩略”现象。即两岸的词汇系统中都存在同一个短语或短语式多音节词,它们在不发生互动的情况下各自以相同的模式进行缩略。例如,海峡两岸都有“电动玩具”这个短语,它在台湾率先缩略为“电玩”,而后,大陆也出现了“电玩”的叫法。大陆“电玩”的缩略途径有两种可能:一是普通话直接借用了台湾缩略以后的名称“电玩”,二是“电动玩具”在普通话中以与台湾“国语”相同的模式自发地缩略为“电玩”。后者即是“同步缩略”。在这里,特定词语出现早晚的时间因素不是根本,相同的生成过程则都体现了语言的经济性原则。
当然,同步现象虽然常见,但是它排除了所有的外因,只考虑了系统内部因素对词语演变的影响。现实中,我们很难排除系统外因素的存在,从一个更全面的视角来看,词汇系统间的接触和词汇系统内部的调节机制往往共同起作用,引发互动和演变。也就是说,单个词汇系统内部因素和其他词汇系统的影响都为互动作出了贡献,内外两种力量汇合成一股合力,形成一种词汇互动的合力作用。其中,词汇系统内部的调节机制决定了互动能否发生,而外部其他词汇系统的影响则是催化剂,对互动和演变起到促动作用。
五、结语
两个社会群体的交往中,影响对方语言系统的同时,也会从对方系统中汲取有效的成分,而且这个过程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分阶段的、时间有长有短的、程度深浅有别的,互动的效果是在系统中的并成系统性的、动态发展的,不仅给双方系统带来新的语言要素,同时也在不断调整着要素之间的关系,从而使语言结构总是处在一种动态的平衡之中。
基于此,本文将海峡两岸词汇系统的互相影响方式归纳为七种互动模式:替换式互动、单边增量式互动、双边增量式互动、返还式互动、他源式互动、新生式互动、激活式互动。这里所说的“互动”就交际总体而言的,并不是所有的互动模式都一定会发生两个词汇系统的互相影响,有的目前还只是单方面的影响,即局部互动,它们是互动的一个环节。此外,根据词语互动能力的强弱和互动时间的长短,我们还将互动分为深互动、浅互动、潜互动三个层级,反映了海峡两岸不同词语在互动深度上的差异。互动过程是一个快慢不一、逐步扩散、由浅入深的过程,而且不同互动模式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的情况,甚至可以说合力作用比单力作用更为普遍。而海峡两岸的词汇系统之所以能发生如此丰富多彩的词语互动,从语言内部看,两个词汇系统有着相似的构词材料和构词规则,这也是同步现象的根源;从语言外部看,是由于两个社区在近几十年来发生了规模庞大的社会接触。
这种基于互动观念的研究为动态地研究词汇乃至语言系统提供一个新的观察视角。过去的相关研究大多是分别考察所受的影响,而对互动式的结构关系关注得不够,较少展开系统的分析。因此我们相信,对海峡两岸词语系统乃至语言交际系统的互动关系的研究,将会推动我们对语言系统的动态发展过程作出新的思考,对动态研究的路径和方法作出新的探索。
注释:
①汤志祥(2006)及刘小林(2006)等文献都将“互动”看作已经影响了大陆的台湾特有词语,本文依此,具体情况还需要进一步考察。作为短语使用,“互动”出现得比较早,如:“凉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侧耳远听,胡笳互动,牧马悲鸣,吟啸成群,边声四起。”(西汉李陵《答苏武书》)现在“互动”的意思也可以看作这种组合词汇化后的自然引申。
②“短语式多音节词”即内部结构是短语形式,但又作为整体使用的一类词,如下文的“厢型小客车”。
③当然也不排除海峡两岸同时减缩某个短语的情况,这就出现了殊途同归的现象。
④根据笔者的调查,“渠道”的比喻义在台湾的接受度也是有差异的,其使用人群往往跟大陆密切交往。“渠道”此义项的引入,在台湾“国语”中必然跟既有的“管道”用法发生交叠,两者正在进一步调整过程中。
⑤于根元(1995,2005)都提到了语言的“新颖色彩”,认为语言在表达基本的理性虑义之外,还要表达色彩和别的。新的语言现象不断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寻求新颖色彩。有的新词新语使用多了,新颖色彩会磨损。
⑥田小琳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提出“社区词”概念,她在《香港社区词词典》(2009)中对“社区词”的定义是:“社区词即社会区域词。由于社会制度的不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的不同,以及不同社区人们使用语言的心理差异,在使用现代汉语的不同社区,流通着一部分各自的社区词。”具体地说,这些社区包括中国内地、台湾、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海外华人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