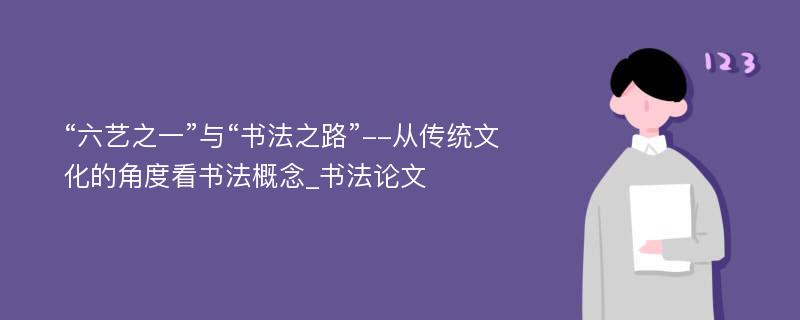
“六艺之一”与“翰墨小道”——传统文化视野中的书法观念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翰墨论文,小道论文,传统文化论文,书法论文,视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从王羲之“为艺所累”说起
宋人洪迈在其《容斋随笔》中,曾这样评价羲献父子的“德”与“名”:
王逸少在东晋时,盖温太真、蔡谟、谢安石一等人也,直以抗怀物外,不为人役,故功名成就,无一可言,而其操履识见,议论闳卓,当世亦少其比。公卿爱其才器,频召不就。……其识虑精深,如是其至,恨不见于用耳。而为书名所盖,后世但以翰墨称之。《晋书》本赞,标为唐太宗御撰,专颂其研精篆素,尽善尽美,至有“心慕手追”之语,略无一词论其平生,则一艺之工,为累大矣。献之立志,亦似其父。谢安欲使题太极殿榜,以为万代宝,而难言之,试及韦仲将凌云榜事,即正色曰:“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长。”遂不之逼。观此一节,可以知其为人,而亦以书名之故,没其盛德。二王尚尔,况于他人乎!①
羲之风概,世所钦羡。献之效父,本属常情。从《世说新语》所载羲之逸事中,我们亦可窥知其“操履识见,议论闳卓”的胸量与眼界:
王右军与谢太傅(安)共登冶城,谢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王谓谢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费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谢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②
正是在此“清言”“玄谈”盛行的时代,羲之却慧眼独具,警告谢安勿作空想,而须务实去虚,如此识见,诚为不易。羲之功业,实不止此,然为世所熟知者,却是其书名,故洪迈叹其“以书名之故,没其盛德”,反照于古贤的德、功、言三立的人生至义,此亦当感慨系之。
然而,后人也有不同洪迈之论者,如元人王恽题画诗云:
王谢当年奕世豪,东山逸兴更滔滔。不应经略中兴志,留在书名与日高。③
羲之艺文才具,世所著称。王恽不仅暗示了羲之以书擅名不仅毫不逊色,而且还隐意他具有超越书名本身的更高功名。其实,这种相左之论,尚不仅见于此,在明人的话语中,也将之作为书艺与功业孰当为重的由头,引而申之。如明代开国功臣刘基为《兰亭序》题跋曰:
王右军抱济世之才而不用。观其与桓温戒谢万之语,可以知其人矣!放浪山水,抑岂其本心哉?临文感痛,良有以也,而独以能书称之后世,悲夫!④
刘基文韬武略,英豪一世。以丈夫之志,辅佐朱元璋安邦定国,成就一代伟业,人皆仰之。在他看来,放浪形骸、临文嗟悼,乃是风雅文人感时伤怀的情调,非羲之本心,更非心系家国天下的传统士大夫所固存的文化心态。然而羲之未能尽用经国济世之才,却终以书艺名世,不免令人惋惜。刘基此意,恰与王恽相反。实际上王恽也是元代政治中的俊才,不仅好学善文,而且颇有政绩,史载他“治钱谷,擢材能,议典礼,考制度,咸究所长,同僚服之”⑤,故其足具治世之能,并非仅通艺文之雅士。也可推知王恽对羲之的褒扬,应是基于“济世之才”的理想而感发。
而晚明李贽(卓吾)对于羲之及其功名,也颇有独见,他说:
先生谓逸少识虑精深,有经济才,而为书名所盖,后世但以翰墨称之,艺之为累大哉!卓吾子曰:艺又安能累人?凡艺之极精者,皆神人也,况翰墨之为艺哉!先生偏矣!或曰:先生盖自寓也。⑥
李贽乃阳明后学中人。王门之学,多染禅风,自性率真,语语胸流。尤其李贽,“离经叛道”、不合时宜,世人多以为异端,目为“狂禅”。其所谓“凡艺之极精者,皆神人”,虽有夸张,然对于“艺之为累”的观点的异议,也当出自性情。
实则艺文之业,虽不如经世大道显赫,但亦可表现活泼生机。如李贽的另一条读史心得,更能证此:
“北海(孔融)大志直节,东汉名流,而与‘建安七子’并称;骆宾王劲辞忠愤,唐之义士,而与‘垂拱四杰’为列。以文章之末技而掩其立身之大闲,可惜也!”
卓吾子曰:“文章非末技,大闲岂容掩?先生差矣!或曰:先生皆自况也。”⑦
李贽引驳的内容,乃是明代大才子杨慎之语。杨慎谓孔融与骆宾王皆因文章之名而掩盖了自己立身处世的基本准则,实为可惜,“君子当表而出之”⑧。此论有本可据:史载孔融“负其高气,志在靖难,而才疏意广,迄无成功”⑨;骆宾王则“落魄无行,好与博徒游。高宗末,为长安主簿,坐赃左迁临海丞。怏怏失志,弃官而去”⑩。但李贽不同意杨慎的看法,甚至认为更像是杨氏“自况”,乃因杨慎及其父杨廷和二人由于“议礼”之事为嘉靖帝所恶,嘉靖“每问慎作何状,阁臣以老病对,乃稍解。慎闻之,益纵酒自放”,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杨慎“好学穷理,老而弥笃。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11)。作为明代著述列冠的文人,杨慎文名不谓不显,然竟也两次受到廷杖,终而流放云南,结局如此,恐有因于文才之自负。李贽此谓杨慎“自况”,实是暗藏了对他的奚落。
上述话语的吊诡,乃因士人对“道”与“艺”的两极观念而产生:一方面他们心怀天下,希望以德言事功标榜,故以“小道末技”为不屑;一方面又深感仕途坎坷,难博青眼,故转而工心艺文,这样既可自适,也可名世。如身居高位的书画大家董其昌,就曾流露此种心迹:
多少伶俐汉,只被那卑琐局曲情态,担阁一生。若要做个出头人,直须放开此心。令之至虚若天空、若海阔;又令之极乐,若曾点游春,若茂叔(周敦颐)观莲,洒洒落落。一切过去相、见在相、未来相,绝不罣念,到大有入处,便是担当宇宙的人,何论雕虫末技?(12)
董氏之言,根于佛禅,然所指则如儒家“担当宇宙”的君子气概。若能经世治道,“何论雕虫小技”。同时,董氏又于书画之事,苦心经营,议论森然。他曾说:
翰墨之事,良工苦心,未尝敢以耗气应也。其尤精者,或以醉、或以梦、或以病,游戏神通,无所不可,何必神怡气王,造物乃完哉?世传张旭号草圣,饮酒数斗,以头濡墨,纵书壁上,凄风急雨,观者叹愕;王子安为文,每磨墨数升,蒙被而卧,熟睡而起,词不加点,若有鬼神,此皆得诸笔墨蹊径之外者。(13)
艺文之事,虽非道济天下之伟业,亦是彰显生命人格的正途。王羲之的功名成就,正处于士人精神与文人末技二元对立的尴尬审视之中。洪迈、刘基、杨慎诸人对于以艺掩德的叹惋,乃是借此突出经略国事的士人理想。孔子云:“士志于道。”(14)此“道”是治世之“大道”,须基于历史精神的丰厚和个体人格的完善而构建,由此方能担当社会责任和安顿文化生命,而非仅以“文章末技”或“翰墨小道”可以彰显。然而这种观念,在一方面凸显经世价值、轻视艺文事业的同时,却在另一方面又营求雅尚之习、精修干禄之技——如对于书学一艺的矛盾心态,便是如此。
二、蒙童识字与“六艺”之“书”
上古之“书”,并非如后来意义上的“书法”,它是基础教育阶段蒙学求知的课目,为“六艺”之一。在周代的教育体系中,“养国子以道”,教之六艺与六仪,是为“小学”。“六艺”者,“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15)。孔门儒学以六艺授徒,其后儒家递相沿袭,教课学童,以备入学修业之需。再后“小学”的范围逐渐缩小,主要指六艺之一的“书”。如东汉马融曰:“书,文字也。……书止为六艺之一,而以之教小学者,盖书者,学之所始,教之于始,固其所以成之也。”(16)在《汉书·艺文志》“小学类”中,所收皆为字书,当有所因。《说文·叙》亦云:“汉兴有草书。《尉律》:学僮十七以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史。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太史并课,最者以为尚书史。书或不正,辄举劾之。”(17)可知“书”的意义已经不只限于识读习字的原初范畴,而更看重审美性的书写。其时,能通《仓颉》、《史籀》篇者,可获任兰台令史,兰台令史是中央政府中的文化机构负责人,“掌奏及印工文书”(18),他们精通字学,博古通今,学识足范世人。唐代国子监下也设有“书学”,主要教习文字与书法,由此,书法正式成为官方教育体系的一个重要门类。当时作为蒙童正字和试策仕进的干禄字书,流布浸广,乃与官方的文化政策深有关系。
由于六艺之“书”原本是一种“技艺”,属“小学”之技而非“大学”之道,以致后人进而将书法视为“末技”,其来有本于此。
最初作为技能的文字书写,一旦社会伦理、制度文化以及审美意识附于其上,便就不只是技巧性的模仿和制作性的重复,而是艺术及其观念的意义再生。由此,六艺之“书”便从功用性的习字上升到道艺兼修的境界,这种意涵的扩展,本质上具有创造性和人文性的双重特征。同时,上方对作为文字书写艺术的书法的倡导和推广行为——如国家政制中与书法相关的文化机构设置、主流话语对经典书家与法帖的推重、意识形态对人品书品关系的特殊演绎等等,各个方面的综合因素,都促使了书法艺术的特征显现和格调升华。耐人寻味的是,此一进程中的主导力量,正是视书学为末技而“志于道”的士大夫们:他们塑造和提升了书法的文化品格,反过来这种品格也丰富和充实了他们的艺术生命。因此,我们会发现,那些一再强调自己不工书法的士夫文人,却对此道颇有修为,甚至是名头和影响力都不小的人物。
尤可注意者,一些贵享九五之尊的帝王,对此道的兴致并不亚于普通知识群体。如唐太宗、武则天、宋徽宗诸帝,已是书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典型人物。至于清代,皇家的热忱参与,更加丰富了书法文化的发展态势。如康熙帝曰:
书法为六艺之一,而游艺为圣学之成功,以其为心体所寓也。朕自幼嗜书法,凡见古人墨迹,必临一过。所临之条幅手卷将及万馀,赏赐人者不下数千。天下有名庙宇禅林,无一处无朕御书匾额,约计其数亦有千馀。大概书法,心正则笔正,书大字如小字。此正古人所谓心正气和、掌虚指实,得之于心而应之于手也。(19)
康熙所称“自幼嗜书法”,考诸史事,并非虚言。这种嗜好,承启下代,莫不浸浸。如雍正帝自述学书之事云:
自古帝王临政之暇,往往留意翰墨。其间名臣哲士,多工书法。汉晋以下,代有闻人,后世采集勒石,俾流传永久。银钩铁画,照耀百世。如三代彝鼎,信可宝玩。盖书学为六艺之一,挥毫濡墨,纵笔所如,而波磔意度之间,结构神采,劲健古秀,斯为上品。……我圣祖皇帝(康熙)法书,云辉星灿,集古今之大成。朕朝夕侍左右,瞻仰天章,时蒙圣训,故留心书法最久,所见历代法帖亦最多。(20)
雍正之“留心书法”,广睹法帖,正因朝夕侍于皇父康熙左右,“瞻仰天章”;而其子乾隆帝更嗜书法,经眼博洽,书迹煌煌,洵为一代胜概。康、乾在位最久,所遗翰墨尤多。二帝皆喜赏鉴与题字,其后诸帝也多所效之。从现在大量遗有的印章与书作来看,即见其书法人文之一斑。在书法史上,康乾二帝对董其昌和赵孟頫的推崇,甚至影响了整个清代书法的走向——尤其是晚清碑学的盛大气象,正是针对前期帖学流弊而发出的强力反拨(21)。当然,基于赵、董帖学而构建的馆阁体,虽然积重难返,但由于科举之需,即便像阮元、康有为此等不屑帖学的文人,如欲仕进,也必先精于馆阁工楷,不敢轻越雷池。
书法一艺,不只是帝王和士大夫用以标举德政、修身养性的重要方式,也是文人才子晋爵扬名的手艺展示和场面功夫,甚至下层民众,也以习书来突出其“文化人”的身份。当然,剥开书法作为人生的高雅修养不论,即以实用而言,它也堪为“有用之技,人生不可缺者”,清人苏惇元对此说得颇为透彻:
书者,小技也,然为六艺之一,古之小学教焉,乃有用之技,人生不可缺者也。上而制、诰、谕、敕,中而表、奏、笺、启、试卷、碑版,下而牒移、文案、契券、帐籍,皆所必须。精于八法者固佳,否则亦宜走笔顺利,清晰整齐。(22)
推而思之,除了由于国家的政治需要而推动书法发展这一因素外,书法相对其他艺术如绘画、雕塑等来说,本身更具实用性,且工具简单,易于入门,不同阶层和地位的人皆可工习——这其实也是至今书法艺术长盛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
六艺之“书”,原本是以习字为核心的书写行为,随着时代的进步和文化的发展,进而受到人们对它的观念提升和意义审视,故其虽为生活常事,亦显文化人生。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中国古代教育体系中重要一环的“书”,不仅是官方的教化之举,也是民间的自觉行为。即如汉魏时期的《熹平石经》和《三体石经》,以及唐时的《颜氏字样》、《干禄字书》诸种,都是具有一定官方色彩的正字之作。由于知识的普及,一般民众的文化意识逐渐增长,因而在官方之外,具有一定水平的文士们,也为满足社会教育与大众生活的文化需求,分类编纂各种浅显易懂的通识性读物,既可借此获利,也顺应了官方意图的宣达和民间文化的发展。如宋代的《事林广记》,元代的《居家必用事类全集》,明代广泛流行的《万宝全书》、《居家必备》、《三才图会》以及清代至民国间各种增补的“万宝全书”等等,皆是如此。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这些日用类书大多数都有相当的篇幅来介绍书学常识,指导技法临习(23)。如此看来,民间社会中的书学,已不只用于蒙学入仕,还具有普及与提升大众艺术素质的作用——当然,它也是日常生活中的一项必备技能。
三、“志道”与“游艺”:从书学小技到立品致身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24)六艺之学,不惟启蒙开智之始,亦为立身行世之需。唐人刘禹锡也曾以书学答问的方式,借题阐释儒家“游艺”之说:
或问曰:“书足以记姓名而已,工与拙何损益于数哉?”答曰:此诚有之,盖举下之说耳,非中道之说。……是数者皆不行举下之说,奚独于书也行之耶?《礼》曰:“士依于德,游于艺。”德者何?曰至、曰敏、曰孝之谓。艺者何?礼、乐、射、御、书、数之谓。是则艺居三德之后,而士必游之也;书居数之上,而六艺之一也。(25)
“艺居三德之后”,并非说“艺”无足轻重,而是强调它要以道德修养为先导,故“士必游之”。书为一艺,既为士人之学,也是君子之修,固非“足以记姓名而已”。明清之际的顾炎武谓“古人入学自六艺始,孔子以游艺为学之成”(26),正与刘氏遥契。儒家如此注重艺术的教化功能,即因艺术不仅能陶冶心性、澡雪精神,而且也能让人尊重文化伦理、回复人性本原。
唐代裴行俭曾对王勃等人“虽有文才,而浮躁浅露”的品行颇有微词,认为“士之致远,先器识而后文艺”(27)。这种观念,乃是本于儒家的积学体验和修养功夫。“致远”之说,出于子夏,其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何晏注云:“此章勉人学为大道正典也。小道谓异端之说,百家语也。虽曰小道,亦必有小理可观览者焉,然致远经久,则恐泥难不通,是以君子不学也。”(28)对此,朱熹进一步解释道:
小道不是异端,小道亦是道理,只是小。如农圃,医卜,百工之类,却有道理在。只一向上面求道理,便不通了。若异端,则是邪道,虽至近亦行不得。(29)
对士人们来说,小道虽然可观,但若要经略治平之大事,则绝不能沉溺其中。由此反观裴行俭之言,所谓“先器识而后文艺”,其终极目的正如对“正典大道”的勉学。
儒家强调“德成而上,艺成而下”(30),即必先“据于德”方可“游于艺”,否则如舍本逐末。尤其对于帝王人主,韵律词曲、书画文章,当是德政臻善后的“游艺”,故若国之不振,切不可刻意为之。如史载晚明万历皇帝曾手书“弼予一人,永保天命”八个大字赐帝师张居正,但张却以历代沉迷一艺而终至亡国的帝王为例,正色谏曰:
帝王之学,当务其大。自尧、舜至唐、宋贤主,皆修德行政,治世安民,不以一艺。汉成帝知音律,能吹箫度曲;梁武帝、陈后主、隋炀帝、宋徽宗皆能文,善书画,无救于乱亡。则君德之大,岂沾沾一艺哉!(31)
此谓“当务其大”,其旨本于孟子,孟子曰:“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32)乃强调君子当有大志,而不斤斤于小者。在张居正看来,帝王“君德之大”,不在一艺之能,而应胸涵宏大气象,以“修德行政,治世安民”为要务。这是传统儒家的为政之道,也是士人的社会理想。是故,他们常不以艺文盛名标榜,更看重社会对自己道德风范和功业成就的肯定和褒扬。无论是否真正出于本心,这种境界超越似乎已成为他们一以贯之的人生愿望。也因此,对于学问文章、诗词曲赋之类的“末艺”,士人们便产生了某种颇为诡异的“偏见”。如程颐认为“作文害道”(33),王灼则谓:“文章小技,何济于横流;忠义大闲,誓坚于素守。”(34)清人陆世仪亦云:“学者既有志于道,则诗文且为末技,况词曲乎?”(35)皆有所自。
相较于作为“小道”的学问文章来说,字学书法则更为士人不屑。如南宋裘万顷有诗句云:“词章末技耳,安能媲皇坟?而况字书学,兀兀纂说文。”(36)若就此类观念再溯其远,则东汉赵壹对书法的批评,更具意气:
草书之人,盖伎艺之细者耳。乡邑不以此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讲试,四科不以此求备,征聘不问此意,考绩不课此字。善既不达于政,而拙无损于治,推斯言之,岂不细哉?夫务内者必阙外,志小者必忽大。俯而扪虱,不暇见天。天地至大而不见者,方锐精于虮虱,乃不暇焉。(37)
赵壹之论,究竟是因承儒家传统的志道游艺观念,还是出于自己拙于书法的泄愤,不得而知。然赵壹也是当时辞赋名家,若按此批评逻辑,则其辞赋之能也“不达于政”、“无损于治”。与之同时的蔡邕,其所论者,也大率类此。据《后汉书》载,熹平六年七月,邕上封事陈政要七事,第五事中曰:
夫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国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经术,听政馀日,观省篇章,聊以游意,当代博弈,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若乃小能小善,虽有可观,孔子以为“致远恐泥”,君子故当志其大者。(38)
蔡邕书法,古来称善。史传蔡邕见白垩刷墙而悟“飞白”,始刻于熹平四年的法书经典《熹平石经》,也正是他主持书石的正字之作。但其谓书画辞赋不能“匡国理政”,并借孔子之语劝谏,知其本意,即源自儒家的经世立场,与赵壹同发一气。
其实赵蔡二人所鸷评者,并非书画辞赋本身,而是朝廷以之作为“教化取士”的政策。后人多视书画辞赋为“小道”,然时移世易,他们对古人持论的有意无意的“误会”和“偏见”,以致在不断的观念演进中,渐至形成一种对艺术品格的自然而然的“小道”思维,如此悖论,殊为可怪。
再如唐太宗,即使他对羲之及其书法顶礼膜拜有加,却对书学之事并不以为高深莫测,认为只要不时留心临习,便有所成。据载:
太宗尝谓朝臣曰:“书学小道,初非急务,时或留心,犹胜异日。凡诸艺业,未有学而不得者也。”(39)
唐代书学大盛,人皆工书,“盖魏晋以来,风俗相承,家传世习,故易为工也”(40)。然其品格较于魏晋,实多不逮。如明人谢肇淛引南宋朱翌(新仲)所论曰:
朱新仲《猗觉寮杂记》云:“《唐·百官志》有书学一途,其铨人亦以身言书判,故唐人无不善书者。然唐人书未及晋人也。欧、褚、虞、薛亦傍山阴父子门户耳,非成佛作祖家数也。右将军初学卫夫人,既而得笔法于锺繇、张芝,然其自立门户,何曾与三家仿佛耶?子敬虽不逮其父,然其意亦欲自立,不作阿翁牛后耳。”(41)
康有为也说:“唐立书学博士,以身、言、书、判选士,故善书者众。鲁公乃为著干禄字书,虽讲六书,意亦相近。于是,乡邑较能,朝廷科吏,博士讲试,皆以书,盖不可非矣。”(42)唐人善书者众,然而却不易“自立门户”,铨选之需、利禄之逐,当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历史地看,在书法作为“教化取士”的重要条件的时代,像赵壹、蔡邕之类的批评者并不鲜见,甚至其中不少人就是以书法名世的艺术家。如明清书法史上颇具影响的傅山,也似乎不屑于自己的善书之能,强调:“文章小技,于道未尊,况兹书写,于道何有?”(43)再如乾隆时期的书家桂馥,史载其“少嗜学,于书无所不读,尤究心小学金石,工篆隶。……兼娴刻印,世人比诸文三桥;然特末技,未足为先生重也”(44)。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何“四库提要”认为书画到了后世已经流为“赏鉴一途”,且将之与琴棋歌舞“并为一类,统曰‘杂技’”(45)。而康有为更斥言书法乃是“艺之至微下者”,为“无用之末艺”,其云:
夫学者之于文艺,末事也。书之工拙,又艺之至微下者也。学者蓄德器,穷学问,其事至繁,安能以有用之岁月,耗之于无用之末艺乎?(46)
又云:
夫书小艺耳,本不足述,亦见凡有所学,非深造力追,未易有得,况大道邪?(47)
很难想象,作为晚清碑学大家的康有为竟持此论。从相关史载中,我们也可见康氏对“大道”与书法之关系的类似观点。如郑逸梅曾记载友人徐润周拜谒康有为一事——据徐氏回忆,康有为见他时,问其年龄,答曰二十六岁,康氏便说:
曾湘乡(国藩)于同岁开始研寻圣道,尔正同此年岁,大可及时求进于道。方今国事阽危,立志以远大为鹄,书法乃小道,仅可馀时为之耳!(48)
其实,康氏骨子里本是传统的士大夫,匡国理政、维新变法,是为人生伟业,故于书艺一道,未想作此大观。康有为曾撰《广艺舟双楫》一书,直面书法艺术的前途,具有划时代的变革精神。虽然我们不排除康氏此书正如其《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之类的著作一样,因应变法之势,为矫枉而过正,但不可否认,对于像康有为一样的士人来说,书法正是他们的艺术血脉,无论他们自己如何批评此等“馀事”,但蕴含其中的文化情结皆难以割舍。
因此,传统士人声称不屑于辞章书画之工巧,然而自己心底对于艺文之事的热衷并不减于他人——甚至身为一国之君者,也并未真正鄙视这种“小道末技”,反而将之上升到治国安邦的高度,如曹丕就说道:“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49)一些士人虽不以工辞章书画显能,却也强调志道与游艺二者的调和融通,如明初的危素就曾为文章之功用辩云:“文章之有功于世尚矣,乌可以为儒者之末技而轻之哉?”(50)而曹丕所谓的“盛事”,危素所谓的“有功”,论之于书法亦然。如唐代张怀瓘就说:
尧舜王天下,焕乎有文章。文章发挥,书道尚矣。夏、殷之世,能者挺生。秦、汉之间,诸体间出,玄猷冥运,妙用天资。……其道有贵而称圣,其迹有秘而莫传。理不可尽之于词,妙不可穷之于笔。非夫通玄达微,何可至于此乎?乃不朽之盛事,故叙而论之。(51)
阐《典》、《坟》之大猷,成国家之盛业者,莫近乎书。其后能者,加之以玄妙,故有翰墨之道生焉。(52)
尤其以“身言书判”为选士标准的科举时代,书法精妙者更易得入仕之便。如明人徐一夔友人周致尧,便以“能书”而获仕,据徐氏记载:
友人四明周君致尧,精敏过人,少游乡校读书,为辞章有声。年二十,从其外氏游宦齐鲁之境,……居无几何,会大丞相为国求福,选天下能书者遍书大藏佛典,而授以文学之职。致尧适在选中,既竣事,出为其乡之鄮山书院山长,再调秀之宣公书院,方是时,致尧年才三十馀,与致尧游者咸曰:“以致尧之材之年,而假兹艺,致身不亦左乎?”余解之曰:“书非末技也,昔人固尝用以取士矣,以书致身,亦入仕一途也,奚名为左?”(53)
“以书致身,亦入仕一途”,正毫不隐讳地点明书法之于利禄的“形而下”意义。像此类以书艺之能而特受上方眷顾者,例不少见。如清人王士禛《分甘馀话》云:
本朝状元必选书法之优者。顺治中世祖皇帝喜欧阳询书,而壬辰状元邹忠倚、戊戌状元孙承恩皆法欧书者也。康熙以来,上喜二王书,而已未状元归允肃、壬戌状元蔡升元、庚辰状元汪绎皆法《黄庭经》、《乐毅论》者也。惟戊辰进士中工二王体者,首推海宁查昇,以其族叔嗣韩兼习《五经》,拔置鼎甲,昇遂抑置二甲。(54)
《清史稿》载姜宸英殿试时受康熙帝赏拔事云:
姜宸英……举颇天乡试。(康熙)三十六年,成进士。廷对李蟠第一,严虞惇第二,帝识宸英手书,亲拔置第三人及第,授编修。(55)
嘉庆时期的何凌汉也以书法之佳,被嘉庆帝从第四特拔为第三,据近人杨钟羲《雪桥诗话》载云:
嘉庆乙丑,何文安(何凌汉谥号)殿试卷进呈在第四,睿皇帝(嘉庆帝)谓笔墨飞舞,拔置第三。(56)
科举社会中,由于应试要求之严格,以致习书为业、以书仕进者多见。社会文化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又恰是以此等“末技”为一种重要的表现方式,故士人们在传统思维的逻辑观照中,对于长于艺文者,又附以“人品”的道德外衣,由“末技”而通“大道”,作为某种程度上的观念调和。为艺者,必先修德养节,方能凸显书法格调。对于此理,古来多所认同。如宋人费衮曰:
书与画皆一技耳,前辈多能之,特游戏其间,后之好事者争誉其工,而未知所以取书画之法也。夫论书当论气节,论画当论风味……至于学问文章之馀,写出无声之诗玩,其萧然笔墨间,足以想见其人,此乃可宝。(57)
在费衮看来,作为一技的书画,本身并不见重于世,可贵的是作者的品德。元人柳贯《跋赵文敏帖》一文,也与之相类:
往予在京师,从文敏(赵孟頫)最亲且久,窃尝有讲于书法曲折。盖书虽末艺,而必以学为橐钥,识为机栝,而区区求精于笔墨之间者,望其阃域,难矣。盖文敏之书,根于英姿敏识,而成于清机绝鉴,非可以一蹴至也。(58)
明人锺惺也以“精神学问”为标准,强调书家当备此素质:
微独书,凡夫操之一人而能为可久者,其精神、学问必有一段不敢苟、不肯轻为同者也。……今遍地皆书家,而古人书法已亡。无他,同而不求其至。叩之以“精神学问”四字,而茫然不能应。……今言书必称江南,以江南人遍地皆书也,试叩之以“精神学问”,应者几人哉?(59)
此即暗示积学涵养裨于艺格境界的提升。清人朱和羹也认为:
书学不过一技耳,然立品是第一关头。品高者,一点一画,自有清刚雅正之气;品下者,虽激昂顿挫,俨然可观,而纵横刚暴,未免流露楮外。故以道德、事功、文章、风节著者,代不乏人,论世者,慕其人,益重其书,书人遂不朽于千古。(60)
这种关于读书助益书法的观点,世之论者亦夥,他们也多认为书法当以德行与学养为基础,方不落俗套,道通大化。在此语境下,作为六艺之一的“书”,又在艺术文化的演进中被推升至另一个道德审美的极端,所谓“人品如书品”、“心正则笔正”、“书贵立品”等等说法,将道德品格与艺术品位挂钩,成为中国美学批评的一种特殊话语。孙犁为《中国书法全集·康梁罗郑卷》的题跋,正可作此印证:
书法者,知识分子之馀事,然亦处世之大节,观此集,可知文字非小道,文人之政治趋避,亦反映其间。(61)
四、自娱与娱人:文人生活中的书法及其观念
晚明李日华在其《六研斋笔记》中对北宋苏轼、米芾、文同诸人的艺与道评论曰:
子瞻雄才大略,终日读书,终日谈道,论天下事;元章终日弄奇石古物;与可亦博雅嗜古,工作篆隶。非区区习绘事者。只因胸次高朗,涵浸古人道趣多。(62)
苏轼尝云:“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63)是谓得古人之“道趣”而不践覆古人,方有“新意”。又云“草书非学聊自娱”(64),此等狂傲风骨,正是基于“胸次高朗”的境界而生发。故清人吴德旋说:“东坡笔力雄放,逸气横霄,故肥而不俗。要知坡公文章气节,事事皆为第一流。馀事作书,便有俯视一切之概,动于天然而不自知。”(65)此说诚然。
书法乃为“自娱”之用,故可“无意”为之;“馀事作书”,正是文人生活世界中的风雅兴致。从明人袁中道的《作字》诗中,可见此等心态。其诗云:
浓寒不释冰,春来砚犹醉。今日天晴明,墨和可作字。我字不入法,聊恣一时戏。
心闲手勤时,间亦多遒媚。作诗惟伫兴,作字亦任意。未常强心为,虽拙大有致。(66)
文人以书法“聊恣一时戏”,“玩艺”的态度大抵如此,如清初方文也是“诵读之馀聊染翰”(67)。文人们在自娱之馀,亦可娱人。在袁中道为徽州墨家方澹玄的墨谱所作序文中,也能见得如此情趣:
当予少时,为举子业,汲汲书行卷字,兔起鹘落,聊以应世而已,亦何论墨之佳恶。行年四十,稍工临池之技,为人书箑,始稍稍知墨之可贵,然亦未常得佳墨也。(68)
此虽论墨,实为学书自述。袁氏当初习字,只为“聊以应世”,以备科举之需;四十岁后方工临池之技,为人书扇,也为应酬之劳。作为士人日常生活的书法,其功用多是在于应制作文、娱情怡性和交际应酬。袁中道的好友谭元春对于书法的态度也与之相类,谭氏云:
余于书法多懒而傲。懒则无意为书,傲则任意不书。予懒人亦懒,予傲人亦能傲,率将临池而罢。(69)
话虽如此,但在谭元春的生活中,以书酬赠之事也属常情。如他书诗与友人时,不忘自谑:“穷乡下里,无心相寄,作得一诗,书之扇,又书之册,又书之纸,如小家人蔬豉鱼菽,设了重设,岂不可笑。”(70)狼狈之状,令人捧腹。谭氏并不善书,他坦言:“我习点画事,未究点画意。”(71)娱己与娱人,都成了艺文生活中的调剂。
像谭元春这种不善书法却常为之所累的文人,并不鲜见,如与他同时的江盈科在书扇酬寄袁宏道时说:“世即无王右军,奈何遂遣不佞捉刀?弟诸箑差堪当葵叶,纵涂抹如老鸦,不悔形秽。”(72)日常书法赠酬在所难免,临池功夫则需精进,学有所成,示与他人,不致汗颜。当然,也有不愿应酬,惟恐避之不及者,如明人陆树声自言:
余无字学,兼不好书,间有挟卷轴索余书者,逡巡引避。(73)
人之好其书,亦因慕其名。即如明代著名山人陈继儒之流,虽书艺草草,却索之者众,应接不暇,如黄宗羲曾记述陈继儒应酬书扇事云:
岁戊辰,余入京颂冤,遇之(陈继儒)于西湖。画船三只,一顿幞被、一见宾客、一载门生故友,见之者云集。……侵晨,来见先生者,河下泊舶数里。先生栉沐毕,次第见之。午设十馀席,以款相知者。饭后即书扇,亦不下数十柄,皆先生近诗。(74)
更有一些不善书法者,却好以论书、学书为能事、雅事。如王世贞“不善书,好谈书法,其言曰:‘吾腕有鬼,吾眼有神。’”(75)清初吴三桂也拙于书法,然喜临池。据《清稗类钞》载:
吴三桂不善书而喜临池。……春秋佳日,三桂辄携笔墨于轩中,作擘窠大字,侍姬数十辈环侍于前,鬓影钗光,与苍翠之色互相辉映,厕身其中,不复知世间有尘俗境也。(76)
同书还载纪晓岚也“不善书”,然纪氏心态不无自嘲:
纪文达公(晓岚)博洽淹通,……独不善书。即以书求者,亦不应。其书斋所设之砚,有匣,镌二诗于上云:“笔札匆匆总似忙,晦翁原自笑锺王。老夫今已头如雪,恕我涂鸦亦未妨。”“虽云老眼尚无花,其奈疏慵日有加。寄语清河张彦远,此翁原不入书家。”(77)
诗虽调侃,却也发自性情。
作为聊以遣兴的书法,并未被士人们视为人生正业,在他们看来,书法不佳,本就无可厚非。因此,像王世贞、纪晓岚这种“不善书”而名世者,也会成为后世文人聊以自慰的参照,如清人昭梿自比曰:
余素不善书,人争嗤之,深以为耻。然明王凤洲尚书素不善书,尝自云:“吾目有神,吾腕有鬼。”近时纪晓岚尚书、袁简斋(袁枚)太史皆以不善书著名。按《晋史》,武帝疑太子不慧,召东宫官领而以尚书疑事命其判决。贾氏乃命张泓代对,而太子手书以呈,武帝称善。按惠帝愚闇,世所罕见,乃能手书决辞以对,笔画端楷可知。然则善书亦何足贵也。(78)
书艺之精远不如治世之能,书学“小道”,不必于此专力究心,而更在于为人之本与为学之功——这恐怕也是传统士人们的共同话语。如晚清大儒郑珍就认为书法只能学其规矩法度,而读书做人方是立身根本。他说:
吾极不善书,然能知书之利病。大抵此事是心画,其本之正、气之大、风格之浑朴、神昧之隽永,一一皆由心出,毫厘不可勉为。所谓学,只学其规矩法度耳。要书好根本总在读书做人。多读几卷书,做得几分人,即不学帖,亦必有暗合古人处,何况加以学力。……余拙于书,自抄书外,亦懒作字,而人多喜其拙,是诚不可解者。……坐谈皆无所用,聊借纸墨送日。(79)
近人姚永朴所记先祖姚莹入朝事迹,读来也颇有意思:
按察公(姚莹)入觐,宣宗(道光帝)询出身,以嘉庆戊辰科进士对。又问何以未入翰林,对曰:“以臣不工小楷耳。”上叹息久之。故为人题卷轴,多倩人代录,末署印章曰“天子知臣不善书”。(80)
姚莹能以“不善书”之名闻于上方,入朝班列,参政议事,不虚为天子之臣,也为昭梿“善书亦何足贵”之语作了例证。另有一位近代史上大名鼎鼎的思想家龚自珍,也与姚莹一样不善书法,未入翰林。但不同的是,龚未蒙圣恩,且以善书入翰林为耻,据清人孙静庵《栖霞阁野乘》载:
龚定庵为道光朝一大思想家,所为文诗,皆廉悍伟丽,不立宗派,思想尤渊渊入微。……遇达官贵人,辄加以白眼。生平不善书,以是不能入翰林。既成贡士,改官部曹,则大恨。乃作《干禄新书》,以刺执政。凡其女、其媳、其妾、其宠婢,悉令学馆阁书。客有言及某翰林者,定必哂曰:“今日之翰林,尚犹足道耶?我家妇人,无一不可入翰林者。”以其工书法也。(81)
不难推想,在“万马齐喑”的年代,龚氏能发出“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强烈呼吁,当是因于对社会与人生的深刻反思。其以书法论世,是为自娱,抑娱人乎?
五、末论
顾炎武曾言:“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82)不止对于诗文,至于书艺,士人们亦常如此理解,如我们从晚明黄道周对于书法的态度中,便能想见传统士人对于儒家道义担当的境界追求。黄道周曰:
作书是学问中第七八乘事,切勿以此为关心。……如写字画绢,乃鸿都小生,孟浪所为,岂宜以此溷于长者。必不得已,如今日新诗初成,抑如曩时长篇间就,倩手无人。(83)
黄道周为南明而死节,然其书名却甚于其忠烈事迹。不为书而书,正是提醒沉湎于“小道末技”之人:非能作计终生,遑论为政致道。
与顾炎武强调的“明道救世”观念相类,清末民初的严复为启蒙开智,痛陈时弊,振聋发聩。其中对书法的批评,言辞颇激:
自有制科来,士之舍干进梯荣,则不知焉所事学者,不足道矣。……鄙折卷者,则争碑板篆隶之上游;……魏碑晋帖,南北派分,东汉刻石,北齐写经。……诸如此伦,不可殚述。然吾得一言以蔽之,曰:无用。非真无用也,凡此皆富强而后物阜民康,以为怡情遣日之用,而非今日救弱救贫之切用也。(84)
严复虽然不像传统士大夫那样以科举入仕,然他对于国学之精研,却不减于时人。即以书学而言,不仅其书法功力不为逊色,而且论书论印诗文,也颇见造诣。只是国难时艰、民众蒙昧,当世变之亟,如此小艺,本非“救弱救贫之切用”之物,宜俟“物阜民康”,能得体泰心闲之时,方可以此“怡情遣日”。严复此论,足可见振起士人精神之用心,亦当使世人警醒。
实则在中国传统的知识社会,无论是官方机构为选拔人才之备,还是文化阶层为涵泳气质之需,作为六艺之一的书法(字学),乃是体现国家文治方略的一个重要手段。虽然这一“小道”并未成为士人仕途上进的主流门径,但对于他们人文精神的提升却有着重要的作用——即便一些士大夫不愿正视或承认,然而从现实看来,对翰墨艺事的经营却是其中不少人安身立命的基本功夫。无论苏黄米蔡,还是邢张米董,为政为艺,恐皆所累,而其政声与艺名相较,相隔则如霄壤天渊,非其不能为政,实多出于“理想”而已。是故,他们的历史生命大都通过这翰墨一艺表达出来。由此观之,古代士人对于“游艺”的轻视,实非真正的贬抑,而是借此以凸显不堕时流的风度气节和经世安邦的政治理想。这种思维,不仅存在于他们的文章言论之内,也会体现在其生命行动和日常生活之中。
注释:
①洪迈:《容斋随笔·四笔》卷十《王逸少为艺所累》,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734页。
②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17页。
③陈邦彦选编《康熙御定历代题画诗》卷三六“右军书扇图”条,北京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441页。
④刘基:《诚意伯文集》卷七《题王右军兰亭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94页。案:王羲之“与桓温戒谢万之语”,据《晋书》载:王羲之曾写信给桓温,大意是说谢万才华横溢,让他在朝廷任职,参与讽谏,将来必成大器。而现在让他去北方顺抚蛮荒,委屈了他的英迈之气,这是不会用人。但桓温不听,结果谢万“矜豪傲物,尝以啸咏自高,未尝抚众”,最终“狼狈单归”(见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七九《谢万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087页)。由此亦证王恽所言羲之的经略之志,盖有所自。
⑤宋濂等撰《元史》卷一六七《王恽》,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933页。
⑥李贽:《焚书》卷五《读史·逸少经济》,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592页。
⑦李贽:《焚书》卷五《读史·孔北海》,第593页。
⑧案:杨慎原文末尚有此七字,见杨慎《升庵集》卷四九,《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70册,第406页。
⑨范晔:《后汉书》卷七十《孔融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264页。
⑩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九○《文苑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006页。
(11)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一九二《杨慎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5083页。
(12)(13)董其昌:《画禅室随笔》,中国书店1983年版,第70页,第67页。
(14)“十三经注疏编委会”整理《论语注疏·里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4页。
(15)“十三经注疏编委会”整理《周礼注疏·保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16页。
(16)卫湜:《礼记集说》卷七二,收于纳兰性德辑《通志堂经解》第13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6年版,第97页。
(17)许慎撰《说文解字·叙》,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758页。
(18)范晔:《后汉书·百官志三》,第3599页。
(19)世宗胤禛纂《圣祖仁皇帝庭训格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17册,第191页。
(20)世宗胤禛撰《世宗宪皇帝御制文集》卷一二《跋淳化阁帖后》,《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00册,第98页。
(21)晚清金安清曾总结本朝书法风尚变化的趋势道:“馆阁书逐时而变,皆窥上意所在。国初,圣祖喜董书,一时文臣皆从之,其最著者为查声山、姜西溟。雍正、乾隆皆以颜字为根底而赵、米间之,俗语所谓墨圆光方是也。然福泽气息,无不雄厚。嘉庆一变而为欧,则成亲王始之。道光再变而为柳,如祁寿阳其称首者也。咸丰以后则不欧不柳不颜,近且多学北魏,取径愈高,成家愈难,易流于险怪,千篇一律矣。然白折小楷仍取匀秀。近日奏折,皆讥取士法不宜专尚试帖小楷。其实嘉庆以前,即有此二事,而不碍其为人才辈出。此语真因噎废食矣。”(金安清:《水窗春呓》卷下《馆阁书变体》,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1页)以此来看清代书法史,金氏此论甚合于实情,尤其所言“馆阁书逐时而变,皆窥上意所在”,就深刻反映了书法艺术的发展受到上方政治影响的尴尬态势。
(22)苏惇元:《论书浅语》,崔尔平选编点校《明清书法论文选》,上海书店1994年版,第859页。
(23)如从吴蕙芳所整理的“明清时期各版《万宝全书》目录”(计81种)来看,几乎每种书皆有“书法”或“字学”一门(吴蕙芳:《万宝全书:明清时期的民间生活实录》,台北花木兰文化工作坊2005年版)。王正华还曾就晚明福建版日用类书中“书画门”进行了专门的文化现象研究(王正华:《生活、知识与文化商品:晚明福建版“日用类书”与其书画门》,见《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1期,台湾“中央研究院”2003年9月)。
(24)《论语注疏·述而》,第94页。
(25)刘禹锡著,卞孝萱校订《刘禹锡集》卷二十《论书》,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49页。
(26)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五《乐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87页。
(27)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九○《王勃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006页。
(28)《论语注疏·子张》,第292页。
(29)朱熹:《朱子语类》卷四九《虽小道必有可观章》,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200页。
(30)“十三经注疏编委会”整理《礼记正义·乐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04页。
(31)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一《江陵柄政》,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45页。
(32)“十三经注疏编委会”整理《孟子注疏·告子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70页。
(33)案:“作文害道”,典出宋儒程颐答问,原文如下——问:“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为文不专意则不工,若专意则志局于此,又安能与天地同其大也?《书》曰‘玩物丧志’,为文亦玩物也。……古之学者,惟务养情性,其它则不学。今为文者,专务章句,悦人耳目。既务悦人,非俳优而何?”(程颢、程颐:《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一八,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39页)程氏以专务章句者视如优伶之类,诚见其文道观。
(34)王灼著,刘安遇等校辑《王灼集校辑·谢交割启》,巴蜀书社1996年版,第147页。
(35)陆世仪:《陆桴亭思辨录辑要》卷五“格致类”,民国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第59页。
(36)裘万顷:《竹斋诗集》卷一《次伯量赠别诗韵》,《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69册,第430页。
(37)赵壹:《非草书》,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选编《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第1页。
(38)范晔:《后汉书》卷六十下《蔡邕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997页。
(39)李世民:《论书》,《历代书法论文选》,第120页。
(40)张耒:《评书》,《古今图书集成》第650册《理学汇编·字学典》卷九十《书家部》,中华书局1934年版,第29页。
(41)谢肇淛:《五杂组》卷七《人部三》,上海书店2001年版,第125页。
(42)康有为著,崔尔平注《广艺舟双楫注》卷六《干禄》,上海书画出版社1981年版,第237页。
(43)傅山:《霜红龛集》卷四十《杂著五》,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33页。
(44)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桂馥》,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175页。
(45)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子部·艺术类一》,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952页。
(46)康有为著,崔尔平注:《广艺舟双楫注》卷一《购碑》,第45页。
(47)康有为著,崔尔平注:《广艺舟双楫注》卷五《述学》,第221页。
(48)郑逸梅:《艺林散叶续编》,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7页。
(49)曹丕:《典论·论文》,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61页。
(50)危素:《说学斋稿》卷四《送刘志伊采大元文乘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6册,第730页。
(51)张怀瓘:《书议》,《历代书法论文选》,第145页。
(52)张怀瓘:《文字论》,《历代书法论文选》,第209页。
(53)徐一夔:《始丰稿》卷二《送周山长考满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9册,第168页。
(54)王士禛:《分甘馀话》卷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9页。
(55)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四八四,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360页。
(56)杨钟羲:《雪桥诗话》卷第一一,北京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504页。
(57)费衮:《梁溪漫志》卷六《论书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72页。
(58)柳贯:《柳待制文集》卷一九《跋赵文敏帖》,民国“四部丛刊初编”本。
(59)锺惺:《隐秀轩集》卷三五《题邢子愿黄平倩手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580页。
(60)朱和羹:《临池心解》,《历代书法论文选》,第740页。
(61)孙犁:《孙犁选集·书衣文录》,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6页。
(62)李日华:《竹懒墨君题语》,《中国书画全书》第3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第1089页。
(63)苏轼:《论书》,《历代书法论文选》,第314页。
(64)苏轼:《六观堂老人草书》,王文诰辑注《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796页。
(65)吴德旋:《初月楼论书随笔》,《历代书法论文选》,第593页。
(66)袁中道:《珂雪斋集》卷三《作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06页。
(67)方文:《嵞山集·续集》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982页。
(68)袁中道:《珂雪斋集》卷一一《方澹玄墨谱序》,第520页。
(69)谭元春:《谭元春集》卷三一《书寒碧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856页。
(70)谭元春:《谭元春集》卷二八《答池直夫》,第782页。
(71)谭元春:《谭元春集》卷三《文天瑞见枉寺中作歌为赠》,第127页。
(72)江盈科:《江盈科集·答袁中郎》,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640页。
(73)陆树声:《清暑笔谈》,车吉心主编《中华野史·明朝卷》,泰山出版社2000年版,第2207页。
(74)黄宗羲:《思旧录·陈继儒》,《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40页。
(75)朱国桢:《涌幢小品》卷二二《好谭》,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39页。
(76)徐珂:《吴三桂作擘窠大字》,《清稗类钞》“艺术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048页。
(77)徐珂:《纪文达自谓涂鸦》,《清稗类钞》“艺术类”,第4058页。
(78)昭梿:《啸亭杂录》卷十《书法》,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41页。
(79)郑珍:《郑珍集·文集》卷四,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8页。
(80)姚永朴:《旧闻随笔》,黄山书社1989年版,第215页。
(81)孙静庵:《栖霞阁野乘》卷下《龚定庵轶事》,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58页。
(82)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与人书二十五》,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03页。
(83)黄道周:《石斋书论·书品论》,引自刘正成主编《中国书法全集·黄道周卷》,荣宝斋出版社1994年版,第329页。
(84)严复:《严复集·救亡决论》,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