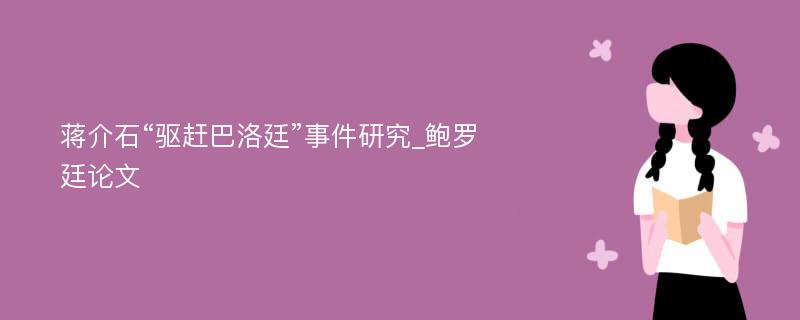
蒋介石“驱逐鲍罗廷”事件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蒋介石论文,事件论文,鲍罗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4.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11)04-0088-10
一、前言
1927年初国民政府迁都过程中的“鄂赣之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其过程和结局均直接影响了国共两党的政策走向和中国革命的进展。期间,蒋介石为争取主动,提出驱逐鲍罗廷以其他人代之,并付之不懈的努力且几近成功。关于迁都过程中鲍罗廷与蒋介石的关系,大陆学者多半关注的是两人之间的权力争斗①,对驱鲍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则极少述及。海外学者较早关注这一事件,但在论述过程中认为,北伐开始后鲍在广东开始反蒋,迁都武汉后鲍挟持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组建武汉临时联席会议,操纵国民党及国民政府,进而操纵中国革命。蒋介石为中国革命前途计,不得已与鲍争夺革命领导权。② 此论似有美化蒋介石的嫌疑,很难说持客观公正的立场。
近几年,笔者有幸到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查阅《蒋介石日记》,试图了解从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到宁汉分裂期间蒋介石的心路历程,无意中发现蒋介石试图将鲍罗廷驱逐回国,但最终没能成功。由于是事件经历者本人的记述,难免有些隐瞒自己个人野心,美化自己思想的痕迹,但仍可以从中看出驱鲍事件的主要脉络。
本文以上述资料为基础,辅之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翻译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和保存在台北“国史馆”的《蒋中正总统档案》及“国史馆”审编处编辑的《革命文献》等资料,探讨蒋介石和鲍罗廷产生冲突的深层原因,蒋介石驱逐鲍罗廷倡议的提出及反响,驱鲍的经过及失败的原因,力图客观反映这一历史事件的真实面貌。
二、蒋鲍冲突的缘起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利用东征和处理“廖案”所建立起来的威信与掌握的军事力量,趁鲍罗廷离开广东赴北京汇报工作之际,制造了“中山舰事件”。事后,蒋介石反复向布勃洛夫使团解释此次行动的原由,共产国际决定对其采取妥协退让的方针。5月15日,蒋介石利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旨在削弱、限制共产党人的“整理党务案”。一方面排斥了共产党,限制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和省执行委员会中的人数不得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另一方面打击了国民党左派势力,以使自己的实力上升,时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兼军委主席、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被蒋赶到国外,蒋取得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兼军事部长的职务。6月5日,国民政府特任蒋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7月初,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临时会议又选举蒋为中执会常务委员会主席,并特任蒋为国民政府委员。这样,在北伐战争之初,就出现了“党权政权军权皆集中于总司令一身”的状况,以至于形成“蒋所在地,就是国民党中央所在地,国民政府所在地;蒋就是国民党,蒋就是国民政府,威福之甚,过于中山为大元帅时”③。同时蒋借北伐之机,大肆扩充自己的实力,军事独裁初现端倪。
对于蒋介石借自己离开广州之际发动“中山舰事件”,鲍罗廷感到十分愤怒,因此前鲍在北京汇报工作时还信誓旦旦表示:“当你们去广州时,你们自己会确信,华南的思想势力范围乃是我们的影响……还有什么问题我们解决不了呢?一旦我们宣传什么,一旦我们提出什么建议,人们就会很认真地听取,并将根据我们的政策、我们的决定,以极大的成功希望来加以贯彻执行。”④ 蒋介石等4个军长“完全可靠”。而蒋介石此举无疑给了自己一记响亮的耳光。但在莫斯科“喘息”和“利用”蒋介石实现苏联利益的政策思想指导下,鲍罗廷放弃了反击蒋介石的想法,反而采取限制共产党以支持蒋介石的政策。因为莫斯科一再指示中国共产党和鲍罗廷:“现在应当客观地把蒋介石看作是革命运动方面一个重要力量”,因为他“作为同孙逸仙联系最密切的人和作为最有军事素养的人,毕竟是指挥北伐的唯一候选人”。⑤ 于是便有了鲍罗廷在“整理党务案”和北伐问题上对蒋介石的让步。
鲍罗廷对蒋介石的让步并不表明其对蒋的革命成功抱有期望,他预测蒋介石的北伐到达武汉时,蒋便会自己遭到失败,共产党要做的只是等待那天的到来。而事实上,北伐军占领汉口、汉阳后,他所认为的蒋介石失败并没有到来,甚至在武昌克复后,蒋介石依旧没有失败的迹象。
在此背景下,发生了国民政府迁都事件,而此事正是蒋本人提出来的。
蒋介石要求国民党中央北移武汉的动机有四:一是便于控制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蒋自率军北伐后,一直担心此前取得的国民党大权是否牢靠,共产党和鲍罗廷是否能让其独揽大权。这种心境蒋在其日记中袒露出来,但蒋以鲍操纵中国革命、自己为争夺民族革命的领导权加以掩饰。蒋在日记中写道:“前后方隐忧亟增,肘腋生患,共党在内作祟,非使本党分裂与全军崩溃而不止。遍地荆棘,痛苦万分。”⑥ 31日,蒋在日记中写道:武昌距离愈近,“而忧患与之俱深,个中心事,其谁知之。”⑦ 之后蒋又叹曰:“鲍等限制革命军发展,防范本党北伐成功之心,到底不懈,悲夫。中师倏忽逝世,何使吾辈后死者艰棘至此耶。”⑧ 很显然,蒋介石再三要求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就是要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跟着自己走,以便控制。二是防止共产党力量占领武汉。蒋介石虽然在前方指挥作战,但他主要考虑的还是政治问题,即中共和苏俄势力的影响和发展问题。为了在北伐中借用工农力量,蒋介石不得不求助于共产党的力量,于是放松了对共产党活动的限制。但是他时刻关注着中共中央和苏联顾问的动向,特别是鲍罗廷的动向,因为鲍罗廷代表苏联的援助。三是遏制唐生智权势膨胀。蒋介石发现,随着北伐由南向北推进,作为两湖战场前敌总指挥的唐生智的势力也随之膨胀,唐不仅占有两湖地盘,负责湖北军事,并在他入赣期间代理湖北临时政务会议主席,其军事实力由湘至鄂也大为扩张。他感到唐的力量增长将成一方诸侯,深恐其不受节制,欲以国民政府派员组织政治委员会以限制唐生智。四是阻止汪精卫销假回国。在蒋看来,在武汉即将成为革命中心时,把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中倾向于汪的部分要员调来武汉,就能分散南方流行的迎汪复职力量,阻止政敌汪精卫复出。
鲍罗廷起先认为迁都应等到占领武昌之后,当务之急是在广东进行新政权的建设。但鲍很快改变了主意,主张国民政府立即北迁,其原因如下:
一是牵制蒋介石,力图使国民政府恢复到“中山舰事件”之前的局面。蒋介石通过“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之后,大权独揽,鲍罗廷对其不满,期望通过扶植汪精卫以形成汪蒋平衡的局面。因此,他主张打击蒋介石,目的是防止蒋独裁和右转,但不想与蒋决裂,造成蒋的势力为帝国主义所利用,还想拉住蒋介石向左转。他说:“许多事情不仅仅取决于蒋介石,或者与其说取决于蒋介石,不如说取决于他周围的人。他周围的这些人是否允许蒋介石向左转呢?”⑨ 据此,鲍罗廷考虑再三后,最终决定将广州政府迁到武汉。二是受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首席顾问铁罗尼的影响。10月30日,铁罗尼致电鲍罗廷,主张迁都武汉。电曰:“国民革命军来到武汉,人民在政治观念上似乎没有什么改变。这件事,我们实在责无旁贷。武汉没有一个中央政治机构。尽管在长沙我们就主张建立这样一个机构,但到现在还什么都没有。国民党省执行委员会缺乏权力和能力适当地处理政治事务。唐生智独自主宰形势,和他对抗的只有邓演达和陈公博这个懒家伙。”“很有必要有二至三名中央执行委员来此建立委员会。因为不如此,就不可能开始严格的工作,不能树立党的权力。”⑩ 铁罗尼的电报对鲍产生了积极影响。三是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到了10月中旬,南昌、武昌相继克复,广东、湖南、湖北、江西联成一片,革命中心已经从珠江流域移至长江流域,国民政府驻地如果再偏驻广州将会对国民革命产生不利影响。“领导机关迁徙到华中是必要的,不然政府就有可能变成对革命进程不发生重大影响的广东省机关,从各方面看来新的中心自然是解放了的武汉。”(11) 就这样,在鲍罗廷的建议下,广州国民政府决定迁都武汉。与此同时,莫斯科自“中山舰事件”后对蒋介石右倾有所察觉,对鲍罗廷的迁都武汉表示支持。
蒋鲍关于迁都各有自己的算盘。蒋介石期望通过迁都维持其之前获得的各种权力,而鲍罗廷旨在通过迁都改变蒋介石大权独揽的状况,由此形成了二人冲突的缘起。
三、蒋介石驱鲍倡议的提出及反响
鲍罗廷携一行人赴汉后,立即成立武汉临时联席会议以代替国民政府行使最高权力。目的是先发制人,造成既成事实,迫使蒋介石处于被领导地位,以便抑制其独裁。同时共产党人到汉后,即刻组织工农,武汉的工农运动很快发动起来了,逐渐形成为革命的中心。此外,蒋介石借迁都打压唐生智的目的未能实现。鲍罗廷到汉后,唐生智采取了拥护以左派为主的国民党中央和拉拢中共的策略,同时,驻守在武汉的张发奎也表现为左倾。这样,迁都武汉反而造成了国民党中央与唐生智等军事首领的联合。武汉临时联席会议成立后,唐生智并未被打压,反与鲍罗廷结合,似如虎添翼。蒋介石力主迁都的目的一个都没实现,遂不惜食言,改变决定,将已到赣之赴鄂人员留驻南昌。
蒋介石挑起了迁都之争后,很快演化成革命阵营的分化,鄂赣双方形成对峙局面。1927年1月11日,汉方为打破僵局,邀蒋介石赴汉视察。12日晚宴会间,鲍罗廷警告蒋:“如果有压迫农工反对C.P.的这种事情,我们无论如何,要想法子来打倒的!”(12) 他指责蒋袒护张静江,视之为党中老朽,丧失革命精神,声色俱厉,使蒋感到十分难堪。(13) 更让蒋介石恼火的是,鲍罗廷竟然当众挑战蒋介石的自尊。据陈公博在《苦笑录》中回忆,蒋介石和鲍罗廷有过一次交涉,任翻译的是宋子文,他们争论了许久,鲍罗廷最后对蒋说:“你想众人都不说话是不可以的。我告诉你一件故事,古时西方有一个国王极讨厌各大臣说话。有一天他对各大臣说:‘你们说话太多了,我不喜欢。’各大臣说:‘只有狗是不会说话的,陛下要我们不说话,只有找狗去。’”(14) 鲍罗廷的讲话使蒋介石受到了刺激。蒋在日记中写道:“席间受辱被讥,生平之耻,无逾于此!”又写道“为被压迫而革命,不自由何不死?余决伸中华民族正气,以救党国,俾外人知华人非尽是贱者,而不可侮辱也。”翌日,蒋叹道:“为何革命而受辱至此?”(15) 蒋多次表示“不胜悲伤!”心情“亦惟沉痛而已!”(16) 鲍罗廷的话使蒋感到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他听了这段故事,遂决定驱逐鲍罗廷。(17)
蒋介石自武昌回南昌后,对鲍罗廷之辱难以接受,驱鲍之意已定。19日过九江,第六军军长程潜与之谈话,蒋直告之与鲍不能共事,“余与鲍罗廷不能相容!既不能为国雪耻,何忍复为余辱国?革命至此,尚受帝国主义与外人压迫,何如及时解职,以谢国民与已死同志灵?”(18) 与张静江谈话时多次“不禁郗慨系之”。(19) 20日蒋介石想到自己“中山舰事件”以来的努力马上就要化为乌有,叹道:“余既不能为国雪耻,何忍为余辱国?今日情况,余惟有一死,以殉国难,为中华民族争人格,为三民主义留精神,使全国同胞起而自救危亡!夫苏俄解放被压迫民族主义,余深信其必不误也;然而来华如鲍罗廷等最近之行动,则徒使我国人丧失人格,倍增压迫,此与其主义完全相反矣。国人有知,应驱而逐之苏俄同志乎?尔诚为解放弱小族,不使第三国际之信用破产,应急自悟,改正方法,不使恢复至帝国资本主义之道路,则世界革命必有成功之一日,否则余虽一死,不足救国,且无以见死同志于地下!余惟愿我全国同胞速起以图独立自主,不负总理四十年革命之苦心。”(20) 蒋介石又言:“余自知初之误信鲍罗廷之非,何敢再误国民,以为万世罪人也!”(21) 此后几天,与张静江、谭延闿、戴季陶等谈党事,在“感郗系之”的同时,痛斥鲍罗廷,“凡有正气者,誓必驱而逐之”。(22) 至此,蒋介石下定决心,尽全力驱逐鲍罗廷。
27日,汉方派遣的劝蒋人员抵赣,蒋介石提出了驱鲍意见,意为试探。蒋说:“余必欲去鲍罗廷,使我政府与党部得以运用自如。”顾孟余、何香凝、邓演达等觉得事关重大,害怕牵动大局,不敢决断。蒋介石甚是失望,叹道:“书生办事,则非至败坏不可!”蒋又同与己观点相近的谭延闿、戴季陶谈至深夜,蒋谓:“余决去鲍,并迁中央党部与政府于武汉,以应付时局。”(23) 谭延闿、戴季陶表示同意。但驱鲍毕竟是一件关系中国革命前途的大事,须慎之又慎。29日,戴季陶、张静江、谭延闿又和蒋介石谈论鲍罗廷,当时“季怯而静硬,组公则默默尔”。(24)
显然蒋之提议并没有得到大家的响应,“连日见诸同志,畏忌俄国,而不敢决然逐去鲍罗廷,余亦未免消极灰心。”(25) 他把原因归结为“病在环境之怯弱,干部之无人也。”认为“然能立于革命地位,则一切揣测怀疑,可以不顾。夫横暴如鲍罗廷,如不速去,大有障碍于革命。”把大家反对的原因归结为,“众皆以为有碍俄交”。私下反省时认为:“余则以为惟顾联俄革命,所以必去鲍,以免两国邦交破裂,否则亦何必去鲍哉?众皆不知此理,一味畏缩,可叹!”(26)
蒋介石连日为驱逐鲍罗廷而得不到大家的支持而苦恼,大家认为驱逐鲍罗廷顾问将对孙中山既定的联俄方针带来负面影响。而蒋介石认为只有驱逐鲍罗廷才可以使中俄关系免于破裂。戴季陶见蒋之提议应者甚少,提醒蒋:“众意皆欲公不可去鲍。”蒋表示:“余坚持前议,不可动也。”此时因汉浔租界事件英国报纸大肆挑拨国民政府和苏联,蒋介石亦认为,此时驱逐鲍罗廷正中帝国主义的奸计,实属不妥。他自叹道:“余本决心去鲍,见此报,则知此事适中帝国主义之计,余惟有忍耐以待将来耳!”(27)“吾不愿为帝国主义者所诽笑,宁屈己卑志,以求革命发展,故放弃主张,虽英国派兵恫吓,日本想来妥协,皆毅然与之决斗,生死成败置之度外而已。”(28) 蒋介石见自己的驱逐鲍罗廷的提议得不到大家的支持,而此时因为汉口“一·三”事件和九江事件而导致的中英关系的影响,不得不暂时放弃了驱逐鲍罗廷的想法。
蒋介石驱鲍倡议在军界引起反响,军中有识之士均规劝蒋介石顾全大局。2月4日第六军军长程潜致函蒋介石:“近时政治问题据传闻甚复杂,然延搁不决,人心必至日益涣散,望公容忍一切,领袖群流,博采众见,自处于调护地位,俾策军事之进行。潜本下愚,对于政治毫无研究,然目见敌势方张,内部似应一致,至于如何而后可以一致,是则运用者不可不思前顾后也。”(29) 2月9日第七军军长李宗仁建议蒋介石,“毅然决定中央政府迅速仍迁移武汉,党国前途实利赖之”;关于党务问题,“俟军事告一段落,再行严密整理,较为妥当。”(30) 蒋之倡议并未得到军界的支持。
四、蒋介石驱鲍的经过及失败
经过各方的努力和争取,2月8日南昌政治会议作出决议,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迁至武汉。面对此无可奈何之结局,蒋在回复谭延闿的电文中表示:“尊意中当遵守,无论何事,祗求当能保持与统一而已。此意可与孙夫人及陈、丁诸同志说明也。”(31) 但心中对鲍耿耿于怀,对即将失去权力“痛苦不堪”。(32) 蒋介石对鲍罗廷记恨甚深,认为“此全由鲍罗廷一人所驱使也”。21日,在致黄埔军校教育长方鼎英并转李济深电中,声称对鲍“誓必驱而逐之”。(33) 为挽回不利局面,思忖再三,蒋介石马上将此前驱鲍的倡议付诸行动。
2月22日、23日蒋介石与维经斯基在九江会谈,蒋介石指出鲍罗廷应该对鄂赣之争负责并请求共产国际撤回鲍罗廷。蒋道:“我个人对鲍没有恶感,我迄今为止一直把他当作老师看待。但我现在反对他,因为他的坚持会造成两个政府的危险方针。我认为这不是共产国际的方针,因为这种政策会在中国人民思想中造成对共产国际的不信任。这不仅在我们国家,而且在东方各被压迫国家都会有反应。帝国主义者对鲍的离去作何解释,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解决根本问题——国民党的内部问题。”(34) 蒋介石表示了对鲍罗廷的不满,认为鲍罗廷的所作所为“会破坏共产国际在中国人和一切东方弱小民族心目中的威信”,表示他“现在反对鲍,也不等于反对共产国际”。他提出“政府任何时候都可以迁往武汉”,但条件之一是“迁政府同鲍离开有关系”。(35) 因为“本党纠纷皆由鲍罗廷一人所起,故政府延期必待第三国际撤回鲍氏,与鲍氏回俄以后,始能定耳。”(36) 很显然,蒋介石将鄂赣之争的责任完全推给鲍罗廷,并将驱鲍作为迁都武汉的条件。
25日,蒋介石与谭延闿、张静江、黄郛交谈,道:“合中外共党之力以攻我,使我内部纠纷,不能统一,鲍之罪不容于天地间。”(37) 最后,他们商量处理办法,一致认为电告共产国际,要求撤换鲍罗廷。蒋介石气愤地认为:“鲍罗廷因为小人,而一般趋炎附势,不知党国为何事者,更可杀也!”(38) 南昌中央政治会议于26日致电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要求共产国际将鲍罗廷撤回苏联。(39)
鄂赣形成对峙局面之后,共产国际远东局并不赞成鲍罗廷的“倒蒋”做法,认为这会激化国民党内部的冲突。(40) 2月22日、2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负责人维经斯基同蒋介石谈话之后,意识到事情远远比他们想象的要严重。为了拉住蒋介石,同时加上维经斯基对鲍罗廷早有不满,遂致电莫斯科要求召回鲍罗廷,因为蒋介石“不会作出让步”。(41)
此时的鲍罗廷有点骑虎难下的架势,他一方面把自己和蒋介石的分歧向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报告,声称在迁都问题上如果对蒋妥协,将会大大加强蒋的独裁地位,自己也将会因此而无法在现在的岗位上继续留任,非辞职不可。另一方面主动同蒋沟通,托宋子文转达他表示愿来总司令部行营随蒋而不问中央事(42),甚至做好了离开中国回俄的准备。
莫斯科对蒋介石正在右转早有耳闻,在其驻华代表中早有人报告蒋“明显企图改变政府的方针,使之右倾”(43),“竭力与国民党右派和买办结成联盟,甚至还公开同日本司令部进行谈判(他的代表戴季陶在日本),而且还通过日本人同张作霖谈判划分势力范围问题。”(44) 但是,出于利用蒋介石反帝和推动中国民主革命的双重目的,莫斯科没有同意鲍罗廷辞职和蒋介石的驱鲍要求,明确指示鲍罗廷在武汉负责政治上的决策,并拥有军事上的决定权。(45) 同时对迁都之争的处理作出指示:“我们认为国民党中央对蒋介石的方针是正确的。要采取措施:第一,不要突出鲍罗廷,免得人们认为这场冲突是鲍罗廷和蒋介石之间为争夺影响而进行的斗争。第二,不要把事态发展到与蒋介石决裂的地步,以蒋介石完全服从国民政府为限。”(46)
通过共产国际召回鲍罗廷的努力失败之后,蒋介石同鲍罗廷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两人已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几乎永久破裂”(47)。蒋介石一边“忍辱负重”、“不忮不求”(48),一边等待时机,期望一击成功。
1927年2月24日,武汉方面派第一军军长兼武汉卫戍司令陈铭枢随陈公博赴赣,劝蒋迁都武汉。蒋介石趁机说服陈铭枢支持反共(49),要求其负责策动在汉的国民党要人驱逐鲍罗廷。陈铭枢返汉之后,即开始行动。3月2日,陈铭枢首先拜访孙科,转达蒋介石驱鲍的意思,并要求孙将此意转达鲍罗廷。此时鲍并未接到莫斯科支持自己的指示,加之鄂赣之争旷日持久,已萌生去意。鲍向孙科表示:必去他亦可,“向中央各同志疏通,必可办到,不过须经过会场正式通过手续”(50)。
3月3日陈铭枢分别拜访了孙科、宋庆龄、宋子文、邓演达等,讨论的均是关于鲍罗廷请辞回国的内容,大家并没有太多的反对意见。4日中午,陈铭枢奉蒋命同鲍罗廷约谈,讨论鲍如何能够安全回国,准备征得鲍同意,即由武汉方面发表蒋的驱鲍宣言。(51) 至此,蒋介石驱逐鲍罗廷的计划几近成功。
正在此时,共产国际指示抵达武汉。莫斯科明确反对蒋介石的驱鲍要求,支持鲍的迁都武汉决定,告诫鲍同蒋斗争时注意分寸,既不能同蒋决裂,又必须让蒋服从国民政府。莫斯科的指示使鲍打消了去职回国的念头,坚定了同蒋斗争的决心。
同时,蒋介石驱鲍的意见遭到了武汉政府中共产党人的坚决反对。4日下午,徐谦、吴玉章、顾孟余、邓演达、陈友仁、陈铭枢等在孙科处开会,讨论驱鲍问题。会上多数人反对撤换鲍罗廷,其中以吴玉章为首的共产党人反对最为强烈。针对徐谦为“照顾蒋介石的面子”而撤换鲍罗廷的提议,吴玉章指出:“这不是面子问题,鲍罗廷是否要换,应由大多数中央委员来决定,蒋介石一句话怎能算数!究竟是蒋介石服从中央呢,还是中央服从蒋介石?再说鲍罗廷的话根本没有错误,凭什么理由撤换他?这不是鲍罗廷个人去留问题,这是蒋介石对中央、对政府的蔑视。我们一定不能让步!”(52) 此前李宗仁也反对驱逐鲍罗廷,李认为鲍顾问是总理孙中山请来,又系第二次代表大会礼聘的,(53) 言下之意驱鲍不合情理。
陈铭枢眼见情势不利,急忙抬出蒋介石以压邓演达,要求邓演达立即发表蒋介石的驱逐鲍罗廷宣言,说:“总座系命交总政治部发表的,总政治部乃受总座命令者。”身为总政治部主任的邓演达无言以对,只好用目光向大家求救。吴玉章道:“如要发表,可由陈同志私人持交言论界发表,党不宜为之负责发表。”(54) 随后孙科打电话到报馆准备登载,但最终未能刊行。这次会议最后决定不接受蒋介石撤换鲍罗廷的请求。蒋利用陈铭枢策动武汉政府要人驱逐鲍罗廷的努力亦遭到了失败。
3月4日晚唐生智派人要求陈铭枢发表支持武汉意见,否则去职。5日陈铭枢将武汉使命失败通知蒋。6日蒋电示陈铭枢:“空气紧张,无足为虑,应以镇定处之。”(55) 陈铭枢最后被迫离汉。3月7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南洋大楼召开预备会,10日至17日召开正式会议,拒绝了蒋介石延迟至12日开会的要求。10日,刚刚到汉开会的李烈钧当场退会并立即返赣,向蒋报告了会议情况,蒋愤怒至极,大骂“鲍氏之肉,尚足食乎”(56)。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统一党的领导机关决议案》、《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案》、《统一革命势力案》、《修正政治委员会及分会组织条例案》、《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执会第三次全会宣言》等文件,改选了国民党中央各机构成员和国民政府委员。3月20日,新一届国民政府委员在武昌宣誓就职。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迁都问题的最终解决。至此,蒋介石驱逐鲍罗廷的努力遭到了彻底失败。
五、结论
第一,关于蒋介石驱逐鲍罗廷的原因。首先,蒋鲍分歧自“中山舰事件”后愈演愈烈,到“迁都之争”时已水火不容。其根本原因是:鲍罗廷期望利用北伐、迁都等机会来限制蒋介石,力图恢复到“中山舰事件”前国民政府党政军分权、国共两党合作的革命局面;蒋介石则期望通过北伐、迁都来巩固自己“中山舰事件”以来取得的各种权力,实现独揽党政军大权的梦想。这是蒋介石驱逐鲍罗廷最主要的原因。其次,蒋介石无法容忍鲍罗廷带有大国沙文主义性质的工作作风。莫斯科把中国革命纳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范畴,并以苏联革命的模式套用中国革命,这是苏联指导中国革命的主要特点。由于苏联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的援助,加上自己深得孙中山的器重,鲍罗廷在赴华不久在指导中国革命问题上占据了重要地位。随着对中国国情的了解,鲍罗廷在工作方法和方式上出现了发号施令、包办代替的大国沙文主义现象,这为蒋介石决定驱鲍找到了借口。蒋介石认为中国的国民革命固然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但中国革命只能由国民党来领导(57),为了中国革命能够独立自主发展,只能驱逐鲍罗廷以争取民族革命领导权。蒋介石多疑、孤傲的性格是其决定驱逐鲍罗廷的又一原因。在迁都之争中,蒋介石总是怀疑鲍罗廷在幕后操纵国民党左派和中共与之对抗,加上1月12日欢迎晚宴上的公开羞辱,使之自尊心受到刺激,故欲除之而后快。“中山舰事件”就是因为苏联军事总顾问季山嘉过于忽视了蒋的自尊心所引起,蒋通过这一事件打击了俄国人的威信,取得了成功。此次受辱更甚,蒋介石当然不能忍受。
总体说来,蒋介石决定驱逐鲍罗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反对鲍罗廷等成立的临时联席会议对其权力的限制是最主要的原因,鲍罗廷工作作风欠妥当及蒋介石的性格则是次要原因。在以往学术界谈到蒋鲍权力争斗原因时,大陆学者往往强调第一点,而对鲍罗廷工作作风问题极少提及;台湾学者则强调鲍罗廷的工作作风问题,而对蒋介石满足个人权力野心避而不谈,两者都是不客观的。
第二,关于蒋介石驱鲍的策略与步骤。在策略上,蒋介石将“鄂赣僵局”的所有责任推给鲍罗廷,声称自己反对鲍罗廷,并不反对共产国际及其政策。“中山舰事件”时蒋介石亦声称反对共产国际代表,并不反对共产国际及其政策,成功地赶走了季山嘉。此时,蒋介石故伎重演,期望通过这种缩小打击面的方式赶走鲍罗廷。
关于驱鲍的步骤。其一,舆论宣传。蒋介石先向党内人士提出驱鲍倡议,期望得到舆论支持,但事与愿违,其意并未得到积极响应。恰逢发生“汉浔租界事件”,蒋意识到此时驱鲍显得不合时宜,加上众多同僚、将领劝其容忍,蒋舆论宣传未达预期效果。其二,行动驱鲍。2月下旬蒋向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表达了鲍罗廷应该对鄂赣僵局负责,要求共产国际撤回鲍罗廷,并以国民党南昌政治会议的名义致电共产国际,要求撤回鲍罗廷。但共产国际明确表示支持鲍罗廷,拒绝了蒋介石的驱鲍要求。随后,蒋介石利用陈铭枢返汉之际,安排其执行驱逐鲍罗廷的任务。蒋的驱鲍提议遭到了以共产党员吴玉章为首的与会人员的反对,会议最后决定不接受蒋介石撤换鲍罗廷的请求。陈铭枢执行蒋之任务功败垂成,蒋介石驱逐鲍罗廷的努力遭到彻底失败。
第三,关于蒋介石驱鲍失败的原因。其一,蒋介石驱逐鲍罗廷的要求遭到莫斯科的拒绝。蒋认为中国的国民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但中国革命的领导者是国民党,在统一战线中的中国共产党必须承认国民党是领导国民革命的政党。(58) 在迁都之争中,他认为鲍罗廷在操纵中国革命,除了他自己能代表领导中国革命的国民党外,其他国民党人士均不能,更不要说共产党了。他驱逐鲍罗廷是为了争夺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同时希望维持同共产国际的密切关系。(59) 但是共产国际将中国民主革命纳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并以苏联革命模式加以指导,加上“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右转迹象明显,莫斯科对其领导中国革命并不放心,但出于利用其反帝和推动中国民主革命的双重目的,共产国际调和蒋鲍之间的矛盾,在拒绝蒋介石要求的同时,指示鲍罗廷对其有限让步。
其二,蒋介石出尔反尔,在“迁都之争”中明显理亏。从蒋介石提出迁都倡议,到发电报承认临时联席会议的合法性,再到无理扣留第二批赴鄂之国府要员,到最后宣称国府暂定南昌,其出尔反尔、自食其言,企图将国民政府玩弄于股掌之上,于情于理不通。蒋在鄂赣僵局之时提出驱鲍倡议,其自称为中国革命前途考虑,实则为实现自己独揽党政军大权的愿望,显然是私欲大于公心。至于其提及鲍罗廷企图分裂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破坏中国民族革命,只不过是他的一个借口而已。
其三,蒋介石的驱鲍倡议未能得到广泛的支持。从蒋介石提出驱鲍倡议,到陈铭枢赴汉执行驱鲍计划,蒋之倡议并未得到国民党政界、军界的广泛支持,甚至在武汉引起了共产党和汉方军界的反对,在此情景下驱鲍行动遭到失败自然在情理之中了。
蒋介石驱逐鲍罗廷事件,反映出中国革命环境的复杂性。它主要反映的是鲍罗廷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和中共与蒋介石代表的国民党右派争夺中国革命的领导权问题,同时一定程度地反映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民族主义革命者争夺民族革命领导权的问题。无论是哪一种现象,其背后隐藏的实质是中国革命道路如何选择的问题。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无论是鲍罗廷代表苏联倡导的中国革命模式,还是蒋介石倡导的革命模式,均毫无例外地遭到了失败。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使中国革命最终取得了胜利。
注释:
① 如丁言模:《鲍罗廷与中国大革命》,宁夏出版社1993年版;曾成贵:《鲍罗廷与国民政府迁移中的政治角力》,《史学月刊》2005年第8期;吴珍美:《析1927年前后鲍罗廷与蒋介石的权力争斗》,《史林》2006年第1期。
② 持此论点多为台湾学者,他们因掌握资料之便,对此事进行过较多的研究。参见王正华:《国民政府北迁后蒋中正驱逐鲍罗廷之议》,《“国史馆”学术集刊》2002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中国与世界(第三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03~218页;王正华:《国民政府北迁鄂赣之争议》,《近代中国》第114期,1996年8月;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6年版。
③ 《中央局报告(九月份)——最近全国政治情形与党的发展》(1926年9月20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41页。
④ 《鲍罗廷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1926年2月15日、17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146~147页。
⑤ 《罗加乔夫关于广州1926年3月20日事件的书面报告》(1926年4月28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第234页。
⑥ 《蒋介石日记》,1926年8月30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以下所引蒋日记出处同此)。
⑦ 《蒋介石日记》,1926年8月31日。
⑧ 《蒋介石日记》,1926年8月31日,上月反省录。
⑨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会和鲍罗廷会议记录》(1926年8月16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第392页。
⑩ C.Martin Wilber and Julie Lien-ying How.Missionaries of Revolution:Soviet Advisers and Nationalist China 1920~1927,Document 69(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9)pp.773-776。
(11) [苏]亚·伊·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92页。
(12) 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下),第537页。
(13) 孙诒编:《民国十六年之蒋介石先生(一月至三月)》遵订稿(一),第4页。《蒋中正总统档案》,“文物图书:事略稿本”,毛笔件。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武汉国民政府史料》,武汉出版社2005年版,第339页。
(14) 陈公博:《苦笑录》,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65页。
(15) 《蒋介石日记》,1927年1月8日。
(16) 《蒋介石日记》,1927年1月8日,上星期反省录。
(17) 陈公博:《苦笑录》,第65页。
(18) 《蒋介石日记》,1927年1月19日。
(19) 《蒋介石日记》,1927年1月19日。
(20) 《蒋介石日记》,1927年1月20日。
(21) 《蒋介石日记》,1927年1月20日。
(22) 《蒋介石日记》,1927年1月21日。
(23) 《蒋介石日记》,1927年1月27日。
(24) 《蒋介石日记》,1927年1月29日,上星期反省录。
(25) 《蒋介石日记》,1927年1月30日。
(26) 《蒋介石日记》,1927年1月31日,上月反省录。
(27) 《蒋介石日记》,1927年1月30日。
(28) 《蒋介石日记》,1927年1月31日,上月反省录。
(29) 《程潜呈蒋中正函》(民国16年2月4日),《特交档案一般资料》,第17册(民国16年2册),第160174号。《蒋中正总统档案》。
(30) 《李总指挥宗仁呈蒋总司令佳电》(汉口,民国16年2月9日),第26号,《革命文献》(北伐时期)第26册,《政治》一,《奠都南京》,第34页。
(31) 孙诒编:《民国十六年之蒋介石先生(一月至三月)》遵订稿(一),第14页。
(32) 《蒋总司令致白崇禧漾亥电》(南昌,民国16年2月23日),第96号,手稿,《革命文献》(北伐时期),第10册,《克复浙沪》,第126页。《蒋中正总统档案》。
(33) 《蒋中正总统档案》,“文物图书:事略稿本”,第1卷,台北“国史馆”,2003年,第22~27页。
(34) 《1927年2月22日和23日维经斯基和蒋介石在九江的谈话记录》(1926年2月26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北京图书馆1998年版,第133页。
(35) 《1927年2月22日和23日维经斯基和蒋介石在九江的谈话记录》(1926年2月26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第133~134页。
(36) 孙诒编:《民国十六年之蒋介石先生(一月至三月)》遵订稿(一),第33页。
(37) 《蒋介石日记》,1927年2月25日。
(38) 《蒋介石日记》,1927年2月25日。
(39) 《第六十六次政治会议议事录》(1927年2月26日),第2页;《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记录》,台湾国民党党史会档案,档号:00-1/32,油印件。
(40) 杨奎松:《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一九二○至一九六○)》,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第1~3页。
(41) The Letter from Shanghai(March 17,1927),Leon Trotsky,Problem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New York:Paragon Book Gallery,1962),p.406。
(42) 孙诒编:《民国十六年之蒋介石先生(一月至三月)》遵订稿(一),第12页;《事略稿本》1927年2月6日条,《武汉国民政府史料》,第339页。
(43) 《维经斯基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的信》(1927年1月21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第94页。
(44) 《阿尔布列赫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1927年2月25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第125页。
(45) 杨奎松:《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一九二○至一九六○)》,第115页。
(46)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87号(特字第65号)记录》(1927年2月27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第118页。
(47) Jonathan.D.Spence:To Chang China:Western Advisers in China,1620-1960(Boston: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69),p.179。
(48) 《蒋介石日记》,1927年2月26日,上星期反省录。
(49) 王正华:《国民政府北迁鄂赣之争议》,《近代中国》第114期,1996年8月。
(50) 《蒋中正电谭延闿接陈铭枢函感言特抄该函与诸同志阅》(1927年3月10日),《筹笔》(北伐时期)拓影,档号:2010.10/4450.01-006/70。《蒋中正总统档案》。
(51) 《蒋中正电谭延闿接陈铭枢函感言特抄该函与诸同志阅》。
(52) 吴玉章:《第一次大革命回忆》,《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141页。
(53) 《蒋中正电谭延闿接陈铭枢函感言特抄该函与诸同志阅》。
(54) 《蒋中正电谭延闿接陈铭枢函感言特抄该函与诸同志阅》。
(55) 《蒋总司令致陈铭枢转朱绍良鱼辰电》(1927年3月6日于南昌),第2号,手稿,《革命文献》(北伐时期),第13册,《宁汉分裂与北伐中挫之(一)》,第21页。《蒋中正总统档案》。
(56) 《事略稿本》(第1卷),台北“国史馆”,2003年印行,第117页;《武汉国民政府史料》,第341页。
(57) [德]郭恒钰:《俄共中国革命密档(一九二六)》,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第216页。
(58) [德]郭恒钰:《俄共中国革命密档(一九二六)》,第175页。
(59) Jonathan.D.Spence:To Chang China:Western Advisers in China,1620-1960,p.179。
标签:鲍罗廷论文; 国民政府论文; 陈铭枢论文; 蒋介石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论文; 革命委员会论文; 中山舰事件论文; 台湾国民党论文; 历史论文; 国民党论文; 军事研究论文; 唐生智论文; 邓演达论文; 第三国际论文; 莫斯科论文;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论文; 世界大战论文; 辛亥革命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