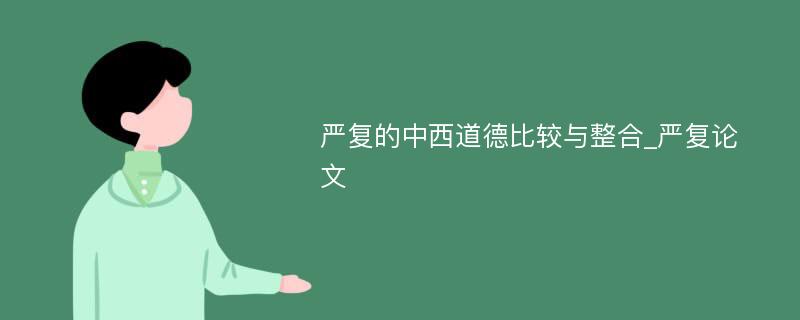
严复中西道德比较与整合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西论文,道德论文,严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道德是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人们行为的重要规范,在社会生活中起着维系人心和秩序的重要作用。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严复对此极为重视。1895年,他大声疾呼要“新民德”、改铸国民性格。这是他启蒙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严复认为,西方“贵信果,重少轻老,喜壮健而无所屈服之风”[1](P1390-1391)的国民性格很值得中国人效仿。西方的这种国民性格是西方道德文化长期培育的结果。因此,在中国培育新的国民性格,引入、学习和吸收西方道德观念是非常必要的。严复同时指出,吸收西方道德观念不是以牺牲中国传统道德优点为代价的,而是主张“阔视远想,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2](P560)严复认为着力于中西道德观念的比较与整合,既是西方道德观念中国化发生积极意义的前提,也是建构起新道德观念体系的理想途径。
一、严复推进中西道德比较与整合的主要内容
1、关于道德基础的问题。严复对“自由则功罪赏罚皆由己出”与“自由未尝立以为教”进行了比较与整合。严复认为,不同的道德基础不仅规定着道德的性质,而且是道德规范能否起积极作用的前提。中西方道德首要的、本质的差异就在于两者具有不同的道德基础。他说:“彼西人之言曰:唯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3](P3)也就是说,在西方“自由”被看成天赋的,人所具有的,不可剥夺的。正是这种天赋的“自由”被视为西方道德的基础,所谓“斯宾塞《伦理学·说公》一篇,言人道所以必得自由者,盖不自由则善恶功罪,为非由己出。”[3](133)以此为基础的道德约束性、规范性因此才能转换为、体现为自觉性、自治性和责任性;也正是因为有了“自由”的基础,西方道德才能“使其民皆若有深私至爱于其国与主,而赴公战如私仇者……,出赋以庀工,无异自营其田宅;趋死以杀敌,无异自卫其室家”。13l(P31)与西方相比,在中国封建社会中,“自由”被排斥在道德之外,没有将人的利益,人的要求,人的个性纳入道德内涵中。也就是说,没有以“自由”作为道德的基础。严复认为:“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3](P2)中国传统道德实际上具有单纯的服从意义和规范意义,人们对道德规范的践履带有不自觉性、被迫性。既不具有自觉意识,也就谈不上责任感。因此,这种道德文化培育下的国民,在严复看来,要么奴性十足,要么虚伪奸诈。所谓“后义先利,诈伪奸欺,……甲午之办海防,水底碰雷与开花弹子,有以铁滓沙泥代火药者”。[3](P30)由于道德基础的差异,铸就了迥异的国民性格。严复这一比较与揭露虽然对中国道德状况的评析并不够全面,但对于改革传统道德体系的弊病,建构新的道德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2、关于道德主体性与规范性的问题。严复对“首明平等”与“最重三纲”进行了比较与整合。严复指出,中西道德观念中“自由”基础的存缺,总体上规定了中西道德性质的差异,这就是主体被迫性与主体自觉性,在不平等条件下践履与在平等氛围中操作的差异。为什么中国传统道德缺乏“自由”的基础呢?严复从道德与政治相互渗透的角度剖析了这一现象。他说:“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3(P30)在封建的中国,等级制度、科举考试、治理天下等政治活动或政治现象都是与道德紧密联系的。等级制度以“三纲”护持,选才以尊亲为尚,治理天下却以“忠孝”为本。这些现象充分表明:中国传统道德缺乏“自由”基础的根本原因就是道德政治化倾向。在封建主义的中国,由于伦理道德本质上是通过驯化百姓而服务于政治的工具,其反自由性也就成为当然。严复指出:“西国言论最难自由者莫如宗教。……中国事与相方者,乃在纲常名教。事关纲常名教,其言论不容自由,殆过西国之宗教。”[3](P134)上述比较分析表明,中国传统道德非主体性的具体表现在于道德依附、服从于政治;而服从于政治的道德是不可能以“自由”为基础的。严复上述比较分析的意义在于:以西方道德与政治的关系为参照,揭示了中国传统道德政治化的本质,剖析了中国传统道德缺乏“自由”的基础;提出了要把中国传统道德转换成以“自由”为基础的道德,首先必须将道德从政治的奴役中解放出来。
3、关于义利观的问题。严复对“开明自营”与“理欲相反”进行了比较与整合。严复十分崇尚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开明自营观”,主张义与利的统一。严复认为,中西古代都以义利分离为事,所谓“大抵东西古人之说,皆以功利为与道义相反,若薰莸之必不可同器。”[1](P1395)严复赞同“舍自营无以自存”的观点,但又认为不全面。他说:“民智既开以后,则知非明道无以计其功,非正谊无以谋其利。功利何足病?问所以致之之道何如耳,故西人谓此开明自营。开明自营,于道义必不背也。”[1](P1395)与“开明自营”的义利观相比,宋儒的理欲分割为二的观点就必须批评了。严复指出:“宋以来儒者以理属天,以欲属人者,致相反矣。”[12](P1395)严复“开明自营”的义利观,不同于传统中某些“因利弃义”学派,视利为凶物。他在为“利”正名的同时,仍然强调“义”与“利”的平衡。可见他的“开明自营”的义利观不仅是对传统义利分裂为二、视义利为绝对对立物等观点的否定,而且还包含着对新型义利观重建的渴望。所以,严复“开明自营”的义利观虽然带有近代资产阶级义利观的烙印,但其中具有超越近代资产阶级义利观的意向。
4、关于利己与利他的问题。严复对“两利为真利”与“独利不利”进行了比较与整合。“利我”与“利他”是道德史上争论不休的问题。严复认为,单纯的利己观念不仅使上下左右不能自由,而且使富强之政的施行受到阻碍。所谓“今夫中国人与人相与之际,至难矣。知损彼之为己利,而不知彼此两利无所损而共利焉,然后为大利也。故其敝也,至上下左右举不能自由,皆无以自利,而自强之政也无行于其中。”[3](P15)基于这样一种思路,严复否定了赫胥黎“屈己为群为无可乐”的观念。他说:“由此观之,则赫胥黎氏是篇所称屈己为群为无可乐,……于理荒矣。”[1](P1395)“屈己为群为无可乐”的观念与“理”相违,这是否意味着“利己”观念弃而不要了呢?严复以为这也不行,因为“利己”观念的丧失不仅与人性相悖,而且也有碍道德作用的正常发挥,从而对社会历史的发展将有消极作用。所以他在确定了“屈己为群”道德价值合理性之后,也肯定了“合理的利己主义”的道德价值。严复主张将“舍自营无以自存”的观念看成生命之学的规律或原则,指出:“而今人则谓生学之理,舍自营无以为存。”[1](P1395)可见,严复在利己利他关系上的态度是,主张二者的统一,反对任何偏向一极的观点。从当时的历史背景看,“两利为真利”的观念是对中西方道德史上利己、利他主义两种极端倾向的否定,对建构新型的利己利他关系观念具有提示意义。从历史的角度看,严复主张“两利为真利”的观念与“开明自营”的义利,都具有反对不讲道义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帝国主义置中国人民利益于不顾的自私与野蛮,以及要求帝国主义放松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约束以维护民族资产阶级自主发展等深刻的内涵。当然,这种道德上的愤怒与呐喊也深刻地折射出严复所代表的封建地主阶级的精神潺弱。
5、关于道德实践的问题。严复对“先义后仁”与“先仁后义”进行了比较与整合。仁,指人与人相互亲爱,是一种偏于情感的道德范畴;义,指正义,是一种偏于理智的道德范畴。在道德实践中,这是一对经常发生矛盾的概念。如何摆正两者的位置,不仅反映出实践者的道德风貌,也是检视一种道德科学与否、健康与否的标准。严复认为,中西方在道德实践中意气完全相反。他通过一位西哲的语言表述了自己这一看法:“西之言伦理也,先义后仁,各有其所得也。东之言伦理,先仁后义,一予之而后得也。”[4](P976)就是说,在正义与亲爱、理智与情感、公与私等现实的道德矛盾面前,西方以正义、理智、公为要,中国则以亲爱、情感、私为重。从君民关系看,中国的先仁后义,表现出对君主依赖式、等级性忠心与膜拜,情感的“仁”模糊而掩盖了理智的“义”;西方的先义后仁,则表现出对君主非依赖式、平等性效力与尊敬,理性的“义”约束而控制了情感的“仁”。从人伦关系看,中国的先仁后义,表现人与人之间道德关系的原始性、狭隘性,以及道德价值取向的落后性;西方的先义后仁,则表现出人与人之间道德关系的近代性、广泛性,以及道德价值取向的进步性。从表面看,严复这一比较,进一步揭示出中西方在伦理道德实践中对正义与亲爱、理性与情感、公与私的不同态度;从深层看,严复这一比较,进一步揭示了中国传统道德的非主体性、服从性本质。严复这一比较对深化中西道德整合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二、严复推进中西道德比较与整合的重要价值
1、开启了中西道德比较研究之先河,提供了中西道德整合的宝贵尝试。严复的中西道德比较与整合是中国道德史上第一次,无论内容上抑或形式上,都对往后的道德观念的中西比较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在进行中西道德比较研究的过程中,严复积极主张并推动了中西道德的整合,认为对中西文化应进行“迭相循环,互为弥补”,对西方文化既不能全盘导入,也不能简单的单项移植。他提倡“阔视远想,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2](P560),反对“以牛之体,以马为用”。同时,严复以中国社会现状为出发点,西方近代道德为参考坐标,积极汲取了西方道德的新鲜养分并与中国传统优秀道德相互融合起来,力图重建具有民族特色和时代特征的近代化伦理思想。这种近代化伦理思想成为当时先进人士的社会共识和凝聚人心的力量,为牵引社会发展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为后人树立了光辉典范。从而激励着近百年爱国志士为“自强保种”振兴中华前仆后继,康有为、梁启超、鲁迅、孙中山、陈独秀直至毛泽东都深受其影响。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5]
2、探讨了道德基本理论的中西差异,推动了传统道德向近代道德理论转换。严复指出中国传统道德是缺乏自由基础的非主体性道德。他批判了封建主义的重义轻利和禁欲主义观点,指出在这种传统道德精神下面,义利观是分裂的,“利己”和“利他”不是统一的,道德实践是讲情感不讲正义的。同时,严复也批判了资产阶级的纵欲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思想。在这种分析揭露的基础之上,严复提出了建设“以自由立教”的主体性道德要求,把传统的仁义道德和近代功利主义紧密结合在一起,即主张“开明自营”的义利观,“两利为真利”的利益关系观和“义”为首位的道德践履观。“庶几义利合,民乐从善,而治化之进不远屿!”[6]就是说,要获得功利,其行为以符合道义为前提,而道义的行为也一定会带来功利,“唯义乃可以为利”,[7]否则就称不上义行,民众也不会乐于从善,社会也就不会进步。这种不背道义的功利,即“两利为利”,“开明自营”,也即合理的利己主义,与极端利己主义是不同的。从中可以看出,严复在道德基本理论上的观点实际上否定了传统道德理论体系,企望建成一种人我两利,义利合一的新道德,即中国式的功利主义道德。严复提出的“两利为利”的道德命题具有超越近代性质,是一种理想状态,想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把个人利益同社会利益完全统一起来是不可能的。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心态在道德观上的反映,是近代中国社会特殊环境下的产物。但就道德文化的独立性方面而言,起了推动中国传统道德向近代化转换的重要作用。
3、提倡并宜传的“双利”等道德规范对今天社会生活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比如严复十分崇尚“开明自营”的义利观,主张义与利的统一。这种义利观对今天的现实生活仍有指导意义。一方面,我们在处理义利关系时,一定不能夸大一方,而贬低另一方,使得义利关系走向极端。第一,“以义释利”进而走向“以义代利”的极端(义排斥利)。由于封建时代的宋明理学家把作为普遍规范的义与理提到权威化的价值地位,从而禁锢了人们对合理的利与物质的追求,特别是用一种抽象的“义”来愚弄人的思想,限制经济的发展。这种现象,今天也有。例如,改革开放以前,在人们的价值观里,多年来只灌输抽象化的“人民利益”、“国家利益”、“无偿奉献”,丝毫不允许考虑物质利益、个人所得、有偿服务。似乎什么都不要、什么都没有,才是“大公无私”,而伸张自己所得、讲求经济效益,就是“自私自利”。此种混乱的价值观,铸成了“大锅饭”、“懒汉多”、“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出工不出力”等社会现象。这样,反而逐渐形成既不讲利也不讲义的潦倒心理;不但培养不出先进,反而造就了无数懒汉;不但没有让社会发展,反而使国民经济走向崩溃的边缘。邓小平同志曾指出:“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精神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8]第二,“以利释义”进而走向“以利代义”的极端(利排斥义)。在宋代,由于北宋新理学家过分强调“重事功”的功利原则,“兴利之臣日进,尚德之风浸衰”,致使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和王安石的“熙宁变法”两次社会变革均以失败告终[9]。这种过分看重物质利益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今天也是触目惊心的。如私欲贪婪所表现的惟利是图、巧取豪夺;良知泯灭所表现的假冒伪劣、见死不救;急功近利所表现的贪图时效、金钱万能。特别是钱权交易的腐败现象日重,使市场经济的秩序出现某些混乱的局面。只有把义和利统一起来,才会真正弄清“见利思义”、“见得思义”的意义。
另一方面,“开明自营”的义利观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开明自营”的义利观主张义和利的统一,这也符合市场经济时代所提倡的“贵义兴利”、“义利并重”思想。这种道德原则,对于我们今天在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加强人的经济行为中正直、正当、正义的品德,注重国计民生的实际效益,使百姓富足安乐、社会稳定,有着强大生命力的价值意义。其一,如果我们空谈道德性命,或者将道德原则同个人福利对立起来,抽象地宣扬存理去欲,就会挫伤人们的工作积极性,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如果只求个人福利,不顾社会正义,置公共利益于脑后,将功利主义引向个人利己主义,甚至不择手段地牟取暴利,势必造成市场经济的混乱,危害社会和谐与安定。其二,传统义利观主张的“见利忘义”、“以义谋利”,警策人们赚取利润时,切不可忘记自己的社会责任和义务,这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劳动生产者、企业家、管理领导者的要求,是完全一致的。为此,各行各业的经营者们应该正确处理义与利的关系,虽然经商盈利是天经地义的,但是要义中求财,见利思义。其三,在从事商业活动中要力求做到严格守诺,讲诚求信。孔子说:“信近于义,言可复也。”将信与义连用,证明信用就是道义,遵信戒欺就是做人的美德。随着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中国步入WTO,中国人就更应该诚信无欺,赢得世界人民的信赖,使自己的产品走向世界市场。中央颁发的《关于深入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进一步加强公民道德建设的意见》的文件中指出,“紧紧围绕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广泛开展‘共铸诚信’活动,加强诚信教育,强化信用意识,……坚决打击制假售假、欺诈经营、虚假广告、偷税漏税等违法行为,引导人们坚持诚信为本、操守为重,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10]此外,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强调要“增强全社会的信用意识,政府、企事业单位和个人都要把诚实守信作为基本行为准则。建立信用监督和失信惩戒制度。”[11]总之,在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大潮中,必须正确处理义利关系,既要用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道德原则去引导、调节人们对利益的追求,保障和促进各种正当利益的发展;又要以经济发展和调节人们利益关系为手段,保证现代社会道义原则的实施和更新。
4、倡导“新民德”,启动了中国近代再造国民性的新思潮。严复认为当时的中国封建统治严重摧残了国民的素质,出现了“民力已苶,民智已卑,民德已薄”的令人忧虑的状况,“民德、民智、民力”方面的高低优劣决定国家、民族的命运与前途。同时由于受斯宾塞等西方哲学家的影响,他认为个体品质的优异有助于群体力量的增强,“国,拓都也;民,么匿也。社会之变相无穷,而一一基于小己之品质。”[12]因此,严复非常关注“民德”建设,在中国道德史上第一个提出“新民德”课题。严复在《原强》一文中指出:“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所谓“新民德”,就是用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平等思想,取代封建宗法制度和伦理道德,提高人民的品质,形成国家观念、主人翁精神和新的道德风尚。中西道德比较与整合是这一课题的主要成果。笔者认为,正由于严复对民德与民族兴衰关系的论证和对“民德”建设的率先提出,无疑对梁启超的“新民说”、孙中山的“心理建设”、以及“五·四”时期“新道德”运动都是有一定影响的。维新派著名人物梁启超说过“严氏于中学西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严复翻释的几部书算是把19世纪西方的“主要思潮的一部分介绍进来了,这是戊戌辛亥期间我国学问上最有价值的出品。”[13]显然严复促进了近代社会声势浩大的再造国民性思潮。这种推论的根据何在呢?第一,中国人之所以在十九世纪末期开始认真全面地检视传统道德的价值,自然是在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冲击、民族灾难空前,传统道德已经暴露出种种弱点这个大背景下产生的。严复认为:“今日之积弱,由于外患者十之三,由于内患治者十之七也。”[3](P63)而在这个大背景下第一个明确提出以西方资产阶级道德为参照、重估旧道德、再造国民性的是严复。第二,严复之前,基本上没有人认为中国传统道德所造就的国民的品格有任何值得怀疑的地方,第一个将另一世界的人的道德观念、民气、风俗引进中国,在中国人心目中陡然树起一个新坐标,使中西道德比较、再造国民性格成为当务之急的是严复。第三,从原因上看,严复提出“新民德”是为了富民强国,梁启超提出“新民说”是为“维新吾国”,[14]孙中山提出“心理建设”,强调“革命事业产生于革命精神”,[15]“五四”运动时期“新道德”运动则是针对国民劣根性而来的。从途径上看,严复提出从教育着手,梁启超亦然,孙中山非常重视对士兵、国民的教育,“五四”运动时期,“新道德”运动实际上也是一场教育革命。上述事实表明,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严复中西道德比较与整合在形成近代再造国民性思潮上的广泛影响。
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历史的原因,作为初创者的严复对中西道德比较与整合不是毫无缺憾的。其中值得指出的是,严复在以西方近代道德对中国传统道德的批判方面是突出的。但他充满激情地指摘传统道德缺点时,疏于对传统道德优秀成份的发掘,从而使其中西道德比较与整合,在态度上显得较为极端,在方式上显得较为单一化。严复在晚年力图纠正这种偏向,但又有走向保守的一面,甚至有某些失误。真可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这也应当成为现代中西文化比较与整合实践之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