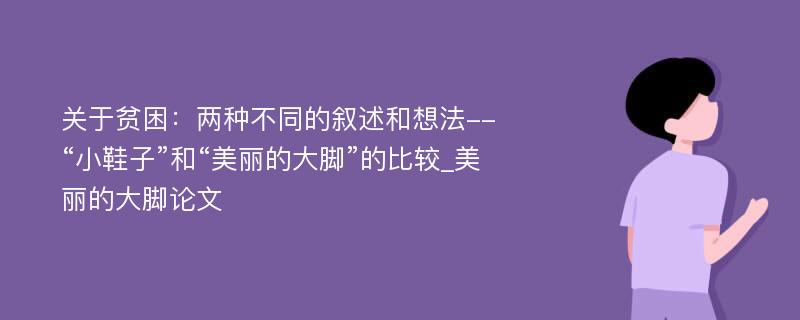
关于贫穷:两种不同的讲述和思考——比较《小鞋子》与《美丽的大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种论文,大脚论文,贫穷论文,鞋子论文,美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伊朗导演阿巴斯·基阿鲁斯达米近年来的电影《樱桃的滋味》、《橄榄树下的情人》、《在沙尘中跳舞》、《我在漫步人生》,以及马哲·马芝迪的《小鞋子》,戴锦华教授认为:“九十年代中后期,在世界(准确地说,是在欧美)艺术影坛内,伊朗电影以其体制内、低成本的温情故事取代了九十年代初精美的中国历史寓言叙述,成就了别样的第三世界电影景观。因此,世纪门槛上的中国艺术电影,便继豪华冷艳的画屏式人生展现转而盈溢起苦涩柔情。”[1]“如此温暖而苦涩的故事,你的眼睛会含着泪,同时会会心地微笑。第三世界的贫穷的生活,顽强的生存意愿。导演给艺术电影带回了故事,带回了朴素而美丽的讲述,带回了生活真切的片段。不是欲望,更不是关于欲望的欲望。了解这些被苦涩的柔情所浸染的影片,就会知道,为什么张艺谋突然选择了《一个都不能少》、张元为什么拍摄《过年回家》——多少因为基阿鲁斯达米引导出一个不同的潮流和表达。”[2]也会明白陈凯歌为什么拍摄《和你在一起》、孙周为什么拍摄《漂亮妈妈》、杨亚洲为什么拍摄《美丽的大脚》了。
伊朗导演马哲·马芝迪的电影《小鞋子》曾荣获1998年蒙特利尔电影节“最佳影片”奖,提名洛杉矶电影节评判团大奖,1998年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奖。
20世纪末,伊朗电影以自己独特的民族风情结合现代的人文意识而在国际影坛引人注目。可以说,他们的电影是把西方电影意识和自己的民族传统结合得最为自然和成功的。最感人的是电影里的人文关怀气息,导演以一种极其温情的目光关注了一个普通儿童以一种挣扎的方式去实现一个梦想的全过程。这种温情还表现在对阿里这样一个在窘迫景况下生存的儿童,导演没有表现出廉价的同情,而是体现出了尊重,在阿里那双清澈的大眼睛中,始终有一种倔强的光芒,这种倔强使阿里始终保持着对目标不懈努力的激情,也诠释着他的许多品质,他对妹妹的关爱,对父母的体贴,对学习的热爱,对善良的尊重以及自己应有的聪明机智,无不发乎内心,出于自然。当然,电影的成功更离不开扮演阿里的小演员哈希曼的出色表现,他的那双情感丰富的大眼睛俨然已经成为伊朗电影的一个经典性标志。[3]
杨亚洲执导的电影《美丽的大脚》讲述的同样是一个关于贫穷的故事。其实贫穷问题并非只是物质问题,它还有着心理精神方面的种种原因。这部影片确实很容易让人一下子就想到希望工程、城乡差别、西部开发、妇女解放等宏大主题,但就是这些,在看过片子以后,也还是感到无论从视角上和伦理上都没有太大的冲击力。给人的第一感觉是,这部片子在往张艺谋的《一个都不能少》上靠:西北、农村、贫穷、落后、教育,主题、场景、音乐(赵季平)等总体风格均较接近。
艺术上的摹仿与创新一直困扰着艺术家,谁都不想摹仿别人,不想与别人雷同,不想重复别人,甚至也不重复自己。导演杨亚洲曾经说:“创作上我有一忌,就是尽量不重复,无论是人物还是题材还是演员的表演。”[4]可这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不重复别人,即超越别人——难;不重复自己,即自我超越——更难。杨亚洲也没有绕开这个艺术的陷阱,他在刻意摆脱自己、摆脱黄建新之时,却无意间走近了张艺谋。且不说在题材、主题、场景、音乐、总体风格上与张艺谋的电影《一个都不能少》很类似,就连演员的选择、情节的编排等都能让观众在其中看到张艺谋的影子:都是取材西部,关于西部的贫困与落后、西部贫困山区的教育问题、西部发展等问题。在王大河与张慧科之间、在《掀起了你的盖头来》与《我们的祖国像花园》之间竟是如此的相似。
其次,影片的主题仍是贫困山区的教育问题,明显有主流意识形态的意图,给人的感觉是唤得人们的同情和感动,鼓励人们到贫穷落后的地区去“扎根”、去“奉献”。
关于西部发展、贫困地区的教育困境问题,在我国则是一个至今未能妥善解决的老问题,不然电影就不会一再涉及这个问题了。改革开放了许多年,我们的观念仍然很陈旧,只要一提到贫困地区,就去寻找那些乐于“扎根”、“奉献”的典型和榜样,然后鼓励动员,最后大肆宣传表彰。结果怎么样呢?尽管有许多的人乐于“奉献”,愿意到艰苦的地方去“扎根”,但这些老少边穷地区至今没有多少起色,它们仍然无法与内地城市相比,更不要说与沿海城市比较了。少数发展起来的地区,大多还是靠了政府的政策和资金,不然的话,一个连水电交通都不通畅的穷乡僻壤,单靠人的奉献精神和吃苦耐劳无论如何也建不成现代化社会的。
第三个问题是故事的结构:写一个好人,写一个好人受难没能得到善终的故事。这类极易赚得人们的伦理同情和道德认同的廉价故事,却是以丧失人性深度为代价的。
在那样一个偏远的小山村,张美丽凭那点可怜的文化知识勉强充当了教师——进行着文明的传承和文化的扫盲工作。城市里的青年志愿者——年轻、时尚、漂亮的女子夏雨“千里迢迢”到来之前,张美丽大概会一辈子就这样教下去,直到年老不能行动为止。可是夏雨的到来,改变了山村小学的习惯和观念:先是夏雨老师纠正了张美丽的错别字和不卫生的翻书习惯,当然这些都是象征,事情不是这么表面。影片中也写到了张美丽好心给夏雨洗衣服,却洗坏了夏雨的衣物,惹夏雨心疼发火;夏雨从城里来,始终不服那里的水土(又是象征)。张美丽让学生去镇上拣橘子皮给夏老师泡水喝,真的可以让夏老师留下来吗?夏老师不过是被张美丽的真情所打动才勉强喝下这橘皮茶而已,这种真情甚至还能让夏雨拒绝男友的劝说,而坚持留下来,可留下来的夏雨又能怎么样呢?靠一两个夏雨和张美丽就可以改变这大面积的贫瘠和漠漠黄沙吗?夏雨最后还是要走了!导演很宽宏,对夏雨,没有道德的责备和情义的挽留。可是,导演却空送了一个人情,出主意让夏雨临走之前提议让张美丽给这个不知道是否能通上电的山村小学校想办法买台电脑,这样即使夏雨老师走了,他们也可以与外界联系,与世界接轨了。当然,这让夏雨的撤退也有了伦理上的借口和心理上的平衡。张美丽“用计”(电影在这里故意朦胧了一下,引导观众猜测是用美丽的“身体”)挣齐了买一台电脑的钱,可是,一台电脑、甚至许多台电脑,又能为偏僻落后的山村改变些什么呢?这真是一个美丽而又肤浅的主意。
于是,后边的故事就不好展开了。所以,正当张美丽从京都回来,即将为家乡致富开辟出一条财路(销售土豆)之时,突然飞来横祸,有着一双“大脚”的张美丽不幸死于车祸,山村的脱贫致富一下子没了下文。设想一下:张美丽不死会是怎样?土豆销售出去了,穷山村致富了,接下来改造校舍,招聘教师,发展经济,招商引资……其实这些问题并不复杂,单靠政府的统筹安排就可以先期解决的,动员有志青年去“奉献”去“扎根”,倒是在绕弯路,把简单的问题搞复杂了。环境改善了,自然有人乐于去“奉献”、去“扎根”。
对于夏雨老师,导演也给予了极大的宽容和理解。夏雨老师回到京城后说再也不去那个穷山村了,而且还劝说张美丽也不要回去了,劝她离开它,不要毁了自己。夏的丈夫刘是一个概念化的人物,在电影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先是“千里迢迢”跑到乡下劝夏雨回京,继而与夏雨离了婚,刘一出场就被导演安排在了道德的审判席上。这里有着深刻的矛盾:理智中不该让夏雨呆在那样一个恶劣的环境之中,情感上又谴责了人们对那个贫困山村的遗弃。这或许是当下我们许多人对贫困山区的一种伦理态度吧。
第四,影片的女主人公选用了央视著名主持人倪萍,不是没有特别考虑的。倪萍最擅长“煽情”,而一个意在鼓励有志青年到老少边穷地区扎根奉献的故事,启用倪萍是再好不过的选择了。
可问题正是出在倪萍的过分表演上。话剧演员出身的倪萍,擅长表演,极易入境。在央视主持综艺节目,以惯于煽情著称。可惜在电影这门艺术中倪萍的所长却是她的所短,表演痕迹太重,有点虚假,这也是她的一贯风格。没想到电影中有一个场景真的需要倪萍煽情的时候,即张美丽带孩子们在京都开眼界时,王大河因再次学驴叫受辱,张老师借机含泪教育孩子们一定要发愤读书,将来好有出息走出大山(不是回去改造山区),走出黄土高坡,一惯煽情的倪萍却是平平淡淡,没能把气提上来,搞得不咸不淡的。
倪萍的陕北方言也不地道,按说话剧表演出身、大牌主持人,学说方言应该不成问题,可倪萍的陕西话一听就假,巩俐在《秋菊打官司》中陕西方言还没有倪萍说的地道,但巩俐没让人感到虚假。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倪萍的虚假感觉呢?戏剧化的表演、小品化的情节,是导致倪萍表演虚假感觉的主要原因。
最后,谈谈创作者(导演、编剧、演员等)在处理现代与传统、城市与乡村、文明与落后等关系时表现出的创作立场上的明显的动摇、混乱和分裂。在爱情上,对传统隐忍的爱情(张与王)和现代开放的爱情(夏与刘)如何臧否?创作者表现出了立场上的动摇。张美丽和王放映员两人的家庭都不幸福。影片一开始,故事就交代了张美丽的丈夫因盗窃之罪被政府严惩——枪毙了。这之后,张美丽把自己的精力一方面用在山村孩子们的教学上,一方面遮遮掩掩地继续着与王放映员那也许早已开始了的婚外之情;王放映员的老婆似乎有点弱智,终日里只知哭闹打骂,王放映员因与张美丽相爱而正想着寻找理由与老婆解除婚约,所以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甘愿忍受着弱智老婆的虐待,等待着“再打一次”,就心理平衡可以提出离婚的理由了。张王的婚外之恋,电影处理得有点儿戏,遮遮掩掩、偷偷摸摸,失却了情爱中的那份圣洁与美好,更没有表现出人性的压抑与挣扎的困惑和追求的无奈。其实,在电影背后呈现出来的却是导演与一般民众对婚外情、婚外恋的伦理观念及道德评判:婚外情、婚外恋是非正当的、不道德的、不光彩的、见不得人的,是违反伦理和挑战世俗的,所以,导演才处理得躲躲闪闪,当事人更无挑战传统的理直气壮。
导演似乎也不认可城市青年夏雨们那种现代开放式的爱情。夏雨与其丈夫之间缺乏应有的理解与沟通,夏雨的丈夫被导演派给了一个自私自利的角色。道不同,不相与谋,最后离开(或着说是抛弃)了夏雨。
关于城市与乡村,这似乎是一个永远的悖论。
一方面像张柠所说:传统的农业社会有许多的弊端,但它却是产生诗歌的又肥又毒的土壤;现代市民社会的确有许多好处,但它却是一块水泥地板,诗歌是无法生成的。另一方面,现代的艺术家们在这个喧嚣、拥挤、纷扰的城市中执著地寻找诗意,享受着城市的现代文明,又冷静地审视着城市的异化,他们中有的人甚至刚刚拿到了城市居民的户口本,便优雅地写起了向往乡村文明的“怀旧诗”。
导演的观念仍是陈旧的、概念化的,依然认为农村虽然落后、愚昧,却充满着温情与诗意;城市虽然现代、文明,却人情淡漠、金钱至上。其实,这又是一种新的偏见。乡村虽然洋溢着温情、荡漾着诗意,但这种自然的、原始的、纯朴的农业文明是与生产力的低下、生活的贫困与物质上的简陋相联系的;现代城市取代了原始乡村,表面的温情似乎不存在了,但代替它的却是一种更先进、更理性、更文明的现代契约社会。19世纪以来,人们对金钱的普遍诅咒,多少带有一种小农的偏狭和仇富心理。可是,这个“浑身上下每个毛孔都滴着肮脏的鲜血”的家伙在现代工业文明中却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电影中有一场戏却很能说明问题:为了筹集购买一台电脑的款项,正直、善良、正派的张美丽却不得不带着她那群纯朴的、天真的、无邪的、可爱的乡下孩子——小学生,为那个散发着一身铜臭之气的小暴发户扮演小丑,并抓起一瓶二锅头一饮而尽,酩酊大醉之后,甚至还可能为此而献出了她美丽的身体。面对文人们一再诅咒的丑恶的金钱,正直善良的脊背并非任何时候都能挺得笔直笔直的。
比较一下《小鞋子》,电影同样是关于贫穷的故事。导演朴素的讲述没有轻薄地去撩拨观众的同情怜悯和正义之感,也没有居高临下轻易地就给出脱贫的途径和蓝图。电影让我们看到了真切、关爱、理解、善良、诚实与勇气,以及孕育自贫穷中的互相照顾、克服困境、突破局限,一家人在超负荷的生活重压之下艰难度日,却不臣服于无奈和气馁,也不乞怜于人。[5]
两部电影的结尾也都有可圈可点的地方。《小鞋子》的结尾可以有几种设计,但都不如现在的结局。应该说,电影结束在这里最合适,电影虽然给观众和阿里兄妹都留下了不小的遗憾,可电影的美学效果却出来了。因为电影打动观众的不是欲望的满足,而是为实现理想而付出的不懈努力,以及在这种努力过程中始终渗透着的那份浓浓亲情,特别是承载这一温情叙事的苦涩环境,主人公是一对刚刚懂事、初涉艰难人生就知道替父母分担忧愁的幼小生命。可是导演太善良了,他也许不忍心让小阿里兄妹如此失望,小阿里的生存环境已经够恶劣的了,他无法再承担精神上的重负,否则他会被压跨的。于是影片在结束之前导演又暗示观众,阿里的父亲从城里打工就要回家了,在阿里父亲的自行车货架上,放着买给阿里和妹妹的新鞋子。
一个蹩脚的情节,删掉它也许更好。廉价的情感慰藉不但冲淡了电影的悲剧氛围,也失却了电影应有的那份艺术震撼力。
如果你是一个真实的人,你需要一种情绪来洗去思想的尘埃,独自地面对生活中的失意,你将坦然接受此时的落寞。人生有很多时刻,你会与自己心爱的人、渴望的事物错过,这时候需要的并非借助虚伪的神话来打破现实的失落和纯粹,而是宁静地与自己相守、坦诚面对、独自承受。[6]
电影《美丽的大脚》的结尾更草率、更不负责任。当年路遥和高加林们没有解决的问题——面对土地的去留问题——杨亚洲今天依然不能不再次面对。20多年过去了,政治与经济都没有为杨亚洲提供任何新的解决问题的方案:在没有去京都之前,张美丽只有一种选择——献身于山区教育;可是,去过京都(或者说走出山区)之后就不一样了,张美丽或者说杨亚洲必须面对“去”与“留”的艰难选择。很可惜啊,杨亚洲却没有20世纪80年代的路遥诚实和厚道,路遥把自己的不解、困惑、迷茫真诚地交给了读者,21世纪杨亚洲面对同样的难题则做出了轻松的选择,当情节不好展开时,他随手打发了观众,让张美丽死于突然飞来的横祸。
叙事立刻终止了,但是问题却丝毫没有得到深入的思考。
标签:美丽的大脚论文; 一个都不能少论文; 杨亚洲论文; 夏雨论文; 倪萍论文; 明星穿搭论文; 剧情片论文; 中国电影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