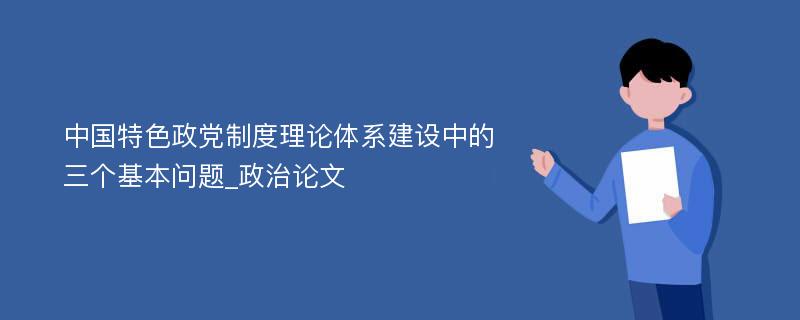
建构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理论体系的三个基本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党论文,中国论文,理论体系论文,特色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OI:10.3969/J.ISSN.1672-0911.2010.04.011
中图分类号:D6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911(2010)04-0011-04
新时期,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理论体系成为理论界的一个热点问题,这既是加强我国政党制度建设、促进政党关系和谐、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践需要,也是对我国60年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实践经验进行科学总结的历史必然,还是应对西方政党制度挑战、正面回应对我国政党制度的质疑之理论需要。总之,理直气壮地对“什么是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予以系统化、理论化的研究与回答,有利于牢固树立坚持走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的信心和勇气,有利于我国政党制度建设与民主政治发展。但是,如何建构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理论体系?这既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在此,笔者对建构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理论体系的三个基本问题略抒己见。
一、建构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理论体系需注意的两种思想倾向
如何建构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理论体系?不同人从不同角度、按照不同的逻辑、根据不同的研究范式可得出不同的结论。其中,有两种思想倾向或研究思路值得警惕。
首先,需警惕的是按西方的政治逻辑、政党理论、分析框架或分析方法来分析我国的政党与政党制度,试图构建所谓“具有普适价值”的政党制度理论。比如,从西方的选举逻辑、竞争性民主出发,认为只有竞争性政党制度即“两党制”与“多党制”才是真正民主的政党制度,在其他的政党制度如“一党制”下难以实行真正的民主。按照这种政治逻辑,则很难解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实际上,二战以后的西方国家,无论是“两党制”还是“多党制”,都是以维护现有的政治制度,在现有的宪政框架下,根据现有的宪法与法律开展活动。所谓“竞争性政党制度”是在根本政治原则一致基础上的有限、有序竞争,所谓的反对党也是在根本政治原则一致下的“建设性反对党”;而且,西方各国的政党制度呈现出明显的国别特点。再比如,从西方的政党理论出发,认为政党是民主选举的工具、政党天生为夺取政权而存在,不以争夺执政权为目的的政党便不是真正意义的政党。按照这种逻辑,则很难解释作为参政党的我国各民主党派的政党属性与政党特点。实际上,二战以后的西方,利益之争已经超越了政治原则之争,各主要政党相互妥协、逐渐趋同;为达长期或轮替执政之目的,各大党往往达成政治默契,通过制定各种限制条款来保护既有大党、排除或打击小党与新党,使大党能够长期交替执政,使小党永无执政或参政机会而成为“万年在野党”。如此看来,所谓“为政权而生”对西方小党而言只能成为一句空话。再比如,按照西方的分析框架或分析方法来分析我国政党制度,必然会得出符合西方价值倾向的结论。因为任何的分析框架或分析方法都以一定的价值取向为前提,即使最简单的分类背后也隐藏着一定的价值倾向,分析方法本身所具有的价值倾向必然会影响有关研究结论。目前,国家与社会“二分法”是流行于学界的政治分析范畴,以此“二分法”来分析政党与政党制度,其必然结论是:要么政党属于市民社会,要么政党属于国家,任何政党都不可能成为国家与社会的领导党,所有政党之间是平等的,政党之间不可能存在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按照这种逻辑,则很难理解我国政党、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很难理解“中国共产党是国家与社会的领导党”,“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或自觉接受领导)关系”。实际上,这种简单的“二分法”对早期资产阶级政党比较适用,如英国早期的“辉格党”和“托利党”都是在议会内部产生,根基在国家之内而不是之外;但对早期群众型政党并不适用,早期的群众型政党正是在争取公民权、选举权的过程中产生的,它们来自于社会,但并不是公民社会(因为当时他们没有公民权);即使对当代西方政党也并不适用,当代西方有学者“把公民社会界定为是反对政党的”,认为在德国,“‘公民社会’被用来指代由其他自发的团体而不是由政党来代表的社会(公民社会对抗政党民主)”;在美国,“‘公民社会’还用来指代社会中未被经济计算所影响的那一部分。”因此,当代政党可能同时属于国家和社会,也可能既不属于国家、也不属于社会。
其次,需警惕的另一种政治倾向或研究思路是:根据“斗争哲学”,延续“政党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一政治逻辑来构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理论体系。的确,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曾经从阶级斗争角度来强调政党的斗争、对抗与革命功能;但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方位已经发生重大转变,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一个在受到外部封锁的状态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当代中国的政治理念与政治生态也已发生了明显变化,民主、和谐、法治、文明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主流政治理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各政党的共同任务。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强调“斗争哲学”与政党的斗争功能显然已不合时宜、违背当代中国的发展要求。
上述第一种研究思路,过分强调民主与政党制度的普适性,有所忽视世界政党制度的多样性、各国政党制度的特殊性,忽视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态与政党制度现实,明显具有“洋教条”倾向。第二种研究思路,固守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表面上看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已落后于当代中国的政治现实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要求,具有“固步自封”或“马克思主义教条”倾向。上述两种观点的共同之处在于,脱离当代中国的国情、党情与政党制度现实,具有主观主义倾向。实际上,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理论体系并非人们主观构建的结果,而是以我国政党制度的形成与发展为历史逻辑,以当代政党政治实践为现实基础,以政党政治实践要素为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政党政治实践经验进行的科学化、系统化、理论化总结。
二、建构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理论体系要树立正确的态度与观念
研究与建构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理论体系,除了要警惕上述两种思想倾向外,在研究态度与制度观念方面,需注意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必须尊重我国政党制度的历史,正确认识其历史合理性;必须尊重、正视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现实,承认其现实合理性与客观性。实际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历史时期的政党制度各具特点,我们不能把政党制度的特殊现象视为“怪现象”,而应把我国的政党制度作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来研究。对此,西方思想家迪尔凯姆认识得很深刻: “要想超越事实,在事实之外去理解和指导事实,只能把事实看成是不合理的东西才行。如果事实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那对科学和实践来说就足够了:因为对科学来说,这时没有理由在事实的外部去探求其存在的理由了;因为对实践来说,事实的有利价值就是其存在的理由之一。”对于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及其理论体系的研究也是如此,既不能脱离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现实而进行主观构建,不能用西方政党理论来裁剪中国现实,也不能教条地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观点、用传统理论观点来裁剪当代中国现实;而是要端正研究态度、正视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现实,立足中国国情与党情,在事实之内来研究,寻求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内在逻辑;同时,要注意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对政党制度的时代要求。
其次,从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政党理论与民主政治理论相统一的角度,从基本政治制度、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高度来看待我国政党制度。要立足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现实,在科学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大胆进行理论创新与制度创新,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反对任何形式的教条主义与主观主义。要统筹兼顾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各个方面,统筹历史、现实与未来发展要求;统筹政党制度的社会整合功能、政治稳定功能与民主政治功能;统筹执政党与参政党、大陆政党与港台政党,注重事关全局的重大政党关系;统筹政党制度的宏观层面、中观层面与微观层面;统筹对政党制度的政党认同与人民认同;统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多党合作、政治协商之间的关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统一,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以民主化、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作为我国政党制度建设的根本目标。
再者,既要具有世界眼光,更要具有中国情怀。要把握政治与理论的话语权,用适合中国国情的分析方法、符合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理论逻辑、符合学术规范的中国语言来分析研究当代中国的政党制度。比如,要立足中国历史与现实进行研究方法与分析范式的创新,用适合我国国情与党情的分析方法如“国家—政党—社会三分法”来分析政党与政党制度,正确认识政党、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及其中外差异;而不是西式的、传统的“国家—社会”二分法来分析我国的政党制度。所谓“国家—政党—社会三分法”,简单说,即在当今政党政治世界,政党、国家、社会构成了现代政治生活的三大主体力量,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政党—国家、社会三者之间既有明显的区别,也有密切的联系。当代政党既不属于公民社会领域,也不属于国家权力领域,而是属于公共领域之公共政治领域。政党不是公民社会与国家权力之间的被动领域,而是具有独立的权利与意志的政治组织,“是以抵抗和统合为媒介以达支配的政治组织”。政党既需要赢得选民或群众的支持而执掌,参加国家政权,又希望影响或主导国家与社会;政党既有融入国家政权的本性,又惧怕脱离群众而失去民意支持,因此,必须与国家保持一定的距离,与社会保持一定联系。人民群众既希望通过政党来组织、引导政治参与,实现人民民主;又希望监督政党与政府,避免政治腐败。比较而言,“国家—政党—社会三分法”比传统的“国家—社会”二分法有更强的解释力。
三、研究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理论体系要坚持正确的民主观
建构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理论体系,除了要警惕上述几种思想倾向、树立正确的态度与观念外,还需坚持正确的民主观,正确处理一般与特殊的关系,用“特殊解释一般及其自身”。
首先,必须树立正确的民主观,以正确的民主观指导政党制度理论创新。什么是民主,不同人从不同角度有不同的理解,如有人从善恶角度对民主进行好坏判断,也有人把民主理解为一种精神、一种作风、甚至是一种工作方法。但从根本上看,民主是一种制度安排,尤其是指国家制度安排;民主的实质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由人民进行统治。但是,我们不能仅仅抽象地来理解民主,也不宜把民主绝对化、理想化;因为民主是相对的、具体的、历史的、发展的。民主形式、实现民主的方式具有多样性,并没有固定不变的统一民主模式。一定的民主必然与一定的时代相联系,与一个国家的国情、历史文化传统、人的素质等密切相关,与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相适应。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有不同的民主表现形式与民主水平。因此,民主不仅是一个复杂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复杂的实践问题;民主既是一种价值与形式相统一的政治制度,更是一个渐进的实践过程,是民主制度、民主实践、民主过程与民主实践者的“共同在场”。没有人的民主素质、民主能力的提高,没有民主环境,再好的民主制度也只能是一种无法实现的理想。
其次,必须坚持处理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建构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理论体系,既要正视、尊重我国政党制度的历史与现实,用适合中国国情的逻辑方法来研究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现实及其内在逻辑。也要注意进行比较研究,不仅要进行中西比较,还要进行东方国家与西方国家、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与非社会主义国家等的比较。但比较的目的不是为了复制或模仿,而是为了借鉴和吸收人类政治文明与政党文明的有益成果来促进我国的政党制度建设与民主政治发展,也只有在全面的而不是片面的比较中才能真正把握世界政党制度的一般性与特殊性。更要正确认识一般与特殊的关系,没有特殊便没有一般,不是一般能够解释特殊,而是“特殊解释一般及其自身”。对此,西方学者说的很精彩:“如果人们想真正地研究一般,就只好找到真正的特殊。特殊比一般更清楚地揭示一切。无休止地谈论一般已经令人厌倦,世界上存在着特殊。如果它们无法得到解释,那么一般也无法得到解释。”这对于研究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理论体系应该有所启发。
收稿日期:2010-05-10
标签:政治论文; 理论体系论文; 德国政党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英国政党论文; 政治倾向论文; 领导理论论文; 政党制度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时政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