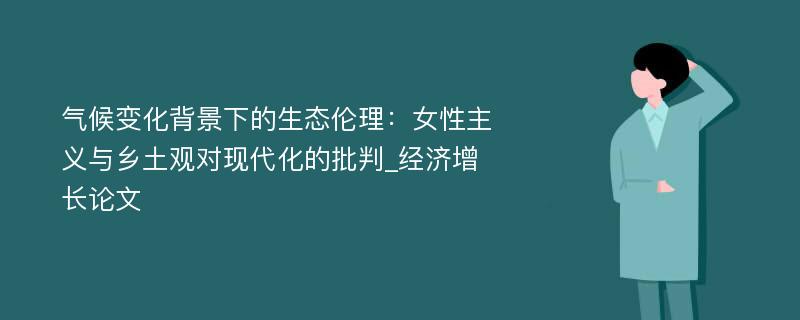
气候变化背景下的生态伦理:女权主义和本土观点对现代性的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女权主义论文,现代性论文,伦理论文,本土论文,气候变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个人到政治,从个体到整个国家的努力,从绿色公司到联合国,尽管我们付出了“最大努力”,但气候变化仍在持续恶化。本文将考察领导力的复杂性、对传统经济学的依赖和人口增长的复杂化,从而勾勒出真正改变主导规范的背景和可能性,这些规范并未能避免二氧化碳当量的碳排放日益增加。 现代世界观所独具的科技、创意和规范化实践已经为我们的巨大成功创造了条件,但气候变化却向我们清楚地表明,成功并不一定兴旺繁荣。为了避免沿着毒物过量的路子继续走下去,我们需要让自身摆脱因怀疑论唯心主义和现代技术而得以发生的异化(Heidegger 1977)。这一转变包括脱离消费主义的现代“世界观”,转向综合性、具体化以及面向未来的“世界图景”(world-scape)。目前对气候变化的应对依赖于短浅的历史认识,同时也依赖于为了让变革切实发生而进行的狭隘政策构思。这种方式,没有分析何为现代性,包括其观念、历史总体及其阴森地迫近的极限。这种视域的缺乏,预先抑制了我们的想象力,抑制了找到替代现有行事方式的其他选择的能力,尽管人们普遍意识到消费主义规范是问题之所在。为了实现这一必要的转变,需要从整体上对现代性加以审视,从其在欧洲城邦国家的最初起源,到以全球资源枯竭、污染、毁林、渔业过度捕捞和气候变化等形式表现出来的极限。这将揭示出什么仍然对我们有所帮助,以及我们需要适应什么。 领导力是适应新条件的重要因素。“领导力”原则适用于由气候变化提出的挑战。领导者不是生拉硬拽让他们的社群改行新的做事方式——领导力意味着鼓舞和支持人们心甘情愿地做出改变。领导者本身则需要对问题的背景和规模有一种很好地理解。与此同时,针对当代文化和气候变化,有几个关键要素:现代技术,规范性经济增长,以及全球人口。虽然领导力对所有这些元素都很敏感,而且在较小的程度上政策也受到这些要素的影响,但我们需要做出实质性的改变,包括对普遍持有的文化世界观的改变。 除了指出需要改变我们的世界观之外,笔者甚至更进一步认为,“世界观”这个概念本身就是将唯我主义的取向(solipsist orientation)置于特权地位,而我们则需要将自己重新想象成世界图景的一部分。与世界观概念不同的是,世界图景概念反映了看待人与环境互动的方法的转变。眼下,由于受唯心论的唯我主义制约,人们将自身视为无论是从地方来看还是从全球来看都是与生态背景相分离的,是高居于生态背景之上的。经济学和消费主义就是以这种人类中心主义观为前提。消费主义的不断增长与温室气体排放的增加密切相关,这是气候变化的根源。 经济学与人口增长 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从其在亚当·斯密著作(Smith[1776] 1904)中的早期古典主义形式到现有的形式,论证了根据个人贪欲的分配在伦理上的公平,更常见的叫法是“理性选择”。这种对消费主义和消费者地位的强调,使得说服现代的社群通过减少消费来减轻其碳足迹变得十分困难。 这种普遍流行的规范,就是让你多多消费。随着印度、中国和巴西——世界上最庞大的人口大国中的三个——的中产阶级不断增多,这种居主导地位的消费主义风气正在不断地巩固,并不断加深人们对温室气体排放的迷恋。 新自由主义理论对理性个体的信念,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怀疑论唯心主义。对市场中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总体理性决策起着平衡作用的“看不见的手”,是对国王得到上帝神圣指引的封建信仰(Devine 2004)的现代形式。将个人贪婪论证为理性的效用最大化,在现代早期的论著当中也并不是没有前提的,尤其是在尼科洛·马基雅维利对美第奇家族统治时期佛罗伦萨的政治分析当中。 经济扩张并不只是部分被选中的家庭、公司或银行的利润增长。20世纪30年代,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用乌托邦式的进步理想鼓励从事劳动的无产阶级致力于参与资本主义的规划。经济增长使老百姓有理由相信他们未来能拥有更多的消费品,而不只是现有的恶劣工作环境。也就是说,他们受到鼓励,在重复、枯燥和异化的条件中长时间地工作,因为他们也可以从消费革命中受益。每年都生产出更新、更好和更廉价的商品,抵消了工厂劳动和服务工作的单调乏味。但是,凯恩斯式的解决办法只有在消费主义(又名“经济增长”)持续上升时才能满足其条件。 20世纪20年代末标志着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第一次重大萎缩。而且,自经济大萧条以来,市场饱和现象频频发生。对此,经济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进步这个唯心主义的前提,并鼓励对产品和效率进行创新,以便继续从实际上已经拥有过舒适生活所需的所有东西的消费者身上抽取利润。在柏林墙倒塌之际,福山在其著名教科书《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人》(Fukuyama 1992)中谈到了这一点。 经济增长在许多国家被写进了法律,通常是要增长2%-3%。经济增长的前提是几个相互关联的因素:银行杠杆率,银行同业拆借利率,通货膨胀,技术创新和效率,市场在消费不饱和贫困人群中的扩大,以及另一个人们不太普遍承认的因素,即人口增长。自从得克萨斯州从墨西哥分离并入美国以来,银行的放贷数是其实际拥有财富的十倍以上。1995年,克林顿政府允许1∶30的杠杆率(Skidelsky 2009,p.7),导致美国产生房地产泡沫,并最终导致2008年到2009年间的金融崩溃。通货膨胀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抵消物质财富与银行持续放出的贷款额之间的差额的90%。 虽然经济增长对古典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都至关重要,但是由于消费永远不断增长的有害后果,所以当涉及气候变化时,经济增长就会成为问题。经济学家如尼古拉斯·斯特恩(Stern 1996)已经将这种联系弱化,他们论证说,政治人物、政策制定者和公众根本无法接受经济增长是问题。因此,《联合国气候变化年度进展报告》(COPs)不能提出经济增长这一议题,尽管意识到消费主义是排放的推动因素。鉴于消费产生的温室气体呈指数性增长,因此需要从更加广泛得多的意义上理解经济增长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 经济学也没有承认人口在其关于经济增长的各种假设中的作用。经济增长的函数被认为是从技术进步中得出的,但是,正如金融那样(Keen 2014),人口增长支撑着消费者人数增加这一前提。人口膨胀在若干方面是很重要的:人口数量的粗数据就意味着一个不断增加的市场;现代性的传播与庞大人口的结合,如中国和印度的情况,创造了越来越大的中产阶级消费群体;而且,总是既存在着将制造业外包给贫困地区的机会,又存在着持续的移民压力,将“发达”国家劳动阶层的工资保持在低水平。 由于在这个星球居住的人口超过70亿,地球上的大多数“生态服务”已经非常紧张。即使没有气候变化这一问题,如果人类再在这个星球上生存200年,那时人口将超过100亿,仅仅这两个要素加在一起,就足以制造一个巨大的需求,要求改变我们的现代文化规范和行为来适应。马尔萨斯在1789年就认为,人口在呈现指数式增长,食物的生产却以线性增加。他担忧最终人口将超过原始的行星资源和食物供给。人们对马尔萨斯提出了很多批判,理由是:尽管一些原材料正枯竭,但技术创新已经能够弥补和代替(Commoner 1971;Feenberg 1991)。在世界的很多地方事实并非如此,水短缺和饥荒已经成为一些地方一再发生的问题,如索马里和苏丹。因此,从本质上看,马尔萨斯(Malthus 1798)提出了一个与凯恩斯(Keynes 1936)相关的论点:经济生产是有限的,而人口规模正以指数速度膨胀,所以,经济扩张无法跟上人口膨胀的步伐。 自马尔萨斯时代以来,统计数字已经发生改变,大规模的人口膨胀正在开始放缓。根据模型预测,全球人口将在2050年达到92亿后进入稳定状态,然后开始下降(US Population Division 2008;Irwin 2008a,pp.88-113)。最新模型预测显示,更晚和更高的峰值将在2100年出现,届时人口将达到100亿,继而在全球范围内人口数量将以无法预测的速度下降(UN Population Division 2012)。古典经济学对人口膨胀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始终保持沉默,而更倾向于将利润与技术创新、效率和新市场的产生联系在一起。 针对人口减少和与之相关的消费需求降低这一问题,已经有两种解决方案:欧洲的解决方案和日本的解决方案。欧洲已经悄然调整其移民政策,以弥补其各国国内出生率的下降,使人口保持缓慢而稳定的增长。另一方面,日本则对其民族国家的种族纯正性采取一种更具保护主义色彩的方法。虽然与近代以前相比日本的人口已经大大增加,但也早已达到平衡,并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不成比例的“老化”。与欧洲和其他富裕国家人口减少不同的是,日本没有采用移民来弥补和大量增加其人口。相反,日本在过去几十年一直小心翼翼地处理人口零增长和低通缩这一问题。 现代性的调整适应 对于以消费为基础的社会中具备生态意识的社群来说,困境就在于如何让一个严重依赖汽车、电力、漂亮新衣服和其他消费产品的社会保持繁荣昌盛而又不让人感到被剥夺。显然,消费主义模式需要对排放这个问题负责,但是企业及在其中工作的员工也无法改变这一方向。我们又有什么别的办法能给千千万万的消费者提供商品和服务?然而,针对每半年进行利润回报计算而作出的标准化的立法,正是股东和政府税务机构的供养来源。除了持续的经济增长和与之相对应的消费主义和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增长,似乎没有了别的选择。从领导力方面看,每年发布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年度进展报告》第15条至第20条都会涉及气候变化的全球应对措施,但是却完全没有发挥作用。不管在全球还是国家层面,领导力方面都出现了危机,并且没有任何一方似乎有能力促成新的立法,以取代《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 相反,从全球层面到国家和区域层面,已有的立法和流程越来越被人们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所特有的愤世嫉俗和利己主义方式来对待。作为“京都协议”一部分的“减缓”和“适应”双重原则就是很好的例子。在全球范围内温室气体排放不断增加的背景下,减缓排放几乎处于停滞状态。 在现代气候变化话语中,适应具有三个要素:脆弱性(和复原力),风险管理,以及功效。如果只是为了强调应对有欠缺,那么就值得对这三个要素进行简单的考察。而且,发生在太平洋地区和美国新奥尔良的三个例子,很好地说明了每一种新自由主义是如何演变的。 适应的三个要素 脆弱性 “脆弱性”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位于太平洋上的袖珍岛礁国家图瓦卢。在那里,珊瑚环礁的脆弱生态系统正在“下沉”。这是因为气候变化导致的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造成的:海洋的酸化,起因于海洋吸收大量二氧化碳产生的副作用,酸化溶解了珊瑚的外部骨架;珊瑚生长的减少,无法弥补海平面的上升,这种上升随着海水暖化范围扩大和陆地冰川融化而发生。这种情况又伴随着健康的珊瑚环礁的消失而加剧,健康的环礁收集淡水资源,从而形成一个未被周围海水污染的淡水蓄水层,使人和动物能够在那里持续地生活。淡水的质量不同于盐水,并且珊瑚本身提供了一道能够渗水的屏障,这样雨水就能够保持未被盐碱化。珊瑚的漂白化和下沉正影响着淡水蓄水层,慢慢地,水体就会盐碱化,从而对生活在那里的动物和人的健康产生不利影响。有很多国家的珊瑚环礁正在面临这种困境,包括所罗门群岛、巴布亚新几内亚、拉罗汤加、纽埃、斐济、汤加、萨摩亚和基里巴斯等。图瓦卢人已经就他们所处的困境频频在国际舞台上发声,提出他们具有气候变化难民的身份,并要求作为一个具有文化凝聚力的群体到澳大利亚生活,这已经众所周知,然而他们的请求曾遭到拒绝。幸运的是,新西兰已经同意,如果他们认为自己的条件不再适合生存的时候,新西兰可以接纳他们。然而,还有成千上万的岛国人民正处于同样的困境,他们的命运还是未知数。尽管包容这些人属于适应“脆弱性”的范畴,但发生在这些情况下,适应能力实际上微乎其微。 风险管理 “风险管理”在美国新奥尔良地区发生的卡特里娜飓风过程中起到了主导作用。在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军已经接受对堤坝系统进行紧急维修的任务,这一系统可以保护该城市免受洪水袭击(US Army Corps of Engineers,New Orleans District 2003)。尽管美军高层提出了抗议,但通过对风险的统计分析,布什政府却认为有理由撤回负责征集维修力量的军队。时任布什政府副总统的迪克·切尼曾任哈里伯顿(Halliburton)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该公司后来负责管理对新奥尔良的清理。生命的损失,成千上万人和另外一些物种遭受的创伤剧痛,被简化成了分类账户上的密码。事实上,对这个保守派政府来说,这是一种双赢的局面,因为他们将军队派遣至伊拉克,并通过对这个城市部分地区的重建赚取了大笔钱财,同时却未能对另外一些地区进行重建,而是把穷人从新奥尔良永远迁出,毫无办法地将他们分散安置到周边的城市和州。因此,风险分析针对的不是人或环境的照顾。它是一种关于重置成本的保险风险的会计工作,从国内生产总值意义上说,是替代灾害损失的会计工作。虽然灾害可以使很多新建筑拔地而起,也因此导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但这是否能代表真实的经济增长,却是值得质疑的(Waring 1990)。 就好的一面来说,气候变化风险管理正在保险业中发挥更大作用。通过保险游说,人们正越来越多地向政策、企业和国际机构施加压力。 功效的特点,可以通过基里巴斯塔拉瓦回合会谈作出概括。在那里,另一群珊瑚岛礁居民亟须援助。基里巴斯于2010年组织召开了一次国际会议,以引起关注,并试图提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真正动议。一些强大的与会国,包括英国、美国和加拿大,参加了此次会议,并影响了问题的讨论,但却没有签署任何文件。《安博宣言》(Ambo Declaration 2010)是一个意义很大程度上已经被冲淡的文件,没有对主动限制温室气体排放提出任何具体建议,也没有来自联合国适应基金(UN Adaptation fund)的具体要求。莫宁斯塔和拉索(Morningstar and Russow 2010)声称,美国通过让基里巴斯和其他岛国可以获得章程规定很含混的“适应基金”这根“胡萝卜”,说服了这些国家签订《哥本哈根协议》(另见Carrington 2010)。该基金从2010年9月才开始分配资金,在墨西哥坎昆召开的十六个缔约方又重新将其纳入世界银行的管理,但是迄今为止,并没有得到来自捐助国的多少具体收入,尽管联合国表示该基金应该超过70亿美元,相当于富裕国家约0.7%的国内生产总值。西班牙于2010年捐资4500万欧元,但来自其他国家的资金非常不确定。 适应的概念来自生物学和关于旧石器时代的地质学,也来自于一些作者的笔下,如林奈、达尔文和斯宾塞。“适应”表明在应对生态环境改变过程中出现了生物物理变化。它具有一种不稳定的、通常很慢的节奏,并且在很多情况下难以成功,从而导致濒危物种的灭绝,这已经众所周知。在达尔文那里,适应有着一种具有竞争性的经济话语的弦外之音(Irwin 2013)。斯宾塞的那句名言“适者生存”早已被解释为暗示一种受害者活该的心态,“弱者”将被“更强大的”物种所打败。因此,在“适应”的论著当中,脆弱性、风险和功效这三个要素都浸透着追逐自我利益的新自由主义框架,通过这一框架,强大的游说团体将他们各自议程的言辞去政治化,避免对他们目前的排放水平负责,更不用说他们的历史责任了。新自由主义的豪言将伦理埋葬于一片沉寂之中,因为承受着遥远现代国家产生的排放物冲击的那些弱势社群无法让这些国家直接负责。满足地势低洼的小岛国和它们的弱势社群的需要被视为慈善,而不是被视为责任、正义或义务。 适者生存并不一定是强者生存。在生态学中,最适合的物种是那些最适应一般环境条件(气候、水、盐度等)并能与占据其生态位(ecological niche)的其他物种相适应的物种。当环境条件在较长时间得以维持时,在某个给定的生态位中可能出现种群数量爆炸式增长。这些物种失去控制的成功会产生有毒的副产物,这些副产物最终可能导致群体灭绝。这种生态综合症完美地描述了我们的全球生态位中的人类种群的特征。 全新世时期(大致为以往12000年)是紧接着更新世的最新、最温和的时期。由于毁林导致地球碳汇减少,进而导致温和的气候变化,所以人类活动有助于气温的相对上升。换句话说,我们是非常成功的,并且对我们的生态位产生了适当的影响,这一生态位实际上帮助我们得以繁盛(Irwin 2010)。然后,经历长期的合适条件,正如其他物种在可比环境中会繁盛那样,我们的人口开始呈指数增长。最初,从数量很少的基线开始,这种增长对全球生态位影响不大。直到大约200年前,人口增长量以百万计,然后以十亿计。 人口爆炸与工业革命的出现是相对应的,但并不完全是以其为条件。1769年,詹姆斯·瓦特的蒸汽机改变了劳动的性质,并让人们与土地和海洋的直接联系纽带得以缓解、解脱或者说疏离,这一论断依据的是分析。稳定的农业环境、新的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储存和医疗,都有助于使得整个18、19和20世纪的人口指数性增长成为可能。就其本身而言,物种的繁盛不应该被视为是问题。但是,正如生态学中通常的情形一样,我们已经成了我们自己成功的受害者。 我们的生产力的影响,正在对我们的生态位产生有毒作用,而在人类这里,这种生态位是全球性的。现代气候变化已经一点一点地将我们从平静而温和的全新世时代正式带人人类纪(Royal Society 2009)。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 2007;2013)描述了现代人类活动(描述工业消费主义的拐弯抹角方式)与失去控制的气候变化之间的相关性。在更新世时期,大气中平均含有280个百万分之一体积(ppmv)的温室气体。2015年2月,这一指标达到400(ESRL 2015)。美国宇航局气候学家詹姆斯·汉森(Hansen 2009)坚定地认为,我们需要将大气中温室气体含量水平降低到350 ppmv以下,从而使气候稳定在我们所熟悉的、能够维持生命的水平。斯特凡·拉姆斯托夫(Rahmstorf 2009)则声称,如果气温比前工业时代标准高出2℃,那么发生物种大规模灭绝的可能性将有50%。2008年,拉马纳坦(Ramanathan)和冯银厂(Feng)指出,已经在进行中的排放量表明,我们已经导致2.4℃的气温上升,并且正在越过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所模拟的较糟糕前景方案。南极和北极冰川的冰盖正在以比任何一种预测模型的结果更快的速度融化。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如果我们继续照常发展,我们就是处在将导致气候变暖比前工业化时代水平升高3℃或者4℃的轨道之上,或者说,鉴于我们目前超出了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所模拟的最糟糕前景方案,气候变暖比前工业化时代水平升高甚至要达到7.5℃。在这些水平上,生物灭绝速度将是毁灭性的。 我们是怎样陷入这种困境的?正如海德格尔(Heidegger 1999b)所说,我们是怎样突然间陷入这种接近虚无主义的区域的?还有,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以做什么来保持我们自己独一无二的成功?在接下来的部分,笔者想研究一下我们的规范性哲学假设如何长久地延续着现代消费主义的条件,而“忘记”了我们被嵌入其中的生态物种条件。现代哲学强调一种人类中心主义观,对气候条件毁灭性改变所要求进行的深刻变革保持着某种故意的视而不见。 现代哲学与技术视野 古典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以关于自我中心主义个体的假设为支撑,这个个体与自然图景相分离并且高于自然图景,而自然图景则被简化为一种可供潜在消费的稀缺资源。唯我主义将主体与客体相分离,是西方存在已久的哲学主题,它可能在笛卡尔《方法谈》(Descartes[1637] 1980)中得到了最好的诠释。这种将人类个体凌驾于客观自然之上的哲学假设,为将世界所有要素视为可供潜在消费者使用的“资源”的经济学态度提供了先例。 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概念是现代哲学的经典依据之一。他的假设仍然起到作为当今实证科学、现代技术、自由市场经济学和启蒙政治之基础的作用。17世纪中叶,笛卡尔在《冥想录》一书中推测,人类的思维从根本上独立于身体,同样,人的主观也从根本上独立于周围的客体。他的方法论是一种对知识来源的深刻怀疑论。他认为,关于某个客体(如一把椅子)占据空间的感官体验,很有可能是完全错误的。他论证说,椅子完全可能只是一种幻觉、一个幽灵,或者一个梦。甚至它可能只是一个试图欺骗我们的魔鬼摆在了那里而已。所有这些可能性都暗中发生作用,导致人体的感官信息不可靠。因此,对笛卡尔而言,唯我主义思想的逻辑演绎是确定客体真实的主要手段(Descartes[1637] 1980;Irwin 2008a)。 将演绎逻辑和思维置于特殊地位,已经被运用到性别歧视和殖民主义的道德政治以及对生态“客体”的大规模使用和滥用当中。对“少数派”和生态图景的政治宰制,都是以缺乏对没有理性思考能力的存在的道德尊重为前提的(Merchant 1980)。这些思想形成了所谓人类概念及其世界观的基础。也就是说,将理性、理性所产生的基本范畴和实体规范(substantive rule)置于特殊地位的做法并不适用于女性。为了让女性取得理性的资质并因此认识存在而让女性与其身体产生的联系太多了。女性曾经常被认为是“歇斯底里的”,这一状态曾被从字面意义上认为是她们的子宫晃荡在她们的器官腹腔之中(在古希腊语关于子宫的单词中,“子宫切除术”/“歇斯底里”这两个单词有相同的词根)。直至进入20世纪,妇女仍是法律上的未成年人,并被认为不具备投票所需要的理性。 妇女曾经并非不受法律保护的唯一群体。虽然殖民主义早于技术现代性,但其对现代思想的传播以及人口的扩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早期现代欧洲人遇到的原住民民族,最好的情况下被认为是“高贵的野蛮人”(如新西兰的毛利人),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则被认为是只优于动物那么一点点儿的群体(例如,在澳大利亚,土地被视为是没有任何人类居住者的“空”地)。一旦被物化,妇女和少数民族群体就可能在同样缺乏受到关爱或尊重的情况下,像原始森林、新渔场或多产矿井一样被利用。 海德格尔基于哲学的理由而非政治的理由批判了笛卡尔。海德格尔认为,笛卡尔应该为其傲慢感到内疚:通过将唯我论置于凌驾在“客体”之上——引申开来,就是凌驾于地球之上——的特殊地位,忘记了“存在”(Being)这个问题。海德格尔认为,“我思故我在”这一概念中的ergo(“故”)并非是不合理的,只是被误解了。笛卡尔未能表达清楚,主体只是相对于客体而言即在与客体相关联的时候,才呈现为个体(Heidegger 1973a;1977,p.131)。如果简单地去除“故”,演绎逻辑的前提被删除了,主体与客体间的关系也就变成了存在主义的关系。 个体唯我论主体被深受怀疑的客体所包围,作为对这种主体的替代,海德格尔认为,我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无意识地专注或沉醉于生活中的事物,即我们周围的“世界”。事实上,我们身边的事物有助于建构“我们是谁”,即我们的主体性本身(Heidegger 1962)。海德格尔认为,我们只有在事物发生问题时和这个问题凸显出其正常功能时,我们才会关注它本身。当你坐在一张椅子上的时候,你很少会注意它,除非它摇摇晃晃,或者它的设计不合理,让你坐得腰酸背痛(Heidegger 1968)。根据海德格尔的观点(Heidegger 1977),现代技术框定了现代思想的视野,所以我们是几乎无法观察世界的前现代或后现代形态的。我们的世界观由有关个体唯我主义自由的言辞所决定,技术在我们自己的知识与我们的环境之间起中介作用的过程中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相应地,关于气候变化的讨论,大多指的是那些将缓解这种危机并使消费主义的照常发展成为可能的未来技术发展进程。 工业革命进行以后,事物的性质以及人与自然和客体互动的方式就经历了变化,这一变化回应了笛卡尔的客体与主体分离。这个论点是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Spengler[1918] 2002)、恩斯特·荣格(Jünger[1931] 1993)以及随后的海德格尔(Heidegger[1954] 1973b)提出的。在欧洲,曾经经历一段长期延续的部落或封建农业时代。早期的技术非常依赖于季节性变化以及与天然能源的接近性。储存和运输可以实现,但是相对缓慢,并且产品可以干燥、烟熏和瓶装等,但这些东西无法长时间保存。 现代技术通过庞大的能源、运输、储存网络和贸易全球化减少本地生态约束的能力,已经彻底改变人们与其所处地域的关系。我们如今摆脱了大自然变幻莫测的束缚。与此同时,正如马克思(Marx[1867] 1887)指出,我们脱离了本地的生产手段。讽刺的是,现代技术的自由或间离效果促使人们重新关注他们个体的身体和头脑,因为这是劳动力的唯一可靠来源。农业生产不再需要我们对当地土地、水源和气候的直接了解,而是需要有关机器、化学品和转基因的专门知识。当地村庄被拆除,以便进行大规模生产。人们的流动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得多,因为他们在寻找工作的过程中被强行剥夺了传统领地和家庭经济。 某种程度上,作为对这种难以应对的困境的回应,技术进步的话语,特别是凯恩斯主义(参见Keynes 1936)对经济增长的承诺,有助于缓解异化劳动的痛苦与错位,使人们能够相信未来会有所改进,相信为了实现未来消费主义承诺的前景,现代生产过程的压迫和枯燥乏味是值得的。因此,反乌托邦和(矛盾的是)乌托邦在现代性的哲学与信仰体系中占据了关键地位。 对于海德格尔来说,对现代性的批判不仅仅是反乌托邦的。他提出的主要问题,采用的是早期天主教会关于语言终结(termina lingua)响声的古老说法,尽管他改变了宗教虔诚并保留了某些前现代的哲学关怀。他关心的是,现代对自然的疏离,无论是技术的疏离还是将主客体分离的怀疑论唯心主义哲学,都导致人们忘记了提问有关“存在”的真正有意义的问题。出于与此相关的原因,海德格尔关注的是,在技术视野之内,知识仅仅是来自于一种还原性很强的理性或逻辑,而没有来自其他的人类理解要素,如诗歌或艺术(Heidegger 1975;1977)。他相信,笛卡尔未能真正理解他自己的洞见,将cogito ergo sum(“我思故我在”)与cogito sum(“我思,我在”)——思考或者说意识到我们如何成为存在——混为一谈了(Heidegger 1982,pp.104-111)。 气候变化 从政治上看,人们很容易沉迷于保持人口量、玩刺激经济增长招数和抑制银行危机问题等短期的复杂性,而不考虑消费主义和矿物燃料燃烧对气候变化的极端的、常常是间接性的、有时候仅仅是预测性的效应。 海德格尔关于物仅仅为物(things simply thinging)、直到某物解体前几乎没有来自单个主体自觉意识的理解的分析,是与人们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未能有所作为相关的。如果变化是很渐进的,并且我们适应了这种异常,那么就很难记录发生了什么不同的情况,而且更重要的是,很难记录到底什么出了错。另一种选择是,让全世界(通过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和其他来源)对气候变化范围的承认凸显出过度利用资源和排放过多有毒物质带来的残酷后果,而这是前所未有的。承认我们通过经济增长来组织世界、将所有东西视为潜在资源的战略的失败,这样的承认应该是明白无误的。一旦意识到这一点,分析所需要做出的变革并开始实行这种变革就比较容易了。除非整个现代社会为适应气候污染作出深远变革做好准备,否则没有一个最高级别领导者能够带来那种必要的深刻方向转变。 要分析作为一种文明的现代性如何塑造我们的思维方式,是很困难的,因为我们的行为规范来源于技术视野(Heidegger 1977)。海德格尔认为,我们所能做得最多是从文明的两“端”将文明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即以文明在古希腊和中世纪早期思想中的发轫(Heidegger 1956)为一端,以文明的大限即他所说的“线”(line)或者说接近虚无主义的区域(Heidegger 1977;1999a;1999b)为另一端。 在一篇篇幅较小、较不知名的题为《论“线”》(Heidegger 1999b)的文章中,海德格尔认为,我们越是接近虚无主义的领域,就越难以回避,也就更容易理解。随着现代性终结的接近,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海德格尔本人著述的年代,有毒污染和对本地环境与文化传统的忽视已经十分明显。现代性的危险,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被希特勒精心炮制的大屠杀和死亡集中营以及战争的工业化所放大。1945年长崎和广岛遭受原子弹袭击后,核毁灭就在眼前,并且持续到随后的整个冷战时期。虽然海德格尔并没有那么早就知道气候变化,但他当然意识到了现代虚无主义的问题。 到如今,现代性容易导致的可怕暴力的戏剧性展示,已经被较好地净化为参与新自由主义形式全球治理的全球性企业、全球银行业和会计行业的正常活动。然而,尽管新自由主义的言辞在“可持续性”(Irwin 2008b;2014b)、“知识经济”(Peters et al.2008)、“创新”等(Marshall 1997)一系列话语中被漂亮地去政治化,但通过气候变化,人们普遍认识了工业主义对环境真实的毒性作用。随之,气候变化如今也在全球范围内为人们所普遍了解,尽管言辞上存在争论。有些人对此仍持怀疑态度,但笔者相信这种否认只不过是对恐惧、内疚和责任的一个心理反应,因此关于气候变化的早期认识已经形成,尤其是在一些较为发达的国家。社会最“成功”的部分,也是需要对温室气体排放负最大责任的部分。这些人习惯于十分正面地认识自己:他们是人类成功的巅峰,是努力工作、理性、技术创新和创业精神的“启蒙”标准。很难将这些成功的惯例与含毒状态画上等号。 社会中很大一部分人没有否认气候变化,但他们不确定自己能做些什么。基础设施不到位,所以无法使较轻的碳足迹成为可能:自行车道很少,公共交通有限,隔音隔热和建筑设计很差,全球化的大联合企业而非本地企业受到立法保护,是可以指出的几个例子。尽管如此,对于前所未有的变革,人们已经普遍有了某种准备。来自不同层面的例子包括:一些游说团体,如350°和气候行动(Climate Action);养老金计划不投资于矿物燃料;一些国家,如德国和日本,对太阳能进行补贴,使太阳能利用具有可行性。 总的来说,联合国系统是一种针对治理和全球立法的新自由主义的、通用的样板方法。在哥本哈根、坎昆、德班和多哈等地年复一年的召开会议后,对于联合国及其成员国在就气候变化进行有效立法、启动从污染向可持续性转变进程的“失败”,人们越来越感到失望。这个建立在起先曾造成气候变化的同样现代前提假设之上的新自由主义模板,其弊端正变得越来越明显(Irwin 2014a)。 无增长的富足 人类这个物种如此“成功”,以至于我们的人口数量已经呈爆炸状态,我们所产生的有毒副产物正在越来越不可逆转地污染全球生态位。我们的“成功”是具有总体性的,因此它正在导致系统崩溃。富有的现代化国家而不是“第三”世界国家制造了温室气体。但是,通过“发展”而不断传播的现代性正在鼓励另外一些国家复制现代性导致的有毒过火行为。并非现代性的所有要素都是问题,事实上,有很多要素都是一种惠益,但作为一个全面而系统的整体,技术视野、生产方式中的工业异化以及现代的概念或“世界观”,都起到将个体化的主体从其对所处地方的物理条件的责任或意识中抽离出来的作用。 将现代性的问题描述为单纯的工业技术生产和资本主义实践,曾经一度很流行。笔者认为,十分具体地说明到底现代资本主义的哪些要素正在造成问题,是很重要的。毕竟,贸易已经持续了6000多年,和人类社会一样历史悠久。在一个完美而自足的持续性、呈指数增长的经济增长系统中,并非贸易本身,而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形式,是与环境相脱离的。这种增长,是以消费的步伐而不是自然可持续性的节奏为前提的。 事实上,有一些其他的方法可以管理经济和人口,这些方法不会导致资源消耗和与之相伴的温室气体排放的持续增长。“凯恩斯式解决”证明经济增长对人民的合理性,到如今已有80多年。经济增长的信念完全常态化了。但是,许多最新研究显示,幸福并不依赖于不断增加的消费。到了某个程度(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低程度)之后,人们并不感到真正快乐,而是变得更为担忧(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Survey 2010)。地位身份与货币资产也并没有必然联系——问问大多数学者吧! 对经济增长的批判,有着悠久而辉煌的历史传统。梅多斯等人(Meadows et al.1972)的《增长的极限》之后出现了很多著作,特别是那些在世界银行等全球性机构工作的经济学家所写的著作。这些著作致力于从整体上研究系统。赫尔曼·戴利(Daly 1996)、约瑟夫·斯蒂格利茨(Stiglitz 2003)、戴维·哈维(Harvey[1984] 2007)以及澳大利亚经济委员会委员蒂姆·杰克逊(Jackson 2010)是对这一领域作出重要贡献的人士。“无增长的富足”(Prosperity Without Growth)成了主旋律,这需要现代经济学的核心前提从盈利底线转而变为让社群和生态系统维持健康的状态。 对现代制度的批判也已经很普遍,并进行了很长时间。伴随着历次联合国气候会议,还有很多类似会议贡献了各种思想。对《联合国气候变化年度进展报告》缺乏变革动能的失望,激励世界一些地区独自举办有关变革的国际会议。全世界的原住民长期以来已经对现代哲学和实践非议颇多。200多年前,北美印第安战争之一的小巨角河战役就涉及现代社会与大自然分离的做法。2010年,在玻利维亚科恰班巴举行的世界人民气候变化和地球母亲权利会议以一种共同的声音对缺乏行动与错误的理念提出了批评: 我们将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视为一种必要,并且考虑将适应视为一个过程而非一种强加的负担,以及视为一种能够有助于抵消这些不利影响的手段,同时表明,在一个不同的生活模式下,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是有可能的。 (People's Agreement of Cocha Bamba 2010,np) 《安克雷奇宣言》(Anchorage Declaration 2009)也表达了类似的主张。原住民坚持认为,客体与主体分离,延伸开来,社群与其当地生态背景分离,是危险的,也是不必要的。 土地(胎盘) 笔者相信,现在是该开始听听这些孕育着能减轻气候变化问题可能性的声音了。在唯心主义传统中,人类一直处于宇宙的中心,这种观点反映的是认为太阳和其他行星都围绕地球旋转的时代。笔者的论点是,需要摈弃这种过时的世界观,从而使人们有可能对人类彼此互动、对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有更具参与性的生态方面的了解。生态研究方法不仅仅涉及本地的客体或本地的生态位,而且包含行星的多个维度,包括气候、海洋、景观和物种,直至包括个体的特殊性。这种摆脱人类唯我论并转向复杂而动态的行星生态的方向调整,对长期以来的信念构成了挑战,这些信念主要涉及唯心主义主体性、认识论、时间、沟通、经济学和“成功”的规范标志。 那些与现代消费主义和现代技术联系尚未如此密切的人们会更容易记住前现代哲理,这些哲理将人类与地球视为一体。他们也更容易记住原住民的人民概念,这些概念通常是以社群为取向而非个人主义。也许更重要的是,他们往往拥有一个整合良好的概念化世界图景,在这个图景里,人们居住并热爱着他们本地的生态环境。在现代技术将我们从本地生产的约束和速度“解放”出来之前,这在某种程度是一种文化遗产。笔者认为,在气候变化带来的全球生态问题将我们带回环境的世界图景、我们征服大自然的狂妄正在显示出缺陷并与日消减的时期,可以用后现代术语对这些想法进行再概念化。 在西方现代性兴起期间,笛卡尔因忙于怀疑自己身体存在的证据,将一种严格还原的理性置于特殊地位,凌驾在真实的环境情景中真实的人类动物所具有的关系之上。这种怀疑论唯心主义世界观已被用来证明一种男性化的理性形式,这一形式让妇女和原住民的声音不合法。经过几百年,与技术有关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失去控制的成功,已经导致广泛的毒性作用的产生,以至于我们现在面临着相当于生态灭绝的困境。现代的做法已经肯定会让地球温度比前工业时代水平高2.4℃。如果我们继续照常发展,我们将会遇到全球温度比前工业时期高3℃至4℃以上的结局,这将导致50%以上的生物灭绝,降低大多数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 毫不奇怪,谈到对现代怀疑论唯心主义的规范性异化的挑战,来自妇女和原住民等被边缘化的群体的概念可谓是硕果累累。新西兰的毛利人有一个概念,或许可以有助于改变怀疑论唯心主义的传统观念,而又不完全消除现代性的某些明显惠益。在毛利人的语言(以及整个太平洋地区的语言)中,人民总是与土地结合在一起讨论。不提“土地”(whenua),人们很少提及“人民”(tangata)。whenua不仅指土地,还指“胎盘”。这个比喻非常重要,因为胎盘可以使母亲和胎儿这两个独立的存在同居在一个身体上。这是一种关于养育、联系和区别的比喻。 “whenua”很少被置于当代全球语境下作为一个哲学概念来深入考察(Park 2006),但这个概念值得置于现代和前现代语境中加以适当思考。传统上,“whenua”有着丰富的内涵,包括地方、联系和社群。它指的是,人们保护和培育土地,而反过来,土地也保护和养育着人们。《安克雷奇宣言》中的表述和我的观点类似,但是可能比我表达得更好: 我们重申土地、空气、水、海洋、森林、海冰、植物、动物和我们人类社会之间牢不可破和神圣的关系,这也是我们生存的物质和精神基础。 (Anchorage Declaration 2009,p.1) 当我们思考怀孕的物理和哲学意涵时,whenua或“胎盘”的另外一面出现了。与不拥有Rh阴性血型系统的太平洋地区民族不同的是,我的血型是Rh阴性。当怀孕的母亲是这种血型,而她的胎儿却是Rh阳性血型时,这就成了一个问题,因为这个母亲的身体会完全排斥这个胎儿。在这个例子中,胎盘的作用得到了很好的诠释。胎盘是一个将营养物质从母亲体内输送给婴儿,等胎儿吸收足够后又输送回母亲身体的器官。胎盘可以将血液养分分解为其原始的化学成分,并转变血液和羊水的物质成分,这些血液和羊水在母亲与胎儿之间循环流动,却并不伤害任何一方。胎盘可以使母亲与胎儿之间存在差异,并且使胎儿、发育长大,而不会导致胎儿的血细胞攻击毫无防卫能力的母亲的血细胞,或者说,如果母亲有对Rh因子的抗体,而她的身体在受孕时重新吸收胎儿,胎儿就能发育长大。 怀孕是一个独特的比喻。它是对难以释怀的现代性个人主义的一种解药。它抨击将心灵与身体进行唯我主义分离的做法。两个独一无二的人(还可能是多胞胎)占据了“一个”身体。没有什么比现代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更不靠谱的观念了。此外,“胎盘”或whenua,是对某种程度的自由、这些独一无二的人们相互之间存在某种差异的比喻,但是,他们又在一个产妇身体的养育区域之内——一种同一性中的差异。whenua是人与土地之间的关系,同时也保持着他(它)们之间相互保护和养育的关系。这个简单的比喻重新将身体与大地带人哲学领域,同时又不让对“启蒙”政治来说如此重要的基石——自由与解放——失去活力。whenua是养育呵护的机制,也是一种差异化的“差异分布”(Deleuze and Guattari[1980] 1999)。 毫无疑问,现代性与生态的疏离已经使一定程度的自由和相比较而言的富裕成为可能,这使得一些社群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得以蓬勃发展。自愿地减少我们生活方式的这种自由,即使并非不可能,也是很困难的。然而,气候变化已经让我们认识到,这种疏离不仅仅损害我们的社群和当地生态系统,而且极有可能导致成千上万的生命形式在较短时间内灭绝。气候变化告诉我们,现代性,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和经济增长,是有局限的。 好消息是,接近虚无主义的区域使我们首次领会到采取行动的迫切性。到底什么需要改变以及我们如何去做这些改变,已经变得越来越清晰。适应必须将重点放在现代资本主义——不是将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带入这种消费模式。我们需要摆脱将盈利作为底线的做法,转向创造和利用尊重当地生态系统的技术实践的机构制度。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将制造更少的污染,排放更少的温室气体,同时维持高达100亿的人民繁盛的需要。 我相信,人们已经为变革做好准备。他们只是需要方向。对笔者来说,这个方向很简单:没有经济增长的富足;从关怀爱护(而不是资产)获得身份地位;whenua,或者说人与土地之间的相互养育。这些想法并不是回归某种神话般的浪漫田园主义,也不是回归再造的部落主义。相反,它们提倡当代技术的世界图景,更加有理有据地强调生态系统——whenua。 如果我们要调整现代性来适应,以减少其对气候的影响,就需要严肃认真地看待那些针对以下各方面提出的重要批判:理性、个体的效用最大化,“看不见的手”,国内生产总值,以及经济增长。资本主义实际上已经破产。股市将制造巨大的泡沫破裂周期,但它在目前风气下仍会被允许运行。只要它仍然是全球经济学的基础,金融杠杆就将继续使经济增长和消费主义的指数增长成为必要。 我们还可能有其他形式的全球贸易,它会继续让地球上的人民获得提升(Jackson 2010)。与“同类”进行贸易可以创造公平的条件。尽管“现代”民族国家会有一些剩余财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财富也会逐渐拉平。对降低全球人口增长和将温室气体排放降低为零而言,需要真正的公平,而不是浅显的花言巧语,这种花言巧语将大国的真实情况去政治化,并且掩盖它们不情愿中断对贫穷国家的持续剥削。要么我们努力实现这一目标,要么听之任之。我们生活着,我们有机会创造文化变革。一旦越过那条线,我们再关注或关心将不再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