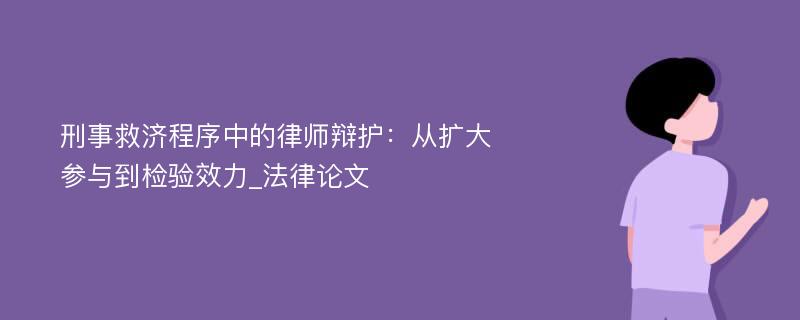
刑事救济程序中律师辩护:从扩大参与面到检验有效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有效性论文,律师论文,程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我国诉讼制度逐步向对抗式转轨的过程中,如果缺少了辩护律师的审判多少有那么点不公正。律师提供帮助几乎成为公平审判的一项核心要素,一是确保控辩平等武装,二是促使法庭不偏不倚,这甚至成为国家自由的一个象征。如果单纯从时间或者阶段来考察,不论律师的帮助权是从审判向前扩展或向后延伸,本身只昭示了律师参与的形式意义,而如果从辩护的有效性角度来考察,这种时间段上的延展并不只强调形式意义上的有无,而更注重考察实质效果上的大小。这种实质性不仅仅强调制度有效辩护的正面保障更侧重未受律师有效辩护的事后救济。目前在我国研究此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从制度演进来看,我国刑事诉讼大体上是一种国家机关行使广泛调查权的持续的分段式的诉讼。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权经1996年刑事诉讼修法从仅以法庭的审判活动为中心延伸到审查起诉阶段,甚至把律师的介入更进一步提前到了侦查阶段。由于侦查的秘密、强制导致问题重重,这种向前延伸的立法变化算是对症下药,起到了预防之效。但是,律师提前介入可能因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先天缺奶”(侦查阶段无调查取证权)、“后天没粮”(复印件主义使审判阶段阅卷权受限)[1]的律师辩护的依仗无异于饮鸩止渴;虽然辩护律师具有独立地位,但是把律师和被控人统称为辩方,这可能会产生“错责错位”的情形,让有天然辩护权的被告人来承受因律师(派生辩护权)的积极错误和消极“怠工”造成的人身、财产甚至生命上的不利后果。其次,在我国“审判”往往就是第一审甚至还只是普通程序的代名词,立法中的“人民法院”也往往被潜意识的理解为一审法院,而二审、再审或者死刑复核程序,或者因为立法对一审普通程序的参照而显得粗略,或者因为事实认定已经丧失了一审程序的新鲜刺激,这些程序中被告人是否享有一种只具有形式意义的律师辩护权都让人狐疑不定,因此突出向后延伸的问题更加重要。再次,我们的一审甚至二审(被称为终审)审判活动往往还不能对事实做到一锤定音,区别于国外续审制和局部法律审,我国二审、再审的事实审和法律审的全面审查的复审制,由于事实发现的无限可能而导致事实认定的不断“返工”,因而为保障事实发现和纠正错误向后延伸到救济阶段的律师诉讼参与甚至比一审更为重要,但是这种辩护要求的不断加码与其效应递减的趋势呈现强烈的反差。最后,我们正在向国际标准或者西方发达国家的诉讼制度接轨而力图塑造的“以司法裁判为中心”的“公正审判”往往被局限于审判阶段,是一种与诉讼阶段论相对应的审判中心论的误植。因此,对被告人权利的真正保障,除了要把律师介入的时间提前,还要向后延伸,除了在各个阶段保障辩护律师的参与面,还要在上诉审阶段检验律师辩护的有效性,甚至通过推翻事实认定、推倒程序经过的方式。
下文首先概要介绍以公平审判权为基础的律师帮助权的核心内容及其从消极抗辩的形式意义向保障有效辩护的实质意义转变的最新发展,接着论述我国刑事诉讼尤其是在一审审判以后的二审、再审、死刑复核等救济程序中试图扩大律师参与面上力不从心,转而论证通过检验律师辩护有效性来保障被告人权利是一个恰当的选择,然后分析了英美对抗制诉讼的国家检验被告人未受有效律师帮助的“行为瑕疵”和“不利后果”双重要件的形成的理论及实践。最后,本文一方面指出与国外在救济程序中关注点从事后救济向同步律师行为监督的方向相反,我国恰恰是从强调辩护律师的参与转向到确立被告人“未受有效律师辩护”的救济制度,要注意这可能与救济审的“全面审查”的不协调,可能打击律师辩护积极性,并在一定程度提出了司法能动性的要求等;另一方面,本文指出与国外因“未受有效律师辩护”检验标准的模糊性而从外部审查转向内部职业自律的方向相反,我国为防止在律师违法违纪上纠缠不清,而强调从律师职业自律转向在诉讼程序中审查律师过失行为是否对被告造成不利后果。
一、域外演进:从形式意义到实质意义
律师有效辩护以公平审判为其基础,受有效律师协助的权利,目的不在改善律师执业水准,而在确保公平审判。①公平审判权是确认和保护每一个人作为人享有的接受公平审判的一系列权利的总称,从制度的发展来看,公平审判权多少有一种渊源于国内法的“不约而同”,例如,从英国1215年的自由大宪章到1679年的人身保护法和1689年的权利法案,从法国的人权宣言到美国的独立宣言和宪法修正案,欧美各国纷纷确立了法律的正当程序和刑事被告人的公平审判权利;这又进一步发展为国际法上不可保留、不可克减的公认准则,②成为国际法确认的一项非常重要的人权。公平审判权具有主体的广泛性(一切人)和内容的多样性(获得司法审判权、接受公开审判权、接受平等审判权、接受及时审判权等)等特征,是最重要的程序性人权,一种以突出保护刑事诉讼中被告人权利的方式来保障所有人的基本人权,被日本学者鹈饲信称为“基本权的基本权”,其实质是保证控辩双方的平等。基于刑事审判程序中控辩双方天然的不平等,获得律师帮助权是其中的应有之意。在美、英等对抗制国家的刑事司法体系中,代表当事人利益的律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律师辩护效果的优劣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着刑事案件的结果。这甚至是一项宪法性权利。在美国,“许多宪法学家认为这是被告人最重要的权利,因为正是通过辩护律师,被告人所有的其他权利被确信受到了保护”[2](P.66)。
在对抗制国家辩护制度的发展史上,获得律师辩护的适用范围不断扩大有两个表现:一是诉讼阶段提前。被追诉人可以获得律师辩护的诉讼阶段逐步提前,从最初的审判阶段逐步扩展到整个审前程序。二是法律援助范围的扩大。从委托辩护发展到国家向贫穷者以及其他符合司法利益案件的被追诉人甚至所有自己无力聘请律师的刑事被追诉人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3]。因此,传统的审判意义已经逐步拓展到为审判进行准备的侦查和起诉程序。当然,这些都还是一种形式上的平等。在对抗制下,辩护人的怠惰、疏忽或者失职问题往往会使刑事被告人蒙受损失,获得律师辩护权还要求对律师辩护效果进行有效性的评价,真正从形式平等逐步向实质平等跨越。现代美、英等国家,获得律师有效辩护已经逐步被判例法确认为刑事被追诉人的基本权利。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1932年在Powell案③判决中首次明确指出“有效的辩护”的意义,突出了州政府对死刑案件贫穷被告人委派辩护人的责任以及被告人自行聘请律师在审判准备和审判进行中没有足够时间和条件提供有效援助,法院为其指派辩护人的职责。1938年要求联邦法院的重罪案件(法定刑1年以上有期徒刑)政府应为无资力被告聘请律师,④1942年联邦最高法院判决“州政府”对重罪案件无此义务,⑤而后随着1963年“正当程序革命”下吉迪恩号角的吹响,⑥联邦宪法第6修正案通过第14条修正案正当程序条款适用于各州,各州政府也应为重罪案件的贫穷被告聘请律师[4](P.7-8)。1970年,联邦最高法院在McMann v.Richardson案⑦判决中将联邦宪法第6修正案获得律师辩护的权利解释为获得有效的律师辩护的权利,把接受“有效辩护”的权利拓及包含接受指定辩护和自行委托辩护的所有被告人,成为一项人人平等享有的基本权。国际人权公约也在许多地方规定辩护律师应向其当事人提供“有效的法律协助”[例如,在1990年哈瓦那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上通过的《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以下简称《基本原则》)第2条、第6条及第21条]。
律师辩护权从被指控人的辩护权派生而来,而对律师辩护权有效性的强调又需要无效辩护制度的保障。甚至在上诉程序中被指控无效辩护的律师数量成为区别英美国家律师辩护能力的显性因素。⑧有学者根据人权概念从传统向现代、从消极自由到积极自由的发展做出律师辩护权在法律上两大演进阶段的概括[3]:第一阶段是被控人从身份关系中客体地位挣脱获得作为公民对抗政府无理追诉的一项权利而出现的消极防御权利;第二阶段是超越个人与政府之间契约关系,从辩护权中发展出获得律师有效辩护的内容,国家因而承担起保障被追诉人获得律师有效辩护的义务。律师具有了被控人权利和国家义务的双重代理人身份。在美国联邦和州法院的定罪后救济程序中基于没有获得有效辩护而提起诉讼是最普遍的权利声称。⑨在对律师辩护有效性的检验标准上,也逐渐从律师行为“不称职”转向律师行为是否导致了审判上的不公,即律师的行为是否对被追诉人如此不利,以致法院可以确认被追诉人没有获得公平的审判。无效辩护制度的机制特征有[3]:第一,它针对辩护律师消极履行辩护职责而侵害被追诉人利益的行为,不是针对律师过分积极行为。第二,它是一种刑事程序之内的权利救济方式(在美国则有定罪后有各州的直接上诉程序和联邦的平行程序如人身保护令程序⑩)。让过错律师承担诉讼程序之外民事赔偿责任或者相应的纪律处分,对弥补被追诉人的刑事司法利益(更主要地涉及公民的人身自由甚至生命)损失远远不够,基于普遍情形下的辩护律师独立诉讼地位以及特殊情形(指定辩护)下其协助国家保护被追诉人利益的义务而产生的法律责任[4],(11)需要通过评判律师失职行为及其对案件结果的影响程度,改变案件的审判结果或重开公正审理案件的程序,以救济被追诉人受到侵害的获得律师有效辩护的权利,进而保障被追诉人避免被错误定罪的风险。这在起到促进有效辩护作用的同时,还发挥了法官在预防无效辩护上的积极功能:(1)法官的指定辩护职责;(2)对程序进行中保障有效辩护的职责;(3)对无效辩护的救济职责。总体而言,有效律师帮助制度的设置既追求控诉方与辩护方攻防力量的平衡,这是外在的公平审判的要求;同时,强调律师诉讼地位和被告人地位关系的平衡,这是内在的责任承担机制的划分。
与国外的制度发展方向相同步的是,我国在被告人获得法律援助方面也不断的扩展着律师辩护制度的范围,律师的辩护权也不断提前。我国宪法第12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这作为司法机关运行中应当遵循的“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的一项原则,是公民享有“有效辩护”的推定性权利依据,该条置于“国家机构”章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节,与“公民基本权利”的表述还是有些差距[5](P.92)。并且,我们一般不能机械地理解为仅仅局限于审判阶段。当然这只是追求一种形式上的平等,而律师的诸多权利仍然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从律师与被控人地位关系来看,在我国辩护人是独立的诉讼参与人,虽然他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专门维护者,但是他独立于法院、检察院,独立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即当辩护意见发生冲突时,可以自己各自辩护(常见于指定辩护)。并且在制度上存在被告人和律师之间在特定法律条件下的相互“拒绝辩护”的制度。律师的这种独立身份含有离心的成分,要求其行为与维护被告人权益相一致,并且要独立承担违法或者怠惰的责任后果。对律师辩护有效性进行检验从而维护控辩力量的实质平等,恰恰是建立辩护律师与被告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微妙平衡上,并且在对辩护律师有效性检验的时候要求法官施以援手。
二、国内现状:从向前拓展到向后延伸
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在提前辩护和律师援助上尽了很大努力,但是这种努力仍然不尽人意,学者多有述及,在此不赘。甚至2007年10月28日修订2008年6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以下简称“新律师法”)仍聚焦于此,但收效甚微。新律师法为解决“刑辩三难”问题做出了一些新规定。例如,会见时间提前,规定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即可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规定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扩大阅卷范围,在审查起诉阶段,关于律师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的材料,在审判阶段,律师能够阅卷的范围是“与案件有关的所有材料”;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不需要经过相关部门的许可和同意,即可自行调查取证。这些只求表面而不求实效的立法,却引发了另一个学术热点,新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该如何选择适用,如何衔接,以及提出尽快修改刑事诉讼法的连锁反应问题。
一直以来,辩护权向一审后阶段的延伸几乎被忽略了。从下面的司法解释可见一斑。1997年11月20日公布施行了针对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请示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死刑上诉案件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是否应为其指定辩护人问题的批复》,2003年9月23日公布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是否应当为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被告人指定辩护律师问题的答复》。之所以请示这样的问题,不仅仅是普通人就是办案法官对刑事诉讼法第34条关于指定辩护规定的“人民法院”习惯被理解为“一审法院”;并且针对一个“指定辩护”的问题就多次“请示”,在规则适用上的极不自信、犹豫不决反而说明了法官的这种潜意识理解的根深蒂固。对委托辩护的理解同样如此,如1990年11月25日颁布实施了针对广东法院的请示《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是否允许不上诉的被告人委托律师作第二审辩护问题的电话答复》。1998年6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高法解释)第252条再次回答了上述问题,“在第二审程序中,被告人除自行辩护外,还可以继续委托第一审辩护人或者另行委托辩护人辩护。”“共同犯罪案件,只有部分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只就第一审人民法院对部分被告人的判决提出抗诉的,其他同案被告人也可以委托辩护人辩护。”这种一审的律师帮助权试图在二审、再审程序中翻版,总是显得不能对症下药。最高人民法院在司法解释中小心谨慎的用语,留下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即第一审人民法院已判处死刑的被告人提出上诉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为其指定辩护人。”而如抗诉案件要不要指定辩护?未提出上诉的同案死刑被告人可不可以指定辩护?这些问题并不是通过“举重明轻”或者“类推”的方式可以解决,还要“见招拆招”式的请示。
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是否应当为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被告人指定辩护律师问题的答复》,根据刑事诉讼法第34条第2款的规定未成年人被告人被赋予了获得指定辩护权利,由于高法解释第36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15条的规定把刑诉法规定的未成年人获得指定辩护的时间进行了双重限定:“开庭审理时”且“不满18周岁”,导致问题的焦点是二审不开庭审理要不要指定辩护,并进一步导致了以何起点判断“不满18周岁”,答复为“以上诉、抗诉期限届满的第2日该被告人是否已满18周岁为准。”这个问题的背后还存在一个难以自圆其说的问题,“开庭审理时”才指定辩护,有时间准备吗?而获得指定辩护权可能是在审理期限时间段的一个游移不定的点,甚至因为开庭审理时间的拖延而使“未成年人”变成“成年人”丧失获得指定辩护的权利。再反观《六机关规定》第16条对根据刑事诉讼法第40条规定“随时”所作的解释,“对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委托诉讼代理人不应当限定为在‘开庭审判前’。”这种随意解释反映了实践中这样一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法院以开庭审理为界限一方面期望委托代理(或者辩护)“提前”以避免干扰,另一方面期望指定辩护“推后”形成被告人“失权”局面。
正因为实践中律师功能发挥欠佳,学者现在仍然极力呼吁要全面扩大辩护律师对刑事诉讼的参与面。以死刑复核程序为例,一般而言,死刑复核程序是审判监督程序还是审判程序的性质界定会影响程序设计[6]。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02条及高法解释的有关规定,合议庭在复核案件时,一般是秘密的书面审,不传唤当事人和证人,控辩双方无从介入,不受任何当事人和证人影响。死刑复核必须由审判员三人组成合议庭,高级人民法院复核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第一审案件,合议时如果意见不一致,应当少数服从多数,最后由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死刑复核后有关人民法院不同意判处死刑的,可以提审改判。现行的死刑复核程序更像是一种行政报核性质的审判活动。而死刑复核程序却设计成由法院一方在操作,整个过程似乎和其他两方没有关系。因此要变封闭的复核程序为开放的对抗式的程序[7](P.271)。根据高法解释第282条规定,高级人民法院复核或者核准死刑(死刑缓期2年执行)案件,必须提审被告人;对最高人民法院在处理死刑复核案件时是否提审被告人未明确,则不是必要的程序,实践中更多的是采书面审的形式。再根据1992年1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律师参与第二审和死刑复核诉讼活动的几个问题的电话答复》明确认为,“死刑复核程序是一种不同于第一审和第二审的特殊程序。在死刑复核程序中,律师可否参加诉讼活动的问题,法律没有规定,因此不能按照第一审、第二审程序中关于律师参加诉讼的有关规定办理。”
由于死刑案件的特殊性和“一审是基础,二审是关键”的理念结合,2006年9月21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死刑第二审案件开庭审理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突出强调了对死刑第二审案件的“开庭审理”程序,某些条文如合议庭庭前审查内容(第5条)、以及一些通知出庭、法庭调查顺序等对高法解释第251、255条等对二审程序相关规定的重申。其中第6条是二审死刑案件被告人可以委托辩护和获得指定律师辩护,以及拒绝指定辩护而另行委托或者由法院另行指定辩护人的权利的规定。此外,第2条规定了第二审人民法院对死缓被告人上诉案件开庭审理的情形,突出了“被告人或者辩护人提出影响定罪量刑的新证据,需要开庭审理的”情形。第8条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办理死刑上诉、抗诉案件全面审查原则及重点审查的内容,列举了“必要时听取辩护人的意见”。第16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在裁判文书中写明人民检察院的意见、被告人的辩解和辩护人的意见,以及是否采纳的情况并说明理由。这些规定从某种程度上对辩护律师参与死刑二审程序提供了制度保障,对公诉审查、证人出庭等诉讼进程或方式都起到了积极的影响作用。不过,可以明确的是,开庭审理也可以是书面审理,死刑二审程序对开庭审理的强调,也不能改变二审案件“开庭审理”和“书面审理”的常态化结合。例如,上述规定第14条规定在坚持第二审人民法院对死刑上诉、抗诉案件的全面审理原则基础上,明确了开庭审查重点,对开庭审理的内容作了适当的分流,如规定了对无异议的事实、证据和情节不在庭审时调查,对原审判决采纳无异议证据不再举证和质证,对非死刑且未上诉的共犯被告人不再传唤到庭,对事实清楚的非死刑共犯被告人不再庭审时审理,对事实清楚的被告人所犯非死刑他罪不再庭审时审理等等。但是这里只是简化开庭审理的内容并不是对此“置之不理”。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统一行使死刑案件核准权有关问题的决定》,2007年1月1日收回死刑复核权。而其后自2007年2月28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复核死刑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是一个只“重实体结果轻程序内容”的规定。虽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2007年3月9日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严格依法办案确保办理死刑案件质量的意见》重新强调了“全面审查”的要求,但是,被告人和辩护人对死刑复核程序的参与“一如从前”,法律只是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或核准死刑案件,必须提审被告人,提审的目的主要是核实证据,而不是让被告人去进行辩护。当然,这并不禁止被告人利用此机会进行辩护。但是其不具有相应的法律知识,被限制人身自由,以及害怕辩解被人误解为抗拒而不敢辩护的心理,使得这种提审不可能对辩护作用的发挥有多大的实际功效。尤其,死刑复核程序中,现行的法律、司法解释并没有明确规定被告人可以委托、或者被指定辩护人。如果在一审、二审程序中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没有得到相应的保障,在死刑复核程序中被告人得到辩护人辩护更显得重要。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一个出奇的结论是,在具有成文法传统的我国,一审后救济程序中的律师帮助权却通过请示、批复及各次司法解释的颁布这种“法官造法”方式来渐次弥补。即使如此,刑事救济程序中的律师辩护在扩大参与面和加大参与度上仍然不能收到满意效果,尤其是掌握在司法机关手中的司法解释权使其对被告人和辩护律师权利的保障上为防止节外生枝而患得患失。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变换思路,并顺应对抗式诉讼模式的引入,适当考虑设立检验律师辩护有效性的机制呢?
三、双重要件:“行为瑕疵”和“不利后果”
在对抗制国家,虽然从来不排除自行辩护,而律师辩护渐渐在刑事案件中必不可少,而辩护权的保障重点甚至进一步朝确保被追诉人获得平等、有效的律师帮助的方向发展。对律师辩护有效性的检验是一种注重律师职业自律性的特殊责任机制。未受有效律师辩护制度主要是一种以不同于民事责任和行政处罚的诉讼内救济为手段来保障被控人可能因为律师的失误而被错误定罪或者不当程序定罪而获得宣布程序无效或者重新审理的权利救济机制。例如,为了加强死刑案件中的辩护,有人提出,考虑借鉴美国的相关经验,我国可以确立死刑案件中律师有效辩护的标准等建议。
(一)美国标准:“行为瑕疵”和“不利后果”的双重要件
美国最高法院通过一系列的判例确定对被告人获得律师有效帮助的宪法要求应当适用于任何诉讼阶段中的律师行为,只要在这一阶段中贫困的被告人有权获得指定律师的帮助或者非贫困的被告人有权获得聘任律师帮助的宪法性权利(产生于第6修正案或正当程序原则的公平审判要求、或者平等保护的概念)[8](P.603-620)。被定罪的被告人如果认为获得有效律师辩护的权利受到了侵犯,则可以提出无效辩护的申请。1984年合众国诉克罗尼克(United States v.Cronic)案和斯特里克兰诉华盛顿(Strickland v.Washington)案的裁决为解决律师有效帮助的概念提供了一个一般性框架结构,从以前的与容易导致帮助不足的某些特定程序因素有关的标准转向依据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的宪法权利的内在目的,从一些关于律师水平或者努力不足的概括标准转向案件中明确的具体事实和可能的不利后果来评价律师的行为。裁决认为,律师需扮演的角色来自于审判程序的对抗式这一本质,并且只要依其对抗式的模式和目前的判断标准,某一阶段也类似于审判,同样的原则也可以适用于刑事司法程序的其他阶段[8](P.664)。(12)上诉法院通过审查被告人提出的理由和证据,判断无效辩护申请是否成立。如果上诉法院支持被告人的主张,原来的有罪判决将被撤销,原审判法院将重新审判案件或者将被告人无罪释放。关于美国律师协助是否“有效”的标准,(13)1970年前多数法院采过于严格的“正义的笑柄”标准(mockery of justice test)(14)也有称为“徒有其表和名不符实”方式[9];1970年McMann v.Richardson提出“合理胜任”标准(Reasonable competence test);然而在何谓“合理”上学者存在固定化和灵活性两种意见的冲突,联邦法官Bazelon提出的“逐项检查或类别化”标准(Checklist or categorical approach)虽获多数学者支持,而未被大多数法院接受;1973年哥伦比亚特区联邦上诉法院的“的库斯特判决”规定律师履行辩护义务的最低水准是遵守美国法律工作者协会(ABA)对刑事辩护的规定,1976年联邦上诉法院终审的“的库斯特Ⅲ判决”提出新的标准要求律师过失行为情节严重,增加了被告人举证辩护人的不当辩护对审判结果产生了不良影响或者存在影响判决公正的情形[9]。至1984年Strickland v.Washington案,联邦最高法院采用上述联邦上诉法院“的库斯特Ⅲ判决”确立此问题的宪法标准,具体分为三种类别(一种采双重标准的普遍情形以及三种例外情形):
1.辩护人造成的错误,需同时具备“行为瑕疵”(the performance prong or deficiency of representation)和“不利后果”(the prejudice prong)二要件。
2.政府干涉行为,包括:(1)政府对律师——当事人关系的间接侵犯,事实上或解释上政府机关否定被告受律师协助的权利,其中“事实上”指当被告有受律师协助的权利时,政府机关却不指定辩护人,或不准被告选任辩护人;“解释上”指法院虽为被告指定律师,但自指定之时间、情状整体观察,等于实质上否定被告受律师协助的权利[4]。(2)政府机关直接干涉辩护人的重要辩护行为,此种情形,不适用无害错误标准来判定,而被推定为已对被告造成不利的后果,因此要求应当被自动推翻。具体情形如,如被告必须作为辩方第一位证人的法律等于限制辩护人决定被告是否要作证、何时要作证之权,违宪;(15)在被告为证人时,禁止辩护人对被告为主诘问以取得证据,违宪。(16)
3.利益冲突。(17)常见的利益冲突情形是律师担任共同被告人的辩护人或者同时担任两个有利益关系案件的被告人的辩护人。其他情形如在第三者付辩护费时,辩护人应遵从被告之指示或听从付费者之指示;又如对被告不利的检方证人前案所聘律师与被告的辩护人为同一人等。利益冲突的情况可能不仅限于律师由于对同案被告人或第三人承担责任而产生的困境。利益冲突同样可能会产生在被告人和他的辩护律师之间[8](P.677)。综上可见,普遍情形下的双重要件标准在如上的一些例外情形下无需适用。1993年案例(18)中在Strickland案基础上制定了更难推翻定罪的标准,为了表明审判不公,被告人必须证明辩护律师的错误是如此严重,以至于剥夺了他享有一个公正或可信赖的审判权,而不仅仅是审判结果不同。其后,2001年Burdine案(19)确认了打瞌睡的辩护律师因为处于无意识状态而等于没有律师推定审讯存在不公。2002年Cone案(20)辩护律师出于策略的沉默是合理的,2002年Mickens案(21)最高法院认为双重代理仅仅表示“理论上的忠诚分离”,是否属于无效辩护,也需要接受不利后果的检验[10](P.517-518)。这些都说明了以对抗为核心、以公正审判为目标的双重要件标准具有一定基础意义。
(二)英国标准:不当行为和不当结果的因果联系
早在1907英国通过刑事上诉法设立刑事上诉法院时,当时的总检察长就指出,辩护律师的误算和失职将会构成一个有效的上诉理由,“如果被告人律师的辩护行为是失职的,辩护律师没有提出其应该提出的问题,并且对应该举出的证据没有举出,那么所有的这些问题将能够导致上诉法庭对该案件进行审查,并且对有罪判决是否成立作出判决”[11](P.446)。1968年刑事上诉法废刑事上诉法院而在上诉法院增设刑事审判庭,该法第2条(对不服定罪案件上诉的处理)第1款(上诉法院准许或驳回上诉的根据)第(1)、(2)、(3)项规定了对(陪审)定罪不妥当、(法官)法律判断错误、程序重大违法的上诉理由及作出裁判无效的处理。在该规定下,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辩护律师的过失行为可否当作上诉理由和撤销有罪判决的依据、判断律师行为存在过失的具体标准是什么引起了争论。长期以来,刑事上诉院坚持认为辩护律师的过失行为不能成为被告人的有效上诉理由。英国判例法中确立和发展的无效辩护检验标准也从最初的被申诉律师不称职的程度转向主要关注律师行为是否导致了审判上的不公。1989年上诉法院思索尔案(22)判决提出了干涉标准,对已经宣告的有罪判决,如果辩护律师的“不可容忍的不合格的辩护”过失行为在程度上足以导致该判决出现“潜在疑问”或“不公正”,那么可以允许被告人以律师的过失为由提出上诉,也可以据此撤销原判。该判决将刑事诉讼中律师过失行为问题的要点集中到判决的公正性和满意度上。1993年的克林顿案(23)判决一改以往用重大违法事实存在与否来判断律师过失的判断模式,审查律师不当行为对审理和裁决造成的实际影响,根据刑事上诉法第2条第1款第(1)项有关“定罪不妥当”的规定决定是否撤销陪审法院的决定。在该案中,刑事上诉法院认为,辩护律师的错误必须是“对正确的辩护规则的蔑视、或者没有依据正确的辩护规则”、或者违背“所有的理智和机智的提示”从而对判决结果产生影响[11](P.446)。前后两个标准都关注不当行为和不当结果的因果联系,但是,一方面,在不当行为上从前者重大违法扩展到后者善意过失而放宽提起上诉的限制,另一方面,在不当结果上从前者“潜在疑问”走向后者“现实影响”而显得苛刻。上诉法院认为审查辩护内容是否充实和正当,不仅仅是为了追究失职律师的责任,而是为了保障更高层次的问题——审判结果的妥当性和正当性[9]。与此同时,苏格兰的权威性判例是安德森(Anderson)案。(24)1998年,英国颁布了《人权法案》并批准了《欧洲人权公约》,法院对无效辩护的判断标准朝有利于被告人的方向发展进行一定的修正。例如,在艾伦(Allen)案中,(25)刑事上诉法院指出,如果律师的行为导致被告人没有获得公平审判,法院有强制干预的义务,法院在决定以无效辩护为由取消对被告人的定罪时,不应当仅限于辩护律师明显不称职的情形。然而,法庭进行干涉之前总是希望找到“不可容忍的不合格”或者至少是“重大过错”,辩护律师的一个轻率的策略决定并不能成为一个有效的上诉理由。
对抗制国家的未受律师有效辩护制度包括申请的提出、审查以及处理后果等内容。被初审法院定罪的被告人可以在上诉程序中提出无效辩护的申请,无效辩护申请可以针对律师在整个诉讼过程中的不称职行为进行,并不局限于律师在审判阶段的表现,同时被告人应当提出相应的证据以证明其理由的存在。由上诉法院根据相关的证据和判断标准对无效辩护申请进行审查;针对意图在律师自主辩护与被追诉人权利保护之间寻求平衡点的“双重要件”判断标准,批评意见认为,双重检验标准的设置阻碍被告人申请无效辩护的成功。一方面,双重检验标准意味着被告人因此承担双重证明责任,并且两项证明都应当达到优势证据的程度。而一般情况下,仅依靠法庭审判记录的被告人很难避免失败的结局。另一方面,法官在运用判断标准时对律师辩护的有效性有着强烈的推定。除非异乎寻常的失职行为,一般的判断错误或疏忽都不足以构成对法官推定的推翻。所以,他们建议,应当减轻被告人的证明责任,减少法官运用标准时的主观随意性,确立更为明确、具体的无效辩护检验标准。(26)上诉法院认为存在无效辩护时,将撤销对被告人的定罪判决。
就我国来看,在诉讼模式转变后,基于公平审判的要求,不仅应重视被追诉人获得律师辩护的权利,而且要更强调律师辩护效果的有效性。当前的刑事辩护实践存在着律师不积极履行辩护职责,走“花架子”的现象。而现有的法律制度对被追诉人因律师辩护不力而造成的程序权利和实体权利侵害“视而不见”。从我国的刑事上诉制度来看,在审查内容上即使其中包括辩护人辩护意见以及采纳的情况[高法解释第251条第(6)项],这仅针对律师的意见结论法官的采纳情况和法官全面查清事实的责任而并非一审过程中律师的失职行为;在处理结果上也并不存在因为未受有效律师帮助而改变一审判决的情形。因此,从公平审判和保障被告人权利的角度,在立法上确立未受有效律师帮助制度,允许一审被定罪的被告人以无效辩护为由申请撤销原判,或者将案件发回重审。二审法院对经被告人提出的理由和证据进行审查的标准也可以借鉴对抗制国家的检验标准,着眼于公平审判权的保障。
四、制度转向:从同步参与到事后救济
未受有效律师帮助救济制度并不是一个不可改变的定律,救济程序对事实和法律的态度如何定位在对律师参与权的肯定和否定上极为重要,也对未受有效律师帮助的救济制度产生重要影响,这不光因为这种救济本身作为一种救济程序自身的一部分内容,更主要的是其救济程序在承认一审程序对事实认定“一锤定音”的态度下,我们程序侧重点就从对事实的无限追求转向对人权的有效保障。
救济审的全面审查原则要求控辩争斗的延续?辩护是否有效,很显然是以辩护权的存在为基础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曾判决,在许可上诉的上诉程序、(27)人身保护令程序(28)中,因程序本身为法院裁量性质,被告也无受律师协助的宪法权利,“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而不得主张未受有效的律师协助。笔者以为,这还可能因为上述程序只解决法律问题,而不涉及事实问题。当然,定罪后程序中律师帮助权的延伸(29)也同样需要保障其有效性和富有意义,(30)而因为救济程序功能的不甚理想,有效律师帮助权也需要从事后救济性到对律师胜任行为的同步监督的转变,甚至因为Strickland v.Washington所确立的检验标准存在心理学上的定罪必然偏见(inevitability bias)在推翻定罪上的结果不理想,因此提出解决之道是从回溯性个案审查转向前瞻性的体制保障。(31)当然,这还可能存在救济程序与定罪程序为同一律师时的律师“自证其罪”的法律和伦理困境。(32)英国上诉法院也有多个判例强调辩护人过失的上诉救济问题,但是由于尊重陪审团判决的制度传统和诉讼经济上的考虑,以辩护人过失为理由的起诉案件受理率不高。(33)与英美的这种趋势相反,我们的定罪后程序仍有可能被反复拿“事实”来做文章,一直考虑的是律师帮助的参与性问题而未虑及救济性问题。沿袭1979年刑事诉讼法规定,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186条规定了刑事二审的全面审查原则:“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就第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全面审查,不受上诉或者抗诉范围的限制。共同犯罪的案件只有部分被告人上诉的,应当对全案进行审查,一并处理。”在刑事诉讼中权力(司法能动主义)和事实(真实发现主义)结合的“职权探知主义”,一方面对法官的中立、全能的深信不疑导致在实现“治罪”、治理社会和贯彻政策的目标时让法官“包办”有利或不利于被追诉者的各个事项,相应的,国家权力的强势主导又可能对当事人主体性的压抑,在面临程序外“意外收获”的事实直指案件的错误结果时又导致对法官的信任危机;另一方面秉持事实发现的客观标准或者瑕疵被多人多次审查更可能被发现,导致正确的永远是“下一个”而久拖不决和“上面就是对的”而不断寻求复审、反复审查、全面审查。因而,近年来随着人们对传统真实发现主义的怀疑、对当事人自主性的关注,对二审全面审理原则的合理性的质疑此起彼伏。而2006年9月发布的《关于死刑第二审案件开庭审理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坚持二审全面审理死刑上诉、抗诉案件,如前所述,被容许的“庭下书面化审查”极可能流于形式,甚至可视为“两高”默许对双方无争议及法院认为无需重点审查的问题不予审查。因此,有学者提出,根据我国社会转型的渐变性和司法境遇的独特性提出了在法律与事实分开、上诉与抗诉分别、上诉请求和理由结合不同案件类型基础上采取或部分审(如事实上诉、抗诉,法律抗诉),或全面审(法律上诉,死刑案件),或开庭审和书面审结合,法官或能动(对“明显”违背正义的事项职权调查)、或消极(对未上诉共犯不主动审查)的改良式全面审查原则[12]。
与我国全部审查相对应,两大法系普遍采用了以上诉请求为审理对象的部分审查,以其纵向上上下级法院之间分权形成双向制约机制[13](P.91)。如法国,“上诉法院并不始终有权按照其希望的方向对一审法院的判决进行全部(所有部分)改判”,“上诉法官的权力实际上有赖于向其提出之上诉的标的。”[14](P.827)以其横向上的控辩审职能分离,由上诉人为控诉方对作为被告的“一审法院”的指控内容决定着二审审查范围,增强了被告人意志对程序运行的影响力,这也阻止了主要体现法官意志的全面审查的可能性。如美国,被告人“不能告诉上诉法院,整个案子的审判是不公平的,需要整个推翻,而必须明确指出法官在哪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同样,联邦法院在审查被告人的释放令请求时,也有它的审查范围。”[15](P.143)但是,有学者认为,如果被告人的律师帮助权没有得到较充分的保障,上诉审对象限于被告人上诉请求,无异于承认被告人有选择“自杀”的权利。(34)而我们不得不承认,事实和法律的同时审查,诉求内外因素的综合考量(内因如请求范围等,外因如法官职业操守和业务素质/公众朴素正义情感和“青天”情结),因为程序对一审的翻版和重复,在二审程序中的律师辩护权问题还是要特别强调辩护律师的参与权,尤其是事实问题的调查,在庭审中以直接言词的方式进行才是最有效的,为了查明真相确保二审事实认定能力、发挥二审监督与纠错功能,我们必须把控辩方争斗的积极性从一审延续到二审。
不过,我们在重复一审程序,在寻求律师广泛参与上“欲罢不能”的同时,更要在检验一审律师辩护的有效性上下功夫。我们承认我国一审法院,尤其是包含陪审员组成的合议庭,与主要依赖于经验和常识的英美法系陪审团、大陆法系国家等公民参与诉讼机制一样对事实判断的“一锤定音”的功效,而对事实不清的问题发回重审的制度也暗含有一审法院更接近事实的潜台词,我们要借鉴美国只能对法律问题上诉的制度,承认一审对事实的判断具有最终效力,而不是由不同级别法院通过反复再审而搞出不同的事实版本;并且我们不是通过一定的程序来达成对不利结果的认同,而是从反面以确认程序瑕疵来推翻不利结果(包括事实结果,如定罪)而直接给予受害者以程序利益。当然我们并不否弃扩大辩护律师在各种救济程序中的参与权,这个参与权也需要监控和审查,并且在程序之内得以解决而防止过分拖延。这样在救济程序中就存在着对定罪程序中律师有效帮助的后续审查和对救济程序本身中律师有效帮助的同步审查。
五、机制衔接:外部审查机制与内部执业自律机制
有学者分析认为我国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权利有限,举步维艰,司法上有法不依、违法不究现象突出导致律师辩护无法落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率较低,这些问题比引入无效辩护制度更为迫切,另外,我国刑事诉讼模式本质上仍然属于职权主义模式而更不具备引入无效辩护的条件[16]。这些说法有其道理,但有限的律师刑事辩护率更要保证其有效性。当然,未受有效律师帮助救济制度对被告人权利保障从防止公权力滥用转向法官施以援手来鞭策律师的有效作为,这可能会产生两种问题,一是律师不接受委托完全不参与刑事辩护从而不存在是否有效的问题;二是被告人的权利救济必须建立在律师被追究责任的制度基础上,虽然未受有效律师帮助救济制度意味着对律师的责任从程序之外转向程序之内,但是如果没有外在的责任追究,律师就不承认程序之内所犯的错误。下面笔者着重从我们所呼吁完善的责任豁免制度和律师惩戒制度与被告人受有效律师帮助权相互关联角度进行探讨。
(一)殊途同归的效果:责任豁免特权与“被告人受有效律师帮助权”
律师维权与责任同被告人未受有效律师帮助权救济是一对矛盾吗?我们在救济程序中采取鞭策律师而放松对司法权力的控制的检验律师辩护有效性的未受有效律师协助的救济制度设计,作为律师责任的加码,可能会使本来因为国家机关的偏见(如“替坏人说话”)、社会大众的误会、公检法机关徇私报复等而艰难前行的律师职业权利保障更是“雪上加霜”,成为被称为“律师管制法”[17]的律师法之外的又一个紧箍咒,助长中国律师“不敢替‘刑事犯罪嫌疑人’辩护”[18]的现象。这种担心并非多余,但是并不意味着对律师放松“警惕”,我们在加强律师执业保障的同时,也要加强内部自律。在一般意义上,例如称职代理,要求律师必须具备进行代理所需要的法律知识和技能,并为代理做必要的调查和准备;勤勉服务,要求在代理过程中勤奋工作,讲究效率;遵从委托人意思,不得损害委托人利益,不得从事利益冲突的代理;以及收费合理,保守秘密,等等[19]。而“称职代理”、“勤勉服务”,“不得从事利益冲突的代理”,这些都是律师提供有效法律帮助所要求的。
为了使律师尽职,应该为律师提供更多的执业特权。两种执业特权最为突出,一是律师作证豁免权,这在于鼓励被指控人全部地、坦率地提供案情,以律师保守职业秘密原则,维护律师与被指控人之间的信任关系,保障律师从被指控人处全面获取信息,而不“出卖朋友”。二是律师责任豁免权,在于保障律师在毫无保留和顾忌的情况下为委托人提供法律意见、展开辩论,独立行使辩护权,而不“把自己搭进去”。然而,有限的律师执业特权使我国律师刑事辩护只能是保守的、被动的、消极的辩护。
首先,我国律师作为特殊行业执业人员的职业道德要求(刑诉法第38条),和作为普通公民的一员举报犯罪事实或犯罪嫌疑人的义务(刑诉法)第48条“作证义务”;第84条“报案或举报”;刑法第311条“拒绝提供间谍犯罪证据罪”,第349条规定的(窝藏、转移、)隐瞒毒品、毒赃罪等极大的冲击着他们拥有的保守职业秘密的优先权利与义务。虽然新律师法取消了律师行为禁止和律师责任承担的“隐瞒事实”的相关规定,并在第38条关于律师保密义务的原则规定上,明确“律师对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委托人和其他人不愿泄露的情况和信息,应当予以保密。”当然,又规定了例外情形,“委托人或者其他人准备或者正在实施的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其他严重危害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犯罪事实和信息除外。”而根据《基本原则》第22条规定:各国政府应确认和尊重律师及其委托人之间在其专业关系内的所有联系和磋商均属保密性的。据此,应赋予律师的作证豁免权,任何人不能强迫律师作证证明其委托人有罪,与职业秘密有关的书信和文件免受检查和扣押,当事人和律师的交谈不得被窃听。
其次,与很多国家和地区都赋予辩护律师在法庭上的刑事责任豁免权以免“后顾之忧”相比,我国相关法律却造就了追究律师刑事责任的制度诱因。在我国相较于刑法第307条“妨害作证罪”,第306条把刑事诉讼中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作为特殊主体来规定,这种“特别规定”确实有“醒人耳目”之感,甚至被称为悬在律师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而“伪证罪”、“包庇罪”与第306条的“法条竞合”容易导致律师“一种行为多种罪名”。该条的罪状描述内容宽泛,语词模糊(如“帮助”、“引诱”),有人将此罪名分解为三个子罪名(毁灭证据罪、伪造证据罪和妨害证据罪)、四个方面客观行为,认为其几乎囊括了刑事诉讼过程中的每一环节与任一阶段的逐个细节[20]。在具体操作上,警检机关可能导致把律师执业中工作上的错误或失误或违纪行为“上纲上线”认定为犯罪,尤其是证人“见风使舵”随意改变证词,导致证人把伪证罪推给律师。新律师法第37条规定了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尤为突出的变化是:(1)增加了律师庭上言论的豁免权,规定“律师在法庭上发表的代理、辩护意见不受法律追究。但是,发表危害国家安全、恶意诽谤他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言论除外。”从中可见这也是有限制的责任豁免权,甚至有学者分析说,这难免会把引入当事人主义情况下辩护中的偏颇和碰撞界定为“恶意诽谤他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情况,也有难免出现把律师在法庭辩护中对国家有关政策的评价拔高到“发表危害国家安全言论”上来。(2)突出了强制措施中的程序保障,规定“律师在参与诉讼活动中因涉嫌犯罪被依法拘留、逮捕的,拘留、逮捕机关应当在拘留、逮捕实施后的24小时内通知该律师的家属、所在的律师事务所以及所属的律师协会。”《基本原则》第16条规定:各国政府应确保律师能够履行其所有职责而不受恫吓、妨碍或者不适当的干涉;不会有与其按照公认的专业职责、准则和道德规范所采取的任何行动而受到起诉或者行政、经济或者其他制裁。第20条规定:律师对于其书面或口头辩护时所发表的有关言论或作为职责任务出现于某一法院、法庭或其他法律或行政当局之前所发表的有关言论,应享有民事和刑事豁免权。因此,赋予律师在履行职务时享有相应的民事和刑事豁免权是一种潮流。不过,律师的作证豁免和责任豁免的消极权利,并不允许其在刑事诉讼中,违背律师职业行为规范和执业纪律的行为。虽然赋予其责任豁免特权以免后顾之忧,恰恰与“被告人受有效律师帮助权”对律师充分、全面的表达辩护意见的要求不谋而合,但是这不是默许其为求胜诉而不择手段。
(二)异曲同工的依据:律师惩戒原因与被告人未受有效律师辩护救济标准
美国Strickland判决没有建立实际性的标准来衡量辩护的有效性,然而,由于美国法律工作者协会制定的行为规范符合宪法第6修正案的要求,因而得到了法院和社会的认可,并已成为检验律师行为和辩护质量的现实标准。在管理和监督律师行为方面,美国的律师行业也从原有的外部干涉、硬性的审查机制逐步转化为通过加强执业律师的伦理道德观念和树立符合宪法要求的执业责任等内部调控来发现问题、解决矛盾,从而建立起提高律师执业水准和自律性方向发展的灵活体制。因为我们的“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我们不轻易承认被告人享有针对律师过失寻求救济的程序权利,除非抓住律师的把柄,这个把柄必须是对律师某种确定的行政处罚或者民事、刑事责任。从规范的内容上看,我国律师行政惩戒的原因也可以成为刑事诉讼救济程序中被告人未受有效律师辩护救济的依据。
1.辩护人造成错误的“行为瑕疵”要件。如新律师法第48条关于律师惩戒行为的第2项:接受委托后,无正当理由,拒绝辩护或者代理,不按时出庭参加诉讼或者仲裁的;以及2004年《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8条规定的“律师惩戒行为”第9~11项:接受委托后,不认真履行职责,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接受委托后,无正当理由不向委托人提供约定的法律服务的;超越委托权限,从事与委托代理的法律事务无关的活动的。
2.利益冲突。我国法律的明确规定几乎使得“共通辩护”在我国没有生存的余地,也使得法官在排除“利益冲突”代理上的司法能动成为不必要。新律师法第47条关于律师惩戒行为的第1、3项规定的“同时多所执业”、“同案双方代理”或者代理与本人及其近亲属有利益冲突的法律事务的;第48条第3款,利用提供法律服务的便利牟取当事人争议的权益的;以及《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8条规定的律师惩戒行为第1~4项:同时在律师事务所和其他法律服务机构执业的;在同一案件中,同时为委托人及与委托人有利益冲突的第三人代理、辩护的;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有利害关系的案件中,分别为有利益冲突的当事人代理、辩护的;担任法律顾问期间,为法律顾问单位的对方当事人或者有其他利益冲突的当事人代理、辩护的。
3.政府干涉行为,主要发生在指定辩护的场合,在我国更多的体现为“解释”上的未受有效法律援助,例如迟延指定辩护问题或者如前所述至开庭审理时间拖延而不需要指定。在法庭上政府机关干涉辩护人的重要辩护行为的情形可能屡见不鲜而无从认定。然而,值得警醒的是,由于我国目前对违法违纪的律师惩戒不力的突出问题几乎使确立被告人未受有效律师协助的救济制度丧失根基。与美国的从程序外干涉向律师执业内部自律转变不同,我们的关注点,从被告人因为律师过失而对审判造成的实际不利影响出发比在辩护律师到底有无违法违纪上纠缠不清要更适于保障被告人的救济权利,虽然这在某种程度上会产生对被告人寻求救济课以对律师不当行为和造成审判上不利后果的双重举证责任的后果。
总之,在刑事救济程序中的被告人未受有效律师帮助的权利救济在我国目前还是一片空白。与其在传统的扩大律师参与面上打转,不如跳脱圈外,把保障被告人有效辩护权的制度设计中心从被告人对抗国家的消极辩护权利转移到积极寻求国家保障有效辩护,从扩大律师的参与面转移到检验律师辩护有效性,从向前的侦查起诉阶段的提前辩护延伸到向后的二审、再审、死刑复核等救济程序,从单纯律师程序之外责任转移到侧重律师程序之内责任。其目的并不是为了鞭策律师,松绑国家机关,而是为了更好的实现公平审判,保障被告人的人权。在承认一审案件审理对事实的比较大的事实确定力的基础上,明列未受有效律师辩护的具体情形如律师的行为、政府的干预和利益冲突的情形,并且确立被告人的举证责任,并做好与律师职业权利保障、律师职业特权和律师责任惩戒制度的衔接。
注释:
①Strickland v.Washington,466 U.S.668 (1984).
②肖宏开:“国际法视角下的公平审判权”,载http://oldfyb.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php.id=96693,访问日期:2008年7月30日。
③Powell v.Alabama,287 U.S.45(1932).
④Johnson v.Zerbst,304 U.S.458 (1938).
⑤Bettts v.Brady,316 U.S.455(1942).
⑥Gideon v.Wainwright,372 U.S.335 (1963).
⑦McMann v.Riabardson,397 U.S.759 (1970).
⑧Peter W.Tague,Faulty Adversarial Performance by Criminal Defenders in the Crown Court; King's College Law Journal,12 K.C.L.J.(2001) 137,at137.
⑨Anne M.Voigts,Narrowing the Eye of the Needle:Procedural Default,Habeas Reform,and Claims of Ineffective Assistance of Counsel,99 Colum.L.Rev.1103,at 1118 (1999).
⑩同上。
(11)1980年前美国大部分法院判决对自选律师不得主张未受有效律师协助,其理由:一、代理人理论;二、欠缺政府行为理论。1980年Cuyer v.Sullivan[446 U.S.335(1980)]案认为,审判本身即为政府行为,自选辩护和指定辩护皆可主张。参见王兆鹏:“受有效律师协助的权利——以美国法为参考”,载《月旦法学》2005年第8期。
(12)Georgetown Law Journal Association,Thirty Second Annual Review of Criminal Procedure,III. Trial:Right to Counsel,91 Geo.L.J.455,478-480 (May 2003).
(13)Yale Kamisar,Wayne R.LaFave,Jerold H.Israel,Nancy J.King.Mordern Criminal Procedure,9th ed.West Group1999.p.1152.
(14)Devid Bazelon,The Defective Assistance of Counsel,42 U.CIN.L.Rev.1,28 (1973).
(15)Brooks v.Tennessee,406 U.S.605(1972).
(16)Ferguson v.Georgia,365 U.S.570(1961).
(17)Cuyler v.Sullivan,446 U.S.335,348(1980).
(18)Lockhart v.Fretwell,506U.S.364(1993).
(19)Burdine v.Johnson,No.99 -21034(5th Cir.2001).
(20)Bell v.Cone,No.01-400(2002).
(21)Mickens v.Taylor,No.00-9285 (2002).
(22)R v.Ensor,[1989] 2 All ER586.
(23)R v.Clinton,[1993] 1WLR 1181; 2 All ER998,1004.
(24)Anderson v.H.M.Advocate,1996 S.L.T.155.
(25)R.v.Allen,2001 WL 753441.
(26)Jeffery Levinson,Don't Let Sleeping Lawyers Lie:Raising the Standard for Effective Assistance of Counsel,38 Am.Crim.L.Rev.147,153(2001) .
(27)Wainwright v.Torna,455 U.S.586(1982).
(28)Pennsylvania v,Finley 481 U.S.551 (1987).
(29)Eric M.Freedman,Fewer Risks,More Benefits:What Governments Gain by Acknowledging the Right to Competent Counsel on State Post-Conviction Review in Capital Cases.4 Ohio State Journal of Criminal Law.183 (2006-2007).
(30)Celestine Richards McConville,The Right to Effective Assistance of Capital Post-Conviction Counsel:Constitutional Implications of Statutory Grants of Capital Counsel,Vol.2003,No.1.Wisconsin Law Review.31,108 (2003).
(31)Stephanos Bibas,The Psychology of Hindsight and After-the-Fact Review of Ineffective Assistance of Counsel.2004 Utah Law Review,March 2004.
(32)Anne M.Voigts,Narrowing the Eye of the Needle:Procedural Default,Habeas Reform,and Claims of Ineffective Assistance of Counsel,99 Colum.L.Rev.1103,at 1118 (1999).
(33)Peter W.Tague,Faulty Adversarial Performance by Criminal Defenders in the Crown Court; King's College Law Journal,12 K.C.L.J.(2001) 137,at137.
(34)Celestine Richards McConville,The Right to Effective Assistance of Capital Post-Conviction Counsel:Constitutional Implications of Statutory Grants of Capital Counsel,Vol.2003,No.1.Wisconsin Law Review.31,108 (2003).
标签:法律论文; 庭审论文; 律师论文; 律师职业发展论文; 刑事律师论文; 诉讼参与人论文; 上诉期限论文; 辩护人论文; 法院论文; 死刑复核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