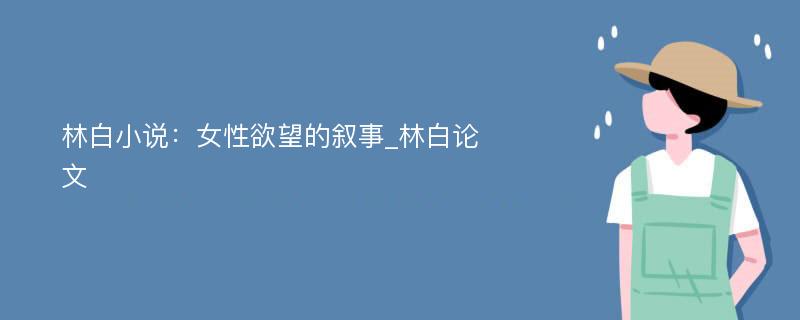
林白小说:女性欲望的叙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欲望论文,女性论文,林白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九十年代女性写作中,林白小说将具有不可忽略的意义,这就是林白小说对于女性欲望的叙事:女性欲望的主题、女性欲望的情节结构方式、女性欲望式流转语言,一个“女性欲望横流的世界”,迥异传统写作对女性欲望的取消,也不同于一般女性写作欲望的空缺或遮遮掩掩流露,在林白小说中,女性写作以其欲望本体的形式呈现空前自由。将林白小说置于中国女性写作话语成长序列,中国女性文学从男性话语场独立而出的绰约姿态就凸现出来。
一
八十年代张浩的女性写作强调女人是人而不是“性”,“女人”作为中心价值其社会价值成为作者表达重心,而在社会理想这一悬置的光环之下,女性实现社会价值的艰难无疑令张浩分裂和痛苦,自称“痛苦的理想主义者”的张洁,于是借助了理想的爱情来调和这种矛盾:钟雨对于白发老干部的爱(《爱,是不能忘记的》)、叶知秋对于改革者部长的钟情(《沉重的翅膀》)、甚至荆华在探讨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时不眩目却内在执著的情爱理想信念,写作的张洁与作品中女性陷入同一探求妇女解放层面,在把女性的愿望与社会理想重叠、女性话语与男性中心话语重合的过程中,不知不觉使女性写作独立话语功能受到消削。张洁小说最终完成了女性价值反叛,而这一反叛原是社会特定历史所需,对于“人”的强调和对于“性”的回避,使张洁在叙述策略上只能是男性话语的翻版,小说刚劲粗砺的风格正是男性话语复仿。张洁小说体现出八十年女性写作在男性话语引力场中艰难跋涉的具体情形。这一情形意味着女性写作所承担的妇女解放实践重荷自“五四”丁玲以来,尚未从中国女性写作中清除。如果说丁玲后来以她的生活方式代替了写作的社会理想,张洁则在社会理想失落之后,不得不蹈入愤怒和诅咒。张洁的《上火》和《红蘑菇》,以其主题对于社会理想的彻底解构和对妇女解放前景“黑夜感觉”,宣告了八十年代女性写作回避女性欲望的困窘。因为从根本上说,女性写作终要实现它在写作上的话语意义。无疑妇女解放探求是它的自始至终使命,但这一使命不是现实功利的,而应从文化的久远角度来评判。女性写作只有获得话语功能独立,写作的女性与作品中女性命运拉开距离,女性写作的文化和美学价值获得保证,才有可能为妇女的特殊存在作证。不仅是女性的觉醒,更是话语权力的觉醒。女性写作要反叛的是女性曾被讲述的命运(而不仅是特定社会时期的命运),为求得经验世界中的真正女性(而不仅是理想中女性),女性写作要求重述女性自身,无论是孤独、恐怖、绝望、疯狂、失败、死亡甚至彻底物化,对女性经验的强调,界入真正妇女经验的深广度及其获取对应话语形式,可以说是衡量女性写作成熟与否的标志。
九十年代经济扩张和中心旁落的话语现实,无疑带给了中国女性写作机遇。女性写作朝妇女经验挺进而建立自身独立美学风貌的写作事实已经建立。(也可以说,女性写作已迈向独立的女性文学诗学阶段。)残雪先声夺人的个人化女性叙述对于生存合理质疑,不依附男性话语而凸现女性灵魂囚禁与探险的强烈个性;陈染坚持“自画像”式女性叙事,在知识女性的“私人生活”深刻点上揭示解放的限度及前途;蒋子丹的“游戏诡计”隐藏着女性智性建设的努力,徐坤以无负荷的叙述审度文化现状,呈现女性解放与建设同在姿势,等等,“如果我们把妇女作品看成是对社会文学现实的有意识的反应”,当代女性写作的美学和文化学意义即自行兑现。而在这一切之中,林白的女性欲望的叙事,确乎是九十年代女性写作对于八十年代女性写作一次反叛性深化:因为确切地说,妇女经验中基本深刻悠久现实的一种,便是对性/欲望的体验,一切的妇女经验背根植于此,这一体验在经济和商业的搅荡中变得更为敏感、裸触——这一体验在八十年代张洁式女性写作中出于对理想的归附曾被一再压抑、延宕,已成为“女性话语期待已久的表达。”[②]诚然八十年代王安忆的“三恋”(《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已然涉入了女性欲望领域,但将性欲移置于“荒山”、“锦绣谷”或“小城”的狭小天地,仍然是对妇女经验现实的畏惧和逃避。这里写作女性对于女性欲望的“压缩式”探索,隐喻了女性写作对自身、对世界别一种体验和表现的可能。事实上正是如此,林白小说最奇异的风景便是推开周遭压抑而流布四漫的女性欲望之水。其间映照和透渗真实深刻现实妇女经验及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所谓女性欲望的叙事,便是从女性的潜意识、女性的愿望和要求,寻求“女性自己的故事”,这是生命的欲望与创造的欲望、性的欲望与话语权力的欲望,说到底是作为女人主体欲望的种种达成或未达成“故事”。这些“故事”过去是今天仍是女性隐秘历史经验,为时间和文化所遮蔽,在女性自身的“容器”中积累、沉默,它们的沉默、持续和恒久恰恰意味着女性愿望和欲求的深度、多元及绵亘。林白小说因返回“女性之躯”源泉,当然地取消了男性主体欲望故事的通常模式“开端——高潮——结局”,(这曾是张洁一代女性写作不得不模仿的模式。)林白小说执著于细节,不断重叙女性幻想,以打破男性描写程式的反复抵达方式,在深入女性欲望层的同时刻划女性文化印记。可以说,如倾覆桌面的流水,林白小说语言和情节(毋宁说是情绪)的自然流畅状态,是对于传统小说章法结构的对立。“女性欲望的叙事”突出向来在男性本文中被取消、剥夺和扭曲的“女性欲望”,叙写女性欲望的绚丽繁复、强烈锋锐、神奇诡秘和咄咄逼人。写作的女性以观审和评述姿态面对女性历史和现实,揭示女性存在真相。在此角度,林白的小说象一个宣谕,从最初的《我要你为人所知》写被流产女婴子宫中生命欲求,《日午》写女性被剥夺话语权而沉默、死亡,到最近引起热烈争论的长篇《一个人的战争》叙写女性自我成长艰难旅程,表现出当代女性写作努力寻求建立于“女性之躯”妇女本文,从“女性欲望”直接提取女性话语,真正达成妇女的自我了解和表达的认真实践、语言企图。置于当代女性写作序列看,林白小说可以说是一次女性话语独立的“成人礼”。但本文并不想仅从宏观角度为林白小说定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做只是为了更方便地分析林白小说的艺术世界——在那些“女性欲望”横流的、却又是精致封闭的艺术世界,林白究竟寄寓着怎样的当代女性生存体验呢?
二
当林白把她的小说创作看成是“一个女人对镜独坐”[③],林白小说的个人话语性质、林白小说人物形象的自我幻像特征,甚至林白小说空间的梦幻化,已经一目了然。而她的自传散文《流水林白》,更可以看作是她全部小说的母体:这篇档案式短小散文,记载了一个女人由小而大、由南方而北方、由无名而奋斗成名的全部事实,正是这些事实,衍化生成了林白目前为止所有小说“故事”及人物。无疑地,林白正是从一个女人的个体生存经验出发去表达一种女人的集体生存经验,而这一经验的内核和汇通便是“女性欲望”:生命和生存双在的欲望,过去和现时并存的欲望。对于一位从南国突入北方,身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北京的女作家来说,个人的不无代表意义的当代生存体验成为她推想妇女经验的源原,也许可以这么说,林白小说是一部商业时代真正的女性寓言。
商业经济加深着人的异化尤其是妇女的异化,城市的挤压既为女性欲望提供出路又导致女性欲望极端物化。不得不投入城市又不能不坚持对异化和物化的拒斥,当代女性经历着妇女解放实质性的尴尬。在林白看来,面临这种尴尬无处可逃,也不可能依赖任何外在的救世主,女性的自救就是唯一前景。表面上看,林白小说并无字面激烈的女权宣言,也没有堪称“妇女参照”的女性形象,但是贯穿林白小说的内在力量可以说正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女性自救精神;来自女性欲望的生命生存、发展欲求和冲动。一方面深刻地透视妇女的现实尴尬,表现女性自救乃“致命的飞翔”,另方面借助叙述主体的话语自觉,塑造充满女性美的女性欲望形象,为女性欲望进取制造依据,并将美的力量与欲望的力量相统一,企图通过“一个人的战争”完成女性的自我战胜从而战胜世界。因着双重的主旨渗透,林白小说流水般语言具有击石穿岩力度。“语言具有非常多的可能性,它能够创造无数的现实,一些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经由语言诞生,语言赋予它高大或细小的身躯,它们细微的茸毛在语言的枝叉上挺立,既然它以如此清晰可感的面目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我们有什么理由怀疑它的真实性呢?”[④],妇女作家对于语言的高度自觉,也就是对于妇女欲求、女性欲望的独立性的高度自在。林白小说首要的艺术价值,就在于语言表现当代妇女经验时,呈现出其女性欲望本体形态。
《日午》是林白第一篇公开发表的短篇小说,收入长篇《青苔》时,被作家改写为《进入沙街:日午》。事实上《日午》正是林白暗示读者进入她的虚构艺术世界“沙街”的钥匙。《日午》的主题是呼唤女性话语,它通过对《白毛女》演出与现实中妇女无法“发言”、无权“主演”的强烈对比,审思当代话语舞台上妇女的真实处境,这是令人震动的“被动”和沉默处境。林白一登上文坛,即以《日午》呼唤妇女自己的声音,即表现出写作女性的话语自觉。而“沙街”系列小说,便是林白创造的“女性之声”。“沙街”表面上以作家的故乡为背景,但这个故乡是“女性世界”,确切的说,是作家精神之乡,女性的精神故乡。“沙街”上生活着全是美丽动人、欲望灼灼、命运叵测的女人,邵若玉、姚琼、以狗为伴的神秘女人、饱经沧桑的祖母,等等,林白写极她们的气质和美貌,不吝啬使用“月光”来形容她们神秘的美。正是月光/夜晚/欲望,林白把女性美与女性欲望内在结构意象化了。女性美的毁灭说到底是女性欲望的被剥夺和摧毁。不可压抑的女性欲望象夜晚当空的月亮,是女性的美和女性沉默的言说,女性话语之泉。林白总是用回忆的视点来写“沙街”,意在对女性隐秘、苦难经验反思和现实中女性欲望重新唤醒。象《同心爱者不能分手》的写法:
“那时候在沙街暗黄色的木楼和土灰色的砖房前,像开花似地出现的这个女人,她的脸像她身上穿的月白色绸衣一样白,闪亮的黑绸阳伞在她的头顶反射出幽蓝刺眼的斜光,随着她的腰身一扭一扭,黑绸阳伞左一闪右一闪,妖冶而动人,那个月白色绸衣的女人在阳伞下只露出小半的脸,下巴像一瓣丰富的玉兰花。20年来我极力回避这个形象,就像我每次路过太平间都极力不扭头看那扇门一样。”
“那时候”与20年来的“现在”是一种对应,叙述的双重意味就在其中。穿月白绸衣的女人是压抑的,最后死亡的女性欲望的化身。这正是“20年来我极力回避”的真相。但留在“20年来”我记忆中的东西,恰恰是一种被压抑的女性欲望神秘穿透力,有如死亡,使生者无法不正视、不惊悚。正如小说结尾所写,这个女人焚火而亡,火声中升起奇怪的歌声。小说强调“我”之“想起”那个女人,是“我”的“现时”——与天秤恋爱,女性个人欲望苏生时,与“那时候”“那女人”发生了下意识汇通,“而“我”通过对下意识回忆清理,发现“爱比死残酷”,产生了新的女性欲望意识。叙述的时间对比呼应,女性的欲望唤醒欲望意识,女性话语由此涌现。《子弹穿过苹果》的内在结构与《同心爱者不能分手》一样,也是在过去与“现在”的比照中领悟女性欲望,但这里传达的不是女性欲望受抑后的强大自虐性,而是女性欲望在释放中的穿透性。小说将男性定型化,(每天做着煮蓖麻油这同一件事。)而使围绕他的女人蓼有如烟雾变幻不定,女性欲望的试探、进退、爱恨纠织,自我迷恋,通过南疆风光的衬照显得有形有色,(需要指出,林白对于南疆风光的迷恋,正如她对于女性欲望欣赏,这一温暖热烈色彩与氛围是林白小说女性欲望意象和布景之一。这是林白对于女性欲望释放而不是压抑的情感和语言态度。构成呼应的,则往往是她用月亮/夜晚表现女性欲望受阻、被拒制的绝望。)“我”不断回忆蓼的过程,正是“我”在异性爱中发现同性文化光谱的过程,也就是女性欲望内在映证、女性话语自我涌现过程。又如《回廊之椅》极写女性之间欲望的温馨强大,以高出异性爱的吸引力“引导”“我”目睹“回廊之椅”女性欲望·生命存在的狭小却方式优雅。这篇小说把女性话语置于革命·时代话语之上,呈现出“五四”以来女性写作未曾有过的新颖姿态。
林白“沙街”世界的丰富多彩是女性欲望话语丰富多彩的一个象征。抽空“女性欲望”,“沙街”即不复存在。在林白看来,女性精神世界乃建于“女性欲望”之乡。在此意义上,“沙街”不过是“女性欲望”的表演舞台,是林白设置的语言宫殿。真正的“女性欲望”来自商业时代、来自远离边缘沙街的现代生活中心地带,过去时代女性欲望的沉默无声和蠢蠢蠕动,因着今天女性欲望的激话才复现。然而过去和复现都并不是传达当下女性欲望的真实“故事”,欲望的本质不是压抑,也不仅是释放,它要求生求生长、创造和飞翔。于是我们看到林白小说中与“沙街”南国对应的另一个艺术世界“北京”。严格来说,“北京”才是林白小说“女性欲望叙事”中真正的叙写地点,但是作家直到表达“创造”性故事时,“北京”才取代“沙街”成为人物场所。(必要时,“北京”就不断与“沙街”呼应。)正是在“北京”,女性的种种欲望获得调动,(反之,受到压抑和扼制。这正是被转移到“沙街”的理由。)女性形象不是以“月光”而是以现实生活中的“真面目”出现。
和“沙街”中女性形象以死亡终结相反,在“北京”女性们“守望空心岁月”,呈现欲望饱满而在无物之阵出击和等待的无奈。应当说,正是“北京”寄托着林白女性主义的热情,“北京故事”的核心是反“性政治”,是女性欲望对于被压抑、被控制的直接抵拒。《致命的飞翔》是“北京”故事最动人心魄的一则。在这里两性的交锋由社会生活领域而性欲,由历史而现实,既在具体生活中展开,也在幻想中进行。女性欲望的浓密粘稠、热烈繁复,通过反控制、反压抑和主体出击,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绝对姿态,即“致命的”“飞翔”的姿态。无论是北诺、李莴、红圆的小凳,还是那把女性幻想中举起的利刀,都堪称当代女性写作中极端的形象:它们在叙述者血色黄昏般的情绪中组合在一起,让人过目难忘。这篇小说采用林白一贯的欲望联想构思,但又不同于“沙街”小说的那些幽深神秘领悟,而是把两个互不相识的现实生活女人(北诺与李莴)在两个不同时空的性体验勾合在一起,以极其明晰的“我们”复数点破女性共同的性命运和相同的性反抗。“我们体内的汁液使我们的身体闪闪发亮。”“我们”具有召醒现实女性的叙述企图。人们不能不意识到两个女人的故事其实就是一个女人的故事就是正在进行着的现实女性故事。“在这个时代里我们丧失了家园,肉体就是我们的家园。”不可能有其他的寄托和幻想,女性的生存既具体现实又悲惨而女性的反抗就在生存中展开。“指望一切性的翻身是愚蠢的,我们没有政党和军队,所以必须利用他们。”没有比这种明智的宣言更具备商业特性的,而林白的出格并不在她对西方女权理论的搬用,却在于她大胆地揭示这种女性境遇尴尬,这同样也是男性的尴尬。问题是,这种尴尬对于女性而言,却还是“进步”的结果——《致命的飞翔》之所以不肤浅,就在于北诺和李莴身后还有另一个女人、另一些女人、另一个时代的女人,她或她们在性的压迫中只能选择踏上红圆木凳,结束悲惨的命运,北诺给红圆木凳罩上凳罩,就是林白为另一个时代拉上幕布,女性的欲望终于要延伸,实物利用使北诺、李莴有可能危中求安。这种“进步”带着林白宿命的历史感。“刀”之成为“致命的飞翔”,成为女性性幻想胜利的象征,可以说是林白女性写作对于男性统治的话语颠覆和个人渲泄。
与《致命的飞翔》相比,《守望空心岁月》侧重于女性欲望细致入微刻画,传达出作家对于女性欲望多重与危险的某种审视与忧虑,其中更多现实生活信息传达。
林白已然把女性欲望视为女性写作之根,在“守望空心岁月”的无奈现实中,写作/欲望成为最后踞点——林白以无奈却坚持的女性写作塑造女性的“北京”/这个语言中的“北京”,也是现实女性、特别是写作女性的“北京”,在“北京”女性话语既获得独立也陷入了无物之阵。
迄今为止林白最出色的小说是长篇《一个人的战争》。《一个人的战争》几乎浓聚了“沙街”和“北京”两个艺术世界的全部人物。这种互文写作虽然影响阅读,但并不构成对林白写作的损伤,相反,形象地再现了林白女性写作的“放大”技巧。那些个人化的经验上升为女性集体经验并为艺术形式所保留,体现了女性写作退回身体又从身体出发的特征。《一个人的战争》体现出作家对于个人化女性经验世界营构的匠心。小说以女性主体成长为核心,编织出女性与自身、女性与世界、女性与男性、女性与女性之间的网状关系,这一网状关系疏密以女性经验的变化为轴心。这里没有一般自传体小说的重大社会环境叙写,没有重大社会事件界入,也没有一般自传体小说的成长楷模范式,有的只是女性的自我认识、自我感知、自我欲求、自我选择,小说再现出处于社会政治边缘的女性的成长史,是一部经验积累、自我积累和自我调整,认识自身而后认识世界的“特殊存在”史。小说主人公林多米自幼丧父,从医的母亲经常不在身边,因此可以说是在“父权”缺席的空隙成长起来的“主体”,一个真正的自生自长女性主体。女性欲望的方方面面在《一个人的战争》中得到了全面、深刻而细致的刻划,身为女孩的自我身体认识,对于生育和死亡的天然关注和恐惧,对于自然外物的探求,对于自我实现的追求,对于荣誉和未知世界的兴趣,对于爱的渴求,总之,一个女人,也就是一个人,她的希望、她的绝望、她的兴奋、她的悲哀、她的爱、她的恨,她的生命就是她的欲求的总和。无疑地,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还没有出现过类似地叙写女性成长、女性欲望历史的作品。《一个人的战争》不是一般反道德意义的女性写作,从根本上就是绝对的女性本文,它强调一个人的战争无所谓胜败,一个人的欲望就是战争就是生命就是存在的一切。这是一支女性欲望的交响,女性生命的悲歌。对于感觉、细节绵绵叙述,对于同一或不同事件反复体验,女性欲望叙事体现了女性的美学原则,女性欲望之流的话语风格:
“现在是我错过的当女先知的第二个机会。我不知道神秘的事物为什么总要找到我,我在那个众人不曾觉察的神秘的隧道口前掠过,一次是预测未来的相机,一次是与冥府接通的女人,但我总是错过了它们,我没有最后选定它们,它们也没有最后造定我。”
唠叨式独白式的语句,没有逻辑的句法,表面的啰嗦以体验为内在支撑呈现为既抒情又思辩,迥异男性叙事的线性推进和理性层次,呈现为一波三折的感受形态。也即女性经验的形态。“女性欲望叙事”造就了林白蔚为壮观的小说世界,从“沙街”到“北京”再到真正的女性本文实现,林白小说象征了九十年代女性写作的美学胜利。从张洁承继“五四”女性写作的“男性叙述”传统,到残雪创制个人化女性叙述,再到陈染女性文本实验,林白以她流丽的女性欲望的叙事,步入了当代女性写作的美学自立。然而,林白小说的局限,也来自于“女性欲望的叙事”。反复呈现的女性欲望场景,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商业物化女性的趣味;拖拉松散的叙述因夹带女性不着边际的性幻想,分散作品主题并导致降低作品的思想性。如何在语言中更深锐地、不带尘俗地再现当代妇女生活、保留当代女性经验,当是林白小说步向更完美境界的一环。
注释:
①安·罗莎琳德·琼斯《描写躯体:对女权主义创作的理解》,见《女权主义文学理论》〔英〕玛丽·伊格尔顿编 胡敏等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2月第1版。
②陈晓明《走进女性记忆深处——简论林白》 载《作家报》1995年12月9月第2版。
③《花城》1994年2期。
④林白《置身于语言之中》 载《作家报》1995年12月9日二版。
标签:林白论文; 小说论文; 世界语言论文; 文学论文; 一个人的战争论文; 致命的飞翔论文; 当代作家论文; 社会经验论文; 张洁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