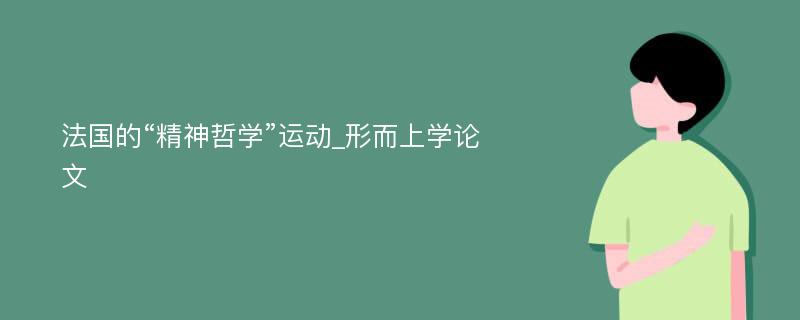
法国的“精神哲学”运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国论文,哲学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法国的“精神哲学”运动开始于本世纪30年代,流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大约二十年间。 1951、 1954年, 运动的倡导者拉维尔(Laveile)和勒·赛纳(Le Sènne )(注:Louis Laveile (1883—1951),René Le Sènne(1882—1954).)先后去世,但运动并未消歇,其影响还在继续扩大。它和存在主义、新托马斯主义、逻辑实证主义等同为当代资产阶级哲学中重要的一支。
“精神哲学”是法国传统的精神主义之再生。但拉维尔和勒·赛纳自称不满意精神主义,不愿采用精神主义的任何型式,否认“精神哲学”为一种精神主义。在他们看来,精神不是本体或关系,不是存在或价值,它是经验的整体。整体、经验的无限是人类智能的两个要求,同为哲学的生命所在。精神就是绝对,绝对和精神是同义的,他们认为这个唯一的、无尽的经验就是哲学家的唯一的、无尽的经验。又认为:提出绝对,绝不涉及神学上的任何暧昧意义;反之,还宣称求助于所谓科学经验的相对性,设想一种能总括人的经验——存在的经验、价值的经验的可能性。
拉维尔在解释“精神哲学”这个名词时说:“……全部哲学的特色不仅在于哲学是一种精神的活动,而且还是对精神的本源和精神的根本任务的一种分析”。“如果哲学不是精神对实在的考量,哲学就一无所有。”“实在和精神对实在的考量并无区别,凭着这种考量,实在本身也成为精神”。他指明精神的任务“是不断地从现象上升到存在,从原因上升到存在的理由,从所与上升到赋予所与的行动,从所遭遇的事象上升到諟证事象的价值。”“精神哲学”运动者自称其目的在追求真理与价值, “为形而上学与道德谋求新的契合, ”(注:Laveile:Laphilosophie francaise entre les deuxguerres.Aubier,Paris,1942,p266—267.)予人以认识和行为的可能。
那么精神究竟是什么呢?何以能执行那样的任务呢?精神哲学者自称不要求构成一个学派;哲学创造的努力是属于个人的,哲学工作的队伍在哲学的探索达到一定的深度时是全无意义的。但对于精神这个字在运动者之间却有共同的、统一的理解。第一,精神是一种活动,是称得起活动这个名称的唯一的活动。一切物质的活动不是主动者和行为者的活动而是被动的被规定的活动。精神不仅不是事物或客体,它只为其自身活动而存在,而且在任何条件下,它始终是自由的先导者及其自身的第一个开始者。它在任何瞬间创造自己。第二,精神不象一般设想的那样是一种暗晦的自然发生的东西,即不是我们只限于认识其结果而不知道它所具有的力量以及在我们之外和没有我们而发生作用的东西。说我们具有精神的意识是不够的,必须说它就是意识自身。它无疑地不能和它的客体分开,也只有在其固有的作用中把捉自己。它是活动,又是光明,是朗照一切已然之前产生其固有的光明的活动。第三,在于重建和扩大长久以来只用于客观经验的经验这个字的意义。经常有人认为没有一个在一切经验之外的精神事件的世界,我们也只能依靠抽象的思辨或想象的梦幻达到这个世界。但毫无疑问,有一种与物质经验相混杂而我们无从把它分隔开来的精神的经验。这种经验向我们指明:在精神产生其自身的瞬间也产生各种事物的意义(而不是产物),这种意义又从别的精神中获得证明。“精神哲学”就在于深化和强化这种经验,依靠这种经验,它在全部存在的领域中探索活生生的无所不在的真实。(注:Laveile:La philosophie francaise entre les deuxguerres.Aubier,Paris,1942,p268—269.)
“精神哲学”运动就是以这种对精神和精神的经验的玄虚的解释反对唯物主义,也反对经验主义、现象主义和实证主义。
1934年起,拉维尔和勒·赛纳主持刊行一套《精神哲学丛书》,宣称其目的在试图再生纯正的哲学思考,探索什么是精神的运动,阐明精神的运动的价值和限度;同时认为哲学负有一种道德的任务,它应和科学的特殊性的研究分头并进,并保证它们的协作以避免由偏蔽、情感所产生的错误,使一切人能体行精神的召唤。丛书除法国哲学家的著作外,还包括大量国外哲学家如黑格尔、胡塞尔(Edmund Husserl)、 舍勒(Max Scheler)、克尔恺郭尔(Kierkegaard)、 怀特海(Whitehead)、索洛维夫(Soloviev)、培第亚夫(Nicolas Berdiaff)等的著作,表明“精神哲学”运动所具有的普遍的性质。
同年,拉维尔和勒·赛纳发表《精神哲学运动宣言》。(注:宣言正式发表于1934年3月1日。)宣言提到四个法国哲学家的名字:笛卡尔、马勒伯朗士(Malebranche)、哈梅林(Hamelin)、柏格森。哈梅林和柏格森曾直接影响拉维尔和勒·赛纳。这两位早一辈的哲学家之间的接合,导致思辨哲学以两个否定的极端,为以后唯心主义哲学的阐发展开了巨大的画面。两人对哲学经验的两个基本性质——无限与整体都无所偏重。 宣言提出笛卡尔, 表明“精神哲学”首先是一种“我思”(cogito)的哲学,由“我思”陆续发现有限与无限,刹那的无常性与永恒。称引马勒伯朗士,表明“精神哲学”运动倡导者的共同的偏爱——偏爱笛卡尔学派在希腊传统、基督教传统和近代科学精神的威力之间所完成的特殊的综合,即从意识的精深的窥察中寻求三者的生动的统一。马勒伯朗士是实行这种综合的先导者,被称为新的心理——形而上学的思辨的尝试的维吉尔(Virgile)。
但更加重要的还是哈梅林和柏格森。两人各自写过一本《略论》,进行过这种综合。(注:前者著: Essai sur les
é l é ments principaux de laréprésentation,Alcan,Paris,1907; 后者著:Essai sur les données immediates de la consience,Alcan,Paris,1889.)他们的作品可以看做一种唯心主义辩证法或描绘性的分析,一种本体论或公理学,一种玄想的吐露或神秘的表达。新的心理——形而上学的思辨的尝试有多种型式。而哈梅林和柏格森的《略论》则是意识的发现或只凭“真实的意识”才能获得的发现。“精神哲学”倡导者自称其目标在于使意识在其存在中与绝对存在相联系,深究意识所固有的内在生命,使意识趋于明朗和精纯。因此,这两位哲学家就更为他们所崇尚。
上面说过,“精神哲学”运动以追求真理与价值自命。它以科学经验的相对性强调精神和精神的经验的绝对性。拉维尔和勒·赛纳担心哲学将让位给科学,人将仅仅生活在现象世界中。因此说:“不要忘记科学的一切神奇的发现只限于物质世界”。
“科学是精神的产物,……精神不能成为自己产物的囚犯。”(注:Laveile:La philosophie francaise entre les
deuxguerres.Aubier,Paris,1942,p263—264.)法国是笛卡尔的故乡,笛卡尔希望精神会使我们成为自然的主人,于是要求回到“我思”,回到马勒伯朗士的“综合”,又回到哈梅林、柏格森《略论》的那种型式,为哲学重建永恒的任务:哲学是理论与实践的认识,是人的命运的意义之精炼化的认识。这是“精神哲学”运动者的愿望和抱负。
二
事实上,“精神哲学”运动不可能对人类思辨的理论与实践的问题提出鲜明的学说。由于强调个人探讨、不自以为要构成一个学派,运动的倡导者之间倾向不同,也有主张上的不同。但他们各自的思想原素、研究主题、方法、思想由来都有其共同的根源。他们的论题是分享,自然地采用的哲学研究和哲学表达的方法是马勒伯朗士和梅纳·德·皮朗(Maine de Biran)的反思的分析。
分享的发现是精神的形而上学的生命。它首先注意树立为实证主义所“贬低”、“排斥”了的意识的力量。这里,柏格森主义似乎是“精神哲学”的直接来源和形而上学复辟的最近的范式。柏格森曾要求哲学家们重新回复到意识的直接材料中去。进入到意识的直接材料的深处,将使精神从重重桎梏中获得自由,强使理智转向外在世界。“精神哲学”运动不同于柏格森主义的是:不以唤醒为理智所窒息的性能来达到这个目的,而要求理智自身实现其固有的转变;理智自身应是回复到具体性的主动者。所以“精神哲学”运动不是反主智主义而是主智主义的。运动的倡导者和柏格森一样不信任抽象的理智,但认为依靠分享,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可以无须求助于超反思意识的直观而获得解决。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起,法国各派哲学唯心主义环绕自然与自由、认识与行为等矛盾展开斗争。实际上,这是对哲学唯物主义的斗争,是形而上学对唯物辩证法的斗争。“精神哲学”运动亦以“解决”这些矛盾自任:分享是获取“解决”的保证,综合是进行“解决”的方法,所谓活生生的统一是“解决”所能达到的目的。拉维尔说:“选择一种解决就是选择命运和尊严,也就是选择一种真实”。(注:见Encyclopédie francaise.p16、06、11.)可知这个斗争的尖锐性。他和勒·赛纳在分头“解决”这些矛盾中阐明了“精神哲学”的“义蕴”。
就拉维尔来说,人之所以能位于存在之列并成为实在,是由于精神的生存。基于精神的生存,他提出所谓“存在的经验”作为既为自我创造的创造者和启示实在的启示者的反思的行为。在反思中意识发现其紧密的统一性,而在这个内在紧密的中心发现意识与绝对的关系。其所以如此,是由于“存在的经验”的存在是一种只有意识能把它显示给我们的内在的存在。拉维尔说:“外在于‘我’的客体,对‘我’来说,只是一种现象,而‘我’则绝非现象。因此,自我意识是形而上学的第一经验,它在使我们深入到我们本身内部的同时,也使我们深入到普遍本身的内部,而在深化和扩张我们本身所有的经验时,我们能获得一种内在经验,并使实在前进。”(注:Laveile:Le moi et son
destin.Aubier,Paris,1936,p26—27.)所以“存在的经验”的那个存在, 又是一种分享的行为、反思和生存、存在的同意和创造。拉维尔试图以这个说法“解决”自然与自由这对矛盾。他认为自然与自由的不协调始终存在。当科学逐渐地制服世界,在役使自然的同时把人从自然手上解放出来,人却并未获得自由。某些主智主义者认为应予人以内在的自由,使理智成为人的情绪的主宰者;近代某些批判理性主义者要求人依靠理智本身的信心的行为寻求一种解决。但并无结果。反之,失却自由使人只看到世界的虚幻,我们的生命在种种表面的境界中消逝,不知道存在本身究竟是什么?还使我们不能不在这个虚幻的世界之外设想另一个或许是实在的世界,而又不幸同这个或许是实在的世界绝无关系。于是意识只能满足怀疑主义或任凭为苦闷所侵扰。生命对其自身失去了信心,它没有重心、力量和快乐。不过如果生命能处于它所固有的、向它完全呈现的绝对中,生命就会展示出一幅前景,苦闷将表现它的希望之最高的膨胀力。(注:参阅 Laveile: La pr ésence totale. Aubier,Paris,1943,p9—10,p13—14、16、35.)
拉维尔批评现象主义者的态度是:既为对存在的否认又为对所以存在的拒绝。必须承认存在,分享存在。他一再强调意识的作用:没有意识,我们将仅仅是一个客体;意识启示我们以真正的存在,并把总体存在的内部启示给我们;意识和总体存在的内部是一体的,它使“我”深入到总体存在的内部并与之同其命运。这也就是所谓分享。所以“我”的发现包藏着存在的发现。纯粹的我既不先于存在,也不独立于存在,而是我的本身的生存,亦即为“生存之我”,它表明“我”的经验包藏着存在的经验,并构成存在的经验的某种定限。正唯如此,拉维尔认为:第一,不能把存在看做静止的、已完成的、一切已经完备了的;存在不是像一个纯粹的客体那样,是那个“我”只能加以諟证而不能加以改变、予以毁损的。第二,部分固然不能离开总体或不能没有总体而存在,但其本身有一定的独立性。因此,总体的存在可以确认为一种无限制的行为,换言之,是一种纯粹的自由;而一切创造,对总体的存在来说,只是它的存在的本身的交通,亦即只能是创造的自由。所以如果每一个意识在每一瞬间为其本身所限制,也必能在每一瞬间超越这种限制。(注:参阅 Laveile: La pr ésence totale.Aubier,Paris,1943,p9— 10,p13—14、16、35.)拉维尔由此提出论断:分享本身不和自由分开,自由是分享的核心。开始分享就是自由,自由消失就是分享消失,因为“我”已经不属于总体,不是总体的一部分了。对我们来说,自由是在总体的存在中的一种确定的前景的选择;同时,自由之所以是分享的核心,还由于只有“我”能进行分享,并依凭“我”所固有的开创力去产生自由之故。(注:Laveile:De I'acte.Aubier,Paris,1937,p179.)
勒·赛纳的哲学思想与法国传统的精神主义更多直接的联系,这是一种导源于笛卡尔而又深受康德的识知和信仰二元并存说影响的精神主义。他提出所谓“价值的经验”与拉维尔“存在的经验”并立,标志着“精神哲学”运动的一致之处和不同之处。勒·赛纳的出发点是笛卡尔的“我思”(cogito),我思就是经验,经验是抽象而又具体的普遍。认识只能求之于经验——一切都应求之于指定的或不可少的经验,而哲学不过是经验的描述。由于强调“我思”,所以在他看来,“我”以其普遍性与卓越性表明其无往而不在。他又把“我思”称为“双重的我思”(double cogito)。“我思”不外推理与直观, 是意识之有限的尝试的与无限之完善的直观的陆续发现。而“我”之所以“思”则是由于矛盾的存在。矛盾是认识的条件,精神法则的本身;“我思”也由于苦痛、困难的侵扰,它们也是矛盾,又或是矛盾的表现形式,又同样是客观所施于主体的障碍。我思这个经验的陆续发现,首先是意识和它的对象之间的矛盾的结果,是意识由不完善、不充足逐渐趋于完善、充足的结果,又即为不断解决矛盾、克服苦痛和困难的结果。勒·赛纳说:“当困难产生时,我被分裂,……经验的内涵,客观地区分为决定与价值,主观地区分为决定之我或我和价值之我或上帝。”(注:参阅Le Sènne:Obstacle et valeur.Aubier,Paris,1934,p5、200—201.“此处主观地区分为决定之我或我”的这个“我”系受动之“我”,P224— 225。)矛盾、苦难之克服是价值制胜了决定,价值之我或上帝超越了决定之我或我。这是价值的经验呈现、增长的过程,亦为人或人类日趋于美、善的过程。勒·赛纳依据这样的经验,从笛卡尔订立“暂行行为守则”的需要(注:见笛卡尔《方法论》第三部分。),进而研究“行动哲学”,探索行动的选择和为生活所要求的抉别力的产生,试图解决认识与行为这对矛盾。他从如何克服矛盾、苦难着眼,批评已有的“苦难哲学”,认为这种哲学或者教我们用巧妙的手段逃避打击,或者劝告我们以让步、忍受来减轻困扰,或者如叔本华那样要求我们抛弃欲望甚至生命来消除苦难的力量,这都是不正确的。正确的是:赋予苦难以真正的意义,接受苦难使之确实成为自己的苦难,从以获取丰富和深化我们内在的存在的方法,并皈依一种快乐的原理。如果从道德学的观点说,接受苦难是德性的起源;勇敢是德性中的第一个德性。(注:参阅Le S ènne:Traité de morale général.P.U.F.,Paris,1942,p532.)
矛盾是诞育和发皇精神生活的第一事象。在完美的和谐中,意识熄灭,而意识是始终需要炽燃和苏醒的。笛卡尔的有步骤地怀疑的真正根源是:矛盾使精神活动。按照勒·赛纳的意见,笛卡尔主义的特点与其说在尊尚思想,无宁说在尊尚那个深附于思想的怀疑。怀疑使思想意识到它自己,为消除怀疑,不断创造为它所固有的真理。但怀疑只是矛盾的理智的形式,苦难则是矛盾的感觉的形式:怀疑是纯粹精神的苦难。苦难把意识安排在矛盾的中心。只有当我们被击败和丧失勇气时,苦难才是不吉利的。反之,运用一切办法解决苦难,苦难就只能为我们展示出无限发展的前途。他说:“我们的生存从来不是极为恶劣的,它始终存在着希望,存在着希望的曙光;也从来不是最完善的,威胁可以远离,但并不消失。”(注:Le Sènne:Le Devoir.Alcan,Paris,1930,p325.)克服矛盾、苦难是“我”的义务。因之,他又把义务称为一切可能性的第一条件。显然,勒·赛纳是在用实践理性批判来使理论理性批判完整化。在任何行为的领域中,精神所需求的发现和克服种种矛盾的发现就是特出的道德行为。认识与行为这对矛盾消失了,实际上是把它吸收在由义务而来的发现这一概念中,而这是一个对意识的任何举措都能适用的概念。这个哲学似乎没有现代存在主义那样的十字路口的经验的苦闷,这是由于它始终求助于上帝:矛盾、苦难的意识与上帝的无所不在——亦即隐藏在人心内部的冥顽的、炽烈的矛盾,苦难是和对上帝的完全信任同时存在的。这是一个建立在人与上帝之间的所谓持续的、生动的、相联系、相沟通的关系中的哲学。所以,勒·赛纳又把“双重的我思”称为“神、人的关系。”(注:参阅Le Sènne:Obstacle
et valeur.Aubier,Paris,1934,p5、200—201.“此处主观地区分为决定之我或我”的这个“我”系受动之“我”,P224—225。 )上文所说的“当困难产生时,我被分裂,……”以及分裂的结果,只表明要求一种超越于一切认识之外的认识。所谓“价值的经验”就像是超验的绝对,而上帝也就是这种绝对。勒·赛纳就在这里提出“精神哲学”运动的论题“分享”,分享使人认识上帝或绝对,并依我们探索、寻求的程度而予我们以价值。于是基本的经验又不外是分享的经验,即活跃精神的形而上学的生命的经验。
三
如上所述,可以看出“精神哲学”运动是一个意识哲学的运动和重建所谓“新的”心理——形而上学的运动。为什么它是“意识”的,又是既“心理”而又“形而上学”的心理——形而上学的呢?按照拉维尔的说法,因为“我们需要一个绝对来树立我们的一切真确性,……而每一个真确性只是在我们自身深处获得其意义的一种尝试。”(注:Laveile: La philosophie francaise entre les deux guerres.Aubier,Paris,1942,p8.)“精神哲学”运动还强调哲学的再生,就是指的这种法国传统哲学的再生,即从笛卡尔起,经马勒伯朗士、梅纳·德·皮朗、拉韦松—莫利安(Ravaisson- Mollien)、 拉舍利埃(Lachelier)、哈梅林、柏格森等人的哲学唯心主义运动的重现。 同时,所谓哲学的再生又是柏格森所要求的使哲学成为“超越人类处境的努力, ”(注:Bergson:La pensée et le mouvement.P.U.F.,Paris,22e édit.P.218.)亦即为法兰西的这种哲学唯心主义面对资本主义社会所作的探索性的努力。
在有关“精神哲学”运动的著作中,随处可以发现这些哲学家们对当代的焦虑,这是对社会中衰飒现象的焦虑,对宗教和已有的哲学唯心主义无法维系人心、解决所谓“内心分裂”的焦虑。在这一意义下,“精神哲学”运动又可以说是一种新的“苦难哲学”运动。即在自由与创造、义务与发现等名义下依凭所谓分享,求助于上帝或绝对,以获取前景,实现希望之最高膨胀力的运动。然而正如上文已经提过的,即使从哲学唯心主义的角度来说,“精神哲学”运动也不可能对人类思辨的理论与实践的巨大问题提出鲜明的学说。某些新名词和若干新术语的摆弄或炫耀显然不能找到哲学的新观点,如列宁说的:“和劳神费力创造‘新’价值论、‘新’地租论等等一样,乃是精神贫困的特征。”(注: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人民出版社,1956,p140.)它的所谓存在的经验和价值的经验的那个经验,不是被解释为客观的、从外面给予人的东西,而是“意识的另一个名词”,是列宁所曾引述和批判过的“意识与直接的心理经验是同一的概念”的因袭。(注: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 人民出版社,1956,p143—144 .)它所强调的分享,无论是拉维尔的“分享就是自由”或“分享产生自由”或勒·赛纳的“分享使人认识上帝或绝对,……予我们以价值,”其前提在于以反思的意识作为我们分享的连接点。其目的在于使人无视这个实实在在的我们所生活在其中的世界,把人带进一个虚幻的境界、一个和用时间、空间来标志其客观的广袤的不同的世界中去。基督教早就主张:受上帝恩宠的状态就是神的生命的分享。为“精神哲学”运动引为同调的培第亚夫甚至说:“上帝生于人中,人由此升华与丰富,人生于上帝中,人由此丰富了他的神的生活。”(注:Berdiaff:Royaume de I'ésprit et royaume de C ésar .Neuchtel,Délachaux,Paris,1951,p31.)而这,也就是所谓“人类处境的超越”。但是在感性的世界以外并不存在着某种东西,而“所有存在的基本形式是时间和空间,离开时间的存在和离开空间的存在同样是最大的荒唐。”(注:恩格斯:《反杜林论》,三联,1956,p52, p117.)用恩格斯的话来说, “精神哲学”运动就不能不是“最大的荒唐”。
由此可知,“精神哲学”运动所企图实现的所谓自然与自由、认识与行为的统一,实际上是一个承认自然界给人以规律的问题,又首先是从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此岸性问题。“自由不是在于想象中的对于自然规律的独立,而是在于认识这些规律,并且在这种认识所给与的可能性之上有计划地使得自然规律为着一定目的发生作用。”“自由是以对于自然必然性的认识为根据的对于我们自己以及对于外部自然界的支配。”(注:恩格斯:《反杜林论》,三联,1956,p52,p117.)而“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注: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人民出版社,1956,p135 .)“精神哲学”运动正是坚决拒绝这一点,这个运动就只能陷入到“苦难哲学”的、神秘主义的泥坑中去。明显的事实是:“精神哲学”运动所自称企求的真理和价值,只有依循站在唯物主义观点上的科学的道路才能获得。
来稿日期:2000年1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