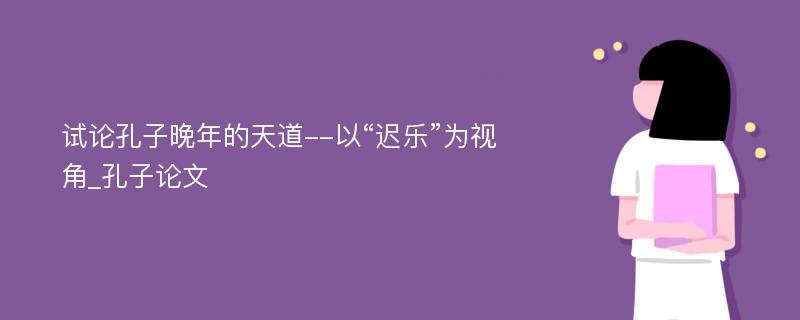
試論孔子晚年的天道觀——以“晚而喜易”爲視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孔子论文,天道论文,晚年论文,爲視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雖然《論語》中孔子多次感嘆“天”①、“天命”,但是他並未論及“天道”。《論語》中唯一提到“天道”,出自《公冶長》篇子貢的感嘆之語:“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但子貢這句話往往被認作孔子不言或罕言“性與天道”的明證。如果聯繫到從孔門後學即戰國儒者大談“性與天道”開始,魏晉玄學和宋明理學家均是藉助於對“性與天道”的新解和自覺體認才開出了新的哲學理論體系的話②,那麼,孔子晚年“性與天道”觀如何實在是哲學史上不可忽視的大問題。 要推進對此問題的認識,不可忽視孔子“晚而喜《易》”這一史實。孔子關於“性與天道”的形上玄思,雖然在《論語》、《禮記》、《孔子家語》等文獻中有重要顯示,但更主要體現於《易傳》中。然而近代以來的學者多否認孔子與《易傳》的思想聯繫,甚至不承認其中的“子曰”即指“孔子曰”。幸而以對帛書《周易》的研究爲契機,近年來學界已形成共識:孔子晚年確曾喜《易》、贊《易》和傳《易》,於《易》深有所得,至少今、帛本《易傳》中的“子曰”是孔子論《易》的珍貴而可靠記錄。③本文擬在學者研究的基礎上,以孔子“晚而喜《易》”爲視角,探討孔子晚年天道觀之內涵。 一、“不言”還是“不聞”:從子貢的疑惑說起 從孔子早年的生命重心和思想核心來看,爲重建社會的禮樂秩序,他注重向人的內心之不安不忍處尋求理論依據,追問“禮之本”(《论话·八佾》),提出“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论话·八佾》)的“禮以仁爲本”的“仁”的學說,注重“求諸己”的道德修爲,强調“修己以安人”的人生進路。這就與老子繼承春秋時期自然主義天道觀,强調“推天道以明人事”的理論建構大异其趣。同時,也與子產把“禮”看作“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即以氣化的自然秩序與禮相配以說明禮制合理性的做法不同。也就是說,雖然孔子曾問禮於老子,稱贊子產爲“古之遺愛”,但他並未將“天道”置於思考的中心,至少晚年以前的孔子是如此。 然而,這是否就意味著孔子没有關於“天道”的哲思呢?顯然不是。就《論語》所見,孔子曾多次情不自禁地感嘆“天道”,如: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論語·子罕》)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論語·陽貨》) 可以體會到,孔子在這兩處感嘆中,內心都是極其豐富的。看到“川流不息”,孔子對於“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④發出感嘆。宋儒將此言當作孔子對剛健不已之天道的形容,乃是不失孔子思想精神的合理引申。而“天”(天道)作爲萬物生生不已的原因和决定性力量,具有不可感知性,乃是通過“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而得以體現和確證的。如果借用《孟子·萬章上》的話,即是“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無論如何歸納《論語》中“天”的屬性,可以肯定,這裏的“天”乃是完全没有人格神特徵的,“無時無刻不以默運的方式在宇宙之中不斷創生的精神力量”。⑤這裏的“言”,楊伯峻先生已指出,並非日常語言,而是“性與天道”類形上哲思之語言。⑥孔子這裏明言“予欲無言”,“天道”需要後學默識體貼,若懂得於“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處感悟“天道”,“天道”明白易曉,否則,“天道”便幽隱難言。⑦ 從這個角度看,子貢關於“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的感嘆似乎更容易理解。從經學史上對“性與天道”章的詮釋史來看,争論主要集中於“夫子是否言過性與天道,子貢是否聞過性與天道”。⑧首先,關於“夫子是否言過性與天道”問題,魏普玄學家多認爲“性與天道”深微難言,所以夫子不曾“言”,因而子貢“未得聞”。如何晏注曰:“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也,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深微,故不可得而聞也。”⑨而以程朱爲代表的宋儒則多認爲孔子曾“言”。如程頤認爲這句話是“子貢聞夫子之至論而嘆美之言也”,朱熹亦注曰:“夫子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聞者。蓋聖門教不躐等,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嘆其美也。”⑩這些意見均有其通達合理之處。根據上文分析,我們不能因爲“不可得而聞”一語,便將“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徑直解讀爲“夫子不言性與天道”,只要將這句話與“子不語怪力亂神”語句相比較便知。關鍵的原委是,由於具有普遍性、超越性的“性與天道”難以用日常語言表達,早年孔子對“天道”更多地强調體悟和默識,所以對弟子的“指點”或者說“言說方式”較爲特別,不如《詩》、《書》、禮樂之教,德行政事之教明白易曉而已。其次,關於“子貢是否聞過性與天道”的問題,宋儒有“聽聞”與“得聞”的辨析。李學勤先生考證認爲,“聞”並不等同於感官的“聽”,《大學》中有“聽而不聞”一語,“聞”應釋爲“知解”,子貢的意思是說:“孔子關於性與天道的議論高深微妙,連他自己也難以知解。”(11)這句話恰證明孔子曾討論過“性與天道”。因此,子貢“不可得而聞”之嘆透露了兩點--是孔子對“性輿天道”談得很少。正如“予欲無言”章所提示的,雖然孔子對“天道”有豐富體認,但常訴諸“不言之教”,强調體認體悟。二是“性與天道”本身深微而“難以知解”,故子貢等高足才有此慨嘆。 如果不局限於“天道”這個字眼,《論語》中有更多孔子致思形而上境域的言論,這些言論均可看作“爲其人道哲學尋找天道依據,將其人學發展爲天人合一之學”(12)的努力。如: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論語·爲政》)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論語·泰伯》) 這種由天而人的“人道觀”透露著孔子“下學而上達”,試圖溝通天人,上達天道,以德合天的努力和價值祈向。 以上還是基於《論語》的討論,其實,《禮記》、《孔子家語》中關於孔子談“天道”還有多處明確記載,只有由於學者過分固執於《論語》中孔子重視“人道”而罕言“天道”,就認爲孔子終其一生並未談論“性與天道”這種形而上的抽象問題,因此,《論語》之外的相關記載被想當然地認爲是儒門後學的假托僞造。如: 公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無爲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禮記·哀公問》) 參嘗聞之夫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曰幽而圓曰明……”(《大戴禮記·曾子天圓》) 孔子曰:“大道者,所以變化而凝成萬物者也。”(《大戴禮記·哀公問五義》) 孔子曰:“天道敏生,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孔子家語·哀公問政》) 首先,無論是“哀公問”,還是曾參“嘗聞之夫子”,顯然都應是對孔子晚年談論“天道”的記載。這與孔子“晚而喜易”後“天道觀”的凸顯或有關係。以審慎的態度來看,没有理由將這些材料簡單地斷定爲假托僞造。《哀公問》中孔子“天道”“貴其不已”的論述與《易傳》中“生生之謂易”及《論語》中“天何言哉”的感嘆,思路完全一致。《大戴禮記》中孔子所說的“所以變化而凝成萬物”之“大道”,顯然就是“天道”。《孔子家語·哀公問政》孔子此言在《中庸》中也被引用到,雖然只出現了“人道”、“地道”,但可以看出孔子將“天道”、“地道”、“人道”三分對言的思路與《易傳》强調“三才之道”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二、“明數而達乎德”:“觀(求)其德”的內涵 基於前文的討論可知,强調“下學而上達”,“吾道一以貫之”的孔子思想中,並非没有對超越性“天道”的思索,只是從《論語》來看,在孔子關於禮樂秩序重建及其價值根源的思考中,“天道”的角色與作用較爲模糊而已。然而,如果我們把視野轉移到今、帛本《易傳》,研讀其中所保存的孔子“晚而喜《易》”之後論《易》的大量言論,讓我們不得不對孔子晚年“天道觀”作進一步的考察和重新認識! 馬王堆帛書《要》篇在考察孔子易學觀上的意義,已被學者充分解讀。(13)根據學者對《論語·述而》“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章的研究,孔子“老而好《易》”的時間應在周游列國後期或自衛歸魯後。(14)帛書《要》的重要之處在於,該文獻中通過子貢的質疑與追問,孔子對自己晚年易學觀發生重大變化的原因做了詳細陳述和澄清。根據廖名春先生關於“夫子老而好《易》”章的“新釋文”,孔子將自己“老而好《易》”的主要原因歸結如下: 答子貢第一問:察其要者,不詭其福。《尚書》多疏矣,《周易》未失也,且有古之遗言焉。子非安其用也,子樂其辭也。 答子貢第二問:《易》之道:良【筮而善占】,此百姓之道【也,非】《易》也。夫《易》,剛者使知懼,柔者使知剛,愚人爲而不妄,漸人爲而去詐……子樂其智之。 答子貢第三問:《易》,我後其祝卜矣!我觀其德義耳也。幽贊而達乎數,明數而達乎德,有仁【守】者而義行之耳。贊而不達於數,則其爲之巫;數而不達乎德,則其爲之史。史巫之筮,鄉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吾求其德而已,吾與史巫同途而殊歸者也。(15) 子貢三問而使孔子晚年“重德輕筮”的易學觀得到了充分自我陳述。孔子自陳自己好《易》乃是因爲“樂其辭”而非“安其用”,是因爲《易》中飽含“古之遺言”和人道智慧,歸結到一點,對《易》愛不釋手是要“觀其德義”、“求其德”,而且是超越巫之“幽贊”和史之“明數”而“達乎德”。這裏的“觀其德義”、“求其德”,若僅解釋爲求取其中蘊含的人道教訓,以期修身寡過並不算錯,事實上,從今本《易傳》孔子研《易》十九則材料就可以看出孔子學《易》的價值祈向,是注重從卦爻辭中發掘恒德、謙德、慎言、知幾、履信思順等修德立身的智慧。(16) 但是,將“觀其德義”僅解讀爲從卦爻辭中求取人道教訓與生活智慧,尚不足以發掘孔子“觀其德義”的深意。最主要的,《易》作爲“聖人之所以極深研幾”,即“聖人用來探究深奧幾微之理的大著”(17),强調“推人道而上達天命”的孔子“居則在席,行則在橐”的研之贊之,難道對其會通天人的形上“易道”没有體悟和闡述嗎?如果承認,《易傳》乃是作爲孔門後學的戰國儒家易學派的作品,那麼,《易傳》中以“陰陽”爲其內在規定性,具有“變”與“生”功能的形而上之“易道觀”(18),難道没有孔子易學觀對其的深刻影響?如果承認,郭店竹簡《語叢一》的“《易》,所以會天道人道也”代表著戰國儒者對《易》之性質的共識,而《莊子·天下》中的“易以道陰陽”乃是戰國士人對《易》之內容的基本認識,那麼,這些理解難道與“夫子老而好《易》,居則在席,行則在橐”没有內在的思想聯繫嗎?畢竟,《易》本卜筮之書,在春秋筮占實踐中一直發揮著溝通天與人事之聯繫的功能,其獨特的卦爻象與卦爻辭結構蘊藏著天人溝通的智慧,孔子本人雖然輕“筮”,但也坦言“百占而七十當”。《要》中更明言其所好之“德義”乃是“幽贊而達乎數,明數而達乎德”而來。綜上所述,我們要對“觀其德義”做出更深刻的理解。 事實上,已有學者指出,孔子“觀其德義”、“求其德”,乃是指探求《易》所蘊含的義理和哲學內涵而言的。如李學勤先生認爲,《要》篇的“觀其德義”中“德義”之所指,就是《繫辭》中引“子曰”而言的“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智),六爻之義易以貢”,“孔子是要通過《周易》卦爻的變化,去窺見義理”。由“幽贊”、“明數”而“達於德”的“德”,“詳言之即‘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19)朱伯崑先生認爲,“窮理”即爲探討陰陽變异的法則。(20)邢文先生考證認爲,“明數而達乎德”的“德”,非“仁義之德”,乃“天理之德”。(21)李景林先生更明確地指出,孔子晚年所把握到的《易》之“要”,即“德義”,乃是《易》中蘊含著的“宇宙人生的超越性普遍原則”。(22)他還認爲,孔子“晚而喜《易》”最重要的原因是,《易》獨特的“設卦觀象繫辭”的思想表達方式,使孔子可以“一改《論語》中之‘無言’的表達方式,而直陳‘天道’”。(23) 綜合文獻材料來看,孔子超越巫史傳統而强調學《易》“達乎德”,的確並非僅僅從人道教訓角度從卦爻辭中“拾取”“古之遺言”,並非脫開“卦爻象”而單論“卦爻辭”,而是在“幽贊”、“明數”的基礎上才“達乎德”,在此過程中必然要“會天道人道”。我們看到,一方面,基於卦爻辭的彈性,今、帛本《易傳》中的“子曰”,從卦爻辭中引申出的人道教訓義,看似鑿之過深,實則亦是推天及人的結果,隱含著以人合天,天人合德的思路;(24)另一方面,孔子對《易》之“精要”有明確論述,如《繫辭上》曰: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 孔子這裏以“一言以蔽之”的語氣,設問說:“《周易》,到底是作什麼用的一部書呢?”然後自答曰:“《周易》是用來開發萬物之理,成就萬民事業的,它囊括了天下所有法則,如此而已。”(25)可見,孔子眼中,《周易》的主要身份和功能已經不是筮占之書,而是“冒天下之道”和“開物成物”的哲學智慧之書。他“好其德義”,也就是好《易》囊括了天下所有法則,“知變化之道”、“損益之道”。《易》能“冒天下之道”,表明《易》之“道”乃是“簡易之道”,可“得一而群畢”。《易》是蘊含天道、地道、人道“三才之道”的智慧之書。 綜上所論,透過孔子論《易》的言論,我們可以肯定,由於“天道”的形上性和超越性,早年的孔子雖有豐富的體認,但只是以“無言之教”引導弟子去自覺地體貼和默識,且生命的重心亦在人道教化和社會禮樂秩序的重建,故而罕言“性與天道”。但是,孔子“晚而喜易”之後,藉助於《周易》“會天道人道”的獨特文本形式和思想內容,孔子吸收《易》之推天及人的思想,從“天道”的角度爲其“人道”思想尋求可能性與合理性的說明,强調“天不只是生命存在的本原,而且是生命價值的本原”(26),人應積極進行德性實踐,修身修德以上契天道,即所謂“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論語》中記載的孔子自陳“吾道一以貫之”,也應放在天道人道相貫通的角度才能獲得正確的理解,即“人道”背後乃是“天道”,孔子的“天道”觀以“晚而喜易”爲標誌,經歷了一個由隱而顯的過程,孔子對“天道”的認識是“一以貫之”的。 三、《易傳》“子曰”中的孔子天道觀 《易傳》中的天道觀不等於孔子的天道觀(27),但是,作爲傳孔子易學的孔門後學的作品,《易傳》中應包含著孔子的天道觀思想。按照“謹慎肯定”孔子與《易傳》之關係的態度,“子曰”部份應當較真實的記載著孔子的易學思想。雖然未標示“子曰”的論述未必就不是孔子的思想記載,但爲嚴謹起見,下文將僅以《易傳》“子曰”材料爲主要依據探討孔子的“天道觀”。 (一)天道乃是陰陽之道。《易傳》將陰陽視爲“道”的基本內涵,如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在天之道曰陰與陽”。那麼,“晚而喜易”的孔子有没有以陰陽論天道呢?如果我們不固執於“唯有《論語》才是孔子真實言論之記載”的觀點,如果我們不再忽視今、帛《易傳》中“子曰”材料的孔學意義,那麼,就該承認以陰陽論天道,是孔子晚年所論及的天道觀。如: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易傳·擊辭下》) 子【曰】:“《易》之要可得而知矣。《鍵》、《川》也者,《易》之門戶也。鍵,陽物也;川,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化……”(帛書《衷》) 子曰:“《易》之義呼陰與陽,六畫而成章。曲句焉柔,正直焉剛。六剛無柔,是胃大陽,此天【之羲也】……六柔無剛,此地之義也。”(帛書《衷》) (孔子)戒門弟子曰:“……故《易》又天道焉,而不可以日月生辰盡稱也,故爲之以陰陽;又地道焉,不可以水火木金土盡稱也,故律之柔剛;又人道焉,不可以父子、君臣、夫婦、先後盡稱也,故要之以上下。”(帛書《要》) 首先,孔子把“陰陽”看作兩種相對的功能和勢力,陰陽交合而形成天地萬物神妙的秩序。同時,孔子認爲《易》之“精要”就是陰陽,所謂“《易》之義呼陰與陽”。廖名春先生說:“‘呼’,當訓爲‘稱舉’。這是說《周易》的義涵稱之爲‘陰’與‘陽’。”(28)而《要》篇在談到損益之道時,從天道、地道、人道三分對舉的角度更加明確的說:“《易》又(有)天道焉,而不可以日月生辰盡稱也,故爲之以陰陽。”也就是說,天道之內涵可以概括爲“陰陽”。孔子的這些論述對於孔門後學明確提出“一陰一陽之謂道”,無疑具有深刻影響。 陰陽在春秋時期本屬天道觀的範疇。“從思想史的大勢看,天地、天道和陰陽是春秋思想界的常用概念,從孔子口中出現這些辭彙並不違背思想史的演進規律”。(29)西周以降,史官群體多以陰陽概念解釋自然現象,這與自然天道觀的發展是內在一致的。春秋政治家範蠡曾將天道的內容概括爲“陽至而陰,陰至而陽;日困而還,月盈而匡”(《國語·越語》)。這便已經超越了傳統天道觀而把陰陽從氣的觀念向上提升,視陰陽爲兩種相對的功能,使之具有普遍性與象徵性。(30)其實,對孔子影響最大的,應該是老子的哲學。老子作爲史官,也非常重視陰陽,他强調“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道德經·四十二章》),天地萬物均是由陰陽和合而產生和演進的。早年孔子曾問禮於老子,對老子的自然主義天道觀應該非常熟悉。但是,雖然拜見老子後,孔子對他稱贊有加,但“知其不可而爲之”的社會政治追求决定了孔子早年的生命重心不在於探究陰陽變易之天道,不在乎個人吉凶、禍福。然而,晚年歸魯之後,飽經人生磨難,也不再寄希望於現實政治,本身便具有大史官素養的孔子,從《周易》獨特的卦爻象中發掘陰陽天道觀,是完全可能的。(31)甚至可以說,是孔子開創了早期儒家易學派“易以道陰陽”之經學主張的先河。 (二)天道乃是損益之道。傳世及出土文獻中,有多處關於孔子談論《損》、《益》兩卦的記載。其中,帛書《要》記載孔子讀到《損》、《益》兩卦時,“廢書而嘆”,並“戒門弟子曰”: 二三子,夫《損》、《益》之道不可不察也,吉凶之【門】也。《益》之爲卦也,春以授夏之時也,萬勿(物)之所出也,長日之所至也,產之室也,故曰《益》。《損》者,秋以授冬之時也,萬勿(物)之所老衰也,長【夕之】所至也,故曰【《損》】……《損》、《益》之道足以觀天地之變,而君者之事已。是以察於《損》、《益》之變者,不可動以憂患,故明君不時不宿,不日不月,不卜不筮,而知吉與凶,順於天地之【□】也,此胃(謂)《易》道。 這段論述中,孔子將《損》、《益》兩卦與四時變化即萬物生長衰老的變化過程相結合,把天道視爲損益之道,懂得損益之道,就可以趨吉避凶。李學勤先生已指出,《損》、《益》兩卦與“時”的觀念有關,可見於《彖傳》,但孔子這裏將《損》、《益》兩卦與“四時”聯繫起來,則爲“十翼”所未見。(32)孔子這裏是說,從《損》、《益》二卦的吉凶變化可以觀察到天地四時萬物之變化規律,即所謂“《損》、《益》之道足以觀天地之變”,而如果把握到《損》、《益》之“變”、之“時”,就可見微知著,“不卜不筮”而做到趨吉避凶。孔子這裏將天道之運行看作損益之道的觀點,與《易傳》“剛柔相推而生變化”的認識是一致的,後者應該受到了孔子的影響。 我們知道,孔子對待文化傳統强調“因革損益”的思想方法和文化品格(33),如《論語·爲政》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這種注重損益的文化精神與孔子讀《損》、《益》兩卦頗有感慨是內在一致的。此外,我們知道,老子也曾以“損益”論天道,如《道德經·六十八章》曰:“天之道,損有餘以補不足。”或許對孔子亦有影響。孔子論《損》、《益》兩卦,在傳世文獻《淮南子·人間》、《說苑·敬慎》、《孔子家語·六本》中均有詳細記載,限於篇幅,茲不詳引。此類文獻中,《淮南子》突出論述利害禍福的轉化;《說苑》、《家語》則結合謙德側重談修養。相比較而言,孔子所談損益之道有差异,李學勤先生推斷這些文獻的來源可能不一樣。(34)但是,這些文獻都記載孔子讀《損》、《益》後,“喟然而嘆”或“廢書而嘆”,都從損益之道引出對利害吉凶的審察。文獻之間的差异恰足以證明孔子確曾對此二卦大發議論,頗爲感慨,或許曾在多個場合面對不同弟子(如子夏、子貢)多次論及。 (三)天道乃是萬物化生之道。今本《易傳·繫辭》中,有“子曰”二字文句者共計二十三條,其中記載孔子專門解說卦爻辭的有十九條,多注重從卦爻辭中發掘恒德、謙德、慎言、知幾、履信思順等修德立身的智慧。其中,有兩條體現著孔子從天道乃是萬物化生之道的角度對卦爻辭的“德義”進行詮釋的例子: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天地絪缊,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這兩條材料分別是孔子對《咸》卦九四爻辭和《損》卦六三爻辭的解釋。上述材料出自《擊辭下》第五章,該章集中記載著十一條孔子釋《易》爻辭的材料,每條都是由“《易》曰+子曰”構成。“天地絪缊”前雖無“子曰”字樣,但根據此章對孔子解《易》的整齊記載,這句話應爲孔子對《損》卦六三爻辭的解說無疑。第一條中,孔子根據爻辭“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尤其是其中的“往來”和“思”字,做出“天下何思何慮”:“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暑相推而歲成焉”的發揮,這與《論語·陽貨》“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章是可以相互注解的,均是孔子對天道運行不已和生物不息功能的揭示和肯定。第二條中,孔子認爲,《損》卦六三爻辭說的是“陰陽合一的道理”,即“天地之氣交感,萬物均得化育。男女精氣交合,萬物得以創生”。(35)應該說,《易傳》講的“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謂易”,這種從宇宙生成角度看待天道,强調天之“生”的功能的天道觀源於孔子。 (四)天道乃是人效法順從的對象。對於天道,孔子强調人要“效”之、“順”之。如《繫辭》中的如下兩段材料: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 《易》曰:“自天佑之,吉無不利。”子曰:“佑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佑之,吉無不利’也。” 第一條中,孔子强調人要“崇效”“卑法”天地,在“天地設位”的前提下,人要效法天地之道而崇德廣業,積極有爲。第二條中,孔子强調“天之所助”者是順從“天”的人,人只有“順天”,順從天道,才能獲得天的護佑。這兩條材料中,孔子强調“效”天“順”天,一方面肯定了“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推天及人的思路,這在《大象傳》中表現最明顯,如所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另一方面,孔子說的“效”天“順”天是要落實於“崇德而廣業”和“履信思乎順”的人道德性實踐和事功實踐過程中的,也就是說,通過“推人道而上達天道”的“下學而上達”的過程,從而實現與天合德的境界,這也是《易傳》“會天道人道”的根本精神。在《易傳》中,這種推天道以及人道的論述非常豐富。如: 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彖傳》) 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節·彖傳》)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咸·彖傳》) 我們目前還無法確定《彖傳》和《象傳》多大程度上屬於孔子的作品,但至少應當看作孔子後學對孔子天道觀的理論化和體系化。 (五)天道可通過“立象以盡意”的方式獲得表達。前文已經論及,天道難以用日常語言表達,雖然孔子內心有對天道的豐富體認,但“老而好《易》”之前,並未找到恰當的方式指陳“天道”,只是以“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的方式指點弟子自覺去體會而已。但是,孔子晚年研《易》後發現,《周易》“設卦觀象繫辭”的文本形式和思想表達方式,恰可以充分表達抽象的“天道”。《繫辭下》記載說: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擊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這段話是中國哲學中“言意之辯”的最經典表述。不要忽視,這是孔子的話,而且是孔子對《易》“設卦觀象繫辭”思想表達方式的揭示。孔子首先指出,“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即文字和語言均有其局限性。那麼,能否“盡意”呢?如何“盡意”呢?這裏的“聖人之意”,可以理解爲“道”,對於認識的終極目標,即求取聖人之道來說,孔子認爲,《周易》“設卦”、“繫辭”、“觀象”的方式有利於表達出形而上之“道”,因爲“卦爻象”通過卦爻辭獲得提示,而卦爻象本身就是“意”的直接外化,“立象”的目的在於“盡意”。王博先生,聖人所立之“象”,就是“意象”,“是揣摩了天意之後的人意的外化。這個意象不是別的,其實就是道之象”。(36)易道在《周易》獨特的“象辭結構”中得以表達,也就是具有普遍性和超越性的“道”獲得了有效表達方式。於是,孔子晚年對具有超越性和普遍性的天道的追問,不必再拘泥於“無言”,可通過觀察“易”之“象”探討其中所蘊涵的天道,並進而確定人道的內容和意義。簡言之,孔子的天道觀,於晚年通過“述《易》”、詮《易》而獲得充分表達。 四、餘論:“性與天道”的一種理解 如果說禮樂秩序如何重建問題是孔子的核心話題,那麼,他“禮以仁爲本”的“仁”的學說的提出,乃是將禮樂秩序根植於人心的努力。“仁”,說到底就是作爲人心之情感的愛。無論是從“心安”的角度回應宰我對“三年之喪”的質疑和挑戰,抑或是針對林放關於“禮之本”的請教,而說出“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的觀點,都表明孔子力圖從生命的內部尋求社會秩序和道德價值秩序之堅實根基和依據。然而,從“晚而喜易”後孔子對“天道”的重視和追問看,孔子晚年又試圖將“天道”納入關於禮樂秩序和價值根據的思考之中。如果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八佾》)的反問和對“仁”的强調乃是向內向下尋求禮樂秩序之根據,那麼,對“會天道人道”之《易》的重視,乃是向外向上尋求禮樂秩序之依據。 可見,孔門後學從戰國開始大談“性與天道”,實乃由孔子開其端。而且,戰國儒者有將二者貫通的努力,只是致思方向有所不同。思孟學派乃是以心性言天道,如有所謂“誠者,天之道也”(《中庸》),“德,天道也”(《五行》),“德猶天也,天乃德已”(《五行》),以及孟子“盡心知性知天”等論述。早期儒家易學派則强調以天道貫通心性,如《易傳》的“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繫辭》),“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繫辭》),以及“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繫辭》)等論述。戰國儒家各派雖然思想重心和對經典的取捨不同,但他們相向而行,均“宗師仲尼”,“游文於六藝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漢書·藝文志》),共同構建了儒家思想的基本性格。 ①楊伯峻先生說,《論語》中“單言‘天’字的,一共十八次”,其中,出於孔子之口的有“十二次半”。參見《論語譯注》中《試論孔子》一文。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10頁。余英時先生認爲,大體上說,孔子的“天”並不指鬼、神世界。“若從‘朝聞道,夕死可矣’的話推斷,其‘天’必與‘道’的涵義相近,可以無疑”。參見氏著《國學與中國人文》,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282頁。 ②向世陵:《“性與天道”問題與宋明理學分系》,《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3年第4期,第126頁。 ③楊慶中先生在其《周易經傳研究》“孔子與《易傳》”一章中,將近代以來學者的觀點綜述分爲“否定說”、“肯定說”和“‘謹慎’肯定說”。至少可以肯定,今本《易傳》的“子曰”,帛書《易傳》中的部份“子曰”係指孔子言論,乃是我們考察孔子易學觀和天道觀可靠而真實的記錄。參見《周易經傳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第150~171頁。 ④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108頁。 ⑤劉述先:《論孔子思想中隱含的“天人合一”一貫之道》,見氏著:《儒家哲學研究:問題、方法與未來開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56頁。 ⑥《論語譯注》,第46頁。 ⑦唐代韓愈對“予欲無言”章的解釋頗爲有趣,可備一說。他說:“吾謂仲尼非無言也,特設此以誘子貢,以明言語科未能忘言至於默識,故云‘天何言哉’,且激子貢使進於德行科也。”見韓愈、李翱:《論語筆解》卷下,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⑧甘祥滿:《〈論語〉“性與天道”章疏證》,《中國哲學史》2012年第3期,第47頁。 ⑨何晏、邢昺:《論語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67頁。 ⑩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77頁。 (11)李學勤:《孔子之言性與天道》,成均館大學儒教文化研究所:《儒教文化研究》(國際版)第十七輯,第232頁。 (12)廖名春:《周易經傳與易學史新論》,濟南:齊魯書社,2001年,第162頁。 (13)如李學勤、廖名春等先生在多篇論文中均有深入解讀,參見李學勤:《周易溯源》,成都:巴蜀書社,2006年,第239-389頁;廖名春:《帛書〈周易〉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85-148頁。 (14)古今學者對於這句話的理解均可謂“觀點紛呈”、“聚訟不已”。筆者認同廖名春等先生的觀點,該章乃是喜《易》後深有所得,而嘆“好易”太遲之語。 (15)《帛書〈周易〉論集》,第165~166頁。 (16)學者對《易傳》“子曰”作過專門研究,如黃壽祺、胡自逢二先生的討論。參見《周易經傳研究》,167~168頁。 (17)楊慶中:《周易解讀》,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451頁。 (18)楊慶中:《論〈易傳〉中的“道”》,《中國哲學史》2005年第4期。 (19)李學勤:《周易溯源》,第86、375頁。 (20)朱伯崑:《易學哲學史》,北京:華夏出版社,1995年,第74頁。 (21)邢文:《論帛書〈要〉篇巫史之辨》,見《簡帛研究》第3輯,桂林:廣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26頁。 (22)李景林:《教養的本原:哲學突破期的儒家心性論》,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29頁。 (23)同上,第38頁。 (24)如《擊辭傳》中,孔子對乾卦爻辭“亢龍有悔”的解釋,所謂“貴而無位,高而無民,賢人在下位而無輔,是以動而有悔也”,是結合爻位而進行解釋的。 (25)《周易解讀》,第454頁。 (26)蒙培元:《孔子是怎樣解釋〈周易〉的》,《周易研究》2012年第1期。 (27)楊慶中先生認爲,《易傳》天道觀可從“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剛柔相推而生變化”、“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四個方面來認識。參見《周易經傳研究》,第260~263頁。 (28)《帛書〈周易〉論集》,179頁。 (29)趙法生:《孔子“晚而喜易”與其晚年思想的變化》,《哲學研究》2012年第2期。 (30)《周易經傳研究》,第201~203頁。 (31)楊慶中先生認爲,《易傳》受老子及其道家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自然主義天道觀,一是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思維方式。參見《周易經傳研究》,第203~209頁。按:孔子贊《易》論天道受以老子爲代表的春秋自然主義天道觀的影響,是合乎思想史衆輯的。 (32)《周易溯源》,第384頁。 (33)李翔海:《論孔子的文化品格及其當代意義》,《中國儒學》(第三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第141頁。 (34)《周易溯源》,第389頁。 (35)《周易解讀》,第467頁。 (36)王博:《中國儒學史·先秦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40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