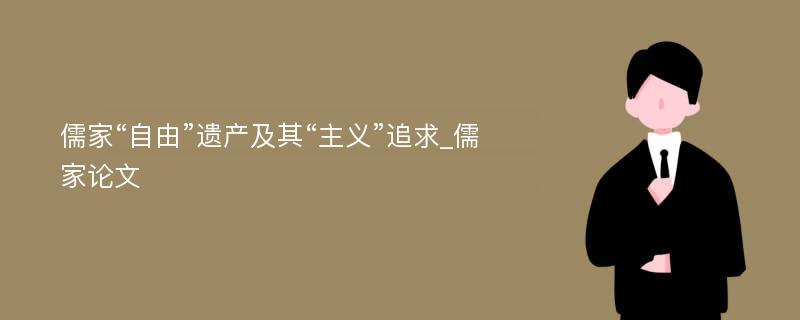
儒家的“自由”遗产及其“主义”追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遗产论文,主义论文,自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B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14)3-0057-10 自严复提出“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以来,“自由”便成为一个贯穿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重要概念。但总体而言,近代以来的“自由”思潮不仅带有明显的外源性质,而且也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将原本作为传统文化之主体的儒学视为自己的强劲对手与推行其“自由”主张的最大障碍。这就构成了近现代中国社会的一个特殊矛盾,也是其他一切社会矛盾的精神母体。 不过,作为近代西方启蒙运动的三大理念之一,“自由”虽然带有明显的外源性质,也具有强烈的制度色彩,却不一定就是西方的专利;作为一种制度,“自由”虽然为西方社会所率先创立,却并不就是西方社会的独享遗产。作为人类精神的一种共同追求,“自由”也同样存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只是由于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精英始终不愿意放弃“自由”的外源招牌以及其所携带的文明进化优势,因而也就不愿意承认中国传统文化中原本就存在着丰富的“自由”遗产。20世纪中国思想界的这一格局,反倒促成了“保守”与“激进”的两极分化与社会层面上“精英”与“民粹”的恶性对垒。实际上,如果我们能够正视“自由”的制度化内涵以及其作为人类精神之共同追求的普遍性品格,那么我们也就一定能够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由”遗产及其“主义”追求。 一、精神与制度:从“自由”到“自繇” “自由”究竟是一种理想性的价值还是一种制度性的权利追求?在严复的翻译中,“自由”首先是作为西方的一种社会制度所体现的精神价值出现的。1895年,正当中国因为甲午战败而陷入割地赔款之空前窘境时,作为第一代走出国门的传统士人,严复便明确地为国人提出了“自由”的理想。他在《论世变之亟》一文中写道: 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彼西人之言曰:唯天生人,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第务令毋相侵损而已。侵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贼人道。其杀人伤人及盗蚀人财物,皆侵人自由之极致也。故侵人自由,虽国君不能,而其行禁章条,要皆为此设耳。① 这可能是国人第一次以制度与理想相统一的方式面对“自由”的话题;至于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与西方人“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无疑既是当时中西方文化对峙的现状,同时也是中国一切现实窘境的根源。从西方“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到“杀人伤人及盗蚀人财物,皆侵人自由之极致”以及“侵人自由,虽国君不能”的诸多规定来看,“自由”显然又是作为西方文明的一种通则性制度出现的。 在那个举国颓丧而又普遍迷茫的时代,“自由”虽然是作为西方世界的文明通则出现的,但包括严复本人,却无疑是从带着文明曙光之理想价值的角度来接受的。所以,“自由”很快便被视为西方文明强盛的根源。而在其同年所著的《原强》一文中,严复同样通过“自由”对西方社会制度及其文明发展之作用进行了说明;而其所谓“原强”,实际也就“强”在其“自由”制度上。严复写道: 自其自由平等观之,则捐忌讳,去烦荷,决壅蔽,人人得以行其意,申其言,上下之势不相悬,君不甚尊,民不甚贱,而联若一体者,是无法之胜也……推求其故,盖彼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一洲之民,散为七八,争雄并长,以相磨淬,始于相忌,终于相成,各殚智虑,此日异而彼日新,故能以法胜矣。② 严复在一年之内两论“自由”,说明在他看来,“自由”既是中国“从未尝立以为教者”,同时也是西方人“得自由者乃为全受”者,因而所谓“自由”实际上也就成为中国社会进步、文明发展的必由之路了。对西方人来说,“自由”既是其个体权利的保障,同时也是其族群能够“联若一体”——“始于相忌,终于相成,各殚智虑,此日异而彼日新”的制度根源。这样看来,所谓“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虽然是严复对西方社会制度与文明通则的一种描述,实际上也就等于为中国社会提出了所应当努力的方向。 严复对“自由”的这一描述,深深影响了中国一个多世纪。不过,值得深思的一点在于,这位最早以“自由”唤醒国人的严复,当他在八年后出版其所翻译的英国人穆勒的名著On Liberty一书时,却不仅不再以“自由”对译“Liberty”,甚至连其译著也不再以“自由”来命名了,而是以《群己权界论》命名。在其关于该书的说明中,严复也明确地以“自繇”置换了原来由他所喊出的“自由”: 中文自繇,常含放诞、恣睢、无忌惮之劣义,然此自是后起附属之诂,与初义无涉。初义但云不为外物拘牵而已,无胜义也无劣义也。夫人而自繇,固不必须以为恶,即欲为善,亦须自繇。其字义训,本为最宽。自繇者凡所欲为,理无不可,此如有人独居世外,其自繇界域,岂有限制?为善为恶,一切皆自本身起义,谁复禁之?但自入群而后,我自繇者人亦自繇,使无限制约束,便入强权世界,而相冲突。故曰人得自繇,而必以他人之自繇为界,此则《大学》挈矩之道,君子所恃以平天下者矣。③ 从原本以“自由”作为救国救民之道,到八年后完全以“不为外物拘牵……无胜义也无劣义”的“自繇”来置换之,此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虽然严复也曾借助训诂及其古义来加以说明,但他同时又申明“不作自由者,非以为古也”④。这说明,其之所以要将“自由”置换为“自繇”,并不是出于文字训诂或出现早晚的原因,而主要在于其作为一种思想主张所起的作用上。再从其“我自繇者人亦自繇,使无限制约束,便入强权世界,而相冲突”一点来看,则其所谓“自繇”显然又是针对那种一味追求自我之“自由”从而“无限制约束”所导致的“强权”恶果而言的。所以,这种作为“群己权界”的“自繇”,实际上正是对原来那种“自由”主张的一种明确修正。 除此之外,严复又对“自繇”作了多处说明,而从这些说明中,我们也不难窥见其从“自由”转换为“自繇”的真正原因: 学者必明乎己与群之权界,而后自繇之说乃可用耳。⑤ 禽兽下生,驱于形气,一切不由自主,而皆束缚。独人道介于天物之间,有自繇亦有束缚。治化天演,程度愈高,其所得以自繇自主之事愈众。由此可知自繇之乐,惟自治力大者为能享之。⑥ 贵族之治,则民对贵族而争自繇。专制之治,则民对君上而争自繇,乃至立宪、民主,其所对而争自繇者,非贵族非君上。贵族君上,于此之时,同束于法制之中,固无从以肆虐。⑦ 须知言论自繇,只是平实地说实话求真理,一不为古人所欺,不为权势所屈而已,使理真事实,虽出之仇敌,不可废也;使理谬事诬,虽以君父,不可从也,此之谓自繇。⑧ 总之自繇云者,乃自繇于为善,非自繇于为恶。特争自繇界域之时,必谓为恶亦可自繇,其自繇分量,乃可圆足。必善恶由我主张,而后为善有其可赏,为恶有其可诛。⑨ 在上述关于“自繇”的申论中,其第一条主要在于强调“自繇”的人伦相关性,所以说是“明乎己与群之权界,而后自繇之说乃可用耳”。也就是说,所谓“自繇”必须是以不妨害他人的“自繇”为自己“自繇”之前提与界限的。第二条则主要在于强调“自繇”的历史与历时性质,这也证明其“自繇”不仅是现实的“自繇”,而且也首先是“自治”基础上的具体“自繇”,所以才认为“惟自治力大者为能享之”。第三条则在于突出“自繇”的全民性、制度性与非阶级专有属性,因为即使是“贵族君上”,也不能突破“自繇”的制度框架以肆虐;当然反过来,作为“贵族君上”,同时也必然享有“自繇”制度的保护。这正是“自繇”之全民性与制度性的典型表现。至于第四条,则主要在于说明“自繇”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它保护每一个体“说实话求真理”的基本权利——既不为君父所牵,也不为仇敌所移。第五条则在于说明“自繇”必须自己对自己负责,是即所谓“善恶由我主张,而后为善有其可赏,为恶有其可诛”。也就是说,作为一种权利,“自繇”同时也必然肩负其相应的责任。 由以上申论可以清楚地看出,与原来的“自由”相比,“自繇”明显地中性化、制度化了,而不再带有理想与价值的色彩。与八年前的《原强》相比,“自繇”也不再是一个理想与价值载体,而只是一种中性化的并且可以确保人们拥有“为善”甚至“为恶”——所谓自我抉择、自我负责之权利的基本制度,当然同时也确保人们“为善”与“为恶”以及“可赏”与“可诛”之不同回报。除此之外,与八年前那种“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之理想性的描述相比,“自繇”也更明确地具体化了。 对于严复从“自由”到“自繇”的这一转变,以往的研究往往是从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及其软弱性来说明的,意即严复是在明确地向封建地主阶级妥协,从而丧失了资产阶级所应有的革命性。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种评价有其正确的一面,因为随着严复对“自繇”之中性制度化色彩的突出与强调,它也就更进一步接近西方“自由”的本质了;而其思想内容的具体化,同时又表现出了一种更为明确地向中国传统文化回归的趋向,从而也就预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自繇”出路。 二、为仁由己:自由的精神支撑 在20世纪的中国思想界,人们往往只知道严复论“自由”,但却几乎不知道其关于“自繇”的论说。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在于人们的自觉选择与自然淘汰。因为当“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之理想性的制度还是人们的主要期盼时,人们就会自觉不自觉地为未来的“自繇”制度附加以理想与价值的色彩。而严复作为第一个引进“自由”观念的传统士人,其对国人的负责精神以及其对“自繇”的深入探讨也使他不得不抹去原来附加于“自由”之上的理想与价值色彩。这种情形,就使20世纪的中国精英宁愿接受其早年并不成熟的“自由”观念,却始终不愿意正视其以后较为成熟的“自繇”论说。 从思想发展的角度看,“自繇”的价值无疑更高,因为它不仅更接近“自由”的本质,而且其“群己权界”的规定也说明它本身就是一种有责任的权利。20世纪的中国思想界之所以选择“自由”而自觉地忘记“自繇”,一方面说明作为制度的“自繇”在中国还没有成为现实,同时也表现着中国思想界普遍的“左倾”与“浪漫化”趋势。但是,一当制度成为“自由”(本文接受约定俗成的时代观念,不再称“自繇”)的本质特征,而“自由”同时又成为一种有代价、有责任的权利时,对于作为制度与权利相统一的“自由”而言,它也就必然存在着一个思想基础与精神支撑的问题。因为即使是西方的自由制度,也仍然存在着一个“唯天生人,各具赋畀”的基础和依据,因而,要在中国建构保护自由的社会制度,也就必然需要一定的思想基础与精神支撑。 据陈静女士所考,汉语中的“自由”最早出现于东汉郑玄的《礼记注》与赵岐的《孟子注》中,并且也都具有“自我做主”的涵义。陈静还考察了“自繇”的最初运用,认为“自由”实际上是比“自繇”出现得更早的概念,从而纠正了严复以为“自繇”比“自由”更为古老的说法。⑩从中国传统文化之概念运用的角度看,无论是“自由”还是“自繇”,实际上都属于较为生僻的概念,这显然与国人之制度意识、权利意识的形成以及对其自觉之晚到有关。但是,如果就作为东方人伦文明之奠基及其做人精神之自觉而言,则国人的这种自觉很早就发生了。而这种本质上作为人伦文明之基础的做人精神,其实也完全可以成为自由制度及其权利、责任意识的基础与支撑。 在这方面,西方文化的对象理性特色及其工商业与市民社会的一并崛起对其权利意识的自觉无疑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而中国的农业文明及其两千多年的重农抑商政策却始终在压抑着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这就是东西方文化在性格趋向上的差别以及其在促进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方面所起到的不同作用,从而也就形成了中西方社会的现实差距。但是,如果我们转向人伦文明本身,则中国人在这方面的自觉却要远远早于西方;而国人关于做人精神之自觉则无疑代表着一种究竟应当如何做人之最基本的权利意识。如孔子就有如下明确的断言: 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 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其志也。(《论语·子罕》) 在如何做人的问题上,芸芸大众究竟有没有一种既不可剥夺也不可让渡的基本权利呢?在孔子看来,只要是人,只要拥有人的主体精神,也就必然会拥有这种不可剥夺的权利。如果说自由首先表现在关于如何做人问题上之一种最基本的抉择权,那么中国人的权利意识也就主要表现在这一点上。(11)对于如何做人这种既不可剥夺也不可让渡的权利,孟子又作了如下范例性的说明: 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孟子·尽心上》) 这究竟算不算一种权利?是否包含主体在关于如何做人问题上的一种最基本的选择权呢?笔者以为,可能没有人能够否定这一点。当然,人们可能会说这只是道德方向上的一种向善追求,但对儒家来说,虽然如何做人是每一个体的基本权利,但道德却并不能决定人就会必然向善,比如,告子在与孟子关于人性之辩中所例举并为孟子所认可的“以尧为君而有象;以瞽瞍为父而有舜;以纣为兄之子,且以为君,而有微子启、王子比干”(《孟子·告子上》)上。这种现象说明,在如何做人的问题上,儒家很早就自觉到个体确实具有一种既不可剥夺也不可让渡的基本抉择权。由于这种权利是远远大于道德向善规定的,因而它确实是一种超越于道德而又遍在于每一个体的做人抉择权。 不仅如此,如果说如何做人仅仅是一种个体的“私德”(其实并不完全是私德,甚至也不完全是“德”)问题,那么儒家的做人抉择权实际上并不局限于“私德”领域,而是面向整个社会及人生之各个方面全面敞开的。对于儒家的做人抉择权来说,根本就不存在所谓“公”与“私”的问题,一个立体的人,本身就是贯通“公”、“私”两大领域的。请看儒家的“私人”或“私德”是如何向公共领域贯通的: 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 在这里,虽然孔子明确主张“庶人不议”,但其所谓“不议”却存在着一个非常明确的“天下有道”的前提;在国君及其私人爱好所导致的“天下无道”的情况下,则庶人之“议”也就必然会像其做人之抉择权一样,成为一种不可剥夺的社会权利。很明显,从国君的私人爱好到庶人之“议”,绝不仅仅是一个私人的问题,而是同时关涉天下“有道”与“无道”的大问题。 实际上,这种由“天下无道”所导致的庶人之“议”并不是孔子或儒家的发明,而首先是中华民族所共同认可的一种历史教训,也是由夏商周三代以来的历史教训积淀而成的传统。夏代那个“不务德而武伤百姓”(《史记·夏本纪》)的统治者桀就曾遭到诸侯的叛逃,最后在商汤的讨伐下死于鸣条。商代那个“知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史记·殷本纪》)的统治者纣可以说就是这种庶人之“议”传统的反向推动者。因为他虽然借助其专制权力囚禁了箕子,并对比干施以剖心之刑,以震慑民众,但民众最后却以出逃与临阵倒戈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议”。到了周代,周厉王虽然“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并一度使“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史记·周本纪》),但正是这种“道路以目”式的“议”,最后却使周厉王不得不成为逃亡之君。从这个角度看,孔子所谓的“庶人不议”实际上也就是以“不议”的方式明确地提出了“天下有道”的方向;而在“天下无道”的情况下,也就等于肯定了民众之天然的议政权。从删诗书、定礼乐一直到著《春秋》,实际上都可以说是孔子为了达到“天下有道”的“议政”之作。正因为这一原因,所以孟子评价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至于孟子的自我定位则是“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孟子·滕文公下》)。所以,对于《春秋》之“议”,司马迁也借董仲舒的话评价说:“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史记·太史公自序》显然,所谓“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实际上正是孔子立足于“天下有道”的标准而对当时政治的议论与批评之举;而作为其绝笔的《春秋》,自然也就可以说是孔子的议政或政治批评之作。 这种从个体之自我抉择、自我负责的做人抉择权到对“天下无道”之议论与批评,在儒家看来,都属于从“天下无道”达到“天下有道”的努力。而在近代以来“自由”与“权利”追求的背景下,它实际上也就成为一种“天赋”的“人权”,问题只是在于如何能够使其制度化、常态化。 三、老安少怀:儒家的“主义”追求 孔子生活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其一生的努力主要集中在“克己复礼”与变“天下无道”为“天下有道”上。当时固然没有今天随着人之全面发展所必然关涉的自由平等权利方面的话语氛围,但由于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立场以及其对人之生命的关爱与尊重,其在关于人的合礼性生存与人伦文明之合理性发展的探讨中,也就必然关涉到人的生命趋向以及人类社会之合理性发展的问题。在这些方面,也就必然存在着和现代文明的接榫之处;而这种接榫,不仅构成了儒家的自由“遗产”,同时也表现着其对自由的“主义”追求。 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自由主义的探讨中,“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是一个热门话题,而能否准确理解“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涵义及其关系似乎也成为是否理解自由主义的一个理论标准。尤为中国自由主义者所关注的是,以前国人所接受的大多是“积极自由”,而“积极自由”往往会成为“暴政”、“暴力”甚或“过多干预”的策源地,而只有“消极自由”才更接近自由主义的内核与本质,因为只有“消极自由”才能有效地防范“积极自由”所带来的各种弊病。这当然都体现着自由主义学理探讨的深入,也是其逐渐接近历史实际的表现。 不过,如果我们不拘泥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也不拘泥于随之而来的主体性体认与对象性认知的不同侧重,那么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其实我们的文化传统曾以做人之基本原则与基本精神的方式同样蕴涵着这些作为自由主义探讨的前沿问题,包括严复后来专门以“自繇”来置换“自由”以及其“善恶由我主张”之类的说法,本身也都具有突出“群己权界”之“消极自由”方面的涵义。再比如《论语》载: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 我不欲人加诸我,我亦无欲加诸人。(《论语·公冶长》) 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然可以说是一种积极的自由,也是人之内在德性“不容己”的表现,当然也可以说是“为人谋而不忠乎”的“尽忠”之道;至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对之进行具体诠释的“我不欲人加诸我,我亦无欲加诸人”,则又可以说是一种“推己及人”的“恕”道,同时也是对他人之消极自由的尊重。再比如前边所征引的“为仁由己”以及“以尧为君而有象;以瞽瞍为父而有舜;以纣为兄之子,且以为君,而有微子启、王子比干”等,如果对应于自由主义的学理探讨,那么这无疑又是一种消极自由,是消极自由在“己”与瞽瞍、象以及微子启、王子比干在具体做人中自我抉择的表现。所以朱熹就曾以“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12)来解释儒家的“忠恕之道”。 当儒家以“忠”与“恕”来表达其做人精神之积极与消极两面时,其实不仅蕴涵着人与人的关系,而且也蕴涵着一种人伦文明与社会关系的模型。所以,当孔子被问及人生志向时,他就明确地以“老安”、“少怀”来表达其人伦社会性关怀。实际上,其所谓的“天下有道”也就包含在这种“老安”、“少怀”的人伦关系中: 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 在孔子这一志向中,所谓“老者”、“朋友”与“少者”看起来似乎仅仅是围绕主体所展开的一般性人伦关系,但由于“老者”、“少者”与“朋友”又分属于不同的年龄阶段与不同的人际关系,因而其所展开的实际上也就是一种立体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既包括血缘,又不限于血缘,而是可以通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的方式将整个社会连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在这种社会中,固然也存在血缘关系,但又不仅仅是血缘;而所谓的“安”、“信”与“怀”也就使整个社会成为一个有距离、层次然而又能够互敬互爱的整体。所以,孟子在其“以及人之幼”的后边接着补充说“天下可运于掌”:至于孔子的“天下有道”,其实也就是这样实现的。 正因为儒家的做人精神并不局限于个体道德基础上的“独善其身”,因而它也必然包含着一种家国情怀——人伦社会关怀,而在先秦儒学的重要文献《大学》中,儒家就依据其做人精神,构建了一个包括家国天下在内之张弛有度的社会。 在以往的研究中,由于受20世纪疑古思潮的影响,人们往往倾向于将《大学》视为秦汉儒家的作品,其实这是一种很大的误解。因为在秦汉大一统的专制政权形成后,儒家就从根本上失去了建构理想社会的话语权,包括具体的言说环境。不仅在“焚书坑儒”且“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秦王朝,儒家没有这种话语权,即使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武帝时代,建构理想社会的话语权也不属于儒家。董仲舒就是因为想通过天人关系来限制恶性膨胀的君权,结果差点丢掉了性命;而其弟子眭孟也因为劝告汉昭帝要效法尧舜以禅让帝位,结果被送上了断头台。 正因为这样一种社会背景,所以《大学》不可能出自秦汉儒家,而只能属于先秦儒家的作品,大概是先秦儒学对应于秦王朝的耕战国策以及建立在武力征伐基础上的统一之路而提出的依据道德理性所形成的统一之路,因而二者(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反差关系。(13)而《大学》的修齐治平之所以被视为儒家关于内圣外王之道的经典表达,也正是以其与秦汉帝国建立在武力征伐基础上的大一统专制政权之强烈反差为前提的。所以,《大学》的倾诉对象并不仅仅是一般儒者,而首先是人间的诸侯王权,这一思想正体现在作为其开篇的三纲领中:“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礼记·大学》)而所谓的三纲领也首先是针对未来的天子而言的;至于其依据三纲领所规定的“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同上),也就只能针对还没有形成或正在形成中的诸侯王权而言,而绝不可能向已经成为人间主宰的天子提出这样的要求。《大学》立足于天子之“明明德”、“亲民”以及庶民百姓之诚意(统领格物致知)、修身(统领齐家),然后通过天子“止于至善”的政策以平治天下,这就是其基本思路。 这说明,关于人伦文明,儒家不仅有其基本的做人精神,同时也有其社会性与制度性关怀;而从做人之基本抉择权到人伦文明之社会性关怀,也都可以构成一整套的自由权利及其关系论说。但由于秦汉以后的帝王专制制度以及其儒表法里的国策,儒家的自由精神及其制度性关怀根本无从提出,这就造成了严复所谓的“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的表象。实际上,儒家的自由精神及其制度性关怀虽然一直受到专制政权的打压,但在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它却仍然顽强地以“天理”与“良知”的方式坚持着做人之自我抉择权(14),并以“乡约”、“家训”与“教规”的方式坚持着其社会性的制度关怀;至于所谓社群主义,则又完全可以说是儒家的人伦社会关系及其制度性关怀的一种典型表现。(15)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对儒家关于人生与道德的关系稍作辨析。在儒家关于人伦社会各种关系的论述中,道德理性与道德关系往往会成为其最重要或者说最根本的出发点,所以儒家的人伦关系似乎也就可以化约为一种单纯的道德关系,因而社会上也始终存在着各种专门针对儒家“泛道德论”的批评。实际上,这是一种很大的误解。儒家固然非常重视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但道德关系只是儒家对人生各种关系进行深入探讨的结论,而绝不是其第一出发点。否则,儒家就不可能承认也无法说明其所承认的“以尧为君而有象;以瞽瞍为父而有舜;以纣为兄之子,且以为君,而有微子启、王子比干”这样的现象,孔子也就不会形成“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这样的感喟了。这说明,对现实人生的关注始终是儒家的第一出发点,所以它就能够看到并且也承认人生中确实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非道德选择;但对儒家而言,其对人生各种关系进行穷根究底性探索的最高结论,则认为只有道德才代表着人之生命的最高本质,也只有道德追求才代表着人生价值的最高实现。因此,在儒家看来,只有在道德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建立起更为合理的人伦关系;也只有在道德理性的基础上,才能有效地实现人的最高本质包括最大的利益。(16)儒家关于人伦社会的建构及其各种权利的实现,本质上也都是一种道德基础上的实现,因而无论是其关于自由的追求还是关于制度的建构,也都必然是一种道德基础上的“自由”与“主义”追求。 四、启蒙裂变下的困境及其出路 在20世纪以自由为核心的启蒙思潮中,始终存在着一种相互补充而又相互支撑的双向前提:一方面,所谓“自由”必然要以西方先进的社会制度与文明作为其文化背景;另一方面,自由观念从思想价值到制度建构两个层面都为中国文化所缺乏。正是这两个基本前提,才使自由观念在中国成为一种世纪性启蒙;但也正是这两个相互支撑的前提,又为西方自由观念在中国的落地生根制造了其所无法走出的困境。原因在于,以自由观念为核心的启蒙思潮发生于中西文化交汇的近代,其直接导因是近代以来西方对中国的侵略;至于其背景性的原因,则又在于自由观念所体现的西方文化及其在文明发展方面的进步优势。这一点在严复引进“自由”观念并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时就已经非常清楚了。也就是说,自由观念之所以能担负起对中国文化进行启蒙的任务,主要是因为其所体现的西方文化在社会进步与文明发展方面的先进性,而这种先进性不仅为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所证实,同时也为以后中西文化交流中西方文明的先进性所证实。 但在20世纪的启蒙思潮中,无论是向中国传播自由观念的西方人还是自觉向西方学习的中国知识分子,都自觉不自觉地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一种因遮蔽而来的简单否定倾向,要么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由资源视而不见,要么就一言以蔽之式地称其为前现代文明。(17)总之,在他们看来,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对自由观念的匮乏,才亟待来自西方文化的启蒙;而西方文明的先进性也使其具有对中国文化进行启蒙的必要与可能。启蒙思潮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看法?在20世纪关于中西文化的讨论中,一元化的线性历史观以及扎根于线性历史的文化观念几乎成为一种时代潮流,当时所有的文化问题都从线性历史——历史进步与文明发展的角度进行评价。由于中国近代极度屈辱的被侵略经历而又回天乏术,其文化也就被视为前现代文明,在这一背景下,接受先进的西方文化之启蒙也就具有了一种历史的必然性。实际上,这种扎根于一元化之线性历史的文化观念及其价值标准完全是以文化之暂时与部分的表现来衡量整个文化。用儒学批评佛教的话来说,这其实就是一种“作用是性”——以一时表现或一个方面的成败论英雄。因为从实质上看,文化主要体现着人伦文明的全面发展,以文化的部分成果或一时成效作为衡量整个文化的标准,谁都可以看出其中的片面与偏颇。 与此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另一种遮蔽主要表现在启蒙思潮对中国传统道德的负面评价上。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是一个没有宗教的民族,但人伦文明与民族精神的全面发展却使其不可能没有信仰。那么,中华民族究竟有没有信仰?其信仰又如何表现呢?这就主要表现在中国的传统道德上。这种作为人生信仰的道德其实并不是从一定时代之人伦关系所引申出来的伦理规范,而是中华民族通过对人生穷根究底性探索所形成的关于人生最高本质的认知。因此,对于中国的传统道德尤其是儒家道德来说,它不仅包含着人生信仰的内容,而且也具有一定的宗教性蕴涵。正因为这一原因,中国的古圣先贤,无论是对人生本质还是对人生价值实现的探讨,无一不是从道德的角度进行规定的。这样一来,中国的传统道德就不仅仅是从那种所谓时代性出发所形成的带有暂时和相对色彩的人伦规范,而是代表着人之生命的恒常本质与人生的最高追求。但在20世纪的启蒙思潮中,传统道德往往被冠以丑陋的恶名,诸如封建道德、伪道学,等等,这就不仅封闭了传统的道德资源,而且还专门以唾弃道德的方式来表现对社会进步的追求。严复之所以要将“自由”置换为“自繇”,并明确以“放诞、恣睢、无忌惮之劣义”来规定“自繇”,实际上正是因为他已经清楚地看到了所谓“自由”对道德的冲击,从而试图以所谓“放诞、恣睢、无忌惮之劣义”来纠偏于那种由一味追求自由所导致的道德缺失或道德滑坡现象。对于一直以道德为信仰的中国人而言,道德的缺失也就意味着人生信仰的缺失,从而也就意味着生命之根的流荡失守。一当社会进步与道德信仰完全成为一种反比关系时,这样的社会进步又将意味着什么呢? 对20世纪的启蒙思潮来说,正是这两个方面的相互支撑,造成了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征服姿态与观念上的取代关系;而这两个方面的相互强化,也就造成了20世纪一浪高过一浪的反传统运动,并以彻底的反传统来表现自己的进步追求。而这种完全以反传统——文化上之自我否定方式所表现出来的社会进步追求,同时也就为启蒙思潮制造一个顽强的对立面,从20世纪初年的义和拳运动到21世纪的民粹思潮,一定程度上都是对启蒙思潮征服姿态的一种反弹,也是在启蒙思潮的强大压力下形成的。(18) 为什么启蒙思潮会为自己制造这样一个对立面?这完全是由启蒙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鄙薄心态及其居高临下的“启蒙”姿态决定的。当启蒙思潮完全无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而一概将其归之于前现代文明时,传统文化非但不能参与中国的现代化追求,反而只能成为一种“历史包袱”,这就不仅遮蔽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而且也封闭了其现代化出路,从而只能将其推向“垃圾堆”一边。启蒙思潮的这种态势,就使其引导下的现代化追求完全成为一种缺乏传统依据与民族精神的照搬运动;而对于中华民族的主体精神来说,则又成为一种完全从自我之当下感受出发的白手起家运动。一当这样的现代化追求面临主体性或民族性反思,马上就会形成一种一概排外而又根本缺乏文化底气的“激愤”主体或“血性”主体。从20世纪初年一概排外的义和拳运动到21世纪正在形成的不仅排外而且仇官、仇富的民粹思潮,也就成为在封闭并唾弃了文化继承权之后中国社会下层的一种自然而又无奈的选择了。 但这两种截然对立的思潮,却又存在一个共同的前提,这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鄙薄与唾弃。启蒙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鄙薄使其根本找不到落地生根的土壤,从而也就只能始终停留在一种观念化的“狂飙”状态(19);而民粹思潮对传统文化的唾弃则又只能使自身成为一种缺乏文化底气与精神依据从而极度短视而又“暴戾”的“激情”主体。至于这两种思潮的对垒与恶性缠斗,既是中国思想界的现状,也是中国现代化追求中的恶性病灶。 面对这样一种现状,中国传统文化负有极为重要的责任。中国传统文化首先绝不应当成为民族现代化追求的旁观者,而应当是其真正的精神主体,因而它也不可能完全无视民族的现代化追求而退缩于古典研究一隅(就像当年面临佛教的冲击那样),而是必须以其真正的主体精神积极参与民族的现代化事业。这就必须加强对传统文化的现代诠释并强化其与西方文化的对话与沟通功能,从而尽快改变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现代化追求中传统文化全面缺位的负面形象。当然在这一过程中,首先需要改变的是启蒙思潮那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当启蒙思潮能够正视中国传统文化的正面价值时,就会改变自己一个多世纪以来摧枯拉朽式的“狂飙”状态,从而真正显现出其能够落地生根的正面价值。与此同时,传统文化的另一重任就在于改变民粹思潮那种一无凭藉的“激愤”主体与“暴戾”心态,从而使其从完全情绪化的“激情”主体转换到真正的文化与民族精神上来。一当民粹思潮能够扎根于传统文化,不仅会改变自己一无凭藉、一任“激情”的状态,而且也会积极探索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出路。 这就是一个多世纪以来启蒙思潮裂变下中国思想界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同时也应当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在启蒙背景下双遣双取、双向扬弃的现代化出路。 注释: ①严复:《论世变之亟》,《严复集》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3页。 ②严复:《原强》,《严复集》第一册,第11页。 ③④严复:《〈群己权界论〉译凡例》,《严复集》第一册,第132、133页。 ⑤严复:《译〈群己权界论〉自序》,《严复集》第一册,第132页。 ⑥⑦⑧⑨严复:《〈群己权界论〉译凡例》,《严复集》第一册,第133、133、134、134-135页。 ⑩陈静:《自由的含义:中文背景下的古今差别》,《哲学研究》2012年第11期。 (11)美国的中国文化专家狄百瑞在其《中国的自由传统》一书中指出:“孔子努力于保存传统文化的菁华,并肯定人类文化的永恒价值。在这层意义下,他可以说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但是,因为孔子认为过去的理想与典范可作为批判当代制度的基础也足以提醒人所秉承于天的伟大天赋,所以孔子同时也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又说:“在传统的思想方式中,个人的自主性或‘顺性’这类观念实不陌生。而且在选择用‘自由’这类名词翻译19世纪西方‘自由主义’观念的时候就蕴涵着某些新儒家的思想倾向。”(狄百瑞:《中国的自由传统》,贵阳:贵州出版集团公司,2009年。第9、56页) (12)朱熹:《四书集注》,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97页。 (13)关于《大学》出于先秦儒者而非出于秦汉儒生的原因,请参阅丁为祥:《〈大学〉今古本辨正》,《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 (14)关于儒家的自由主义精神及其与“天理”、“良知”的关系,请参阅狄百瑞:《中国的自由传统》,第19-91页。 (15)关于儒家人伦关怀中的社群主义特色,请参阅杜维明:《儒家与自由主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该书以对话的方式对儒家的社群关怀进行了非常细致的讨论。 (16)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孟子·尽心上》)此即认为只有圣人的德性,才可以使人的自然之性充其极,得到最完美的发展和运用。 (17)狄百瑞指出:“在中国人近代的经验中很不幸地失去了这种直觉的本性,在现代化过程中也暂时失去了他们的自尊,放弃将新的经验与固有的传统消化溶解。将所有的价值都看作是从西方来的,或将所有的价值都以将来为目标,而不扎根于他们的过去,这种态度使近年来的中国人无法从他们的本性中找到‘道’的真理,这种脱离自己根源的结果与它强烈的影响,在‘文化大革命’中尤为明显。”(狄百瑞:《中国的自由传统》,第146页) (18)20世纪中国的启蒙思潮与民粹思潮之所以成为一种孪生关系,首先是由于启蒙思潮的高调征服姿态造成的。因为在启蒙思潮的征服姿态下,不仅中国传统文化成为“封资修”与“垃圾堆”,而且也必然会得出中国今日之“一切不是是”的结论,这就必然会否定国人生存的现实合理性,从而又恰恰成为民粹思潮崛起及其激情与激愤主体的根源。 (19)狄百瑞在批评中国20世纪的自由主义思潮时指出:“如果认为自由主义唯有存在于过去的西方,认为是舶来品,不能与中国的生活及文化方式融合的话,那么这也可能因此反而破坏了让它从自己的根本自然地滋长的机会,更也破坏了今日世界,和平生存而必然要接受的文化交流。”(狄百瑞:《中国的自由传统》,第145页)标签:儒家论文; 国学论文; 孟子思想论文; 孟子·尽心上论文; 华夏文明论文; 理想社会论文; 孟子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大学论文; 孔子论文; 读书论文; 有道论文; 严复论文;
